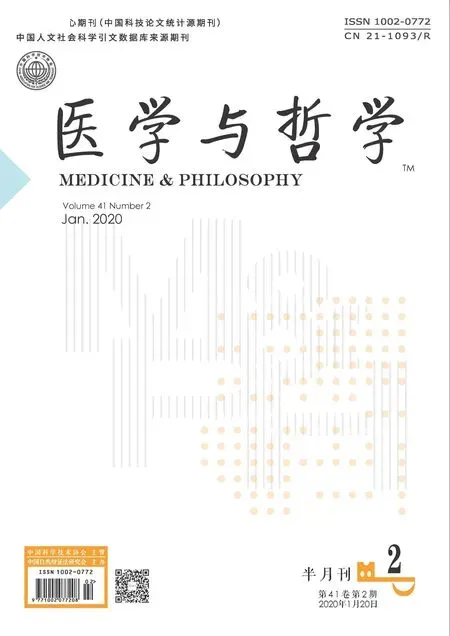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在重症医学科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2020-02-16王莎莎
周 军 王莎莎 孙 璇
不断改进的机器、技术、新药和侵入性干预措施是重症医学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特点[1],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2]的今天,医疗技术的提高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对部分患者来说也许是一种痛苦的延长,特别是在ICU许多终末期患者仅靠先进医疗设备来维持仅有的生命体征,但最终仍逃不过死亡的现实,不仅增加了患者痛苦,还给家属带来了一定负担。这一现象由多种原因引起,与患者及家属的价值观和死亡态度联系最为紧密。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在国内是一个较新的名词,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患者的治疗意愿和价值观,当这种意愿能付诸实践时就会减少过度治疗的现象,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
1 ACP相关概念
ACP是一个反思、讨论和沟通的过程,是在患者有决策行为能力的时候为自己未来的医疗意愿进行决策,阐明关于维持生命治疗和结束生命治疗的护理偏好,并确定医疗决策代理人,从而保证患者自主决定权和知情同意权,体现患者自身的生命价值观[3]。
预先指示(advance directives,AD)是在ACP形成的基础上将患者的意愿和偏好形成的一份完整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应的书面文件[4]。由于在概念上没有进行明确定义,有学者也将AD称为生前遗嘱或医疗授权委托书。
2 ACP国内外应用现状
2.1 ACP国外应用现状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受人口老龄化[5]和医疗资源的压力以及不同思想文化的影响,ACP广为接受,随着法律文件的诞生,ACP得到了进一步快速发展,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家ACP发展已经比较成熟[6]。在德国一项单中心横断面研究中调查了998名ICU患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有521名患者已经完成ACP文件,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患者将接受ACP,且2007年~2014年ACP在ICU的使用率逐年增加[1];美国是率先通过立法来保障ACP开展的国家,美国ICU医疗资源压力较大以及财政负担占比高,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美国ICU护理成本占美国医疗成本的13.4%,占国家卫生支出的4.1%[7],所以ACP在美国不断得到推进,相关法律文件也在不断完善,同时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宣布,将为讨论ACP提供补偿[8],2000年~2010年,美国死亡患者中有AD的比例从47%上升到72%[9];2014年,在挪威所有的疗养院中进行一项关于ACP实施情况调查研究,有57%的护理人员接受了调查,结果表明其中2/3的人在疗养院进行ACP,1/3的人已经有了书面的AD[10]。亚洲国家由于受不同文化影响,人们对医疗决定的认识不同,AD发展较慢,西方国家注重患者自我决定,强调独立自主,而亚洲国家倾向于家庭决策,2016年韩国一项研究表明,随着人们对生存质量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医疗自主权的意愿逐渐强烈,许多人表示赞同ACP的推进[11],包括日本也一样,在ACP推进的过程中和韩国一样没有美国、德国发展的迅速,在立法保障上也较缺乏,自2016年以来,日本医学会一直鼓励初级保健医师组织推广包括ACP在内的培训方案,并于2018年3月发布了一份向日本公民介绍ACP的文件[12]。通过研究不难看出,在ACP上东西方有一定差距。
2.2 ACP国内应用现状
在我国一项全国多中心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只有38.3%的人听说过ACP[13],人们对ACP的知晓度仍然较低,ACP的概念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在中国,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谈论死亡和生命终结的相关决定,因为这是一个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禁忌话题。但是在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ACP发展较快,“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颁布[14]以及老年群体合适文化的ACP策略探讨,推动了ACP的发展,2013年台湾地区提出只要有1名关系最亲近的家属见证即可完成ACP[15]。在我国香港虽然ACP长期以非立法的形式存在[16],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在ACP临床应用上我国主要在肿瘤科开展较多,其次是老年病科,有少数学者研究痴呆患者及儿童终末期患者,在ICU目前研究寥寥无几,纵观西方国家的研究发现,ICU的ACP应用价值较大,值得进行研究。
3 ICU推行ACP的价值意义
3.1 减轻患者和家属心理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在我国目前的医疗发展下,各大医院的ICU成了许多终末期患者度过临终生命的场所,特别是一些限制性生命疾病患者反复进出ICU,家属只能在外面慢慢等候不能陪伴,不仅增加了患者和家属的心理压力[17],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由于ICU医疗技术和设备先进、24小时医护照看,医疗费用较普通病房要贵,对于一些限制性生命疾病患者家庭往往最后人财两空。ACP可以根据患者和家属的意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入住ICU的次数和ICU住院时间[18],减轻一定的家庭经济负担[19]和家属人文负担。
3.2 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降低患者痛苦
先进设备、先进技术、灯火通明成了ICU的代名词,许多ICU住院患者出院后对ICU产生了恐惧感,感觉自己被医疗仪器所包围,没有白天和黑夜,产生了心理创伤[20],一些ICU的过度治疗可能违背了患者的治疗意愿,仅仅依靠先进医疗设备来维持仅有的生命体征对医院来说是一种医疗资源的过度使用,特别是许多侵入性操作增加了患者痛苦。ACP有利于患者自身治疗意愿的表达,不进行过多延长生命的侵入操作及治疗,对患者来说可以减轻痛苦[7],对医疗来说可以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和减少浪费。
3.3 减少决策冲突的发生
在国外一项研究显示,当ICU住院患者没有AD,发生紧急情况需要抢救的时候家属间的决策往往会产生冲突,这会使得家属心理产生悔感,因为在事先不了解患者治疗意愿时家属处于治疗不足和治疗过度的矛盾心理,这种决策冲突引起的心理压力迟迟不易消去[21]。在国外往往通过AD或者决策代理人来解决这件事,在国内由于文化差异,ACP一般以家庭为中心并结合患者自身意愿进行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减少了家庭决策冲突[22]。
3.4 降低ICU的医疗成本
美国一项研究统计发现,2005年急救护理成本估计为820亿美元,占住院医院成本的13%,医疗资源大部分用于危重患者的护理[18],而且其中一部分医疗成本花在了死亡患者身上,为了缓解这一资源压力美国极力推行ACP的发展,首先在立法上进行保障,这也是美国ACP发展迅速的一个原因。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限制性生命疾病患者增加,给ICU带来了挑战,ICU患者病情重变化较快,如果没有ACP就会使得治疗过度从而增加医疗成本。
3.5 促进安宁疗护的发展
ACP是安宁疗护的一个部分,是安宁疗护发展的前提准备,在ICU推进ACP的实施是对国家安宁疗护的积极响应,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安宁疗护的发展,2017年,国家卫健委发文明确要求要规范安宁疗护服务,使患者能够优逝[23]。ACP的开展有利于推动安宁疗护的发展。
4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ACP的影响
4.1 文化影响生死观
西方国家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不断进行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思想解放运动对他们的生死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权至高无上。同时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生死观、生命价值观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督教思想认为人的生命来源于上帝创造与恩赐[24],生命是神圣的,是自由的,人是上帝的代表,应该独立自由的存在,上帝的意志才是最终极的价值标准,对生命的保存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死亡是与上帝的合一,死亡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更美的复活[25],死亡不是令人害怕的仇敌,而是人脱离尘世的希望,死亡是由上帝决定的,人为地延长生命可能违背上帝的意愿。因此,在既有的思想基础加上宗教文化的影响,西方国家对待生死是坦然的态度,生而自由,死不畏惧。这种生死观念恰好与ACP思想一致,因此ACP被西方国家广为接受。
在我国受传统文化影响,人们总体上是一种内敛、保守的观念。传统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人们总是“乐生”而“恶死”,民众普遍追求阳寿,渴望寿命的延续[26],再加上受民间鬼魂文化影响,逃避死亡,恐惧死亡,认为死是不吉利的,在社会生活中, 人们都极力回避与死亡相关的话题, 甚至对“死亡”一词予以回避[27]。久而久之形成了生而不言死的观念。孝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主流,但是在面对死亡观、疾病观时却存在过激的判定,即当父母生病时子女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如果选择放弃治疗就会背上不孝的骂名,会遭受舆论的谴责,因此各大医院过度治疗的情况比比皆是,医疗压力巨大。当然这种对孝道的理解相对于目前的医学模式来说是过激的,但人们思想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ACP会随着人们生死观的转变逐渐被接受。
4.2 文化影响决策权
在西方文化中人人生而自由、人人享有自主权利,即使病情危重自己有权利知晓自己病情,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选择,这种知情权和自主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们也乐意决定自己的偏好,因此西方国家鼓励人们签订AD,人们也愿意接受ACP。我国受家文化影响,强调集体或家庭主义,家庭凝聚力高于个人偏好,人们倾向相信家庭成员的医疗决定,当然他们不认为这是对自由权的剥夺,而是看作是对自己关心的标志。因此大部分的医疗决策就会由家属来决定,同时在某些地方有隐瞒病情的习俗,但是这种隐瞒病情的习俗被人们接受为善意的谎言。由此可见文化的差异影响着医疗决策。
5 在ICU开展ACP的影响因素分析
5.1 文化因素
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人们对死亡有一定恐惧感,人们总是忌讳谈论死亡[28],认为谈论死亡是不吉祥的,在这种思想长期引导下人们对死亡缺乏正确的认识,当疾病来临威胁生命的时候缺乏应对能力,不知所措。同时在我国孝文化的背景下,不管疾病预后怎样家属总是竭尽全力治疗,如果不进行积极治疗会承受不孝之义,人们对孝道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延长生命的阶段,也未考虑患者真实意愿以及无畏的过度治疗会增加患者痛苦。
5.2 认知不足
由于ACP普及不够,许多患者及家属对ACP认识不足,没有真正理解ACP的价值意义,在他们理解中ACP等于放弃治疗,剥夺了患者生命希望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加上患者和家属对许多疾病缺乏认识,特别是对一些限制性生命疾病认识不足,认为只要治疗就有希望、所有的治疗都是有利的。此外由于医护人员未接受专业培训对ACP的理解不够深入[29],在向患者及家属解释的时候缺乏技巧,不能很好把握ACP开展的时机,导致ACP开展困难。
5.3 法律政策缺乏
缺乏法律政策保障,法律是支撑我们开展ACP的根本基石[30],目前我国ACP立法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同时ACP也未纳入医疗保险体系,这是影响ACP的重要因素。
5.4 ICU患者病情紧急危重
由于ICU比较特殊,患者病情重,病情变化快,对医生的专业技能要求较高,很多时候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在加上ICU许多患者入科时意识不清甚至昏迷,医疗意愿完全掌握在家属手里,这就对患者及家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医护人员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6 推行以家庭为中心,家属共同决策模式的ACP
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往往很少宣扬个人主义,大部分都是强调集体或家庭主义,这在我国医疗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31],当患者生病时家属被视为最信任的人、最了解的人,在ICU患者往往没有了自主决策的能力,此时家属所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因此在ICU实施家属共同决策模式[28]是很有意义的,家属共同决定模式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患者入科后医护人员要尽快与家属及患者建立信任关系,在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中要逐渐全面评估患者及家属,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患者及家属的死亡观、疾病观、家庭观[32],家属的情况收集可以在入院24小时内以简单会议进行,此次会议以倾听解答为主。其次,掌握基本情况后召开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要求护士参加[33],逐渐引入主题讲解ACP,循序渐进引导家属结合患者意愿进行选择,护士此时应倾听家属的想法,当家属模棱两可的时候适当将患者在病房的意愿传递给家属,并通过医务人员的角度进行诱导分析[34],此过程中讲解尽量通俗易懂让家属理解,如果家属还是不能决定时不要盲目强求决定,散会后留给家属一个时间段让其考虑好决定,最后家属决定后达成书面协议实施ACP方案。对于ICU入科就丧失决策行为能力的患者,此时医护人员要根据病情判断引导家属早做决定[34],此类患者生命有限,也许紧接的医疗操作就会增加患者痛苦,因此尽早实施ACP对患者对家属都是有益的。
7 结语
ACP目前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知识仍在探索,通过国外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ACP的价值意义深远,在我国是值得推行的,目前推行阶段有一定困难,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在国家层面需要立法来保障其合法性;医疗保险层面需要逐渐将ACP纳入医保范围;教育层次需要加大对国民的死亡教育以及ACP的教育;社会单位或者组织要大力宣传ACP知识;医疗单位要组织医护人员进行ACP专业知识培训,培养一批ACP专科医护人员;推行试点工作探索经验;个人层面我们要敢于接受新的知识,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在国内目前的研究中涉及ACP的文献数量有限,说明我们对ACP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多是关于肿瘤患者,并且多涉及现状分析,研究层次有待扩展,一些调查研究缺乏大数据支撑,在以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可以朝着这些方面进行深层次研究,为我国ACP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