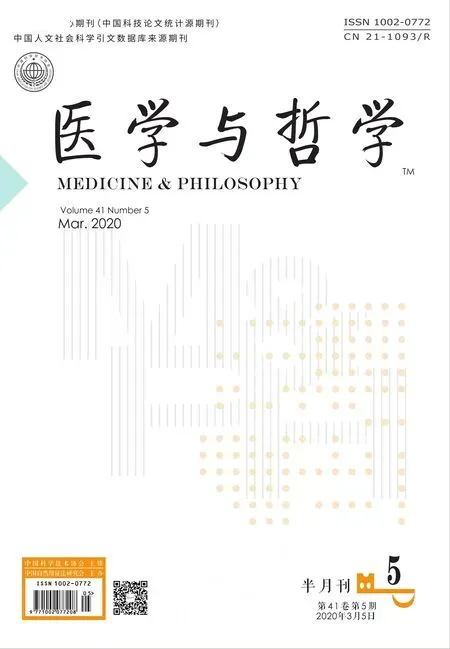让器物说话
——器物医学史:一种新的编史学视角
2020-02-16王一方
王一方 耿 铭
1 聚焦器物:编史视角的转换及其理论注脚
一部医学史,无论是学术史,还是思想史,除了刺眼的“强光带”之外,还存在着忽明忽暗的“弱光带”,聚焦器物的医学技术史(器物医学史、技术史)就处在这一光谱之中。背后是“耀眼”的精英叙事与“昏暗”的民间叙事之间的落差。因为器物的医学史常常被视为一种非理论化的历史研究现象(有人指责碎片化,有人指责随机化),需要从编史学上给予阐释,才能赋予这个范式以理论支撑。历史学家的对象物大多聚焦于文献与文物(远古器物),其背后存在着器物(级)与文物(级)之别,蕴含着一种历史年轮与价值权重的落差,以及厚古薄今的价值选择。毫无疑问,在正统医学史研究谱系中,首重文献(典籍、著作)、观念、人物,日常医疗、健康器物常常被遗忘,或者归于民俗研究,除非是历史久远的出土文物器具,近现代散落在民间的器物也太过平常,太过杂芜,它们不过是一些日常健保用品,就是些医疗技术物料,但它却隐藏着近现代医学技术演进的密钥,是观念的医学史、人物的医学史、事件的医学史之外的别样风景,也是现代医学察势观风的别样窗口[1],也就是说,倡导近现代器物为中心的医学史研究,可望成为主流医学史的必要补充。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有三个基本任务,发现与甄别史实,重新书写,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当然,史学还有更为闳阔的心愿与功用,在于捕捉一个时代的“风标”,那么,在技术史的层面,最易感知风向、风势、风力或许是器物、图像。譬如中国古代对马镫(器物)的发明与推广使得骑手在马上身体的稳定性提升,带来骑射征战能力质的提升,继而影响世界军事史,由此改写了历史的走向与格局。1958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南郊金盆岭一座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古墓中发掘出了一组青釉骑士俑(器物),其中一件骑士所骑的马身左侧鞍桥之下,塑出一个由革带吊系的小马镫,镫呈三角形,外貌简陋,革带也很短[2]。1961年,杨泓[3]撰文指出,该骑俑马镫,应该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知最早的马镫实例。据此,有美国学者称:“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镫,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4]同样,列文·虎克处理凸透镜的技能决定了人类对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的观察、探测潜力,开启了细胞生物学与微生物学及天文学(星空探测)的新领域。背后是历史学的理性与物性之辨,因为“历史不能简化为抽象的、预言性的描述(原理与法则,范式或模式),而舍弃掉所记录生活的特征细节……以及所有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存在着的有意义的碎片”[5]7。
无疑,器物医学史带来了历史叙事的变轨:基本路径是走出观念史,走向田野,沉入世俗。回归人-物的二元性,过去历史叙事常常重视人,而忽视器与物,立体的人物镜像应该是人与器物的交集、互相映衬。在历史的记忆深处,物比人长久,人因物而立,人去器物还独立存在的局面比比皆是,器物虽然不说话,但承载、凝集着人的历史遗存、风貌与风范。
在研究视野上,医疗、健康器物的解读呈现出医学史(明确的专业指向性)与文化史(泛化的/生活化的医学情境、语境)的交映,无疑,器物史的研究通往文化史的幽谷,吉尔伯特特别指出文化史研究具有四大特征,一是政治光谱(标识),二是跨学科眼光(杂合性),三是建构主义导向,四是历史境遇的分析意识(情境+语境)[5]478。器物史的拓展必然循着这四个阶梯推进医学科学史与技术史的交融,开启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对话,抵达医学文化史(文化史视域中的医学)的新边疆。
方法学拓展上,器物的加入融会了考据(文字)与考证(器物)的境遇,实现文献学方法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交映,有助于时代性格的白描与深描[6]。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指出“记忆是历史的原材料”[5]493,相对于观念史来说,具体的器物承载着更朴实的生命故事与生活记忆,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可望辟出一个创造性的解读空间(非宏大叙事,非辉格预设)。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所有的个人记忆都定位于社会情境中,而那些社会情境构造了它们被唤醒的道路……并最终被镌刻为“社会定式”(social stereotypes)[5]495。而那些被器物“唤醒的道路”,被镌刻的“社会定式”亦可以被理解为那个时代的健康与医疗的时尚风标。
2 器物医学史:近代新史学理念的启迪
1897年,梁启超首次撰文主张建设以民史为中心的“新史学”,但如何表现“民”的历史,没有具体的路径,人们不知从何下手。王国维[7]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二重证据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古文献+文物、器物)……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在这里,王国维所言地下之新材料,包括古(甲骨文、碑铭、简牍)文字、古器物(陶器、铜器)。但基本上是考古,历史久远,留存有限。近现代器物的留存就十分丰富了。1928年前后,顾颉刚为新创立的《中大语史所周刊》(1927年11月始刊)和《民俗周刊》(1928年3月始刊)写了两篇《发刊词》。在顾颉刚看来,要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学界开辟学术新路,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学术方向和范围、材料的状况和最新治学方法等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设新学问须打破学问的功利性,以求真为目标;须打破偶像的权威,以彰显理性。在此基础上,他呼吁“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中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8]这是顾颉刚到民间去求新史学的重要表述。其要旨是“眼光向下”,走出书斋,拓宽了搜集材料的路径与范围。认为“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主张通过田野调查或者考古,广泛搜集社会各个角落非文字的材料,诸如民间传说、歌谣、谜语、谚语、神话、童话、故事,以及被传统学术研究弃之不顾的档案、账本、契约、民俗物品等材料,来拓展研究的范围。其所谓“眼光向下”,一是单纯地依靠从故纸堆中寻找材料的纯文献研究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需求,他们重新估定文献的价值,开始走出书斋,眼光向下,实地搜罗材料,各种民间文献、实物、语言、图像和口述资料进入了史料的搜索范围。二是告别旧史学的“君史”,“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9]
中国近代的巨变,在器物、图像、技术层面上是最直接、最剧烈的。器物层面的变革,始终贯穿在近代中国医学史的脉络之中。虽然大多数技术精英不曾用文字记录器物的演进历程,但在他们的从业过程中,仍然会被动地留下一些文字、影像资料。器物医学史的信念与目标也在于发掘民间叙事的医学史,从民俗生活来认识医学与健康。
历史书写,并不是随心所欲地编造,而是立足于证据,主要是物证来复述(再现)某一个历史事实与场景,刻画某一个历史的内核。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而,证据在哪里?不能只盯着藏有古籍的图书馆,藏有文物的博物馆,还要将视点移至民间收藏和民俗生活。新兴的人类历史学将人类学理念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赋予器物医学史全新的权重。那就是历史边缘的中心化取向,给予民俗事件、民间收藏的器物以创造性的解释空间。毫无疑问,器物医学史作为民间记忆的医学史,人与物交映互鉴的医学史,每一件器物背后都有年代感,都有相关人士的情感寄寓。
器物医学史,关注点有器有物,器侧重于医疗活动,物侧重于百姓保健活动,器具侧重于传统医疗(如炼丹的器皿、陶器),器械侧重于近现代医疗(早期的光学仪器,后来的光电一体化、电磁仪器),器物医学史的目光主题涵盖健康(保健)器物、医疗文书(病历)、医疗器械、医学科学仪器、医学教育文书、医学博物馆展品等多个相关领域。器物医学史就是在历史中做田野考证,通过医疗保健器物的发现和发掘还原历史的脉搏、温度与细节。器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蕴含着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撑,体现了二战以后军事技术大量转移到民用领域的历史轨迹,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循环加速机制,譬如CT、磁共振成像技术的背后涉及多项物理学的最新发明,其中,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发明赢得四次诺贝尔奖。1924年,泡利提出假说,原子核中的质子或中子在某种情况下会以角动量运动,即所谓自旋,因此变得具有磁性,他由此获得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37年,前苏联物理学家证明液氮中具有磁性。同年,拉比计算出磁动量,获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46年,潘塞尔与布罗奇分别宣布发现核磁共振方法,用于测量原子核磁场,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NMR最先用于化学分析:微量标本测试技术不断扩大使用对象,后来发展到建构多维人体图像。2003年,劳特布(发现磁场梯度可以产生二维图像)与曼斯菲尔德(建立了磁场梯度的信号分析与图像转换方法)因这些磁共振成像技术领域里的突破性成果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
3 器物医学史:研究谱系的展开
当下,器物医学史的拓展不必追随文献医学史的脚步与节奏,而是要聚焦于历史潮汐的潮头与转折点,尤其是西学东渐的巨大历史变革。无疑,器物医学史是近代医学西学东渐的物证谱系。
其一,光学器物的横空出世是一个转折点,400年前,荷兰人列文·虎克的透镜加工术带来显微镜、照相术的发明,打开了探索、记录生命微观世界的窗口。明末清初,大量西方光学器物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专家分析,欧洲光学器物东传的几种不同途径,如贸易、朝贡和传教士等。外来的取景暗箱、透视画、变形镜、多面透镜、魔灯等在我国民间都有流传。照相术的发明与摄影器具的传入,使得医学、保健主题的图像进入医学史的视野,派生出图像医学史的研究分支。
西方光学器物不仅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十分有趣的不同文化角色,明清诗歌曾对西来光学器物的文化史进行解读,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孔尚任在《节序同风录》中,就记载“九月初九:登高山城楼台……持千里镜以视远”。西方舶来光学器物的在地化与工艺史值得深入发掘。明末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有一定的西学基础,著有专著《镜史》一部,制造各类光学仪器达七十余种。清代著名科学家郑复光在《镜镜冷痴》一书中对各种铜镜的制造、透光镜的透光原理等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应该从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开始,“此无大用,取备一理”,万花筒“其制至易,而其理至精”[11]。
清末民初,光学仪器开始明显地用于医疗目的,观测生命与疾病指征,始于病原学、病理学探究的设备,如显微镜,随后是1895年伦琴X射线的发现与X光机的发明。在当时,它是现代医院里第一款大型医疗器具,而且需要与电力设备配套使用,据《点石斋画报》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美国教会创办的苏州博习医院就引入一宝镜,“可以照人脏腑……其镜长尺许,形式长圆,一经鉴照,无论何人心肺肾肠,昭然若揭”,科学技术史界不认可这件宝物就是X光机,一是时间太近,伦琴1895年才发现X光现象,当时不可能在第二年就有普及化的机具生产与出口;二是形态功能也不准确,最初的X光机还无法检查所有内脏器官,真正可以采信的引进X光机的新闻是1918年浙江宁波慈溪保黎医院的X光机,据谢振生先生考证,该设备由美国GE公司进口,慎昌洋行代办,机器、运费、关税总价4 368.968元(银元),由于当时慈溪尚不具备电力供应,医院自建发电机房,延宕到次年才投入使用[12]。随后的X光器械的发展轨迹不仅有物理当量、检测功率的不断加大,设计理念的升级换代(计算机技术的导入),制作工艺的不断精细,还有医生防护水平的不断提升,从无防护到低防护,再到高防护,体现了医护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厂商设计理念的进步。
第二是外科器具,是近现代形成谱系的医学器物,历史上,中医的外科发展前盛后衰,《周礼·天官志》中就有“疡医”之分,历朝历代连绵不断的征战都需要外科疗治,三国时期的华佗就曾经尝试过外科手术疗法,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手术刀是青铜“砭镰”,该器物做工精细,形制像一把缩小的“戚”或平头的“戈”。刃口锋利,明显有打磨过的痕迹,三指捏拿,操作方便,如同刀片一般,可精细削割人体器官[13]。但宋以后外科陷于停顿,演变成为以药物为主的外治之术,西学东渐之后,才脱胎换骨成为以手术为特色的临床科室,外科医疗器具日渐丰富,随着精细机械加工、制作工艺的提升,各种手术刀、剪、钳、夹、皿应运而生,消杀、麻醉、输血技术的发展也诞生了许多专门器具;现代牙科的兴起,更带动了成套口腔检查治疗器具的繁盛。其背后是医疗器械工业化雏形的凸显,包括专业医疗器具的临床动因、研发团队、模型制作工坊、生产加工的设备、精度、质量控制、临床测试、定型,以及销售促进、进出口业务、广告文书的大量涌现。
此外,第三类是随着化学药品逐渐取代原生态的植物、动物药品,而催生的近代工业化的实验研发、提纯技术、药业加工、临床试用、审核准入、市场化的销售和包装、药店陈列、媒体推广(广告)而派生的一系列器物。
第四类是近代检验、检测技术与护理技术的萌生而派生的采血、化验、体温、血压检测、注射给药、吸痰、给氧、导尿、止血、包扎等症状处理的系列器物。
第五类是近代战争境遇中急救、转运、手术、输血、护理,及临时救护所组建过程中的器物。如白求恩大夫在冀中根据地发明并设计制作的被称为“卢沟桥”(加载在马背上)简易战地外科器具箱,以及简易外伤消毒、固定装置[14]。
第六类因近代医疗器物是由现代医学教育的兴起,带来教科书、参考书出版的繁荣,以及考试、考核、培训、认证卷宗、文凭、文件、教具、挂图的丰富。
第七类近代器具是伴随着诊所到医院的转型,医疗流程的变革,不仅医疗器具越来越系列化,也带来医疗、财务文书的标准化,医疗过程记录从无到有,从略到详,由自由体病案向契约特征的挂号及收费单据、标准化病历与病志、手术记录、护理记录、疗养记录的转身,其次是医疗账目由传统流水转向复式记账的现代簿记,以收支平衡、资产负债、现金流量等表单为标志的现代财务制度显现雏形。
不同于经典与文献导向的医学史研究,器物医学史是某一(类)实物为基础的研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和路径。立足于新近发现的器物,或司空见惯却寓意不彰的器物,透过实物的细节说话,注重时代性、年代感独特标志的发掘,以及社会文化心理投射,但200年的近现代化进程脚步实在太快,我们只顾一路高歌猛进,缺乏驻足回味、系统收藏、梳理更新换代器物的集体意识和管理机制,譬如最早一批显微镜、X光机被新型机具替换时,没有被保存下来,而是作为废物而遗弃或扔进冶炼炉,大型的机具器物尚且如此,小型器物更加离散无踪,难以成套归聚,一些重要的器物全凭民间收藏的有限渠道加以回收,珍藏,20世纪六十七年代政治运动对民间收藏的摧残,更加速了近代历史遗存的消弭,仅凭分散、随机聚集的器物如何还原一幅大的近代历史图景,仍然是一个悬题。首先必须充分发掘民间收藏的潜力,将家庭隐形收藏品变成半公开的可供学界研究的展品,征集、组织主题、年代特色的医学技术器物展览是一个好形式,每一个展览留下一个藏品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一扇可征集的研究窗口。还可将目光投向公共博物馆,从其馆藏中发掘医学器物,丰富学术研究谱系。研究发凡部分着眼于近现代医疗模式(形式、内容)大关节(低倍显微镜到高倍显微镜,再到电子显微镜,从手动X光机到自动X光机,再到CT,增强CT)的变轨、变奏,创新与回归。
在器物的研究方法上,要高度重视比较研究,开启古今、中外医疗器物的比较,如日德与欧美、同款器物比较,还有同一国别、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流派(如中医与蒙医、藏医、苗医)器物等多元比较谱系,揭示医学器物发生、发展、传播演变的历史层次,破除器物的零星碎片化带来的困惑和不确定。在器物研究成果的叙事方式上,提倡风格多样、文体多元、媒体多融,可以是单一器物微小体征、意义的深度发掘,也可以是某一类器物的系统研究、比较研究,还可以是器物的多媒态呈现。
器物医学史的研究既要动员医史专家、收藏大师或系统、或分类进行有深度的研究,形成专著或专题文集,也要组织和发动医生、药业、医疗器械从业者,医学生参与征集、研究与写作,形成各个层级互补的研究格局。最终达到激活全社会、全行业的历史遗产(旧器物)意识,以器物医学史的征集、研究推动医学教育史,院校、医院等机构史,医药行业史、药业、器械业企业史的升级换代,形成器物医学史研究和展示的群体、群像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