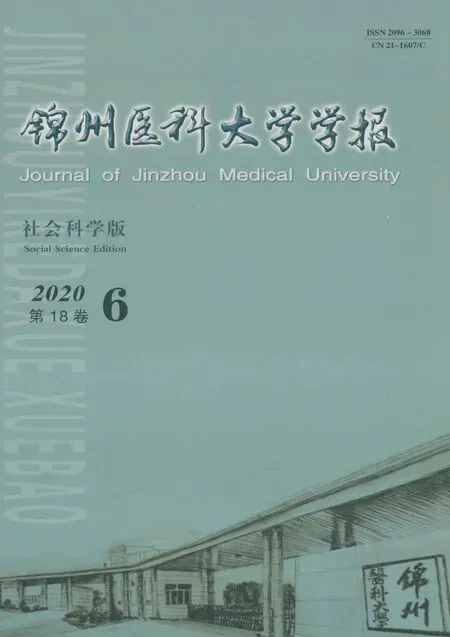陈志潜的公共卫生实践与时代启迪
2020-02-12王廷龙张玲
王廷龙,张玲
(川北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1]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时刻,回顾著名公共卫生学家陈志潜教授的公共卫生实践与思想,从中获得借鉴与启迪,对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公共卫生防治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融“小我”于“民族大我”的爱国情怀
1903 年9 月10 日,陈志潜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华阳县(今成都市双流县)。陈志潜从孩提时起,就目睹了街坊百姓和自家亲人在愚昧落后、庸俗迷信、医药短缺的状况下,被疾病折磨痛苦离世的种种惨剧。“在我们幼年时,除了父亲和他弟弟以外,家中每个人都在我童年时逝去。父亲的妹妹可能也和我母亲一样死于结核病,我弟弟死于伤寒,我们从来不曾知道是什么病夺走了我姐姐的生命。”[2]童年时期这些病痛与死亡的经历,使幼小的陈志潜暗下决心,寻求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医疗技术、医疗体制,以治病救人,服务社会。
从1921 年至1929 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期间,陈志潜认识的世界已远远不同于在成都童年时期的那个世界。20 世纪20 年代民族意识风起云涌,经常性的反帝反政府抗议活动与思想解放潮流相结合,加速了民族文化觉醒进程。陈志潜从1925 年起,“热情地投入到全民族的觉醒活动,并埋头于研究由此而产生的一些理论和社会问题。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驱使我决心探讨改善普通人民健康状况的方法。”[2]在与新结识的朋友们,如燕京大学教授许仕廉博士、英语报刊编辑陈友仁等进行的政治性讨论和辩论过程中,他逐渐产生了将在学院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际的新思路。[1]
由学社创刊并由陈志潜担任主编的《丙寅医学周刊》,“是受了五卅运动爱国思想的影响才创办起来的。在全国医学院校的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爱国表现”。[4]“本刊的产生既非出于聘任,又非本于其他一切的利害关系,完全由于少数同志抱牺牲的精神,服务的毅力,自动创办,以期籍此尽我们对于人民的一部分责任,发泄我们所积蓄着的热诚与愤慨”。[5]在5 年办刊期间,陈志潜亲自撰稿100 多篇,为我国20 世纪早期现代医学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临近毕业时,许多老师都希望陈志潜留校搞临床。恩师兰安生对他讲:“临床医学之于病人,如同面对森林里一棵棵树,哪棵树生病了,就去治哪棵。公共卫生学面对的则是一群人,保护的是一大片森林。你认为,目前的中国最需要怎样的人?”[6]面对兰安生的提问,陈志潜毅然决定选择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职业,即公共卫生的研究与实践。晚年陈志潜谈到自己青年时的职业选择时亦讲道,“从个人前途着想,留校专攻临床的确是很有诱惑力的建议,但是面对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社会,尤其是民众饱受战乱、贫穷、饥饿和疾病折磨的现状,迫使我不得不走出象牙塔,为变革现实而奋斗。”[7]
1929 年夏天,陈志潜下到南京晓庄,协助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卫生试验。1930 年赴美哈佛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9·18”事变后回国。这时晏阳初先生邀请他到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去看一看。“尽管当时定县人民的生活还十分艰苦,但他却在这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新生。于是他赶快和妻子及三个儿女连同他的岳母一起来到定县安了家,一干就是6年。月薪比在大城市少一半,吃的是小米粗面,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毛驴,开始了这场‘博士下乡,为老王老张们服务’的运动。”[8]
从1939 年到1952 年期间,陈志潜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重庆大学医学院院长、重庆中央医院院长等职务。1952 年以来,任四川医学院、华西医大(现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代理系主任、尘肺研究室主任。1996 年,93 岁高龄的陈志潜依然去简阳县养马镇卫生院调研,奔波在中国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第一线。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9]陈志潜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政治起伏的煎熬,但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成就了卓越人生。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新时代,我们回看走过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更应把个人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跑好接力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努力开创中华民族公共卫生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贯彻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的指导思想
近代中国社会,“仅极少数国人接受环境可影响疾病的发生,或很多疾病具有传染性的观点,因而导致对预防问题不予重视,治疗医学而非预防医学被视为卫生保健的核心成分。”[2]陈志潜所理解的社区医学,“是建立在治疗和预防相结合的方法上,而不仅是依靠治疗技术的医学。”[2]陈志潜认为:“公共卫生是涉及影响全民健康的环境和条件的一门科学。预防医学是组成公共卫生两个要素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要素;关于它的治疗要素,强调的是早期诊断。”[2]
陈志潜在《反顾一年》中批评道,“一百年来中国所有的西方医学,通同都在治疗方面,所以今日人民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进步,社会对于‘医’字仍然认为是‘吃药’、‘打针’……这是根本上的误解”。[3]《丙寅医学周刊》部分文章表达了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如果一些疾病比如伤寒、结核、白喉和破伤风等传染病可得到预防,则很多生命可以被挽救,而社会经济损失也可大大地减少……如果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懂得预防医学的目的和技术,并组织社区的力量加以实践,那么将使我国繁荣富强。”[2]
1929 年协和医学院毕业后,陈志潜与妻子一起去南京晓庄师范搞卫生示范区。陈志潜的工作得到了陶行知的大力支持。作为晓庄当时唯一的卫生学教师,陈志潜对当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系列举措:如撰写医学讲义,进行公共卫生知识普及教育,施种牛痘,改良水井建筑,注重预防;用创造性的临床医学方法开展临床教学活动,治疗头癣复发,重视治疗。晓庄实验,奠定了陈志潜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的思想和原则。
1932 年冬天,在晓庄经验与姚寻源前期试验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陈志潜开始在定县创建“区(县) —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实施内容“包括治疗医学和预防医学,齐头并进,而不是以何者为主,何者为第一。无论在计划、分配经费、训练内容等方面,两种都不偏废”[4]。对于当时社会上发生的预防医学与治疗医学等等的争论,陈志潜讲道,“这种现象,在今日的中国里,是不应当存在的,也是我觉得不必存在的……若是以社会问题为对象,我们看见定县每千死亡者三分之一在死前未得到任何医药的照护,当然得想如何普遍治疗救济的方法。同时看见去年夏天霍乱流行,死者络绎不绝,治疗效力甚小,传染由于井水不洁,当然得想如何普遍预防科学。”[10]
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就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11]长期以来,在“防”与“治”的关系问题上,预防体系建设往往遭到忽视。重温与学习陈志潜教授倡导的“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的公共卫生思想理念,对于遵循公共卫生建设内在规律,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贯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12]的基本原则,“实施健康中国战略”[13],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农村卫生体系
陈志潜注重科学的社会调查。“面向农村,没有社会调查的资料作为依据,其结果必然是生搬硬套,想当然地瞎指挥,劳民伤财,得不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14]在通县陈志潜有感触地讲道,“我的逗留是短暂的,只能表浅地观察当地人们的需求,而没有机会体验真正的农村生活,即使在那短暂时间里,我仍发现一些可以通过公共卫生措施加以改善的问题,医疗保健的缺乏和乡村极落后的条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陈志潜认识到,“在我们努力把现代医学带给人民方面,我国必须在自己的条件和资源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模式。而不能依赖借用国外医学校的模式,外国模式充满着风险和问题”。[2]
陈志潜主张从具体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他在定县创建公共卫生模式时评论道,“近五十年来,我国人所犯之病最大者莫过于‘瞎胡抄袭外人’。鸦片与甲午战后,中国整个纸灯笼国家被人揭破,一般人无论朝野上下之心理由蔑视外人一变而为崇拜洋人。于是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凡属外国政府所有事业之办法,无论合用与否,一律‘瞎胡抄袭’。在卫生方面亦是如此……所以我以为在今日中国,无论创办任何事业,必须首先打破‘瞎胡抄袭’之心理,振兴创作之精神。所以,今日在中国办卫生事业,除遭遇过渡时代意料中困难外,尚须从事试验,以达到创造目的。”[15]
陈志潜主张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他认为:为解决中国的愚穷弱私,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必须从农民环境中创造起来。”鉴于定县农民的普遍贫困,陈志潜认为,“卫生发展的程度以国家经济状况为标准,农民经济既然如此困难,一切卫生设施,当然不得超过农民负担能力……在经济极端困难之下,吾人对于各方面之基本问题,更不能不有确切的认识,卫生基本问题何在,为决定卫生计划范围之根据。”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陈志潜教授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人民在公共卫生事业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陈志潜教授身上展现出来的“立足本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信念,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启迪我们在防范化解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坚持完善特色公共卫生制度,推进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征程上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