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界: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域界的表示
2020-02-10鲁西奇
鲁西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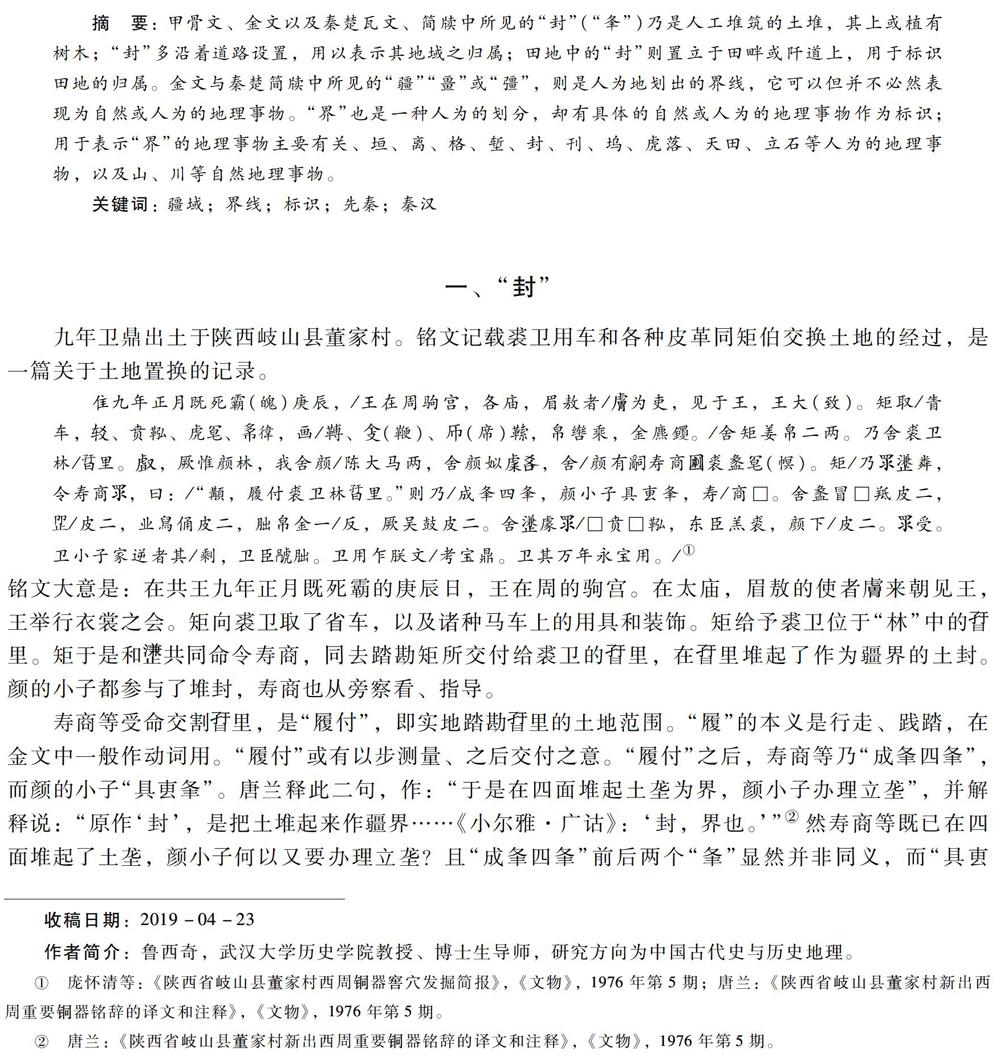


摘 要: 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并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
关键词: 疆域;界线;标识;先秦;秦汉
一、“封”
九年卫鼎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铭文记载裘卫用车和各种皮革同矩伯交换土地的经过,是一篇关于土地置换的记录。
隹九年正月既死霸(魄)庚辰,/王在周驹宫,各庙,眉敖者/为吏,见于王,王大(致)。矩取/眚车,、贲鞃、虎、徫,画/、(鞭)、(席),帛辔乘,金麃。/舍矩姜帛二两。乃舍裘卫林/里。,厥惟颜林,我舍颜/陈大马两,舍颜姒,舍/颜有寿商裘盠(幎)。矩/乃粦,令寿商,曰:/“顜,履付裘卫林里。”则乃/成夆四夆,颜小子具叀夆,寿/商□。舍盠冒□羝皮二,/皮二,业舃俑皮二,朏帛金一/反,厥吴鼓皮二。舍豦/□贲□鞃,东臣羔裘,颜下/皮二。受。卫小子家逆者其/剩,卫臣胐。卫用乍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用。/①
铭文大意是:在共王九年正月既死霸的庚辰日,王在周的驹宫。在太庙,眉敖的使者来朝见王,王举行衣裳之会。矩向裘卫取了省车,以及诸种马车上的用具和装饰。矩给予裘卫位于“林”中的里。矩于是和共同命令寿商,同去踏勘矩所交付给裘卫的里,在里堆起了作为疆界的土封。颜的小子都参与了堆封,寿商也从旁察看、指导。
寿商等受命交割里,是“履付”,即实地踏勘里的土地范围。“履”的本义是行走、践踏,在金文中一般作动词用。“履付”或有以步测量、之后交付之意。“履付”之后,寿商等乃“成夆四夆”,而颜的小子“具叀夆”。唐兰释此二句,作:“于是在四面堆起土垄为界,颜小子办理立垄”,并解释说:“原作‘封,是把土堆起来作疆界……《小尔雅·广诂》:‘封,界也。”②然寿商等既已在四面堆起了土垄,颜小子何以又要办理立垄?且“成夆四夆”前后两个“夆”显然并非同义,而“具叀夆”之“具”当作“完成”解;“叀”字则当为动词,唐先生盖解作“立”,而未作说明。按:“叀”字,当即甲骨文所见之“”(,)字,金文一般作“”,《说文》叀部作“”,古文作“”。徐中舒先生谓甲骨文字,“象纺砖上有线穗之形。”【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卷四,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2页。】颇有启发。盖“叀”字本当像以线系石块之类重物。若然,则“叀夆”当即在“夆”上挂以线系石块之类,作为标识。然则,“叀峯”及“成夆”之“夆”就应当是土堆,而不会是一条长长的土垄。这样,寿商等“成夆四夆”,颜小子“具叀夆”,就是寿商等在里堆筑了一些土堆,而颜的小子在那些土堆上挂了石块之类,以表示其归属。
叀与邦、封相联系,在甲骨文中即有所见。《甲骨文合集》36530:
己酉,王卜,贞。余征三邦……叀令邑,弗每。不……亡……在大邑商。王曰:大吉。在九月,遘上甲□五牛。
叀令。【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1页。】
邦,或释作“丰”,同“封”。甲骨文中,封、邦、對三字大致通用,且不论。“叀令邑,弗每”,当解作征服了三邦(封)之后,在那里标志了“”的符号,任命了邑的首领或长官,却未加以训诲。这个邑,很可能就叫作“”邑。“叀令”,也是指命名邑、任命其首长。
那么,卫鼎铭文所谓“成夆四夆”,是不是在里的四周堆筑了一些“封”,其所包围起来的地域就是里呢?我们以为并非如此。著名的散氏盘铭文记眉、井二邑之疆界甚详。铭文曰:
用夨散邑,乃即散用田。眉: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以陟,二封,至于边柳。复涉瀗,陟雩、、、,/以西,封于城,木,封于刍逨,封于刍内。陟刍,/登于厂湶,封,,、陵、剛,,封于兽道,封于原道,/封于刍道。以东,封于东疆右。还,封于眉:道以南,/封于谹逨;道以西,至于,\[叀\](莫)“眉”。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东,一封;还,以西一封;陟刚,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刚,登,降棫,二封。夨人/有眉田鲜、且、微、武父、西宫、襄,豆人虞丂、录贞,师/氏右眚,小门人繇,原人虞艿,淮工虎孝、丰父,/人有、丂,凡十又五夫,正眉、夨舍散田。土/□□、马兽,人司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眉/田戎、段父、父,之有司橐、州、焂从,凡散/有司十夫。隹王九月辰才乙卯,夨俾鲜、且、□、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爰/千罚千,传弃之。”鲜、且、□、旅则誓。乃俾西宫、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湿田、田,余有爽变,爰千罚千。”/西宫、襄、武父则誓。厥为图夨王于豆新宫东廷。/厥左执史正中农。/
,小川琢释作“”,引《方言》:“,续也。”解作夨地与散邑相连。陈梦家释为“接”,谓夨地接壤于散邑,故租用其田而田之。【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5页。】夨、散二地接壤,二者之间围绕着土地问题发生了一些纠纷,乃共同划定了疆界,并将过程与结果铭于此盘。“封”字于铭文中凡十七见。陈梦家先生说:
(“封”)实乃《说文》卷二廾部奉(从手)所从而省手,象两手封(植)树之形……此铭“封于某地”之封为动词,“二封”“三封”之封为名词。古代封立田界,乃是在人工堆聚的土堆上更植以相宜的树木,以为标志,故封有聚土之义。《周礼大司徒》注“封,起土界也”;《周礼封人》序官注“聚土曰封,谓堳垺及小封彊也”;崔豹《古今注》曰“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示疆境也,画界者,于二封之间以为垺以画分界域也。”封土之上,树以树木。【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346页。】
铭文涉及眉、井二邑田地的疆界。自第一行“眉”,至第四行“\[叀\](莫)眉”,述眉的界域:(1)从眉溯瀗水而上,向南行,在大沽(当即大湖),做第一封;渡过大沽(大湖),到边,做第二个封,上植以柳。再溯瀗水而上,登上雩、、、(当是不同的塬)。(2)向西行,在城做一个封,上植树;在刍的谷口做一个封,然后在刍的谷道里再做一个封。登上刍(当是山名),越过山崖和泉源,
在做一个封,上面植以木。
在、陵、刚(岗)各做一个封,在刚的封植有木。然后再在通往兽的道路口立了封,在通往原的路口立了封,在通往周的路口立了封。(3)在东面,沿着的东界立封,界的右边(西面)属于眉。(4)回到眉邑,在眉地做封:沿着道路向南,在通往谹的谷口做一个封;沿着道路向西,到,立一个封,在封上标明是“眉”。自第四行“井邑田”,至第五行“二封”,述井邑的疆界:从眉,沿着桹木道东行,到达井邑,在井邑立一个封。沿着道东行,做一个封;回到井邑,沿着道路西行,做一个封。(向南)登上山岗,做第三个封。越过山岗,在通往同的道路口做一个封。(向北)越过州岗,做两个封:岗上的封植木,岗下的封植棫木。这些封,有的位于湖边,有的位于谷口或谷道内,有的位于岗塬之顶或岗塬之麓,有的位于道路之侧。封大抵多沿着道路设置,只是在路上某处堆起土堆,上面植有相应的树木,表示这些封所标志的地域属于某邑。各封之间其实并不能联成一条线,明确表示某邑的界域,而只是在道路或山谷口、山顶显要处置立标识,以表明其地之归属。据此,卫鼎铭文中的“成夆四夆”,也当解作“做了四个封”,而不能理解为在里的四周都做了“封”。
据散氏盘铭文所记,参加勘定眉、井二邑疆界的双方,夨人有十五夫,眉人有十夫。陈梦家先生说:“此二十五人,皆属于双方的有司,其官名有司工、司马、田、虞、录、小子、师氏、、宰、。”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夨人参与勘界的有司除了眉田鲜、且、微、武父、西宫、襄六人之外,还包括豆人虞丂、录贞、师氏右眚、小門人繇等四人,以及原人虞艿,淮的工虎孝、丰父,人的有司、丂。参与勘界的散有司,除了司土□□、司马兽,散人小子眉田戎、段父、父等五人外,还包括人司工君、宰德父,之有司橐,州,焂从等五人。据上引铭文,由眉向西行,有一条通向“原”的道;则是靠近眉、立有封的一处地名。据此推衍,原、、豆、淮、、以及州、焂,都应当是在眉邑附近的聚落名。这些聚落的有司(焂的从也应当是一种有司)都参与了勘界,说明这些聚落均包括在勘界所及的地域中。他们当然也参与了堆筑“封”的活动。然则,这些封,联结起来,也并不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而是用以表示地里之所至,是标识“封”所在地域之归属的。
《周礼·地官司徒》“封人”条:“封人掌设王之社,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二《地官司徒·封人》,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90-891页。】社,即社坛。封人负责建设王的社坛,在王畿的四周设立封,且于封上置树。这里的“封”,和社一样,也是土堆。凡封国,均在国都立有社,在四疆则用“封”表示其疆界所至。历来论者,对“封畿”“封其四疆”究竟如何“封”,颇多讨论,意见纷纭。而由散氏盘铭文所见,则知所谓“封畿”“封其四疆”及“封域”,并非在畿的四周、国的四疆或辖域的四面,各筑一系列的“封”,将畿、国、域围起来,而是在王都、国都或其他都邑设一个“”(可视为一个大的“封”),然后沿着向四疆伸展的交通道路,各堆筑有若干的“封”。距离王都、国都或其他都邑最远的“封”,当然就是王畿、国境、都邑辖境的边界。
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所记是战国时期秦国分封宗邑的情况。其文曰:
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胙)。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取杜才酆邱到于潏水,以为右庶长歜宗邑。”乃为瓦书,卑司御、不更顝封之,曰:“子子孙孙以为宗邑。”顝以四年冬十壹月癸酉封之。自桑之封以东,北到于桑匽之封。一里,廿辑。大田佐、敖豪曰末,史曰初,卜蛰,史羁手,司御心,志是霾封。【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中国古文字学会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7-196页。】
四年,一般认为即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歜受封的宗邑在杜(县、邑)之酆邱到潏水之间,具体范围是在桑界以东、桑堰界之南。“一里廿辑”,诸家解释不同,然大抵以“里”为居民编排单位,“辑”则或解作“家”,或解为“聚”。“敖豪”之“豪”,诸家多释为“童”,今细辨拓本图影,改释为“豪”。“大田”,应是“里”之上的管理单位,或即相当于乡。末是当地的豪帅(敖豪),担任大田佐,当即乡佐。司御、不更顝受命去“封”右庶长歜的宗邑,即去给歜的宗邑做标识。“封之”,当解作立封以志之。写明“子子孙孙以为宗邑”的瓦书当即悬于封上。顝至少主持置了两个封,一是“桑之封”,一是“桑匽之封”(两个封的四周当围以桑,或在封上植有桑)。具体参与立封的,有大田佐末、史初(名为初的史)、卜蛰(名为蛰的卜)、史羁以及司御心等人。
青川木牍中亦见有“封”,其性质当是“田封”,即用来表示田地归属的土堆。木牍正面文字有三行: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氏臂更脩(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畮(亩)。畮(亩)二畛,一百(陌)道。百畮(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脩(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脩(修)陂堤,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章手。/【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于豪亮:《释青川秦墓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后收入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3-166页。】
二年,即秦武王二年(前309)。木牍文字大意谓:(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初一,王命左丞相甘茂、内史匽、氏臂,更修为田律。律令如下:如果一块地宽一步、长八则(每则三十步),就是一亩;一亩地(二百四十步),要修二条畛、一条陌;一顷(一百亩)地,要修一条阡道。阡道宽三步。封,高四尺,其底部的长、宽均为四尺。埒,高一尺,下厚二尺。每年秋八月,修封、埒,端正疆、畔等域界,并刈杀阡陌上的荒草。九月,整修道路,一直到山阪高险之处。十月,造桥,修陂堰,筑堤坝,清理河道湖陂中的杂草积木。纵使没到修整道路的时节,如果道路毁坏不能通行,亦当随时修治。
这里的“封”与“垺”并列。于豪亮先生说:封是田界的表示。汉尺一尺为二十三厘米,因此,封的长、宽、高各为九十二厘米。而垺高一尺,下宽二尺,是低矮的土垣。“田界除了以封作为标志外,封与封之间还以矮墙相连,这样,各户所占有的土地界限就很明确了。”并引崔豹《古今注》所云“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也。画界者,于二封之间又为垺,以画分界域也。”【于豪亮:《释青川秦墓木牍》,《于豪亮学术文存》,第163-166页,引文见第164页。】其说颇可信从。然谓垺连接二封,说服力则欠缺。盖田一顷修一条阡道,而每亩又要有一条陌道,自是便利田地耕作与联系;若各户耕种的土地四周又围以垺,则必然会阻断阡、陌。而且,上引《田律》谓“修封、垺,正疆、畔”,则封、垺与疆、畔相辅相成,但并非同一事物。如果疆、畔是界线(见下文),那么,封、垺就只能是界线上用于标识的点。所以,“垺”也应当是土堆,只是比“封”要低矮且小(“封”高四尺,“垺”高一尺)。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亦见有“封”:
“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第108页。】
这里解释“封”即“田阡陌”。释文解释“即”作“就是”,遂将“封”等同于田中的阡陌。然简文又称“封”在“顷半(畔)”,即田地的边上,则“封”并不是阡陌。故“即”当作“在”“靠近”解。“封即田千佰”,当解作“封在阡陌之上或其旁”。“顷畔封”,当是在一顷田地的边上置立一个“封”,就在百亩之田的“畔”上。“盗徙封”,就是偷偷地移动“封”固有的位置。
二、“疆”
上引青川木牍《田律》中謂秋八月当“修封、垺,正疆、畔”。《国语·周语》:“修其疆畔”。韦昭解曰:“疆,境也。畔,界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页。】《礼记·月令》记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郑玄谓:“封疆,田首之分职。”并释经作径,术即遂,而以步道为径,小沟为遂。【(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一五《月令》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7页。】释“疆”为境,“畔”为界,就一般而言,自无疑义。然疆、畔究竟为怎样的境、界,却仍需再加考量。
《说文》释畔,谓“田界也,从田,半声”。【(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1页。】《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子产曰:“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春秋)左丘明著,(晋)杜预集解:《春秋左传集解》卷一七《襄公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1页。】农夫耕田,均有其界,很少越过,说明“畔”是农夫之田的界,有具体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诗经·国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郑笺:“泮读为畔。畔,涯也。言湛与隰缘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无所拘制。”【(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下《国风·氓》,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8页。】则“泮”指湖沼之崖岸。据此推衍,“畔”当指田地的边上与未经垦辟的草地或山林相分隔的那条线:畔并不是田地中间的道路或田埂,而是田地与其外的草地山林间的界线。《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王逸注:“履荆棘也”。【(宋)洪光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页。】则知“泽畔”是指湖泽与陆地相交的岸线。因此,“畔”乃是一种自然的边界,是垦殖的田地尽头处、与尚未垦辟地草地山林之间的交界线。
《说文》:“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汉)许慎:《说文解字》,第291页。】畕,“比田也”,二田相连,中间无界;则“畺”就是将田地划分开来的界线,是人使用工具划分出来的界线。徐中舒先生解“畺”字,谓:“从畕从弓,为疆之原字。古代黄河下游广大平原之间皆为方形田囿,故畕正象其形。从弓者,其疆域之大小即以田猎所用之弓度之。”【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卷一三,第1475页。】所说颇有启发。永盂铭文曰:
唯十有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厥/命,锡畀师永,厥田阴阳洛,/疆师俗父田。厥公出/厥命,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公乃命郑司徒父、/周人司工、史、师氏、邑/人奎父、毕人师同,付永厥/田。厥率履厥疆宋句。永拜/稽首,对扬天子休命。永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盂。永其/万年,孙孙子子,永其率宝用。/【唐兰:《永盂铭文解释》,《文物》,1972年第1期。】
十二年,唐兰先生认为当是指共王十二年。铭文记周王分封土地给永(“师”是他的官号),益公负责传达周王之命。这年初吉丁卯,益公受天子之命,赐给师永田地。赐给永的土地之所在及范围是“阴阳洛疆师俗父田”。此句之句读,一般将“阴阳洛疆”连读。唐兰先生说“阴阳洛疆”是指陕西的洛河南北,“属于边疆,而敔簋记南淮夷来伐是一直到阴阳洛的”。【唐兰:《永盂铭文解释》,《文物》,1922年第1期。】可是,若如此解释,则“阴阳洛疆”遂得与“师俗父田”并列,而前者只是指一块大致的地域,后者却有明确的归属。此句或当解作“锡畀师永,厥田阴阳洛,疆师俗父田”,即赐给师永的田位于洛水南北,其疆界与师俗父之田相接。师俗父之田显然就在阴阳洛,所以他也受命参与此次畀田师永之事。具体负责土地交付的,有郑司徒父、周人司工、史、师氏、邑人奎父、毕人师同。他们“率履厥疆”,当是指踏勘土地。宋句,诸家皆无解。句,《说文解字》:“曲也。”【(汉)许慎:《说文解字》,第50页。】宋句,很可能是宋地出产的一种曲状的测量工具。若然,郑司徒父等在划分给永的田地疆界时,使用了一种称作“宋句”的测量工具。《周礼·考工记》:“覆之而角至,谓之句弓;覆之而干至,谓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谓之深弓。”贾疏云:“此以下论弓有六材,角干筯用力多,特言之。若三者全善,则为尤良;若一善者为敝,二善者为次。今此先察一善者至,谓若余干筯不善,直角善,可以为句弓。”【(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卷八六《冬官·弓人》,第3567-3568页。】句弓用于射,乃是一种差的弓。“宋句”,或者就是与《考工记》所记句弓相似的一种测量工具。墙盘铭文述及康王时周的势力大张,“(遂)尹啻(亿)彊(疆),宖鲁邵(昭)王,广楚荆”。【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1978年第4期。】“啻(亿)彊”之“彊”,当是一种计量单位,说明“疆”乃是用一种类似于弓的工具测量的,而这种测量工具的长度,就成为一种测量单位。
则垣与门是两个里之间的界。在这里,“界”是用具体的人工建筑的垣和门表现出来的。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
□、相国、御史请:缘关塞县道群盗、盗贼及亡人,越关、垣、离、格、堑、封、刊,出入塞界,吏卒追逐者得随出入服迹穷追捕。令/将吏为吏卒出入者名籍,伍以阅具,上籍副县廷。事已,得道出入所出人〈入〉。盈五日不反(返),伍人弗言将吏,将吏弗劾,皆以越塞令论之。/【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页。句读有所不同。】
塞界,当即缘关塞县、道的边界。用于标志“塞界”的地理事物,有关、垣、离、格、堑、封、刊等。“关”,即关口、关隘。“垣”,是在关口两侧修筑的土垣,羊马墙之类。“离”,即篱,指篱笆。“格”,即木格,以木做成十字交叉之形,置于平地,以阻碍人马通行。甘肃敦煌酥油土D38烽燧所出汉简:“丙午,虏可二百余骑,燔广汉塞格。至,其夜过半,时虏已去……。”【李均明、何双全编:《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句读有所不同。】虏所燔的“格”属于广汉塞。“堑”,即壕沟。“封”,是堆筑的土堆,已见前。“刊”,《汉书·地理志》“随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句下颜师古注曰:“栞,古刊字也。奠,定也。言禹随行山之形状,刊斫其木,以为表记,决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其安定。”【《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4页。】则“刊”当是指斫木以作为标志。关、垣、离、格、堑、封、刊等,都是人为的地理事物,它们共同构成并标识“塞界”。
又,坞也是表示疆界的地理事物。居延汉简13.2:
到北界,举坞上旁蓬一通夜。坞上□【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这个坞位于“北界”上,旁边有一个“蓬”。坞(包括其旁的蓬)构成了北界的组成部分。塞上又有所谓“天田”。居延汉简18.8:
卒郭钤乙酉迹,尽甲午,积十日。/卒董圣乙未迹,尽甲辰,积十日。/卒郭赐之乙巳迹,尽癸未,积九日。/凡迹廿九日,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28页。】
这是一份戍边士卒巡边的记录。郭钤、董圣、郭赐三人共巡察了二十九天,没有发现人、马越过边塞“天田”的踪迹。居延汉简45.17:
上□北界毋兰越塞天田出入迹。【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79页。】
居延汉简206.2:
吞远候史李赦之/三月辛亥迹,尽丁丑,积廿七日。从万年隧北界,南尽次吞隧南界,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三月戊寅,送府君至卅井县索关,因送御史李卿居延,尽庚辰,积三日不迹。/【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319页。】
天田,又作“沙田”。《汉书·晁错传》“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句下注引苏林曰:“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见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师古曰:“苏说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连遮落之也。”【《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2286-2287页。】苏林以为“虎落”即“天田”,顏师古已指其非是,然苏林对“天田”的解释是正确的。据颜师古的解释,“虎落”乃是藩篱之类,置于关塞之下或险要之处,用于阻挡人马通行;根据苏林的说法,“天田”则是人工铺设或平整的沙地,亦设于关塞之下或险要之处,其用途却是检查有无人马通过。天田是“画”的。居延汉简306.21:
卒卅七人
其二病十四人作堑
辛亥三人养 九人画沙
定作卅二人九人累土【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502页。】
这个守卫据点驻有士卒三十七人,辛亥日,除二人生病、三人休假外,有三十二人参与劳作。其中,十四人“作堑”,即挖掘壕沟;九人“画沙”,即平整沙地;九人“累土”,即堆筑土封。堑、沙、封,都是用于标识边界的人为地理事物。
新始建国四年(12)连岛界域刻石,位于今连云港市连岛镇东连岛村。刻石有二,其一为苏马湾刻石,位于连岛苏马湾沙滩南缘一块独立的石壁上,存字十二行,约六十字:
东海郡朐,与/琅邪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与柜分高/□为界。东/各承无极。/始建国四年/三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
其二是羊窝头刻石,位于连岛最东端,共存字八行,约四十字:
东海郡朐,与/琅邪郡柜为/界:朐北界尽/因诸山山南,水以北/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为/界。东各承/无极。/【连云港市文管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东连岛东海琅邪郡界域刻石调查报告》,《文物》,2001年第8期。】
朐、况其、柜均为汉县名。《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朐”县原注:“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有铁官。”【《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第1588页。】《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朐”县刘昭注补引《博物记》:“县东北海边植石,秦所立之东门。”【《后汉书》志二二《郡国志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58页。】《水经注·淮水》谓淮水迳广陵郡淮浦县故城东,向北有一条分枝,称为游水。游水“历朐县,与沐合。又迳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县立石海上,以为秦之东门。崔琰《述初赋》曰‘倚高舻以周眄兮,观秦门之将将者也。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苍梧徙此,云山上犹有南方草木。今\[青\](郁)州治。”【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淮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2-2564页。】汉朐县故城,一般认为即在今连云港市海州区孔望山南。其时郁洲与朐县陆地尚未并岸,是海中的大岛;连岛更在其外。况其,又作“祝其”(东海尹湾汉简亦作“况其”)。《汉书·地理志》东海郡“祝其”县原注:“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莽曰犹亭。”【《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88页。】《水经注·淮水》说游水经朐县后,又北经东海郡利成县故城东、羽山西,然后经过祝其县故城西。其所记之此段游水,大致相当于今新沭河。故况其(祝其)县当在今赣榆县西北境、山东临沐县东南境一带,其治所很可能是在今赣榆县夹山乡祝其山一带。柜县属琅邪郡。《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柜”县原注:“根艾水东入海。莽曰祓同。”【《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86页。】《水经注》卷二六《胶水》记有艾水,谓:
(艾)水出拒县西南拒艾山,即《齐记》所谓黔艾山也。东\[南\](北)流迳拒县故城西,王莽之祓同也。世谓之王城,又谓是水为洋水矣。又东\[南\](北)流,晏、伏所谓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胶水者也。又东入海。《地理志》:琅邪有拒县,根艾水出焉,东入海,即斯水也。【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二六《胶水》,第2280-2281页。】
注文谓艾水东北流,然今山东半岛东南部的地形,决定诸水不可能东北流,而只能东南流,故径改。艾水(或作“拒艾水”)当即今流经山东日照市南境的傅疃河。然则,汉时拒(柜)县当即在今山东日照市一带。
连岛界域石刻所记,就是朐与柜(拒)二县的分界:朐县在南,柜(拒)县在北。结合二石所记,知二县东端的分界沿着“诸山”:山南属朐县,山北是柜县。诸山,当指从连岛到云台山(古郁洲)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脈。调查报告说:“苏马湾刻石和羊窝头刻石的刻面面向均为0°,这绝不是偶然巧合,说明刻石者精心挑选出壁面面向为正南北的岩石作为刻立北界的所在。苏马湾刻石位于东西连岛中部偏西,羊窝头刻石则位于东西连岛的最东端,也正是控制南北海域的咽喉要地。再者,二刻石两点成一线,正好可作为划分界域的界线。”【连云港市文管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东连岛东海琅邪郡界域刻石调查报告》,《文物》,2001年第8期。】可是,二刻石连线的走向,却与连岛—云台山的走向正相垂直,并不能构成“因诸山”为界。所以,二刻石正当是在“诸山”顶端的两侧,其中间则正是诸山的余绪。
刻石中的“水”当即指上引《水经注》所记之游水(大致相当于今新沭河),水南属朐县,水北属柜(拒)县。沿着游水向西,直到祝(况)其县境,朐、柜(拒)二县分高□为界。“高”字下所缺之字,二刻均难以辨识,然其为地理事物,当无疑问。“东各承无极”,是指二县的领域向东延伸到大海,至于远望之极。
这样,东海郡朐县与琅邪郡(国)柜(拒)县间的分界,就是从今连岛的二刻石中间位置,向西南方向,沿着连岛—云台山的山脉脊线,向西(略偏南),至海边;渡过海峡,接着游水,溯游水而上,至于朐、况(祝)其、柜(拒)三县交界处的高□,朐、柜(拒)二县沿高□的分水岭分界。这条二县分界线虽然由山(诸山及高□)、水(游水)构成,但却是人为划定、并指明由上述山水作为分界标识的。
莒县宋伯望刻石,又称莒州刻石,现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其四面刻文连读,曰:
汉安三年二月戊辰朔三日庚午平,莒男子/宋伯望、宋何、宋□□,在山东禺亭西界,/有田在县界中□。元年十月中,作庐望田中,/近田。望恐有当王道。□曰:古有分堵,/无分民。望等不知县图、界□,有行/事。永和二年四月中,东安塞宜为/即丘民相、相弟明,所□发所在,望等/所立石,书:南下水阳,死千伯,上道东。/东安游徼玉纪,与莒/禺亭长孙著是□著山□/归□,莒贼曹掾□仲诚,游徼徐□、审/□,贼曹掾吴分,长史蔡朔。望等告:/□发石,上有故千县界,有北行车道,千、封/上下相属,南北以千为界,下有受明。□□□/田名分明:千北行至侯阜北,东流水□/别界;南以千为界,千以东属/莒,道西□水南流属东安。明/□宜以来,界上平安。后有畕/界,以立石□□□□□行事。/□□壬、癸,□□□□;/□在丙、丁,界上□□/立界,民无所□租以□/道地界,所属给发/出更赋,租铢不逋。/【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6页;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一册,第144-149页;邢义田:《秦汉平民的读写能力——史料解读篇之一》,邢义田、刘增贵主编:《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古代庶民社会》,“中研究”2013年版,第241-288页。】
按:此刻旧定名为“莒州宋伯望买田刻石”,然碑文并无有关买田内容,不知所据。今定为“莒县宋伯望刻石”。碑文字体朴拙,刻画粗陋,自来释文多不能通解。今在前人基础上,勉力试释如上,或可大致知其意:盖汉安三年(144)二月三日,莒县男子宋伯望、宋何等,在山之东面、禺亭西面的一个地方,竖立此碑。宋伯望等有一块田地,正处于莒、东安二县的界线中间(田跨二县)。在此之前,元年十月中,宋伯望在自己田中建了一座草庐。宋伯望等担心这样做,不合乎朝廷的法规。有人说:“古有分地,无分民”,所以宋伯望等没有去弄清楚两县分界的图及相关规定。永和二年四月中,东安县塞宜(乡)为即丘的民相和他的弟弟明,上报说:宋伯望等人的土地上,曾经有一方立石,上面写着“南下水阳,死千伯,上道东”等字样(这几个字当是所发现的原碑的残字,不能通读)。东安县的游徼玉纪,与莒县禺亭长孙著、莒县的贼曹掾□仲诚、游徼徐□、贼曹掾吴分、长史蔡朔等,乃一起调查东安、莒二县在宋伯望田地一带的分界情况。宋伯望等报告说:在自己田地里确实发现了界石,上面写明故阡道乃是县界,以及向北行的车道,阡道与土封相互对应,南北向以阡道为界。于是,两县官吏乃共同确立二县分界,明确田地、民户的归属:沿阡北行,至侯阜北,以东流水为界;向南,以阡为界,阡以东归于莒县;车道以西,水南流,属东安县。自从协商妥当以来,界上都很平安,以后如果发生田地纠纷,则以此次立石为准。县界阡道两边的田地,要根据其所属,纳赋服役,不得逃避赋役租税。
在上录背面碑文的上首,还刻有一个大圆圈。圆圈中有三行字,多不能辨识。邢义田先生据原碑首次识出了其中的四个字:
□赋毋□
□发□□□
……之……
结合上录右侧碑文所谓“民无所□租以□道地界,所属给发出更赋,租铢不逋”,可以推测,碑文的核心内容与目标,并不是划分并标识宋伯望等人的田界,而是在宋伯望等人的田地上明确莒、东安二县的界线,从而明确宋伯望等人的田地,哪一部分属于东安县,哪一部分属于莒县:属于东安县的部分,要向东安县纳赋服役;属于莒县的部分,要向莒县纳赋服役。此碑的意义,在于县界落实到了具体的田地中间,要求明确分辨出同一户主的田地,究竟属于哪一个县,以确定其赋役的归属。也因为此,界线的分划与标识更为具体、细致。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在宋伯望等人的田地里,有古老的阡道和车道,阡与道相交处有“封”,与上文描述的先秦以来的情形相接近。而此次划分并确定县界,就是在已有阡、道基础上,立石以标明界线。二是以水的流向确定田地的归属,显然使用了“分水岭”的概念与方法。
因此,至遲到汉代,人们已较为普遍地使用不同的地理事物,包括自然的山、水,历史留存下来的古阡、道,以及人为造作的关、坞、垣、篱、格、堑、虎落、天田等,以边疆界线、行政区分划界线以及田地界线,并用刻石、立石以及“刊”等方式,表示界线两侧地域或田地的归属。
责任编辑:孙久龙
The Feng (Agger), Jiang (Line) and Jie (Boundary): The Expression of Boundaries in Early Ancient China
LU Xi-qi
(Department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The Feng (“封”,“夆”), seen in the oracles, bronze inscriptions, brick inscriptions and bamboo slips of State of Qin and Chu, refers to the mound that artificially stacked and on which some trees are planted. The Fengs (Aggers) usually were set up along the roads to indicate the attribution of its territory, while the Fengs in the field were placed on the banks of the field or on the road through the field to mark the attribution of the field. The Jiang (“疆”、“畺”、“彊”), seen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bamboo slips of State of Qin and Chu, refers to the line that was been artificially drawn, it can but does not necessarily manifest as natural or man-made geographical things. The Jie (“界”) is also an artificial division, but there are specific natural or man-made geographical things as the logo. The geographical things that used to denote the “boundary”in Qin and Han period mainly included some man-made geographical things such as the castle, outpost, barrier, roadblock, agger, trench, abatis, stela, as well as mountains, rivers and other natural geographical things.
Key words:territory; boundary; logo; the pre-Qin period; Qin and Han Dynas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