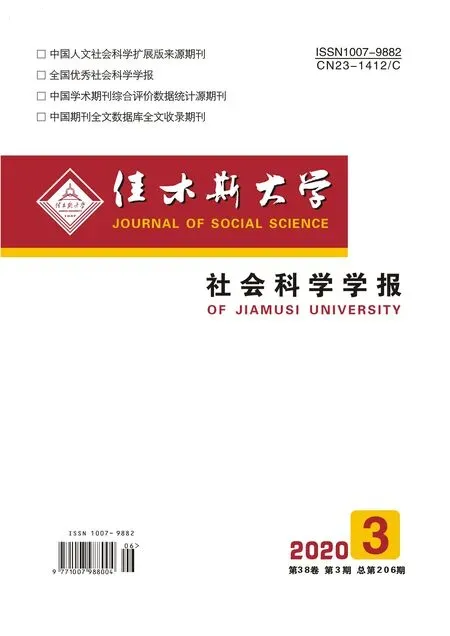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中农民人际关系与现代意识的互动*
2020-02-10廖斌
廖 斌
(福建武夷学院 中文系,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拉尔夫·尼科尔斯说: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理解和被理解。人是社会的群居动物,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人际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社会学将“人际关系”定义为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建立在个人情感基础上的相互联系,具有三重特性: (1)个体性。在人际关系中,角色退居到次要地位,而对方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人成为主要问题;(2)直接性。没有直接接触和交往就不会产生人际关系;(3) 情感性。人际关系的基础和主要成分是情感因素。[1]185
新时期以来鲜少单纯聚焦农民人际关系及嬗变的小说,众多评论也仅仅将农民“人际关系”置放在“乡村伦理”嬗变的宏大框架,从“道德沦丧”“伦理崩解”的视域加以价值判断,而忽略将其作为农民现实生活中最直接最真切的现代体验去考察,缺乏微观视角的解剖。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特性并不表现在宏观的‘中国经验’之上,而具体地体现在微观的‘中国体验’之上。‘中国体验’——在这个翻天覆地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2]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逐渐深入乡村,作为农民之于“现代体验”的一环和检验指标,无论是居乡农民或农民工,其人际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新时期小说《鲁班的子孙》(1983)具有先声意义地书写了由城返乡的小木匠黄秀川和贫弱的富宽大叔关系的转变:由亲昵的邻里、互帮互助的师徒转化为“虚假朋友”,实则是陌路人的关系。那么,1978年之后的40年间,农民的人际关系在现代性冲击下,究竟发生怎样的改变,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呈现其怎样的动力机制、变化特征,现代性与农民的体验结构彰显怎样的互动模式?本文就此做一梳理。
一
无论是文学抒写还是现实生活中,一直给人一个总体感受,就是在农村人情味浓重,农民热情质朴。费孝通认为,乡村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的基础是农民间的血缘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缔结的地缘关系,血缘和地缘关系是乡土中国人际关系的基石。[3]30农民之间基于乡村熟人社会的规范、共识和数百年儒家思想教化,逐渐发展出礼让互助、尊老爱幼、尚亲昵子、诚信友爱等人际关系原则,成为农民为人处世和人际交往的价值准则。正如许倬云指出,“地缘的土著和亲缘的结合,同一地点的乡亲住在一起久了就变成一家人,使得在土著之外也有亲缘上紧密的结合”[4]15,地缘和血缘的结合使农民形成稳固的共同体,形成所谓的“熟人社会”和“关系主义”。
新时期文学中,早期主流文本更多展示农民人际关系积极、温馨的面向。如赵本夫的《卖驴》(1981)写老实巴交的孙三作为脚力,风里来雨里去不辞辛劳为村民代办各种物品十数年,赢得了全村人的信任、感激;田中禾《五月》(1985)写香雨一家在村里是小姓,缺少劳力,在农忙时节众乡亲为她家“双抢”赶工,描绘了邻里互助和谐、一个好汉三个帮的美好场景;王润滋《内当家》(1981)写解放前在地主刘金贵家当奴婢、饱受欺凌的新槐妈,改革开放后捐弃前嫌深明大义,以大度平等的主人姿态迎接“海外归侨”的重要客人——昔日老东家刘金贵;邵振国《麦客》(1984)写雇主张根发的父亲知道雇工吴河东利用割麦的空档,偷盗了张根发的手表,临别之际却因怜悯吴河东的穷苦而为他遮掩。这类小说集中书写农民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处世哲学的美德。比如,孙三的诚信守义、新槐妈的以德报怨、张根发父亲的隐恶扬善等等,在在契合儒家传统思想教导。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虽然鲜少接受正规圣贤教育,说不出成套连篇的大道理,但“做人”——如何与他人交往,深受儒家思想教化,早已化做他的血脉精髓、精神财富而世代沿袭了。
《公路从门前过》(石定,1983年获奖小说)就写活了农村的人情美。王老汉的家建在公路边,随着交通条件改善和通车, 每天有两趟班车要从家门前经过, 附近村里的乡邻进城的、赶墟的, 都要到此候车。王老汉生活虽然刚刚宽裕些,“他想他正可以在这里为大家做点什么”。从此王老汉“生活又多了一样新鲜的内容” ——招呼客人。比如,免费为过路人提供饮食、遮风避雨。有一次车子在家门前出了故障, 王老汉招呼车上的人到家吃早饭, 几十个人摆了好几桌, 像大宴宾客一样, 一家人都齐刷刷上阵帮忙, 好吃好喝一阵招待。王家成为乡亲们的车站、歇脚点甚至是食堂。用王老汉质朴的实诚话, “他希望人们喜欢这个地方, 喜欢到这里来等车”。此外,迟子建《逝川》(1996)中,依据阿甲渔村旧有的传说,泪鱼沿江下来时,如果哪家没有捕到它,一定会遭受不幸。但在捕捉泪鱼的紧要关头,吉喜大妈舍弃机会去为当年弃她另娶的恋人胡会媳妇接生。吉喜接生后再赶到逝川,结果一条泪鱼也没捕到,失望之中却惊讶地发现她的木盆里竟跳跃着十几条泪鱼。在此,我们看到农民心灵的朴素善良、美好清纯,这种底层民众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令人感到温暖。在瑶族作家陈茂智《归隐者》(2012)中的香草溪是瑶族同胞聚居地,是一个和谐温馨、充满爱的伊甸园。在这片古老瑶寨里,人们彼此和谐相处、亲如一家,过着自由自在的原生态生活。无论“随便走到哪一个寨子,哪一户人家,不管认识与否,只要说一句香草溪,那都是亲人”,就连讨饭的叫花子到了香草溪都说香草溪好,舍不得走。
改革开放深化后,乡村加速现代化征程,经济建设等政策刺激了农民的致富欲望,激活了沉潜在农民身上的经济意识,自此,物质利益成为农民现代性追求的首要任务,乡村人际关系呈现出理性的特征,也催生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农民争得了土地的个人所有权,成为自家的主人,不必向任何人报账,这些都成为小经营者的骄傲和渴望,然而,他们却不得不为在自己的职业盛行的个人主义而哀叹”。[5] 98乡村出现了“理性经济人”。由此,金钱关系介入到农民的人际交往中,就逐步取代了人情的循环往复、预期回报,而转化为可以算计且便于结清。换而言之,原来混沌模糊的“人情”实现了价值换算,人际之间浮现和横亘了一个介质——金钱。自此,人情最初基于“亲密情感关系”的部分退居幕后,隐含的“契约思想”便格外地凸显出来。正是这种便于计量的介入,使得看似显得虚情假意、拖泥带水、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乡村人情,统统沾染了金钱气,变得精确量化和两不相欠与干净利落,人们不再担心不等价交换或者平白付出而吃亏,也不用虚与委蛇、遮遮掩掩而坦然大方地通过金钱“买断”。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将“礼尚往来”的人情,通过金钱报酬转化为一次性的短期行为,泯灭了各自的预期,弱化其中“感情”成分。这种新型人际原也开始渗透到家庭中,原来不分你我的一家从上阵还需父子兵的亲密无间逊位给了简单明了的雇佣关系,这一切都是以金钱作为度量衡的。
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四妹子》(1987)就悄然展现了代际的疏离:富有商业头脑、敢想敢干敢闯的四妹子在包产后搞起家禽养殖业,丈夫吕建峰开了个摩托车修理行,两个人生意忙不过来就聘请了公公吕克俭帮忙。吕克俭认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自己理所当然帮儿子媳妇分担一点工作,可四妹子却给他开了工资。父辈与子辈之间的血缘、亲缘转化为以金钱为中间物的雇佣关系。不管吕克俭最开始是否适应,是否觉得多么的“见外”和“不自然”,但金钱的介入使乡村一个传统的核心家庭成员由原生血缘关系转化为工作雇佣关系,排斥了其中的亲情,颠覆了原来的人伦定位。从此,功利化观念全面侵入乡村及农民家庭,以更加赤裸裸的方式展示它的面目,人们从你我不分的“一家人”的“混账”(账混在一起用)过渡到宁可“见外”,也要追求独立自主、人情减负的过程。今天,无论是文学和现实中,常常可以听到农民抱怨,“这年头,人情薄如纸”、“桥归桥路归路”、“各人只能顾各人”等等成为口头禅。这样的叹息与抱怨,表面是一种消极心态,实则是之于人际关系复杂难言的现代体验。这是农民现代人际观念“新传统”的构建和主体意识觉醒、成长的过程,农民也完全卸下了那份背负千年的“人情”包袱、淡漠了原本热热乎乎的人情。他们由“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和谐相与、平等相处发展到今天的“老死鲜少相往来”。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时,对人情与金钱关系有如下分析:“金钱是人情的离心力”。在金钱面前,人情荡然无存;之后他进一步谈到金钱——货币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时又指出:“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6]112
周克芹《邱家桥首户》(1982)中黄吉山老汉家所发生的一切,是改革开放发轫年代中国乡村家庭人际关系变迁——从 “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化的典型缩影。乡村致富能人黄吉山老汉精于算计,为确保家庭在县里继续当“冒尖户”,集全家之力“把家底子弄厚实点”,而枉顾亲情将算计的天平倾斜在子女身上:想方设法延迟女儿桂桂、香香的婚事,忽视儿子个人意愿,只想尽快招儿媳进门,抵消因女儿出嫁引起的劳动力损失。黄老汉心疼女儿出嫁,是因为 “我们家一笔收入,就流到他王家去了”;也因此,老汉娶儿媳的目的就是增加吃苦能干的强劳力,“只要人老实,勤快发狠”,而不是儿子的人生幸福。上行下效,黄吉山老汉的孩子们也各有打算:大女儿桂桂想早早出嫁重起炉灶,“伙起伙起有个什么意思,不如散了吧,各人展劲个人热和”;两个儿子荣荣、四娃“在家又吵又闹”,早想自立门户卯足劲来干,认为“这样统着,他们干得没劲,个人展劲个人热和”。在此,我们不无伤感地看到,经济利益促使这个主干家庭的成员各怀心思进而四分五裂。他们之间不仅感情淡漠,代际也日渐疏离了。李泽厚认为:“中国社会的生活实体现在正处于大改变之中,工业化、都市化、生活消费化带来的个人独立、平等竞争、选择自由、家庭变小、血缘纽带松弛、乡土观念削弱等状况,使人情淡薄,利益当先,数千年传统所依据的背景条件几乎全失,而且也使人情本身有了变化:不再是稳固的血缘亲情,而是不断变异着的个体关系之情逐渐占据主导。”[7]100
总之,就像《邱家桥首户》中的分田到户以及新世纪《出梁庄记》中梁庄的恒文因为雇佣的亲外甥离心离德而不得不将分店转手盘给他一样,1980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大到农村宏观政策,中到利益调整、乡村治理,小到家庭建设、农民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都离不开一个“分“字:分田、分配、分家、分离、分裂、分包、分手、分心、分神……,成为当代中国转型社会“无名”时代新的主题之一和鲜明特质,并延续到新世纪而变成农民人际关系的“常态”,也成了乡村人际交往的新鲜体验和总体趋势。
二
有学者认为,“‘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能动的,不是既定的而是建构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和活动的萎缩”,[8]25而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9]18。市场经济深化后,乡村经济发展使利益在人际交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农民人际受到影响,宗族家庭观念遭遇颠覆性冲击,农民的人际关系日渐出现人情淡漠的总体趋势,利益原则、效率至上、交换思想、保护隐私、尊重私权等“现代”观念占了上风,再加上农村大量人口外流,旧有的邻里守望、串门唠嗑、吃百家饭、村庄大众广泛参与的“公共舆论空间”等处于萎缩或消亡状态。外出打工的新生代农民融入城市后,人际交往也发生极大嬗变,二者催生了当下农民人际交往的“新传统”:人情淡漠化、家庭分离化、邻里利益化、代际疏离化、农民(外出务工)原子化和干群冲突化的样貌,读者可以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文本中发现其若隐若现的草蛇灰线。
李海清的《立秋》(1991)预言了这样的趋势。因为距离城市较远,村民们进城一般要搭乘顺顺的面包车。开始厚道的顺顺没有想到向沾亲带故的邻里、人情浓厚的乡亲收费,可是有一天顺顺突然含含糊糊地暗示乡亲们要花钱买票。虽然觉得难以接受,村民们在微微的不适应之后终于认可了买票乘车的“现代”规则与契约,并慢慢形成上车自觉主动买票的习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讲究的是交换逻辑、商品意识、互利原则,一切行为均可物化并化做商品出售,天下没有白乘的汽车,顺顺的“不经意”提醒和“天经地义”收费,显示出等价交换的商品意识对农民的虏获和旧思想的改造。与《公路从门前过》中的王老汉相比较,这样的嬗变不单是代际的,更是思想观念的。有学者认为,“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在农村的推进,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利益至上等意识不断向农村社会渗透,个人利益逐渐突破道德的约束,成为人们行为的唯一目的,利益也因此越来越成为决定村民关系的最大砝码,人际交往的功利性日益加重。”[10]
侯波的《胡不归》(2018)是当下农民人际关系的典型文本。小说描写陕北某乡镇世宁村的治理、文化建设的困境以及农民人际关系的淡漠与原子化。一方面,这几年村里村民几乎都脱贫致富了,很多人还在县城购置产业,小轿车也成了稀松平常的代步工具,然而村里的事务却无人问津。村里现在连个村长都没有。另一方面,“这村里都是些老虎豺狼黄鼠狼,个个鬼心眼,说人话不做人事。”挂点的乡镇领导评价说,这几年,农民赚到了钱,可是个个变得自私自利了,一些人对村集体漠不关心,装聋作哑;一些人等看笑话,幸灾乐祸;还有一些人,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家是非黑白不分,什么礼义廉耻、文明道德,统统弃之脑后了。一句话,乡村空心化、农民功利化的颓势难挽,曾经的“乡村共同体”趋于崩解,原来集体互助、邻里守望的人际交往冷却,家庭核心化、农民原子化是大势所趋。小说写到,世宁村虽然大部分村民都是“薛氏后裔”,但老一辈的宗族观念、家族亲缘关系慢慢被新生的逐利思想取代,人们开始抛弃这些“障碍”,撕下乡村熟人间、家族成员间过去惺惺相惜、相安无事的假面,为土地的流转大打出手、为多赚钱罔顾亲情乡情而收取高额水费等等,乡村再现了农民的阶层分化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争斗。
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人际冲突常见的是大户欺负小户,大姓挤压小姓,富人威逼穷人、干部鱼肉百姓的描绘。这种恃强凌弱势必激起马克斯.舍勒所谓的弱者对社会类似“一剂毒药”的“怨恨”情绪。舍勒提出了道德建构下的怨恨心理,即人心灵的一种现代性的社会体验结构才是怨恨情感的实质。怨恨是一种群众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它与社会道德、人际体验相联系,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共存的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在现代社会中,怨恨型人格的产生离不开社会环境,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攀比、盲从、不公平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平等的社会待遇而产生。[11]在世宁村中就不乏人际矛盾。秀兰嫁到薛家后早年丧夫,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艰难,在村里处于弱势。她不反省自己的自私自利和蛮横无理、心态偏狭,动辄将家庭不幸归咎于同姓人的“欺负”。不能上台参演,她发泄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合伙起来欺负我一个。当年,你祖上就欺负我娃他老爷了,趁我们家背运的时候把我家的地全买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落井下石!儿子上访闹事被追究,她说:我知道,这全村人都欺负我们哩。娃爷受欺负,大也受欺负,娃也受欺负,我们这家算是翻不过身了。丧失感、贫富分化加剧了农民的“怨恨”而进一步侵蚀乡村原本尚且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在现代转型社会,乡村因为阶层差异、利益纠纷等导致的人际冲突,越来越多地引发“弱者”的怨恨乃至报复。最极端的例子是胡学文的《马嘶岭血案》,向导兼挑夫将斧头挥向科考队员时,就是怨恨的积蓄与爆发,也间接表征了城乡关系、人际关系的持续恶化。
到了新世纪,荒湖的《谁动了我的茅坑》(2008)不仅直面乡村农民的人际冲突,还进一步蠡测了在此基础上的阶层分野及其趋势:花头与疤子多年邻居,早先关系不错,疤子建新房时,花头还“送了礼金和两个义务工”。疤子进城后发了财,于是想强占村里邻居花头家的茅坑宅基地建设车库,这理所当然遭到花头的反对。在红黑(村长和黑社会)两道的威逼下,最后以花头将茅坑的无偿交付而告终。但是,农二代的花头粗通文墨,见多识广,现代启蒙触发了他的某种阶级意识,他眼见前来相帮的堂哥临阵倒戈而训诫说:“我今天提醒你一声,你和我一样,都是这社会的穷人,穷人要站在穷人的一边,不要糊里糊涂地站错了位置……历次革命告诉我们,一个人站错了位置,到时候是要吃亏的!”——就是这样一个遭受黑恶势力和富人欺辱的花头,气急败坏地以“政治话语”对“穷人”进行范导,试图凝聚起“想象的共同体”,宣示他对“阶级压迫”的反抗。在读者看来,这样的“垂死挣扎”不仅没有显得滑稽古怪和小题大做,反而感到隐隐不安。花头虽然败给了邻里关系,但是,他以偷偷向疤子家里撒尿、摸疤子老婆的屁股的方式进行报复,这又令我们想起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想起了斯科特的著名论断:“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12]2如果说疤子对花头的压迫是有恃无恐的,那么《寻根团》(2011)里的邻里关系,就更令人齿冷心寒。在外工作的王六一回乡为父母扫墓,偶然发现用油漆画着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咒的木头橛子插在坟头上面。王六一知道,按老家楚州民间的说法,“那被钉的人家,却会家宅不安。”愤怒的他最后发现,下毒手的竟是王家一直以来无私帮助的马老倌,而马老倌的儿子马有贵外出打工患上职业病——肺矽病,在求告无门的困窘下,还是王六一利用记者身份向老板讨了20万元的补偿款。马老倌的“以邻为壑”不仅是乡村愚夫愚妇的封建迷信使然,也生动表征乡村邻里关系的种种乱象,令王六一“再次逃离”。
舍勒通过对质料价值伦理学的研究发现,现代社会之所以问题丛生,归根结底在于“价值的颠覆”,即价值秩序发生错乱和颠倒:自我获得的价值凌驾质性价值、生命价值逊位于实用价值,世俗价值超越神圣价值。[13]农民在当代转型社会所发生的人际关系的位移,就是典型的“价值秩序颠覆”——将一切人际交往定位为“有用”与“获得”。从前乡村的淳朴人情逊位给了今天的“实用”,亲情让渡给了金钱,理性战胜了情感,交付输给了交换。具体落实到农民对人际关系的考量上来,就是传统的人伦关系越来越被轻视,而主要聚焦于自我获得价值——以金钱为度量衡——的实现。在梁鸿的“非虚构小说”《出梁庄记》(2013),就呈现了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人际嬗变:
“我原来在金川那个点儿,可是我老婆的亲外甥在看着,来的时候啥也不会。是我一把手教他出来的。后来,又开分点的时候,就让他在那里管理,……可是他不给你说实话。去问他,总是说没活儿,…… 后来,想着管不住,算了,干脆几万块钱转给他算了。他可高兴,我找那地方是个好地儿。为这事儿,都犯过生涩。闹的矛盾可大,有的亲爹亲妈都不放心。”[14]107
与此相仿,《谁动了我的茅坑》里的疤子进城之后,随着人际交往的扩展和利益的共同体连接,不仅与村长这样的先赋性人际关系更加紧密了,又与城里的黑社会熟识起来,缔结成后致性利益联盟。相较之与花头的脆弱的“邻居”关系,在利益的权衡与冲突下,前述两种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就马上凸显出来。有专家指出,现代社会经过“祛魅”和“世俗化”后,货币及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成为社会的基本逻辑,生产和竞争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现代人自然形成了无所敬畏、敢于挑战 、乐于竞争的心性结构,这种心性结构使得人们在价值追求上过分看重感官价值和实用价值,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的追求。[13]而且在当下,数字媒体等权力技术所营建的人际鸿沟和脱域机制,进一步弱化和隔离了人们面对面的交流,使得新生代农民更多沉溺在网络空间中,科技进步与价值伦理颠覆的叠加效应,加速了农民在人际交往传统方面的嬗变——未来更多的“人际交往”或许就在虚拟空间里漫不经心、真假莫辨、虚与委蛇地进行。
三
丁帆指出:“乡土外延的边界在扩张,乡土文学的内涵也就相应的要扩到‘都市里的村庄’中去,城市中的‘移民文学’无论内容还是外延来说,都仍然是属于乡土文学范畴的。”[15]显然,这些“移民”就是由城入乡的农民,他们人际关系也发生着重大转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 不仅与自然发生联系, 人与人之间也会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活方式决定的”,而且“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显示出历史”。马克思还指出, 生产本身“是以人们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形式又是生产决定的”[16]34-25。在此,马列经典作家揭示了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人际关系及变化的科学规律。
1990年代后,改革开放日趋深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迥异于依土而生的农耕时代,其相对封闭的人际圈子解体,过去基于血亲、姻亲、地缘等方式缔结的人际交往弱化,而在城市工作地的交际网络随之扩展。换而言之,处于后乡土时代的农民人际关系出现“算计化”倾向,主要表现为: 人际交往的理性算计; 基于算计基础上的“自主塑造人际关系”。由于农民不能够选择出生,不得不在成长地遵循人际的“差序格局”,因此,他的初级人际圈是一出生就“给定”的,随着进城后现代意识的建立,他们尝试摆脱原有的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人际网络,自主选择并再造人际网络。就像《寻根团》里的王六一“逃离”烟村后,长期在东莞打工进而晋升到中产阶级、当上记者,他除与原工友马有贵还保持断续联系外,就在东莞发展了自己崭新、后致性的人际圈子——楚州籍同乡会,并跻身老板商人混迹的“新阶层”,返村后只与堂哥堂嫂相熟识。有学者指出,农民进城后“人群关系已由亲族的、地域的、阶级的取向,渐渐为职业的、兴趣的以及社区的取向所替代。”[17]70王六一的人际关系及变化,生动地表征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影响,并反过来还原了中国当代社会机制(户籍制度从严苛到松动)、社会结构(城乡关系从二元对立到双向互通)、社会形态(乡村文明迈入城市文明)三大方面转型的鲜活历史。
新世纪以来大量农民进城“蜗居”,他们接受现代化洗礼,现代意识的建立也带来人际关系的如下嬗变:一是进城谋生,村民间的联系松散化、淡漠化、表面化。传统乡村被滕尼斯称为“通体社会”: 它是“活生生的有机体”,表现为乡村中有实质上一致目标,人们为共同利益而共同劳动,把人们联结起来的是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家庭和邻居的纽带;特征是“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其成员由共同的语言和传统维系在一起;通体社会表现出“我们的”意识,在“通体社会里”,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这种“自然的”社会风俗、人伦关系支配一切。[18]103然而,随着农民规模大、时间长、流动快地在城务工,乡村“通体社会”崩解,旧有关系逐渐退场,农民更多的是被抛入城市的“联组社会”,他们的交往进一步扩大,人际网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梁鸿的《出梁庄记》关于“出”的抒写不仅是农民“出走”、进城打工的体验,更是在城市“联组社会”的“断零”体验。这个断,是斩断,割裂了所生活的故土,断了与乡村熟人乡亲的联系,像断线的风筝飞向遥不可知的时空。这种熟人间广泛“失联”的断零人际体验令人意外,也让人震惊:
梁鸿返乡想通过一个乡亲联系一下在广州一带打工的梁庄人。可是,一通电话打过去之后,只联系到三个人,另外两个手机已经是空号。随后在梁庄逗留的日子里,梁鸿逐户走访,打听电话号码,持续辗转联络,但是,进展缓慢,没有多大的效果。这分明生硬地提示着人们,出梁庄的打工者,早已淡漠了与家人、村庄的情感联系,彼此之间生疏而又隔膜。[14]9-10
二是农民的交往日趋选择性和理性化。所谓“理性化”是指社会个体: (1)明确意识到行动目的,且把所追求的具体目标作价值排列; (2)根据目的有比较地选择手段,以付出最小而收益最大为选择标准; (3)个人理性化是指,人们把以往由感情、个人魅力、个人信义、仁慈心、道德等支配的东西合理化。[19]也就是说,在传统乡村熟人领域,农民彼此之间知根知底、平日里互动频繁、联系热络、相互倚靠,村民间的感情是笃实、关系是密切的。但在利益面前,团结互助成为稀缺资源,脆弱的“兄弟情谊”①溃不成军,原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今天成为相互暗算。残雪的《民工团》中,往昔一起手胼足胝、共同打拼的工友们为了换取轻松的工作,争相讨好班组长,甚至不惜相互检举揭发,致血缘亲情于不顾。小说中的“我”对人我是非唯恐避之不及,只想专心做好自己分内事,却不由自主地陷入告密的旋涡。因为反抗或背弃告密这一潜规则,就意味着被惩罚、边缘化乃至被谋杀。作者以令人惊悚的笔触刻画出在以利益和交换为原则的现代社会冲击下乡村人际关系的变迁与异化。《出梁庄记》也不乏乡亲互相伤害、告密、拆台的类似例子:有打工的老乡偷拿厂里的东西,其他的老乡就给韩国老板打小报告邀功请赏,最后,老乡被老板开除了……。[14]267
我出来这么多年,能和内蒙古人打交道,不和老乡打交道,人家不算计你,咱们那儿人斗心眼。[14]116
梁庄在北京的“成功人士”李秀中以过来人的身份批评乡党之间的互相算计:河南人不抱群,只要有什么事,各奔东西,各找各妈。一个修水箱的老板跟我说,他手下有几个修水箱的河南人,争着说对方坏,后来没办法,只好都不让他们干了。[14]173
正是如此,在晚近的人际交往中,一方面,农民基于功利目的对先赋的血亲关系“选择性”大大增强。除了与家人关系较为紧密外,其他亲戚的交往深度并不遵从血缘的远近亲疏,而更多取决于对方在自己的发展需要中所能发挥的作用。[19]另一方面,因应流动性加大和个体需求增加,加之农民在乡村的先赋性关系先天不足,能量有限,受过现代教化的新生代农民无师自通地更注重“后致性”关系的建立,他们通过培养、维持和扩展的方式,将学缘、业缘等非亲缘关系中的朋友、同学、工友、生意伙伴等纳入自己的人际网络中。[19]这种自主建构的人际网络的重要性,远超泛泛之交的外围亲属,这种扩大社会网络为获得更多支持的主动选择生动地昭示了农民的现代体验与心性进步。
三是农民在城市中人际关系的隔离化。这就涉及到市民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刘庆邦的小说《我有好多朋友》(2013)是农民进城后人际关系的一个鲜明喻示。文本塑造了一个青年小保姆申小雪。申小雪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当保姆,虽与年纪相差无几的女主人以姐妹相称,但女主人内心并不认可她。她对主人宣称,自己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因此,作为一项工休权利,每到周末申小雪就必定外出一天和朋友们约会:去酒吧喝酒、去KTV唱歌、到天津吃狗不理包子、开车去品大闸蟹……,她的周末如此繁忙、时尚与热闹、充实,以致女主人都羡慕她交友甚广。但是,这却是申小雪的谎言。事实上,申小雪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她在北京举目无亲,那些所谓的朋友、激情四溢的城市化生活、娱乐完全是她杜撰的。其实她周末的打开方式是这样的:孤身一人在公园漫无目的逛荡,在地下招待所无所事事玩游戏,在平民扎堆、喧闹污浊的小餐馆里渴望邂逅……。她的人际关系建立在虚幻的想象和自欺欺人之中,或者说,申小雪全部的人际关系就是她自己,她终日与孤独为伴。标题“我有好多朋友”别有蕴意,毋宁说:我有好多孤独。小说折射了进城农民内心世界深刻的枯寂、凄清,也正面抒写进城农民逼仄促狭的人际空间以及进城“被隔离”后既希望拓展、被认同容纳,又不自觉地自我归类等诸多复杂暧昧的心理。社会学家图纳提出“自我分类”的社会身份理论。其意为,人们以某些社会分类的显著特征为基础,将自己和他人归于这些社会分类,这一过程使人们产生了某些特定的态度、情感和行为。他还提出“规范性匹配”的概念,意即某一社会分类中的成员的行为与该社会分类被期望或应该表现的行为相一致的程度。[20]332小说中,既然申小雪无法融入代表北京的主人阶层,作为农二代且深具“身份意识”的打工族——农民阶层,她只能逃避并靠编织“梦幻”来安抚自己孤独的心。可以说,她的“朋友梦”“城市梦”就是打工族这一社会分类阶层的特有表征或变形隐喻。她混迹的地下室、小酒馆、免费公园等,无不是与其相匹配的“底层”标签。显然,申小雪们虽然进城了,但他们的人际关系仍拘囿在所处阶层,其格局、广度、高度都难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有效拓展。
四是在城农民之人际关系情感与理性的二律悖反。在《出梁庄记》中,梁鸿有一个新“发现”,那就是进城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再造”和拓展——“扯秧子”,显示了亲情与“有用”相交织、感情与理性相排斥的新鲜、矛盾的过渡性状态,那既不是古老乡村农民质朴人际关系在城市的简单复制,也不完全是资本和利益操弄下,农民在城里的尔虞我诈和相爱相杀,而呈现出转型社会一种新样貌:合作中有竞争、亲情中有攻讦、矛盾中有调和、和谐中有算计、传帮带中有留一手、抱团互助中有彼此拆台、羡慕嫉妒恨中有瞧不起和打压……,这一切既是旧人际网络在城市的下载、更新,又是先赋性人际与后致性人际的排除、重组和叠加,他们不是旧式的商帮、会馆,也不是现代的商会、合作社、同乡会,却又浸润着亲情、义气、狭隘、计较、争斗。扯秧子,这一词语涵盖了黄光国所归纳的:情感性、工具性、混合性,[21]深具乡土气息和民间烟火味,也形象地说出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及相互交错的存在:就像禾苗在地里的生长,盘根错节、彼此连带、你中有我、顽强恣肆,富有草根性、自发性、坚韧性、复制性、前现代性。他们先是一人在城里立足,而后一个带一个,一家带一家,先后在城市安家,他们亲缘相通、业缘相近,形成远近亲疏不同的人际圈子和庞大关系网。一部《出梁庄记》就是农民在城市的“移民史”“奋斗史”“心灵史”。在这里,有变形的半熟人社会,这个半封闭又时时呈现出现代性的半新不旧的过渡性“乡村”小社会,这个既有“通体社会”特征,又有“联组社会”属性的“共同体”是农民在城市生存所要依赖的,又是他们“成功”后竭力摆脱的——去历史化的冲动。比如梁庄的朝侠在呼市安家立业,衣食无忧。可她成不了呼市人。她的朝思暮想、她关系的重心,仍是梁庄这一帮亲戚和老乡,虽然她时时嚷着要摆脱掉。在此,农民的思想呈现出情感与理性的悖反。又比如,梁庄年轻人向学的事业(开校传动轴修理店)、婚姻(老乡熟人介绍)、生活,大多倚靠在乡村形成的庞大的先赋性人际关系网络而成功。无论在哪儿,他还得仰仗他在吴镇的人脉。作为一个进城农民工他的人际网络必须通过自带的、旧有的社会关系完善。他仍然生活在“扯秧子”里,他与打工过的郑州、北京等城市鲜少交集。一句话,农民是与市民同处于城市世界、现代社会的二次元。“扯秧子”,扯出农民的人际小生态,作为城市中的低阶人际单元,梁庄农民利益结盟,保护自己地盘和业态并争夺新地盘;扯出那些被现代性、城市化所摒弃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扯出农民的人际经济学。这些生命力旺盛的梁庄“秧子”,发狠地在城市水泥地扎根,野蛮生长。
总之,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农民面临传统人情的压力,自身也经受感情与理性的煎熬,但理性最终战胜情感。与重人情、讲秩序的传统相比,他们的人际关系变化显示出现代特征,与其现代意识同行同构。张连义认为,传统农民的思想逐渐变化,传统人情和人际关系发生现代嬗变,经济和理性慢慢在思想占据第一要素。乡村经济发展一方面促进农村生产方式改变、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也使传统人情遭遇剧烈冲击,金钱逐渐取代人情获得支配地位,农民的现代转型显示出两面性。[22]306
四
刘庆邦《我们的村庄》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 2009年十佳中篇小说,《北大评刊》对它的现实意义有重点评价。笔者以为,正是它所具有的统摄能力和及物思想,为自身赢得褒扬。它蕴含三重“人际关系”:首先,它是乡土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当下乡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拖累者、漏斗户,需要再次被启蒙与振救。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抒写乡村竭尽全力追赶现代化的小说蔚为大观;现实中,建设新农村、乡村振兴等,都可视为这一关系的有力佐证。其次,它是城与乡的关系。“我们的村庄”预设了一个对镜:城市。文本的隐喻和强烈现实关怀直指在城市映衬下,乡村的凋敝与沦陷。小说有着见微知著和形而上的“表意的焦虑”。也就是说,主人公叶海阳实际上是一个符号:象征在“城市包围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及其子民深刻的孤独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心冲突与悬置状态、焦躁不安、无所适从。叶海阳的破坏欲、不甘寂寞、自暴自弃、占山为王等,不能仅看作是某个“村霸”的塑造,而是对农民在乡村沦落之际,畸形抵抗、自我放逐的隐喻式抒写。再次,它是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一篇新世纪的《阿Q正传》。流氓有产者、返乡恶棍叶海阳的“恶”:盗窃、敲诈、猥亵、忤逆、强奸、家暴、欺凌……,是以周边环境和所有人为敌的:众多村民、外来打工者、躲避计划生育的超生家庭、爷爷、母亲、妻子、沦为娼妓的本村弱女子……,所有这些都指向:乡土中国及其人际关系的解构。透过叶海阳在城市无处安置,在城乡之间的进退失据,以及由此产生的挫败感、怨恨、绝望、虚无和无处发泄,读者可以体会他的“恶”来自于“人际孤独”与被抛弃,这恰恰是他与生存环境对立着的衍生物。或许可以进一步推演,我们考察当下农民的人际关系嬗变,不能封闭自足于这个“果”,要从“我们的村庄”及叶海阳的喻示拓展开去,从现代性楔入、环境变迁、社会结构转型中去寻觅耦合因素,并报以“历史理解之同情”。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23]34这说明,蕴含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和群体意识是对人类社会文化生命的肯定和维系,而且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这种肯定和维系成为一种最根本的精神渴求。我们期待一方面处于旧有人际网络解构,另一方面在后致性人际关系建构中无所适从、摸爬滚打的农民以及叶海阳们能够圆融地在当代转型社会找到自己的“类和群”,更迫切希望在当下乡村加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得以真正融入城市文化与现代文明,找到维系的精神皈依和身份安顿,爱无等差地乐享属于自己的人际关系。
[注 释]
①本文借鉴“姐妹情谊”一词。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吉娜维斯认为“姐妹情谊”通常被理解为妇女在共同受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相依为命的一种关系。姐妹情谊在英美文学中有很深的传统,而倡导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理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