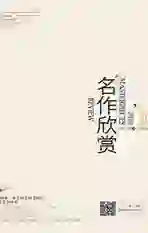唐宋时期陶诗的“重”与“赏”及诗分唐宋的延伸体现
2020-02-04周怡然
摘 要: 钱锺书先生论陶渊明诗的显晦问题时,举出并驳斥了蔡宽夫、李审言二人之观点,认为杜李韩三人并非不重陶渊明诗,但未详细展开。实际上杜李韩三人就像唐代众多诗人一样,并不是不重视陶诗,而是不懂欣赏陶诗。及至宋朝,宋人开始从更加多样的角度剖析品味陶诗,自然就能发现其生命力的丰富,故渊明文名,至宋而极。其实这本质上仍是诗分唐宋这一观点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陶诗 唐 宋 诗分唐宋
《谈艺录》二十四《陶渊明诗显晦》一文论述了陶诗在六代三唐时期的接受情况,虽然题为“显晦”,其实内容上更侧重于“晦”之时期。宋代以前,陶渊明之生平诗文多作为典故为后代诗人所用,至宋,正如全文开篇所言:渊明文名,至宋而极。
钱先生举蔡宽夫、李审言二人之观点,又添补定一:《有不为斋随笔》 卷壬亦谓太白、少陵、昌黎皆不重渊明。可见前人对陶诗显晦认识之态度:认为其在唐代即是不为人所重,唐人无知其奥,唐诗成就最高者杜甫、李白皆不重其诗,文章大家韩愈亦不重视。此说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正如钱先生所评:近似而未得实。
《谈艺录》第88页“陶潜避俗翁”一句出自杜甫《遣兴五首》其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a“枯槁”一语出自陶《饮酒诗》:“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b《杜诗详注》中言:“彭泽高节,可追鹿门。诗若有微词者,盖借陶集而翻其意,故为旷达以自遣耳,初非讥刺先贤也。”黄庭坚曰:“子美困于山川,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寄之渊明以解嘲耳。”c可知此句本意就非评议陶公出世避俗,只是借用典故抒发心中结郁而已。故“陶潜避俗翁”一句本身就不足以作为杜甫因陶渊明不加齿敍而不重之的证据。除此,杜诗中直接提及陶渊明处,还有《复愁十二首》:“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d也只化用典故而已,难以见得杜甫不重陶公。用陶公故事典故或诗文典故处则有许多,如“桃源”,有《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e《巫峡蔽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传语桃源客,人今出处同。”f此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有:“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g乃是化用陶公诗句“闲居三十载”,一作十三载。绩古逸业书景宋本配毛氏汲古阁本《杜工部集》、清乾隆五十七年阳湖九柏山房刻本《杜诗镜铨》及《杜工部草堂诗笺》《全唐诗》《杜诗详注》中皆为“三十载”,唯清卢元昌撰《杜诗阐》中认为作此诗时杜甫不到四十岁,故“三十载”应为“十三载”。诚然,杜甫自开元二十三年(735)参加进士考试到天宝六载(747)李林甫上表“野无遗贤”使无人入选,其间恰好为十三年。二说在情理上皆有可取之处,但更古早的版本皆作“三十载”,故以此为准。《醉时歌赠广文馆学士郑虔》 《五盘》《春日江村五首》等诗中皆可见陶公诗典,可见杜甫作诗常用陶令事,这点与李白相同。蔡梦弼《草堂诗话》卷一秦观评杜甫诗,言杜子美之诗,有陶潜阮籍诗冲淡之趣h,可知杜甫作诗,有陶公之风,又熟悉陶诗典故,其必精读陶诗,怎能说不重陶诗?司空图评价韩愈诗:“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i而《荐士》《秋怀》《晚菊》《南溪始泛》《江汉一首答孟郊》(即钱先生所言“江汉虽云广”一诗。“江汉虽云广”乃《江汉一首答孟郊》首句)较其他诗作冲和许多,尤其《南溪始泛》三首,其二平淡朴质最甚。蔡宽夫评《南溪始泛》云:“独为闲远,有渊明风气。”j可推测韩愈此诗潜移默化中受陶诗影响。可知钱先生所言具实。少陵、太白、昌黎三人不重渊明之语似是而非,但又似非而是。
为何说似非而是呢?少陵、太白、昌黎,乃唐代诗人,并非不重陶诗,而是“不赏”。唐人作诗常用渊明诗典事典,确是事实。论渊明之诗多空泛语,但唐代亦有效陶风气。沈德潜《说诗晬语》曰:“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k王、韦二人之诗钱先生已分析过,效陶诗最高境界当是不言效陶而神似,韦应物于唐贤中最有晋宋间格,其《与友生野炊效陶体》《效陶彭泽》二诗实得陶公冲和之气,刘克庄评《效陶彭泽》:“此真陶语,何必效也。”l《种瓜》一首不言效陶,但以农事为题,真实平易,于质朴之中见生活感悟,真神似陶语。言至于此,怎能说唐人不重陶诗?
钱先生《谈艺录》中有一句“虽道渊明,而未识其出类拔萃”m,可知时代时局对世人眼界的制约,唐人看渊明,识其隐逸而不识其豪气;识其淡泊而不识其风力;识其朴质而不识其丰腴;识其文拙而不识其炼字。《宋书·隐逸传》《晋书·隐逸传》具言陶公隐居之事、故唐人重其人而不重其文,将其视作古时隐者,诗文中每谈隐逸、田园、饮酒、重九、辞官、归隐之事,陶公典故,信手拈来,又不加研究其诗文情感,故多空泛语。诗中言及陶公其人,多美其志节;言及陶公其诗,与其志趣相投但未必真正理解陶诗,虽有效陶之作,数量毕竟稀少,佳作更是罕见,且多承其闲远恬淡之趣,于力量上还是不如陶公。钟嵘《诗品》推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唐人作田园生活、归隐之诗,偶效渊明亦是情理中事。陶诗之奥,唐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实乃时代所限。
反观宋人,颇能觉陶诗之高妙。欧阳修推《归去来兮辞》:“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n宋蔡正孙撰《诗林广记》,卷一即论陶渊明,朱文公云:“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沖淡之趣,不免局促于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o是对陶渊明诗艺上的肯定。 黄山谷云:“渊明之诗,所谓不烦繩削而自合者。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与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p可知渊明作诗并非如颜延之所云“文取指达”,而是于质朴无华之下,藏着琢磨考究、炼字推敲的功夫,但又不致让人轻易察觉到雕琢的痕迹,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陈后山云:“陶渊明之诗,写其胸中之妙。无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耳。”q刘后村云:“陶公如天地间之有醴泉庆云,是唯无岀,出则为祥瑞。且饶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8全然不似唐人评议陶公之诗。风评既转,宋人作文谈艺亦有所变。陈仁子撰《文选补遗》,增陶诗四十首,又添《感士不遇赋》《闲情赋》《祭程氏妹文》《祭仲弟文》《自祭文》,并附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
诗文如此,而宋人于平易质朴之中能见陶公丰富多情之处,较之唐人,亦是一大进步。例如苏轼评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仕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s,赞其真率;辛弃疾《贺新郎》“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t,若不是看出陶诗平淡自然之下流动的隐忧,怎在忧愁之际会联想到《停云》?此具为唐人所未见之处。自宋以后,陶诗解读之广之深,较之以往皆有所不同。归有光见陶公乐天安命之实,刘熙载赞陶公介拙高格,在宋人之境界上更高一层。
文人对渊明之诗的接受,何以实现由唐至宋之转变?钱先生在《谈艺录》开篇《诗分唐宋》中言:“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1所谓唐人、宋人于陶诗的接受理解,本质而言是性格相异两类人于陶诗的看法。故虽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 2,仍有王夫之、黄承吉、包世臣诸人不以为意;钟嵘并非宋人,《诗品》中,“陶公位列中品,但记室评其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推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何其高妙!”@ 3(钟嵘未选陶公入上品,却给如此盛赞,许是与时代格局有关,南北朝时人赏陶诗者凤毛麟角,记室不得不考量)评诗固然与各人之品鉴水准、品位喜好有关,但与古诗“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做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4亦有关联。唐时陶诗不被赏识,是主流文人诗人之性格喜好所致。并非唐人皆未识陶诗之奥,宋人皆识之,此处“唐”“宋”为品性之分,而非朝代之别;也并非唐人赏诗水准一定低于宋人,横看成岭侧成峰,是陶渊明诗内涵之丰富,境界之高远,使后人得以从各个角度品味琢磨,唐人所见陶诗一角,而宋人在前人基礎上更有新得,故陶诗初问世鲜有问津者,随时代变迁而逐渐得人赏识,推为一等。陶诗之显晦,可看作“诗分唐宋”说的又一例证。
acdefg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70页,第470页,第1438页,第115页,第1388页,第66页。
b 王叔岷 :《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0页。
h宋刻本《草堂诗话》卷一。
i四部丛刊景旧钞本《司空表圣文集》卷二。
j宋刻本《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七,古诗三十二首。
k清乾隆刻沈归愚诗文全集本《说时碎语》卷上。
l四部丛刊景旧钞本《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六。
m@ 1 @ 2 @ 3钱锺书:《谈艺录》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页。
n四部丛刊景宋巾箱本《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opq! 8蔡正孙:《诗林广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s请乾隆刻本《苕溪渔隐夜话全集》前集卷三。
t汲古阁影宋钞本《稼轩词》卷一。
@ 4明夷门广牍本《诗品》中。
参考文献:
[1]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卢佑诚.钱锺书的陶渊明接受史研究[J].皖西学院学报,2003(1).
作 者: 周怡然,上海大学文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