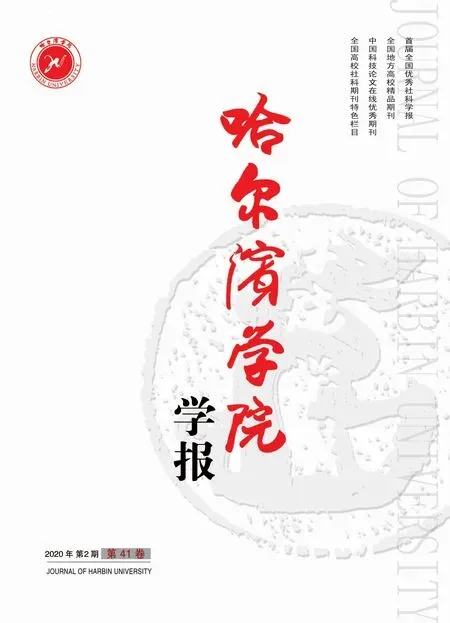金海陵王毁寺建陵原因探析
2020-01-19姜子强
姜子强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海陵王即为金朝海陵郡王完颜亮,字元功,本讳迪古乃,生于金天辅六年(1121),[1](P91)卒于正隆六年(1161),年四十。[1](117)完颜亮于皇统九年(1149)十二月通过政变即位,并改元为天德元年。[1](P93)海陵王即位后,于天德三年(1152)四月,下诏迁都燕京,[1](P97)并于贞元元年将燕京改为中都。[1](P97)迁都完成后,又于贞元三年(1155)三月:“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戊申,山陵礼成。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到正隆元年(1156)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群臣称贺。”[1](P104)在营建山陵时,海陵王将原来的大房山云峰寺平毁,在寺基之上修建祖宗陵寝,并在大殿佛像上凿穴来奉安祖宗神位。[2](P1751)中国古代王朝虽有营建皇陵的行为,但平毁佛寺来营建山陵,在历代都是绝无仅有的。海陵王完颜亮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其特定政治目的的,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一、海陵王毁寺建陵
海陵王完颜亮毁寺建陵一事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中引《金虏图经》中载:“虏人都上京,本无山陵,止迨于护国林之东,仪制初草创。迨亮徙燕,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岁余,方得良乡县西五十余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龙衔峰,冈峦秀拔,林木森密。至筑陵之处,亮寻毁其寺,遂迁祖宗、父、叔改葬于寺基之上,又将正殿元位佛像处凿穴,以奉安太祖旻、太宗晟、父德宗宗干,其余各处随昭穆序焉。唯亶被杀,葬于山阴,谓其邢余之人不入。”[2](P1751)可以看出,金初本无山陵之制,在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先将国都由上京迁至燕京,后又改为中都。在迁都完成后,着手进行营建山陵的工程,命司天台在燕山周围卜选陵址,找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找到大房山这一处“冈峦秀拔,林木森密”之地。陵址选好后,完颜亮于贞元三年毁寺营建山陵,将太祖、太宗、德宗并排葬在寺基之上,其后又在主殿的元位佛像凿穴来奉安太祖、太宗和德宗神位,而金熙宗完颜亶因其为“邢余之人”未被葬入金陵中,而是被葬在了山阴之地。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引《金虏图经》的作者为张棣。据《直斋书录解题》载:“承奉郎张棣,为淳熙中归明人,记金国事颇详。”[3]关于张棣归宋时间目前有几种说法: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认为张棣是在宋淳熙时(1174—1189)归宋,即对应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174—1189);[4]刘浦江先生认为张棣很可能是在淳熙末,即大定二十九年(1187)自金奔宋的;[5]孙建权认为张棣归宋的时间在绍熙中(1190—1194)而非淳熙中归明人。[6]由上可知,张棣由金奔宋的时间上限在公元1174年,下限在公元1194年。而海陵王完颜亮毁寺建陵的时间在贞元三年(1155),说明早在张棣归宋之前,金陵已经修建完成。《三朝北盟会编》中载张棣为金朝官吏,后归宋朝。张棣在金朝为官,建陵又在这期间,因此张棣对于毁寺建陵一事应了解,说明《金虏图经》中对于完颜亮毁寺建陵的记载是比较可信的。至于文中将大房山误作大洪山应是传误,因为早在北魏时已有大房山之名称,据《魏书》中记载:“良乡二汉属涿,晋属范阳,后属。治良乡城。有大房山神”。[7]在《金史》中亦为大房山,说明由北魏至金一直为大房山并未改名。
完颜亮毁寺建陵也被考古发掘所证明。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发掘中,先后发现了M6、M7、M8、M9,其中科学发掘清理了M6。它位于九龙山主峰下,地宫形制为石圹竖穴,四壁为岩石,无墓道。地宫内瘗葬4具石椁,编号分别为M-1、M-2、M-3、M-4,其中M-4龙纹石棺被人为砸毁成碎片,残留东侧椁壁,外壁雕刻云团龙纹,其余三个石椁均保留完整。龙纹石椁的破坏正与文献的记载相对应,因此可以推定M6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睿陵,[8](P153)并以此推定M7为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恭陵,[8](P154)M8为金德宗完颜宗干顺陵,[8](P154)M9金世宗完颜雍兴陵。[8](P157)在太祖陵东南第四台地,西距金世宗墓室70米处探测出一处长6米、宽5米、深6.5米的疑为一处墓葬,并按昭穆制度推测,此处应是金睿宗完颜宗尧景陵。[8](P156)现存的金陵陵墙将太祖睿陵、太宗兴陵、德宗顺陵三陵围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三座帝陵并排且三陵之间相距仅1.5米左右,与文献中海陵王将太祖、太宗、德宗并排葬在寺基之上的记载相符,[8](P164)因此可以推断海陵王完颜亮确实是毁掉寺庙来营建祖宗陵寝。
二、毁寺建陵之原因
对于完颜亮毁寺建陵的原因目前在学界有多种看法。王德恒先生认为海陵王完颜亮平毁寺院,在寺基之上修建祖宗陵墓,此事可看出他藐视一切陈规陋习我行我素的风格。[9]阎崇东先生则认为寺庙是所谓有“风水”的地方,而云峰寺正好建在这样一个风水宝地。于是完颜亮便“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10]都兴智先生则认为这是完颜亮对佛教实质有着精辟透彻的理解,他不信佛,毁寺建陵是他限制佛教的一种表现。[11]因此,影响完颜亮毁寺建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王德恒先生将基归结于完颜亮个人的性格;阎崇东先生则认为风水是主要原因;而都兴智先生则认为这是完颜亮限制佛教的一种表现。笔者对都兴智先生的看法十分赞同,只是完颜亮毁寺建陵除了限制佛教外,他还想有加强君权的目的。
营建山陵之前的贞元三年,“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1](P103)此事在《金史·张通古传》中的记载更为详细:“会磁州僧法宝欲去,张浩、张晖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闻其事,诏三品以上官上殿,责之曰:‘闻卿等每到寺,僧法宝正坐,卿等皆坐其侧,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国王子,能轻舍富责,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僧,较其贵贱,未可与簿尉抗礼。闾阎老妇,迫于死期,多归信之。卿等位为宰辅,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张司徒老成旧人,三教该通,足为仪表,何不师之’召法宝谓之曰:‘汝既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宝战惧,不知所为。海陵曰:‘汝为长老,当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张浩、张晖杖二十。”[1](P1861)可以看出,完颜亮对此事极为在意,为此还诏令三品以上官员上殿加以警示。从海陵王杖张浩、张晖和僧宝的原因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以刘浦江先生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完颜亮这么做是有意贬低僧侣的地位,同时达到限制佛教教团的目的;[12]第二,王德朋先生认为,在官吏与僧侣相处之中,僧侣居正坐,大臣坐在侧面,这种现象颠倒了本来该有的礼制关系,从而使海陵极度不满。从表面看,海陵所杖责的是法宝、张浩和张晖的肉体,实际上,他是想维护君权至上的政治理念,[13]这也是其诏令三品以上官员上殿的原因。二位先生所言都极有道理,且并不相矛盾。海陵王正是通过有意贬低僧侣地位、限制佛教教团,以此来达到维护君权至上理念的目的。这是因为辽代对于佛教的态度非常虔诚,“帝后见像设皆焚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14](P31)辽代僧侣之显贵者,甚至可以与帝王分庭抗礼。[12]海陵王借此事,小题大做,借机削弱僧侣的地位,其想改变辽代以来僧侣尊贵的地位,来加强君权。此事件与海陵王毁寺建陵仅隔几天的时间,因此据笔者推测,这一事件应是海陵王毁寺建陵的诱因。
海陵王将祖宗陵墓建在寺基之上,可以看作是将崇祖凌驾于崇佛之上。这是因为在辽代,崇祖与崇佛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重合,这是辽代契丹文化的一个特点。[15](P43)为了适应统治需要,辽代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积极接受佛教在契丹社会的广泛传播,逐渐使契丹部落联盟时期的神权与皇权的分离状态合流并集于一体,实现了利用宗教构建皇权和巩固皇权的目的。[16]据《辽史》载:“太祖在幸幽州大悲阁时,迁白衣观音像,建庙于木叶山,尊为家神。”[17](P835)在辽太祖时,尊白衣观音为家神,白衣观音庙就具有家庙的性质了。[15](P43)辽道宗于清宁八年(1062),在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17](P506)可以看出,在辽代崇祖与崇佛不仅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合,甚至崇佛可以与崇祖相平等。祖神可以看作是君权的代表,佛则是佛教教权的代表,崇佛与崇祖相平等,导致辽代教权甚至可与君权分庭抗礼。海陵王为了削弱佛教地位,加强君权,故将崇祖凌驾于崇佛之上,使君权的地位远远高于教权的地位,以此来彰显君权的至高无上。正隆元年十一月,海陵王下令“禁二月八日迎佛”,[1](P107)又在正隆二年十月拆毁上京储庆寺。[1](P108)可见,为打击佛教势力,海陵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毁寺建陵可以看作是削弱佛教势力、加强君权的系列举措之一。
海陵王之所以这么做是吸取“辽以释废”的教训。从金末元初,一直以来都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18]的说法,刘浦江先生对辽朝佛教全面考察后,认为“辽以释废”的结论大致可以接受,并提出无节制的崇佛佞佛是辽灭亡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12]由于建国前的女真曾被辽朝长期统治,因此,辽朝崇佛之风不免对金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但金朝除了受到辽代崇佛的影响外,还吸收了辽代因崇佛而亡的教训。所以,为避免重蹈“辽以释废”的覆辙,金对佛教采取限制与利用相结合的做法,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君权,从而巩固金王朝的统治。海陵王即位后,虽然也是对佛教利用与限制结合,但海陵一朝对佛教的限制始终多于利用,而毁寺建陵恰可以看作是其通过限制佛教来加强君权政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