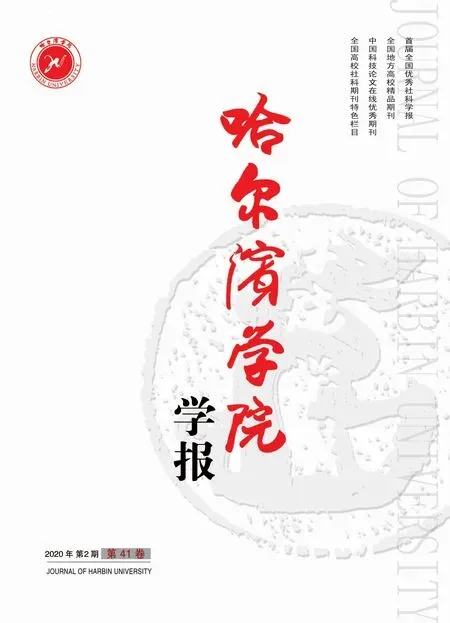唐人对唐朝东征高句丽起因的认识及态度
——由西安新出《焦海智墓志》所见
2020-01-19单敏
单 敏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近年来,在西安发掘出较多与东征有关的墓志,《焦海智墓志》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于2011年藏于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志高八六、宽八六点五、厚一二点五厘米,铭文三六行,行三八字,楷书,四侧蔓草纹。盝顶盖,盖高八六、宽八六、厚九厘米,铭文三行、行三行,阳刻篆书,四杀蔓草纹饰。”[1]利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代墓志简要介绍该墓志中可补折冲府的双池府、丰谷府、义安府,为研究唐折冲府提供了新材料,此外并未见其他学者加以详细论述。志主焦海智历经太宗、高宗两朝,两次参与征辽,后卷入高宗朝权力之争,因之以升降沉浮,历经荣辱。因志主是唐中下层将士,从墓志中可以透析唐人对当时征高句丽的原因认识以及当时的东征态度。
一、关于墓主家族世系源流
曾祖建,即焦建,又名独如建,墓志云“周闵帝初赐姓独如氏”,《周书》所见,周时文武百官赐姓者众多,其中“宇文氏”和“拓跋氏”最多,但唯独赐姓“独如氏”缺载,笔者怀疑是“豆卢”的另一种翻译。实封为“益昌县开国公”,益昌县在隋唐时期属山南道利州,地处利州西南部,相距45里。另分封为县开国公,属于郡县开国公、侯、伯、子、男九等之列,并无官土。开国县公属从二品高官,理论上食邑一千五百户,但墓志中并无实封户数的记载,根据焦建勋官很高的级别及周闵帝赐姓,猜测理应是实封之地。
“祖长卿,隋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海州刺史,海州诸军事,上柱国,袭封益昌县开国公,加上大将军。”子承父爵,袭封益昌县开国公。祖辈焦长卿实封为海州刺史及海州诸军事。海州又名东海郡,“梁改东海郡为北海郡,武帝末年,大江以北,并附于魏,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为海州,移理于旧州南龙沮故城。隋开皇三年自琅邪城移州于今理(朐山县),大业三年罢州为郡。唐武德四年,臧君相以郡归顺,复为海州,置总管府,领海、涟、环、东楚四州,海州领朐山、龙沮、新乐、曲阳、沭阳、厚丘、怀仁、利城、东海九县。”[2](P564)由上可知,海州在武定七年(549)到大业三年(607)之间和武德四年(621)之后称为海州。607年以后隋炀帝改州为郡,“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西北至东京一千四百六十里。西北至西京一千八百八十五里。西北至长安二千七百四十五里”。[3](P456-457)隶属河南道的海州位于长安、洛阳的东南偏东方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江苏交界地带,属于沿海地区。隋朝581年至607年称之为海州,通过检索资料,正史中只有淮安王神通之父李亮和房恭懿曾任隋朝的海州刺史,隋朝曾在北齐秘书省任职的阳玠考证“以任用尉迟迥之党房恭懿一事,以谋取私惠、暗结朋党罪名被劾除名,卒于家。时薛道衡为吏部侍郎,也流配岭南。”[4](P119)本条事当在开皇九年(589)左右。李亮在新旧唐书无传,只知其在唐初被追封为郑王,因此海州刺史也应是死后追封。结合这两点,加之祖焦长卿隋初复姓焦氏,可知焦长卿在隋初依然健在,可以推测,其在房恭懿之前担任过海州刺史。如果淮安王父李亮确实担任过海州刺史,那么这三者的任职次序应该为李亮、焦长卿、房恭懿。
“父儒彦,皇朝任左十府车骑将军,寻授左武卫丰谷府右别将、上骑都尉,以益昌之第四子别封括苍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焦儒彦任官左武卫丰谷府右别将,受封括苍县开国男,括苍县在江南东道的东部地区,在今浙江省境内。武德四年(621)置括州领括苍县,直到天宝年间才改名为缙云郡,期间丽水县、永嘉县和安固县并入,使其地域扩大。
墓主焦海智夫人是南阳张氏。南阳城在河南道陈州宛丘县境内,在县东三十里。焦海智死后其夫人被封为正平县君,笔者查找资料发现《大唐故正议大夫使持节延州诸军使延州刺史上柱国宋府君墓志铭并序》[5](P272)宋讳祯的夫人河东薛氏也被封为正平县君。二者都是夫君死后被封为正平县君,因此并非实封。另外,根据墓志还了解到焦海智有一子名焦思庆,但遗憾的是除此之外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
二、墓主生平
墓主焦海智,字巨源,在两唐书中均无传所载。卒于高祖永隆二年(681),春秋七十二,因此可以推测其出生于隋大业六年(610),历经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祖、唐高宗五代。“陇西南安人”,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渭州陇西郡,中都督府。县四。襄武,上。陇西,上。鄣,下。渭源。上。”[6](P1041)即陇右道渭州陇西县人,陇西县位于渭州东部,位于渭水之上,与今日陇西相比处于东南的位置。
由上可知,墓主焦海智出身于武将世族,受家族影响,焦海智年十八参军,即贞观二年(628)左右,最初被授予太子左卫率翊卫。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后,唐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于李世民,十月李世民立李承乾为太子。后贞观十七年(643)废皇太子李承乾为庶人,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在此期间东宫多次易主,隶属于太子左卫率府领的翊府即内府,“左右卫率掌东宫兵仗羽卫之政令,总诸曹之事”,[7](P1911-1912)实际上负责太子东宫的兵仗护卫等事务。可知焦海智任职东宫十七年,品级并不高,但一开始就能进入内府想必与祖父辈门荫有关。
贞观十八年(644)出征高句丽,次年二月跟随唐太宗与高句丽在驻跸山一战。此战是安市城之战的先锋战役,参与此次战役的人数是唐军攻打安市城总兵力的数倍,正史中所载驻跸阵一战较为简略且很顺利,实则是唐军难以抵抗辽东酷寒,斩首四万余级后还朝。“太宗之破高句丽,名所战六山为驻跸,播谓人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跸,此盖以銮舆不复更东矣。”[7](P4954)太宗将山名更改为“驻跸”,也从此战认识到东征之艰难。这一战唐朝当时未胜,但回朝后太宗册封了许多勋官,而志主焦海智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封为“上骑都尉”,但封官级别不算较高。高宗时随辽东道总管契苾何力再次征伐高句丽。龙朔元年(661)“夏五月丙申,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尙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卫江道大总管,以伐高句丽。”[7](P81-82)契苾何力的部队在鸭绿江一带受到泉盖苏文之子泉男生军队的顽强抵抗,又遭遇气温骤然下降的恶劣天气,不得不辗转回朝。高句丽再次得以绝处逢生。此战没有明确的唐胜高败,但是归朝后焦海智被封为“上轻车都尉”,八转,视正四品,连升两级。这两次征战后的册封或许是朝廷体谅将士征东之不易,同时也达到鼓舞军心的目的。
起初焦海智被封为周王府右帐内典军,周王即中宗李显,显庆二年(657)被封为周王,授洛阳牧。仪凤二年(677)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因此,可以推断焦海智可能在662年至677年担任右帐内典军,又改授沛王府左帐内典军等职,期间散勋官不断升迁。但是武则天与李贤不睦,调露二年(680)即永隆元年武则天亲信明崇俨被杀,武则天怀疑是李贤所为,于是派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揭发李贤谋反,在东宫搜得铠甲数百件,于是李贤被废为庶人,遭到幽闭。主降臣迁,沛王府官吏受到牵连,焦海智也不例外,被贬为左骁卫安州都督义安府左果毅都尉。安州属淮南道,在今湖北省境内。在义安府任左果毅都尉期间,焦海智宽猛合度,深得士兵的敬佩。永隆二年(681)送兵南邓,检索有关地理志,并无发现“南邓”这一地名,因此笔者猜测应该是“相对于长安洛阳靠南的邓州”的缩写或者是因为原先叫“南阳郡”而书写为“南邓”。邓州属山南道,“西北至上都九百五十里。北至东都六百四十五里。”[2](P532)邓州作为古代的军事要地,应该是当时军事储备的重要地点,因此才会送兵到邓州,但是正史中并没有看到相关信息。
志主焦海智最初从军仅为正八品上的太子左卫率翊卫,沛王被立为太子后,职事官等级达到顶峰,为正四品上的右监门率,沛王与武则天发生冲突后,主降臣迁,至少连降三级成为折冲府的左果毅都尉。唐代勋官是按战功大小而授,从墓志看,焦海智跟随唐太宗破驻跸之后被授予上骑都尉,跟随契苾何力破鸭绿江后授予上轻车都尉,并非滥授。但由于沛王之事受到牵连被贬,其晚年较为凄惨。
三、墓志中所反映的问题
1.墓志所见唐代折冲府补考
对折冲府记载最为详细且时间最早者当属《新唐书·地理志》,但其中错讹、失载者亦不在少数。关于唐代折冲府数目的记载。《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均作594,《通典·州郡》作593,《新唐书·兵志》作634,《新唐书旧唐书·职官志百官志》与《唐会要》均作633。关于记载数目差异的考订,谷霁光和岑仲勉[8-10]等做过相关考证。唐长孺在《唐书兵志笺正》中所言:“盖军府初无一定之成数,而其废置,又因细碎,史所不载,故无以确知其数。”因此,近年来通过对墓志研究,新补及新证了一些折冲府。就该墓志来讲,新补折冲府二,新证折冲府一。唐前期国家实行府兵制,府兵由各军府掌管,分别隶属于十六卫和十率府。其中军府分为内府和外府,内府包括亲府一、勋府二、翊府二,外府就是折冲府。墓志称墓主“乃除左骁卫安州都督义安府左果毅都尉”,“义安府”在《新唐书·地理志》有载:“安州安陆郡,中都督府。县六:有府一,曰义安。安陆、云梦、孝昌、应城、吉阳、应山。”[6](P1055)安州在淮南道,在今湖北省境内。由墓志可知,义安府隶左骁卫掌管,但治所所在地缺载。
墓主在龙朔元年被授予“左屯卫隰州双池府左果毅都尉”。“隰州”,属河东道,“西南取慈州路至上都八百八十五里。东南至东都八百八十里”,[2](P345)在今山西省境内。下辖六县:隰川、蒲、大宁、温泉、永和、石楼,州境内缺载双池府,可补史缺,但不知其治所在何处,只知其隶属左屯卫。
丰谷府,“父儒彦,皇朝任左十府车骑将军,寻授左武卫丰谷府右别将”,丰谷府并不见于史书,但是从《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二》“沣水”条有:“沣水,府西三十里。出鄠县南山谷中。汉志注云:‘源出秦岭,西北经子午谷,又得丰谷口水,故名焉’;张楫曰:‘沣水出鄠南山丰谷也,东北流经故长安城西,又北至咸阳县境入渭’。”[11](P2521-2522)可知,鄠南山有丰谷,是沣水流经的地方,因此笔者猜测丰谷周边或许有丰谷府的存在。另外,在墓志中左武卫之后不加属于何州的丰谷府,其他出现的义安府和双池府都能看到所属州郡,因此极有可能就是在长安附近的地区。
2.唐人对唐征高句丽的起因的认识及态度
目前,关于唐征高句丽起因的成果已很丰硕,刘进宝认为是唐朝与高句丽之间的政治冲突,唐朝欲统一中原王朝,但高句丽始终横亘其中,阻止统一;祝立业认为唐朝欲恢复旧疆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解如智认为唐朝要夺取辽东,制服高句丽,进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是其真正目的;李德山认为拯救新罗,稳定朝鲜半岛局势才是太宗义无反顾东征的原因;张暾认为高句丽企图联合百济征伐新罗,这与唐朝试图构建东亚秩序是相违背的,高句丽与百济的勾结无疑是对以唐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严重威胁,这是征伐高句丽以及其后伐百济的主要原因;刘琴丽整理唐初碑志,从士人角度罗列士人对唐与高句丽战因的认识,给予作者很大启发,[12-17]以其搜集整理的碑志为基础,结合新出焦海智墓志进一步探析唐人对唐征高句丽起因的认识,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对唐朝的认识,以及唐人对历史的选择性认识。
首先,唐人认为朝鲜半岛内乱,高句丽违背唐朝命令同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是引起唐朝征伐高句丽的主要原因。《焦海智墓志》:“至贞观十八年(644),以鳌峰窃抃,鳀壑潜游,暂举青丘之缴,遽肃玄夷之丑。”“鳌峰窃抃、鳀壑潜游、玄夷之丑”当是指高句丽借助地理位置优势,与百济联手征伐新罗,唐太宗出征则是为了肃清朝鲜半岛的内乱。这与“玄夷之孽”“偷安缇壑”“玄夷背诞”“鲸海扬波、鼇峰恃险”这些用语同墓志中的很多字眼多有重合基本相同,都对唐朝出兵有统一而简要的说明。张士贵的墓志说明则相对具体,“洎朱蒙之绪,背诞丸都,枭镜辽海。王师底伐,属想人雄”。以上皆在阐述高句丽进攻新罗一事,而非泉盖苏文篡夺高句丽王政权之事。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泉盖苏文弑杀对唐有妥协之心的建武王,立高臧为王,专事国政。亳州刺史裴行庄因之请唐太宗征高句丽,太宗答:“因丧趁乱而取之,虽得不贵,且山东凋敝,吾未用兵也”,[18](P6181)可知太宗并未因高句丽内乱而生征高句丽之意,甚至在十七年(643)遣使册封高臧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承认泉盖苏文扶植的傀儡政权。贞观十七年百济义慈王“与高句丽和亲通好,谋欲取新罗党项城,以绝入朝之路”。[18](P5330)如果放任高句丽与百济进攻新罗,唐朝将失去新罗这个重要的同盟,破坏唐朝试图在朝鲜半岛构建的政权平衡秩序,并且还会对唐朝边境构成威胁,埋下隐患。于是命相里玄奖赐书高句丽王“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戟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18](P6204)对高句丽与百济下达最后通牒,若不收兵,来年将兵戈相见。但次年泉盖苏文又率兵攻新罗二城,表示隋时新罗乘衅曾攻高句丽,恐怕不得不攻伐新罗,公开与唐朝对抗,相里玄奖归国后具言其状,唐太宗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18](P6207)于是决定将亲征高句丽。由上可知,促使唐太宗下决心攻伐高句丽的原因是高句丽作为唐藩属国,不听从唐的劝告,执意进攻邻国新罗。从以上墓志用语可知,当时社会有部分士人甚至是社会舆论都站在政府角度,认为唐征伐新罗是正义之举,是为了肃清“玄夷之丑”,维护以唐为中心的天下一统秩序,为了“江干御侮”,维护唐朝的大国尊严。
《焦海智墓志》中墓志主随契苾何力第二次东征高句丽的原因是“复以海若未宾,黏蝉再扰”。撰碑志者用“三韩作逆,九种不宾”“据鲸海而不宾,恃鳌山而缺贡”“属九夷齐礼,楛矢不朝”“狼顾青丘之塞,鸱张碧海之滨”“属海夷未宾,王师备警”“辽东未宾”等语句来阐述唐朝征伐高句丽的原因,即认为高句丽对唐朝“不朝”“不贡”“不宾”是唐出兵的原因。作为唐附属国却不尽藩属国之职,不事朝贡,损害到唐朝的大国尊严。但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属实。唐建立之初武德四年(621),“乙丑,高句丽王建武遣使入贡”;[18](P5923)武德七年(624),“丁未,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18](P5976)贞观十六年(642),太宗拒绝裴行庄出征高句丽时,太宗曰:“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18](P6181)皆可证明高句丽并未不朝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黏蝉再扰”当是说永徽五年(654)“高丽遣其将安固将高丽、靺鞨兵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大败高丽于新城。”[18](P6282)次年,“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刺史都督程民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击高丽。”[18](P6287)高句丽不仅再次与百济联手侵伐新罗,还试图侵入辽东地区,这直接促使唐高宗把征伐高句丽提上议程。因为高句丽的行动不仅再次影响到朝鲜半岛均衡局势,甚至将影响唐朝对东北边境的管理,直接威胁到唐朝大一统的局面。从司马博陵阎慎从撰写《焦海智墓志》可知,当时一部分士人认为高宗朝东征高句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高句丽不事朝贡,二是再次联手其他国家引起朝鲜半岛内乱甚至将爪牙伸向唐朝的东北边境,同样是从唐朝的立场出发去说明东征的原因。因此可以看到士人对于唐朝东征的合理性、正义性的支持,以及唐征高句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黏蝉”“高丽小丑”“玄夷之丑”也能说明当时社会对高句丽带有仇视的情绪和负面态度。这可能是由于自隋以来,为征伐高句丽,隋唐国内征伐大量士兵,然而对东北恶劣气候的不适应、高句丽地区易守难攻之势的影响,死伤无数,增加了国内不安定因素,加重了社会上对高句丽的仇视。另外,贞观五年(631),唐“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时战亡骸骨,毁当时所立京观”,[18](P6169)此京观是积隋尸二而成,高句丽对隋战士极为不尊的表现及狂妄自大的态度或许使唐人愈加憎恨高句丽。
四、结语
通过对《焦海智墓志》梳理与分析可知,焦海智家族世代为武将,焦海智半生辉煌、半生因为政治局势变动受牵连贬官,任安州都督义安府左果毅都尉期间因送兵南邓而遇难。从此墓志以及唐初其他东征将士的墓志可以看出,唐人从朝廷的立场出发,认为唐东征高句丽正义而合理的,甚至以战死沙场为荣,同时从墓志措辞窥探出唐人仇视高句丽、对高句丽持负面态度,说明唐东征高句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正史中唐人对征高句丽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