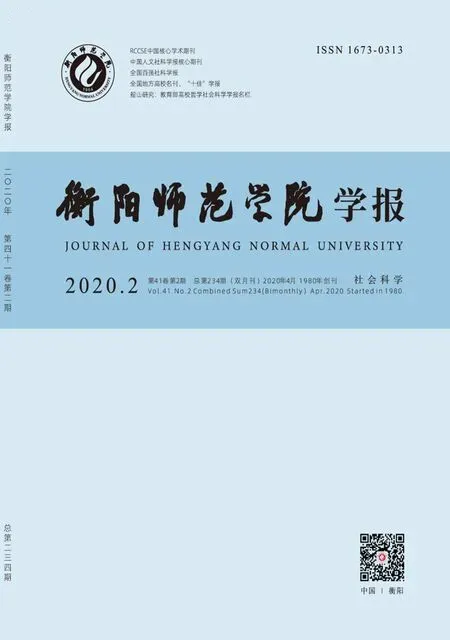试论张惠言礼学的精神向度与历史意义
2020-01-19吴戬
吴 戬
(衡阳师范学院 船山学基地,湖南 衡阳 421002)
张惠言是清代文化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才学俱佳,贡献多元,在诗、词、散文、辞赋的创作上造诣非凡,开创了对清代文坛影响深远的常州词派、阳湖文派。此外,他在经学领域亦有惊人表现,尤以《易》学、礼学饮誉学界。《清史稿》本传称其:“生平精思绝人,尝从歙金榜问,故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易》《礼》。”[1]13242其对虞氏易的系统研究填补了学界空白,被阮元许为专家孤学,在清代易学史上举足轻重。张惠言《读仪礼记》对《仪礼》进行训诂性解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捕捉文本的真实,其中《仪礼图》对《仪礼》图表式的诠释,再现了仪礼的空间感与过程性,而《原治》《吏难》等篇章融《礼记》的义理阐释与《周礼》的制度设计于一炉,彰显出浓郁的社会关怀。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多瞩目于张惠言的词学、易学、文章学,对其礼学则不甚措意,除了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基博《经学通志》、邓声国《清代〈仪礼〉文献研究》有所触及外,对张惠言礼学进行专题探讨的论著至今付之阙如,不无遗憾。
一、形式与内容的交互
在对礼的本体认识上,张惠言提出了礼合文质的重要主张,具有丰富的礼学意义与思想指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就礼的起源而言,礼文因情、事而设,表达了特定的礼意,因此礼仪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盖先王之制礼也,原情而为之节,因事而为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乐之情,即有饮食男女声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故为之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之礼,而因以制上下之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进退揖让升降之数。[2]112-113
在张惠言看来,因质(情、事)而设文(礼仪),因文(礼仪)以见质(情、事),制定相关的礼仪,节制人的物质与生理欲望,以挖掘人本身存在的道德伦理感。物质生理欲望的不定性意味着礼存在的必要性,而道德伦理感的先验存在则说明礼存在的可能性。二者共存相依,不容分割,这是对“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缘人情而制礼”(《史记·礼书》)传统认识的继承与发展。而就礼的目的而言,张惠言强调礼的分殊性、等级性、秩序性、过程性。这与荀子的观点一脉相承。
其二,礼的构成要素兼具文、质两个方面。
张惠言认为,礼应当本末兼该、文质彬彬,礼意是礼成立的基础和根本,礼文是礼践履的途径:
是故文质之为礼,犹麴糱之为酒也。[2]166
礼乐者,道之器也。文质者,礼乐之情也。尚文尚质者,所由入礼乐之途也。先王之以礼乐教天下同,而天下之所以用礼乐者,不能不异。盖君子之于礼乐也,赅其本,备其末,范其过中不及而一于道,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190
这与孔子追求的文质彬彬有相似之处,即注意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也有所不同,孔子论礼更看重礼意:“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记》亦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礼记·郊特牲》)“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礼记·乐记》)
宋明理学家同样重礼意、轻礼仪。程颢云:“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3]18程颐云:“大凡礼必须有意。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3]177朱熹云:“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别有个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4]王阳明云:“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5]
礼合文质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张惠言追求礼仪和礼意的并重。他对礼意是重视的,如其晚年基于礼意的维度对宗祠的社会功能予以肯定:“宗祠非古礼而得礼意,后之君子,恒兢兢焉务之。”[2]151但更多的时候,张惠言侧重于礼文的强调。这是因为文、质具有互涵性,尚质轻文会导致质的凋丧,例如,汉唐以后的统治者崇尚简易,导致民俗败坏与政治动乱:
历观汉唐以后得天下者,莫不崇简易,尚惇朴,而无以成其教,则民俗不变,治亦不长。盖民之欲反质之势千有馀岁而未尝改,而迄不得圣人为之,遂坏乱而不救,使异端得以乘其隙,可慨也。后世之民,日益苟简,起立、拜跪、周旋、裼袭之数,仅有存者,质既尽丧,而复相与自去其文,治天下者,得不早为之所哉?[2]167
张惠言对宋明理学轻视礼的器物、节文颇为不满:“尼父删述,六经载采;汉初萌芽,唐犹傀儡;宋学刓其圭璧,明制遗其鼎鼐;更降迭替,越二千有二十载,而后大道之行,于此乎在也。”[2]101鉴于宋明理学的偏失,张惠言虽然文质并重,实际上更注重礼文,因为他认为礼文与礼意的单向侧重与偏枯发展均会出现流弊,或导致放纵恣睢,流于自然主义,或导致虚伪狡诈,泥于形式主义:
质之敝也,民之喜怒好恶肆然而自遂,虽置之琴瑟羽籥之侧,习之俯仰揖让,其自遂者自若也。文之敝也,天下务饰其具,机巧诈伪相冒,散然而无以相属,虽去其所以自饰者,而犹不得所属也。[2]166
不同时期对礼文与礼意的侧重不同,只是因时制宜的权衡机变,而非礼乐之中道:“圣人合文质于礼,而轻重之,以为教,犹酒人之轻重其麴糱以为齐也。”[2]166“故主文主质者,非道之中也,所由适于礼乐之路也。”[2]165
礼文是有内容的形式,礼意也需要通过形式加以表达、显现:“故文者,作其不容已之情而已;质者,反其不容伪之诚而已。情不容已,故手足耳目皆有所曲,而致诚不容伪,故周旋进反皆有所丽而存。”[2]166
民众在对礼文的身体力行与耳濡目染中,也会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实现礼意:“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而生,而邪气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饮食,知能所及,思虑所造,皆有以范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2]112-113
其三,礼合文质的关键和本质在于确立等级秩序,在日常行为仪节中自然渗透:
文质者,其要在父子君臣之序,六亲上下之施,其事正于坐立、拜跪、裼袭、差杀、升降之际,而出入于性情之间。[2]166
因此他反对吴德璇以礼乐为文的观点,认为父子之仁、君臣之义是礼乐的归宿:“吾之所谓文质者,固将从兴礼乐始……是足下之意以礼乐为文,而以父子君臣为质。夫父子君臣,文质礼乐之归也,而岂与礼乐为文质哉?”[2]190
张惠言的礼学研究实际上是以《仪礼》为中心,其《仪礼图》对宫室、器物、仪节的描绘,以及其《读仪礼记》对仪文的文字校勘与辩证,均可看出其对礼文的重视。他十分注重礼仪的空间感与过程性,将宫室图提到首要地位。《仪礼》由于跟现实的具体生活有着紧密的关系,其场所的界定和方位显得非常重要。而宫室正是仪礼展开的空间基础,具有定位作用:“惟是读《仪礼》者,必明于古人宫室之制,然后所位所陈,揖让进退,不失其方。”[6]252张惠言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仪礼图》将宫室部分提到了关键位置,予以了格外重视。其《仪礼图》开卷即绘宫室图,有《郑氏大夫士堂室图》《天子路寝图》《大夫士房室图》《天子诸侯左右房图》《州学为榭制图》《东房西房北堂无房堂诸图》。这一点得到了阮元的高度评价:“宋杨复作《仪礼图》,虽礼文完具,而位地或淆。编修(案:指张惠言)则以为治《仪礼》者当先明宫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诸儒之义,断以经注,首述宫室图,而后依图比事,按而读之,步武朗然。”[7]244尽管黄以周对张惠言的宫室图有所辨驳,但依然承认“图宫室者以张皋文《仪礼图》为最当。”[8]突出宫室的好处在于,可以知道礼仪施设的场合和位置,从而能够产生更为立体直观的视觉效果,也能更好地复原历史礼仪的生动场景。此外,张惠言将仪节依次详实细腻绘出,富于立体感与过程性。曹元弼云:“张氏作《仪礼图》,详审精密,胜于宋杨氏书。”[9]张惠言绘图不仅根据仪礼的次序分别画图,而且每一种礼的每一个细节、过程,都尽可能将其绘出,力图再现礼仪践履的过程性、层次性与现场感。如“燕礼”,张惠言在绘出燕礼所需的馔具之后,先后精细地绘出了卿大夫士入位、宾入拜至、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献公、主人媵觚于公、媵觯于公、举旅、行酬、献卿、献大夫、献工献笙、立司正、彻俎、献十、宾媵觯于公主人献庶子等礼仪节目,又如“聘礼”,张惠言依次绘出夕币、释币于祢、受命、受劳、傧劳者、致馆设飧、迎宾、聘、享、礼宾、宾以臣礼觌、宾觌、介以臣礼入觌、辞介礼、上介觌、士介觌、答士介拜、公出送宾、送宾大门内、致饔饩、傧大夫、饩士介、问卿、宾面卿、上接口卿、众接口卿、夫人归礼陈位、大夫饩宾陈位、还玉、反命。其它诸礼,无不如此。将礼仪节次与礼器用具均尽可能直观形象的描绘出来,这样下来,给人一种强烈的立体感,有利于再现历史礼仪的具体场景与操作流程。根据《仪礼》篇目次序,张惠言详考吉凶冠服之制,依次绘图,不能绘图之处,以表代替,并且辅之以简约之说明。如《衣服》绘有《冕弁冠服表》《妇人服表》,《丧服》绘有《亲亲上杀下杀旁杀表》《丧服表》《衰服变除表》《麻同变葛表》,对各种服制予以分类清理,让人一目了然。
二、崇实黜虚的思想诉求
张惠言礼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抟虚为实,颇具以礼代理的倾向。这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张惠言提出“求孟自荀始”的学术认知路径,以礼作为实现儒家道德理想的根本途径。
虽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义,荀子则约仁义而归之礼。夫义者,仁之裁制也;礼者,仁义之检绳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检身也详。韩子曰:求观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后之学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2]25
张惠言认为,荀学重礼,而孟学重义,二者在归宿上并无二致。荀子的性恶论备受后人非议,而张惠言为之辩护,认为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在走向仁义之教方面异曲同工,“昔者孟子言性善,荀卿反之,言性之善恶虽异,而其教人为尧舜仁义则一也”[2]35。但张惠言强调求孟自荀始,实际上确认了由礼到达仁义的道路,从而否定了理学的路径,相当于以礼代理,为张惠言礼学的逻辑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篇文章写于1788-1794年之间,其时四库馆开已久,汉学风气正浓。钱大昕、谢墉、四库馆臣均对荀子予以肯定。汪中的《荀卿子通论》表彰荀子的传经之功:“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10]412以为荀子得周孔真传,“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10]412。与张惠言同时的淩廷堪、郝懿行,均对荀子予以表彰,一时荀学蔚为风尚,张惠言自然也不例外。
其二,与重荀思想相一致,张惠言极力突出礼的经学地位和社会价值。
张惠言晚年从徽州金榜研习礼学:“嘉庆之初,问郑学于歙金先生,三年,图《仪礼》十八卷。”[2]118在金榜去世后,张惠言写的祭文中明确提出了“六经同归,其指在礼”的思想:
六经同归,其指在礼。谁与明之,北海郑氏。经唐涉宋,大论日芜;天鉴圣清,笃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榛兑途,洒流就东。厥有继者,休宁之戴;先生起歙,并黻联佩。戴君宏通,众流并泳;志修年短,厥绪未竟。先生精研,思约理积;掉头庌庑,壶奥独辟。既启其室,遂周其藩;桴杗(木咨)(木而),既固既完。笺礼九篇,以郑正郑;惟其匡捄,是谓笃信。一义之发,迩于睫眸;先生不言,千载其幽。较其所成,于戴盖多;婺源之传,岱、华比峨。[2]161
可见,张惠言企图将六经均纳入礼的体系中,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礼的经学地位。同时,张惠言对礼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郑玄、江永、戴震、金榜予以表彰。他以江永直续郑玄,可见他认同的是徽州学派的礼学,彰显出其礼学的渊源有自。值得注意的是,与张惠言同时的凌廷堪也认为礼是贯穿群经的关键所在[11]64,可以看出时代的风尚。
张惠言对礼的社会价值与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他赋予礼以至高的地位,将礼视为人之至教,“礼者,人之至教,道在勉强而已”,[2]215这是对荀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荀子云:“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张惠言还将礼提高到国家兴亡的战略高度,“礼止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坏国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不去,而风俗隳,国家败者,未之有也”[2]113-114,也是与荀子“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一脉相承。
为什么张惠言认为礼是人之至教?这是因为张惠言认识到礼治内外,且有人道凝聚的功能。一方面,礼本身是思想行为的规范、道德情感的标准:“礼者,仁义之检绳也。”[2]25“礼者,情之检也。”[2]223“夫决嫌疑、定犹豫、别是非,舍礼,何以治之?故礼者,道义之绳检,言行之大防,进德修业之规矩也。君子必学礼,然后善其所善,而过其所过。”[2]65另一方面,礼可以移风易俗,形成互爱互助的良好氛围:“一代之兴,必更制度,作礼乐,移风易俗。非有所明著其教,则上下不可以相喻,而化不兴,俗不成。”[2]165“圣人者,作其情而用其耻,故能使相救犹一身,而相爱犹一家,则礼之效也。”[2]172而且,礼可以稳定秩序,保证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张惠言认为:
是故先王之制礼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简,而施之也甚博。政也者,正此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乐也者,乐此者也。是故君者,制礼以为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礼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礼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常习,故政不烦也。权礼之所禁,而轻重之,以绳不合者,故刑不扰也。民习于礼,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后有羞恶,是故赏罚可得而用也。民习于礼,故知有父子君臣长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长幼上下,然后又孝悌忠信,是故军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习于礼,故有孝友睦姻任恤,有孝友睦姻任恤,然后有智仁圣义中和,是故其人材成者,可得而用也。故曰:礼止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坏国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不去,而风俗隳,国家败者,未之有也。[2]113-114
其三,将《易》礼象化,从而对宋明理学的基础义理易釜底抽薪。
就易学的发展历程来看,魏晋以来,郑氏《易》一度被王氏《易》取代,“王学既盛,汉《易》遂亡”[6]7“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故《隋志》易类称郑学寖微,今殆绝矣”[6]6。王弼的易学颇具革命性,他摧毁了牵强附会的汉代象数易,为魏晋玄学开辟了崭新的道路[6]6,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宋明理学之思想先导:“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6]6如程颐的《程氏易传》本身以王弼易为基础,四库馆臣称:“其书但解上、下经及《彖》、《象》、《文言》,用王弼注本……今考程子《与金堂谢湜书》,谓《易》当先读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谓程子有取于弼,不为无据。”[6]12
鉴于王弼义理易与宋明理学的密切关联,张惠言对其抨击甚烈:“自王弼《注》兴而《易》晦,自孔颖达《正义》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学者争说性命,莫不以王、孔为本。”[2]59这体现出张惠言严正的汉学立场。由此亦可看出,张惠言将《易》事象化、礼象化用意正在崇汉黜宋,以礼代理:
重事象轻理数,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虽姬孔靡所据以辨言正辞,而况多歧之说哉!设使汉之师儒比事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后之学者有所依逐,至于今,曲学之响,千喙一沸,或不至此。[2]40
基于汉学立场,他将《易》学事象化不难理解。同时,张惠言礼学家与易学家的双重身份,也便于他发现《易》与《礼》的深刻关联性。
张惠言尽管《易》《礼》兼擅,但乾嘉时期的学者,似更倾向揄扬其《易》学。如其同年陈寿祺赞誉张惠言“绝学吞爻接孟僖”[12];阮元着重表彰张惠言《易》学为“专家孤学”[7]37,他编纂的《皇清经解》收入了张惠言的六种易学著作,而《仪礼图》《读仪礼记》则付之阙如。直到晚清,才出现张惠言礼学优于易学的声音。陈澧云:“张皋文之学以《仪礼图》为最,其次则《易义别录》也。”[13]在区分张惠言的学派归属时,章太炎基于礼学的考虑将其纳入皖派朴学家之阵营,“张之《易》近吴派,其《礼图》则得诸皖,仍可入皖”[14],颇耐人寻味。
其实,在张惠言的心目中,礼似乎占据更高的地位,如在《虞氏易礼序》中张惠言更明确提出了“《易》为礼象”的命题:“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记》曰:夫《礼》必本于太一,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礼》象也。”[2]39张惠言还在文中指出,郑玄以《易》言《礼》,以礼解易,虽然其以爻辰取象不足以查究天地消长、盛衰之由,但可以借此考察周一代之制度规模,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这说明张惠言虽然对郑玄通过爻辰取象考究天地消息的方面有所批判,但非常欣赏郑玄因《易》求《礼》的学术取径。郑玄是东汉的经学大师,尤精于三礼,在注《易》的时候,郑玄或直接取自《三礼》,或借助互体、爻辰取象,然后推出礼仪制度。受郑玄的影响,张惠言十分注意沟通易学和礼学的关系,甚至以《易》证礼,以期对古礼有更好的把握。如其撰《虞氏易礼》一书,正表现出他致力于将虞氏易学作礼学化的阐释。柯劭忞云:“郑君据礼释《易》为专家之学,虞氏诋郑注为不得其门,则虞氏不主言礼可知。惠言谓揆诸郑氏源流本末,盖有合焉,未免曲为附会。然其原文本质,发挥经义,足以补康成之缺,正不必援虞入郑,混淆家法也。”[15]虽未必合乎虞氏易的原意,但从中亦可窥见张惠言重礼的用心所在。
而在《周易郑荀义》中,张惠言归纳出中春嫁娶、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天子之女、后无出道、郊禘、时祭、祭礼盥而不荐、二簋同享、长子主器、享西山、时会而盟、尊酒簋二用缶、朝觐、聘、侯封、贡赐、中国七千里、大夫有地、军赋、宾士、世子不孝之刑、剭诛、圜土等二十三种礼象。他对《益》卦进行礼学解读,认为益卦的前四爻中体现了吉礼、军礼、凶礼和宾礼的相关信息,可见其“《易》为礼象”诠释的生动性:
《益》之初曰:“利用为大作。”大作,国之大事,祀与戎也。其二曰:“王用亨于帝”,亨者,祀也。其三曰:“《益》之用,凶事。”凶事,丧也。其四曰:“中行,告公从。”告公,朝聘之礼也。“利用为依迁邦”,言大封也。故吉、凶、军、宾之礼,具于《益》焉。[2]66
张惠言易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是虞氏《易》,虞翻传孟氏《易》。值得注意的是,孟氏《易》、虞氏《易》在诸家《易》中非常注重人事,因此并非一般形式的象数《易》与玄学《易》,而是今文学形式的《易》。虞氏《易》在研究天地消息时多有独步之处,郑氏《易》则在以《礼》解《易》、以《易》证《礼》方面为张惠言所欣赏[2]40-41。而张惠言特别推崇虞氏易旁通变化、气象闳大,以《易》达人事、通社会的学术精意,“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气以定六位,运始终之纪以叙六十四卦,要变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发挥旁通,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以则四德,盖与荀同原而闳大远矣”[2]41,张惠言重象轻数,“《易》者,象也。《易》而无象,是失其所以为《易》;数者,所以筮也。圣人倚数以作《易》,而卦爻之辞,数无与焉。汉师之学,谓之言象可,谓之言数不可。象、数并称者,末学之陋也”[2]60,从而将易学实体化、礼象化,旨在推求人事,故其对惠栋亦有不满,而甚为推重郑玄《易》中求礼的方法:
韩宣子见《易》象曰:“周礼在鲁矣。”是故《易》者,礼象也。是说也,诸儒莫能言,唯郑氏言之。故郑氏之《易》,其要在礼。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画以求其变,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质损益,大小该备,故郑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郑氏之所以为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2]60
可见张惠言注重郑氏易和虞氏易,正在于郑玄是以礼来阐发易蕴,而虞氏易则注意人事之阐发引申,可以用于现实关怀。在张惠言的心目中,《易》是礼的一种表现形式,《易》的内涵和精蕴及其意指在于传达礼、表现礼之精神,《礼》似乎占据着更为核心的地位。
张惠言将易学事象化,抨击易的理数化。其易学重人事,轻天象,实际上为《易》《礼》的贯通奠定了基础,毕竟事象化的易与仪节化的礼在人事层面有了契合与交集:
故郑氏之《易》,其要在礼。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画以求其变,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质损益,大小该备,故郑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郑氏之所以为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2]60
夫理者无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虽姬、孔靡所据以辨言正辞,而况多歧之说哉!设使汉之师儒比事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后之学者有所依逐,至于今,曲学之响,千喙一沸,或不至此。[2]40
最早将礼学与易学沟通的是郑玄。以礼注《易》开始于郑玄,这与他精熟《三礼》有着密切关联。虽然郑玄在注释《易》的时候,不时引用礼学的话语作为证据,但属于“援《礼》注《易》”,并无意于将《易》礼制化,相反而是让礼象来丰富、说明《易》象。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曾将《易》与《礼》进行了沟通,如其云:“礼之兴也于中古,《易》之兴也亦于中古。《易》与《礼》相得以章,而因《易》以生《礼》,故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16]在王夫之的思想体系中,《易》更为根本,《礼》在《易》的面前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但张惠言在《易》《礼》的沟通上有别于郑玄的“援《礼》注《易》”和王夫之的“以《礼》辅《易》”,而是试图实现《易》的礼制化,从而实现由“礼为易象”到“易为礼象”的根本转变,可以说,张惠言在《易》的象数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易》的礼制化,这是对义理《易》更为彻底的瓦解与扫荡。
清初学者出现了对回归礼学的趋向,《仪礼》日益得到士人的关注。乾嘉时期《仪礼》学大兴,尤其是褚寅亮《仪礼管见》确立了郑注在《仪礼》学中的典范地位;凌廷堪《礼经释例》以条例的方式解读《仪礼》,并独尊《仪礼》,抨击《周礼》《礼记》,将《仪礼》的地位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仪礼》的节文度数,纯为征实之学,非发挥义理所能阐释,故称为清代汉学狙击宋学的重要战场:“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注其书者寥寥数家,即郝敬《完解》之类稍传于世者,大抵影响揣摩,横生臆见。盖《周礼》犹可谈王霸,《礼记》犹可言诚敬,《仪礼》则全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可敷演,故讲学家每避之而不道也。”[6]257《仪礼》的节文度数、器具仪节,无疑与象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张惠言在三礼中注重《仪礼》的研究,尤其是以绘图的方式阐释《仪礼》,应该说是其“重象”思想的一贯推进。从本质层面而言,张惠言的《易》学研究倾向于破,旨在瓦解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石,而其礼学研究才是立,也是其归宿所在。
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
张惠言家境贫寒,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姜氏为之守志,家计艰难[17]到了“无屋可居,无田可食,才力又不足以给生事,游十年而困益甚”[2]201-202的困窘境地。寒士的生活,使张惠言对社会民情有着深刻的体会。乾隆后期以来,社会危机加重,内忧外患丛生。一方面,士风庸陋,嗜利无耻:“今之君子则不然,其志之所愿,不过身家衣食功利之务;其学问之所及,仅仅知恶之不可为,而未必识其所以。”[2]142民俗浇漓,礼教荡然:“吴中风俗浇漓。方今吾乡风俗益偷,礼教益薄,此世道之忧,缙绅先生之耻也。”[2]149“三吴地狭人众,民贫而俗者,矜利势,其为士者,没于禄宦,走衣食,往往游于四方,或数十年不入家门者,以千数。”[2]201此外,吏民隔阂,民生凋敝:
愚以为方今之患,独患吏与民阔而不相亲。民之视吏也,惮然若神鬼之不可即;吏之视民也,芸然若履崇山而视原隰之草木,无所别之。民之疾痛颠连而濒于死者,有执途人而哀之者矣,未有号呼求拯于州县者也。其愚者,不知州县之职宜生我也。其知者,知号呼之无益也。且不惟无益而已,州县出一令,行一法,传呼者数十人,奔走者数百人,利未见而已受其害。[2]168-169
官吏的庸贤与否均无法改变民生凋敝的现实境况:“民富者、贫者、安居者、转徙而流亡者,吏不肖,不知其何以然也;贤者知之矣,然而不可如何。”[2]168“吏无虐、无墨、无失法,而民之死者,已不可胜数矣。”[2]168这足以说明重用刀笔之吏的制度性危害。
另一方面,白莲教起义与西方殖民者的活动对清廷统治构成直接的威胁:
方今天下之患,楚、蜀、秦、豫之间则有教匪,江浙闽广负海之地则有洋匪,是皆数十年渐渍引蔓,根蟠柢互,有司漫不为意,又殴良民而附益之,及其一旦不可盖覆,乃始相视狼顾莫之如何。[2]197
但更可怕的情况是,人才匮乏,难以应对艰难局势。对此,张惠言有清醒地认识:“且夫以今之将卒,治今之盗,虽增兵至数百万,其不足恃,章章明甚。”[2]198“凡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无人任之。无人任之者,非无人为之也,为之而不足以胜之也。”[2]70常州之地,自明代唐顺之以降,经世之风连绵不绝,明清之际高攀龙、顾宪成等东林党人更造就了经世思想的高潮,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受地域传统的潜移默化,张惠言亦抱有经世之志,满怀着“兼济天下”的社会情怀。如其同年陈寿祺云:“君(许宗彦)与张皋文,咸天才绝特,慨然有用世之志,而两人位既不显,年又止于强艾,不得施其所学,以济于时,斯不能不为天下人才惜也。”[18]张惠言的思想哲学偏向于行动践履与实用理性。“天下不动之物不可以久。”[2]215“古之为学,非博其闻而已,必有所用之。”[2]61而礼学正是其经世济用的重要手段。
针对上述社会危机,张惠言以礼作为移风易俗、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手段,将礼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风俗厚薄的战略高度:“坏国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不去,而风俗隳,国家败者,未之有也。”[2]113-114始终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思考礼,是张惠言礼学的卓越之处,显然受到了荀子、《礼记》思想的深刻影响。《荀子·修身》云:“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记·礼运》云:“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这也与张惠言所处的时代情势分不开。可见张惠言的礼学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既有对国家秩序的担心,也有对民生世风的忧虑。
国家秩序层面。张惠言认为礼可以培养人的道德伦理意识与等级秩序意识:“盖先王之制礼也,原情为之节,因事为之防……故为之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之礼,因以制上下之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进退、揖让、升降之数,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气不得接焉。”[2]112-113有了道德伦理意识和等级秩序意识,民便便于管理、控制:“民习于礼,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后有羞恶,是故赏罚可得而用也。民习于礼,故知有父子君臣长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长幼上下,然后有孝弟忠信,是故军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2]113-114同时,人才也因此可得而用:“故民习于礼,故有孝友睦姻任恤;有孝友睦姻任恤,然后有智仁圣义中和,是故人才成者,可得而用也。”[2]113-114由此,他认为礼具有止乱之源的稳定功能,“礼,止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2]113-114显然受到了《礼记》相关思想的影响。
世风民生层面。张惠言从吏治入手探讨是世风败坏、民生凋敝的根源。他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事务倒持于书吏之手:“国家养文武士,一百五十年矣,其为泽至深厚。而为士者,日以嗜利而无耻;为兵者,日以怯弱而畏死。是岂无故哉……古者郡县掾吏,皆官长辟除,孝廉、茂才则于是乎选,故守令常恃以为治。今者悉更之以书吏,官待之以仆隶之体,而吏自待以商贾之心。夫责仆隶以礼,而冀商贾以廉,无是理也。”[2]122地方治理缺乏成效在于社会上下层的脱节和不信任:“夫立法而不便者,上不悉下;法便而民不劝行者,下不信上也……故苟有以相亲,则百万之众措之若指臂;苟无以相亲,则内治一妾,外驭一仆,且不足审其旦莫所事,而何以谋长乎?”[2]169张惠言认为,礼治可以使民情上达,减少官吏对民众的滋扰。
诚能略仿《周官》、《管子》之意,立之教法,使各掌其治,以时课而问焉,暇则与之论利害,省谣俗,闾阎幽隐之故,必可知也。[2]169
是故君者,制礼以为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奉礼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礼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常习,故政不烦也。权礼之所禁,而轻重之,以绳不合者,故刑不扰也。[2]113
书吏不可废已。若仿古三老孝弟之制,乡举其贤能,以宾礼礼之,使为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则催租捕盗之吏,可以不至乡里,而县无事。[2]122
礼使人相爱相救,具有凝聚人道的功效,“圣人者,作其情而用其耻,故能使相救犹一身,而相爱犹一家,则礼之效也”[2]172。
张惠言往往通过《周礼》《仪礼》并用,以移风易俗,“上之所以教者如此,民之嗜利而无耻,岂足道哉?愚以为方今之势,教民之要有五:一曰立宗法;二曰联什伍,三曰联师儒,四曰讲丧祭之法,五曰谨章服之别……五者之教行,而偝死忘义之风革,惇厖纯固之俗成,民有以相养而无以相弃,上不费而惠遍,则三代之治,不是过也”[2]174。除立宗法、讲丧祭之法、谨章服之别与《仪礼》息息相关外,另外的两要则与《周礼》关联密切,如联师儒这其实源自《周礼·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美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19]154联什伍亦出自《周礼·族师》:“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19]178
而其《与金先生论保甲事例书》所提及的保甲一法,原于《周礼·大司徒》比闾族党之制:“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19]155张惠言认为保甲法是为了民众互保互助,同时又强调杜扰累:“保甲之意,所以使民相保相受,乃是百姓自顾自家,自保乡里,并非官为督责。自来行之不善,官民相违,胥役滋扰,往往反以病民。今惟责成本乡绅士,遵照条法,实力举行,地方官止受绅士成报,时加劝导,不得令差役挨查。”[2]184
礼的好处在于对上下阶层的适度约束:对上约束,而政不烦、刑不扰;对下约束,内化为道德,故民力可使,人才可用。礼是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不仅有对下层百姓的管理与约束,也有对统治阶层的监督和制约。这使得张惠言的礼学既具有严正的秩序意识,也有着鲜明的民生关怀。
四、经典的回响与历史的变奏
张惠言的礼学在清代占据重要地位。《清史稿》认为其《仪礼图》《读仪礼记》“皆特精审”[1]13244。其《仪礼图》得到阮元、周中孚、包世臣、曾国藩、陈澧、黄以周、皮锡瑞的高度评价,被梁启超视为清代《仪礼》学的四大名著之一:
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各走各的路,各做到登峰造极,合起来又能相互为用,这部经总算被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尽了。[20]
张惠言研究《仪礼》首重宫室的思想,也得到了阮元、周中孚等人的称赏。而其礼学经世的相关主张得到晚清士人的高度认可。其《原治》一文被魏源收入其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之“礼政一”(即礼论),排名第三,仅次于凌廷堪的《复礼上篇》《复礼中篇》。值得注意的是,“礼政一”还收入陈廷敬、魏象枢、顾炎武、张尔岐、王懋竑等人的26篇文章,可见这一排序依据的并非时间先后,而是价值重轻。《皇朝经世文编》有治学兼行的特色,主张学术为其纲领,全书都贯穿着从理论到实践的层次感。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礼学上深受张惠言的影响,不仅其解读《仪礼》从张尔岐、张惠言取径,其《读三礼录》中亦颇采张惠言之观点,同时他极力凸显礼学的地位,并将礼提高到正俗济世的社会高度,与张惠言同条共贯、一脉相承。而曹元弼《礼经学》亦将张惠言《原治》与凌廷堪《复礼》并置,视为《仪礼》学的理论要旨:“凌氏、张氏发明礼教,言则大矣,美矣,盛矣,言近于此而已乎!”[9]58由此可见张惠言礼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张惠言与淩廷堪堪称乾嘉时期礼学的双子星座。两者所不同在于,淩廷堪虽然将礼学提高到思想话语的高度,但对三礼的认识不无偏见,标举《仪礼》而贬斥《周礼》《礼记》,纯然乾嘉汉学之门户壁垒;而张惠言礼学则将《仪礼》《周礼》《礼记》熔于一炉,既体现了对仪文度数的细节考究与过程再现,也表现出正俗经世的宏远意图,彰显出乾嘉之际的学风嬗变,也预示了从乾嘉朴学到晚清经世之学的历史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