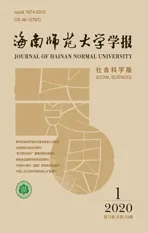《雪鸿泥爪:现代文学史学研究片论》与新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史学研究
2020-01-19邱慧婷
邱慧婷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和研究与外在社会文化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迭出新质。一部优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其生命力不过二三十年,其间新的撰史探索不断出现,突破原有书写理念的桎梏,推动学科发展。从表面看,这是一种宿命,其实质是社会文化语境变化所致。建国后,“阶级论”和“现代性”的撰史理念先后统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历史发展已经证明,“现代”视角对“阶级”视角的超越是一种必然,与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相对应,但就目前来看,“现代”又形成了新的遮蔽,其弊端愈来愈清晰,变革探讨的呼声也越来越强。
一、新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史学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变革的探索“复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火热情景,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核心集中在文学史观,先后出现了“现代中国文学史观”“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汉语新文学史观”“民国文学史观”“民国文学机制”“大文学史观”“华语语系文学”等不同的思考。
“现代中国文学史观”是朱德发提出的新的治史理念,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现代国家”视角。以“现代国家”为切入点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本不是新话题,但朱德发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判定与学界已有的探析略有不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维新运动倡导的君主立宪已把中国纳入现代化国家的轨道,虽然这只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肇始,却为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提供了‘现代中国’的生态环境。”(1)朱德发 :《维新变法:中国文学转换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规律》,《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在朱德发的思考中,“维新变法”尽管持续时间较短,却已经是“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实践物,可以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起始点的标志。现代国家意识的出现提供了文学史书写的空间,只有当文学自身也出现变化时,此史观的根基才会坚实。“所谓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主要指戊戌变法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约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到二十世纪头十年。”(2)朱德发 :《中国五四文学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5页。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论题,学界探析颇多。王德威、杨联芬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了晚清文学的蕴藏。朱德发提出的以维新变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起点,突出的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强调的启蒙理念,对应着中国传统文学的解体,在前置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时,带来的是关于现代性的不同认知和看法。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关注突出的是二元对立,即以“五四”为标志,截断中国文学的发展,突出两个不同时期。不论是新民主主义论,还是启蒙现代性,都将新文学置于旧文学的对立面,强调的是“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现代中国文学史”意在以国家的现代取向消解文学史书写中的二元对立,凸显不同文学形态的史学价值。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承载着语体变革中的价值判断,即白话文对文言文的超越和白话与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同构。语言本无“新”“旧”,只是人们交流使用的工具,但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出于启蒙民众、传播思想等目的,通俗的、易于理解的白话文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使命,成为启蒙的手段。“革命”凸显的是断裂,是二元对立,当语言变革被赋予革命性的意义,白话文对文言文的超越价值被放大和强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突出了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战斗,强调了白话文在变革中的作用,导致“新文学”在价值形态上对“旧文学”的超越,成为“现代”的代表和现代性的体现。这种现代的呈现方式,带来的是新文学以外的其它文学形态无法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注视域。朱德发“现代国家文学史观”的出现,在直观层面上是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起点提前,但实质上是对“现代”不同理解的呈现,是对现代性问题的新思考。“‘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比‘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只在纵横向度上作了极大的拓展,为文学史探讨和书写提供了不少新的空间和领域,这无疑是新的知识增长点和新的学术增值点。”(3)朱德发 :《现代文学史书写在突围解惑中创新趋优——治学修史的粗浅体会》,《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朱德发对不同文学形态一视同仁的写史追求,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回响,与“民国”“民族”视角的探索形成了呼应。
“民国文学史”等民国视角治文学史理念的探索是近年研讨中的热点论题,丁帆、张福贵、陈国恩、张堂锜、林秀琴、熊修雨、傅元峰、赵学勇、赵普光、黄轶、贾振勇等是民国文学史理念研讨的参与者,李怡、周维东、郜元宝、张中良、刘勇、宁新芳等参与了“民国机制”的研讨。“民国文学史”倡言历史视角治史理念的重要性。“有一个很现存的又通俗易懂的名称,可供选换,那就是‘民国时期文学史’。‘民国时期’基本上与这一学科研究的这段历史是一致的。”(4)陈福康 :《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李怡,张堂锜编 :《民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第一辑》,台北:秀威经典出版社,2015年,第17页。较之于陈福康,丁帆对“民国文学史”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考要更为具体。丁帆以新中国建立为时间划分点,认为1912—1949年的文学归入“民国文学”的范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地区的文学称为“共和国文学”。尽管“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的指称不同,但丁帆认为二者在追求现代的取法上是同一路径。“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在基本精神、气质等方面必然是相通的。这就是说,二者在一定的创作历程中所自然形成的审美范畴差不多是一致的。”(5)丁帆,施龙 :《从历史的夹缝中寻找学术良知——丁帆教授访谈》,《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民国文学史”的建构理念源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现代性文学史观的不满,但不少学者的建构考量并没有走出“现代”的藩篱。以丁帆的探索为例,当“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在现代取法层面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价值也就丧失了。较之于“民国文学史”,“民国机制”更强调民国时期文学场域的复原,追求将文学放置于众多的生态系统中考察其发展变化,摆脱单独关注文学的研究局限,建立文学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关联。“民国”视角尽管与“现代国家”的治史理念不同,但二者的核心指向均是“现代”的建构与当前文学史著作中“现代性”的重新审视。“民国文学史”的治史视角强调不同文学形态相同的入史待遇,“民国文学机制”强调文学生态场域的复原,关注的都是不同文学形态的史学价值,不再是新文学一种形态的价值。在此种条件下,“新”对“旧”的超越和“雅”对“俗”的超越已不是关注重点,更不是“现代性”的呈现方式,凸显的是“现代”的实现不以排斥和漠视“异己”为追求的史学观。这种关注现代包容性特质的研究取向同样引起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关纪新等倡言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有相近的关切。
在关纪新和一些民族文学研究者看来,少数民族文学尚未受到研究界的足够重视,其价值被忽略。“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部的‘中国文学史’,它们却绝少不是‘汉族文学史’之著称。因为那些著作大都只是论述古往今来中原文坛上的桩桩件件,即便其中有较少段落涉及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也总是一笔带过,抑或是从汉族传统的批评尺度出发来做些隔靴搔痒的估价。”(6)关纪新 :《应当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中国民族》2007年第4期。“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不独关涉中国现代文学史,更牵涉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治史都牵涉到现代性问题。从直观形态看,少数民族文学由于语言的隔阂或书写题材、关注视角、写作技法等层面的原因没有得到写史者的重视,但此种现象的出现实质是对现代及现代性的不同理解造成的。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不断突出和强调现代是“线性”和“突进”的,在这条前进线索中,与之相吻合的被概括为现代,反之,则被漠视。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读者很少能感受到这种现代。这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和作家不同的知识储备,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不太关注历史发展的前瞻性,因此较难洞见出历史的走向和趋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在“线性”追求的概括下,必然会藉“现代”之名突出一些作品,同时遮蔽一些作品。这种线性进程先在地预设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走向,在走向确立的基础上考察不同文学创作、思潮流派的发展,将进程一致的概括为“现代”或追求现代,与之相反或相异的创作则被排斥在现代之外。此种写史追求可以直观地将文学发展与社会走向建立关联,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积极作用的凸显,但不利于丰富史实的呈现。“不注重细节,对文学文本的细节和文学历史的细节都比较忽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往往都被忽略掉了。这是教科书性质文学史的通病。”(7)陈平原 :《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由此,不论是“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民国文学史”“民国文学机制”,还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变革探析的深层指向是现代性的治史理念及其桎梏的突破问题。
二、《雪泥鸿爪:现代文学史学研究片论》的突破及价值
不同建构探索的声音层出不穷,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已有探索,系统关注研究趋向的发展变化,有利于现代文学史学的探析走向深入。王瑜著《雪鸿泥爪:现代文学史学研究片论》(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版,以下简称“《片论》”)关注探析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撰史中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新”“旧”文学关系、“雅”“俗”划分方式、文化语境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等,试图找出学科的深层支撑和发展中的制约因素以及变革突破的方向,取得了一定的收获。
“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较难处理的论题,暴露了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局限。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新文学”和“旧文学”都有自己的历史追溯,本不存在入史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也是将二者杂糅进同一撰写体系的。建国后,以新的方法讲述新民主革命文学阵线上取得的成就成为大学课程的要求,“中国新文学史”的编写也提上了日程。当时编写出的文学史均是以“中国新文学史”命名,指向新文学的发展及其历史。1955年丁易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命名的文学史著,也是历史上系统成书的第二部“中国现代文学史”(8)任访秋1944年在河南前锋报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第一部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随后,“大跃进”的思潮充斥在国家的各个领域,文学战线也不例外,“中国新文学” 的气度似乎太小,“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开始出现并成为主流。“‘现代文学’作为文学史概念,是‘大跃进’的产物。尽管描述对象一样,这些文学史被普遍命名为‘现代文学史’。”(9)李仰智 :《颠覆与重建——近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述评》,《中国出版》2006年第5期。语词的转换带来的影响是极大的。“中国新文学史”只是新文学形态发展历程的总结,不论它的发展如何辉煌,也仅仅是众多文学形态中的一种,与其它文学形态共同归属于现代中国,受现代时期中国文学历史化进程的统领。在中国新文学史内质没有扩大的情形下,从命名上直接将其提升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建立了新文学发展和国家文学历史书写的同构关系,新文学不仅成为现代中国时期文学唯一合法化的存在,更直接影响了其它文学形态历史化书写的落实,遮蔽了其它文学形态在国家文学视野中的价值。“新”与“旧”都是形容词,本身不是价值判断的标准,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凸显的是不断追求变革的理念,“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强调的也是不断积极进取的精神。“新”在中国文化中更多指向过程、途径,蕴藏着动势和能量,是至善追求的实现路径。中华优秀文化中“新”的内涵在晚清时期被改写,影响到后续诸多理念的变异。当“新”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时,建构新文学与新民主革命之间的联系更有利于中国革命成果的展现。
清季之前,国家财力雄厚,但由于思想领域的停滞,对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皇帝和王公大臣做着春秋大梦的同时沉溺于僵化体制带来的舒适和愉悦,不思进取,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停滞不前,不但不积极研讨创新,反而加以排斥。晚清列强入侵惊醒了有识之士,在不断的反省中,变法之士倡导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思想等领域全面开花,其间影响最大,且引起国人追捧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达尔文强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本是应用于生物学的理论,凸显的是生物不断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强调生物体对外在环境的适应力,由于退化和异化等现象的存在,理论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瑕。“物竞天择”的理念给国人带来了希望,也让国人逐新驱旧,向往以“新”代“旧”,实现国家的强大。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无法清晰认知进化论社会学等领域应用的危害,忽略了达尔文对“进化论”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警告,将之应用于社会变革的追求中,单纯地认为“新”是更符合时代发展的,将“新”与社会进程建立联系,推动了“新”“旧”成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形成。在文学领域,当“新”“旧”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后,“新文学”对“旧文学”的优越感就直观地呈现出来。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无保留、无顾忌地向旧文学开炮并不是出于对旧文学的仇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过旧文学的熏陶和滋养,是从旧文学的母体中成长起来的,义无反顾背叛的姿态背后是对“新”是优越价值的深信不疑。中国新文学之于旧文学的优势十分明显,当其成为现代中国时期唯一被历史书写文学形态后,对旧文学的挤压就更为突出,旧文学也丧失了入史资格。文学的“新”“旧”之争从表面看是文学形态的冲突,但实质上牵涉极多,进化理念、价值判断、治史思考等均牵涉在其间。不论是“进化论”在中国语境中的“误读”,严复翻译时有选择的忽略和增加,还是“新文学史”命名向“现代文学史”的转换,《片论》都提出了相对独特的看法,对于丰富和拓展相关研究起到了作用。
除“新”“旧”问题外,“雅”“俗”问题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重要关注,关涉到文学标准的确立、文学性的评判等。文学起源于群众,“兴观群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但由于其承载着统治阶层意志传达,也就具有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走向了“雅”。从发展过程看,“俗”是文学的底色,是文学活动最初的根基;“雅”是“俗”的提升,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精良化的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本应涵括不同的文学形态,因为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并不相同,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都有自己的市场,界限并不明晰。范伯群倡言“两翼说”,认为通俗文学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母体上共生出的两翼,共同推动新文学对旧体文学的超越。这其间,有两重意思,即“新”“旧”文学的对立是大视野,新文学内部“雅”“俗”分化是小事体,类似内部矛盾。知识精英文学延续着启蒙现代性,通俗文学向往的是俗世生活的现代。启蒙现代性影响大,波及深远,广受瞩目,世俗现代性与生活息息相关,虽不及启蒙现代性耀眼,但存在更久,在晚清甚或更早时期即已出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定程度上指摘的正是此论题。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需要受众的参与,需要受众具有一定的识辨认知能力,民众认知力的最初提升与通俗文学的繁盛紧密相连。故,启蒙的追求和世俗的沉溺,看似截然不同,却有着内在的联结。经过不懈的努力,通俗文学研究改写了对“鸳鸯蝴蝶派”负面认知,复原了其通俗的价值,与知识精英推崇的新文学发生了联系,成为新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构成。在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一体同构的论题上,尽管有些研究者已经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通俗文学依旧很难融入现代中国文学历史化的进程中。《片论》对此做了探析,在探析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历程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学史观,发现治史的气度和已有文学史观的涵括力均不能同时收纳知识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著者提出——“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凸显的是“新”对“旧”的超越和取代,是为精英文学活动树碑立传,通俗文学是排斥和打击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下,阶级视角的探析凸显的是文学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知识精英倡导的文学活动更具有引领作用,“通俗文学与之相距较远,这使它又丧失了被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机会”(10)王瑜 :《雪鸿泥爪:现代文学史学研究片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4页。;现代性的文学史观本属启蒙理念的呈现,与世俗的现代追求是不同的路向,通俗文学创作很难被有机地融合进来。在此基础上,《片论》认为在当前的治史理念下,通俗文学无法被有效吸收入既有的书写中,相关研究者努力将之拉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体系的冲动很难达到目的。“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其研究对象的划分、研究范围的确定、研究方法的运用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体系,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突破,要想使学科建设获得新突破是很难的。”(11)王瑜 :《雪鸿泥爪:现代文学史学研究片论》,第100页。《片论》结合“全球史观”和当前学界的探索,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对两翼的融合与互动提出了思考,有助于研究新取向的形成。
语境变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变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片论》对此亦有探析。中国现代文学史大规模的编写是由于教育的需要,生产出版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潜在地指向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与其所处的意识形态文化语境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2)陈平原在谈到文学史时,从四个方面概括其存在:“第一,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第二,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第三,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第四,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参见陈平原编 :《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新中国成立时,基于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文学活动受其影响较大,当时译介和引入了许多苏联的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一定程度上也得以保留着著史者的个体思考。目前看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线索,对于许多重要的作家“拒呈现(non-representability)”,遮蔽了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但叙述中亦流露出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的个体思考,展现出了写史者的主体素养。这种情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已难觅踪影。随着我国与苏联外交关系的变化,以苏联道路和模式想象中国文学的方式被否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走到了治史理念“一体化”(13)参见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情境中。许多文学史不再是个体撰写而是集体合著,以阶级意识为主导的写作思想被进一步强化,使整个文学史的书写走上了较为褊狭的路径。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摆脱了外部研究的制约,回到了文学本体,以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衡量其史学地位,重新发掘出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也“呈现(representability)”了一些文学新质。这些现象的出现,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文学回归自身的象征。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文艺界解冻复苏的标志。“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理念得到一致的认同。由文学为政治服务到文学为人民服务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其所带来的震撼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转型背后意识形态文化语境变化的新诉求。“四人帮”倒台后,各个行业展开了对其遗毒的清算,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如果说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突破了“文革”时期理论话语斗争模式的封锁,那么回到内部以美学价值的高低衡量作品价值的研究方法就开启了文学研究模式的转变。“审美论”在文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均有应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中突出地表现为以现代性的文学史观统领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变革与当时中国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的变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与苏联外交关系破裂后,中国在国际话语秩序中一度处于更加孤立的位置。1978年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开始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对话与交流,现代派、现代主义等不同的创作取向也逐渐被国人熟知。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胡乔木归纳的第四点原因是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7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14)胡乔木 :《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变革与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以审美现代性为代表的转向从表面看是研究取向的变化,实质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语境及国际定位发生变化相关。
文学活动有较为完整的生态链,文学研究同样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生态系统而言,外部语境的变化对其书写会产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当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变革的探析有很多,但忽略了外在语境对其产生的影响,当关注不同建构理念时,也并没有参照不同语境中的研究变化及其影响。在此种情形下,《片论》对20世纪80年代审美和启蒙的转向问题做了探析,指出审美和启蒙视角的新开拓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研究的“回归”,而是迥异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外在语境催生出新的研究范式。审美研究范式的形成从表面看是文学内部的研究变革,背后更有着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的支撑。这种探析方式对当前的现代文学史学研究有借鉴价值,可直接促动新建构理念不走偏。
三、《现代文学史学研究片论》及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撰史问题的探讨又一次成为热门论题,引发众多学者不同层面的关注。尽管研究的牵涉面多,有些关注还是跨学科的,但综合起来,当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变革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文学性、教育属性、文学传统等几个方面。
前文已谈及文学领域中的新旧雅俗等问题,当前一些研究的关注点已超越传统论题的探析范畴。王德威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带来了关于文学性的反思。在王德威的撰史理念中,文学不再局限于诗歌、小说、散文等不同的划分,直接突破了语言的限制,打破了传统的分类标准,音乐、图像等皆可进入文学史的视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曾将崔健的《一无所有》写入文学史,引起争议。一些研究者从拓荒的角度肯定此书写的价值,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Bob Dylan),较之于1953年授予丘吉尔此奖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此种现象的出现,对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书写的冲击是巨大的。文学史是在民族国家视阈下,精神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与时代语境、社会文化语境等牵连紧密,当时代阅读出现新趋势和新发展后,文学活动范围的扩大如何反映到文学史的书写中就成为绕不过去的论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中,越界与突围从既有研究体系看是僭越,但往往蕴藏着强大的能量。文体分类的关注方式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书写模式,以“文学性”虚化和泛化文学作品的同时,能否开拓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值得研究者以较为切实的态度探析评判。“中国的文学传统,文学,这是‘文’的学,文章之学,今天到了此时此地,这个‘文’的观念——我再卖弄一次英文,manifestation——呈现,‘文’是一种纹理、脉络,一种形式、形制,是用各式各样符号建立起来的一种辨认世界、让世界表意的体系。”(15)陈平原,王德威,[日]藤井省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文是审美的创造,也是知识的生成”。(16)王德威 :《“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文学性的论题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前沿,牵涉的是文学史书写的框架,更与时代变化密切相关。对文学现象和发展要历史化的理解和考辨,“文学”一词的内涵变化亦复如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中,“文”的价值多是从审美的范畴被追认,关注的是不同文体,落实于小说、诗歌等文类。这种对文的理解与西方的影响有关,也是新文学对旧文学的突破和超越的落脚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何谓文学是一个时代特色浓厚的论题,文学是历史的产物,“文”的内涵也是历史化的构成部分。当前文字和图像、声音等媒介的融合更加紧密,文学性体现与呈现的探索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体系的更新与增长等。《片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撰史中的文体分类、经典塑造、语境与史观等均做了关注,展现和提出了一定的思考视阈,但对具有本体意义的文学性问题关注不够,是一个遗憾。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繁盛,已有的著作多达数百种,繁荣的背后更多是教育的需求。1950年5月,教育部在北京开会研究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将中国新文学的学习纳入到教育体系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得以成为中国高等学校人文专业尤其是中文专业的必修课。“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17)王瑶 :《自序》,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新观点”“新方法”凸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育功能,在当时的语境中,强调的是革命性和革命教育中的价值。尽管不同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注重心不同,其创新突破均不能脱离教育属性的制约。这是很多研究者未能注意到的。“无论是备受压抑的1960年代,还是扬眉吐气的1980年代,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始终跟国家的命运及意识形态变迁联系在一起。”(18)陈平原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2页。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不能忽略其教育属性的存在。“从1903年开始建这个学科,‘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就与晚清以降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现代文学’之取代‘新文学’,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强势的学科,更是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19)陈平原 :《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新中国的建立先天地保有紧密联系,建国后的结盟在情理之中,也是历史化的必然。《片论》在引言中谈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育属性,并没有深入展开,缺失了从教育视角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探索,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存在的自我确证,是一个遗憾。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不断出现冲突,尤其是海外学者的探索和内地研究者之间对同一问题的探索往往展现出不同的判断,其重要根源在于是否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育属性。
在研究的传统方面,《片论》注意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史传统,并对之做了一定的探索,试图发掘其新时代语境中价值的呈现,但视野过多集中于国内的探索。对进化论、阶级论的文学史进行探析时,关注到了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呈现,对于二者的渊源也做了回顾,并没有将之放置于生成的本源状态中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传统,海外学者的关注和中国学者的研究互为“犄角”。总体而言,海外学者重视文本本身,强调作品内在价值的凸现,突出表现在以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和王德威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为代表的文学史中。回到文学内部,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参照海外的文学创作,观察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价值,是他们的主要研究方式,并注意到了文本内部的抒情性,挖掘出了“抒情传统”等概念。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更多把现代时期的作家作品放置于中国革命和现代性追求的进程中,考辨其与中国社会进程走向的关联,发掘其蕴藏的价值。这种研究方式更多关注的是外部研究,早期呈现形态是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关注文学与社会现代化走向的互照和同构问题。海内外不同的研究取向带来的是不同传统的形成。二种取向有交流的空间,更需互融互利相互借鉴取法。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已成为显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变革理念催生出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已很难适应当前时代的发展需求,相关变革探索也已如火如荼的展开,在此情形下,对不同研究传统的重视和发掘有利于更好地推陈出新。当前的相关研究可扩大视野,收编海内外的不同理念,相互借鉴融合,以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问题更好地被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