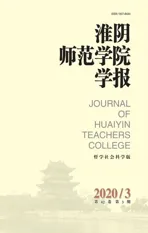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浮现》中的本土性构建
2020-01-19丁林棚
丁林棚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 北京 100871)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加拿大的文学女皇。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一直关注加拿大文学与文化事业,成为加拿大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言人。正如克莱瑞所指出的,“作为加拿大最负盛誉的文学家之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1]45。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化和文学的关心使她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加拿大文化情结,并以文学的想象积极建构加拿大的文化和民族身份。阿特伍德“为自己的身份意识和普通加拿大人的身份意识绘制了一幅加拿大想象的地形图”[2]117。科尔茨称阿特伍德为“一名文学英雄”,认为“和其他加拿大人相比她更懂得加拿大的民族性格”[3]506。
阿特伍德在《浮现》中强烈地表达了对加拿大文化的关注,这和她的民族主义情结不无联系。阿特伍德认为文学不能脱离民族和国家的形象塑造,作家首先应当关注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我生活在这个国家,阅读这个国家的文学只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它属于我,包括它所涵盖的全部地域意识。……只有发现你生活的地方,你才能发现你自己。”[4]113因此,加拿大作家有责任肩负起在文学上塑造加拿大形象的神圣使命,并在文化上努力消除来自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影响,抵制美国文化对加拿大的侵蚀。阿特伍德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思想独立的符号,加拿大人应当寻求树立与美国人不同的文化身份形象:“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或许看起来彼此相似,但他们脑子里装着的东西却是截然不同的。”[4]380
在阿特伍德看来,用文学表达加拿大性(Canadianness)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展现加拿大独特的地理想象和文化风貌,使之成为加拿大文学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摆脱“文化殖民主义”对加拿大的统治,就必须弘扬加拿大文化的独特性,使之区别于欧洲文化与文化的传统,即构建文学的本土性。阿特伍德把目光转向了对本土性(indegeneity)的弘扬和构建,寻求从印第安文化中汲取精神成分,构建文化的加拿大性。事实上,阿特伍德本人一直致力于用文学创作在本土印第安传说和神话中寻找加拿大身份的历史。学者们一致认为,她的作品“受到了印第安神话的深刻影响,……她的许多诗歌都……和印第安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故事非常相似”[5]16。阿特伍德也强调加拿大文学中本土文化的重要性:“许多加拿大白人宣称他们拥有‘印第安血液’,并引以为豪。”[6]187例如,在《奇异的北方》中,她探讨了如“大灰鸮”(Grey Owl)、“温迪各”(Wendigo)等故事,指出了加拿大文学想象中“白人对印第安性的欲求”[7]。白人对印第安性的吸纳不仅能够完成加拿大民族神话和文学想象的本土化使命,还可以使“加拿大白人对自然世界采取一种更具本土传统的态度,对土地充满敬畏而不是随意掠夺”[8]72,通过塑造“加拿大人的原型,摆脱掉欧洲过去,并通过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印第安人来建立和新世界荒野的联系”[9]223。加拿大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克罗齐也认为,“对我们的想象来说,我们还有另一系列可以继承的来自祖先的文化”[10]7。阿特伍德也认为,“白色印第安性”对于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构建具有本质的意义:“如果说存在加拿大文化传统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具有悠久历史的白人转变为印第安人的主题就属于这个传统的一部分。”[7]
需要指出的是,加拿大白人文化对印第安本土性的吸纳不但是构建民族性的本质,也是反抗英国和美国文化殖民的重要方式。通过对印第安性的容纳和吸收,阿特伍德继承了早期加拿大文学中的本土化文学想象。例如,约翰·理查生(John Richardson)、厄内斯特·汤姆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等都在作品中运用印第安神话、动物故事和文化形象表达了印第安性。此外,阿特伍德的文化本土性构建呼应了阿什克罗夫特(Aschcroft)所提出的后殖民主义“帝国反写”理念。在《帝国反写》中,阿什克罗夫特指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欧洲的移民定居者在文学与文化表达方面“面临着构建他们自己的‘本土性’的使命,以突显他们与欧洲传统的差异”[11]134,这成为这些国家文学的一个重要后殖民主题。当然,白人文学的本土性构建不同于印第安人的文化重构,因为后者的文化重构是在结束外国统治之后对文化霸权的一种反抗,而“移民定居者则必须通过构建本土性发现他们……和宇宙的本初联系”[11]134。同样,加拿大白人文学的本土性认同并不是“对(欧洲)起源的天真的‘回归’”,也不是在新土地上“建立一个和世界的亚当式伊甸园联系”[11]134,因为这种联系仅仅让新土地成为对欧洲伊甸园历史和传统的模仿。在阿特伍德的《浮现》中,文学的本土性认同具备文化反抗性的意味,它寻求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本土起源和国家神话的构建,这是文化和文学上的一种独特的考古发现和现实构建,是作者所独有的“女性主义后殖民叙事意欲表达的反殖民主义”尝试[12]29。在小说中,阿特伍德尤其强调了文学与本土性构建在树立“加拿大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她表达了“同他者的深度认同”,并表现出从“内化的殖民心态向反殖民主义世界观的转变”[13]110。
在《浮现》中,阿特伍德的本土化首先表现在对加拿大人的文化异化和身份困惑的描写之上,刻画了无名主人公对加拿大土地的矛盾性认同。女主人公刚刚做了流产手术,又踏上了寻找父亲的旅途。父亲在多年前神秘地消失,她希望能够在荒野中寻找到父亲的遗迹,并发掘关于他的过去和家族历史。因此,女主人公对个人和家庭身份的探索和对加拿大文化传统的发掘成为小说中的平行主题。通过女主人公的精神之旅,阿特伍德塑造了一个多重异化的加拿大人的形象。女主人公的流产和寻父之旅分别象征她对过去和未来的迷茫,她是被放逐在时间性之外的加拿大人的隐喻。作者从头至尾并没有透露主人公的姓名,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深刻蕴意的安排,代表了加拿大人对文化身份和现状的迷惘,这象征对加拿大作为前欧洲殖民地身份的拒绝。小说一开始,女主人公一行就被描写为文化外来者的形象,他们虽然身处加拿大土地之上,却成为徘徊在加拿大本土文化时空之外的旅行者,他们必须通过和加拿大土地的亲密接触来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因此,女主人公的寻根之旅也是她对印第安土地和文化进行探索的旅途。例如,在小说第一章,女主人公就在加拿大荒野中迷失了方向,成为土地的陌生人,她感到“这条路有点不对劲,要么是他们三个走错了地方,要么就是我走错了地方”[14]8。然而矛盾的是,这条路却是他们的回归之路,因为多年前她的父母在失踪前就一直住在此地,“他们的父辈了解这条路的每一寸,甚至可以蒙着眼(据他们自己说)走下去,而且他们也一直是这样的”[14]14。
这种外来探索者和回归者的矛盾状况无疑象征着加拿大人寻求与证实自己身份所表现出来的内心彷徨。弗莱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加拿大人的典型的“边哨心态”,他认为加拿大人是在英国殖民地影响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夹层间生存的民族,困扰他们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这是哪里?”[15]318小说女主人公意识到,“我们踩在脚下的是家园的土地,异乡的疆界(home ground, foreign territory)”[14]9。通过这种时空的矛盾性描写,阿特伍德巧妙地凸现了加拿大白人作为“本土外来者”的矛盾性:他们既在“家里”,又不在“家里”,处于一种文化的居间状态,这是对加拿大民族身份困境的一种形象刻画。因此,《浮现》是一次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回归,是寻求个人归属和文化归属的朝圣之旅,是发现加拿大土地和民族身份内在联系的精神之旅。无名女主人公寻找父亲遗迹、探索曾经熟悉的家园和构建本真自我这三个过程相互融合,成为一次文化民族主义的本土性回归。正如戴维森所说,《浮现》是一个关于“成长仪式”的小说,在魁北克荒野之中,女主人公“终于开启了她自己的身份”[16]38,获得了对自身的真实认知。
在《浮现》中,阿特伍德通过对加拿大人作为外来者矛盾困境的描绘探讨了边界、空间性和民族性的相互关系,强调了本土性回归过程中加拿大地理想象对民族和文化身份的深刻影响。在魁北克北部文明与荒野交界的地带,女主人公发现,“这里就是边界的国度(border country)”[14]26。作者借用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加拿大民族构成的矛盾性,加拿大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各种边界和疆界上的国家,除了讲法语的魁北克人和讲英语的英裔加拿大人之外,还有印第安文化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文化,这种充满内部边界的多元文化构造对加拿大的民族性理解形成了挑战。不过,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暗示了一种解决之道,即通过时空的穿越和交融来建构新的文化秩序。小说中女主人公意识到必须“消除一切”先前的空间和时间,消除关于自我的历史记忆,“必须为自己创造出一片空间”[14]143。通过这种空间隐喻,作者暗示,加拿大文化的构建是在文化本土化基础之上的跨文化多元空间的融合。女主人公意识到,使她与现实“隔离的是时间,我曾经是个胆小鬼,我不愿意让他们进入我的岁月、我的地方。现在我必须进入他们的时空”[14]177。“他们”在此代表了本土历史和印第安时空。这种交融空间呼应了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空间。对阿特伍德来说,加拿大的身份构建并不是对欧洲传统的简单延续,因此,女主人公称加拿大是一个“边界的国度(border country)”,一个超越了重重边界的“表达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 of enunciation)”[17]37。根据巴巴的理论,文化身份总是在这种矛盾和模糊的空间中形成,那种等级性的纯粹文化是不存在的。第三空间使得《浮现》的女主人公表达了加拿大的文化多元状况,凸现了文化差异基础之上的混杂性。巴巴认为,这种“居间空间”承载着文化的一切意义,而对阿特伍德来说,“边界的国度”就是一种“居间空间”,是加拿大摆脱文化殖民主义的一种表达空间,显示了加拿大的不同,也就是加拿大既不是英国殖民地也不是“另一个美国”。
小说女主人公的空间认知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不再取决于空间的有形边界,甚至超越了边界的空间融合。在面对魁北克湖区的广阔空间时,女主人公发现,她和加拿大的地理空间交融在一起,她不仅“被空间包围”,而且“在湖面或我的内部,距离不断地压缩”[14]131。当她不断地接近死去的父亲和母亲的真相时,她“现在懂得了这一切规则。他们不可能存在于任何有显著标记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加拿大的土地是一体的,空间性即是人的存在,因而“他们是没有边界的”[14]132。女主人公进而认识到,“要想和他们对话,我必须进入他们为自己创立的空间”[14]132。通过这样的描写,阿特伍德暗示了地方、空间和民族性乃至主体性之间的相互交融关系,而在后殖民时代的加拿大,作为一个白人定居者为主流的社会,恰好体现了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的这种相互转换。实质上,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地理学中,空间常常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场所,它既是限制性的空间,又是开放的想象空间。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地理是在与人的种种关系中产生的”[18]273,因此空间自然也就承载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成为阿特伍德回归本土性的基础。
显然,居间性的本土混杂空间表达了加拿大的后殖民状况,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状况,也就是说,这种第三空间所表达的独特性内容就在于加拿大的荒野意识,而荒野则是代表加拿大文化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象征,如同美国西部神话一样具有民族性色彩。荒野使加拿大民族性和北方性(nordicity)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北方荒野不仅代表了加拿大独特的地理特征,更是加拿大人的精神世界的反映。正如克雷格所说,在加拿大文学中,荒野和大自然“在加拿大文化和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荒野也成为加拿大作家和艺术家的主要创作源泉”,并且“给所有加拿大人带来了一种自豪感和归属感”[19]15,甚至成为加拿大人内在的环境伦理。弗莱曾经用“灌木丛花园”这样的比喻指出加拿大人的“边哨心态”[15]220。阿特伍德本人也在著名的《存活: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中把荒野、殖民主义心态和加拿大人的生存意识联系起来。在她看来,加拿大北部荒野就是本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象征,“对一个国家或文化的成员来说,他们对地方的共同知识,也就是他们对‘这里’的认知,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的知识。没有了这种知识,我们就不会存活下来”[20]19。在《浮现》中,北部荒野成为加拿大的本土象征,而这片荒野却受到外来力量的侵蚀。阿特伍德通过这种对立性的描写暗示了加拿大在面临来自美国商业和文化影响的状况下所面临的文化殖民主义现状和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文化危机。例如,主人公一行四人看到高速公路旁边到处都是好莱坞电影明星的肖像、纽约大都市棒球队的徽标、华纳兄弟的动画片形象等等,这代表美国大众文化对加拿大精神世界的入侵,代表美国商业消费主义的城市逐渐侵蚀了纯洁的荒野,进入加拿大人的思想和文化空间。在女主人公看来,这些在荒野边缘新兴的小镇和城市“从来不是一个城市,而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边哨地带”[14]7。阿特伍德的描写无疑是对弗莱的“边哨心态”的回应。在她看来,城市化进程中的加拿大在文化上已沦为美国工业化的一个前哨,这种处于文明与荒野之间的矛盾状态反映了加拿大尴尬的文化地位,实际上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和商业化对加拿大的文化殖民入侵。阿特伍德进一步用隐喻描写了加拿大荒野所受到的外来威胁。女主人公看到,大片的白桦树正在枯死,“病毒正在从南方向这里扩散”[14]7。在此作者用“南方”影射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代表北方的加拿大精神空间的侵蚀。小说中高速公路也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象征,主人公看到高速公路两旁竖立起了“通往北方之路”的标牌,并由此联想到“未来就在北方”这句充满美国文化帝国扩张主义的标语[14]9。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路的另一侧却竖立着醒目的标语,上书“维护权利”几个字[14]9,这显然是对加拿大反文化殖民主义的一种暗示。在女主人公看来,魁北克的大小城镇就是一块块“已经扩散了不少的”肿瘤[14]9。女主人公的北方之旅和美国商业化北部扩张因而形成了鲜明对照。对于女主人公来说,北方意味着她的过去和加拿大民族的历史,而对于美国工业化入侵来说,北方却意味着未来的文化殖民同一化。这种并列无疑代表了加拿大民族性构建和美国文化殖民主义的冲突。
在《浮现》中,文化的本土化不仅体现在对本土地理空间的探索上,“居间空间”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就是对印第安民族独特的动物认同的融合和吸纳,这种动物认同成为加拿大民族性构建过程中与加拿大地理空间深度交融的关键。小说中加拿大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遭到了外来游客尤其是美国人的肆意破坏,加拿大的本土空间正在遭受美国消费文化和工业化的侵蚀。女主人公不无讽刺地指出,对那些无节制破坏资源的人来说,“唯一称得上有生命的就是人类,也就是和他们一样的那种人类,穿着得体的衣服,浑身上下挂满了各种饰物的人类”[14]128。女主人公意识到,他们这些人对待脚下的土地根本没有任何敬畏感,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一些国家,动物可以是祖先的灵魂,也可以是一个神灵的孩子”[14]128。以西方英美文化为中心的想象中,动物都是“人形的狗熊和会说话的猪”[14]57,它们只不过是人的变形而已。但是在印第安神话中,人类、动物和植物的边界却是不明确的,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的确,传统印第安神话中女人可以变成狼[21]60-63或者生下幼熊[22]157-60,人的存在和动物的生存是一致、连续的。在此,阿特伍德显然描写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摹人论(anthropomorphism)和加拿大本土印第安民族的摹兽论(zoomorphism)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伦理观的对立。小说主人公逐渐形成了土著人的生命世界观,即人类和其他生物都是一个循环的生命圈,没有哪一个是高等动物,因此也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成为其他生物的主宰,它们和土地一样都是没有区别的存在。这种无等级无差别的生物观和基督教把人置于一切生命中心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女主人公在看到路旁死去的动物尸体时感到“这些动物死去是为了让我们活着,它们是替代的人类”[14]140。
女主人公对印第安动物伦理的本土认同是回归本土性,是构建民族身份独特性的一种深层的文化努力。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和美国游客之间的反差进一步凸现了加拿大本土性世界观的独特性。随着无名女主人公深入魁北克荒野腹地,她逐渐深入到了原住民文化和史前神话主导的文化空间,这里是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核心地带,只有和这种颠覆性的动物观和土地观进行交融才能确立起加拿大不同于英国和美国的身份形象。在《浮现》中,阿特伍德对动物身份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寻求加拿大身份的隐喻。对阿特伍德来说,动物反映了人的态度、情感、道德,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性格象征。阿特伍德在诗歌《那个国家的动物》中借用动物的意象影射了加拿大和美国身份的差异:“在那个国家/动物具有人的脸庞……在这个国家/动物具有动物的脸庞。”[23]48正如莫斯所说,阿特伍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广泛关注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荒野动物、家庭宠物和实验室动物,但这些动物“常常是加拿大身份(或者身份缺失)的象征”[24]121。阿特伍德在《幸存》中通过“动物受害者”明确地把动物和民族身份相互联系起来。她认为“英国的动物故事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故事,美国的动物故事是关于人类屠杀动物的故事,而加拿大的动物故事则是关于动物被屠杀的故事”[20]74。在阿特伍德看来,加拿大的动物故事“总是失败的故事”,动物总是被屠杀而死去,这象征着加拿大民族身份的缺失。加拿大动物故事中那些“被猎杀的生命”的悲惨故事在阿特伍德看来就是加拿大的殖民地地位和作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附属地的受害者的一种政治和文化隐喻。因此,阿特伍德指出,加拿大人“在内心和动物的认同表达了深刻的文化恐惧”,即加拿大人“作为一个民族所感受到的几乎灭亡的威胁”[20]79。因此,在《浮现》中,女主人公和加拿大土地与动物的认同不仅是回归本土性的努力,更是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一次朝圣之旅,因为这样不仅凸现出加拿大和美国、英国文化形象的鲜明差异,更鲜明主张了加拿大的独特民族性格和文学想象。
加拿大学者芬得利在一篇题为《永远本土化》的著名文章中指出,后殖民主义时代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构建不仅应当像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说的那样“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还应当“永远本土化(Always indigenize)”[25]308。本土化使得加拿大在“弱化欧洲中心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小成果”[25]308。《浮现》中的本土化贡献在于,阿特伍德借用女主人公对魁北克荒野的亲身体验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土地观和人类观,表达出强烈的反美主义立场。正如芬得利所说,欧洲中心主义的一大顽固性信念就是“土地空虚论(terra nullius)”,即“加拿大看成一片空荡荡的土地——也就是说渺无人烟的开阔土地,或者把它看成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形式的土地,因而不能达到欧洲的完全‘人类’社会的标准。正是通过这种认知方式,加拿大在立法、宗教、政治和文化上遭受了殖民化的理解”[25]308。
《浮现》中这种人和动物的相互融合不仅体现了加拿大文化中的深层生态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个体身份和加拿大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融合。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身体不再是个体的存在,而是和加拿大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合而为一,因此,个人的身份就是民族的身份,总和加拿大的土地有着内在的关系,它们是不能相互分割的。换句话说,《浮现》是一个关于女主人公身体和加拿大土地、地理空间的平行隐喻或寓言故事。女主人公在小说中不仅是人类一员,更重要的是,她代表了加拿大的地理存在和其间的各种生命形式。女主人公的这种文化象征使小说具有神秘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例如,在小说结尾,无名女主人公最后离开了她的几个同伴,独自来到湖边,化为众多动物中的一员。她的身体紧贴水面,“就像浮游生物一样自由”[14]177,身旁的潜水鸟“对我视而不见,把我接受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14]178。女主人公甚至开始像动物一样吃草根、植物,并在“土地上排便,然后用土掩埋起来”[14]178,她开始“呼唤”自己体内那个“浑身长满皮毛、长着尾巴和角的神灵”[14]181。此时的她最终实现了“人类—动物(man-animal)”这种不可分割的存在形式[14]149。她感到自己的存在就是环境和事物本身的存在:“我斜靠着一棵树,我就是一棵斜靠着的树。”[14]181当人类语言褪去之后,女主人公从自然割裂开来的身体也随之褪去,从而达到了完整统一的本真存在:“我不是一个动物或者一棵树,我是这些树和动物生长和移动于其间的事物,我是一个地方。”[14]181这种主体和客体的模糊性深刻传达了加拿大民族想象中人与地理之间的内在认同。显而易见,阿特伍德所描写的这种人与土地互不分割的存在状态是对土地空虚论的强有力的讽刺,女主人公通过和加拿大土地和环境的相互交融完成了她的探寻历史和根源的精神之旅,同时也象征着加拿大不同于英国和美国的一种崭新的身份面貌。
在《浮现》中,阿特伍德的土地和动物隐喻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体现出加拿大人独特的民族心态和集体认同,还从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等形而上的视角剖析了加拿大人的精神现状。女主人公和死去的父亲代表了和美国完全不同的加拿大的自然观和文化价值观念。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父亲的神秘失踪和加拿大北方的神秘性一起成为女主人公探寻过去和未来身份的核心焦点,是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仪式。父亲选择在远离社会的荒野中心独居,因为他认为人类“是无理性的”[14]59。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总是不可预测”,是受到权力与欲望所支配的,正如希特勒发动的无理性战争一样,这“并非邪恶的胜利,而是理性的失败”[14]59。阿特伍德在此彻底颠覆了传统人类理性主义的思想,把动物和理性相联系,并把人视为毫无理性可言的生物。一方面,这体现了加拿大人独特的人性/动物性相统一的自然生态观;另一方面,阿特伍德通过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视角颠覆了以美国工业和商业发展逻辑为核心的“工具理性主义”的统治,从而暗示了加拿大民族性格中可能存在的另一种不同的文化逻辑和意识形态。的确,小说中美国旅游者对加拿大动物的无理性大肆屠杀就是对阿特伍德所批判的人类无理性思想的最好注解。对女主人公来说,加拿大人不仅要“拒绝成为受害者”[14]191,而且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性形式,也就是动物理性,这种理性形式拒绝把大自然视为人类的他者,并从加拿大的地理想象中构建加拿大人的民族身份。正如女主人公父亲那样,当他选择远离人类社会居住时,他希望“那里除了森林之外什么也没有,除了伴随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存在。当他们说自由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并非完全指它的字面意义,而是说不受干扰的自由”[14]59。女主人公父亲的存在方式就是阿特伍德所赞颂的加拿大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受干扰的自由”和大卫所说的美国式的“自由国度”形成了强烈反差,并更多地和加拿大的土地发生精神上的认同和内化。对阿特伍德来说,这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本身就是一种加拿大人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以自然为出发点,却没有美国式的进步主义和物质主义成分,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统一。正如女主人公所说,美国人对于荒野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他们是快乐的猎杀者,没有节制,没有良心或敬畏感”[14]127,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文明和进步的核心就是“电流的冲击波”和“直接的权力”[14]127,而“只有人类才具有生命价值,也就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类”[14]128。如果说美国人对荒野的文化符号解读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民主和物质进步的话,那么加拿大人的荒野符号则表现的是集体的文化认同、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和土地的认同。换句话说,美国人的荒野文化价值观是以人和社会为中心的,而加拿大的荒野意识却更多地以自然为中心,强调自然和地理特质与加拿大民族性格之间的某种联系。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这种自由更多地表达了人与动物边界的自由和流动性。例如,在《苏珊娜·穆迪日记》中,女拓荒者穆迪发现“最终动物们/开始抵达并在我身上栖息”[4]92。阿特伍德通过诗歌的想象把身体与加拿大空间的边界消解,这是一种更具颠覆性的自由,是加拿大人与土地的深度重合,而非人类社会对土地的殖民统治和利用开发。的确,阿特伍德借助《浮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性,即以物质主义和进步主义为核心的人类工具理性和以生态共生为核心的动物理性,这两种理性对于荒野和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分别代表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与各自的民族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阿特伍德在《浮现》出版约30年后的《疯狂亚当三部曲》中对这种动物理性作出了更加深入的阐述,她通过对吉米这样的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家的工具至上和理性中心主义的讽刺,阐述了人性与动物性统一的思想,把自然抬高到了超越文明的优先地位,描绘出一个与美国理性主义不同的加拿大文化价值观。这种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包含了对土地、动物和人类的共同关照,颠覆了传统自然与文化、直觉与逻辑、男性与女性、情感与理智、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是对加拿大文化和思想状况的再现。《浮现》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加拿大的象征,她既是加拿大土地的化身,又是自然和动物的化身,因此,女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宣布:“我是一个地方”[14]181。小说中地方、自然、动物和人的边界在女主人公抗拒成为受害者的过程中再一次变得模糊,她把自己想象为那只被残害的苍鹭,成为加拿大荒野的化身,遭受着美国入侵者的残害:
不能信任他们。他们会把我当成一个人类,一个裹着毯子的裸体女人。或许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我:如果它逃脱了,没有主人的管束,那为什么不占有它。他们不会知道我究竟是谁。但是如果他们猜出我的原形,我的身份,他们一定会射杀我或者用棍棒打碎我的脑颅,然后把握双脚悬空倒挂在树上。[14]183
在这一段描写中,以占有、征服和开发自然为核心逻辑的美国工业与商业消费价值观充斥着暴力和贪婪。相反,阿特伍德所提出的加拿大的文化与自然价值观不同于美国,人们通过与广阔的自然景观的相互联系定义自我,或者说景观就是自我的内在化地理呈现形式。这也是阿特伍德对弗莱所提出的“这里是哪里?”这个问题作出的回答。通过将民族性与地方相互联系,阿特伍德创造了一种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价值体系,它标志着加拿大想象空间的去殖民化过程和塑造民族身份的文化努力。阿特伍德取消了加拿大文化想象中独特的人性与动物性边界的融合,女主人公的状态可以用阿特伍德所谓的加拿大人“内心的‘动物’”一词来描述,传达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所感受到的几近灭亡的威胁”[20]79。小说中拒绝成为受害者的主题因而是一个具有三重意义的抵抗过程,即加拿大荒野与动物对无节制工业破坏的抵抗、加拿大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对来自英美文化和商业侵略的抵抗,以及加拿大人在定义自我的过程中对文化他者身份的拒斥。
需要指出的是,在《浮现》中,阿特伍德对本土性的描写不只局限在对地理空间的关注上,还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和艺术的本土性,女主人公的旅程因而就和她的精神和文化之旅相互平列。在潜入湖底寻找父亲的遗迹时,主人公坚信父亲一定留下了蛛丝马迹,只要她能够不断接触湖底,她一定能够找到父亲的过去和自己的身份。随着她的发现一步步深入,对父亲的探索成为对土著人的岩石壁画的探索,而对这种史前艺术的痴迷正是加拿大文化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小说女主人公对印第安人的史前艺术的探索也是加拿大移民定居者同这片“外来疆界”进行历史和文化认同、构建民族性的一次重要的精神交融,是对民族本真性的一次探索。在和本土艺术接触后,女主人公逐渐意识到了加拿大在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方面所遭受的文化殖民主义入侵。在小说第六章,女主人公告诉我们,她是一名“商业艺术家”[14]52,她的工作就是给海报、广告、杂志封面设计图案,她最近的一次任务就是为一本题为《魁北克民间神话》的儿童故事书绘制图画。这些艺术创作实质上充满了铜臭味,就连女主人公都承认,“这不是我的领域,但是我需要钱”[14]52。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艺术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美国文化消费市场的需求,因此,女主人公发现商业消费和文化市场的价值观蒙蔽了人们对自己本质的认知,使人满足于表面的统一审美,因而是不真实的。她发现她选择这个职业“是仓皇突兀的决定”,她根本“没有这个本意,……也总觉得非常不自在”[14]52,她的“艺术家”的头衔也像“水肺”或“假肢”一样只是强行嫁接在她身上的,就连童话书中的那些故事“也不是我所期待的”[14]53。的确,在女主人公不断深入加拿大北部的过程中,她不时地看到美国流行文化对加拿大人精神世界的统治,从而强烈地表达了加拿大人的文化殖民受害者的现状。在女主人公的眼中,大卫在和其他几位同伴说笑间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非常滑稽,就像美国动画片中的啄木鸟伍迪和高飞狗那样,和加拿大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文化艺术视角的本土化进一步深入了精神领域,鲜明地突出了加拿大人在意识形态上构建民族性的历史使命,使文学和艺术成为反映民族性格的一面镜子,因而是更加深刻的本土化尝试。对《浮现》中的女主人公来说,对文学和艺术想象的本土化意味着对进入土著居民神话和传说的空间探索,正是这种与加拿大地理和历史空间结合的本土化神话才是加拿大民族身份和想象构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总之,在阿特伍德的《浮现》中,作者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通过小说女主人公的寻父之旅,展现了加拿大人的民族性构建的文化旅途。作者在小说中强调了本土性构建对于民族身份的重要意义,尤其凸现了加拿大在地理想象、空间性、土地和动物伦理以及对印第安艺术与神话的认同,这种地理、文化与精神的本土化呼应了“彻底本土化”的号召,是在文学领域内构建加拿大民族性和身份形象的一次非常关键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