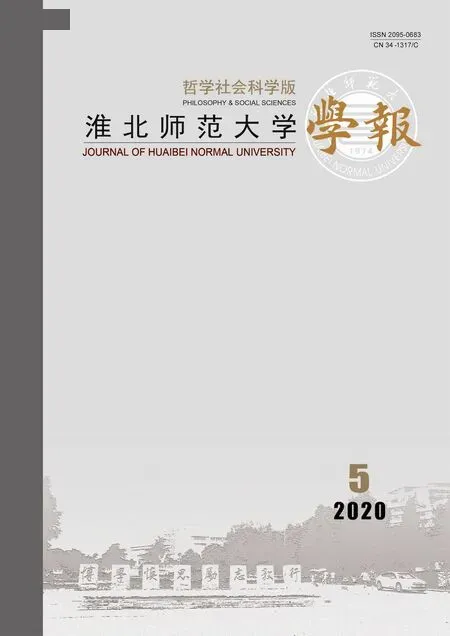句式糅合的界定、研究现状及句式糅合说的解释力
2020-01-19叶建军
叶建军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325035)
近代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句式糅合现象,在历时发展中有的已逐渐淘汰,有的延续到了现代汉语,且已习用化、规约化。汉语句式糅合现象长期以来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这可能与学界对句式糅合现象的认识有关。学界一般认为,句式糅合现象是一种不规范的语言现象。我们认为,糅合是汉语某些特殊句式的一种生成机制,所谓的规范或不规范是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人为性的,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句式糅合现象。近十年来汉语句式糅合现象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尤其是近代汉语中的句式糅合现象。本文拟对句式糅合进行明确的界定,概述汉语句式糅合现象研究现状,并阐述句式糅合说的解释力,以引起汉语学界重视汉语句式糅合现象,加强对汉语句式糅合现象的研究。
一、句式糅合的界定
一提起“句式糅合”,一般会很自然地想到现代汉语中一种常见的语法失误,即“句式杂糅”。众所周知,句式杂糅一般被学界看作一种难以接受的不规范的语言现象。句式杂糅通常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将两个命题义相同的句式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句式。同样一个意思,可以用多个句式来表达,如果言者既想用这个句式表达,又想用那个句式表达,那么就会造成这两个句式混杂在一起。这种句式杂糅的后果有可能是句法结构混乱,句式意义冗余等。句式杂糅的另一种情形是,两个紧邻的具有某种逻辑语义关系的句式,因言者忽视其各自相对的独立性而黏合在一起,往往是把前一个句式的结尾用作后一个句式的开头,生硬地将两个语义不同的句式连成一个句式。这两种句式杂糅现象,学界一般认为具有消极性,是应该避免的。但是我们认为,相对来说,第一种句式杂糅现象往往有一定的可接受性,甚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试比较下面二例:
(1)我们飞行队的人都慌了,不知出了什么事,问调度值班室,他们也不说。(王朔《空中小姐》)
(2)接着他又像刚想起来似地笑说:“刚才我过来,看到美萍一个人在门外抹眼泪,不知出了什么事?”(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上面二例出自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形式完全相同。一般会认为例(2)也应该像例(1)一样使用陈述语气,但是却使用了疑问语气。很显然,这是陈述句式“不知出了什么事”与疑问句式“出了什么事”杂糅的结果。
这种陈述句式与疑问句式杂糅的现象并不少见。再如:
(3)“有一件事我可以替你帮忙,不知道你愿意干不愿意?”周少濂问。(老舍《赵子曰》)
(4)“一定!马来人是由上海来的,父亲看不起上海人,所以也讨厌马来。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看不起上海人?”小坡摇着头说。(老舍《小坡的生日》)
(5)一别将十年,他黄叶飘零也似的生命,不知还遗留在这秋风冷落的人间么?(钟敬文《黄叶小谈》)
(6)那位领导就说:“有这句话就好办一半了。因为政策关系,地富子女上学的机会不多,大半没文化。不知你对这方面挑剔不挑剔?”(邓友梅《兰英——巴黎城内的山东大嫂》)
(7)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吕叔湘早就注意到了此类语言现象,列举了清代白话小说《红楼梦》中三个类似用例:[1]290
(8)你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红楼梦》第二十回)
(9)你到林姑娘那里,看他做什么呢?(《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10)大娘说有话说,不知是什么话?(《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吕叔湘认为,“有些问句,用‘你说’、‘不知’等开头”,“按形式说,是命令句或直陈句包含问句,可是就它们的作用而论,仍然是询问性质。一般的间接问句不能加疑问语气词,但这类句子可以照常加用。我们不妨仍然把它们算做直接问句,把‘你说’、‘不知’等算做发问词”。[1]290吕先生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叶建军侧重考察了晚唐五代时期禅宗语录《祖堂集》中类似的语法现象,认为类似的句式可以看作糅合的疑问句式。[2]259-270值得注意的是,叶建军使用的术语不是“杂糅”,而是“糅合”。
类似的将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合并成一个新的句式的所谓“句式杂糅”现象,无论是在现代汉语中还是在汉语史上,都有一些具有极高的接受度,且往往具有普遍性。如“果不其然”与“果不然”,最早均出现于明末清初,均属于确认事实义句式。如果探本穷源,“果不(其)然”应是由肯定形式的确认事实义陈述句式或感叹句式“果(其)然”与否定形式的确认事实义反诘句式“不其然乎”类糅合而成的。“果不(其)然”逐渐丧失反诘语气,沿用了下来,成为确认事实义陈述句式或感叹句式。[3]笔者认为,不宜将类似的语法现象称为不规范的“句式杂糅”现象,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句式糅合现象。“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所谓的‘规范’或‘不规范’是要受到时间、地域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的,具有相对性、人为性。一些语言现象即便真的是所谓的‘不规范’,但是也可能‘习非成是’”。[2]329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奇特的语法现象,所以我们这里使用中性术语“句式糅合”,而不使用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的术语“句式杂糅”等。
要对“句式糅合”这一术语进行界定,有必要先对“句式”进行界定。学界对句式的理解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句式是根据句子的局部特点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型。句式又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分出一些次类,如以谓语部分的特殊结构为标记,可分为主谓谓语句式、双宾语句式、兼语句式、连谓句式等;以句式中出现的某个特殊词语(如介词、动词等)为标记,可分为“被”字句式、“把”字句式、“对”字句式、“连”字句式、“比”字句式、“是”字句式、“有”字句式等;以句式的特殊语义范畴为标记,可分为被动句式、处置句式、比较句式、存现句式、肯定句式、否定句式等。[4]
关于句式的界定,范晓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句式是“句子的语法结构格式”或“句子层面的语法构式”,“应该把句子语法结构格式和短语语法结构格式区别开来,前者称为‘句式’,把后者称为‘语式’”。[5]其实所谓的“语式”与“句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二者都是句法上的结构式。根据研究实际,没有必要将二者严格区别开来,所谓的“语式”也包括在“句式”中。
这里所说的句式是广义的,特指句法层面的结构式,涵盖了一般所说的句式。它主要用作一个句子或分句,有时也充当句法成分。比如肯定义的“好不A”,可以独立成句,如例(11);也可充当补语等,如例(12)。由于肯定义的“好不A”属于一个句法层面的结构式,因而我们将其看作句式。
(11)店主人遂将相见之事,代张仪叙述一遍:“今欠帐无还,又不能作归计,好不愁闷!”(《东周列国志》第九十回)
(12)行过几处房屋,又转过一条回廊,方是三间净室,收拾得好不精雅。(《醒世恒言》卷十五)
“汉语的句式系统是个开放的系统,其内涵可以因为实际需要有一定的弹性、宽容度、多元性,不必强求一致。事实上,最重要的一些句式大家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作为研究体系和教学体系,或者根据实际需求,句式的内涵完全可以有多有少。”[4]所以对于句式的分类,我们还可以句式典型的语气等为标准,因而有陈述句式、疑问句式、祈使句式、感叹句式等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不使用“构式”这一术语,因为构式语法理论对“构式”的定义极其宽泛,认为构式是语言中形式和意义的匹配体,将构式与语言单位等同起来,将句法结构、词甚至是语素都看作构式。[6]4“构式”这一术语要比我们界定的句式包括的范围广得多。事实上,近些年来学界所探讨的所谓的汉语构式问题,基本上都是汉语句式问题,换言之,讨论的基本上是汉语句法层面的结构式。很显然,用定义极为宽泛的“构式”来指称汉语句法层面的结构式不是最好的选择。既然我们的汉语语法学已有一个为大家熟知的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句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抛弃这个术语。
什么是句式糅合呢?宽泛地说,两个句式只要能合并成一个新的句式,就可以看作句式糅合。但是如果这样处理,那么很多较为特殊的句式都可看作句式糅合的结果,如兼语句式、紧缩句式等,因为这些句式都是由两个句式套叠、紧缩或合并而成的。显而易见,如此处理无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汉语的特殊句式。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句式糅合”作出科学而明确的界定。这里所说的句式糅合,是特指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A 与B,因某种语用目的主要通过删略重叠成分合并成一个新的句式C的过程或现象。例如:
(13)才下到法堂外,师姑问十三娘:“寻常道‘我会禅’,口如铃相似,今日为什摩大师问著总无语?”十三娘云:“苦哉!苦哉!具这个眼目,也道我行脚!脱取纳衣来与十三娘著不得。”(《祖堂集》卷九)
“口如铃相似”就是由语义相同的句式“口如铃”与“口铃相似”糅合而成的。[2]324-325这类语言现象才属于我们所说的句式糅合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概念整合理论所用的术语“概念整合”与我们所说的“句式糅合”是极不一样的。概念整合理论的“核心是多选输入模型结构的整合,认知模型的构建及通过整合产生新创意义;整合理论研究的是心智空间网络动态认知模型的合成原则或发话者参照表征物的合并、完善及深化,对类推、隐喻、双关语、幽默等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理性的阐释力”[7]xvi-xvii。概念整合理论的研究范畴远远大于句式糅合,概念整合理论更加关注的实际上是意义的整合,其虽然也涉及形式与形式的整合,但是并不特别关注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的整合。
二、汉语句式糅合现象研究现状
汉语句式糅合现象其实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吕叔湘先生在20 世纪40 年代出版的专著《中国文法要略》及发表的论文中就有涉及,且均是使用“糅合”这一术语,而不是使用“杂糅”这一术语。不过吕先生仅仅是提及一些汉语句式糅合现象,并未进行更多的阐述。
吕叔湘在讨论被动句式时指出,“事实上,确也有把‘把’和‘被’两种句法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并列举了二例:[1]37
(14)我是被一起子听戏的爷们把我气着了。(《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
(15)算来都不如蓝采和,被这几文钱把这小儿瞒过。(严忠济〔双调〕《寿阳曲》,《全元散曲》)
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均有大量的肯定义句式“好不A”,如“好不热闹”就是“好热闹”的意思,其中的“不”是羡余的。对于肯定义“好不”和肯定义句式“好不A”的来源问题,吕叔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好不’连用,‘好’字有打消‘不’字的作用。这个解说有点说不过去,‘好’字并非一个否定词。这‘好不糊涂’大概是‘好糊涂’和‘岂不糊涂’两种说法糅合的结果。”[1]313关于肯定义句式“好不A”的来源,之后学界提出了“反语说”[8]、“反问说”[9],遗憾的是,均未对吕先生的卓见予以重视。
吕叔湘认为,古汉语中的被动句式“R 为A 所见V”是由“R 见V 于A”与“R 为A 所V”糅合而成的。例如:[10]
(16)壶年九岁,为先母弟表所见孤背。十二,蒙亡母张所见覆育。(《晋书·卞壶传》)
(17)孤以常才,谬为尊先君所见称,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镜之明。(《晋书·秃发傉檀》)
在吕先生看来,“此种句法不免叠床架屋之嫌,故不恒见”。[10]
王海棻注意到六朝以后汉语有一些句式糅合现象,不过称之为“叠架现象”,认为将两个意义相同或相类的句子格式“重合交叠起来使用”,“在语义上犹如叠床架屋”。[11]王先生列举了“被……见……”“为……所见……”两种被动句式的糅合现象,也列举了“不……(以)不”“莫……否”两种疑问句式的糅合现象,[11]不过并未对这些句式糅合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对这些奇特的句式的看法非常谨慎:“这种现象应视为非规范仿古而形成的病句,还是视为一定时期内出现的新句型?笔者尚无定见。”[11]
孙锡信发现汉语史上存在七种糅合的被动句式:(1)“为V 于A”;(2)“为A 见V”;(3)“见V 于A”;(4)“为A所V”;(5)“为A之所V”;(6)“为A所见V”;(7)“为A 之所见V”。孙先生称之为“合成式的被动句”,认为其“是在‘于’字句、‘为’字句、‘见’字句基础上,用交叉或重叠使用表示被动义的虚词和糅合不同的被动句式的方法衍化出来的”。[12]358-360值得注意的是,孙先生也使用了“糅合”这一术语。
孙锡信还发现近代汉语中有被动句式与处置句式糅合而成的句式。[12]364例如:
(18)店家不肯当与,被郭威抽所执佩刀,将酒保及店主两人杀死了。(《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平话》卷上)
孙锡信认为:“这种被动与处置结合运用的句式从逻辑上看是啰嗦重复的,以‘被郭威……’句为例,如果说成‘郭威抽所执佩刀,将酒保及店主两人杀死了’是处置句;如果说成‘酒保及店主两人被郭威抽所执佩刀杀死了’是‘被’字句。现将两式糅合,结果是缺了主语(受事主语因充当‘将’的宾语,不能再在‘被’前出现),又多了‘被’字,造成句子既残缺,又赘余。”[12]364
汉语史上判断句式的糅合现象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袁宾敏锐地观察到,元明时期的文献中出现了两种表示判断的糅合句式,即“主语+是+表语+便是”和“主语+乃+表语+是也”,不过其称之为“混合句式”。[13]221袁先生认为这两种糅合句式是由判断句式“主语+是+表语”“主语+乃+表语”分别与“主语+表语+是(是也,便是)”糅合而成的。[13]221
江蓝生将元代白话文献中的糅合句式“主语+是+表语+便是”记作“S+是+N(的)+便是”,试图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对其产生的动因进行解释。江先生认为,元代白话文献中出现的介绍人物称谓的判断句式“S+是+N(的)+便是”是“汉语与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的判断句相融合而产生的叠加式,即:SVO+SOV→SVOV”,语言接触是元明时期糅合句式“S+是+N(的)+便是”产生的直接动因。[14]
曹广顺也从语言接触的视角观察到了元代白话文献中的句式糅合现象,不过称之为“重叠”或“混合”。[15]曹先生认为,“在汉语与其他语言发生语言接触的时候,汉语固有的与外来的两种意义相近的语法格式,常常会重叠使用,经过一段混用之后,实现归一。就目前所见,这种情况在元代的白话文献中比较多见”,如判断词重叠式、介词与格助词重叠式等。[15]
汉语中存在较多的否定形式的句式与肯定形式的句式同义现象,如否定形式的句式“没VP 之前”在语义上等同于肯定形式的句式“VP 之前”。学界一般认为这种否定形式的句式中的否定词语是羡余的,但是对这种否定形式的句式的来源却一直未进行充分、合理的解释。鉴于此,江蓝生提出了基于概念叠加的构式整合说,并对否定形式的句式与肯定形式的句式的不对称现象进行了解释。江先生认为,“叠加现象的产生是基于词或概念的同一性,这种创新现象,既发生在构词层面,也发生在句法层面”;“所谓句法层面的叠加,是指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叠加后整合成新的构式”。[16]江先生所说的句法层面的叠加,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句式糅合。江先生联系汉语史用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说对正反同义句式“差点儿VP”与“差点儿没VP”等的“生成及语用动机作了统一的解释”。对于汉语史上句式糅合现象,以往的研究侧重于静态描写,而江先生的研究则侧重于动态解释。这是非常可喜的一大变化。不过,江先生的解释主要是从宏观上着手的。
汉语史上疑问句式糅合现象也较为普遍。叶建军在研究唐五代时期禅宗文献《祖堂集》疑问句时发现,其中存在大量的疑问句糅合现象,糅合式疑问句可以分为“祈使句与询问句糅合的疑问句、陈述句与询问句糅合的疑问句、测度问句与正反询问句糅合的疑问句、选择询问句与正反询问句糅合的疑问句等”。[2]259叶建军发现《祖堂集》中除了疑问句式的糅合,还有比拟句式的糅合、判断句式的糅合、感叹句式的糅合等。[2]321-329叶建军也尝试着对这些糅合句式的生成动因进行了解释,并认为“文献的口语化程度越高,句式的糅合现象越突出”,“句式糅合说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汉语史上很多‘奇特’的句式唯有从句式的糅合这一视角才能得到合理而一致的解释”。[2]328
汉语史上存在诸多形式上是双重否定而语义上是一次否定的句式糅合现象,如“拒而不V单”“拒不V单(O单)”“拒O单不V单(O单)”“拒绝不V单”“拒不V双”等。叶建军探讨了这些句式的来源,认为这些句式均是由两个语义相近的否定句式糅合而成的,糅合的动因是兼顾事件的客观性与行为的主观性。[17]
叶建军提出了句式糅合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语义相近原则、时代先后原则和成分蕴含原则(或语义蕴含原则),[18]并对近代汉语中若干句式糅合现象,如“X胜似Y”“被NP施VPNP受”“果不(其)然”、“非得X不Y”“X不如Y较A”“除非X,不Y”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探究了这些特殊句式的糅合机制、生成动因、历时演变或相关问题。[18][19][3][20][21][22]
现代汉语中的句式糅合现象,近些年来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沈家煊用糅合机制对“王冕死了父亲”这类句子的生成方式进行了解释,认为“从糅合的角度看,‘王冕死了父亲’这句话是‘王冕的父亲死了’和‘王冕丢了某物’两个小句的糅合”。[23]沈先生的研究范围基本上限于现代汉语,其所提出的“糅合”实质上是概念或意义的整合。沈先生并不关注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在形式上的糅合。
车录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内涵、分类等方面概述了现代汉语“糅合构式”的基本情况,部分内容涉及了现代汉语中的糅合句式。[24]
总的来看,汉语句式糅合现象长期以来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不多。学界一般认为句式糅合现象是一种偏离常规的语言现象。如汉语史上所谓的零被句“被NP施VPNP受”,在我们看来就是句式糅合现象,但是王力将这种句式视作“脱离常轨”的句式,[25]431孙锡信甚至将这种现象视作“一时的不规范的语言现象”。[12]364学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句式糅合现象的普遍性、多样性、系统性,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糅合实际上也是句式的一种生成机制。因此汉语学界对句式糅合现象或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这就必然导致汉语句式糅合现象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尤其是侧重理论解释的更为罕见。不过近十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特别是近代汉语句式糅合现象得到了应有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既有细致的事实描写,又有深入的理论解释,并证明了糅合是汉语某些奇特句式的生成机制。但是汉语句式糅合现象是开放的,仍然有待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汉语句式糅合现象还存在哪些类别,句式糅合的动因还有哪些等问题,仍有待探究。
三、句式糅合说的解释力
笔者认为,糅合是汉语某些奇特的句式的一种生成机制,句式糅合说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句式糅合说可以科学、合理地解释近代汉语中某些奇特的句式的来源问题。如近代汉语中奇特的“X 不如Y 较A”类差比句式,其语义与“X 不如Y(A)”类差比句式一致,其中的程度副词“较”等是羡余的。“较”等羡余的程度副词的出现,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表层的词语添加问题,而是一个深层的句式生成问题。从句式糅合的三个基本原则及同义句式的共现来看,“X不如Y较A”类差比句式的生成机制是糅合,其当是由“X 不如Y(A)”类不及义差比句式与隐含比较项X 的“Y 较A”类胜过义差比句式糅合而成的。[21]再如具有被动意义的所谓零被句“被NP施VPNP受”,与典型的被动句式“NP受被NP施VP”很不一样。从句式糅合的三个基本原则、同义句式的比较与主语羡余句式“NP受被NP施VPNP受”的生成三个视角来看,“被NP施VPNP受”的生成机制是糅合,其是由被动句式“(NP受)被NP施VP”与主动句式“NP施VPNP受”糅合而成的。[19]如果离开了句式糅合说,近代汉语中这些奇特的句式的来源问题是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的。
句式糅合说还可以纠正汉语学界某些所谓的“定论”。如近代汉语中大量存在的“莫VPNeg”类疑问句式,学界一般认为其属于是非问句式,句式末尾的否定词已语法化为疑问语气词。这是以今律古,从现代汉语的视角来看汉语史上的问题,缺乏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事实上,如果从句式糅合的三个基本原则来看,我们会发现,“莫VPNeg”类疑问句式的生成机制是糅合,其是由测度问句式“莫VP”类与正反问句式“VPNeg”糅合而成的;句式末尾的否定词仍是否定词。[26]句式糅合说能够合理而有力地解决此类句式的来源问题及相关问题。
现代汉语中诸多常见句式,如“X 胜似Y”“X胜如Y”“非得X 不Y”等,我们并不觉得其有什么特别之处。实际上,如果考察其来源,追溯到近代汉语,就会发现这些句式原来都是糅合句式,或者说这些句式原来都是句式糅合的结果。如“X 胜似Y”,始见时代可以追溯至宋代,原来是由差比句式“X胜Y”与平比句式“X似Y”糅合而成的。[18]再如“X 胜如Y”,最早见于宋代,是由差比句式“X胜Y”与平比句式“X如Y”糅合而成的。[18]又如“非得X不Y”,最早可能出现于清中叶,其生成机制是糅合,是由双重否定句式“非X 不Y”与隐含结果“才Y”的肯定句式“得X”糅合而成的。[20]这些糅合句式后来逐渐规约化了,到了现代汉语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不从句式糅合的视角来观察,是无法解释其来源问题的。换言之,句式糅合说可以解释现代汉语中某些常见句式的来源问题,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句式糅合说也可以解释现代汉语中某些词语的来源问题。如《现代汉语词典》所收词语“果不其然”与“果不然”,[27]500如果从来源来看,实际上是糅合句式的规约化或词汇化问题。“果不其然”与“果不然”均始见于明末清初,均属于确认事实义句式,是由肯定形式的确认事实义陈述句式或感叹句式“果(其)然”与否定形式的确认事实义反诘句式“不其然乎”类糅合而成的。二者后来规约化了,成了确认事实义陈述句式或感叹句式,其中的“不”成了一个羡余的否定成分。到了现代汉语,“果不其然”仍是确认事实义句式,但是“果不然”有副词化倾向,不过其词汇化程度不高。[3]如果不从句式糅合的视角来看,便无法回答“果不其然”与“果不然”的来源问题,无法解释其中的否定词“不”为何成了一个羡余成分。
结语
近代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句式糅合现象,具有普遍性、多样性和系统性,有的已逐渐淘汰,有的延续到了现代汉语,且已习用化、规约化。这里所说的句式糅合,是特指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A与B,因某种语用目的主要通过删略重叠成分合并成一个新的句式C的过程或现象。句式糅合现象不能简单地看作不规范的语言现象。所谓的规范或不规范是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人为性的,即便真的是“不规范”的语言现象,也有可能习非成是或积非成是。因此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句式糅合现象。
汉语句式糅合现象长期以来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不多,尤其是侧重理论解释的更为罕见,研究基础尚相当薄弱。不过近十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尤其是近代汉语句式糅合现象得到了应有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既有细致的事实描写,又有深入的理论解释,并证明了糅合是汉语某些奇特句式的生成机制。但是汉语句式糅合现象是开放的,仍然有待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汉语句式糅合现象还存在哪些类别,句式糅合的动因还有哪些等问题,仍有待探究。
糅合是汉语某些奇特句式的一种生成机制,句式糅合说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句式糅合说可以科学、合理地解释近代汉语中某些奇特的句式的来源问题,可以纠正汉语学界某些所谓的“定论”,可以解释现代汉语中某些常见句式的来源问题,也可以解释现代汉语中某些词语的来源问题。我们应该重视句式糅合说的解释力,加强对汉语句式糅合现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