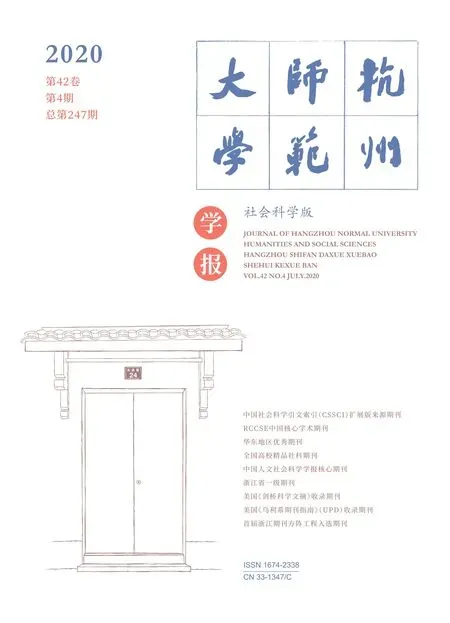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交往及思想地图
2020-01-19彭春凌
彭春凌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一、引论
哲学家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ō,1855-1944)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巨人。他是日本人中第一位哲学教授,自1890年留德归国到1923年期间一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897-1904年间任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长。凡此间东大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宗教学、教育学、社会学、国文学、中国及印度哲学、英文学、德文学各科的学生均受过他的影响;哲学家井上圆了(Inoue Enryō,1858-1919)、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ō,1870-1945)、桑木严翼(Kuwaki Genyoku,1874-1946)等亦均是他的学生。作为日本近代学院哲学、伦理学的开拓者,他融合东西洋哲学,建构了“现象即实在论”的哲学观。(1)关于井上哲次郎的生平与思想,他本人有大量的自述可供参考。重要的几种包括:《明治哲學界の回顧》(东京:岩波书店,1933年)、《怀旧录》(东京:春秋社松柏馆,1943年)、《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富山房,1973年)。在日本近代儒学史上,他亦“位居其首”(2)引语参见卞崇道《论井上哲次郎儒学观》,《东疆学刊》,2004年第3期,第8页。中国研究界也早就有分析总结井上哲次郎哲学观的作品,比如方昌杰、朴昌昱《日本观念论哲学的形成与井上哲次郎》,《东方哲学研究》,1979年12月。,不仅开始以哲学立场研究日本儒学思想史,并且参与明治二十年代重兴儒学的运动,力挽之前西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儒学颓势,其标志即是他1891年推出《敕语衍义》。该书后经文部省审定,作为师范学校和中学教学用书进行推广,一向被认为是《教育敕语》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解说书。他以儒学忠孝伦理为核心建构国民道德论,辅翼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国体。
谈及井上哲次郎与近代中国思想的关系,此前往往循两条路径而展开。一是关注他所编著的多种修身教科书在中国的译介和运用情况,辨析其中新旧伦理的融汇与异同问题。如樊炳清1903年即翻译了井上《新编伦理教科书》,定名为《伦理教科书》出版;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1907年)及其修订版《(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则借鉴井上哲次郎参与编著的《新编伦理教科书》《中学修身教科书》(1902年)两种德育教材,等等。(3)参阅龚颖《蔡元培与井上哲次郎“本务论”思想比较研究——兼论中国近代义务论形成初期的相关问题》,《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1期;周晓霞《一种“思想资源”——井上哲次郎修身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的受容》,《南开日本研究》,2017年。一是在梁启超受明治日本影响的脉络中,爬梳井上哲次郎一系观念的冲击。如梁启超《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新民说·论私德》都留下了参考或阅读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的痕迹(4)参阅荻生茂博《幕末与明治时期的阳明学与明清思想史》,载严绍璗、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8-298页;狭间直树《关于梁启超称颂“王学”问题》,《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李亚《梁啟超による幕末の陽明学の発見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学研究》,2014年,第299-307页。;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论述框架则取自高濑武次郎(Takase Takejirō,1869-1950)的《墨子哲学》。高濑是井上哲次郎的学生,包含《墨子哲学》的《杨墨哲学》(1902年)一书几乎是高濑在为井上学说作代言。(5)参阅末冈宏《梁启超与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末冈在文中还提到,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的《附言》(《新民丛报》1904年第9号,总第57号)涉及武士道精神的部分,是读了井上哲次郎发表在《太阳》杂志第10卷第14号的《时局杂感》后所写。此外,末冈宏《梁啓超にとってのルネッサンス》(《中国思想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史研究会19号,1996年12月,第265-287页)指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清朝的考证学看成是文艺复兴这个观点是从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上得到启示。然而,就章太炎与明治思潮的关联,虽然说近年来学界的研讨续有展开,但井上哲次郎甚至都还没有作为一个思考方向被纳入视野。(6)迄今无论是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もう一つの近代》(东京:研文出版,2006年)、坂元弘子《中国近代思想的“连锁”——以章太炎为中心》(郭驰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还是近年来关于章太炎研究的各种论文,都几乎没有处理过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思想的历史关系。这也导致,迄今对章太炎与明治思潮关联的理解,存在某种结构性的缺憾,难以窥见许多案例背后的内在联动机制。
广泛意义上的西学东渐,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降建立在科学革命和生物进化学说基础上的宇宙及人观念的传播,乃是撬动东亚思想版图的关键驱力。这一点在井上哲次郎和章太炎各自的思想发展历程上,都能得到印证。然而,他们从主要接受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进化学说,过渡到糅合德国形而上学和佛学来重建观念体系和伦理依据,呈现出轨迹乃至细节上高度的相似性。特别是,在章太炎“转俗成真”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深入阅读、援引过姉崎正治、井上圆了、森内政昌等井上哲次郎学生的作品;而几乎还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日本汉学家馆森鸿(Tatemori Kō,1862-1942)的札记《似而非笔》,留下井上哲次郎和章太炎在1899年彼此结识并有多次交流的记录。本文将首次掘发、披露相关证据。这就意味着,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并不是两颗运行轨道相似的“孤星”,太炎思想历程中很多看似偶然的遇合,大概率属于有意识的主动行为。而他们所涉及的中、日、英、德几种语言圈人际交往、观念迎拒的复杂线索,更辐射出一幅繁星满天的思想地图。由此出发,进化学说揭示出的宇宙本性(cosmic nature)与伦理本性(ethical nature)之间的冲突(7)这里用的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说法,参阅Thomas. H. Huxley,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5.p.viii。,在环球的同一个时空中,就呈现出普遍性;而各个文明的思想家所作的解答,又显露出差异性。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不仅作为思想史的历史主体(the historical subject),并且还各自作为近代观念传播与生产的历史中介(the historical agency),其价值,惟如此方得彰显。
二、一段呼之欲出却似踪迹难寻的关系
在外来学说的冲击下调整自身思想,井上哲次郎和章太炎的经验轨迹呈现高度的相似性,即他们都先是深受以达尔文、斯宾塞为主,由英语世界传入的生物和社会进化学说影响,而随后又融合佛教和德国哲学来解决深层次的形而上学问题。只是从时间上讲,井上哲次郎远早于章太炎。
井上哲次郎曾对吴汝纶如是讲述自己精神上学问大起的过程,“明治十五六年之顷,进化论始入我邦,而精神上之问题始起,同时基督教传来,博爱平等之说亦行,因讲究哲学。虽此后尚有世运之变,本于精神上之议论者为多”[1](《井上哲次郎笔谈》,P.89)。井上哲次郎出生于福冈,他自小跟从汉学者修习《诗经》《尚书》《左传》等经典,从事经史研究、作汉诗,13岁左右学习英文。明治四年(1871年),他17岁时去长崎,在广运馆学习,并由英美人以英语教科书授课。明治八年进入东京开成学校预科,明治十年(1877年)在刚刚成立的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主修哲学。1877年,美国人莫斯(Edward S. Morse,1838-1925)即在东京大学理学部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1878年,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芬诺洛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被聘任为东京大学的外国人教师,并成为了井上哲次郎的老师。在芬诺洛萨和外山正一(Toyama Masakazu, 1848-1900)的推动下,东京大学成为日本传播斯宾塞进化学说的基地。(8)关于日本对斯宾塞的接受,参见山下重一《明治初期におけるスペンサーの受容》,载日本政治学会编《日本における西欧政治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山下重一《スペンサーと日本近代》,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83年。井上哲次郎后回忆起芬诺洛萨时说:
进化论在当时俄然流行起来,差不多在我国学界呈风靡之势,我们学生也以非常的兴趣对之进行研究。然而同时,我们学生也读施韦格勒的哲学史,乌伯维格的哲学史。不只是接近德国的哲学思想,又同时听原坦山氏《大乘起信论》的讲义。通过《起信论》的讲义,不仅知晓了“真如实相”,并且思考德国哲学中也有和其相似的思想。通过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斯宾塞所言的进化主义的哲学等,无法解决哲学的困惑;寻求另一种比它更深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之念头便旺盛起来。[2](P.202)
施韦格勒,井上原文作“シュヱグレル”,指的是德国哲学家和新教神学家阿尔伯特·施韦格勒(Albert Schwegler,1819-1857)。乌伯维格,井上原文作“ユーベルウェッヒ”,指的是德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弗里德里希·乌伯维格(Friedrich Ueberweg,1826-1871)。井上哲次郎当时主要通过英译本来了解德国的哲学思想。原坦山(Hara Tanzan,1819-1892),曹洞宗僧侣,1879年任东大印度哲学科最初的讲师。井上哲次郎对佛教和德国哲学的关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明治十六年(1883年)正式出版的《伦理新说》,就是他早期诞生的成果。该年亦正好印证他和吴汝纶谈话中提及的“明治十五六年之顷”。井上哲次郎后来回忆说,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对于所谓进化论者,总觉得虽然能确认其为正确的科学上的一新说,但归根结底仅仅是关于现象的理论”,不能用进化论来解释世界,“因为世界不仅有现象,还有现象以外的实在,实在并不跟从进化的法则”。由此,他反对“以进化论来包含哲学的全体”,此即《伦理新说》出版的缘起。而他此后“关于哲学、伦理、宗教等的主张,和当时《伦理新说》所述的内容也是一贯的”。[3](PP.241-242)《伦理新说》的主旨乃“本于化醇主义,遵循化醇的纪律,以达于完全之域作为道德的基址”[4](《绪言》,P.5)。“化醇”亦正是井上哲次郎早期为进化(evolution)拟定的汉字译词。(9)井上哲次郎等编的《哲学字汇》将“evolution”翻译为“化醇、进化、开进”,在“化醇”一条后说明道:“按:《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疏》‘万物变化而精醇也’。又‘醇化’之字出于《史记·五帝本纪》。”见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增补《哲学字汇》,东京:东洋馆,1884年,第42页。
进化的宇宙观带来的伦理冲击,成为井上哲次郎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他始终相信自己站在理想主义的一侧,与部分进化论者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机械主义进行战斗。[5](P.73)
井上哲次郎的自述,符合后来思想史家对他的判断。即从1880年代中期开始,井上哲次郎就展现出,“将西洋思想和传统思想包括进同一次元之中,并从此出发来构筑统一的思想体系”。“现象即实在论”洗练表达了井上哲次郎一贯的思想体系,也是他作为日本型观念论确立者的标志。其名称虽然最早见于1894年的《我世界观之一尘》,但其基本构想在1883年的《伦理新说》中已经差不多表现出来。历经1897年的《现象即实在论的要领》(刊于《哲学杂志》)、1900年的《认识与实在的关系》(刊于《哲学丛书》),该理论最终完成。(10)参阅渡边和靖《明治思想史:儒教的伝統と近代認識論》(增补版),东京:ぺりかん社,1985年,第99、109页。换言之,在1884年官派留学德国之前,井上哲次郎已经开始结合德国哲学与佛学来建构新的实在论,以抵制进化主义对于儒教既有伦理秩序的挑战。这也就是他自己所标榜的,从《伦理新说》开始,思想“一以贯之”,此后数十年只是把疑问“次第通过经验与学问得以确定” [3](P.242),而并非有所更革。也有论者因此而讥讽他,在70余年的思想活动中,体现出“看不到一点动的发展之停滞性”,即便留德六年也是“不毛”,“也仅仅是摆弄式的为了装饰‘实在’而获取名辞,结局是什么也没学到”。[6](PP.115-116)
章太炎在《菿汉微言》中自述,“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所谓“转俗成真”,指的是从早年专注于儒学中的荀学一派,在“囚系上海”的1903-1906年转向接受佛教,特别是其中的法相唯识学。他出狱之后,即“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融合“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7](PP.60-61)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则有对出狱后思想活动更详细的描绘:“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按:即叔本华)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楞伽》《瑜伽》者。”[8](PP.1-2)可以说,太炎“转俗成真”之后的主观唯心论,即主要得益于唯识佛学与以德国哲学为主的西洋哲学之交互熏染。(11)这一点,小林武在《章炳麟と明治思潮:もう一つの近代》(第175页)中已有所分析和揭露。
太炎自称 “转俗成真”之前,“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 [7](P.60),也仅仅能概括他早期思想取自于中国既有传统的这个侧面。事实上,虽然不能直接阅读英文书籍,太炎早年和井上哲次郎一样,大量摄取由西洋传入的近代知识。他在诂经精舍时期即“近引西书,旁傅诸子” [9](《与谭献》,P.12);1897年就宣称志愿是“以欧罗巴学上窥九流”[10](《〈实学报〉叙》,P.27)。而最终,是斯宾塞从宇宙天体演变到人类社会形成、文明变迁无所不包的进化学说,给予他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框架,来阐述宇宙、生物、人类文明(包括古代神权与王权、语言和文字、法律与宗教、各种礼仪风俗等诸种表征)的由来和演变。(12)关于斯宾塞进化学说与章太炎早期文化观的关系,参阅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7-39页)、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2辑),以及彭春凌《关于“变化”的观念碰撞和知识生产——全球史视域下的汉译〈斯宾塞尔文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8期)、《章太炎儒术新诠中的近代学术嬗变》(《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何为进步:章太炎译介斯宾塞的主旨变焦及其投影》(《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1898年,他与曾广铨合译了《斯宾塞尔文集》,登载于《昌言报》一至八册(第七册未刊)。此即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Essays:Scientific,Political,andSpeculative)中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ItsLawandCause)与《礼仪与风尚》(MannersandFashion)。两篇汉译名为《论进境之理》《论礼仪》。他随后的著作《儒术真论》(1899年)、《訄书》初刻本(1900年)就多方面展示了斯宾塞学说的影响。《儒术真论》及附文《视天论》、《訄书》初刻本之《公言》《天论》诸篇,承续斯宾塞多次推荐的星云假说(Nebular Hypothesis)及基于机械论(Mechanics)的宇宙观念,倡导“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 [11](P.1507),来否定超绝于人间的神秘力量。《訄书》初刻本《原人》《原变》《族制》诸篇讨论生物、种群的演变和进化,彰显斯宾塞所宣传的拉马克主义“用进废退”理念。《订文》涉及语言文字的变迁,有大段篇幅直接引用《论进境之理》的译文。至于《冥契》《封禅》《河图》《榦蛊》诸篇,梳理古代社会早期的权力结构、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化,几乎是在演绎《论礼仪》篇的题旨。
值得一提的是,太炎彼时相信,进化学说所揭示的宇宙天体运转、演变的规律,至少在太阳系的范围内,是至确的“公言”。如谓,“若夫宗教之士,剸其一陬,以杜塞人智虑,使不获知公言之至,则进化之机自此阻”。[12](《公言》中,P.14)《冥契》描述早期人类社会所有文明的统治者,都集世俗与宗教权威于一身,谓:“彼神灵其国主,翕然以为出于朱鸟权衡之宿。其于中夏,壹何其矩范之合也?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凡长人者,必雄桀足以欺其下,以此羑民。是故拱揖指麾,而百姓趋令若牛马。章炳麟曰:大哉黄中通理!”[12](《冥契》,P.29)“黄中通理”,典出《易·坤》“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孔颖达疏曰:“黄中通理者,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职,是通晓物理也。”[13](P.38)《冥契》一篇三次使用了该词,这里表达的正是他对斯宾塞社会进化学说解释力的信服。
可以说,章太炎学问“转俗成真”的过程,也是他融汇佛学和德国形而上学,对宇宙、生物、社会之进化学说所带来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问题进行深刻反省的过程。1906年的《俱分进化论》,称索宾霍尔(叔本华)“稍稍得望涅槃之门”,“索氏之所谓追求者,亦未尝不可称为进化”,并对“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观点予以反唇相讥。[14](PP.1-2)《四惑论》批判“以进化为主义者”的“进化教”[15](PP.13-14),即可见一斑。
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思想关系,还不仅仅表现在他们有相似的发展轨道。耐人寻味的是,在章太炎发生思想变化的过程中,他汲取了不少日本论著的营养,其中关键的几种,就出自井上哲次郎的学生,姉崎正治(Anesaki Masaharu,1873-1949)、井上圆了与森内政昌(Moriuchi Masayoshi,?-1907)。太炎1902年2月第二次东渡日本,极为关注姉崎正治的宗教学著作。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包括《原学》《清儒》《通谶》《订文》所附《正名杂义》及《原教(上)》等多篇文章,都有段落出自姉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及《上世印度宗教史》;《原教(上)》更几乎全篇译自《宗教学概论》的附录《宗教概念的说明契机》。(13)参阅小林武《章炳麟〈訄書〉と明治思潮——西洋近代思想との關連で》,《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5集,2003年,第196-210页;彭春凌《章太炎对姉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3-115页。1903年,太炎与人合译了井上圆了的名著《妖怪学讲义》,其中的宗教观念,影响到太炎的《建立宗教论》。[16](PP.24-33)1905年,章太炎囚系于上海监狱时写成《读佛典杂记》,该文主要借鉴的作品,就是森内政昌的《认识与实践、实在观念与理想观念》(《認識と實踐、實在觀念と理想觀念》)。森内这篇文章刊载于1900年井上哲次郎所编《哲学丛书》第1卷第3集。《读佛典杂记》留下了章太炎衔接佛学与叔本华哲学的痕迹。(14)详细讨论,请参阅彭春凌《章炳麟〈読仏典雑記〉と井上哲次郎編〈哲学叢書〉》,神户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第93号,2019年12月。
虽然说,无论思想的大致轨道还是具体痕迹,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联系紧密;他们之间的某种交往关系可以说呼之欲出。然而,迄今无论是《章太炎全集》《年谱》,还是各类传记、选集,(15)比如最新的《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017版,2018年20卷本)、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都难以寻觅到他们交往的记录。诡异的是,章太炎生平的不同阶段,共有三次集中回忆他和日本学者的交往,加上文章中直接的援引,对象遍及井上哲次郎在东京帝国大学各个年龄阶段的前后辈同事、学生,却没有井上哲次郎本人。一是1899年太炎《致俞樾》函中,谈到他对若干日本学者的印象。除了彼时已经过世的冈本保孝(1797-1878)、安井息轩(1799-1876)、照井一宅(1819-1881)等汉学家外,还特别提到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重野安绎(Shigeno Yasutsugu,1827-1910)和根本通明(Nemoto Michiaki,1822-1906)。这两位是井上哲次郎的前辈,彼时都年逾七十,太炎评价重野安绎“宗祢方、姚,不越其则”;根本通明则是“独精《易》说,宗仰定宇,亮为奥博”。[9](PP.8-9)二是1911年的《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太炎猛烈抨击明治汉学。除了老一代的重野安绎、星野恒等人外,他特别针对彼时东大汉学的中坚力量,比井上哲次郎年轻10岁左右的服部宇之吉(Hattori Unokichi,1867-1936)和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1865-1942)。[17](PP.85-87)三是1931年,太炎与桥川时雄(Hashikawa Tokio,1894-1982)谈话,提及帝国大学的汉学家,重点依旧是根本通明、服部宇之吉和白鸟库吉。[18]
从引用来看,除了上文提到的姉崎正治、井上圆了与森内政昌外,太炎亦偶有援引井上哲次郎学术圈周边其他人的成果。比如1902年《文学说例》一段引文出自《加藤弘之讲论集》。(16)此即章太炎《文学说例》(刊《新民丛报》,第15号,1902年9月2日)内自注出处,曰:“案蒲斯门人种,以同部女子为男子所公有,故无夫妇妃耦之言,妇人处子,语亦无所区别,见《加藤弘之讲论集》”(第52页)。经查,这段文字本于《加藤弘之讲论集》第1,载加藤照麿编《男尊女卑の是非得失》,东京:金港堂,1891年,第62页。加藤弘之(Katō Hiroyuki,1836-1916)是东京大学早期的综理、总长(相当于校长),长期与井上哲次郎共事。井上批判进化论者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多半指向加藤弘之。加藤弘之和重野安绎一样,都是井上哲次郎《怀旧录》中予以专章纪念的人物。章太炎1904年《訄书》重订本《订孔》篇征引了桑木严翼《荀子的论理学》。[12](《订孔》,P.133)桑木严翼是深受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哲学家。他先是井上哲次郎的学生,于1896年毕业于帝国大学文科哲学科,1914年又返回东京帝大任教,成为井上哲次郎的同事。(17)参阅笠松和也《戦前の東大哲学科と〈哲学雑誌〉》,见东京大学哲学研究室《哲学雑誌》のアーカイヴ化を基礎とした近代日本哲学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分析的研究,基盤研究(B),18H00603。太炎1906年的《诸子学略说》,谈到村上专精“以为因明法式长于欧洲”。[19](第5册,P.2193)村上专精(Murakami Senshō,1851-1929)是明治时代著名的佛学者、佛教史家。他虽然迟至1917年才到东京帝大担任印度哲学讲座,但井上哲次郎对他的情况非常熟悉,还高度评价《因明学全书》在整理印度系统论理学上的贡献。[20](P.51)
也就是说,东京帝国大学由井上哲次郎辐射出一个人际和思想的圈子,章太炎几乎和这个圈子的重要人物都有某种点对点的关系。但由于一直未有发现井上哲次郎和章太炎的直接联系,致使太炎和这个圈子中心机轴部分的关系色调灰暗。哪怕周围有星星点点的光亮,只要机轴没有点亮运转,就始终难以参透太炎思想与明治思潮,乃至与19世纪末欧亚思想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笔者最近翻检1899年章太炎第一次旅日期间日本方面的记述,找到了他和井上哲次郎交往并多次交谈的确凿证据,从此出发再重新梳理太炎与这个圈子的思想关系,直有“以无厚入有间”之感。
三、原是旧相识
1899年6月10日,章太炎在好友日本汉学家馆森鸿(Tatemori Kō,字子渐,1862-1942)的陪伴下,从基隆出发搭乘横滨丸,于14日抵达神户,开启了他的第一次日本之行。他8月16日从横滨启航,搭乘神户丸,经神户返回上海。太炎一共在日本待了两个月,游览了京都、东京等地,拜会了数十名日本学者。馆森鸿将二人的游踪以及太炎此间所作诗歌和笔谈,写成札记《似而非笔》,以“袖海生”为笔名,登载于同年10月1日至11月10日《台湾日日新报》“落叶笼”栏目。(18)大山昌道、林俊宏《19世纪末中日学术交流的一幕——以馆森鸿〈似而非笔〉为中心》(《鹅湖月刊》总第426期,2010年12月,第25-34页),率先依据《似而非笔》,大致还原了此次太炎访问日本,参观游览各地,拜访数十位日本汉学家的经历。文章最可贵的地方,在于结合日本外务省档案,几乎考察了章太炎每一天的居住地、行程。文章提及章太炎会面的日本汉学家中有井上哲次郎,并且在论述“章太炎与根本通明”时,谈到章太炎在与井上哲次郎见面时,读到根本通明的《读易私记》。虽然该文仅止于此,未对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交往和思想关系作任何分析梳理;但本文从这两处简单的描述中得到启发,通过深入阅读《似而非笔》,发现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交往的其他细节,进而重构他们的思想关系。此外,关于章太炎与明治汉学的关系,笔者另有文章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似而非笔》中馆森鸿记述的部分用日语书写,摘引章太炎笔谈的部分则直接采用太炎本人的中文书写。其中,日文的记述部分有两次,中文的笔谈部分有一次,一共三次提及井上哲次郎。
第一处是日文叙述:“枚叔在井上哲次郎处一见健斋的《读易私记》,评论道……”(原文:“枚叔は井上哲次郎の處に於て健齋が讀易私記を一見し評して曰く……”)。[21]
第二处也是日文叙述:“闻知井上哲次郎住在近邻,时常和枚叔谈话”(原文:“聞く井上哲次郎が近鄰に住し時々枚叔と談せりと”)。[22]
第三处则是馆森鸿与章太炎交谈,馆森鸿引用李白《嘲鲁叟》“鲁叟读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芒若坠烟雾”,来感慨迂阔儒生以精力注于著作,以待千载知己的虚妄之感。下面录有太炎的笔谈答语:“枚叔曰:子云没身之后,人尚知重其书,若处今日则生时书或可传,十年后则渐微矣。百年则如水之涸矣,千年则如火之熄矣。若欲待之,如入深谷,步步愈近暗处,此所以可慨也。然而亦有以文学自命,不营仕官者,则非如井上哲次郎之学不可也。”[23]
章太炎6月14日抵达神户后,先是游览了京都,经大津、名古屋,6月18日抵达东京。在东京期间,6月21日他就迁往小石川梁启超的寓所居住。此后梁启超虽然带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到镰仓参观、游览江之岛等,梁启超于小石川的寓所是太炎在东京的固定居住地,直到8月15日他离开东京,从横滨归国。小石川位于东京大学本乡校区附近。据井上哲次郎的儿子井上正胜记述:“父井上哲次郎,从明治二十三年从德国留学归朝以来虽然短期之内住居未定,但从明治二十五年以来一直住在小石川表町一〇九番地(现在东京都文京区小石川三丁目二〇番一一)。”[24](P.88)井上哲次郎1892年开始,就一直住在小石川。这也从侧面证明,馆森鸿所言井上哲次郎和章太炎住在“近邻”,是确凿的记录。
梁启超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和东京哲学圈多有接触。1899年5月13日在麴町富士见轩举行了哲学会春季大会,参与者包括加藤弘之、重野安绎、井上圆了、元良勇次郎(Motora Yūjirō,1858-1912)、中岛力造(Nakajima Rikizō,1858-1918)等20余名日本学者,在姉崎正治的介绍下,梁启超发表了《论支那宗教改革》的讲演。(19)《哲学会》,《哲学杂志》第14卷第148号,1899年6月10日,“杂报”,第487-488页。另外,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刊于《清议报》(1899年6月28日),在序言中,梁启超也提到了哲学会邀请他讲演的情况。参阅《清议报》(影印本)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31页。梁启超因和东京哲学圈有联系,或许充当了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引介人。住得邻近、又有近两个月的时间,这使得章太炎和井上哲次郎有机会时常交谈。馆森鸿只记录了其中一次相见的情况,即章太炎在与井上哲次郎那里,读到了根本通明(健斋)的《读易私记》,并发表评论。由笔谈来看,章太炎和馆森鸿都对当时情势下,读书人乃至知识的命运深表忧虑,都感到如像以往儒生一样,追求著述以待千载,是十分虚妄的。太炎甚至说,读书人在世时书或可传,时间愈往后推移,影响愈步入暗处;十年微,百年如水涸,千年如火熄。但也有例外——“亦有以文学自命,不营仕官者,则非如井上哲次郎之学不可也”。换言之,不依靠官场权力,而想著述流传千古,除非有井上哲次郎那样的学问才可以。这是太炎对日本学者作出的最高评价。在传统知识普遍式微的情况下,太炎认为,井上哲次郎代表了读书人未来的方向。此次日本之行,太炎对日本学者有褒有贬,他完全没有必要出于客套来说这番话。这个评价,是他多次和井上哲次郎交流后的由衷感言。
那么,井上哲次郎究竟和章太炎多次交谈中聊了哪些内容,让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呢?馆森鸿的札记并没有明确记录。即便如此,通过井上哲次郎这个阶段的思想状态、他和中国知识人交流时一般会涉及的话题,以及比照太炎旅日期间的其他言论和他此前此后的思想,仍旧可以大致框定井上哲次郎和章太炎交谈的内容。
中国知识界对井上哲次郎有所了解,是始于他留德期间。1887年,德国政府基于俾斯麦的东方政策,创办了柏林大学附属的东方学校。井上哲次郎因官派留学期限已到,为了能继续留在德国学习,遂在该校担任日本语教师。在这里,他认识了担任中国语教师,教授北京话的满族人桂林(字竹君)和教授广东话的番禺人潘飞声(1858-1934,号兰史),三人经常作诗酬唱。通过他们,井上哲次郎又结识了柏林中国公使馆的姚文栋、陶榘林等人。《申报》1889年就对井上哲次郎的事迹有零星记载,既有他为潘飞声《万里乘槎图》题诗(20)《题潘兰史先生万里乘槎图》,《申报》第9版,1889年3月30日。全诗如下:“五羊才子乘槎客,得意长风迭远游。剑气拂来重海日,诗声吟过万山秋。定知草稿红关济(时君方草柏林游记详论德意志用兵之法),翻喜萍纵共唱酬。何日招邀泛牛斗,樱花红处是瀛洲。(君约异日游日本)日本井上哲君迪稿。”,又有关于他的流言,如他用德语讲演,批评“日本风俗惟妇人最坏,动辄离婚他适,又每日必向浴堂洗澡”云云,引起日人公愤。[25]而向国人介绍井上哲次郎事迹最多的,是潘飞声。井上哲次郎1889年为潘飞声《西海纪行卷》作序。1890年7月,他们又一起乘船从欧洲出发东归,经意大利、红海、锡兰、新加坡抵达香港。潘飞声将这一路的见闻包括和井上哲次郎的酬唱之作,编成《天外归槎录》刊行。1905-1906年间,潘飞声担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其间所作诗话,后辑入《在山泉诗话》,这也是香港的第一部诗话。诗话有《井上哲》一篇,其文曰:
在柏林时,日本文士多往来游宴,有哲学博士井上哲最称莫逆。井上字君迪,挟书百箧,著作千编,能以英、德、法语演说。年仅三十,而劬学博涉无出其右,德人皆称之曰井上先生。与余同为东校长,邻居三年,归又同舟,海外文字缘,证以佛氏,必非无因者。生平最深哲学,所论见吴挚甫京卿《东游丛录》。复有《巽轩诗文》二卷,诗皆少作,盖井上不欲以诗名也。兹录其数首,亦清新可诵。[26](P.30)
《东游丛录》是吴汝纶1902年赴日本考察教育的记录,内有井上哲次郎的长篇笔谈。潘飞声认为《东游丛录》所载井上哲次郎之论说,和自己10多年前与其交往的印象相当。这恰好又证明了井上哲次郎从《伦理新说》(1883年)开始,思想一以贯之。而潘飞声对井上哲次郎“劬学博涉无出其右”的评价,和章太炎“非如井上哲次郎之学不可”的震惊感,也极为相似。1899年井上哲次郎与章太炎交谈的内容,大体也不会越出1887-1890年间潘飞声对井上哲次郎的记录,以及1902年《东游丛录》井上笔谈的范畴。
潘飞声以及《东游丛录》展示的井上哲次郎,思想主要呈现两个方面的特点,而它们都能在章太炎1899年左右的言论中找到共鸣或某种回应。
第一,井上哲次郎既博通西学,又有强烈的东洋思想学术自觉,乃至亚洲连带感。
对明治初期激进西化浪潮的反省,是井上哲次郎大学时期学问的出发点。他认为东洋有西洋未尝研究过的固有之哲学,主张将东西洋思想纳进同一次元。他的哲学方法论强调西方对东洋哲学的重视和东洋哲学的视野。[5](PP.85-86) 1890年井上哲次郎一行人抵达锡兰岛时正值月夜,潘飞声赋诗一首:“飞轮不碍重溟阔,日月星辰近可呼。山矗波涛随处有,诗开榛莽古来无。客心渐放倾洋酒,舟夜多闲译地图。幸与故人相慰藉,防身一剑未嫌孤。” [27](《将抵锡兰岛月夜得句同竹君君迪作》,P.142)“日月星辰近可呼”不仅是海上观天的特殊效果,亦是洋酒微醺之后心象的放大,颇有诗仙太白“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浪漫感。难怪井上哲次郎多年后追忆起来,都难忘潘飞声的“诗才”。[28](P.327)写同题之诗,井上哲次郎则更显哲人的理趣,“西溟月即东溟月,来照归舟意倍亲。旧梦关山经七载,此时尊酒更三人”。[29](P.143)西溟月和东溟月又有什么分别呢?明明空中只有一个月亮,所谓东西不过是站位差别所致。东西精华融于一冶,对应着井上哲次郎“现象即实在论”所追求的那个实在。他后来向吴汝纶介绍日本教育时,也说“敝邦教育,以融合调和东西洋之思想为目的。自然科学,莫如西洋,然唯取自然科学,而无精神以率之,则将不堪其弊。故以我精神运用之,此我教育所由而立也”;总而言之,“今日之伦理,非打东西之粹而为一冶不可,我邦学者所努力在此”。[1](《井上哲次郎笔谈》,PP.86-87)
如前文所述,“近引西书,旁傅诸子”,“以欧罗巴学上窥九流”是太炎戊戌时期主要的学问追求。这些话也有融东西洋为一冶的意思。在访日期间,他也屡有类似表述。比如,他翻阅重野安绎门生所撰有关子学的论文二三十册,表示“弟实觉其可喜,以子家合西学,是弟素志也”[30]。馆森鸿谈及西人大量翻译日本和中国典籍时,章太炎评论说,“大抵天资高者,必能知西学经学之互相为用。若天资中等者,宁使讲西学而为有用,勿使讲经学而为无用也。若天资最下者,讲西学则炫耀新奇而不知实体,讲经学则株守陈腐而不能旁通,是无一而可也”[31]。井上哲次郎受过传统经学训练,能写漂亮的汉文汉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英、德、法三种语言十分流利,可进行讲演,并且还学习过意大利语、梵语、希腊语及拉丁语,以用于研究。就连西班牙语、荷兰语、丹麦语的书籍,他也可以借助辞书进行阅读。(21)井上哲次郎的语言能力参见他的自述,见井上哲次郎《八十八年を顧みて》,《怀旧录》,第334页。他本身的能力和他融东西洋于一冶的主张是完全匹配的;观其人听其言,自然会得出其人“知西学经学之互相为用”天资极高的印象。相较而言,章太炎虽然也主张以子家合西学,但毋庸讳言,不通西文,多少令他难以施展抱负。太炎自知其短,这也是他由衷感慨著述如要传世,“非如井上哲次郎之学不可”的重要原因。
井上哲次郎虽然强调伦理上也要融合东西,需弥补古来所缺乏的“崇人格之观念”,“重个人之权利”,“自由平等之精神”[1](《井上哲次郎笔谈》,P.87);然而,他始终对基督教博爱平等之说保持警惕,认为其极大挑战忠孝观念,就如同墨学异端挑战孔孟正统。[32](P.3)博爱平等也不符合《教育敕语》忠孝一体之精神。先不论双方对儒学忠孝伦理的定义有差别,至少从大面上讲,章太炎此一阶段和井上哲次郎一样抵制基督教,主要在其宣传“宠神上帝,以为造万物” [12](《天论》,P.16),并引发众多教案。基于荀学的立场,太炎驳斥“欲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10](《平等论》,P.24)的平等说。在伦理观上,他和井上哲次郎还有不少共鸣。
1889年9月,由井上哲次郎召集,日本人日高真实、千贺鹤太郎,暹罗人袁森,印度人杜鲁瓦、那萨尔,中国人陶榘林、姚子樑、桂竹君、潘飞声与张德彝参与,组织了“东亚洲会”,也称“兴亚会”。随洪钧出使德国的张德彝,在《五述奇》中记录了相关情况。潘飞声所著叙文,阐述西力东侵,“萌芽于明季,纵肆于今日,以致藐视南洋,蚕食印度,全洲披靡,罔不郁其怒而不敢鸣”,亚洲各国必须联络以自强。“无问中与日、印度、暹罗各国也。同洲之国,当以同国视之。如兄弟,如手足,戮力同心,共修国政,以御外侮。”井上哲次郎与杜鲁瓦的发言,则强调东方文明自身的本位意识,“谓西国之物大半创自东方,今西人讲求精益求精,吾人游历非为尽学其所能,无非择其所长以补我所短而已”。[33](PP.339-341)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立了诸如“兴亚会”(1880年)在内的组织。[34]井上哲次郎在柏林召集兴亚会,从思想到组织形式,都是日本国内亚细亚主义的延长。将亚洲视作一个命运共同体,特别能拉近中日知识人的情感距离。比如井上哲次郎夸赞潘飞声“足称我亚洲筹海者轨范”[35](P.89);潘飞声与井上哲次郎道别时,赋诗曰:“竹君与我若兄弟,君迪交谊笃同洲。……濒行强慰以壮语,筹画兴亚思神州。” [27](《既送竹君君迪归舟别情未尽再赋长句分寄》,PP.150-151)
章太炎在戊戌前就对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有所了解。《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称:“昔兴亚之会,创自日本,此非虚言也”;在他看来,亚洲诸国中,中国和日本的合作最关利害,“以赤县之地,近在肘腋,可以相倚依者,阖亚洲维日本”。[10](PP.4-5)他政变后流亡台湾、旅迹日本,也和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相关。上海的日本人团体乙未会,是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会的基础组织。乙未会于1898年6月创办了《亚东时报》,由山根虎臣(1861-1911,号立庵)担任主编。章太炎正是在山根虎臣、安藤阳洲的帮助下得以赴台,在《台湾日日新报》任职。太炎停留日本期间,还在《亚东时报》上发表诗歌《赠袖海先生并简阳洲立庵二君》,将馆森鸿、山根虎臣、安藤阳洲视作“东国忧难之交”。[36](P.24)太炎描述此次日本之行的《游西京记》,后来也登载于《亚东时报》。[37](P.16)在兴亚的话题上,章太炎自然能与井上哲次郎产生共感。
第二,作为德国观念论哲学在日本的代言人,井上哲次郎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念兹在兹。章太炎关于“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意识萌生于此一时期。他和井上哲次郎也交流了“哲学”问题。
中国虽然早在明末就有对philosophy的介绍,如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 年)将之音译为“斐禄所费亚”,意译为“理学”。清末亦有“智学”“格致学”等不同译名;[38]但在整个汉字圈中,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是由西周(Nishi Amane,1829-1897)在1870年代提出,1881年井上哲次郎与人合著、于1884年又推出的增补版《哲学字汇》,吸纳了西周所译众多哲学名词。(22)《哲学字汇》将philosophy对应为哲学,参阅井上哲次郎、和田垣谦三等编《哲学字汇》附《清国音符》,东京大学三学部印行,1881年,第66页;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增补《哲学字汇》,东京:东洋馆,1884年,第91页。“哲学”遂逐渐被普遍采用,取代了此前较常用的“理学”。虽然从名词上,井上哲次郎继承了西周“哲学”的说法,但在内涵上,以井上哲次郎及东京大学为代表的“学院哲学”,主要取径德国唯心论,主张“纯正哲学”之形而上学。他们恰恰是要克服留学荷兰的西周及津田真道(Tsuda Mamichi,1829-1903)所代表的“启蒙哲学”,尤其是其侧重穆勒、孔德实证主义的内容。(23)近代日本学院哲学的兴起,参阅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马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6-165页。中国近代对日本“哲学”语汇的输入,较早见于黄遵宪《日本国志》(1895年)介绍东京大学哲学科。[39](P.1412)1898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在“理学门”之下列入22种哲学书,其中就包括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等《(改订增补)哲学字汇》,以及井上圆了《哲学要领》《哲学一夕话》《妖怪玄谈》,“心理学”部分则列入井上哲次郎所译的《心理新说》。(24)见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1、293页。据张晓编著《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8、391页),1899年时,还有两种与井上哲次郎相关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一是罗布存德著、井上哲次郎增订《英华字典》,东京:藤本书店,1899年;一是井上哲次郎著、毕祖成译述《东乡平八郎评传》,上海:昌明公司,1899年。关于日本的“哲学”的用语和观念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参阅景海峰《“哲学”东来与“中国哲学”建构》,《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桑兵《近代“中国哲学”发源》,《学术研究》,2010年第11期。这些作品都没有讨论1899年章太炎对日本“哲学”用语和观念的接受。
戊戌政变后旅迹台湾,章太炎的文献中已经集中出现了“哲学”一词。如评价送他东渡的殷守黑“参贯天人,于哲学、经世学,皆能道其究意”[40]。他在与梁启超信中说:“鄙意哲学家言,高语进步退化之义者,虽清妙阔疏,如谈坚白,然能使圆颅方趾,知吾身之所以贵,盖亦未始不急也。”[41]他评价,“穷万物之性质,辨人天之境界,与哲学相出入者,盖莫尚于佛经”[42]。这意味着,太炎其实早于1903年撰《哲学辨惑》的王国维,早于1905年感慨“举世人人谈哲学,愧我迂疏未研榷;谁知我即哲学家,东人有言我始觉”的俞樾[43](P.80),已经对日本“哲学”有所了解和评述。
太炎劝诫馆森鸿道:
学问一事,必认定一路,乃可收效。如西学,兄虽涉猎及之,然观兄所好,终在彼不在此。近闻德人讲哲学者,颇寻求《周易》,则旧学之在他日,安知不更为新学乎。[31]
章太炎尝在井上哲次郎处见到根本通明的《读易私记》,并发表评论称,“根本《读易私记》,大破革命之说,于共和民主无论矣。此公盖经之夷、齐也”[21]。而他此行和馆森鸿拜会的日本学者,多是汉学家。在这些汉学家中,能跟他随口谈及德国人如何讲述哲学的,无疑是井上哲次郎。“近闻德人讲哲学者”这段对话,乃是由他和井上哲次郎讨论《易经》生发而来。章太炎还阅读了东京专门学校有关哲学的书籍。他和馆森鸿讨论经学,论及公羊学时,就借点名批评康有为,谈到了他所理解的“哲学”:
康以惠、戴诸公专讲考订为大诟。其说流传于贵国。前在专门学校见一册书,专论哲学,并列东西诸人皆言经学无用,诚然,然今新学岂必皆有用。如哲学即最无用者,天文动植诸学虽有小用,深求之亦无用也。而西人孜孜于此,彼亦岂人人求有用乎?大抵世治则才智之士得有余闻,必将冥心孤索于此,今贵国亦略近升平矣,治(经)何不可。弟则处于乱国,不能不旁求新学耳……(25)袖海生《似而非笔》(十二),《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第1版,1899年10月14日。因原报纸文字溃漫,括号内的字为笔者的猜测;实在看不清的文字,用省略号替代。
章太炎彼时理解的“哲学”是“最无用者”,换言之,它并非指向日本启蒙哲学所强调的实证主义,而是学院哲学如井上哲次郎倡导的纯正哲学之形而上学。虽还不清楚章太炎具体说的是哪一本书,但彼时东京市面颇多类似作品,比如井上圆了在哲学馆所讲的《纯正哲学讲义》(1894年)、《纯正哲学总论》(1899年),松本文三郎的《哲学概论》(1899年)等。这段谈话表明,如哲学这样“无用”的新学,在太炎看来,并非处于乱国的中国学人所急需。他最青睐的,还是斯宾塞一系、有用的社会学。此时太炎虽然已经了解到哲学,但他真正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实现如井上哲次郎1880年代似的转向,要等到1903年后在上海的囚禁时期。这个时间差,并非单纯表明两人获取知识的早晚有别,而是暗示着,在对社会学和哲学的相关事实认知逐渐趋同的情况下,章太炎和井上哲次郎存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取向上的殊别。
四、得鱼忘筌
章太炎1899年夏在东京初识井上哲次郎,多次交谈之后,惊叹井上氏学问之广博,感慨未来著述要传世,“则非如井上哲次郎之学不可也”。他也对井上哲次郎所推介的德国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井上哲次郎周边东京哲学圈的人事有所了解。比如,一个名叫久保的学者,谈及西历五百年一商人来华,带走了蚕种回到罗马,基督教早进入中国。“枚叔曰:此真妖僧矣,非井上圆了之比也。”[22]这说明,太炎已经知道了井上圆了的名著《妖怪学讲义》;并且,此书非如书名所示的那般通俗猎奇,而是严肃的哲学著述。所以他才说井上圆了非“真妖僧”。这就为他1903年参与翻译该作埋下了伏笔。
然而,太炎并未立即对“哲学”投入太多心力,他感兴趣的,依旧是社会学。馆森鸿较详细记录了太炎和汉学家冈鹿门(Oka Rokumon,名千仞,1833-1914)26岁儿子冈百世的谈话。听说冈百世在大学专修哲学,并且也讲究社会学,“枚叔大悦,为种种问难”。章太炎脱口而出的“社会之理”,是斯宾塞、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在黄白种争中的效应:“须边撒、达尔文辈以生存竞争之学提倡全欧,闻欧(室)欲淘汰黄种以至于尽。今东亚之人,实二公笔墨所杀也。”[44]章太炎体认到,生物进化学说将人纳入自然秩序。人并非凌驾于万物之上,而同样是处于进化环节中的一个物类。人这一物类中,不同的种群又通过生存竞争分出强弱,优存劣亡。1898年,和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尔文集》时,章太炎就将斯宾塞原文中讲述动物因环境需要而改变习性的段落,扭曲为丛林之中弱肉强食的叙述,凸显了“相逼相变”中,处于“食物链下方”的民族之焦虑感。(26)斯宾塞原文参阅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1868, p.48。译文参阅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4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2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204-205页。冈百世问太炎,东亚人是否属于劣种。太炎举印度的例子,十分忧虑地指出,人种的优劣是可以变化的。古代的印度有许多博学之士,“不可谓非最优之种也”;但由于白人的殖民统治,“势力屈尔,一屈之后,白人以愚黔首之法愚印度,则自是为劣种矣”。[44]
担心民族会退化为劣种,甚至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或沦为低等物种,是进化学说带给章太炎的主要精神困扰。他此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说,“使支那之氏,一旦替为台隶,浸寻被逼,遁逃入山,食异而血气改,衣异而形仪殊,文字不行,闻见无征,未有不化为生蕃者”,甚至“后世将返为蛮獠猩狒”。其理据就在于,人作为万物中的一个物类,同样遵循自然进化的规律,“异物化人,未有底止,人之转化,亦无既极”。[41]他也将类似的意思告诉冈百世,“夫自脊骨之鱼以至于人,其相化相搏相噬不知其更几何世矣;岂化至于人,遂截然止乎?他日人又必化一高等之物,而此圆顶方趾者,又将为其牺牲”[44]。
进化学说,将人类整体抛入了一个不由自己掌控命运的自然秩序之中。由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同文明的思想家,需要面对的问题。虽然说,章太炎一面继承了儒家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一面又通过斯宾塞接受了宣扬“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始终相信人面对自然进化,是有所作为的。如谓,“空理征之于天,实事为之在人,故必排上帝而后可办事。庄周有言,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小人。盖今日则宁为天之小人,必不(愿)天之君子也”[44]。然而,斯宾塞坚持“前达尔文的宇宙观”[45](P.150),相信宇宙自然本身是在向善演化。与斯宾塞不同,章太炎的观点更接近达尔文、赫胥黎,宇宙本性是“自行其是”(self-assertion)(27)参阅Thomas. H. Huxley: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p.ix。的,无所谓善和恶。如果一定要用人间善恶的标准来判断,那就是既可善亦可恶。用《俱分进化论》的话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14](P.2)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相遇时,乃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与进化论所带来的全新宇宙观挣扎共处。并且,基于民族、人类命运之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惴惴不安,他艰难地重新思考人的本性及伦理。他找寻的资源,很长时间内也都是社会学。(28)据馆森鸿《似而非笔》的记载,1899年太炎在日本期间,馆森购买了诸如有贺长雄《社会进化论》《族制进化论》等著(《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第1版,1899年11月8日)。太炎的《訄书》初刻本《榦蛊》篇就引用了有贺长雄的《宗教进化论》。1902年旅日期间,太炎更是翻译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章太炎与社会学的相关问题,笔者另有论文讨论,此不赘述。在他看来,“如德国哲学,已多凭理想,而少实验矣,恐穷极必归于佛耳,讲各种哲学而遗社会者,其国必弱”[44]。
井上哲次郎早在大学时代就化解了进化论的宇宙观所带来的危机。或许,他并没有真正在精神上经历这段危机,就迅速将人类在进化的自然秩序中命运的不确定性,当作名为物质主义、功利主义需要去克服和战胜的敌人。他的解决之道,观念汇总为包容主观与客观的“一如的实在”;所谓“一如的实在”,乃是“终局的实在,世界的本体,理想的极处”。[46](PP.201-202)在井上哲次郎看来,哲学的终局目的,就在“明晰此实在观念” [46](P.232)。从《伦理新说》开始,他就将古今东西哲人解释宇宙的关键概念,孔子之徒的太极、老聃的无名、庄周的无无、释迦的如来藏、康德的实体、斯宾诺莎的万有本体、斯宾塞的不可知等等[4](PP.40-41),都纳入他后来所采用的“实在”这一概念所指涉的范围中。有研究指出,“实在”概念极富“柔软性”。井上哲次郎思想的本质是“折衷主义”;这一体系,“在被称为‘实在’的暗闇里来溶解异质性而得以成立”。井上的“实在”,“并不是通过和新的思想接触来养育自己的有机的存在,乃是如同吞下对象的所有一切的万籁俱静的无底之沼”;而其精神的内奥,是作为“略微的怀旧”残留的东西,是隐秘存在的传统价值观。从他体认“实在”的方式,即“通过‘穷理’与‘居敬’两种方法来体得宇宙遍在之理”,能反映出他受到朱子学的影响。[6](PP.114-118)
事实上,为抵抗进化所带来的人类命运及伦理的不确定感,井上哲次郎嫁接综合了斯宾塞继承自18世纪自然神学的“前达尔文的宇宙观”与日本的神道教,在伦理观上打开了“实在”通向“皇道”的路径。
斯宾塞哲学的基础,是区分“可知”(the knowable)与“不可知”(the unknowable)。他认为,“人类理智的力量可以处理所有那些在经验范围内的事物;它无力来处理所有那些超越于经验的事物”。所谓“超越于经验”,超过认识范畴的事物,就是“不可知”。这也意味着,“绝对知识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事物之下存在着看不透的神秘”。[47](PP.59-60)在科学急速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斯宾塞试图用基于自然神学的“不可知”,来缓解人们所面临的信仰危机。井上哲次郎在《认识和实在的关系》中承认,斯宾塞辨明了“实在”的不可知,不将“实在”作为认识的对象,和自己的见解“可谓同出一辙”。[46](PP.157-158)尽管他批评进化论者的唯物主义,但他总是格外为斯宾塞辩白,指出因为斯宾塞主张“不可知”,所以不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5](P.73)在井上哲次郎的学生时代,斯宾塞曾经是影响他最大的思想家。欧洲求学期间,他于1888年的暑假还专程从德国去英国,并拜访了斯宾塞。他在英国的乡间寻访斯宾塞的部分,是整个《怀旧录》描写欧洲经历最生动的篇章。[28](PP.331-333)尽管他后来奚落斯宾塞驱驰哲学的本领不足,不能进入纯正哲学的深远境界,但是井上哲次郎的“实在”与斯宾塞的“不可知”有共同的自然神学的特征。用哲学史家大岛正德评价斯宾塞的话,即一个“明白的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者和绝对主义者” [48](PP.208-209)来评价井上哲次郎,也是适用的。
井上哲次郎认为,现象和实在的关系是“差别与平等的关系”,“由于世界之差别的方面称为现象,世界之平等的方面称为实在。所谓的差别即实在,即是现象即实在的思想”。(29)原文:“處が現象と實在との關係は云ひ換へれば、差別と平等との關係である。世界の差別的方面を現象と稱し、世界の平等的方面を實在と稱するので、差別即實在といふのがこの現象即實在の考へである。”见井上哲次郎《結論——自分の立場》,《明治哲學界の回顧》,第74页。解释世界的终局最大主义,“即是平等无差别的实在”。[46](P.167)他解说国体论,“皇道是宗教以上的宗教,从佛教、基督教开始,儒教也好,哲学也好,全是皇道的范围”;“皇道是道德以上的道德,使所有的人类获得满足的生活者,无论如何的宗教,皆在皇道的范围之内”。[20](P.41)如此包摄所有、溶解一切异质性的皇道,正是“平等无差别的实在”于伦理上的对应物。
章太炎1902年第二次东渡日本后修订《訄书》,援引姉崎正治著论,开始逐步接触井上哲次郎周边人物的书籍。井上哲次郎之于太炎,如同一个捕鱼的篾篓。通过井上,章太炎得以框定其周边的重要阅读对象,他们大都融汇了佛教与叔本华一脉的德国形而上学。章太炎从这些对象那里,采择支撑或组建自身思想的元素。但是,得鱼而忘筌,在“转俗成真”之后,太炎的认识论和伦理观,与井上哲次郎竟大相径庭。
太炎援引姉崎正治《宗教学概论》《上世印度宗教史》,参与翻译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借助这些著述,他除了运用西方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生物学的理性话语来重新解析传统中国相关学术概念外,更重要的是,还深化了对宗教与革命关系的理解。一方面,姉崎正治研讨宗教“齐物论而贵贱泯”[12](《原教》上,P.286),解释了宗教观念的豫言激发人热情憧憬的机制,增强了太炎对外抵制基督教宗教侵略、对内动员革命群众的理论信心。另一方面,井上圆了高度认同佛教能使人“转舍生死之迷而开现涅槃之悟”,达至“无限绝对之心体”,意即“真如”。[49](P.362)这给予了太炎“继起之宗教,必释教无疑” [50](P.26)以理论支持。1905年,太炎在狱中阅读井上哲次郎所编《哲学丛书》,内收有井上哲次郎《认识和实在的关系》《利己主义的道德之价值》、森内政昌《认识与实践、实在观念与理想观念》等多篇文章。《读佛典杂记》显示,森内政昌文章所介绍的叔本华哲学,解释欲望(意志)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太炎最为动容。虽然说,章太炎欣赏井上哲次郎、森内政昌所介绍的德国直觉派的观点,即以“情力的活动”作为人行动的目的。(30)井上哲次郎《认识和实在的关系》论证主观的实在性时就说:世界万物共通之处,都是指向“活动”;“活动”虽然不能说是世界的实在,但是最接近世界的实在,即是从现象渡入到实在者。物质不灭,比如原子;精神也不灭,因为虽然作为个体的状态会变异,但活动的状态是永远存续的(《巽轩论文二集》,第190-199页)。森内政昌《认识与实践、实在观念与理想观念》继承了这一观点,而通过森内,章太炎也表现出对该观点的接受。详细的论证,参阅彭春凌《章炳麟〈読仏典雑記〉と井上哲次郎編〈哲学叢書〉》,神户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第93号。但是,在伦理观上,太炎和井上哲次郎、森内政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认同叔本华将“活动的抑压(Verneinung des Willens)”[51](P.830),或曰“意志的灭却”,作为人生的解脱之道。
井上哲次郎、森内政昌师生都难以认同叔本华将厌世、意志的灭却,作为涅槃的取径。井上哲次郎指出,叔本华的涅槃论,乃是“小乘灰身灭智的寂静之道”,而不是“常乐我净的积极的涅槃”。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1842-1906)的《无意识的哲学》,虽然比叔本华对佛教的理解更进一层,但仍未达到大乘佛教的境界。[20](P.43)自然法(Naturgesetz)和伦理法(Sittengesetz)有差别,“利己”即便是事实,也并不构成道德。人类需要构造利他的道德理想。因此“己”的观念不应该指向一己之身,而是“连结祖先和子孙无限的连锁的一部分”,是社会有机体这个“大我”的一部分。[52](PP.1073-1096)森内政昌同样主张调和一切活动,以达于利他、理想的至善观念。[51](PP.840-853)《读佛典杂记》针对井上哲次郎的观点,指出“自利性与社会性,形式则殊,究极则一”[53](第4册,P.1339)。太炎根本不能认同有高于自利性的社会性存在。《四惑论》主张,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15](P.2)。思想“转俗成真”之后,太炎的“已”就是指向一己之身的个体本位,可以脱离出五伦的社会性关系。他的伦理观越来越贴近叔本华,所谓“厌世观始起,而稍稍得望涅槃之门矣”[14](P.1),诸般种种,皆与井上哲次郎相悖。
事实上,在“决然引去”之外,太炎更欣赏的厌世观是“以世界为沈浊……不惮以身入此世界,以为接引众生之用,此其志在厌世,而其作用则不必纯为厌世”。[14](P.12)这里就涉及了章太炎与哈特曼之间的思想关联。井上哲次郎推崇哈特曼,在德国期间还多次拜访、交谈。后来,哈特曼推荐了科培尔(Raphael von Koeber,1848-1923)来东大担任哲学教授,科培尔遂成为叔本华-哈特曼一系哲学传入东亚的重要桥梁。
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提到哈特曼的《宗教哲学》,其文曰:“吾尝读赫尔图门之《宗教哲学》矣,其说曰:‘有恶根在,必有善根,若恬憺无为者,其善根亦必断绝。’此谓恶尚可为,而厌世观念,则必不可生也,不悟厌世观念,亦有二派。”[14](P.12)太炎所引语句,乃是对姉崎正治所译《宗教哲学》相关文段的缩写。(31)原文为:“惡衝動、根本惡の我意も始には潜勢力たると同じく、道德的意志も亦惡の顯動する迄は潜伏せるなり。惡の顯動前には、一個人にも人類にも善惡の芽のみにて未だ之を開發せざる未發の恬澹狀態あり。人は顯動の惡なきの故を以て、此狀態を無罪過と稱するなり、然れども無罪過の狀態にては顯動の惡なきと共に善も顯動せざるなり、人が無罪過にして道德的意識を開發せざる間は、道德的意志亦開發せず、其道德的世界秩序に適合するは偶合のみ。”(参考译文:恶冲动、根本恶的我意开始也同样是潜势力,道德的意志也即恶的显动那时之前还依然处于潜伏状态。恶显动之前,一个人也好,人类也好,都仅有善恶之芽。这样的人处于其善恶之芽还未得到开发的恬澹状态。人们往往以无显动的恶之故,称此状态为无罪过。然而,无罪过状态在无显动的恶的同时,也无善的显动。人无罪过即是未开发道德意识的状态,道德的意志亦未开发,其适合于道德的世界秩序仅仅是偶合。)见 ハルトマン著、姉崎正治译《宗教哲学》,东京:博文馆,1898年,第221页。太炎批评哈特曼对厌世观念理解不确。但事实上,据姉崎正治的概括,哈特曼不满基督教依靠他人,将基督作为神和人之间的媒介;他提倡的是依靠自力的“具存一体教”,又叫精神教。精神教以宇宙的大悲壮为目的,即充分知觉精神自身犯罪,又以自身偿罪。空无现象界的差别,皈依于本体界,全然生成渐次进化的大宇宙的解脱。甘于悲壮,在此世界中觉悟自己成为其他的牺牲,以慈悲和献身作为道德的基础。[54](P.26)太炎所选择的“不惮以身入此世界,以为接引众生之用”的厌世立场,其实和哈特曼的精神教是非常近似的。哈特曼仍旧是井上哲次郎思想圈辐射到的人物。井上哲次郎却并不认同哈特曼的伦理立场。章太炎通过阅读井上一系所译的哈特曼著作,获得了思想的养料。这同样属于得鱼忘筌。
五、结语
关于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关联,细如关键哲学术语“终局目的”的挪用,阔如两人儒教、佛教认知的差别以及相对于各自传统的变异,还有不少问题值得继续研讨。本文论述的重心,乃是通过确证1899年章太炎在东京与井上哲次郎交往的事实,发掘章太炎与明治思想界、乃至与19世纪末欧亚思想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从受到英语世界传入的生物和社会进化学说影响,到融合佛教和德国哲学来解决深层次的形而上学问题,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思想轨迹高度相似,转折的发生却存在有意味的时间差。章太炎几乎和井上哲次郎辐射出的人际和思想圈重要人物都有某种点对点的关系。通过馆森鸿《似而非笔》透露的关键事实和蛛丝马迹,结合潘飞声记载的旅德经历,以及吴汝纶东游的笔谈,基本可以框定章太炎和井上哲次郎多次交谈的大致范围,包括东西洋思想的融通、亚洲的连带以及德国哲学。章太炎此后围绕井上哲次郎周边人物姉崎正治、井上圆了,以及《哲学丛书》等著作进行阅读,并非偶然遇合,而属于某种有意识的寻访。
海轮、铁道辅翼了跨国人际交往,如井上哲次郎之拜会斯宾塞、哈特曼,章太炎之结识井上哲次郎;大学、印刷媒体在东亚的推广,造就出获取成体系的近代知识之途径;这些都是从人物关系出发观察近代思想地图,可以看到的“显像”。在“显像”的背后,其实还有近代思想地图的“实像”。进化学说将人类卷入不由自身掌握命运的巨大不确定性之中。井上哲次郎“没有深深用心捕捉”[6](P.119)近代认识论所造成的主客观的分裂。他迅速整合各种前达尔文的宇宙观,不论是斯宾塞继承自18世纪自然神论的“不可知”,还是儒教的“天理”,形成融合主观客观的“一如的实在”,溶解了各种异质和分裂。在伦理观上,他也打开了“实在”通向“皇道”的路径,实现了对忠孝一体的拟血缘制国家的国民道德论述。进化论的不确定所带来的危机感则几乎重塑了太炎的经验世界,他沉浸于悲观之深渊。思想“转俗成真”,以森罗万象的世界都是心中幻象,“宇宙本非实有”[50](P.16),虽然让他拥有一定的安稳感;但是,幻象中的宇宙,善恶、苦乐永远共存,仍使他将叔本华“意志的灭却”作为根本的解脱之道。加上对个体本位的确认,伦理上他再难返归以礼仪法度化性起伪的荀子,“回真向俗”之后,遂逐渐走上“以庄证孔”[7](P.61)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