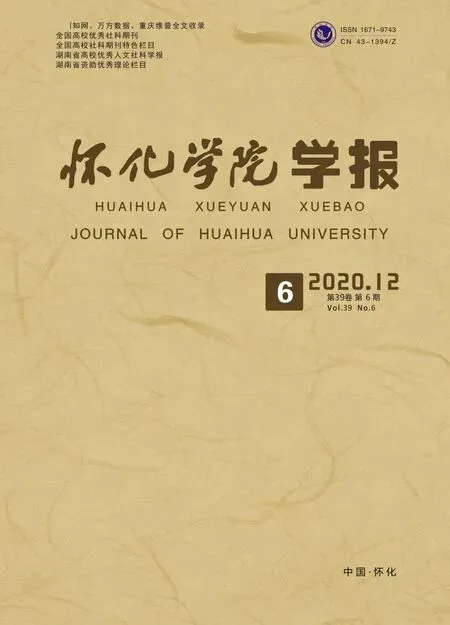刘天华的 “ 国乐改进 ” 观及其历史意义
2020-01-19陈劲峰
陈劲峰
(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湖南岳阳414006)
刘天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其一生致力于国乐改进。而其 “ 国乐改进 ” 的思想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三大社会思潮特别是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提出来的。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爆发于20 世纪初,被视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分水岭。这次新文化运动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剧烈冲击和深远影响,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与转型的步伐。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与学术环境所具有的极高自由度与极强包容性,使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发展状态,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十余年时间,形成了 “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思潮交错共在、话语权争夺激烈的一个时期 ”[1]。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器乐开始了现代化的变革进程。 “ 新文化运动时期,民族器乐的‘现代性’主要受到源于西方认识论背景的科学主义思潮、文化融合意义下的中体西用思潮和旨在改善人类生存状态的平民主义思潮等的综合影响 ”[2]。具体而言,民族器乐的现代转型源于科学主义思潮,中体西用思潮为转型提供方法与手段,平民主义思潮则是民族器乐现代性转型的目标与归宿。而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器乐的奠基人,刘天华的艺术观念和音乐创作等民族器乐现代化变革实践活动都受到上述三大社会思潮特别是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他提出的影响深远 “ 改进国乐 ” 主张,从理论到实践都特别注重与民众审美的对接,注重切实反映民众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研究刘天华 “ 改进国乐 ” 的思想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刘天华的平民音乐观及其形成
作为近代民族器乐艺术改革与发展的奠基人,刘天华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国乐改进方面,如记谱法、乐器改革、国乐新作品的创作等等。刘天华的理论著述较少,也难以形成系统,其作品主要发表于其创办的《新乐潮》 《音乐杂志》 等音乐理论刊物,代表性的有《梅兰芳歌曲谱·编者序》 《〈除夜小唱〉、(月夜) 说明》 《国乐改进社缘起》 《国乐改进社成立刊·发刊词》 《我对于本社的计划》 《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 等。刘天华音乐观最为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其平民性。而这一平民性特征的形成是与当时所盛行的平民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的。
平民主义是随着西方近代民主观念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萌芽的,它倡导争取个体自由与解放、追求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创作美好生活的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不仅文学界出现了 “ 平民文学 ” 的潮流,而且教育界也倡导发展 “ 平民教育 ” ,政治领域也提出了实行 “ 平民政治 ” 的主张。而刘天华的兄长刘半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不仅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及语言学家,而且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 “ 平民文学 ” 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首先提倡收集与研究民间歌谣,为民间文学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并获得相应地学术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平民主义思潮特别是刘半农平民创作观的直接影响下,刘天华也着眼于从平民的视角来思考中国音乐的创作与教育问题,并形成了其平民音乐观。
刘天华反对将音乐仅仅作为权贵阶层的专享,明确提出音乐要服务于平民大众。他在《〈除夜小唱〉、(月夜) 说明》中指出: “ 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 ”[3]在他看来,在当时社会局势动荡、传统国乐发展落后的不利情况下,无论何种音乐形式与表现手段,只要能给广大民众带来精神及心理层面的抚慰,能表现当时民众的生活状态与观念见解,就已非常难得。他强调音乐要给普通民众带来精神层面上的抚慰。事实上,刘天华音乐创作成就中最具代表性的十首二胡名曲,均体现出 “ ‘以民众嗜好’为宗旨 ” “ 面向平民、面向生活,反映广大民众的思想感情 ”[2]的平民性特征。
二、刘天华的国乐改进实践
20 世纪初期西乐东渐后,为了便于区分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便将中国传统音乐称谓 “ 国乐 ” 。对于 “ 国乐 ” 的内涵,我们可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视角去理解。从狭义的视角看,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音乐学家王光祈为代表,认为 “ 国乐 ” 仅指中国古代的音乐,尤其是指代表儒家提倡的礼乐精神的中国古代音乐。在王光祈看来,新时期国乐的构成须具备 “ 代表民族性 ” “ 发挥民族美德 ” “ 畅舒民族感情 ” 三个条件[4]。二是以叶伯和等为代表,认为 “ 国乐 ” 即代表或象征国家政权的仪式性音乐。叶伯和在其《中国音乐史》中指出: “ 古来一朝一代,都要制一个曲子,拿来纪念,并且一切仪式都要用它,恰像现在的国乐。 ”[5]此处所谓 “ 国乐 ” ,即指近代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代表国家政权用于官方仪式等政治活动的音乐类型。从广义的视角看, “ 国乐 ” 涵括中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刘天华所持的是广义国乐观。他将国乐比喻为 “ 大花园 ” ,认为其中 “ 既有名花亦有野草,既有震人耳鼓的锣鼓也有音韵幽静的古琴 ”[3]。
(一) 刘天华 “ 国乐改进 ” 的主要动因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国内对西方音乐的学习与传播也迅速发展,相比之下国乐的发展则相形见绌。这种一边倒的落后局面,引起了一些有志投身国乐的人士的极大担忧。仲子通曾在《我们音乐界应该怎样来努力》一文中说道: “ 吾国乐,垂沿至今,很有几千年,但是乐界方面,到底没有什么进步。……倘吾国乐,长此以往,不为设法改革,总难占艺术界中的一席地位。 ” 这就是说,与西方音乐的快速发展相比,国乐几乎没有进步,甚至是日渐萧条。王光祈则认为,从音乐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已不存在 “ 国乐 ” 。在中国最为常见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中,使用最普遍的胡琴和琵琶等乐器就不是本土固有之乐器。在音乐活动中,西方音乐才是主流的风向标, “ 学校之中则改用西洋风琴,军队之中亦使用外国军乐,甚至民间婚丧大礼亦以一用外国军乐为快 ” 。至于 “ 昔日之笙箫七弦,喇叭大锣……盖早已成为《广陵》绝调,不复再闻矣……故今日之中国,可谓无乐有之,亦非国乐 ”[4]。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以后,无论是萧友梅、王光祈这样赴欧美留学深造、受到西方音乐学院派训练的新一代音乐家,还是长期在国乐领域深耕并取得过突出成就的本土国乐家,均认为国乐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作为后一类本土音乐家的代表,刘天华对当时国乐的发展状况甚为担忧,他指出 “ 我们的国乐的花园里久已没有园丁了。野草与名花也都是自由生长。自震人耳鼓的锣鼓以至音韵幽静的古琴,这中间有的是野草,有的是名花…… ”[3]换言之,国乐艺术作为汇聚与浓缩了民族情感的 “ 百花园 ” 已经变得萧条不堪,无论 “ 名花 ” 还是 “ 野草 ” 都处于自生自灭的野蛮生长中,因为保证他们健康发展的关键 “ 园丁 ” (国乐音乐家)已后继无人。正是出于对国乐发展落后状况的担忧,才让身为专业音乐家、在北京艺专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担任教职,并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等担任国乐导师的刘天华,下决心改进国乐。
国乐发展落后,在当时的国乐家及其他音乐界人士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记谱方式的落后;二是作曲技法落后。就前者来说,当时的进步音乐家普遍认识到,作为中国传统记谱方法的工尺谱等,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五线谱。即便是通晓工尺谱的刘天华也认为记谱法落后是造成国乐发展落后的首要缺陷。他指出,正因为 “ 记谱之法不完备 ” ,才导致中国自古至今的国乐作品大多无法查证;即使是有乐谱留存的音乐作品,其中的记谱也有很多不完善、不准确之处,从早期的作品 “ 如唐之卷子本《幽兰》谱,朱子仪礼经传之十二诗谱,姜白石之词谱者等,或仅备律吕,或只载简字,谱不足以赅乐,徒费考古家之周章,于事实无补 ”[3]。近代流传出现的古琴作品、昆曲唱段的乐谱等,其记载的完整性已有显著进步,但对音乐的音高、力度、速度、表情等的记载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刘天华认为 “ 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徐疾之分,必其谱能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 ”[3]。刘天华认为,学习音乐主要通过听觉、语言和视觉三种感官,听觉容易遗忘,语言容易不准确,惟有视觉最真切。在他看来,西方的记谱法无疑是西方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要改变我国记谱法的落后状况,就应该学习、借鉴与应用西方音乐的记谱法。由此,刘天华便开始了他的国乐改进之旅。刘天华的国乐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传统乐器的改进或改造;二是对固有国乐作品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三是国乐的新创作品与新的音乐创作理念与主张。
(二) 刘天华 “ 国乐改进 ” 计划
国乐改进,必须建立在对旧有国乐进行整理、研究与保护的基础上,这是国乐改进的基本前提。为此,刘天华和他所领导的国乐改进社为国乐的改进与复兴拟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几乎囊括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关于保存传统音乐所要做的一切工作,如古代音乐文献的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生活中 “ 活 ” 的遗存的收集、记录,国乐教育与研究的推动以及对现有国乐作品不足的改进与完善,等等。刘天华甚至还提出了建立专业音乐图书馆与音乐博物馆的构想。不过,遗憾的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刘天华这些构想大都无法实现,其主要的实践除了创办了近代音乐史上极具影响力、仅仅出版过十期的《音乐杂志》外,便是在日常的音乐教学活动中从事国乐的教学传承,并在业余时间亲自收集、整理民间音乐。
(三) 刘天华 “ 国乐改进 ” 实践
具体而言,刘天华改进国乐的实践主要包括对记谱法的改造、对二胡和琵琶乐器两种乐器的改造、对国乐新作品的创作探索等。第一,对记谱法的改造。他不但使用西方的五线谱来记写他收集的传统音乐和自己的新作品,同时还借鉴简谱对传统工尺谱进行改进,使其更易于理解。比如在字谱的左方加上直线,用以表示时间长短;谱面由直排改为横排;等等。第二,对传统乐器的改进。乐器改进方面,刘天华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对二胡和琵琶的改进。他指出: “ 胡琴当然不能算做一件最完美的乐器,但也不如一般鄙视它的人想像之甚。 ”[3]身为二胡演奏家的刘天华,本着对二胡音乐表现力的不断拓展与完善,对二胡进行了系列改进。经过他的努力,原来 “ 仅限于使音区翻高一均或两均的简单三把演奏法,发展到七把,与小提琴相比,达到了小提琴把位的极限 ”[3]。此外,他还借鉴了西洋小提琴的固定音高定弦法、弓法等演奏技巧,使改良后的二胡在音域、音质、音色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刘天华在二胡改进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使得二胡这种在改进前地位低微、常常被忽视的普通民族乐器,转而成为现代民族器乐艺术上不可或缺的代表性乐器。琵琶改进方面,在刘半农先生的帮助下,刘天华成功地实现了十二平均律在琵琶上的应用[3]。第三,新国乐作品的创作。在国乐作品的创作上,刘天华做出了杰出贡献,不仅创作了《光明行》《良宵》 《空山鸟语》 等十首二胡曲以及《虚籁》《歌舞引》 《改进操》等三首琵琶曲,还改编了国乐合奏曲《变体新水令》,创作了47 首二胡练习曲和15 首琵琶练习曲。刘天华所创作的二胡曲和琵琶曲至今仍是中国民族音乐中的经典,成为国乐在20 世纪上半叶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与里程碑。刘天华的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其主张中西融合的创作思想,也反映了一名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的真实情感,是 “ 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 ” 的创作观的印证。从其创作的二胡音乐中,既可以领略到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时期的苦闷与彷徨,又能领略良宵佳境与空山鸟语的生动情趣,还能听到精神振奋、催人奋进的光明之歌。在这些新创作中,刘天华开始尝试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手法和音乐语汇,且运用恰当、巧妙,毫无生硬之感。如创作于20 年代初的二胡曲《光明行》,借鉴西方音乐中的进行曲风格,将作者对光明的向往与进取精神表现得特别生动,其宫调式的运用带有西方大调式明朗与坚定的色彩,其近关系转调以及 “ 和弦琶音 ” 的手法同样是对西方音乐的借鉴。除此之外,还有二胡曲《烛影摇红》中的复拍子、《苦闷之讴》中的变奏手法、《悲歌》中变化音与动机模进等,无不是刘天华在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三、刘天华国乐改进观的历史意义与现代启迪
由上可见,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平民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中西体用三大思潮的影响下,刘天华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国乐改进的思想,而且在致力于国乐改进的实践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刘天华不仅立足于中国的国乐传统,借鉴西方的音乐理论,提出了独到的国乐发展思想,创作了大量的独具一格的国乐作品,而且将国乐改进的思想拓展到音乐教学的改革实践中,在其所开设的新式二胡专业课程中,一改我国传统国乐教育中那种主要依靠师徒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方法,而引入欧洲先进的音乐教学方法和手段,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融贯中西而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音乐教学训练体系。刘天华的 “ 国乐改进 ” 实践不仅在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启迪。
(一) 刘天华 “ 国乐改进 ” 观的历史意义
可以说,一方面,刘天华等的国乐改进实践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民族器乐独奏曲创作中演奏家兼作曲家的模式,并确立了此类音乐家在民族器乐领域里创作兼表演的身份认同。此类音乐家不仅把对民间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和加工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且在音乐表述形态上保持了音乐作品的地域风格和乐器技艺特征,促进了近代时期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与转变。另一方面,自刘天华等的国乐新创作实践开始,中国民族器乐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独奏曲创作为主的创作风气,这为之后中国器乐独奏音乐体裁的广泛发展奠定了基础,伴随着从传统独奏乐器琵琶、二胡、古琴、古筝到新晋成为独奏乐器的笛、管子、唢呐、板胡等的发展与改良,逐渐形成了民族乐器独奏音乐作品风格的基本语汇和技法体系,从而显现出独奏音乐在不同时期音乐生活中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地位。
总而言之,刘天华等的国乐改进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器乐发展史上的重大建树,在国乐改进与发展方面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可以说,刘天华等的国乐改进实践,不仅将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民族器乐的现代化进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中国现代时期音乐创作民族风格的形成以及中国民族音乐的整体进步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刘天华等的国乐改进实践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 刘天华 “ 国乐改进 ” 观的现代启迪
在国乐改进的实践中,刘天华及其国乐改进社的成员如萧友梅、黄自等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和观点。一方面,他们站在创建中国国民乐派的高度来致力于国乐改进工作,主张新国乐的创作应建立在中心音乐交融的基础之上,在创作新国乐的过程中不仅不能站在保守的立场排斥和反对西方音乐,而且应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音乐,吸取西方音乐的创作方法。唯有如此,国乐的创作才能超越传统国乐的局限而获得突破性发展。另一方面,所创作的新国乐,就其内容来说,应当 “ 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 ” ,而不是局限于延续旧有国乐音乐及其情趣。如果仅是重演古代音乐,或是以旧有形式抒发前人感情,那将难以使国乐获得当下广大民众的认可。 “ 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 ” ,突显的是国乐创作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它不仅指明了新国乐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也强调了新的国乐创作必须在 “ 立 ” 和 “ 破 ” 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出一种有别于传统国乐的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的表现形式。刘天华等关于如何处理中西音乐关系的看法及关于如何创作新国乐的见解,不仅反映了当时音乐发展的趋势,有力地推进了当时的国乐改进实践和近代中国音乐的转型发展,而且为当今如何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推进中国特色音乐理论的发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诸多启迪。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有历史眼光。所谓历史眼光,也就是要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和创作方法。所谓中国特色,既指要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国情,也指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和创作方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批判和弘扬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和创作方法,并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学发展的趋势和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使中华音乐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也才能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食粮。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要具有世界眼光。音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世界各国都在其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音乐文化。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尽管都各有不同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特色,但也存在着诸多可以交流互鉴的因素。音乐文化的交流互鉴是推动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我们要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发展,除了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和创作方法外,还要注意借鉴和吸取西方的音乐理论和创作方法,尤其是要根据世界音乐的发展趋势,立足于世界音乐理论发展的前沿,用融通中外的方式创新音乐理论,提升中国在世界音乐领域的话语权,为世界音乐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