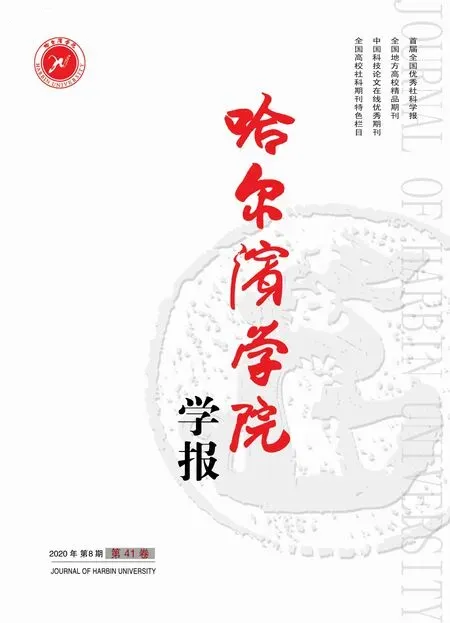安东尼·特罗洛普小说作品的叙事伦理
2020-01-19崔洁
崔 洁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一、特罗洛普小说与叙事伦理
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位卓越的社会问题小说家。但其作品直到20世纪才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外研究者对特罗洛普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其作品中的社会现实主义、人物、艺术特色、叙事风格等方面,国内研究者尤其对特罗洛普的政治观、欲望书写及其作品中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特罗洛普是一位道德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他秉承英国文学的道德传统,其伦理道德观自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评论家们开始关注特罗洛普的小说艺术与其伦理道德观之间的相互作用,杰弗里·哈维的专著《论特罗洛普的艺术》分析了特罗洛普艺术创造表达其伦理道德观的过程,在“成就”一章中,哈维介绍了詹姆士一世时的戏剧对特罗洛普小说创作的影响,并集中分析了小说《首相》中几处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关键性引用,不仅体现了特罗洛普关于“政治生活的戏剧性”的认识,同时指出在其主要作品中,特罗洛普精心设置的戏剧性场面在主题表现方面很好的契合了小说创作的需要,引用莎剧无疑对特罗洛普道德意图的表现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1](P53)另有国内学者分析了特罗洛普的小说叙事艺术与道德倾向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并分析了小说家独特的同情观。[2]综上所述,国内外特罗洛普的研究者们已在叙事研究与伦理道德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鉴于特罗洛普众多的小说作品,在形式批评与道德诗学相结合的视角方面,仍有很广阔的研究空间。
特罗洛普的小说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大小说系列:即反映19世纪英国教士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巴塞特小说”系列和以描写政界风云为特色的“议会小说”系列。在这两大小说系列共十二部作品中,特罗洛普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其中不乏怀揣远大抱负的年轻人物形象,如《阿灵顿的小屋》中的约翰·埃姆斯、《索恩医生》中的弗兰克·格雷莎姆、《你能原谅她吗》中的约翰·格雷、《菲尼斯归来》中的菲尼斯·菲恩、《首相》中的斐迪南·劳佩兹、《公爵的儿女》中的弗兰克·特莱格,等等。其中,菲尼斯·菲恩和斐迪南·劳佩兹是特罗洛普着力刻画的两个人物,他们均出身寒微,有着类似但又本质不同的奋斗历程,以及截然不同的结局。在呈现两个人物不同生命体验的叙事过程中,作家的伦理取向也被放大和凸显。本文拟以围绕这两个人物的叙事为例,从叙事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分析特罗洛普小说作品的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即作为“伦理的叙事”,纽顿在《叙事伦理》中将叙事伦理划分为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个层面。其中叙述伦理是纽顿重点讨论的,意为“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叙事中的互动关系”。[3]特罗洛普的小说作品在叙事话语呈现方面密切关注了莎剧作品,正是通过莎剧作品这一他者身份的映照,特罗洛普的伦理取向才以一种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方式展现出来,体现了作者的同情观。同时,特罗洛普以触动读者心弦的方式表现了伦理道德问题本身具有的真实性和多维性,也为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叙述者、莎剧背后的伦理话语体系、读者之间的伦理对话提供了可能。
二、特罗洛普的同情观与叙事话语的呈现
特罗洛普一生都“保持着稳定的伦理化诗学观:小说的道德化意图与引发读者同情的诗学效果”。[2]特罗洛普认为“小说,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就是要让读者对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同情。”[4](P141)特罗洛普如此重视“同情”这一关于道德的概念,除了宗教思想背景和社会文化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与作家自身的阅历和信念相关。特罗洛普深信“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都应把进入议会视为最远大的理想。”[4](P181)特罗洛普也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但并未达尝所愿,也许正因如此,特罗洛普在书中常常表达出对怀揣政治抱负的人物的同情。
特罗洛普表现“同情”这一伦理立场主要是通过在叙事话语层面进行伦理干预实现的。特罗洛普的小说在叙述中大量引用和关联了莎剧作品,超出了他引用其他作家作品的总和。首先,近四分之一的关联是小说人物将自己比作莎剧中的角色,并用对话方式呈现出来,具有戏剧化效果;其次,通过小说叙述者的议论将故事人物与莎剧人物相关联。通过以上两种叙事话语的呈现,作者的伦理立场便以一种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得以表达。
小说《首相》中的反面人物斐迪南·劳佩兹是特罗洛普笔下最为矛盾多面的人物之一,这一点可以从与他相联系的众多莎剧人物中得到佐证。劳佩兹向其岳父沃顿先生解释自己的生意时把自己比作是莎剧中的威尼斯商人,他深信自己的投机生意不应受到社会道德的规约。在生意合伙人塞克斯提面前,劳佩兹又把自己称为夏洛克,借以凸显他作为种族歧视受害者的境遇。反过来,沃顿先生出于无奈把钟情于劳佩兹的女儿艾米丽下嫁于他后,愤恨的把自己比作是一个被黑皮肤的摩尔人偷走了女儿的布拉班丘,诸如此类细节也同样表现了对劳佩兹种族背景的仇视。
从叙事话语层面来看,在劳佩兹这个人物的呈现过程中,特罗洛普重点关联了莎剧《哈姆雷特》中的经典独白——“生存还是毁灭”。劳佩兹投机生意破产后,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是否要割断自己的喉管,承认自己一生一事无成,因而痛痛快快的了此残生?他(劳佩兹)对自己说道,‘这毕竟是了结破产苦恼的最好办法。’”[5](P390)后来,劳佩兹想强行带着妻子艾米丽离开,但却不得不再一次向岳父沃顿先生索取钱财,以换取海外职务,沃顿先生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劳佩兹的要求,当劳佩兹的希望再次破灭时,特罗洛普又关照了“是生存还是毁灭”的片段:“若不能到危地马拉去,那他自己该怎么办?他该到何处去?就这样,他在房间里来回转了一个小时,一支手枪,一把刀片不就可以彻底解决他这些困难吗?”[5](P420)至此,走到穷途末路,一向鹰视狼步、利益熏心的劳佩兹终于想到了卧轨自杀。哈姆雷特关于生存与毁灭的独白恰到好处的渲染了劳佩兹走向毁灭的悲壮。特罗洛普继续写道:“假如劳佩兹继续活下去,继续忍受‘那欺人命运的剑伤枪挑’,没人敢说,这些话是过于严厉的。但一死百了,把许多过错都抹掉了,在许多人心目中,由懊悔而自杀会把一个黑不溜秋的人洗刷的几乎洁白如玉。”[5](P444)特罗洛普对于小说的“悲剧性”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恐怖事物的简单堆砌不会触动任何人,更不是悲剧,反而会渐渐失去其可怖的特质。”[4](P141)所以在处理劳佩兹这个人物的退场上,作家没有着意呈现血腥的画面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刺激,而是在叙述中成功地将一个投机商人在自杀与苟活之间选择的内心活动赋予了悲剧人物戏剧独白的恢弘场面。
特罗洛普将一个身负家仇国恨的王子和一个卑鄙小人并置的艺术安排,使得莎剧的历史言说与特罗洛普小说的当下言说之间产生了张力和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莎剧人物(哈姆雷特)对于特罗洛普小说来说是一种他者的身份,也正是通过这一他者身份的映照,特罗洛普小说及隐含作者的伦理取向以一种象征性、隐喻性的方式展现出来。所以,特罗洛普采用这样的艺术安排有着浓厚的叙事伦理意义,折射出特罗洛普的伦理倾向——对劳佩兹抱负的同情。
特罗洛普的同情立场在劳佩兹自杀前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作者不仅描写了劳佩兹在自杀前本性中善良的一面,更关键的是在于对人物的离场进行的悲剧性渲染。一个为抱负而奋斗的悲情人物,即使其奋斗的手段备受争议,当他悲壮的走向毁灭时,针对他的伦理判断也必定不是绝对的,小说叙述者无疑是想批判劳佩兹这个人物的,但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在潜意识中为这个人物所做的各种辩解。小说中独特的叙事话语呈现使得作者、读者、叙述者的伦理意识在交互中产生了碰撞与矛盾,原因在于特罗洛普笔下的劳佩兹是一个极具矛盾性的人物:一方面,他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利用身边所有的人,包括妻子艾米丽和生意伙伴塞克斯提,他也有足够的手段攀附上公爵夫人,意图在银桥选举中获取席位,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猎食者”。但是另一方面,他的犹太身份决定了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被主流社会倾力碾轧的外来者。叙述者借由公爵夫人的思绪说明了这一点:沃顿家族作为一个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对素不相识的人反感,抱偏见,提防他们,不让他们打进他们的圈圈,没有人比他们更费尽心机地要把女儿留在自己的圈子里……。然而这个一半异国血统,一半犹太血统的人,一个照现在看来不名一文的穷光蛋”,[5](P554-555)竟插足了艾米丽原本门当户对的姻缘。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只有同整个世界作斗争,才能爬得上去,因此在他的斗争中有一种勇敢、崇高、诗画般的近乎美妙的成分”。[5](P172)再者,由于劳佩兹饱受其作为葡萄牙裔的犹太投机商,一个外来者身份的困扰,他“将成功等同于社会认同和社会地位的提升”,[1](P156)他做投机生意是为了快速致富,娶艾米丽为妻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参加竞选是他向权力靠近的第一步。早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要成为被关心和赞同的对象,一个人就必须拥有财富和优越地位。我们对这种人(抱负)的满足有特殊的同情,……对因他们遭遇不幸引起的同情比因别人遭遇同样的不幸而带来的同情多得多,甚至这种同情代替了我们以前对他们的愤恨。”[6](P191)
很明显,驱使劳佩兹奋斗的动力反而成了阻碍他实现目标的障碍。劳佩兹竞选下议院席位能否成功无疑也牵涉着小说中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所以特罗洛普塑造劳佩兹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不仅反映出伦理判断的复杂性,而且通过该人物向读者们传达了“与以程序正义为特征的法律公正相比,更重要的是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应当具备一种公正的同情,或是公正的同感’”。[7]这也是伦理道德的情感之维,体现出作者对伦理道德问题本身具有的真实性和多维性的认识。
三、惩恶扬善的道德法则
劳佩兹自杀前,思考着“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菲尼斯·菲恩面对重要人生抉择时,犹疑着是奋起一搏,还是随遇而安,这对他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二人不约而同的想到用“一把尖刀”来了此一生,但二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一个从恶,一个从善。在表现对人物同情的同时,特罗洛普的善恶是非观展露无遗。在刻画劳佩兹和菲尼斯这两个人物时,特罗洛普采用了相似的叙事话语策略,但却取得了不同的叙事效果,体现出特罗洛普对善的肯定。
菲尼斯·菲恩是特罗洛普“议会小说”系列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在《菲尼斯归来》开篇,新婚妻子离世,菲尼斯再次离开爱尔兰来到伦敦,踟蹰着是否重新追寻自己的政治抱负。这里的心理描写除了引用哈姆雷特独白中的“一把尖刀”,似乎还遵循着“是生存,还是毁灭”片段的思路来展开的:妻子撒手而去,菲尼斯变得一无所有,这与哈姆雷特痛失父亲母亲改嫁叔父时被抛弃的悲痛绝望何等的相似。“这世上还有哪一个人比他更有把自己的前途赌上一把的权利?”[8](P9)这与“是生存,还是毁灭?”几乎是同一性质的问题,表达了说话者对目前状况的悲叹和对未来的彷徨;“如果舍弃现在的地位与钱财,又有什么可怪罪于他的呢?”[8](P9)哈姆雷特也有过这样的疑问“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9](P150)而菲尼斯马上有了答案,就算是为了国家、为了认识他的人考虑,没有地位和钱财的他,也不能到处混饭吃。菲尼斯想到孑然一身的他,没有牵挂,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不幸的是,他没有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资本,似乎又否定了拿前途、命运做赌注的念头。哈姆雷特也斟酌着进入死亡的睡眠固然可以免去忍受世上的痛苦,可是一想到会做些什么梦,不禁让人放弃死亡的想法,继续忍受折磨。菲尼斯想到逃脱困境的办法——“一把尖刀”。他又想到或者可以把自己的轻生设计成一场意外,但总有一些人生准则能够推翻一切逃避问题的做法,也总有些人没有胆量违背这样的人生准则而选择死亡。这便对应了哈姆雷特的顾虑,“谁也不甘心呻吟、流汗拖着这残生,可是对死后又感觉到恐惧,又从来没有任何人从死亡的国土里回来,因此动摇了,宁愿忍受着目前的苦难而不愿投奔向另一种苦难”。[9](P150)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现世的羁绊,使人们不得不放弃轻生的念头,这样的顾虑同样困扰着菲尼斯,但更让他纠结的是要赌上他现有的一切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还是安于现状,一生碌碌无为。
这一段心理描写表面上看表现了菲尼斯关于前途命运的内心冲突,由于导入哈姆雷特的独白,这段描写具有明显的双声对话性。菲尼斯与哈姆雷特在面对生死荣辱的人生转折时,历经的思想与心灵的矛盾与冲撞在彼此呼应与衬托下,呈现了明显的复调效果,突显了取与舍、对与错之间相对峙的伦理意识的交锋。
菲尼斯最后还是选择了放手一博,期间经历了种种考验,其中最为险象环生的是他被指控是谋杀其政敌邦丁的凶手。若不是沙凡布拉斯律师的机智辩护和一直对菲尼斯颇有好感的格斯勒夫人多方奔走查找真正的凶手,菲尼斯险些背负谋杀的罪名。该辩护过程是特罗洛普所有作品中最为精彩的庭审现场片段之一。沙凡布拉斯律师在证明谋杀邦丁先生不是罪犯一时冲动的想法,而是早有预谋的举动时,请菲尼斯的同僚(同时也是一个业余文学创作者)邦斯先生确认几起出自莎翁悲剧的谋杀案中的凶手无一例外都是提前策划了谋杀,而不是当场为之,这也足以推翻了菲尼斯因一时意起而谋杀了邦丁。这几起谋杀全部出自莎剧,即《哈姆雷特》《麦克白》《奥赛罗》。
之后,菲尼斯被无罪释放,他的政治理想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反而赢得了更广泛的,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同情;菲尼斯与富有的寡妇格斯勒夫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同于劳佩兹的命运,菲尼斯对财富、权力、优越地位的追求最终都有了丰厚的回报。值得注意的是,菲尼斯的爱尔兰背景也决定了他相对于英国政治体制的“他者”身份,这使他在追求政治抱负的征途上和劳佩兹几乎站在了同样的起跑线上。如果不去考虑种族和身份背景的因素,在劳佩兹与菲尼斯的对比与反衬中,特罗洛普想要向读者传递的讯息是:“一个实实在在、诚实勇敢的人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卑鄙的行事始终是丑恶和可憎的。”[4](P91)
所以,虽然特罗洛普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物充满了同情,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指向了善得善终、恶有恶报的道德法则。特罗洛普努力实现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最基本的道义责任,那就是惩恶扬善,这与莫里兹·石里克在《伦理学问题》中提出的观点“社会强化人的道德行为趋向的根本之法,是使德行真正导致行为者的幸福,亦即使德行本身具有快乐的价值”[6](P462)是一致的,所以特罗洛普的创作思想对于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启迪意义。
四、结语
在小说《巴彻斯特大教堂》的尾声部分,特罗洛普慨叹道:“我们男女主人公的伤心事,广大的读者啊!他们的伤心事,他们的罪恶,或是他们的愚蠢行为,这些才是你们的乐趣,而不是他们的德行、见识和随之而来的报酬。”[10](P636)这句话乍一听是揶揄的,而实际上表达了特罗洛普强烈的呼吁,他不希望主人公们的“德行”“见识”和“随之而来的报酬”成为“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特罗洛普的呼吁并没有声嘶力竭般的无力,而是通过特定的叙事安排,在潜移默化中展现了更宏大的叙事伦理修辞。
特罗洛普作品中不乏攸关生死荣辱的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和悬置性,以及在表现这些伦理问题时,作者对莎剧人物的密切关照,决定了其作品的伦理具有广阔的对话性和交流空间,具体来说是莎剧中所蕴含的道德伦理话语体系与小说文本自身所拥有的叙事声音产生的对话性。当人物经历着思想与心灵上的巨大矛盾与波澜时,在善与恶、取与舍、对与错相对峙的伦理意识的交锋中,这种对话性就变得尤为强烈。
特罗洛普像伟大的史诗诗人一样,通过巧妙的使用戏剧性话语,以隐喻的形式探讨伦理道德问题的多维性及复杂性,并展现其伦理价值取向。特罗洛普的叙事也充分展示出他本人对于身处漩涡、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物的同情,这极为符合叙事伦理研究的初衷,即“在叙事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以‘对生命的热爱与人格的尊重’为核心的人文关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