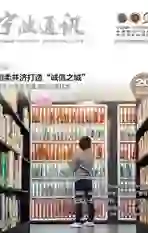“正向激励+信用修复”为诚信履行者派司法“红利”
2020-01-18胡珊
胡珊

今年9月中旬,在“移动微法院”上接到慈溪市法院法官发送过来的自动履行证明书,北京某信息技术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长吁一口气。
2个月前,这家公司因一起金额近190万元的合同纠纷,被宁波某视讯公司起诉,账户也被法院冻结。打官司倒在其次,让信息技术公司负责人感到焦虑的是,公司目前正在冲刺新三板精选层申报,涉诉可能给公司“小IPO”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得知宁波法院可以为自动履行当事人开具诚信证明,在法院立案后的第11天,信息技术公司就以最快的速度与宁波某视讯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并在当天把履行款项打入了视讯公司的账户。
“有了这张自动履行证明,公司涉诉处理情况一目了然,面对券商和银行的审查我们也比较从容了。”信息技术公司的负责人说道。
促使信息技术公司快速履行调解文书的,是宁波市镇海区法院在全国首创的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该机制与信用修复机制共同构成了宁波法院“自动履行为主、强制执行为辅”执行体系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逐渐成熟的奖惩并重、刚柔相济的宁波信用体系中的关键内容之一。
什么是“正向激励+信用修复”机制?
这个看起来有点拗口的概念,通过案例说明最为清楚明了。
在宁波有一家建筑集团公司,3年来,它在法院作为被告的案件共有8件,标的额达近9000万元,但案件均在进入执行程序前履行完毕。这家诚信履行的企业,根据镇海区法院给它开具的自动履行证明,从镇海农商银行获得了2000万元的“诚信履行贷”授信。
这就是被最高人民法院写入2020年法院工作报告的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具体而言,它指的是对于自动履行裁判义务的当事人,法院可给予降低诉讼成本、出具自动履行证明等“红利”。同时,在建立自动履行与提升信用评价挂钩机制的基础上,法院还会定期将诚信履行名单推送至市场管理、税务等部门和金融机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使自动履行法院生效裁判(调解书)的当事人获得相应的社会信用评价。
在宁波,还有一家置业公司,因拖欠施工方1000余万元工程款成为被执行人。公司虽然有强烈的履行意愿,但因被列入失信名单,无法融资复工。关键时刻,宁波市江北区法院将该公司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暂时屏蔽。公司顺利完成融资,恢复在建工程,并最终还清欠款。
这就是由江北区法院首创的信用修复机制。信用修复机制为失信被执行人提供了“造血再生”的机会。即将被纳入或已经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经当事人申请并由法院审查后,如果同时符合5个条件(经传唤于规定时间到达法院配合执行;严格遵守财产滚动申报规定;严格遵守限制消费令;配合人民法院处置现有财产;有部分履行行为及明确的履行计划,且不存在妨碍、抗拒执行,恶意规避执行等情形),法院即可暂停对其的信用惩戒。
两项机制运行得怎么样?
“正向激励+信用修复”机制诞生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遇到的现实困境。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法院诉讼案件量居高不下,其中,执行案件占近四成。如何从源头上减少执行案件,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源源不断的执行案件给法院造成了巨大压力,较低的执行到位率难以让胜诉当事人满意;另一方面,部分暂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主动申报财产,履行意愿强烈,却因社会评价降低,社会活动能力受限,致使其履行能力进一步被削弱,经营活动更加困难。在此类案件中,信用惩戒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而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让自动履行者享受“红利”,将问题解决在“执行前”;信用修复机制,为自愿履行者再“造血”,将问题化解在“执行中”。两者相辅相成,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共同构成了宁波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中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
正因为此,在经过成功试点后,2019年9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在全市法院推广这两项机制。同年底,宁波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将两项机制纳入市级重点改革项目。今年3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信用办共同建立两项机制联席会议制度。5月9日,全市自动履行正向激励及信用修复工作推进会召开,4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会。此次会议的召开,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度参与两项机制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月13日,宁波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在全市推广两项机制。市人大协同各部门深入开展调研,多方听取意见,力求在立法层面推动两项机制推广完善。
据介绍,这两项机制自实施以来,已经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今年1—7月,宁波市两级法院自动履行案件5967件,发放自动履行证明1649份,16家企业、47名个人从多家银行获得贷款授信1.1亿余元,完成信用修复666件,修复后履行标的额为2.98亿元。
会不会纵容失信者?
當然,每一次创新都可能带来不同的声音。在两大机制全面推进的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机制规范、顺畅运行,防止相关权利被当事人滥用?
对此,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两项机制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对失信者的纵容,更不代表着对强制执行措施的削弱。“假借信用修复之名转移财产、拖延执行等行为将被视为以其他方式抗拒执行,法院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行为人进行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司法机关将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该负责人说。
为此,全市法院也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对于正向激励机制,镇海区法院对已经纳入该院诚信履行名单的当事人实施动态监管。今年5月,一家企业因成为其他法院的被执行人,被镇海区法院移出诚信履行名单。北仑区法院则制定了负面清单,明确若存在四类情形,当事人即使自动履行也不能享受“红利”。今年以来,北仑区法院共有191名当事人当庭履行义务,该院甄别出不符合正向激励条件的当事人20名。
8月15日,围绕如何进一步推动完善这两项机制,宁波邀请来自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12名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业内人士就两项机制的完善路径、实施边界和提升推广等展开广泛交流。
关于两项机制下一步的发展规划,与会专家表示,两项机制需要进一步提升外部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并纳入信用体系建设和社会综合治理的大环境中,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深度参与。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通过探索和完善信用等级制度、从信用信息归集到信用修复的闭环链路建设机制等,达到精准惩戒、精准修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