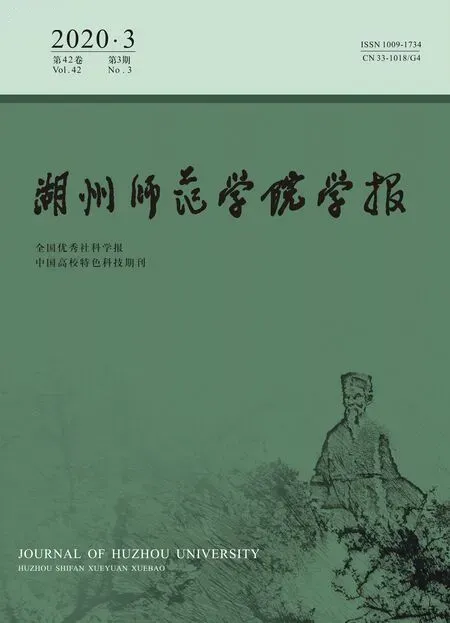周密笔记中的生命体验及其审美超越
2020-01-18刘师健
刘师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弁阳老人、四水潜夫,宋亡之后,隐而不仕,以整理和记载故国文献为己任,周密今存十三种著述,其中笔记九部,据夏承焘《草窗著述考》,笔记作品成书均在入元之后,作者以易代之际的独特视角抒写人情世故、世道兴衰,极具史料价值[1]337-341。以往学者或从年谱、传记、笺注入手对其人其作作基础考据的系统整理;或揭示其笔记在戏剧、园林、舞蹈、语言及宋史等方面的文献价值;或从“史”的角度对笔记文本的书写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至于笔记文本中呈现的作者对自我生存的关注、自我内心世界的剖析,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省思与置身离散中所体验到的属己的焦虑、忧伤与无告等刻骨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却多为学术界所轻忽与遮蔽。鉴此,笔者冀通过对周密笔记作品中关于时间书写、离散书写以及历史书写的探析,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与诠释文本中蕴含的个体在动荡时局中所承受的苦难与惶迫,感知他化遣内心忧愤、纾解文化冲突缠缚、反思人生意义的遗民生存范式,以此揭示一个更为真切的周密及其笔记文本世界。
一、时光省思
对时光的感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展现对生命意义探讨的突出表现。面对时间的无尽流逝,自古文人多是一面切己地体认生命的有限性,而不免生发惶惑与惆怅之感,与此同时,又总是锲而不舍地追寻精神上的超越,力求立言与传远。周密笔记中对时间的书写,亦诠释了对时间无尽流逝的叹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生有限性的认识,他由此在看似退让的归隐中,试图在岁月奄忽中营构内在的心理时间,竭力在“逝者如斯夫”的时间长流中,感慨人生世事,以个体话语参与存在的对话,拷问着生命的真谛。
(一)逝者已矣
周密笔记中的诸多书写,往往瞩目于静谧中归于虚无的意象,藉由寓意虚无的物象作为情感的“客观对应物”,以此刻画心中的茫然,表达对往昔的痛悼与追怀。一则以往日的地点“临安”为意象,书写昔日的繁华盛景。《武林旧事》中,作者饱含深情地记下南宋临安市民的礼乐文化、节日风俗、诸色杂艺、美食、酒楼酒名等。一则藉由岁月奄忽中已逝的故人,将心碾碎在无望的天涯:“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霞楼,调手制闲素琴,作新制琼林、玉树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笑语竞夕不休,犹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2]第七编第十册,309时光荏苒,只叫倾诉终难了,词语中传达着人天永隔、不胜今昔的伤感。“青灯永夜,时一展卷,恍然类昨日事,而一旦朋游沦落,如晨星霜叶,而余亦老矣。噫,盛衰无常,年运既往,后之览者,能不兴‘忾我寤叹’之悲乎!”[3]第八编第二册,5无限低徊与感叹之意,衰飒与惆怅之情,尽在其中,含蓄地呈现了抒情主体对时间的深刻体认。
死,是世间最难忍情的,可又总是在无法预料之时,仿若势不可挡般地攫走世人所珍视的一切,仅仅留下再也无力寻回的破碎世界。于是,作者在伤逝中,努力搜寻心灵的栖息之地,在属己的心灵家园中,追忆并再现从前的景况,惘然之中寻找安放心灵的归宿,期冀心灵与之重新交叠与会合,以此在死生流转中渡越时间的剥蚀与痛苦的渊潭。他由此追怀东坡的禅意之境:“东坡诗云:‘卧闻禅老入南山,净扫清风五百间。’其宏壮自昔已然,今益侈大矣。”[3]第八编第二册,64其间可见作者以佛家“空观”对执着的人生态度。《齐东野语》“形影身心诗”一则之中,我们还可见出佛家“中道”思想对周密的影响,他借此阐发陶渊明《形影神》诗中泰然委顺的思想,其坦然超脱的心迹可见一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事勿多虑。’此乃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乃得神之自然,释氏所谓断常见者也……盖言影因形而有无,是生灭相。故佛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正言其非实有也,何谓不灭?此则又堕虚无之论矣。”[2]第七编第十册,144-145在他迟暮的哀愁里,我们可以体认到其深受佛家思想的浸染,只是,禅的至境是无悲无喜、无生无灭的寂灭之界。周密却在洞彻自身有限性的永恒悲剧和痛苦之后,仍然以坚毅的精神,执着于对生命本身的探求。于是,在死的阴影下,在多忧而寡欢的艰难生活中,他通过对往昔的追忆与感怀,在物象与意象的转换中,试图熔铸内在的属己的心灵时间,抗拒沧桑洗礼,在光阴的河流里执念于对意义的追寻。
(二)文化乡愁
世变之后,天地不复存在,人何以存乎?这成了作者反复叩问自己的命题。《癸辛杂识》中,他引用陈过的言论对此进行了阐发:“夫徒以其统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则自今以往气数运会之参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侥幸者,皆可以窃取而安受之,而袅、獍、蛇、豕、豺、狼,且将接迹于后世。为人类者也,皆俛首稽首厥角以为事理之当然,而人道或几乎灭矣,天地将何赖以为天地乎?”[4]第八编第二册,235面对残酷的浩劫,他以书写抗拒遗忘,以俟“后之览者”藉此重回往昔、重温旧梦。于是竭力在岁月的废墟中找寻昔日的残片,“嘉与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象承平文物之盛焉”。[2]第七编第十册,92极力书写前朝文化昌明昌盛之物,以引起来者对故国的思念。
处在王朝更迭、地域失序之际,作者的生存际遇更为艰难,其不以形迹累心,更为注重自我心灵体验的心境凸显,冲破“为尊者讳”的藩篱,对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权臣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他指出:“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贾相持丧、起复、辞免,虚文汩汩,殆无虚日。如此三阅月,内外不安,而国事边事皆置不问。”[4]第八编第二册,194其“著《癸辛杂识》诸书,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韩、贾,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5]102。他进而将国运衰竭不振与士大夫不顾廉耻、君臣之义薄弱并举,《齐东野语》中就对诸多士人的品行不正、腐败无能、挥霍无度等进行了着力书写,充溢着对时局的反省与责难。就如盛杲在《齐东野语》后序中所感叹的,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个中缘由:“大抵宋季士大夫议论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轧如若聚颂然。是知国势之不竞,不当专责之秦、史、贾、韩辈也。”[2]第七编第十册,348
可以说,在审美视域中,周密更多看到的是历史的美学而非历史的全体。追忆中,尽管有着省思与反讽,却并不足以抵消作者对往昔的眷念与惜逝,他瞩目于往昔雅致的生活,如《武林旧事》卷十《张约斋赏心乐事》详尽描述了张约斋与文人之间的雅事;《齐东野语》卷二十《张功甫豪侈》中,极尽书写之能事,叙述了其豪奢的生活:“园池声妓服玩丽甲天下。”“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2]第七编第十册,338张约斋其雅致的生活、精致的品味令置身于陌生的历史、文化时空中的周密神驰意往。于是,在对往日的不尽书写里,书写者(周密)将重新回归自我,重拾失落的过往,吟味曾经的气息。追忆因此使得时间获有了心灵的、情感的维度,不无理想化的往昔,遂成为抵御历史洪流的心灵家园,开启对存在的思索,安顿了他的文化乡愁。
(三)敢期他年扬子云
宋元之际,周密政治理念中体现着强烈的“行道”理想。他在《齐东野语》卷十六“贾岛佛”中,对士人如何保持内在逍遥的精神境界,又同时兼顾个人社会责任,他找到了一个平衡范式:“盖酸咸之嗜,固有异世而同者,长江簿何以得此于人哉?凡人著书立言,正不必求合于一时,后世有扬子云将自知之。”[2]第七编第十册,268-269他坚信,书写能够跨越岁月铸就的隔阂,立言传远,不必求合于一时。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信念,周密于文字推求备至。一方面,总是表露出“务求事之实,不计言之野”的撰述追求[2]第七编第十册,13,另一方面,又极力追求语词的“近雅”风格[3]第八编第二册,5。这种语词风尚的推崇使他对理学家崇尚性理、卑视艺文的作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宋之文治虽盛,然诸老率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氏云:‘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言乎。”[6]146士人岌岌于功利,皆以“斯文”为己任,“文”的意蕴内涵受到剥蚀,周密对此深表痛心:
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醇厚,时人谓“乾淳体”,人才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万里习《易》,自成一家,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徐霧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竟趋之,即可以约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至咸淳之末,江东李谨思、熊瑞诸人倡为变体,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时人谓之换字文章,对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绕”等语,以至于亡,可谓妖矣。[4]第八编第二册,206
从字面上而言,周密看似是在漫不经心地梳理宋室南渡以来太学文体的流变情形,那些不复“道”的文章除求科第官禄于时矣外,终将是蓦然回首,时移事往,为世人所遗忘。什么能够不被遗忘?又怎样方能传远?这恐怕是作者始终隐含于其中的终极目的。外在的事功已无可为,唯有将心中对理想生活世界的思考与憧憬,公诸同好、留予后世,方能突破一己的时空而进入宇宙周流的大化之中。于是,藉“书写”的强力介入,回返心灵的家园,对时间的超越,由此成为可能;对“不朽”的冀望,由此得以实现。
二、离散书写
宁知无望,周密依然渴望原乡,其家乡吴兴先祖墓侧的冢室,即命为“复庵”,还曾如此与袁桷谈及此庵的命意:“复,反也,反诸其本也。圣人作《易》之义,深矣?余取斯名也,厥有旨。昔太公表东诸侯归葬于营丘礼,以为不忘其本。余家故齐人,虽南徙吴兴,而其遗礼,三世犹守之。自余失仕,居钱塘,非有酣豢之乐而忘其归,不幸而不得归者,势也。今老矣?苟终无所归,则与复之道奚取!亦尝推死生昼夜之理,其变无穷。反身而观,虚一而明者,物莫能御。则兹丘之乐,殆与造物者去来,而莫穷其所止也。”[7]486文字中充溢着强烈的离散情结,实是作者极为矛盾复杂困惑的内心世界的告白,在时光与地域的交错中,痛苦与彷徨的撕裂中,浸透的是期冀与现实的裂变、原乡与家乡的纠葛。他当如何纾解寻根的焦虑,如何在离散情结的撕扯中重构自我认同。
(一)“齐”:想象的乡愁,身份的建构
“齐”频频出现在周密的笔记文本中,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学者萧鹏、张薰、刘静等认为,这里的“齐”应是指向中州正统的齐鲁文化;韩国学者安芮璿则根据“齐”往往被目为“俳谐”“怪异”的代名词,认为其对周密“滑稽”“简易混俗”的性格特点有深远影响。[8]129这里,研究者均从静止的视角对“齐”进行了各自的解析,这种解析视角未免有将其文化属性固化、简单化的嫌疑。其实,物之文化属性又并非只有其固化的一面,社会学研究就曾对此指出:“绝非永远固着于某些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受制于历史、文化与权力的不断运作或操纵”,还特就弱势族群的视角,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说明:“建构历史的第一步就是取得发言位置,取得历史诠释权”,而“过去不仅是发言的位置,也是赖以发言的不可或缺的凭借”[9]70。这里就指出了“文化属性”不仅是存在的,也是生成的。鉴于此,笔者认为,周密于文本中流连低徊的“齐”,既非仅仅空间内实存之“齐”地,同时,也不完全仅仅指向“齐”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对原乡反复言说的用心,是在“取得发言位置,取得历史诠释权”。
易代之际,周密旨在藉由对原乡的认同,并于此认同中达致自我认同,他在《齐东野语》序中即言:“异时展余卷者,噱曰:‘野哉言乎,子真齐人也。’余对曰:‘客知言哉?余故齐,欲不齐不可。虽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无所言也,无所不言,乌乎言’。”[2]第七编第十册,13-14以此取得以“野”自处、自我放逐于主流之外的“发言位置”。并且,周密的文本中,“齐”总是连通着国族的播迁、家族的离散,个体信奉的价值的支离破碎、面临的虚无和失根的焦虑,以及记忆迷茫无际的恐惧。诸如:“余世为齐人,居历山下,或居华不注之阳。”[2]第七编第十册,13“弁阳老人周密,字公谨父,其先齐人。”[10]142“我家中丞公,实自齐迀吴,及今四世,于吴为家。先君尝言:‘我虽居吴,心未尝一饭不在齐也。岂其子孙而遂忘齐哉。’”[2]第七编第十册,11透过作者在此对“齐”所做的这些无穷的思索与追问,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话语或言说的“齐”,是一种关于权力话语的言说,它体现着多重文本的属性,周密于此,一方面书写自己的人生历程、无法释怀的乡愁,另一方面,则试图以“放言善谑、醉谈笑语”的野人畸士的立场,挑战甚或是抗拒由胜利者书写的正史。其对原乡对“齐”的关注,事实上是对“失去”的一种执迷、一种眷恋,潜流着周密历经世变彷徨于无地的困惑与焦灼,以及在这样的动荡中对重构自我认同的渴求。
(二)“耽美”于物
历史已成惘然,何不回归自我的空间,著述立言,寄托对逝去时空的记惦,以此完成生命的蜕变。诚然立言传远的理想甚为宏大,生命似乎又必须藉由某种媒介,方能有所附托,以垂之不朽。于是,作者“耽美”于物,每于书籍、法帖、鼎彝间,寄予无限的深情,探寻生命的意义。作者常常详细地描绘其赏玩之“物”的圣洁精美、动人之处。在《水落石出笔格》中,作者是如此情文并茂地描绘灵璧石小峰:“长仅六寸,高半之,玲珑秀润,卧沙水道,裙摺胡桃文,皆具于山。峰之顶有白石,正圆董如玉,徽宗御题八小字于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无雕球之迹,真奇物也。”[4]第八编第二册,288峰之灵秀与清幽无不令人神往。在《向氏书画》中,又别有情致地称谓雪白灵璧石:“高数尺,卧沙水道悉具,而声尤清越,希世之宝也。”[4]第八编第二册,218灿若珍宝的碧石总是令作者无限深情萦回其中。在《华夷图石》中,甚是夸赞奇石为异物:“汴京天津桥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华夷图》,山青水绿,河黄路白,灿然如画,真异物也。”[4]第八编第二册,248往昔熟悉地点中的大片奇石也是作者神驰意念之物。
诚然,耽物中隐含着作者对人生悲欢的叹惋与哀伤。《癸辛杂识》“白玉笙箫”中写道:“理宗朝,张循王府有献白玉箫管长二尺者,中空而莹薄,奇宝也,内府所无。即时有旨补官。未几,韩蕲王府有献白玉笙一攒,其薄如鹅管,其声清越,真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军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4]第八编第二册,287“画本草三辅黄图”中亦载:“先子向寓杭,收拾奇书。大庙前尹氏书肆中,有彩画《三辅黄图》一部,每一宫殿绘画成图,极精妙可喜,酬价不登,竟为衢人柴望号秋堂者得之。至元斥卖内府故书于广济库,有出相彩画《本草》一部,极奇,不知归之何人?此皆画中之奇品也。”[4]第八编第二册,287昔日皇宫中的白玉箫管、白玉笙不翼而飞,竟是“皆在军中日得之北方”;宋朝内府“极精妙”的书画却在“至元间被斥卖于广济库”。话语中浸透着作者因往日精美饰物失去的痛惜之情,蕴藏着作者对人生的留恋和对存在的思索,对心灵家园的执着追寻,对华夏正声的依归。故国、故园、故旧,固然都已只是意念之中的记忆了,离开物质碎片的符码,感知甚难,作者借此以局部、片段来关涉所有的逝去,其用心在于使其为后人提供一份可供追忆的情景,不至随着故国的覆灭而烟消云散。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周密耽溺唯美的内在动因,是特定之“物”与他个人情感与记忆的内在关联。面对世变的纷乱,作者试图通过特定之物找回自己的影子,在并不完美的生活中捕捉、创造着美,以此在赏玩过程中产生亲切感,重温过往,诠释美好,感悟人生,以凛然的浩气叩响着灵魂的正声。
三、写在历史的罅隙与劫灰中
历史的时间序列中,记载着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正史者着眼于历史的兴亡贤愚,这种追溯是单向的,只是简单地向读者陈述历史事实。书写历史的真正用意在于追索往事来“镜”“鉴”当下。周密对这种儒家史书的书写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其笔记既将原本隐匿的生命痕迹和历史真相从历史尘烟中发掘出来,同时,亦以其抒情、怪诞、悖谬的独特方式,寓“悲”于“喜”,外“谐”内“庄”,书写着身世零落之感、失家亡国之痛,讲述着今生恍若隔世的故事,以期透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物象的细腻书写折射出历史的年轮与时代的面影。
(一)道学反思,解构神话
笔记中,周密以世变以来的历史作为参照系,就道学与晚宋政事的关联作了深刻的现实评判。《癸辛杂识》“道学”条,揭露道学之士“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其反求诸己、内向闭塞的滑稽现象由此可见,整日清谈不休,以不论国事为冲淡、为高士、为旷达悠远,“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4]第八编第二册,290。还以正史不载的轶闻闲话,在谐谑说笑中慨叹、沉痛以至斥责伪道学种种以“雅流自居”的怪异、迂腐、自大的一面。如饶双峰“自诡为黄勉斋门人,于晦庵为嫡孙行”,罗椅“平生素诡诈”、“为巨富家子”而“青鞋破褙、蓬头拒面,然一贫儒”,方回“其处乡专以骗胁为事,乡曲无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齿。……老而益贪淫,凡遇妓则跪之,略无羞耻之心”。在貌似诙谐的背后蕴含着他对当代士风士行的深刻反省。
(二)关注边缘者,打破权力的独白
周密强烈质疑着当时的主流思想文化,拷问着时局政治的缺失,揭露着丑恶的宫闱秘闻(1)参《齐东野语》卷十一“慈懿李后”条(《齐东野语》,第七编第十册,第188页),《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条(《癸辛杂识》,第八编第二册,第308页)。,同时,也还有他对边缘者的深切关注,诸如市井卖艺算命者、盗贼、仆役,以及被边缘化的女性等都记录在案。如风趣而有义理的“王小官人”,周密赞许其是“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4]第八编第二册,174还如知恩图报的张约斋的佣工,“尚义介靖”不忘旧主的张防御、沈垚,不以文天祥题诗换钱的烧饼主人等有仁有识的市井小人物,周密叹其“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谓公论在野人也”[4]第八编第二册,305。即使是关于士人的记载,周密亦是侧重于关注那些国史中隐没不闻的中下层士人。如《齐东野语》卷十一《何宏中》中“其志亦可哀矣!国史乃失其本传焉”[2]第七编第十册,181。周密深深感叹这些或卑微或边缘的人们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寻社会精英阶层业已失去的豪侠、节义与风华,写下自己严峻犀利的评断,示其本相。
(三)写在历史边上,拷问复杂人性
在探辨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周密不惮于拷问、书写人性的复杂。如享誉后世的道学家朱熹,作者也不惮刻写他人性中的弱点。《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记录唐仲友自恃才华轻视朱熹,在陈同父挑唆下,两人结怨,之后朱唐两人互相搜集对方罪证,上奏皇帝,皇帝依据王淮“此秀才争闲气耳”的解释方两平其事[2]第七编第十册,295。在国事繁多、边境不安之时,他们不思为国效力,反而逞一时之气相互攻讦,让正史中单质化的朱熹由此变得立体、多元。再如《野语》卷三《诛韩本末》中,记载韩侂胄因得罪皇后与其兄杨次山,招致飞来横祸,中下史弥远等人之计,而被诛杀,从中可见南宋朝廷血迹斑斑的内部政治斗争。作者不惮通过这些复杂的斗争,不寓回护之意,写下人性的残暴。
周密在历史书写中,融入学者特有的深邃历史知识与敏感的审美判断,不但关注大历史叙述,同时还试图填补历史边缘的缝隙,让沉默的历史与历史中“沉默的大多数”发声。这种对于历史的微观片段叙述,在不断填补历史缝隙的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对历史宏大叙事的解构作用。这种悲悯的人文情怀和对普通民众的关注,催生了作者自觉反思的沉痛与愤懑,他以僭越正史自成一格的勇毅,开始了对群体命运的探辨、反思,以此示范了不同于历史传统官方形态的另类书写模式。
四、周密笔记生命体验中的审美超越
置身易代文化冲突的生存困境中,周密在对社会人生、历史往昔深情追询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情感上的体认与把握,更多的是对人生意义进行彻底的思考与追询,他着眼于心灵的自我完善,透过书写倾听且回应历史,在文本与记忆的召唤中获得心灵的净化、情感的升华,展现了由依靠外在因素的消解转向主体内心境界的提升。
(一)自我书写与自我涤荡的美学典范
在生命的迟暮时分,周密似乎愈发避隐、退居于与人无竞、与世相忘的自我时空中,进而在笔记中,以易代之际的独特视角感事抒怀。这似乎有些落寞,有些悲凉,但面对厄运,他始终保有一份率真放达、自娱调侃的尊严与优雅,往往于文本中展现、描摹种种无可诉说的悲苦、惆怅、忆念。按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的观点,离散赋予离散者双重的对位的视域,于是,一些看似悖立的、矛盾的思想情感会奇妙地汇流在他们身上。周密亦然。如坚毅刚正的节行与宽和豁达的胸襟,闲适淡泊与耽美于物,对道统的重视与对个体独立自主意识的关注。正是这种悖立与整合,周密一生历经诸多坎坷、挫败,却始终执着于自己的理念,执着于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即使是在亡国后的归隐闲居之中,亦不忘追忆故国、省思历史;即使是在玩乐戏游之中,亦自觉地思索人生、壮心明志,始终存有对永恒事物的思辨。
事实上,身为南渡士人,年迈之时又置身于王朝鼎革、地域失序、蒙元新政、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共存的时局中,周密的生命体验中始终伴有一种边缘性,似乎陷入一种不知所措、孤立无援的境地。但他似乎又总是以老者遍阅风雨、洞观世事的悲哀与超脱,以智者的明智豁达与独立卓见,藉由智性的微笑与谐趣的方式表达对苦难的体悟与包容,坚持以自娱娱人的方式在不完美的生命中淡忘逝去、追求美好。他由此打破文本的封闭与自足,跳出历史的传统官方形态的书写模式,以自身独特的视角书写人情世故、世事沧桑。由此,文本中的大量史学记载便不再仅仅只是一种事实的记录,它传达了作者在历史更替、文化转型时期紧迫煎熬的内心世界,是一种着眼于自我心灵发展的人格境界的重构,诠释了作者对生命体验和现实关怀的全新阐释与融合。通过这种自我书写,作者不仅达到了自我的净涤,还不间断地引导我们回归到审美活动中个性化、多样化的感性生命形式本身,唤醒我们内心中的生命意识,由此让我们体味历史、享有世界,进而深入探索其内在的深层精神实质与情感本体。
(二)审美与抒情观照的生命范式
在宋元鼎革之际,面对病痛、死亡、乱离,周密在离散中深悟生命之真谛,挥却羁绊,回向自我,返璞归真,坚持以独立批判的精神识见与道德勇气,著述历史,品评人世;以优雅的品位、深厚的涵养,豁达的胸襟,在国破家亡的灰烬中,还之以学术的开创、审美的超越、人格的升华;在至为艰难的境遇中闭门著述、努力不懈,顽强地记录晚宋繁盛的历史文化、辉煌的文学艺术。
据此,我们正可理解晚宋在文化上达到的新高度,正是基于大量类似周密这样的士大夫群体的优雅情怀与潜心著述,在文学作品中自由而全面地反映自我的内心世界与情感,将笔端指向心灵与个人进行自由的人性抒发,以追求学术、文学的全面发展为理想典范。他们是晚宋社会的中坚力量、精英阶层,以其真实丰富的生命体验记录了时代的优雅闲适的日常生活,展示了时代典雅精致的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为易代之际的一种人格范式,周密给后来者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他不仅以浩瀚的著述,突破了人的生存困境,更以丰富、深邃的内在生命体验,彻底追问与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折射出作者在易代之际直面地域失序、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共存的理性自觉,以及立功不成、反诸立言以超越现实困境的主体意志。
王朝鼎革之际,面对地域失序,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共存,周密不以形迹累心,寓隐于物,注重自我心灵体验与感受,着眼于自我人格境界的提升,将心中最普遍、最深刻的东西通过真实的生命体验表现出来,于著述中臻至不忧得失兴废,不念沉浮毁誉,泰然处之,耽美于物,实现了于喧嚣嘈杂的世俗社会中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超越,这种圆融冲和、随性自适的审美人格境界,是对长久以来“学而优则仕”的人格的消解,是士人主体意识觉醒与重建理想人格的一次努力。他不再如以往的遗民颓废自怜、披发入山野,也不是同时代诸多士人表现出的闭门遁迹、独立岁寒之操,周密于现实困境中将人生导向审美化,构建孔颜新境,其表现无疑是更具主动性与自我个性。中国文化中的遗民心境,于周密这里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