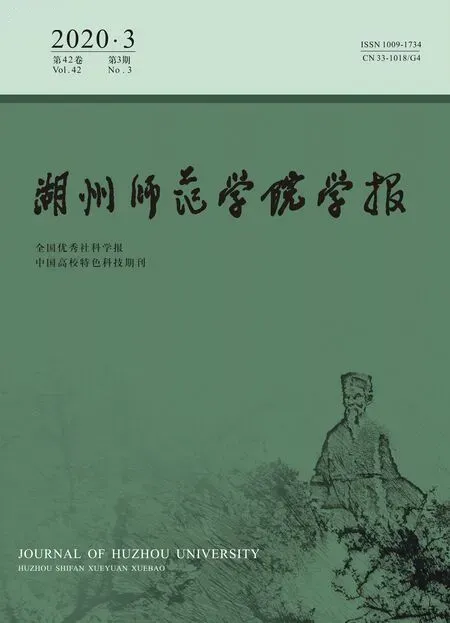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民主体性的演进特点与对策
——基于湖州乡村旅游地调查
2020-01-18刘战慧
刘战慧
(湖州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地农民进行乡村旅游创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部分农民在获得较高收入的同时,其文化素质、服务技能、经营管理能力均获得大幅提升,并逐渐形成一个规模不断扩张的阶层。乡村旅游创业助推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和形成,其对构筑我国乡村振兴的农民主体具有深远意义。
一、乡村旅游地新型职业农民主体性的演进特点
通过对湖州典型乡村旅游地的调查发现,农民通过乡村旅游创业趋向职业化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嵌入性视角的离土脱嵌到返乡重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深入推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即老一代民工潮中的农民工。21世纪,随着80后以及90后的加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双重脱嵌”的困境: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制度脱嵌),又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传统脱嵌)[1]170-188。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传统纽带的存在降低了其对城镇制度保障的各种要求;而当新生代脱嵌于传统时,“制度脱嵌”的负面效应会被相应放大,他们对城镇排斥性制度的忍耐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脱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乡村旅游发展不仅与农民创业存在时间上的关联,而且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职业化之间存在契合关系。水口乡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西北部,乡域面积80km2,其中核心旅游区面积16.8km2,户籍人口1.8万,历来以唐代贡品——紫笋茶、金沙泉而闻名,有“茶文化圣地、生态旅游乡”之美誉。水口乡的受访村民表示在2000年之前,乡村旅游还未发展起来时,有约半数的村民外出打工,经历着和全国大多数农民工一样的脱嵌困境。2002年长兴县乡村旅游开始起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被媒体称为旅游业发展的“长兴模式”。其客源主要是距离长兴100km~200km的沪、苏、浙等地城市居民,以长兴为吃住基地,实现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式的度假生活。水口乡坚持把乡村环境和乡土气息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元素,坚持农民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以农民乡村旅游创业为主线,实施村民自主经营。2018年水口乡已有各类农家乐500余家,床位数20 000余张,餐位数25 000多个,从业人员2 200多人,共接待游客356万人次,旅游收入9.48亿元,村民人均收入3.6万余元,户均营业额约70万元。(1)各具韵味!湖州将新增三个省级旅游风情小镇.浙江在线.http://huzhou.zjol.com.cn/yw18229/201912/t20191227_11520118.shtml.由于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创业收入远远高于外出打工收入,原来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返乡加入乡村旅游产业,通过乡村旅游创业,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大幅提升,并且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培训也提升了村民的素质水平和服务能力。农民通过乡村旅游创业克服了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脱嵌”的社会问题,这种返乡重嵌使得农民在本乡本土通过多种兼业实现了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化。
(二)治理性视角的双重消解到聚合新生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着剧烈的、深刻的变化。1920-1949年,在内生性的乡村治理崩溃的情况下,民国政府启动了保甲制,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践。梁漱溟先生的村民自治、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在当时虽有很大成绩,但仍然不能挽救当时乡村逐渐凋敝的现实[2]70-75。1949-1978年,新中国对农民实施动员,中国最基层农民的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空前觉醒,干劲高涨,合作意识增强,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但反过来也瓦解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固有的乡土社会的治理机制。1978年之后,当人民公社逐渐解体,毛泽东时代的乡村治理体系日渐式微,农村又出现了大量乡村治理的真空地带。之后的乡村治理面临着双重消解,一方面是内生性的乡土社会治理体系消失,另一方面是嵌入式的依靠国家能力的农村管理也日渐衰弱,即“双重消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很多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的状态。
从湖州典型乡村旅游地的调查来看,农民在乡村旅游创业过程中,尝试按照旅游体验是旅游世界的“硬核”这一理念,围绕乡村旅游体验产品的创造、生产、销售、提升等环节构建独具特色的价值链,涵盖了乡村旅游体验产品的设计、配套环境的治理、体验产品的营销、消费与服务提升等各个流程,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村民参与,且都被赋了不同的价值,形成了一个农民广泛参与的基于商业利益的动态平衡治理体系。
湖州德清县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坚持“政府主导、村民主体、市场参与”的原则,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以增强农民获得感为根本,重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整合各方惠农政策,形成工作合力和内生动力。重视激发乡村集体经济活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水口乡顾渚村为了发展乡村旅游,先后成立了农家乐协会、农家乐诚信联盟、工商消费维权站、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农家乐党支部等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在表象上看是为乡村旅游发展服务,实质上也是对新时代乡村内生性治理的探索。
(三)文化性视角的人为流散到本土延承
21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日益市场化和商品化,乡村道德评价标准和乡村道德体系逐渐混乱无序,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超越了传统的道德态度和伦理原则,乡村伦理的价值目标日趋崩塌,传统道德不断呈现碎片化。我国农村传统的生活秩序和精神秩序也发生着急剧的变迁,乡村劳动力出现了大规模的区域转移和流动,乡村人才出现断层,由农村人口流动引起的农村整体经济社会功能的综合退化呈现为村落空心化、家庭空心化和劳动力空心化等复合体。乡村文化日益边缘化,认同感日益疏离。从根本上说,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很多文化因素都已经面临式微或消散。乡村文化整体上处于一种断裂的状态,在形态上不断地被扭曲和撕裂,多种文化元素并存,但又混乱无序[3]6-11。乡土文化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因此表面上的文化衰微并不能反映实质上的民众抛弃。对因囿于现代技术文明而找不到“故乡”归途之路的现代人来说,乡村旅游无疑是对“根基持存性”失去的弥补。乡土情结点燃和维持着人们内心深处对乡村的热切期盼和回归。
2002年以来,湖州乡村旅游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作为乡村旅游开发的主要承载者,湖州乡村旅游地的村民逐渐认识到乡村文化对游客的深层吸引力,依托当地独特的文化价值,发挥乡村文化的载体作用,借旅游发展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采用各种形式和方式的文化解读、景观塑造、互动体验,以及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和现场展示,构筑乡愁载体,实现乡村文化的再生产。通过乡村旅游的这种符号化阐释,使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逃离乡村而又对乡村无限眷恋的人们的乡愁在乡村旅游中实现审美化和抒情化的释放,如此缓解了乡村和城市在分裂对立中造成的病态和伤痛。
湖州市安吉县山川乡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运用国际化设计理念,充分挖掘传统农耕文化、乡土文化、民族文化遗产资源,新建或恢复江南威风锣鼓、大里双龙、竹马灯、鳌鱼灯等民间文艺队伍,关注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再现村庄记忆,向游客展现“山水乡村”生活区,“安逸隐世”住宿区,“山民生活”体验区,铸就乡村旅游的乡土文化灵魂。百翠山庄的建设理念是将“天人合一”的传统养生理念与现代农业休闲统一起来,积极发展生态有机农业,以原生态的自然农耕产品为主打特色,对传统乡村农耕样貌适当恢复。农民在乡村旅游创业中更加侧重于“农”字,回归老本行,精耕细作农村每一分土地,构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地田园景观。深耕农业、经营田园,既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和主业,也是一种新兴、时尚的生活形态。乡村田园挖掘“乡愁元素”、发展“乡愁经济”,为都市打拼的人们提供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体验。
(四)产业链视角的自在参与到自为耦合
产业价值链是一个基于商业利益的动态平衡系统,乡村旅游创业农民在价值链上是竞争与合作关系,需要建立一种尊重和符合各方利益的机制,如此才能促使该链条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农民乡村旅游创业也基本经历了这样一个从自在参与到自为耦合的动态调整过程。价值链节点企业追求的经济价值,是通过满足价值链终点的客人的体验价值来实现的,即旅游者体验价值与创业农民的经济价值的一致性是旅游价值链稳定并动态优化的前提条件。基于此,从价值链优化的角度看,旅游价值链所创造的总体价值如何在价值链节点企业或参与者之间实现均衡分配,是解决体验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性的关键。
湖州乡村旅游地农民在创业中,从开始发现商机时的自发、被动、零星参与,到目前建立的有效约束与激励机制,使价值链节点的参与者的价值取向不断地与价值链总体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从而最大化地减少价值链的损耗。湖州乡村旅游集聚地价值链的整合优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创业与职业化的成长过程。
二、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主体性面临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湖州模式”的乡村旅游发展已取得良好成效,农民主体的收入与参与度大幅提高,呈现出乡村振兴的良好面貌,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职业化认同的惯域思维有待突破
农民职业化是当今世界上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的普遍选择,是发达国家消除城乡差别的重要标志。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受习惯领域的思维局限,以及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权利的不足,农民的现代化和职业化推进相对比较迟滞。湖州乡村旅游地农民通过创业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长,已经在心理上萌发了从身份到职业的转变。但从整个群体意识和自觉性上来看,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与职业化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政府提供外源性支持和培育,更需要从根本上生发农民自身的内源性发展动力和能力,理顺农民职业化的发展路径。
农民职业化从根本上说是传统小农经济走向整体性消亡的现代化过程,是部分农民完成非农产业转移的同时,由原来从事农业生产因其出身自然决定,变为现在的自愿选择过程,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由自然、半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向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转变[4]199-204。尽管乡村旅游创业活动在提升农民收入同时实现了对农民职业化的心理启蒙,但农民真正的现代化和职业化还应体现在心理层面的职业认同。目前,农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心理上的职业认同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收入的工具理性上,而反映精神生活高层次需要的道德理性和文明理性还没得到充分的发展。农民职业化发展仅仅凭借经济上的工具理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道德理性的发展,使道德理性与工具理性形成良性互动,这样才能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如此一来农民的职业化才是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农民也才能在心理上产生职业认同。
(二)农民主体形成的价值共创机制有待完善
乡村旅游的价值创造会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他们共生于价值链的各个节点。湖州乡村旅游地农民创业中虽然经历了自发到自觉地聚合协调,发生了诸多有益的变化,但是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瓶颈。相对来说,农民对价值共创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在组织管理、技术开发等环节未形成普遍的合作共创的集聚优势。政府、村民、旅游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旅游服务创新的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机制还不完善,各利益主体通过价值链与节点合作伙伴的共同行动相对迟缓,价值共创与利益共享的总量不高。这也成为农民职业化转变的一个困境。
(三)农民主体的文化自觉性有待提升
近现代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与转型,农村社会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解构浪潮。在乡土文明和乡村文化日渐式微的过程中,农民群体面对变迁苦苦挣扎,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呈现出碎片化的在场或离场状态,在农业生产、文化传承方面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主体隐退现象。
从乡村振兴的主体视角来看,农民更多意义上是具有乡村社会文化特征的人或群体。在乡土文明和乡村文化日渐式微的过程中,湖州乡村的大部分农民群体在农业生产、文化传承方面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主体隐退现象。调查发现,61%的受访者不认同自己是农民,其中过半数的村民有致富后迁居城市的想法;村民认为市民和农民的区别主要集中在经济收入和福利配置方面,几乎很少有人区别城乡群体的社会文化属性;39%认同农民角色的受访者中绝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人,且受过高中(中专或技校)及以上教育的人数显著偏低。精神层面的文化自觉是目前制约农民职业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障碍因素。
三、乡村振兴视角下提升农民主体性的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方式。通过乡村旅游创业助推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培育和形成,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具有深远意义[5]102-118。
(一)加强农民创业教育与培训,提升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
培训可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和就业水平,从根本上激发其潜在的创业热情与活力。大力弘扬创业文化,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发挥农民创业典型的带动作用,大力宣传他们的创业精神、成功经验与模式,把创业成功者推上农村社区管理者的位置,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与自信心,从而带动其他农户创新创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强化针对性培训,提高农民的创业能力。引导科研机构、培训机构、行业组织等参与农民创业培训,提供常态化的教育培训、技术指导、管理咨询、企业诊断等服务;成立农民创业讲师团,聘请高校教师、职业指导师、成功农民企业家、农业技术专家等,对农民创业过程中急需的乡村旅游知识、市场营销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各种专业技能进行定期指导和答疑解惑[6]179-180;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尝试对创业农民进行个性化辅导,如按年龄、文化水平、创业方向等划分成具有一定共性的小群体,进行专题培训,从而使培训内容与创业需求、理论与实践能够更好结合。
(二)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增强乡村振兴的外源支持
强化政府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推动。乡村振兴离不开现代化的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部门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保证其顺利实施。
改善农民参与和利益分享机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村民、旅游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旅游服务创新的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机制。在政府和农民合作组织的推动下,建立知识分享、技术共享、渠道共用、资源互补的机制,从产品开发、成本改进、流程优化等环节,实现知识、规划、流程、资源与关系的协同和一体化行动。
建立多元资金支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农村金融监管,规范农村民间资本市场,提供方便、快捷的适合农民乡村旅游创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建立多元的农民创业引导基金,对社会效益好、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农民乡村旅游创业项目进行保障和支持。
(三)增强农民文旅融合的热情和动能,坚定乡村振兴的主体自信
乡村作为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农民开展创业和实践乡土文化的空间载体。在乡村旅游发展进程中,要更多地引导农民对优秀乡土文化进行现代建构和旅游阐释,使其成为乡村旅游产业兴旺的魂魄和文化名片;并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旅游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实现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基层政府和乡村社区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使农民在乡村也能感受到市民的福利配置,增强对农民职业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成功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经济自立和文化自信的过程。通过强化农民经济自立和文化自信,更多地关照反映精神生活层次需要的道德理性和文明理性,使其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使农民对职业化和对乡村的认同能够相对稳定和可持续,进一步坚定乡村振兴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