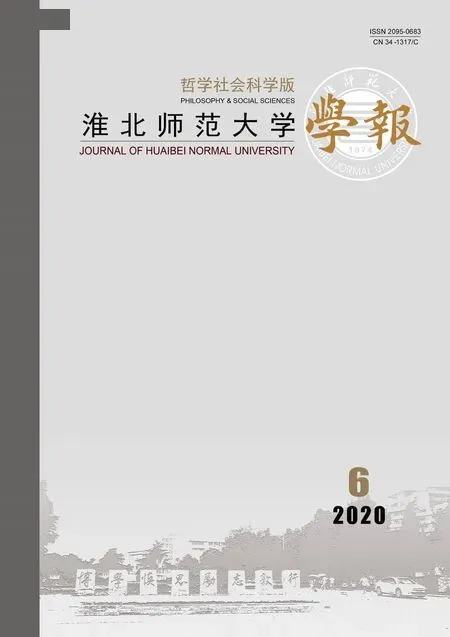论晚清皖中地域文学体貌生成与时局映射
——以“合肥三家”为中心
2020-01-18史哲文
史哲文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230051)
鸟瞰文学史演进历程,历代文坛诗脉壮大与延续,一个重要表现是文学流派的成熟与流衍:“流派论的提出,既是文学创作成熟的标志,也是文学研究成熟的表征。”[1]清诗体派的地域特色突出,在上层诗家形成一时之体的同时,地方诗界也存在一地之派,呈现出大家巨擘与地方诗群同时共通的态势。清代安徽诗人辈出,诗歌成就斐然,前人多有阐论,但依然有不少诗人诗派虽在当时颇有影响,却未被后世熟知。近代不少文人对晚清江淮地区文人群体如“庐阳三怪”“合肥三家”“城东七子”“三老会”等有简略叙述①详见陈诗《皖雅初集》、李家孚《合肥诗话》、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马祖毅《皖诗玉屑》等文献。。“合肥三家”是其中风格明确、记载详细、声名显著的地域诗派,从体貌气象、地域特色、诗学承继上看具有典型意义,能够表现地方诗学发展的脉络细节,反映地域文学板块的形成流变,不可逸出研究视线,同时前人著述如《安徽文化史》《安徽诗歌》等曾提及此三家,但对其认识存在偏差,应予以反拨。
一、《合肥三家诗录》成书辨析与“合肥三家”诗歌体派由来
“合肥三家”语出谭献于光绪十二年(1886)所辑地方诗歌总集《合肥三家诗录》二卷,谭献于光绪十年(1884)到光绪十二年官宰合肥县,《合肥三家诗录》即在此期间纂成。是集收录清代庐州府合肥县徐子苓、戴家麟、王尚辰三人诗作,上卷收徐子苓诗六十三首,戴家麟诗三十四首,下卷收王尚辰诗一百一十四首。
清人李国松称赞三人道:“(徐子苓)崛起道咸之际,与戴、王二老狎主坛坫,声誉流闻。”[2]680可知彼时三家诗名彰赫。徐子苓(1812—1876),字西叔,号毅甫,又作懿甫,官和州学正,著《敦艮吉斋诗存》《敦艮吉斋文钞》《闲闲园古文钞》。时人称徐子苓:“先生诗与文兼胜,而诗尤极其诣力,足以上继龚、李,称后劲焉。”[2]680“龚、李”即龚鼎孳、李天馥。王尚辰(1826—1902),字北垣,号谦斋,晚号遗园老人、五峰居士等,官翰林院典籍,著有《谦斋诗集》《遗园诗余》。时人对王尚辰评价也很高,论者如方濬师便激赏有加:“谦斋诗,读之如太华三峰,耸势争奇;如黄河水从空来,汪洋恣肆,末由揣测;如疾雷怒电,惊惮蛟蛇蝄蜽,而无所逃避;如张乐洞庭之野,白虎苍龙,鼓瑟吹篪,度曲未终,云飘飘而雪霏霏,令人目夺神駴。”[3]177戴家麟,约咸同时人,字子瑞,咸丰初贡生,官宿州学正,后改国子监学正,著有《劫余轩诗存》《听鹂馆文集》,《庐州府志·文苑传》评价其诗曰:“诗尤清修脱俗。”[4]113显示出迥异时人的面貌。
谭献于光绪十年至合肥后,先订讫王尚辰《谦斋诗集》,于日记中记载:“合肥王尚辰《谦斋诗集》七册属予审定,讫。”[5]124又于光绪十一年选定徐子苓《敦艮吉斋诗集》,谭献在日记中称:
选定徐毅甫《敦艮吉斋诗集》,将与谦斋合刻。……予刺取其苍秀跌宕之篇,固江淮间一作者。参张亨甫、鲁通甫、叶润臣、莫子偲,季孟之间,亦无愧色。同时戴子瑞广文,诗未成家,亦有生气、有真意也。[5]128
这段话既点明《合肥三家诗录》的辑选意旨,又看出徐、王、戴虽称三家,但是内部又有高下之别。陈衍认定:“戴不如王,王不如徐。”[6]谭献此处未评价王尚辰,不过对徐子苓赞赏甚高,认为其能与坛坫名宿张际亮、鲁一同、叶名澧、莫友芝等人相颉颃,王揖唐也称:“谭复堂有《合肥三家诗选》,徐西叔最工。”[7]293
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三人中徐子苓诗歌成就相对最高,但是集中选诗数量却并未占最多篇幅,反而与戴家麟同列一卷,似乎不合常理。其实,这与谭献本人交游情况有关。谭献在编《合肥三家诗录》之前有合徐子苓、王尚辰二人为《淝水二子诗选》的设想,他在日记中又说:“择(王尚辰诗)言尤雅者,或合徐毅甫为《淝水二子诗选》,或舍毅甫而入予《复堂朋旧诗录》独为一卷,与陈少香相次。盖毅甫诗集已刻,予又未相识,不当登诸《朋旧》也。”[5]259这段话提供三点信息,一是谭献赏识王尚辰的诗作,二是徐子苓本人诗集已在《合肥三家诗录》之前刊刻,三是谭献与徐子苓并不相识,正是这三点影响了《合肥三家诗录》的编排思路。
那么,为何谭献如此看重王尚辰这样一位今人不大熟知的诗人?事实上,谭、王二人交往甚密,他在《谕子书》中坦言:“王谦斋先生,名贤巨学,著作大家,一见倾心,定千秋金石之交,如积素累旧者然。”[5]291据前人统计,谭献在日记中有关与王尚辰往来的记载达十四处,如记载王尚辰为自己修订诗文:“为例将寄诗文回杭付刻,稍整理之。改诗数句,从谦斋所定也。”[5]257据查阅钱基博藏《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内载王尚辰寄谭献信札三十六通,在众人中数量最夥,札中诗词交流极为密切,落款语气亦师亦友,如“录请复堂先生一粲”[8]39,“仲修家师订正”[8]62,“奉和仲修老父母留别”[8]69,“仲修使君以《施口秋泛》一律见示,即衔尾句意和韵呈教”[8]70,从诗札数量与内容上可见二人交谊。
就上述材料来看,谭献在日记中所称,选定徐子苓与戴家麟诗“与谦斋合刻”,又设想选王尚辰而“舍毅甫……独为一卷”的潜在语意,表明《合肥三家诗录》以徐子苓与戴家麟诗合为上卷,王尚辰独占下卷的安排,正是选谦斋诗作在先,再选徐、戴二人诗作辑成此集。因此,徐子苓诗集已刻,没有必要再全部录入《合肥三家诗录》内,即便徐子苓诗歌成就高于王尚辰,谭献与王尚辰的深厚情谊应是其编《合肥三家诗录》关键缘由。
不过,三人被确立为一个诗人群体,并建构为地域诗派,绝非是谭献一人之意,徐子苓、王尚辰、戴家麟本有交往,他们的业缘关系也是“合肥三家”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徐子苓与王尚辰友善,王尚辰本人诗集内有多首诗作记述与徐子苓交往,如《辛亥四日徐毅甫子陵孝廉过墨春轩索兰花隔日酬以诗又乞盆梅却答兼招饮》中句云:“兰以比君子,相交臭味亲。名园添石友,余意结梅邻。”[3]249徐子苓与王尚辰曾经共事安徽巡抚英翰幕下,而戴家麟与王尚辰也有交集,戴诗云:
月色荒城静,寻君独款门。云归天外雁,水失旧时村。铸错平生几,论交尔我存。子山风味别,佐酒问东园。(《月夜过王谦斋》)[9]363
去日惊心百计疏,里门渐抵岁时除。行藏郁郁双蓬鬓,天地悠悠一草庐。斫剑君非因酒病,挂冠我岂为山居。男儿合向青藤老,犹胜虚名秽史书。(《将抵里门寄王谦斋》)[9]364
还需说明的是,徐、王二人又与朱景昭被称为“庐阳三怪”“合肥三怪”,《合肥诗话》云:“翰簿放诞,毅甫孤僻,默存傲慢,时人目为三怪。”[10]531《皖雅初集》亦称:“毅甫先生尝佐合肥令英果敏公翰戎幕,后英公至皖抚,欲疏荐之,与同僚朱默存景昭、王谦斋尚辰皆拂衣归里,时人谓之‘庐阳三怪’。”[11]《皖志列传稿》《皖诗玉屑》《清史稿·文苑传》也有类似记载。朱景昭(1823—1878),字默存,“平生慕方苞之为人,古文亦具桐城体”[12],著《无梦轩遗书》,不过诗名不昭。“三怪”虽在当时已有并称之名,但非因文学之名,而是由于性情异于常人,同时,他们同进退的一致经历也应是被时人视作一体的原因。
许总先生认为,诗歌体派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某一特定时期带有普遍性与倾向性的诗坛风气与审美时尚”,其二是“若干趣味相投的个体诗人通过交游酬唱等社交应酬性联系而聚合为规模或大或小的诗人群体”,其三是“某些诗人之间当时并未意识到在创作题材或艺术体性方面的类似而为后人确认为一种独特的体格或流派”[13]。故而,谭献在《合肥三家诗钞序》云:
诗也者,贤人君子不得已而作也。三君子者,不得已之故,同不同亦未可知,惟志隐轸而行高清者,则无不同。故平居相慕悦,论交相友善,文章各有趋向,亦犹立身之各有本末。至于希古乐道,与夫观时感物,如笙磬之同音焉。[14]189
“合肥三家”体派之名,是他们本人并未意识到在创作题材或艺术风格方面的类似性,而被他人确定为一个诗歌体派的。但是在构建这一地域诗歌体派的过程中,有两点须注意,一是他们彼时有交游之实,二是命名者谭献与他们所处时代相同,能够真实观照当时诗坛原貌。既然徐子苓、王尚辰、戴家麟被确认为一个诗歌体派,显然在诗学风貌与诗歌内容上应有一定共性,那么我们可以深入到三人诗作文本中来看是否如此。
二、时代变幻下“合肥三家”创作风貌: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在乾嘉以盛世之音为尚的风潮过后,自道光为关捩,至咸同为激变,东南一带诗人的诗法趋势一转怡情雍容之气,更追求沉郁慷慨之风,咸同以后归于平淡,至光宣“诗界革命”体格又一变。既被目为一个群体并称的地域诗歌体派,那么“合肥三家”理应或客观上具有较为统一的创作风貌,在《合肥三家诗录》中,三人所选诗后大多有谭献点评,结合诸别集、诗评、诗话,可以较为明晰地考察此三家的诗学风貌与创作成就。
先看徐子苓,徐诗学杜,谭献称其“郁郁莽莽,刻意杜陵”[5]128。徐子苓有《哭阿健五首》,谭献批点道:“尤为沉郁,源于杜陵。”[9]353又评《姥山歌》曰:“高瞻远瞩正尔,含凄古淡,骨韵双绝,前无古人,心目中不必无《同谷七歌》,亦正不必有也。”[9]356毅甫性情孤傲,其诗自有清隽奇气,如《姚司马行为石甫先生作》,姚司马即姚莹,谭献评价此诗曰:“骨气清高,奇情横溢。”[9]358道出徐子苓清高之骨,奇崛之情。姚莹本人则认为徐诗“体洁思清,时获妙绪,佳者在高岑王孟之间”[15],也抓住了其诗“奇清”的一面。而结合前文谭献认为徐子苓与鲁一同可并峙而无愧色的观点,钱仲联先生一方面认为鲁通甫“沉雄开阖,神似杜公”[16],另一方面亦称:“孙鼎臣题词以子苓与鲁一同并举,以为鲁之精整似程不识,徐之雄奇似李广。而孙尤叹服徐。徐诗为同时桐城派作者和宋诗派巨子所推崇。”[17]恰从两方面证明徐子苓学杜而超脱奇清的审美特征,诚可谓当时名家。
再看王尚辰,其诗熔铸诸家,唐景皋称其“沉郁近杜,豪肆近苏”[3]170,谦斋既取法唐人,近“唐贤三昧”[9]375,又得苏陆豪宕之风,有纵横生气。谭献称:“徐诗鸷悍,不参异己;谦斋则苏、陆、王、孟,时掇其胜。近岁且慕高淡,渐近自然。毅甫没,无抗颜行者矣。”[5]124《晚晴簃诗汇》收其诗三首,皆写景之作,并非本色。学杜是王尚辰诗学源流所在,谭献评《淮雨怨》曰:“真气盘郁,直接浣花。”[9]369评《杂感》曰:“语奇句重,是真杜诗。”[9]374与毅甫鸷悍孤傲不同,谦斋性格放诞不羁,但学杜老成:
谦斋早岁即从杜诗入手,故举止老成,不免质直。……乱定后,渐趋平淡,乃觉大雅不群。近作尤多弦外之音,王、孟、苏、陆,转益多师。异时论定本朝名家,自有一席。[5]259
故而诗中常有硬直苍豪之音,奇中生劲,而内在潜涵的诗情则沉郁真挚,可称“奇劲”,时人江有兰云:“昔读谦斋诗,如入五都之市,百货具陈,珠贝珊瑚,龙宫灿烂,于世者久矣。今观此卷,又变化从心,寓清新于警炼,含苍劲于婀娜。”[3]197-198是对王尚辰以挚情驾驭的“奇劲”诗歌特点做出的准确概括。
徐子苓、王尚辰皆尚浣花,究其原因,乃晚清家国动荡直接映射于诗作所致,兵乱之时悲欢离合的景象往往触发诗人的诗情感慨。谭献曾分析王尚辰学杜的缘由:“中更兵乱,自在戎马间奔走皮骨,悲歌慷慨,遂与老杜时地相副。所短者天性峭厉,处境悲凉,遂觉一发无余,尚少含蓄变化。”[5]259王尚辰以杜为尊,尤其表现在咸同之时的诗歌创作中,如其《癸丑人日卷石山房题壁十首》:
皖公半壁倚长城,号召新标保卫名。未按舆图谁聚米,坐挥尘尾浪谈兵。上游已失樊篱固,下策徒劳铁索横。整顿乾坤须巨手,道旁筑室总无成。(其五)
一局纷更等弈棋,河山举目不胜悲。浮生久已梦胡蝶,世事何如食蛤蜊。十笏清闲摩诘地,一编涕泪少陵诗。愁中似厌春光早,新柳垂垂绿几丝。(其十)[9]367-368
题中癸丑人日即咸丰三年正月初七,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沿江而下,攻下武昌,直逼安庆,即诗中“上游已失樊篱固”所指,合肥虽尚未遭到围攻,但战事已迫在眉睫。王尚辰之诗正反映出动乱局势下传统文人悲愤愁苦的心绪,谭献评此组诗得“杜神杜法”[9]367,欣赏有加。王尚辰诗风转关恰在此年,清人方濬师认为王尚辰的诗风在咸丰三年后为之一变:
癸丑以后,各诗直逼杜陵,声调悲凉,风格遒上,身所历、目所接,胸中愤懑不平,悉寓于章句中。空同、于鳞无病呻吟,那复有斯!沉痛捧诵数过,佩服无地,非诗能穷人,穷者自工。[3]200
是时王朝突遭巨变,半壁震动,太平天国达到鼎盛时期,十一月胡以晃率军围庐州,当时王尚辰奔走抵抗,至咸丰三年十二月,太平军攻下庐州。所谓“癸丑以后”,正是指王尚辰诗风在庐州失陷后的变化。谭献评价此时王尚辰诗作曰:“与《羌村》貌异心同。”[9]368又如其《除夕读杜诗书后》:
余亦遭戎马,酸吟独此篇。君亲增涕泪,魂梦扰烽烟。老作诸侯客,难为时世宾。一官虽落拓,犹见中兴年。[3]474
兵燹时事与王尚辰宗法少陵的诗学根柢交汇,老杜的沉郁心绪也与之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感。时人方希孟对王尚辰诗风转变上具体年份的分界则有不同见解:“壬戌以前,以雄丽胜。癸酉以后,以平淡胜。为境屡变,而亦各有所失。最盛者,其癸亥至壬申之间乎?”[3]200-201壬戌即同治元年(1862),时年清军夺回庐州,癸酉即同治十二年(1873),清军平定洪杨。癸亥即同治二年(1863),壬申即同治十一年(1872),这段时间是清军逐步取得胜利的时间段,方希孟与方濬师观点稍异,认为谦斋诗在庐州收复至太平天国灭亡之间为最盛。而至癸酉以后,时局稍平,正是所谓同治中兴之时,王尚辰诗风也归于淡泊,王尚辰本人便意识到“五十以后所作,渐趋平易”[3]3,也就是前文谭献所说“渐近自然”的情感内因,方希孟“各有所失”之语也恰与谭献所云相印合。即便方濬师、方希孟、谭献表面上观点有所区别,但他们认为战争导致王尚辰诗风变化与诗学成就提升的内在思维是统一的,在王尚辰的诗风嬗变上,映射出皖中诗坛的文学现场。
至于戴家麟,前人研究认为“合肥三家”具有诗学少陵的一致特点[18]。而谭献仅认为徐、王二人宗杜:“谦斋早饮香名,淮南文学有志节之士也,与徐子苓毅甫齐名……诗与毅甫皆学杜。”[5]124宗杜是徐子苓与王尚辰的诗法相近之处,然而戴家麟是否也学杜呢?谭献并未说明。有关戴家麟诗学特色的文献记载除了前文《庐州府志》以外鲜见,不过阅读戴诗可以发现,如果说,徐子苓诗重“奇清”,王尚辰诗自“奇劲”,那么,戴家麟更多的是以“奇逸”而得以并称,胜在诗有生气真意。谭献赞赏其诗“飘飒俊逸”[9]361,又如《客中述怀》,谭献评云:“奇气宕逸,不仅一结。”[9]363包括前引谭献语“清修脱俗”正与奇逸的诗学审美相一致,却与杜诗风貌相异,综观《合肥三家诗录》对戴家麟的评点,并未有一处称其学杜。
徐子苓、王尚辰侧重唐风无疑,戴家麟《过项王墓》被评“不著议论,唐贤高格”[9]362,结合其他诗作,其诗风更偏向中晚唐一路。因此,认为徐、王、戴三人皆学杜的观点未免轻率,其个性特色也各有当行,之所以三人同列,从诗学角度而言,在奇清、奇劲、奇逸的个性之上,其共性实在于皆为宗唐之故。
就诗作内容而言,袁嘉谷《卧雪诗话》云:“康乾之际,诗家类少言时事,殆鉴高启、袁凯之辙。咸同来,国势日岌,始尟顾忌,而有关史乘之章,风涌云起。”[19]风会不同,诗材亦异,咸同时期由于政局交困,束缚渐松,内外诸事皆入诗笔,以诗纪事补史的诗篇大量出现,反映在“合肥三家”诗篇内容中较为显著。
一是老树新发,以时代演进下进入文人视野的时兴事物丰富诗歌书写内容。自鸦片战争后膏土贩卖肆无忌惮,咸丰帝即位后废弛鸦片禁令,时人王之春即在日记中云:“江南未败时,和、邓诸帅莺歌燕舞,吸食鸦片等事恒有之,面临危险而不自知。”[20]皖中诗人深有痛感,如王尚辰《相思曲》、徐子苓《烟灯行》《阿芙蓉行》《黑银叹》等诗作,如其《黑银叹》诗前序云:“客有转贩阿芙蓉者,积产不赀,群贾居奇,隐其名曰‘黑银’云。余数往来江湖间,见闻所及,次第其语,俟采风者观焉。”[2]706至咸丰初年,清军面对太平军节节败退,长江沿线省份兴兵戒严,诗中即有“沿江火速兵符下,连日黑银占高价”[2]706之语贩贾借此时机囤积鸦片,牟取暴利,此诗更从另一面揭露鸦片之弊,讽刺时事。又如《烟灯行》,于《敦艮吉斋诗存》题作《西原叹》,该诗痛陈鸦片危害,时名颇著,谭献评之“冷水浇背,今之变风”[9]353,金武祥也称此诗“出言沉痛,足以警世”[21]。
二是着重反映咸同战争局势。如徐子苓《会城叹赠汪果》,此首《合肥三家诗录》与《敦艮吉斋诗存》皆载,字词略有不同。汪果,嘉兴人,工书,与徐子苓善。此诗虽为赠酬之作,却可窥彼时史实,先看首二联:“昔者君来时,会城峙皖江。今者君来时,会城寄庐阳。”[9]360清廷避太平军锋锐,将安徽省会迁治庐州,首四联领起全篇,之后四联写与旧友相逢之喜,又八联追忆和平时期皖省繁华景象,至“繁华一朝尽,铁马荆榛荒”[9]360,转入现实,其中记载太平军传教,“沿门呗耶苏”[9]360,忆昔悲今,书写战伐之痛。关爱和认为:“战争以绝对的权威,支配着咸、同之际的文学空间。”[22]通过刻画兵燹场面,表现战争残酷,使得战争书写成为当时诗作的重要题材。
《安徽文化史》《安徽诗歌》等书认为“合肥三家”的创作是“形式主义诗歌”[23],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有充分依据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所以,在对时代准确把握之下,诗作内容能够针砭时弊,以诗纪史,又保持较高的艺术特色,显然会得到接受者的欣赏,这既是诗人本身的造诣所致,也同样不失为时代风向造就的结果。回过头来,“合肥三家”以诗鸣时,以诗存史也是除诗学风尚之外得以受到谭献欣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三、咸同变局与晚清庐州文学板块形成
梁启超认为,清代诗歌自“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24]。实际上,咸同时局动荡,诗界亦气象丕变,一扫乾嘉以来空谈格调之病,安徽诗坛与时世动向相纠葛,逐渐在地理上以巢湖为中点,在区划上以庐州府为核心,联系和州、六安州等地的江淮之间地区,形成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板块。
一个地域文学共同体的成立首先应当是地理范围的明确。江淮之间地理区位优势明显,控淮右而揽大江,巢湖居于中。从历史进程来看,清代庐州一带正是在咸同时期崭露头角,庐州一地据皖之中,“居江淮之间,湖山环汇,最为雄郡”[4]4,《庐州府志》称:
国朝桐城姚京卿鼐之序《庐州府志》……曰:“……若以地势宽平,原隰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未有宜于合肥者也。”姚先生皖人而所见若此,与李梁溪后先同揆,其言尤天下之公言也。咸丰三年粤氛东下,东阿周文忠权安徽巡抚,疏请迁省治于庐州府,嗣是遂为重镇。……论者咸知庐州一府为全省胜败之所关系,中原大局之所维持,非浅尟矣。[4]4-5
可见,自咸丰三年(1853)后,安徽行政中心从安庆府转移到庐州府,军事与政治价值凸显,“嗣是遂为重镇”,使得以庐州为中心的皖中地域自咸同时期受到重视与发展。
行政区划的改变与行政重心的转移,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化重心的改变。清代庐州诗坛,自清初龚鼎孳、李天馥为翘楚之后鲜有声名,至清中晚期时忽为一振,造皖中诗界之变,庐州人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即有论断:“吾邑风雅,盛于咸同。”[7]351庐州诗坛于咸同之时脱颖而出,并非巧合,乃是时代变革使然,“合肥三家”体派应时而生,恰是此变局的鲜明体现。徐、王、戴三家所处之时,安徽南北时局板荡,文人难以置身事外,如徐子苓曾入江忠源、曾国藩幕,与刘铭传等淮军将领多有往来,王尚辰曾随其父王世溥建办庐州团练,与淮军亦有渊源,戴家麟虽然未入戎幕,但“兵燹后,人多非学,麟尽心诱掖,多所成就”[4]113,参与战后重建,同样与时局密切相关。
不惟“合肥三家”,稍早庐州又有“城东七子”(一说为张丙、赵席珍、王垿、卢先骆、吴克俊、蔡邦甸、戴鸿恩,见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一说为李文安、余榜、张丙、赵彦伦、王垿、吴克俊、盛议卿,见李家孚《合肥诗话》),其中不少人员与淮军兴起关系颇深,如蔡邦甸与李鸿章有师生之谊,吴汝纶代李鸿章为蔡邦甸诗集作序称:“蔡篆青先生,吾先人行也,某少长继游从。”[25]又如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嗣随袁端恪公归里办团练,毁家纾难,遂为淮军所自始,文忠昌大其绪,卒佐中兴”[7]351,表明淮军显赫武功助使庐州当地文名被世人所知,所以谭献在《合肥三家诗钞叙》称:
咸丰初,欃枪明于上,萑苻应于下,异军苍头特起。蜀山、肥水数百里间,骧跃于行陈者相望,文武材用,有奇必显。于是乎貂蝉兜鍪,盛于一方,尊于薄海矣。……蓄志隐轸,而制行高清,……徐君懿甫、戴君子瑞、王君谦斋,其斯之谓与?士之表见于世者,出则展其用,处则章其文。……江淮之间固多异人哉![14]189
咸同之际是淮军迅速崛起,庐州地区人群自我认同日趋强化的时代,也是当地地域文化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有清中兴时代,吾乡人才辈出,李文忠、张靖达、刘壮肃其尤著也。”[7]256从文化心理接受上说,当一地某方面声望得到广泛认同后,会产生联动效应,令其他方面的声名也得到关注并随之被提升,使得人们在心理接受上产生一种趋向性。咸同庐州之诗名骤兴与淮军崛起确有相关,清人黄云称:“淮军继起,遂成中兴之功,……(庐州)人士文经武纬,震耀一时。”[3]188类似的现象在同时期湘军与湖南文人群体的互动中也有体现,有学者认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起于嘉道,盛于咸同,……在‘湘军网络’中,个人感召力、同乡、师友、姻亲等关系与上下级的外在强制性规条错综复杂的交织融合,使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以组织化、结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26]所以,淮军崛起是咸同年间“合肥三家”出现的客观因素,也是晚清庐州一地诗名升拔,于皖省诗界开疆拓土的直接缘由。但是需要指出,如果没有卓著诗篇令人感同身受,即便淮军功业如何浩大,诗家的桂冠也不会落在徐、王、戴等人的头上,这也正从地域文学的角度印证了文学史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如果说,对核心文化地区的树立是地域文化认同的首要因素,那么,对文化地区内部其他地域与核心地域关联性的确定,则从整体上证明地域文化乃至地域文学板块成立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六安州于雍正二年(1724)从庐州府分出,俗尚相近,本为一体。而和州西毗庐州,同样与之关联密切。陈廷桂于道光时纂《历阳诗囿》,其中“吴盛藻”条下小传云:“观庄七律才思宏富,句格壮健,位置当在卧子、梅村间。于乡里诗老中,亦不居龚端毅下。”[27]吴盛藻,字观庄,又字采臣,和州人,著《天门集》。小传前半段褒赏其诗成绩,更重要的是后半段,龚鼎孳为庐州府合肥人,吴盛藻为和州人,陈廷桂本人籍贯为和州,直接即以“乡里”称龚、吴二人,由此说明晚清时庐州与和州已被当地邑人视为同一片文化地域,揭示出这一地区内部的文化认同事实。
文学演进与政局变化保持着既密切又疏离的关系,就清代而言,乾隆晚期到嘉道两朝,浙派、桐城诗派等地方诗派不断壮大声势,至咸同之时,在时势变迁下诸州府地域呈现各显面目的地域文学气象,正是时代变局对清末诗学的密切作用所致。桐城久居坛坫盟主,省内诸家沾溉桐城家法是不争的事实,庐州风雅虽“盛于咸同”,但其与桐城派绝难完全割裂开来,如徐子苓被列入《桐城文学渊源考》中,表面上似乎承于桐城一脉。然而,道咸以降,梅曾亮推举苏黄,作为桐城派中兴代表的湘乡主将曾国藩更以山谷为趣,开宗黄之风,前文已论,同时期以“合肥三家”为代表的庐州诗坛却以唐为尚,较为明确地呈现出与同时期桐城诸家相异的诗学旨趣。
国有兴亡,诗派亦有盛衰,在刘大櫆、姚鼐等人的光环消解之后,桐城诗派再无足以总揽天下的宗师人物。姚鼐之后,其弟子开枝散叶难挽颓势,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政局变动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学变局,桐城诗派对各地诗家的影响亦大为削弱。所以,安徽诗学版图内部逐渐分化出新的边界,皖江地区逐渐衰落,以巢湖为地理中心,以庐州为区划核心的地域形成地缘文化上的向心力,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学面貌,“合肥三家”的确立即为咸同时期皖省诗界变化的直接表现。
如前所述,晚清变局对诗学上的直接作用,是导致了诗人对以诗存史、保留记忆的崇尚,这一诗学倾向恰与庐州一带的人文俗尚相合。《庐州府志》载:“其俗勤而无外慕之好,其才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土厚水深,士生其间,刚劲笃实,足以任重。”[4]128《直隶和州志》载:“历阳人性躁劲,风气果决,……儒雅之风尤甚。”[28]《六安州志》载:“州及二邑之俗自昔淳朴,……敦崇气节,不屑营私。”[29]晚清皖省屡遭离乱,文献焚毁,这一地区人民安邦守土的信念尤为深重,不慕浮华、刚劲笃实的民风孕育出其坚韧的文化性格以及存续文统的焦虑心态。自觉挽救文化记忆与文脉传统的信念尤其反映在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成就上。清代皖地“刻书风气繁盛,以刻书优势带动刊印总集”[30],咸同战后,皖中诗老极力搜寻残章页纸,集中辑纂、再版地域诗歌总集,历时多年以至绵延到民国时期,如庐州府有陈诗《庐江诗隽》、刘原道《居鄛诗征》、方澍《濡须诗选》、陈诗《庐州诗苑》,和州有陈廷桂《历阳诗囿》、佚名《龙亢间气集》、郑洤《历阳竹枝词》等。庐州一带正依靠战乱后自觉的收录辑纂行为保存文化记忆,从而延续地方文脉。
“咸同之际,谋奇伟略之士,蹈百死而戡大难,载在国史,声绩懋焉”[31]。初萌于嘉道,骤变于咸同,远播数十年的时代动荡,促使旧秩序加速崩解与新秩序艰难重建。安徽作为时局变动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分与合之中逐步建构出庐州地域文学。所谓分,一是政治中心转移,在战争中兴起的淮军势力,使得庐州地区文学声名在乡土意识与显赫武功的基础上卓然升拔;二是由于军事政治旧秩序瓦解而导致文学领域旧秩序难以维持,庐州地域文学客观上逐渐摆脱桐城一家影响,涌现出如“合肥三家”的地域文学体派,显示出相对独立的文学板块面貌。所谓合,一是以江淮为界,巢湖为地理中心的地缘聚合,庐州一带风土民情与人群聚落的天然相近相亲;二是因之于咸同战乱,当地毅然而集中地保护文脉,留存文化记忆,体现出这一文学板块自觉的向心力。故而,在分与合的双向作用下,庐州文学板块于晚清时期孕育而生。
结语
有清一代,各地诗人群体数不胜数,着眼于晚清庐州一带,除了如“合肥三家”“合肥三怪”“城东七子”外,更有不少文会、诗社,仅合肥一地,如田实发,雍正庚戌进士,“少时与同邑夏栩庄、许柳亭、徐越江、许双溪、王两溟、萧立亭、程卬浦、倪东闾九人结诗社”[10]545;胡楚材,咸丰贡生,“与同邑张延邴、王汝贵、蔡邦甸结率真诗社”[10]587;王晋铨,咸丰诸生,光绪间“与戴曙林明经、宣薇墀孝廉结社邑东,文酒过从,迭为宾主。时三先生年均八十,人称之为‘三老会’”[10]571等等。这些诗人结社行为彰显出江淮地区的深厚文化底蕴。透过地域诗派来观照地方诗坛,之所以拈出“合肥三家”,缘由有三:首先,“合肥三家”在晚清皖地诗界乃至东南一带确有诗名,而并非籍籍无名之人,从而决定其立足文学史的合理性。其次,咸同之时皖省板荡纷纭,而庐州作为危难之际临时省会所在地,其诗坛在社会记忆、身份认同、世情书写上有代表意义,“合肥三家”正能见证剧烈时局,具备当地诗界的同一性。最后,“合肥三家”能够昭示出晚清当地诗歌的发展变化,既与盟主之桐城派有一定承传联系,但其沉郁雄奇,以唐为好的诗学品格又显示出庐州诗坛的自张一军,同时受淮军勃兴影响,展现出其地域诗学的特殊性。事实上,清代数量庞大却身居下层的文人书写时代变动,折射出地域文学体派的诗歌风貌、体格、内容嬗易,更为深广地改变地域文学版图,应得到更多研究视线的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