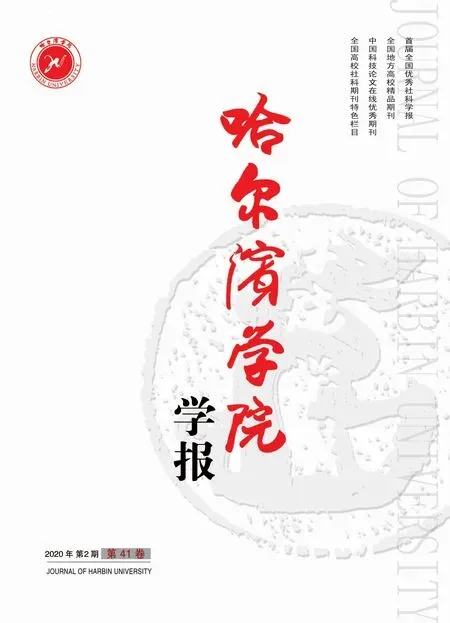从对抗到妥协
——嘉靖年间明廷对辽东兵变的处理
2020-01-17胡业成
胡业成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军队不听指挥甚至发动叛乱时,这种情况视为“兵变”。
据林延清教授统计,明正德四年到崇祯十七年间,仅规模较大的兵变就爆发了六十余次,平均每两年一次。兵变与奴变、民变一道,成为明代中后期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一现象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林延清在《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和历史作用》一文中,将正德四年至崇祯十七年的历次大规模兵变梳理成表,从卫所制下军户负担的研究入手,揭示了军户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以及因国家财政长期败坏而导致边军无粮可食,为此,军士被迫起身反抗,以期获取安身立命之地。[1](P368-372)方弘仁的《明嘉靖朝五次兵变初探》,研究重点是通过历次兵变的过程,探究兵变在制度上的成因;[2]而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一书中兵变与奴变一节,更多关注于明代军户制度下,军官对于军士的压榨和随之产生的反抗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宏观的剖析;[3]邓涛的《明代兵变的转折点——嘉靖朝时局与甘州兵变》,则强调嘉靖即位之初的甘州兵变对于之后兵变的示范作用,以及这场兵变对明朝与吐鲁番关系的影响。[4]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更倾向于兵变的成因及对当时造成的时代影响,而很少直接关注兵变处置过程中朝廷处置方式方法的变化及是否得当,以及这些处置方式对后续兵变的影响。本文由此出发探寻朝廷对于兵变的处置方式的变化及“乱兵”应对朝廷策略的改变。
一、关于辽东镇
明代辽东一般是指辽东都指挥使司所统辖的区域。根据嘉靖年间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魏焕所撰《皇明九边考》载:“幽州即今广宁之地,营州即今辽阳之地。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元城,一千七十里。”[5](P18)由于辽东在明代疆域中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有“京师左臂”之称。
与其接壤的外部势力有三个:“三卫为繁,女直次之,朝鲜无患。”[5](P24)“三卫”是指蒙古兀良哈三卫。它作为草原部族,既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又具有以小博大的战斗精神。因此,即使面对大明这一周边大国,也会积极主动地进行抢掠;其次是女直,即俗称的女真。虽然自永乐起就对其设置官职及有通贡之好,但由于其属于部族统治阶段,仍然会发生对明王朝的劫掠情况。不过与三卫有组织的和明朝对抗相比,其规模与频率都要小很多;最后为朝鲜,明代建国之后其每年通过辽东都司派兵接送使节的固定方式奏请贡献。因为其经营统治国家的方式与明王朝相似,且长期保持着恭顺态度,故被认为不属于外患。由此可见,嘉靖时期辽东边镇的主要对手是位于其北部的兀良哈三卫,同时,还需要负责应对女真部落。
而辽东镇的收支情况,据《皇明九边考》记载,辽东镇“屯粮二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石,各折不等共折银二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五两。补岁用不敷引盐银二万四千一百三十九两”。[5](P24)这个数目在《皇明九边考》中各个边镇钱粮费用中总数排第五位,而在需要中央支持的财政数目当中排名仅次于宁夏镇和大同镇。可见,辽东镇的军士生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的拨款。同时,根据时人陆深从户部移文又得知“近得户部移文,闻称辽东岁用银三十九万四千八百七十余两”。[6]按《皇明九边考》刊行于嘉靖二十一年,成书年代相对较早,而《俨山外集》则相对较晚。故而我们也可以看出辽东边镇每年耗费朝廷的银饷呈上升趋势。
二、辽东兵变概述
自正德年间以来,明代进入兵变高发期,而进入嘉靖朝,更是“多事之秋”,从世宗登基时爆发的甘州兵变,到嘉靖十三年的第三次大同兵变,总共爆发了八次较大规模的兵变。[1](P368-372)这些兵变虽然都被明廷镇压,但所谓“法不责众”,政府不可能将所有参与兵变的军士全部处罚。同时,朝廷为了尽快平息兵变,采用了诛杀首恶、胁从不问的处理方式。[2]这种处理方式给其他正在遭受压迫的军士以遐想的空间。之前兵变带来的效仿效应鼓励辽东镇的军士,而新任巡抚都御史吕经的举措,使辽东镇的军士不得不进行这种尝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嘉靖年间辽东镇日常运转方面出现了问题。辽东镇原额屯粮七十万石,但由于卫所制度本身的缺陷和长时间的腐化堕落,在正德嘉靖之间锐减到三十八万三千八百余石。[7]嘉靖十三年,当原云南布政使吕经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时,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清查活动,希望解决这一问题或缓解这种情况,以缓解辽东的军饷供给。然而,吕经的整顿措施不是针对贪婪的军官,而是普通的军士。关于军官的侵吞、克扣军饷,早在宣德时代就屡见于史料。嘉靖元年九月,原任大同副总兵张輗贪污马草价银受到下狱追赃的处理,[8](P576)但仅仅一年之后就被重新启用为京营大营的坐营管事官。[9](P937)可见,当时军队的积弊主要是军官的贪婪,而对于这种行为,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一般仅是追赃,而当事官员在事件平息后还能得到重新任用。
正是因为朝廷对军官贪赃的姑息,让吕经不愿通过整治军官这种得罪人又不讨好的方式来缓解辽东镇的弊端,只能将缓解财政压力放在了普通军士身上。按照惯例,辽东各个卫所每军一人用三个余丁供应,每一匹马给予牧田五十亩。而吕经上任后将其改为:“每军给余丁一,余悉编入徭册征银,解广宁库。追牧马田还官,招佃纳租。”[10](P3772)余丁的由三改一,在增加纳税人口的同时,加大了军士的生活压力。而将牧马田追夺还官,则大大减少了军士们的收入。这些措施让本已不堪重负的边军军士生活更加拮据。因此,辽东镇的军士对吕经抱有很大的怨气。只不过,此时的军士们并没有采取反抗措施,还都只是敢怒不敢言。
嘉靖十四年三月,“是月,(吕)经巡视辽阳,檄将吏并城筑围墙。及台将吏希经意,督并严急,诸军遂大噪”。[10](P3772)吕经整顿边防的初心是好的,但他并没有吸取当年大同兵变的教训。更为致命的是,吕经在增加军士工作量的同时,拖欠军士的月粮,如《殊域周咨录》所记:“栽柳种田,不得休息,月粮失期。”[11]本来修城筑墙就已经让军士苦不堪言,而已然被克扣生计的军士又遭遇了月粮拖欠,这更是将辽阳的军士逼上了绝路。
辽阳位于今辽宁省中部,沈阳南部,是原辽东都指挥使司驻地,当地驻有山东布政分司、行太仆寺、东路副总兵府等机构。据《辽东志》记载,嘉靖八年,巡抚改驻辽阳,原辽东都司西侧被改为巡抚行台。[12]除了总兵驻守的广宁之外,明政府在整个辽东的职能机构都在辽阳,是明政府统治辽东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嘉靖十四年三月末,忍无可忍的军士们涌入巡抚院中,罢工并要求“免马田租”。[10](P3772)吕经指挥刘尚德呵斥士兵退下无果时,下令左右殴打前来请愿的军士。被压迫已久的军士们感到别无他路,只有反抗才是唯一的办法。据时人沈越所撰写的《皇明嘉隆两朝闻见记》载:“军聚众为乱,欲执尚德杀之,尚德走免,乃围经署,鼓噪不已。”[13]可见,当时有可能由于兵变军士无法控制情绪,而击杀长官的情况发生,只是被刘尚德逃脱了而已。不过在找到吕经之后军士们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而是将他幽禁起来。可见,当时兵变的军士中有头脑清醒且具有一定威信的人,并在现场指挥控制。接下来的关闭城门及“出故游击高大恩于狱,拥以为主”的情况,[14]都说明了当时辽东镇的军士们受到长久的压迫,并且也掌握了一定的斗争艺术,懂得推举一个有一定官职的人出来增加兵变集团的凝聚力。
朝廷在得知消息命令当地巡按御史与总兵官一同勘察,然后在辽东副总兵李鉴的控制下顺利安抚住兵变军士。辽东兵变的第一个阶段——辽阳兵变被朝廷顺利控制。
若无其他变故,辽东兵变可能仅仅会在辽阳一地短暂的爆发,随后结束。但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嘉靖十四年四月丙午,吕经接到回京命令后,在广宁城收拾行装。
广宁即今辽宁省北镇市,位于沈阳西部,是辽西走廊的咽喉地段,在明代是保卫京师的重要屏障,是辽东总兵驻地,也是吕经返京的必经之路,镇守太监亦驻扎于此。
由于广宁没有吸取辽阳的教训,“经拟扣诸军月草价为饰装具,悍卒于蛮儿等狃辽阳前事,鼓众倡乱”。[15](P3784)
据《国朝典汇》中所记的辽东兵变事中找到在广宁激起兵变的祸首,“其中军袁璘拟扣诸军月草价为饰装。其悍卒于蛮儿等因鼓众倡乱”。[14]同时在《殊域周咨录》中也有“袁璘传称经要办毡扛”[11]的说法。无论是《国朝典汇》还是《殊域周咨录》,其作者都为嘉靖末期或万历时期参与政治的进士,并且都曾在中央政府任职过,可以阅读到大量当时的往来文书。因此,此事件应为吕经的中军袁璘为了乘机营私,于是下令克扣草价。
虽然这类克扣士兵待遇的现象自明代中期以后屡见不鲜,但就在辽阳城刚发生兵变且前巡抚吕经权威扫地时发生,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以于蛮儿为首的广宁士卒效仿辽阳兵变,再一次将吕经抓住,羞辱了一番:“非尔汰我余丁徵猺银耶,非尔夺我牧马田耶,而复能虐使我筑墙种树终岁勤苦不遑耕织耶”。[15](P3784)从这里可以看出于蛮儿的指责几乎包括了吕经上任以来的所有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影响了军士的正常生活。由于辽阳兵变的激励,加上朝廷之前的妥协式处理,广宁的军士也用同样的方式奋起反抗。
不同于辽阳兵变的是,广宁兵变士兵没有大规模的烧毁破坏行动。根据当时的记载,监军王纯、总兵刘准等人还能为吕经向军士求情。兵变领导人于蛮儿带头向管粮郎中李钦昊讨要粮赏,[11]而不是直接开门抢劫。从这些行为可以看出,广宁兵变军士并没有控制全城,也没有完全破坏城内秩序。并且从兵变第二天起,他们就开始筹划后路。他们胁迫镇守太监王纯和都督刘淮各自上疏:“言璘阿附经激变,数经十一罪,请逮京问理。而乞遣故总兵郤永、侍郎周述赴辽抚镇”。[14]广宁兵变与辽阳兵变已然有了不同。辽阳兵变更多的是当地军士对吕经过多压榨行为不满,从而导致的临时性群体事件,事后立刻被平息了。
嘉靖十四年五月癸酉,锦衣卫捉拿吕经的官校到达广宁,却被兵变士兵怀疑为假,以为是来帮吕经脱身的。于是将这些锦衣卫关进广宁监狱,直到“总镇等官谕以祸福乃出官校”。[16](P3785)兵变军士对奉旨捉拿吕经的锦衣卫非但不加以配合,反而将其关押,如此举措对朝廷权威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三、朝廷在两次兵变中的处理过程
要考察朝廷对于兵变的处理方式变化,则需要了解在兵变的各个阶段,朝野上下对于兵变处理的争议。通过这些争议,以及明廷最终采取了哪种方案,则可以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政局提供思路。
辽阳兵变发生后,时任左都御史的王廷相在奏疏《为激变地方事》中提出:“众军拥赴都察院喊呌亏枉、不过欲巡抚控求免困苦而已。使当时为吕经者善于应变,镇静不动,不致越墙而走,则亦军民越诉之常耳。”[18]他认为,辽阳兵变并非军士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巡抚吕经在处理“军民越诉”时没有采取合理的解决措施,最终导致前来陈情的军士失去控制而发生的。他认为辽阳兵变与之前的大同兵变不同,完全是巡抚事发时处置失误导致的。所以,不需要派遣大军前去征讨,只需要“索其为首之人。彼亦自然听服”。[18]
对此事件反应激烈的兵科都给事中曾忭,也认为不需要派大军进剿。虽然他认为辽阳兵变与大同兵变性质同样恶劣,尤其是“边镇之兵一纪四叛”,对其他边军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但他还以为“今日之事异于大同亦远矣”。[19]不过他所考虑的不同之处在于,辽阳相比大同而言没有坚城利甲,且没有外虏可以引以为援,而非兵变军士的行为区别。因此,不需要朝廷通过派遣军队的方式解决问题,只需要“悉付巡按御史从公体勘,长虑周谋”[19]即可。这些思维都表明了朝廷对于辽阳发生兵变没有如临大敌的感觉,认为此事交由当地官员处理即可,不需要来自朝廷的援助。
不同于大同兵变时朝堂上群情激奋,认为“大同之乱由边卒之骄。而边卒之骄由朝廷恩威之废”,[20](P1097)主张用兵进剿。这其中也包括在大礼议当中首先站出来支持嘉靖帝的张璁。但相较于大同兵变时的强硬派,辽阳兵变后朝堂上的强硬派少了许多。
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当时的财政状况来窥视一二。嘉靖十三年二月,户部官员上疏称:“以边方多事,自十二年十一月以来不满三月费太仓银不下一百二十万,即太仓有余,犹宜节省况渐竭乎。”[21](P3563)同年十二月,户部的官员再次上疏哭穷,称“顷者诏免今年夏秋税粮之半,业已颁布各省。以银计凡六百八十一万九千两有奇,此皆岁正供经费不可缺者。乞通行天下,亡论山海诸赋及寺观田园仓库赎锾徭役等银悉行会计,以补原额。上不许,如岁用不足令该部通融处。”[22](P3712)前一则材料中所说的自(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三个月内费银不下一百二十万,正是调兵平定第三次大同兵变时调动客兵的费用,足见出动大军征讨兵变部队花费实在巨大,已不是太仓银所能承受的了。后一则材料则是因朝廷减免了夏秋税粮的一半,导致了朝廷日常经费的不足。由于嘉靖帝不许户部增加额外收入,而要求户部尽量通融处理。由此可知,当时明廷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很难承受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花费。
鉴于明廷紧张的财政状况,强硬派官员对兵变态度再怎么严厉,也无法提出派遣大军征伐的建议。当兵部尚书张瓒接到消息后还没有从大同兵变的恶劣影响中走出来,为了防止激化矛盾直接建议:“以激变坐经谪戍边”。[13](P10)
朝廷得知消息当天即“令巡按御史会同总兵官从实查勘”,[10](P3773)辽东副总兵李鉴奉命进入辽阳城维持秩序。朝廷在照常性的要求兵变军士“各归营伍以保身家”的同时,废除了吕经的各项改革措施,并下令将刘尚德革职听勘,以及将巡抚吕经“取回别用”,[10](P3773)可以看出朝廷为了防止出现更大的变乱,在兵变时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这些让步也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李鉴入城之际,被兵变军士们推举出来的临时领导主动入狱,表明兵变军士没有进一步与朝廷做斗争的意图,他们只是出于自身生存原因才反抗吕经的。巡按御史曾铣进城后,进一步控制了局面,使得发生在辽东的第一次兵变得到顺利解决。
虽然之前兵科都给事中曾忭上疏要求严惩兵变军士并为吕经开脱,认为一旦严惩吕经将会有损朝廷的威望。但嘉靖帝对于兵变能快速平息感到十分快慰,因此他并不介意牺牲吕经来平息兵变军士的愤怒之情。于是,他在给曾忭为吕经开脱的奏疏上只是十分冷淡地回复了四个字“兵部知道”。[13](P10)同时,朝廷作出以安抚为主的决策,将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韩邦奇升为右副都御史,代替吕经巡抚辽东。
而之后发生的广宁兵变,辽东镇的军士已经不满足于朝廷空洞的许诺了。他们要求通过干涉朝廷用人情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类似于中唐时期各个藩镇的牙兵一旦对于节度使不满,便犯上作乱驱逐节度使,自己推举一人然后等待朝廷的追认。这类效仿行为让朝廷感到忧心忡忡,生怕边镇军士纷纷效仿。朝廷有部分官员持这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礼部侍郎黄宗明,由于朝廷已下旨改变吕经的改革措施,他便认为“前者辽阳之变固生于有激,今重复苦役皆已改正矣,嚣然而起复谁激之。此于法不宜复宽贷”。由于他并未出任过边地职务,因此对于边军的凄惨生活没有直观的了解,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认为这是当地军士无理取闹,伺机邀赏。因而黄宗明以鹰派的观点向嘉靖皇帝建议“令新巡抚韩邦奇督兵压境扬威声,罪取其首恶,且邦奇恩威素着。若假以便宜权使之悉心经画其事必办”。[15](P3785)这也是朝廷在辽东兵变发生后首次出现以军事实力威胁兵变士兵就范的声音。
对比第一次辽阳兵变时朝廷舆论反响的不同可以发现,辽阳兵变发生时,哪怕是反应最为激烈、急忙为吕经开脱的兵科都给事中曾忭也没有动用武力的想法,只是试图通过将罪责归结于首恶的兵变士兵来减轻吕经的罪责。不过,在辽阳兵变以朝廷妥协而告终之后,广宁又起,这就让朝廷中部分鹰派人士产生了怀疑,认为是朝廷在辽阳兵变中给出的退让妥协太多了,导致边军但凡受到一点委屈就绑架,乃至于折辱上官,所以一定要通过军队的镇压才能让这些军士头脑清醒起来。
嘉靖帝对于时局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于嘉靖三年大同兵变时,嘉靖帝迫于张璁等支持大礼议的朝臣的压力而做出了出兵决议。此时的嘉靖皇帝已经稳居帝位十四年,对于朝政的掌控已经不同于当初。也许是出于对财政压力的警惕,又或者是担心一旦大动干戈会造成严重的边防体系破坏的后果,嘉靖帝最终选择了听从镇守太监王纯的请求,“遣官校逮经,而璘及各官有罪者下巡按御史逮问,止韩邦奇毋行”。[15](P3785)嘉靖帝没有对兵变士兵的要求通盘答应,并让本已准备上任的韩邦奇毋行。可见,嘉靖帝对于兵变集团还是存在妥协心理的。他们害怕一旦矛盾激化,会带动其他区域共同反抗,给明帝国带来更大的压力。但如果让嘉靖帝按照兵变军士的要求任命总兵郤永、侍郎周述前往辽东,显然是不可能的。就算嘉靖帝愿意答应这样的条件,朝臣们激烈的反对也不可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明代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制度自信的政权,不愿回到晚唐那个藩镇割据的时代,不可能同意彻底按照兵变军士的要求来行事。为此兵科都给事中曾忭还专门上了所谓的《正名罪慎举用以杜奸萌疏》来为嘉靖皇帝开脱。奏疏的开头先是引用了嘉靖帝关于广宁兵变处理的圣旨。接下来便自顾自的为嘉靖帝解释了起来:“陛下所以罢邦奇不遣者,盖察邦奇非辑宁才。故欲易之。此固陛下知人善用之意,非因军士之请而欲望以叙更也。”[23]将嘉靖帝这一举措解释为皇帝圣明,察觉到韩邦奇不是戡乱人才,而非嘉靖帝对兵变军士做出的妥协。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王廷相也在《为激变地方事》一疏提到“唐人姑息,终成藩镇之强,职此故也”,[24]提醒嘉靖帝注意对兵变军士的退让幅度。
事实上,以明代的边镇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唐末的藩镇。唐末藩镇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掌握了财政自主权。而根据之前所引魏焕撰写的《皇明九边考》中可知,嘉靖时期,明代九边长期处于依靠朝廷的盐引银等财政支援才能维持日常开支的状态。因此,嘉靖皇帝不担心一时姑息可能导致的边镇的自立,因为从财政角度来考察,只要中央政府中断对边镇的财政支援,边镇便有自行崩溃的可能。并且参与兵变的都为底层普通军士,没有诸如参将、总兵之类的中高级军官的参与,无法形成一个长时间具有凝聚力的集团。故而嘉靖帝并不介意对广宁兵变军士也作出退让,只求能息事宁人即可。
在随后的广宁兵变军士将锦衣卫官校抓捕下狱之事时,朝廷面对这种明目张胆挑战朝廷的行为,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上疏称:“夫都御史者天子之重臣也,庸隶下卒敢执缚困辱之,是无朝廷也。近闻差去官校亦被囚,系迹其狂悖视大同尤甚。臣意本兵大臣宜为国讨贼,乃专事姑息,致叛卒益骄朝廷之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但林希元却不知道,之前有大臣谈论过派出大军武力镇压,但真正做出对兵变军士妥协决定的是嘉靖帝本人。所以,林希元的上疏让嘉靖帝十分气恼,遂下令锦衣卫查实是否出现兵变军士扣押锦衣卫官校的情况,锦衣卫指挥王佐出于担心自己受到惩罚,因此而选择欺骗嘉靖帝:“覆言原差官校未尝被系,然官校实被系。第佐等讳言之耳。”因此,嘉靖帝认为林希元欺骗君上,再加之其对妥协政策的批评,便将其贬为广东钦州知州。[25](P3804)
以此来看,嘉靖帝是铁了心的要通过温和手段解决发生在辽东镇的多次变乱了。当然,实践证明这一手段也是卓有成效的。
四、余论
事后,曾铣在给嘉靖皇帝所上的《勘定三城疏》中自豪的宣称:“今者仰赖处置得宜,开谕明切。故首恶就擒,边境之危殆者已安,人心之动摇者咸定。”俨然充满了不动一兵一卒平定叛乱的自豪感,而称赞嘉靖皇帝“独断辽东之事,而不疑于群言,真御乱之上计也”。[26]则是一边拍了皇帝的马屁,一边也突出了自己这个现场执行者临危不惧为皇帝排忧解难。在处置兵变参与者及矛盾激化者的问题上,朝廷贯彻了只诛首恶,胁从不问的方针。一场波澜不断的边镇兵变的最后处置结果仅是将赵劓儿和于蛮儿等八人处死,激发兵变的刘尚德和袁璘发配戍边,其他中级军官大多革职闲住,这可以说是一个较为柔和的处理结果。
旁观者清,参看当时被充军到辽东,素有直言敢谏之风的御史程启充的记叙:“边兵构患,始宁夏,而甘肃,而大同。当其时,非无抚按也。特以处置失宜,玩兵激寇,损师累月,费数十万,杀伤数万。俾朝廷旰食可慨也。唯辽变起,三城五路震撼。先是,御史请勿问悉解,及其决策不假兵革,群凶就系。弭兵裕民,万全无害,虽古管、葛岂其过之。”[26]
在这篇材料中,他将曾铣对于辽东兵变的处理大加赞赏,认为与管仲和诸葛亮相差无几。原因便在于在面对当地最高军政长官被士兵羞辱及辽阳等处失去控制的情况下,没有出面支持朝中强硬派官员的用兵严惩建议。而是坚定地说服朝廷通过“抚”来解决问题。这就比之前的动辄大军进剿显得更加务实,但也是明王朝缺乏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实现对全国军事实力进行完全控制的体现。
从兵变军士的视角来讨论,则能看出自从辽东兵变起,兵变的士兵也开始掌握斗争的艺术了。也许是被之前朝廷大军围困大同叛军的雷厉风行所震慑。无论是发生在辽阳还是广宁的兵变,无论兵变军士对吕经有多大的怨念,都没有发生擅杀主官的事情,只是通过羞辱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怒。兵变从之前打破脸皮的鱼死网破,变成了生活不下去的士兵们讨价还价的本钱。尤其是在广宁兵变中,虽然兵变士兵很快控制了全城,但他们只是限制了监军太监王纯等人的自由,并没有全部下狱,而是利用这些没有被完全控制的官员为自己的待遇讨价还价。在御史随后的劝说下也是将吕经交给朝廷,而非握在手中作为奇货。这些都可以看出,兵变的参与者侧重于对抗的策略性而非单纯的蛮干。
因此,朝廷与广大军士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奇妙的默契。那便是只要参与兵变的军士没有发生劫杀主官之类的恶性事件,那么朝廷便不会出动军队来进行围剿。如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发生的甘州兵变,以及嘉靖三年七月和嘉靖十二年十月的第二和第三次大同兵变,发生了军士劫杀主官之事,情节恶劣,所以在发生伊始便引起朝廷的重视。尤其是发生在大同的兵变,一经发生朝廷即刻调兵遣将准备平叛,这充分显示了朝廷对于劫杀主官的零容忍态度。反之,考察辽东兵变之后嘉靖朝的历次兵变可以发现,除嘉靖三十九年南京振武营兵变逼死督储侍郎黄懋官之外,嘉靖朝的历次兵变再没有出现对上官痛下杀手的情况了。同时,朝廷也并没有再派遣大军征讨,以图平定兵变,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官员与兵变士兵进行沟通,通过安抚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军队作为国家镇压内部反抗、抵抗外敌入侵的重要工具,一旦工具不好用了,对于朝廷的统治会带来很大的威胁。军队发生叛变无论是武力平叛还是采用招抚手段,都会对朝廷的权威以及自身的力量造成一定的损失。因为当发生兵变之日,军队既是镇压者同时也是被镇压者,这对参与平叛的士兵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嘉靖登基以来,就面临着南倭北虏的局面。各方面用兵需求较大。原有的卫所制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对内和对外的军事需求。因此,只有采取募兵的形式。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及募兵规模的逐渐扩大,国家不得不拿出巨额的白银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并且不断克扣原有卫所制军士的生存待遇来缓解财政压力。于是就形成了矛盾。募兵的不断增加需要更多的白银,则朝廷希望在卫所军士手中克扣。而卫所军士因为生存难以保障,进而发动兵变求得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兵变发生之后朝廷则需要武力征讨或花钱招抚来寻求稳定。这就是嘉靖朝以来,朝廷军费支出攀升的重要原因。在两者不断的反复中,明王朝的财政收入节节攀升,最终达到入不敷出的境地,并走向了灭亡。
之所以需要花费高额的白银来支付军饷,原因有二:一是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自嘉靖朝以来明王朝边患不断,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维系统治;二是为了保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力。如果朝廷能够为招募的军队提供足额的军饷,那么在作战时就能使之如臂,军队便是“国家之军”。但当朝廷无法满足军队对于白银的需求时,轻则军队扰民,重则发动兵变要挟国家,乃至成为地方私人军阀的私军。因此,自嘉靖朝以来高额的军费是不得已为之。而其后形成的不劫杀主官便不进兵征讨的惯例也是不得已为之。但姑息也会带来相应的后果,正如在振武营兵变发生之后当时的兵部侍郎李遂发出一句感叹“兵自此益骄矣”。[27](P5421)就在这军队不断地挑战朝廷的底线,朝廷不断妥协退让的过程中,军队也就失去了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相反它本身成为了一只吸血虫,盘踞在明朝政府身上,不断地吸取养分,直到明政府的灭亡也没有改变其花费昂贵而不堪大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