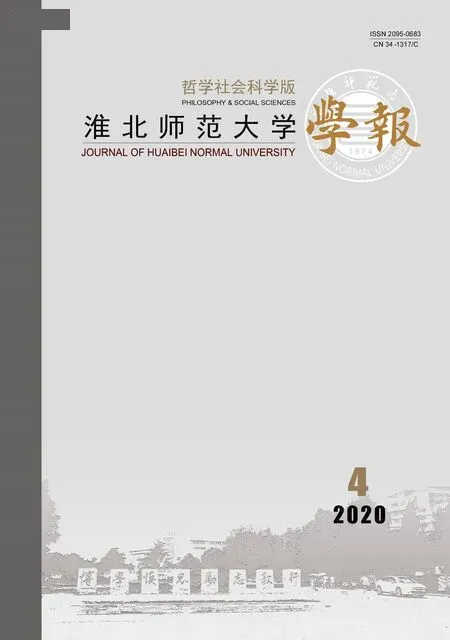阿英佚文辑补三篇
2020-01-17杨志敏
杨志敏,于 洁
(1.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475001;2.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000)
阿英,本名钱德富,1928 年改名为“钱杏邨”,1957 年后,常用“阿英”笔名。阿英生于1900 年,逝世于1977 年,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新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中野美代子称其为“真正是一位跟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活下来的人”[1]。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阿英在上海求学,他深受震撼,随后回到家乡芜湖致力于新文化的宣传。1926年,阿英经周范文、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往当时的革命文化阵地——上海,此后的15年,阿英一直活跃在文艺战线最前端。1927 年,阿英作为“太阳社”的中坚与战将,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时期,任执委会常委,为左翼革命文学植立基石;“孤岛”时期,更是在逆境中前行,坚守阵地,组织并主持上海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在这一时期,阿英高举“力的文艺”与“文艺大众化”大旗,为新生、稚嫩的无产阶级文学呐喊助威,同时确立文艺服务于革命斗争的理念,以战士的姿态从事文学活动。
阿英不仅以战士的姿态在文艺界奋斗,同时还是文艺界的多面手,“评论、诗歌、杂文、散文、小说、戏剧、电影、文艺史、俗文学研究等都有所建树”[2],著述百余种。2003年《阿英全集》出版,该书12卷共500余万字。“收入了现在所能搜集到的阿英先生的全部著作,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创作,以及中外文学批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话、史论、日记和书信。”[3]2006 年《阿英全集附卷》出版,分为“补遗”与“附录”两部分,增收《阿英全集》未录的佚文、札记、书信等计66篇。全集求全,但遗珠散玉,在所难免。笔者在翻阅报刊时,发现了三篇阿英佚文,兹述如下。
一
第一篇是《观中心剧团首次公演》,刊载于1938 年6 月30 日《新阵地》旬刊第12 期,署名阿英。在《新阵地》第11期,阿英以鹰隼的笔名发表了《周作人诗记》,该篇收入《全集》。《观中心剧团首次公演》原文如下:
观中心剧团首次公演
阿英
中心剧团的这次在金华作处女演出,是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的!我相信由于这次演出,对今后的演剧水准一定可以提高不少。虽然他们是处女演出,虽然他们自己很谦卑的说很幼稚,而从他们演技的炉火纯青,后台的秩序井然,就可知道他们是一个有组织,有训练的剧团,在他们不断的虚心努力下,将有极光明的前途;而全省的剧运领导权,也将必然地落在他们身上。
我们每个爱好戏剧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对中心剧团抱着热烈的希望的,所以我们希望中心剧团的诸君特别要认识自己的责任,不畏艰苦的担负起来,首次公演的成功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谨希望以后继续不断的有所成就。并且希望不单在舞台剧有深刻的造诣,而在街头街尾,庙台戏,方言剧……以至土戏改良各方面,都有所贡献。还有,就是不要老停在金华,而能够流动到各地去,使浙江的戏剧水准普遍的提高,战时剧运普遍的展开。
最后,我们用“我们的故乡”中老林对那青年战士仲文说的一句话来勉励中心剧团诸君,和全省的戏剧工作者:“好好儿干,别叫大家失望啊!”
《新阵地》于1938年3月5日在浙江金华创刊,主要反映浙江文化界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建设与各种文化活动,宗旨是力求激励民族信心,争取抗战胜利,在江浙一带颇有影响力。该篇刊于12期,结合《新阵地》第11期的剧坛消息,“中心剧团”即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中心剧团,于1938年6 月16 日在金华长乐戏院进行了首次公演,公演剧目为《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故乡》是一部洪深、章泯等集体创作的抗日三幕剧,该剧自1936年问世后,先后在上海、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多次上演。
在这篇文章中,阿英给予《我们的故乡》首次公演极高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期盼——希望剧人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提高戏剧水准,进行戏剧改良,扩大影响力。这与阿英文章一贯坚持艺术的的现实性、针对性相契合。阿英强调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他明确地说过:“我们必然的要承认文学的时代的使命以及阶级的使命,必然的要承认文艺所担负的时代的任务。”[4]这个任务就是增强文学的感染力,最大程度地启迪鼓舞民众,使百姓增强抗敌信心。“阿英始终是一名党的文化战士,或者可以说,他是以文化人的身份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的。”[5]文化战士的自觉性使阿英在创作中始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与“力的文艺”的创作理念,醉心于喷薄怒发的力之美,他在文集《力的文艺》中反复声明:“我是一个力的崇拜者,力的讴歌者。”[6]要创作“烈风暴雨般的粗暴伟大,力量感很足,感人很深的文学……跃动的,有新生命的文学。”[7]
在戏剧创作上,他同样秉持这种观念,偏重戏剧的内容与主题,强调没有主题就是没有中心,“剧本不但要有主题,主题还要含有积极性”[8]。而佚文中提倡的方言剧、庙台戏等土戏的改良,正是在保留土戏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的基础上,进行主题和内容上的改良,“在旧形式上注入新的营养”[9]139,使其成为力量感足、有新生命的戏剧。在“现代戏剧”盛行的时代,阿英逆流而上,对土戏予以极高的关注与评价,并开出土戏改良的“药方”,体现了他思想的创见性。而他之所以提倡土戏改良,固然存在当时“剧本荒”的原因;但更关键在于,土戏改良能最大程度地完成动员民众、鼓舞人心的任务,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使土戏重新拥有生命活力,同时扩大戏剧的影响力。这种将斗争意识灌注其中的“感情与思想社会化的手段”正体现了阿英“力的文艺”戏剧观念与美学追求。
二
第二篇佚文是《人日读“天国春秋”》,刊载于1944年2月20日出版的中华剧艺社旅内公演纪念特刊——《剧华》,该刊为纪念中华剧艺社在四川内江公演郭沫若《孔雀胆》一剧而出版,刊载了少量剧评,其中便有阿英这一篇,现抄录如下:
人日读“天国春秋”
阿英
孔雀胆闭幕后接着就是“天国春秋”的上演,在正月初七的雨夜里,剧场中又多了我这位义务场记。
本事和台本用不着我来赘述,至于简又文等所整理的太平天国新史料,现在更是无从说起,记得何子贞“金陵杂述”有两首诗,一写:乾嘉风雅萃随园,书画琳琅紫雪轩;遗塚荒凉无可觅,苍山何处托吟魂!一写:贞白烧丹有旧邱,张郎觞咏剧风流;三间柏木厅犹在,可惜藏书转角楼!(自注云,陶菴主人张徵斋藏书甚富,今余柏木厅址。)这些吟篇,都是为了太平军焚毁江南文物典籍所发的哀吟。
一点也不错,傅善祥说天国的君臣都是一批“老粗”,可不是吗?杨秀清虽为广东花县的富绅,他出了无数的金钱,接济太平军,取得了南京,功绩可就不小啦,然而他结果是少读几句儒书,弄到悲惨的结局,自然,傅善祥是早知道有这一天的,怎奈忠厚自负的东王何?杨秀清的饰者项堃,从他装饰到台词动作都深深体贴得出存心忠厚,头脑单纯的英雄人物,其成功虽不在“光绪皇帝”之上,总之是无瑕可指的,韦昌辉这位代表太平天国的总崩溃的人物,(张逸生饰)奸顽,刻毒,阴险,从他的言谈,举动,作为皆可算表现尽致,刻画入微,饰傅善祥的金淑之,文雅风流,大有鹤立鸡群之概,令秀清眷恋难忘,原属人情中事,洪宣娇这位女英杰,在服装方面我觉得稍嫌过于紧找,然而泼辣,豪迈,醋劲各味可算是发挥无遗矣,其余各演员都能洽到好处,在大体上说这是一部好戏,有完整的结构,有洁练的对话,有紧张的场面,但据以群在“文学创作”里的批评说:“这似乎不是一部好的历史剧,原为它离开历史的事实太远,以杨,洪,傅的恋爱斗争做了该剧的主题,于‘剧场的’效果固然很好,但太平天国的精神却为之湮没,以致剧本原有的优点,也暗然减色。”据传闻编者杨翰笙先生所以这样强调的去描写“吃醋”及韦昌辉等派,是有特别用意的,不管怎样,这次中艺的角色配搭得相当齐整,在演出上说是获得最高度的成功。
这个剧本在另一种社会意义上说也具有相当的教育因素,就是说太平军取得江南的时候,竟视一切旧籍为妖书,一见即毁,据“蛮氛汇编”所记。沿江各郡藏书家,如汉阳叶云素,扬州阮文达,陆敦夫,程穆堂各家,皆牙签万轴,不啻天禄琳琅,而太平军所过,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衬马蹄,擦遗夫,斯文不幸,毒于秦火矣!呜呼,以一批“老粗”而信洋教,结果弄成内溃一发不可收拾,可悲也已。又“随园轶事”内载有:“袁枚恩假归娶图”,按即袁子方以翰林归娶,倩人绘图以记其事者,图上题跋,不下数百人,皆雍乾的名流耆硕手笔,尤为稀世之珍,太平军陷金陵时,图遂被毁,作者以画人立场,更不敢赞同洪杨此种自掘坟墓之妄举,后来弄到互相火拼而亡,虽曰天命,其实政策之错误为致败之大端,故孙总理以实现三民主义恢复固有道德,发扬固有文化为推倒满清建立民国之总原则,此不但可为吾国万世之一定目标,亦可纠正太平军之失策矣。
“中艺”是中华剧艺社的简称,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著名剧团,1941 年5 月在重庆创办。1943 年6 月,由于国民党的苛刻政策,尤其是对“中艺”的政治迫害,以及“中艺”自身长期入不敷出的窘境,“中艺”做出退出重庆的战略决定。1944 年1 月,“中艺”开始转战川西南,25 日,抵达内江,当夜即开始演出,演出了包括《天国春秋》在内等八部优秀剧目[10]。《剧华》纪念特刊由《内江日报》发行,出版于1944年2月20日,而“人日”指正月初七,翻阅年历,1944年的正月初七即公历1944年1月31日。文中提到的以群对《天国春秋》的评价,刊载于1943 年4 月1 日《文学创作》第1 卷第6期,那么此篇文章最早为读者所见也应当是在1943 年4 月以后。因此,这篇佚文应是作于1944年1 月31 日,出版于1944 年2 月20 日。文中还提到“至于简又文整理的太平天国史料”,阿英在1941 年于《万象》上发表的《太平天国史料钩沉——校本<独秀峰题壁诗>》一文附记中,也曾提到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由此,可以确定这篇文章为阿英佚文。
阿英在佚文中提到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该剧发表于“皖南事变”爆发后,以“杨韦事变”为中心,描写了太平天国由于内部分裂导致的革命失败,讽喻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制造冲突的现实,以借古喻今的手段将历史与现实打通,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激发民族热情,鼓舞民族志气。这一时期的文坛,历史剧创作在质与量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借古喻今,成为这一阶段话剧创作及演出的主要手段,“借历史的题材,对现实有所启发”[11]。这不仅符合阿英的“以历史还历史”的历史剧创作原则[12],同时与阿英一贯坚持的文学要表现时代,配合革命运动的开展,成为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相吻合。本篇佚文中也不乏阿英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痕迹,文末阿英借“画人立场”,在观看演出之余,指出党派相争,无疑自掘坟墓之举,“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自己的内部要是不互相团结互相谅解,顾到共同的利益,在共同的愿望底下竭其真诚的向前,前途——实在是可怕得很!”[13]
该篇佚文,在见证了“中艺”对《天国春秋》的精彩演出之余,还反映了战时大后方的剧运形势。通过分析这篇佚文的内容,阿英的人生态度、爱好旨趣跃然纸上。
三
第三篇佚文是《连环图画琐谈》,刊载于1936年《书报展望》第1 卷第4 期,署名阿英。全文如下:
连环图画琐谈
阿英
只要曾经在上海生活过一个短时期的人,或者在自己家里有着小孩子的人,大概谁都能了解连环图画在妇人孺子,以及在广大的市民间势力影响的雄大。“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门版书摊在上海之多,颇有这样的景象,而每个摊上所陈列的书,至少也有一两百种之多,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种类出版。
然而我们的教育家,文学家,对于这样严重的现象,是并没有予以怎样的注意的。特殊是小学里的学生,以此作为课外的家庭读物的,尤其普遍得很。可是小学教师们,似乎并不感到这些读物给予儿童的危害。在文坛上,虽也曾一度注意及此,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也就寂然无闻。
这一类充塞门版书摊的大众读物,主要的不外是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电影故事,才子佳人小说的改编。也有少数的历史演义。虽说有一部分已突出拥护封建势力的范围,大部分却依然是旧势力的助长者。
自从“王先生”诞生以后,较进步的连环图画是时有发现。如胡考的“西施”,张光宇的“费宫人”,以至在儿童刊物上所发表的,都可说是较进步的好现象。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满足。原因很简单,其一,是这一类的连环图画,究竟还不能跑到门版书摊上去,以之替代原有的那些封建性的拙劣作品。其二,这些作品依旧不能很好的捉住时代的脉搏,从作品上完成他们应该担负起的任务。“消极的讽刺”,现有的较进步的连环图画,所能做到的,不过如此而已。
我们不能以此自满。我们希望教育家,作家,画家们,能把眼光向这一方面移转去了解这一类读物在民间的影响,内容所含的毒素,究竟可怕到怎样的程度。从这理解上,来认识大众与儿童的需要,集合多数人,来从事新的作品的创制,逐渐的赶掉这些应该放在历史馆,垃圾堆的废物。真正为文化努力的新的出版家们,也不应该忽略此点。
特别是在这非常时期,连环图画的作者应该了解自己的任务,多多的从事于有国防性的故事的写述,唤起大众的积极的反帝情绪,了解自己民族历来所受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九一八”,“一·二八”,“一二一六”几个大的事变的经过,共同起来从事于保护国土完整的运动,反对出卖中国的汉奸,准汉奸,要求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我们携起手来,自然,反封建的运动,一样的是要继续。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不应该忽略的救国工作之一。
我想,如果我们的连环图画作家,能在这些要点上努力,产生崭新有力的新作品,不会不受到民众广大的欢迎的,他们现在所以仍旧不能不在现有的一些连环图画里兜圈子,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种种。一般的作品,如科学常识,生活常识等等,我想大众也是同样的需要,在制作上也同样的不能忽略。
阿英曾在《大众文艺与文艺大众化》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大众化问题的实质,就是具体的集中在制作有大众性的作品,和经过组织的活动把这些作品贯注于劳动者和人民层两点。”[14]连环图画作为一种普及性极强的艺术,其大众性不言而喻,因此,阿英曾多次撰文呼吁连环图画的创作。如在《抗战期间的文学》提出:“连环图画、墙头壁报之类的作品,无论是在前线在后方,是一样的迫切需要。”[15]在《再论抗战的通俗文学》更直言,“他们(民众)能充分的接受一个故事,一本连环图画所暗示给他们的教育,但他们难以接受有同样意义的论文或专著。”[9]138《杂谈抗战画片》中也有类似论述。阿英认为连环图画如果运用得当,完成作品应当担负的任务,同样可以成为大众文艺的有力作品,成为推动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手段,在这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支配下,阿英对于连环图画的创作与发展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1957年,阿英酝酿已久的《中国连环图画史话》发表,该文不仅从形式、内容、题材等方面梳理了连环图画的历史与演变过程,同时又为连环图画的由来、形式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考证。中野美代子称赞:“它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占有很独特的地位,对它加上更多的资料再给以理论上的展望,不仅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还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一定会打开完全新的局面。”[1]
佚文中提到的“王先生”,出自叶浅予从1928—1938 年十年间在《上海漫画》《图画晨报》《滑稽画报》《时代》连载的连环图画《王先生》中的主人公,而“王先生”在阿英《中国连环图画史话》中同样出现过,“这一类的连环图画,当时最为读者喜爱的,有叶浅予的《王先生》”[16]。这部连环图画之所以广受读者喜爱,不仅仅在于作者画功优秀,更关键是相较当时市面上其他的连环图画,《王先生》紧扣时代脉搏,反映当时政治与社会生活状况,借古装童话故事讽喻现实,生动而极富意趣,同时期胡考的《西施》、张光宇的《费宫人》同样采用这种艺术手法。这种浅易的形式与精深的意蕴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更容易为大众接受喜爱,因此,阿英呼吁作家秉持启蒙者立场,发力创作以鼓舞民众。指出对广大小的市民阶层和工农大众而言,作品的通俗性和时代性尤为重要,“对于抗战胜利的前途,关系是更为重大的”[15]103。这篇佚文,表明了阿英的文艺思想在连环图画方面的体现,同时也能补充阿英对于连环图画的研究。
结语
上述三篇佚文,不仅见证了阿英坚守文化前线、开展进步文艺运动的社会活动与历史轨迹,同时还从某一侧面体现着其坚定的政治立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念,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