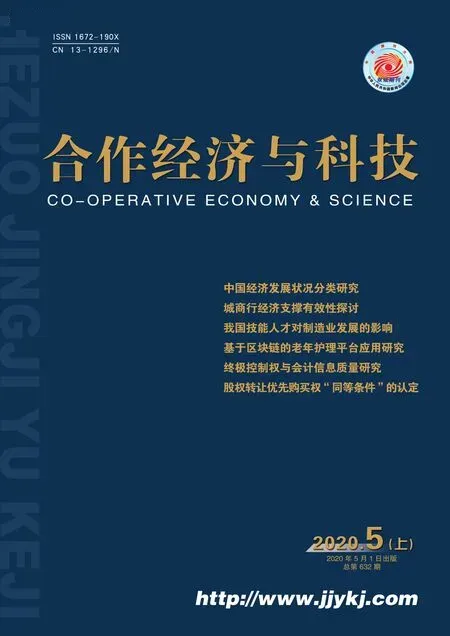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
2020-01-17刘正之
□文/刘正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提要] 人工智能生成物已进入大众视野,但该生成物是否属于“作品”尚未得到学界和法律的统一认定,现阶段难以将其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结合社会与市场的需求,人工智能生成物应当受到法律的规范和保护。可以考虑设立新类型的邻接权,在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规制的同时,维护现行著作权体系的稳定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量的大数据、深度学习算法以及云平台等强大的计算能力让机器得到了进化。在创作领域,人工智能从辅助者过渡到创作参与者甚至独立创作者。它们可以根据人类的简单指令或模板,半自动或自动生成与指令相关而区别于以往内容的文本,代替人类的一部分劳动和“思考”。2015年,腾讯自动化机器人Dreamwriter发表了一篇新闻稿件,会写稿的机器人在我国首次亮相。2017年,微软“小冰”出版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首部由机器人100%创作”的诗歌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冲击着人类作品的定义和市场,法律法规应警惕地给予回应。
一、人工智能创作物纳入现行《著作权法》的障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作品是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具有独创性的可复制的智力成果。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构成作品,在于其内容是否具备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
从《著作权法》的主体来看,根据传统的著作权理念,独创性的源泉是人类。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在其《著作权法》第二条中明确要求了“个人”的主体身份。欧美法系的美国在“猴子自拍案”中通过否认猴子的人格主体,从而否定其著作权,实质上是排除非自然人的创作。我国国家版权局明确表示,作品“必须是人类意志的产物”。人工智能并非“血肉之躯”,难以获得《著作权法》的主体资格。
如果不讨论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天然的鸿沟,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备“独创性”,从而使其纳入《著作权法》有了可能?王迁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本身并不理解“创作”目的和其“创作”产物之间的关系,其创作本质属于“执行既定流程和方法”,而非“创造”,遑论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标准仍然是基于“人类”的精神生产,通过人工智能的非人类身份而否定其创造性。吴汉东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只要独立生成内容,就构成受《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至于其用途、价值和社会评价则在所不问。熊琦教授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表现形式上进行分析,认为既然无法根据表象来分辨人工智能生成物和人类作品,则应当认定前者在客观上满足最低创造性的要求,认定其为作品。总体来说,学界对“创造性”的标准尚无定论,难以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定性。
二、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必要性
与学界胶着的讨论相对比,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根据乌镇智库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融资规模达157.54亿美元,占亚洲人工智能企业融资的93.09%,占全球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数额的46.94%。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布局最多的国家,数量略微领先美国和日本,三国占全球专利公开数量的74%。
从积极必要性角度看,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有助于繁荣文化市场,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迎合国家战略需要。创作时效短、内容有创作价值的机器生成物为市场带来了新的竞争力,从而促进人类作品向高质量发展。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立法保护,也能趁机对其进行梳理和规制,引导其健康、蓬勃发展。
从消极必要性角度来看,未来人工智能自主性会更高,创作能力会更加突出,对现有《著作权法》的冲击将愈发猛烈。如果其生成物不受保护,那么大量没有版权的机器生成物将充斥市场,成为新类型的“无主作品”和“孤儿作品”,这不利于著作权市场的稳定性。从作品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既然存在无版权的作品,他就没有必要选择有版权、需付费的作品,那么除了依赖作者名声威望或本身具备高度独创性的作品外,大部分人类作品的版权将失去市场,急速贬值。人类作品的传播性被大幅削弱,人类自主创作失去了经济动因,这明显和著作权促进人类创作激情、推动文化事业繁荣的立法初衷相违背。
此外,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受保护,对其进行使用就没有了限制;如果有人对有创造性价值的机器生成物进行二次利用,那么会产生如下问题:首先,人类作品和机器生成物会混杂在一起,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内容可能通过人的行为而受到保护,本来不作为甚至不存在的著作权人可能享有作者权利,这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大量负担;其次,模糊的界限可能使得投资人有所忧虑,为避免风险势必拘束其投资欲望,这对所涉行业的发展不利;最后,许多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表现形式上与人类创作作品无本质区别,在机器本身缄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知情者举报,二次利用的行为很难被发现。综上,著作权法有必要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法律保护。
三、我国学术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模式
(一)降低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归于法人作品。大陆法系国家要求作品具有“作者个性的烙印”,这导致人工智能生成物即便在表现形式上符合作品的要件,也会因其创作者并非人类而被拒之于被保护的范围之外。如果降低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视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即可用著作权进行保护。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可以用法人作品制度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法人等组织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与其利用人类来创作相仿,因此可以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视为代表设计者或者训练者意志的创作行为。将人工智能的作品归为法人作品的行列,将著作权归属于法人等组织,既避免了创设新的法律法规,也避免了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上的作者。但是,学术界对独创性的标准本来就不明晰,又要以何标准进行降低呢?降低后的独创性标准又应如何规制?而且,降低独创性标准可能使著作权保护对象的范围扩大,这会引起新的问题。人工智能本身不具有意志,又如何“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采用法人作品保护模式,其实忽略自然人的主体,如果人工智能的所有权人是个人,则无法适用法人作品要求,因此这种保护模式在实践中依然面临很多困难。
(二)扩张邻接权的权利种类,为人工智能生成物设立邻接权。邻接权最初是为保护那些“未能体现创作者个性或创造性程度不够的劳动成果”。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独创性”标准上遇到的阻碍和上述劳动成果类似,这为人工智能的法律保护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能。
通过扩张邻接权的种类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保护,其优势有两点:一是这可以维护现行著作权体系的稳定性。设立邻接权不会对现有作品要件进行冲击,同时还避免了著作权因过多或不当赋予人工智能及其生成物带来的法律纠纷,这间接地排解了人工智能编程人员、投资者和人工智能生成物使用者的忧虑。二是它还避免了人工智能与自然人的身份纠葛。邻接权不仅避开了著作权法中独创性对自然人限制,还杜绝了人工智能被赋予人格权的可能。邻接权一般不包括人格权,而对财产权的内容也会因邻接权保护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但是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归于法人作品,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享有署名权等人格权利,主体和客体的权利混淆不清。
当然,以邻接权作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模式也存在问题。根据传统观点,邻接权主要是保护传播者在作品传播中的投入,如不能合理解释这与人工智能生成物之间的联系可能会产生混乱。
(三)承认人工智能主体地位,单独立法对其生成物进行保护。欧盟数据库指令所建立的特殊权保护模式单独设立新的法律法规,以便更加全面地对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以及其生成物的权利归属、保护内容、保护期限等进行详尽的规制,而避免其与现行著作权法可能产生的矛盾冲突。但是,单独立法的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很高,从初步确定单独立法到最终发布还需要很长的过程,可能无法及时解决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
综上观之,第三种保护模式虽然可以对人工智能的生成物进行详尽全面的保护,但与人工智能的现实发展状况不匹配;第一种虽然在程序设立者和人工智能之间找到了平衡,但是在实践中很难执行。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邻接权入手。
四、人工智能生成物具体保护路径
邻接权也称“相关权”,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被称为“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根据WIPO在《知识产权手册》的解释,邻接权包括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和广播组织者权,这也是狭义邻接权的概念。
随着时代变迁,现代邻接权制度的种类已大大丰富,很多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对邻接权进行了拓展。比如意大利将独创性不高的摄影作品、戏剧的布景作品、个人书信和肖像等归入了邻接权之中;法国将计算机软件列入邻接权的保护范围;德国《著作权法》规定的邻接权多达十一种;我国《著作权法》将出版者权加入到邻接权保护范围。由此可见,邻接权本身并不必然被拘束于狭义邻接权的概念之中,它的本质是弥补因独创性标准过高无法受到法律保护的生成物,这为人工智能生成物被纳入邻接权的保护范围提供了基础。
那么,如何具体地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法律保护?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邻接权的权利主体。人工智能生成物从其产生到最终传播到市场主要涉及三方: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传播者。人工智能一直作为权利的客体出现在大众视野。《德国民法总论》认为,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得转换,那么作为权利客体的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成为权利主体,而只能是法定支配权的对象”。虽然现行著作权法中将法人视为主体,但法人的本质也是对自然人意志的集中体现,依然没有跨越自然人的边界。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邻接权的主体,那么法律主体为自然人的界限将会被打破。无限制地扩大主体的内容,将会最终导致权利主体失去意义;另一方面,赋予人工智能以权利主体的地位,还会衍生出其相应的权利义务问题。因此,应将邻接权的权利主体归于后两种情况。
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制造了人工智能这一客观存在,赋予其数据和算法,为人工智能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将开发者视为权利主体的观点有国外立法依据,比如英国版权法就是将计算机生成作品进行必要程序者视为该作品的作者。但是,根据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开发者已经在计算机程序及软件开发等方面享有著作权,如果将邻接权的权益也赋予开发者,则会出现双重激励的情况。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传播者是“对生成物之传播进行必要工作安排者”,其应当在推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传播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物仍需要人类对其进行最后把关,尤以新闻稿件为例,这就需要传播者对内容进行处理,最终将其公之于众。即便是依赖性较小的美术、音乐等作品,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传播者的劳动。将其视为邻接权的权利主体,符合邻接权对促进“作品”传播的理念,也不会产生权利重叠的情况。
(二)邻接权的内容。邻接权的权利内容,即邻接权主体享有的具体权利。一般认为邻接权的内容不包括人身权,这与人工智能的非人类性不谋而合。有人认为可以将署名权赋予人工智能,以便让人工智能和其生成物之间产生纽带,这利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市场传播效率。但是,赋予人工智能署名权可能使人工智能和自然人的权利义务再次产生混淆,对邻接权的权利内容也做出了改变,在这种可能的后果面前,署名权是否仍然足够便利,以使得人工智能享有该人身权?
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回到邻接权对财产权的规定,并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益限制在财产权之中。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至(十七)项规定了十三项关于财产权的内容。然而在“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中,财产权的内容被大大缩减。比如在第四十二条中,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只享有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而非全部财产权。
在实践中,除去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制度设计中的障碍,还要考虑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和权利限制。如果不加区分地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全部权利,很可能导致反公地悲剧。人工智能相对于人类而言,具有信息捕捉快、数据储备多、生产效率高的优势,未来可能出现机器生成物数量在某领域远超人类作品数量的情形。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过剩的法律保护,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成本和使用成本激增,反而会阻碍其流通和传播,这和保护初衷不符。
人工智能在音乐、美术、视频等方面虽然可以创作出和人类作品表现形式别无二致的内容,但是在文字类创作上的创造性和价值还有待提高,比如新闻稿件。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财产权也应被适当缩减,可以考虑只赋予其复制权、发行权和网络传播权。这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主要传播途径和法律纠纷可能产生的领域,只对这部分进行规制,一方面可以有效保障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邻接权,另一方面也避免过多权益导致的保护过剩问题。
(三)邻接权的期限。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对狭义邻接权的三种权利类型的保护期限为50年,而对图书、期刊的版权设计权的保护期为10年(第36条)。根据《保护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第十四条,对上述权利的最低保护期限是20年。德国的《著作权法》对邻接权保护期限的规定更加丰富,比如对数据库的保护期为15年,对狭义邻接权的保护期限为50年,对特定版本的保护期限为25年。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邻接权的保护期限设定不同,即便是同一国家,对不同邻接权类型的保护期限也有所区别。一般来说,越接近著作权对作品的要求,其保护期限越长。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生产效率高,作品更迭快,也很难具备经典作品的内容价值高度,如果赋予过高的保护期限,可能对市场不利。因此,可以参考德国对数据库的规制,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期限设定为从人工智能生成物发表之日起15年;对于创作完成后15年未发表的,法律不再对其进行保护。
五、结语
如今,我国正在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整,迎面撞上人工智能的热潮,应考虑在布局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同时,借机在著作权法中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回应。从法教义学的角度,人工智能难以寻求现行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对著作权法的挑战被扩大到作品的源头和创作过程,这对著作权法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表现形式与人类作品没有区别,而在生产效率上远高于人类作品,这对文化市场造成了冲击。因此,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法律保护势在必行。在考察国内外现有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分析国内学术界现有的对保护模式的讨论后,邻接权制度的优势和合理性凸显出来,或可作为突破口。可以预想,未来的人工智能会更加精妙发达,其生成物也将更具创造力和价值,法律法规要跟随实际情况作出深入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