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和姥姥
——伊甸的父亲汪静之和母亲符竹因的故事
2020-01-17
公公和姥姥,是我对外公和外婆的称呼,叫了一辈子,很顺口,很亲切。别人会觉得不对,有点儿南辕北辙了啊!为什么不是“姥爷姥姥”?因为他们是南方人啊。为什么不是“外公外婆”?因为我是北京人啊,因为同学都叫姥姥啊。我从小任性,姥姥随和便依了我,而公公坚持也就由了他。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家人,随性。
一
公公汪静之1902年出生,祖籍徽州绩溪八都余村人。姥姥符竹因1903年出生,杭州临平人。他们几乎是世纪的同龄人,他们的生命历程亦是几乎与时代同步。
20世纪20年代初,公公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姥姥在浙江女子师范读书,他们相恋在杭州西子湖畔。他们的故事应该从这里开始,而与他们的故事有关的另一些故事还是要从更早说起。
公公静之自出生起,就被母亲和母亲的结拜姊妹指腹为婚,指腹的未婚妻姓曹,名秋艳。秋艳12岁夭折,而两人娃娃时是拜过宗堂入了族谱的,两家的过从和情义亦深重,故静之一辈子都称秋艳的父母为“岳父母”。曹家还有一个女孩名珮声,是秋艳的小姑姑,三人年龄相差在一岁之间,一起玩儿着长大,青梅竹马,非常亲密。15岁时,静之为珮声写了他的第一首爱情诗,旧体的。珮声说:“我是小姑姑,我们之间没有可能。”此后终生,两人是最亲密的朋友。晚年珮声还乡时留给静之保管的诗文,亦尊从遗嘱在她逝后销毁,虽然在守信和不舍之间公公徘徊了很久。
公公静之6岁入私塾,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接着读《孝经》《四书》《千家诗》《幼学琼林》《唐诗三百》《诗经》《古文观止》《左传》……写的也是旧诗文。
13岁时,公公被父母安排去茶庄和纸墨店学徒,走的是传统徽商发展的路。耐不住独子万般发誓“不喜从商”,父母也就疼爱地从了,送他进学校去读书。我家保留着母亲抗战时的“逃难日记”,那些日记本都是公公教她自己制作的。如何用手裁纸,如何把一沓软纸掇齐,如何用棉纸做捻,如何装订……这些手艺都是公公当年在纸墨店学徒时学到的,还都用上了。
姥姥竹因的父亲较早接受了维新思想,家里的女孩是要上学读书的,而且上的是公学。竹因进的是浙江女子师范附小,进而浙江女师。她在学校里功课门门优等,人漂亮,字也写得漂亮。竹因的诗歌、小说选集《未画完的女像》1931年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
竹因和珮声在附小和女师都是同班,很要好,是珮声撮合成全了静之和竹因。竹因原名叫竹英,是公公改的,取意“水竹姻缘”(水指汪)。静之也是公公自己起的,他原名立安,读书后自号静之,取意“静者能安”。恋爱时,公公曾在一天内给竹因投出十封爱情的信,而在女师一个女生一天收到同一人寄来的十封信,动静很是大了一点儿,引起校方关注,让竹因非常难堪,差点儿被开除。
1924年4月4日“湖畔诗社”成立纪念日那天,静之与竹因在武汉结婚,从此两情依依,他们共同注释爱国诗选和文选,共同度过艰辛的岁月,相知相守了一生。
公公朋友很多,姥姥相反不爱交际。公公说:“除了湖畔诗社的几个朋友,竹因不同人来往。郁达夫和郭沫若都是到我家里来才见到的。胡适想见见让他侄儿相思致死的美人,她也没见。”胡适的侄儿胡思永是胡适三哥和珮声三姐的儿子,同静之从小也是一道的,他本来有肺病,喜欢竹因又不得,心绪郁闷总不利于病情,而所谓相思致死也是朋友间说说而已的吧?
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公公在屯溪的徽州茶务学校读书。相比家乡的大山里,屯溪是个城市,可以看到杂志报刊,他接触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期刊。胡适在北大提倡文学革命运动,首创白话诗文。北大的《新青年》《新潮》刊载了很多新诗歌,那时的青年们都在用一种革命精神学写白话诗文。公公爱诗,17岁已经写了很多旧体诗文。受到新潮思想影响,他烧掉所有的旧体诗,开始学着用白话写新诗,写出几首,就寄给倡导新文学的同乡胡适,求指导。胡适也是绩溪八都人,他很高兴地给小同乡回信:“你能够写新诗我就很高兴,说明我提倡新诗这一点是很成功了。”胡适喜欢静之的诗“天真烂漫的孩子气”,静之自然是受到鼓励,便常写信寄诗给先生看。
公公讲过,一次给胡适先生写信,提到父母代订婚约,自己不认识也不愿意,如何是好。先生回信说:“父母代订的婚姻,切勿遵命服从。必须自己选择,自由恋爱。婚姻问题,宁可牺牲老辈,不可牺牲少年!”静之感念先生身受母亲代定婚姻之苦,“由痛苦之心情结晶成两句珍宝般的良言:宁可牺牲老辈,不可牺牲少年!”在先生鼓励之下,他坚持拒绝了父母代定的婚姻。一年多后,收到父母发来电报“已退婚”。这件事每次提到都会让我感动,宗法与诚孝实在是那辈人心中万般纠结而难以逾越的坎儿,尽管他们都在追求着理想的“自由”,尽管他们都十分勇敢地冲破了许多座“大山”。胡适先生牺牲的是自身“少年”,他的这个“牺牲”未尝不是一种挣扎着的痛。
胡适先生为静之的《蕙的风》写了序言,为静之的《作家的条件》题了封面,还曾三次援助过静之的经济困境。先生与静之,是师,是友,是缘分。
1920年,公公离开家乡徽州,顺新安江到达杭州,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一师是当时南方地区最早响应北京大学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学校。公公喜欢写诗,同学们都叫他“诗人”,认识潘漠华、魏金枝、柔石、冯雪峰都是因为写新诗。四个好朋友组织了“晨光文学社”,请老师叶圣陶、朱自清做顾问,出版《晨光》文学周刊。这是浙江省的第一个新文学团体。

胡适为汪静之《作家的条件》题写的封面
公公那时年轻自信无顾忌,还不到20岁就开始在《新潮》《新青年》《诗》《小说月报》《晨报》等杂志发表新诗。《诗》杂志是刘延陵、叶圣陶和朱自清先生创办的中国新文坛第一部诗期刊。
静之的爱情新诗表达着恋爱的情感,单纯、直白、自然、清新,受到青年的欢迎。应修人看到他的诗后写信与他成为了知心好友。1922年春,修人从上海到杭州,与静之、漠华、雪峰同游西湖,发起“湖畔诗社”,并为四人的诗歌合集《湖畔》题名。“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湖畔诗人是新文学的实践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风华正茂的他们,满怀着对生活、对诗歌的无限热忱,用白话写诗,写爱情诗,自由地放声歌唱,诗风清新淳朴,在当时的诗坛独树一帜,他们的友谊亦几十年忠诚不变。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团体。
“老师叶绍钧讲:你写了这么多的诗,可以出版了。”静之把诗选了一些,寄给专出新文学作品的亚东图书馆。《蕙的风》1922年初版,至1931年第六版,发行了两万余册,销量仅次于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朱自清、胡适之、刘延陵写序,周作人为封面题名,竹因题写了扉页“放情地唱呵”,令涛设计了封面“弹竖琴的爱神”。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爱情新诗集。
爱情诗集《蕙的风》的白话新诗无拘束地放情歌唱,直抒爱情的欣喜和苦闷,纯清质朴,风靡文坛,亦掀起了巨大的反响,进入文学史。不仅是冲破了旧诗词格律而采用白话,推动了新诗尤其是爱情诗的创作,也不仅是采用爱情题材,催生了一代新人,《蕙的风》所引起的是一场“文艺与道德”的论战,对反封建斗争起到紧密的配合作用,它的意义超出对它的评价。今日再读《蕙的风》,仍感阵阵清风拂面。
朱自清说,《蕙的风》“向旧社会道德投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这颗炸弹不是激进的政治宣言,不是文学革命的呐喊,而是一本娇美清新的小诗集。这颗炸弹引起的反响,有顽固派攻击爱情诗败坏道德教化,也有革命家认为爱情诗有害。鲁迅、周作人等前辈及新文学青年们纷纷投入笔战,撰文驳斥针对爱情诗和作者汪静之的诋毁,肯定诗集《蕙的风》的价值。关于《蕙的风》的争论反映着20年代初进步知识分子维护个性解放的坚决态度,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几年后沈从文回顾说:“《蕙的风》的诗歌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文坛”,“所能引起的骚扰,由青年人看来,较之陈独秀在政治上的论文还大”。
公公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说:“家人爱我,老师爱我,同学爱我,朋友爱我,从来没有人骂过我。《蕙的风》出版,是我第一次被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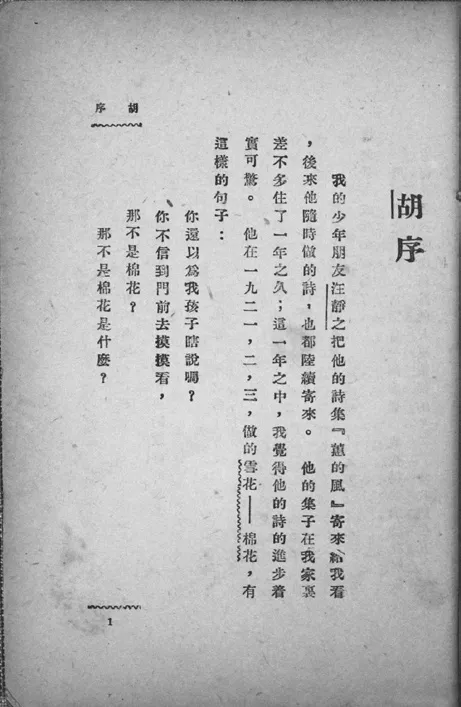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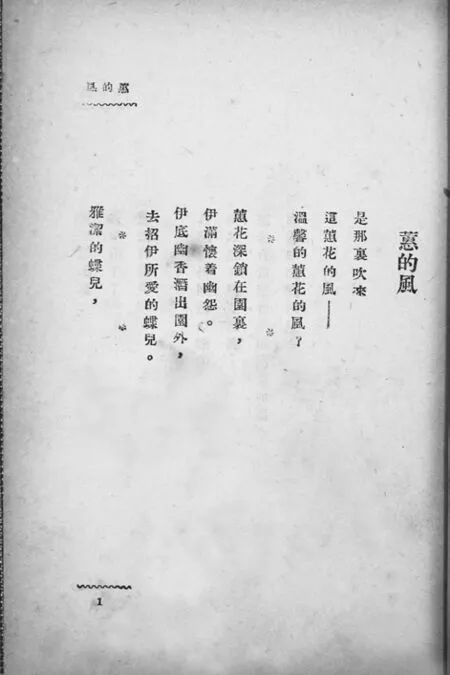
《蕙的风》1922年版
公公也尊鲁迅先生为师。初时,公公给鲁迅写信附新诗,请求指教,“寄回的诗稿上有不少诗改过二三字”。先生评说:“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几次信中的话,有鼓励,有指出缺点,有谈新诗问题。1925年暑假,公公在“老虎尾巴”第一次见到了鲁迅:“他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有补丁,很肮脏,头发也不梳,好像脸也没有洗,全身都不整洁。第一眼看见,好像一个穷秀才。”那一次鲁迅先生对公公说:“青年人有写恋爱诗的权利。”
1922年8月,三个文学团体在上海组织《女神》出版一周年座谈会,有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叶圣陶、郑振铎,汪静之和应修人代表湖畔诗社参加。众人一见如故,会后郁达夫和郭沫若邀静之和修人回泰东书局他们的住处聊了通宵。《蕙的风》8月1日刚出版,郭沫若说他已看过。
《蕙的风》带给公公很多朋友,他们因诗结缘,相识相知,成为终生的挚友。也是这些朋友们的帮携和真诚给了公公更多生存的机会和勇气。1923年,静之父母的生意被伙计卷款逃匿而遭失败,不再能供他读书。很多朋友都帮助接济,应修人寄钱,胡适寄钱,胡浩川帮助,还有上海“胡开文”老板也接济帮助。后来公公工作很多年慢慢地帮助家里还清了负债。
三
北伐期间,郭沫若在武汉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他介绍公公任宣传科编辑、《革命军报》特刊编辑,兼国民政府劳工部《劳工月刊》编辑。1927年初,北伐形势大好,长女在武昌出生,公公乐观地给她取名“伊甸”,寓意“乐园”。那时应修人也从黄埔军校调到劳工部。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身份是公开的,几个月后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开始屠杀共产党。应修人离开,公公也搭乘外商轮船到上海转回杭州。
诗人很难靠写诗来谋生的。公公大半生以教书为业,他曾辗转芜湖、武昌、保定、上海、南京、安庆、汕头、杭州、青岛、浦东各地,在十几所中学和大学教过书,抗战时期在黄埔军校任国文教官。姥姥也在中学校任教职。公公总说:“我一生很忙,忙着教书糊口,忙得交朋友的时间也没有,更无余暇写作。”“不教书时,生命还是消磨于柴米油盐之中。除诗以外,著书都为稻粱谋,为了养家活口,救等米下锅之急。”他似乎是歉疚的,因为很多人在问“汪静之怎么不写诗了?”而这其中的难愁只属于他自己。
1933年,公公和卢叔桓、章铁民等在青岛市立中学教书一年。校园在半山,原是德国军营。他们在校园内的住所,北依太平山,前瞰大海,被朋友们誉为“山海楼”,据说“故居”小楼现在还在。叔桓和铁民都因《蕙的风》与公公结缘,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叔桓认识公公有点儿传奇:“有一天我在邮局寄信,他看见我拿的信封上写着汪静之寄,就对我说读过我的诗,很喜欢,我们就这样交了朋友。”后来叔桓和竹因的妹妹天恩结婚了,成了母亲的小姨夫。铁民是徽州人,北大学生,喜欢公公的诗就通信成了朋友。他俩后来都在浦东中学和暨南大学任教,两家都在浦东六里桥杨家花园租房住。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公公“忧虑亡国灭种之祸”,就和姥姥开始着手选编爱国诗文,希望能起到教育青年起来保卫国家的作用。从1931年到1936年,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觅爱国诗文,编选和注释。日本侵略形势越来越紧,边教书边作注太慢,“怕是要亡国在先了”,公公决定辞职不再教书,全力投入注释工作,得到了胡适和王云五的支持。胡适说:“中国自古无爱国诗文选本,你第一个做了自古以来没有人想到的好事,对教育青年爱国很有用,是必不可少的爱国教材。”王云五则当即预付了一千元。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爱国诗选》四册注毕,交付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爱国文选》四册1939年至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公公在抗战期间讲课的教材主要就是这两部书。《爱国诗选》和《爱国文选》的出版在当时是创举。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枪炮声中,公公带着全家从浦东的家出走,几千册书和衣物全部丢弃,只带着尚未注毕的《爱国文选》手稿。两天后,慌乱疲惫的他们来到杭州竹因哥哥士丰家。忽然想起《爱国文选》书稿忘在人力车上了,大人们急得不知所措,7岁的儿子神奇地说出了那部人力车的车牌号码,书稿失而复得,众人认为不可思议,公公感叹儿子是“救命菩萨”!逃难途中公公和姥姥没有停止注释工作,书稿陆续交付出版。
战争迫使公公和姥姥带着一家人,先到了杭州姥姥的家,又去了徽州山里公公的家,再去武汉找朋友求职,又由朋友介绍奔了黄埔,上海、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重庆,跨越九省,历时九年。离乡背井,沦落天涯,他们和亲朋好友相携相助。
1938年在武汉,住在世交曹家的“师竹友梅馆”,那是公公少时学过徒的纸墨店,也是公公指腹“亲家”的家,公公说过,早年他们在武汉结婚时“岳父”还摆了酒呢。
那段时间郁达夫一家也在武汉,住得不远,郁夫人是姥姥在女师的同学,两家人碰到一处就会常聚,孩子们也都是好玩伴。母亲记得,在青岛时郁达夫曾画了郁飞拉屎的背影逗他们小孩子玩笑,都是开心的记忆,也有故事。
日军占领安庆,再上来就是九江、汉口,政府向四川转移。1938年7月,全家乘火车撤离武汉。章铁民介绍公公到黄埔军校任教,郭沫若也写了信带去。到达广州时正逢“七七”国难周年,这天全城餐馆只有素食。当年中国百姓反侵略的心志,仍能令今天的我们心动。
德庆、柳州、宜山、定番、独山、贵阳、重庆,“一直走在日本人的前面”。贵州独山是抗战时期黔桂铁路的终点车站,是重要的物资运输中转中心和重要的军事基地,盟军在那里扩建了机场。独山也是大后方难民最集中的地点之一。飞机轰炸的威胁没有停息过,公公一家在这里四年多,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跑飞机”。
公公任军校国文教官兼校图书馆主任,还参与编辑校刊。独山军校本部离城五里,各大队都分散开几里路,去各大队上课要走很多路。每个大队都有二百人以上,讲课需要大声叫喊才能听得到。这些聆听他授课的黄埔学生,即将奔赴战场,为祖国献出青春和生命,公公的心中永远都为他们骄傲!
逃难路上,舟车船辇,徒步艰辛,7岁小儿4岁小女,或背或抱或一副担子两头各挑着一个,10岁的伊甸都是自己走下来的。最小的女儿在避难贵州时出生。颠沛流离中没有学上的时候,公公和姥姥就是老师,姐姐哥哥也是弟弟妹妹的老师,孩子们记日记,读书报,写作文,去教堂练习英语。逃难的生活十分简朴,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做自己补,做玩具也都是孩子们快乐的游戏。那样艰难的环境中,公公和姥姥坚强地支撑着他们的家,爱护和教育着四个子女,令他们长大以后各有所成。
独山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货币严重贬值,军校教官都要另辟生路。公公在中学兼课,还和姥姥一起在城门外开了几亩地种菜,自给之余,就晾干菜,还做“盐酸”来卖。母亲说“盐酸”是独山特有的一种泡菜,极好吃,但自己也都舍不得吃呢。后来公公还自己酿酒卖,以维持全家生计。
1944年12月初“黔南事变”,独山成为日军在华攻占的最后一城。古城被大火焚毁,军需通讯交通设备被摧毁,深河大桥也为阻断日军被炸毁,独山百姓牺牲惨重。国民政府1945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文书中说:“要以去年为危险最重而受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犯到贵州独山,这一年实在是第二期抗战中最堪悲痛的一页。”深河桥成为日军败亡的转机点,有说法称“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足见独山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意义。
关于深河桥有个感人的故事:独山撤退时,美军伊文思上尉负责摧毁机场设施、仓库和独山深河桥,他没有按计划炸毁深河桥后坐飞机离开。因为太多的难民北撤贵阳需要这座桥,美军上尉先炸毁机场,然后守在深河桥北,看着难民源源不断地通过,直等到日军冲上了桥,最后关头才下令爆破,而后他和难民们一起徒步去往贵阳。他掩护和救助了更多普通的中国人,我的公公也在其中。
独山撤离时,姥姥和孩子们有幸坐上一辆堆满物品的卡车,公公带着行李和其他人一起徒步走向贵阳,走了11天,行李也丢了。这11天,局势危急不定,亲人安危未卜,姥姥带着四个孩子承受着怎样的焦虑和等待,终于亲人安全归来时,他们又是怎样的欣喜和安慰,现在的我们是难以体会的。
1945年1月,公公决定脱离军校,去到重庆。他做酒失败,合伙开饮食店再失败。关于那段一筹莫展的日子,公公这样说:“自己做跑堂酒保,忙于打酒舀豆浆,端菜捧蒸笼。全家濒于饥饿边缘,仅免饿死。借了几块钱用来买米。少年时不屑学生意,这时不得不靠做生意苟全性命于乱世。”
1945年8月10日晚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庆祝痛饮,公公大醉痛哭:“国家胜利了,我自己却失败了。”
铁民曾来信要公公回军校,以免饥寒,他拒绝了。抗日统一战线已开始破裂,公公最要好的朋友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他给我们讲了“曳尾涂中”的典故,说他愿意像庄子那样,做在烂泥里摇着尾巴的乌龟,自在地过自由的生活,生活得像一个隐士,哪怕是贫困交加。他后来去了白沙大学先修班任国文教授。
回家的船等了一年,买到的是“活统票”,一种连四等舱位都没有的无座票,还是朋友帮了忙的。在船顶上铺了张席,全家人已满心欢喜,毕竟是踏上了回家的路。
1946年中秋当天,一家回到杭州临平。公公去徐州江苏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姥姥在杭州救济总署浙江分署工作,孩子们留在临平。浦东杨家花园住处楼梯下存放的书籍还在,其他衣物等都没有了。
四
1947年至1952年,公公在上海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0年他在政治研究院学习“改造思想”,因为在旧中央军校教过书,而成为“政治上不合格的教授”。1952年离开复旦。公公和姥姥教书近三十年,为生存,也为育人救国的理想。
50年代,因为需要有政治面貌,公公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
1952年,应老友冯雪峰之邀,公公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籍编注。开始时他编校新中国第一版《红楼梦》,在家里他常会和姥姥一起很有兴致地研究《红楼梦》中的各种谶语和诗词隐喻,作版本比较,但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就被取消了。1954年他被停发工资,被解职。两个孩子还在上学,生活仅靠积蓄维持。因长久深沉的忧虑,他还得了严重的失眠症。
1956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公公激情满怀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酝酿创作新的诗篇。公公对音律追求尽善美,不断吟咏推敲不断修改,写一段就念一段给姥姥听,她会说哪儿好哪儿不好,也会一如既往地帮着他誊抄。寄出的诗稿在耽搁很久之后退了回来,他无奈地笑笑,他不在意,他相信自己的作品。政治生活是他不熟悉不理解的,注定了他的失败,最终他烧毁了写了十多年的诗稿。他曾谦诚地检讨自己:“过去我写得多的是爱情诗,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的一种罪过。”
1957年《蕙的风》再版,公公对诗集作了“认真全面的修改”。他删除了约三分之二的诗,包括大多数当年被激烈抨击的段落和句子。那场关于《蕙的风》的大辩论,亦被历史的潮汐冲击着淹没了,似流星闪亮地划过天际,没有印迹地消失了。公公和《蕙的风》的命运反映着整个时代的变迁。
“反右”时公公被贴了许多大字报,但没被划为“右派”。公公曾问过邵荃麟:怎么没划我“右派”?回答:有三次反对言论划“右派”,两次就算思想错误。作协开会动员大家提意见,公公发言说给作家的待遇太低;《人民日报》开会他又说了一次;文化部开会他不想再说第三遍了。“那次如果发言,就是‘右派’了。如果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或者复旦,一定会有三次发牢骚的机会。所以我是很幸运的。”淡泊是公公的天性。
1965年,小女儿伊虹大学毕业。两个月后,公公和姥姥悄悄地回杭州隐居了。毕竟西湖与他的诗歌和他们的爱情紧密相连,他们爱恋西湖,他们会见容于西湖的。谢绝与外界的往来,杭州望江门外市民杂居的居民区里,居住着白发苍苍的老诗人,没人认得他是谁,也没人想追究他是谁,他们被世间遗忘了。十年风暴,公公和姥姥奇迹般地成为未受任何冲击的“五四”老人。1979年召开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浙江省文联找到望江门,街道云:“不知道汪静之是作家,他不声不响,只是每天来看报,从不说话。”
1969年,住在杭州姥姥家的时候,我上八一中学,其实那时没上什么课了,都在搞革命。因为我从北京来,学校还让我当广播员,参加宣传队。一次老师家访离开时跟我说:“你家怎么有那么多书啊,没被抄过家吗?”我回来跟公公一说,他紧张极了,当即下了一道禁令:“从今以后谁都不许带外人回家!”把我也吓坏了,幸好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也许老师只是感慨,毕竟那个年代难得能看到那么多书了,尤其是那些老书。
五
1986年3月19日,姥姥竹因病逝。公公曾对母亲说:“你们的母亲是死于贫困……”
抗日战争时期和五六十年代,他们都很艰苦。回杭州后,津贴更少,生活更拮据。他们非常节俭,衣服用具破旧不堪,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家里只用8瓦的灯泡。抽屉里总有许多一面空白的废纸,包括牙膏盒、药盒、包装纸,都用来写草稿、写备忘。每支铅笔用到握不住为止。公公还常常会为排长队买到划算的食物而高兴。但不管多难,他们总会在需要时力所能及地帮助邻里街坊,好像是一种本能。
我们家孙辈九个孩子,小时候都在姥姥家住过。“文革”期间,七个孩子曾经同时住在杭州望江新村的姥姥家,约有半年,最小的7岁,最大的14岁。我们的父母正有着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公公姥姥接纳我们,保护我们,给予了我们家的欢快和温暖,而孩子们的天真可爱、聪明顽皮,也带给了他们无尽的欢乐。我们那时完全不知道公公姥姥其实是那么苦那么难,他们也从来没有让我们感受到过任何的窘迫和不堪。我还记得那段时间的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
公公特别爱吃酒酿,他会自己做。酒酿发到刚好时很甜,小孩子都能尝一口,醇醇的香甜,特好吃,那个味道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不会消失。慢慢地酒酿的味道凶起来,小孩子就没份儿了。公公就喜欢凶的,越凶越好。长大以后知道,姥姥不许公公喝酒,他就自己做酒酿来过把瘾。那时跟公公出去,他会在路边小店买一小罐甜酒酿给我当零食,我很享受,他自己却不吃。
在姥姥家,每天一次饭后发糖,每人一粒黄豆大小的,是那时的“奢侈”了。做错事要“罚糖”,表现好有奖励,罚糖的机会更多些,被罚的都会很难过,奖励难得,也会很得意。记得一次是什么地方闹水灾了,公公提议一个月不发糖,把糖钱捐给灾区,我们都赞同。晚饭后是全家一起聊天的时候,七嘴八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特别热闹。有趣的是,最后要有一个总结,今天都说了些什么,从哪儿说起的,怎么就说到这儿了…… 最小的表弟小荣记性特好,会把当日话题的来龙去脉都讲出来,让大家吃惊。小荣出生十一个月就到姥姥家了,是跟着公公姥姥长大的。

姥姥与小荣
最快乐的当然是跟着公公游西湖,孤山、白堤、苏堤、三潭印月、玉泉、龙井、灵隐寺、宝俶山、雷峰塔……一次去灵峰看梅花,公公说,从前梅树稀少,树上的花也稀少,要到幽深的地方去找才能看到,所以叫“灵峰探梅”,现在满山满坡都种了梅树,开满了花,根本不用探了。他还带我们去看每年一次的钱塘江大潮,公公说他年轻的时候年年都要去,他见过的钱塘潮,潮头有两丈高,像一堵长长的高高的墙横着移动,隆隆轰鸣,震天撼地。后来看到的钱塘潮,都没能有过公公讲述的那般景象了。
记忆中,公公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是坐在书桌前的藤椅里,手里拿着一本书,微微地摇动着身躯,用古音轻声哼唱着似歌的韵律,这种时候是不能打扰的。那时我就想,诗是歌,是要吟唱的。我有幸见识过“吟诗”这种已经消失了的文化,也感受过那种吟唱带来的恬淡和宁静,十分美好。

1947年9月,伊甸考入浙江大学英国文学系
回想起来,各种艰难中公公和姥姥都保持了他们秉性里的清正与优雅,挺伟大的。
六
公公从小读的是私塾,古诗文基础很好,但他不认识ABC,考中学时英文都是不及格。后来学写新诗,想多读一些外国诗,需要英文,他就到上海中国公学暑期英语补习班学习。再后来父母生意倒灶没钱继续学业,要自己挣生活费,他便寄希望于孩子们能学好英文,可以帮他翻译英文诗歌。
逃难时,孩子们难得有机会上学读书。公公自己给儿女上课,英文则上夜校,在独山是姐姐伊甸去夜校学,回来再教弟弟。学会音标以后,他们就用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读本》自学。此外,姐弟俩还常到教堂去和外国传教士练习英语。
逃难结束以后,伊甸和弟弟飞白以同等学力考入浙大英语系,她还记得当时考试的题目是写一篇英文作文《一个梦》,这篇英文作文让她成功了。
新中国初建,急需俄文翻译。1949年12月,伊甸和飞白来到北京铁狮子胡同1号,进入华北大学俄文专修班学习。华北大学1950年10月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应招来自全国各大学的学生有五百多名,请了许多苏联专家当老师,伊甸的老师是别烈兹卡娅。
参加革命队伍后,母亲把名字改成汪晴,因为“伊甸”这个名字常会被人误解她是个基督徒。飞白也是舅舅在报考浙大时自己改的名字,后来他去了四野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
1951年6月,母亲被借调到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随周巍峙率领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到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全团二百多人两个翻译,一个是英语,另一个俄语就是母亲了。在开往欧洲的火车上,母亲天天都跟烧锅炉的工人练习口语,到达柏林的时候已经可以用俄语流利地讲话了。联欢节之后,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文化大使”,他们访问了苏联、东欧多国和奥地利,1952年底回国。母亲总是骄傲他们在柏林参加过清理德国国会大厦二战轰炸废墟的义务劳动,而且还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之后,母亲还随团去到东欧各国交换动物,用中国特有的华南虎、猴子、鸳鸯、扬子鳄,换来狮子、白熊、鸵鸟等,几个月后回来,建立起了北京西直门外著名的“北京动物园”。因为参加接待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母亲还翻译了很多波兰民歌,其中一首《小杜鹃》曾经广为流传。

1947年12月20日,浙江大学外文系欢送北上同学留影,第一排左三为伊甸、左四为飞白
20世纪70年代,从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回京后,母亲来到位于北京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进入外国文艺研究所,从事外国当代艺术的翻译和研究。她在各种刊物发表过几十篇译文和论文,还有译作《七十年代美术》《新艺术的震撼》。那时了解外界的机会不多,这些译作和文章稀少而珍贵。
离休后,母亲和舅舅飞白合译的《勃朗宁诗选》曾经获得第五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三等奖。舅舅飞白后来成为多语种诗歌翻译家。
不知道是不是公公的影响,母亲和舅舅都从事翻译工作,最终又都在诗歌的翻译上有所成就。
七
晚年公公深切怀念他一生挚爱的湖畔诗友:1931年柔石牺牲;1933年应修人牺牲;1934年潘漠华牺牲;1972年魏金枝病逝;1976年冯雪峰病逝。每次说起这些年轻美丽和年老亦美丽的生命的逝去,公公都会泪如雨下。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努力奔走,得到叶圣陶、巴金、丁玲、艾青的签字支持,也得到胡耀邦和陈云专门题写的匾额。90岁时,公公亲手布置的“湖畔诗社纪念馆”在西子湖畔开幕。
公公1996年10月10日辞世,姥姥早他十年先走了。他们遗嘱将骨灰混合,撒在杭州西湖孤山的梅树下。诗人走了,留下了爱情。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过伊家门外》(1922)
2019年11月30日 于北京
汪静之主要作品:
1922《蕙的风》
1926《耶稣的吩咐》
1927《寂寞的国》
1927《鬻命》《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1927《诗歌原理》
1928《李杜研究》
1929《人肉》《父与女》
1933《文章模范》
1937《作家的条件》
1938-1940《爱国诗选》《爱国文选》
1958《诗廿一首》
1996《六美缘》
2002《漪漪讯》
2006《没有被忘却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