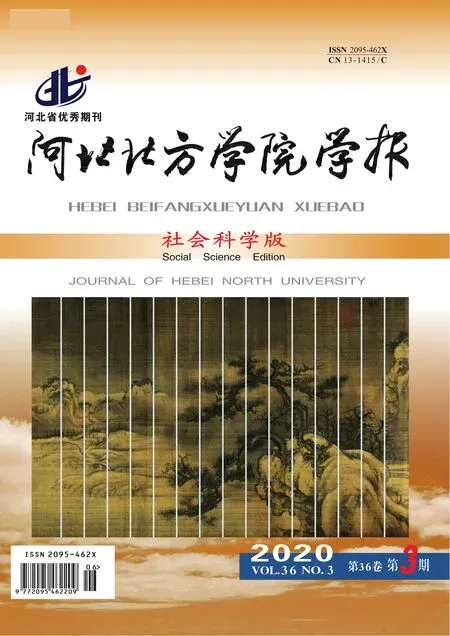孝弟为仁之实
——略论罗近溪的仁孝观
2020-01-16石霞
石 霞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祖籍江西南城,一生讲学不辍,是泰州王门学派的重要人物。近溪常以“求仁”和“孝悌”概括孔孟思想核心:“孔门宗旨,止要求仁”[1]277,“孔孟之言皆必归会孝弟”[1]53。“仁”与“孝”是近溪思想的核心。他坚持孔孟仁孝互释与仁孝一体的思考方式,对“仁”与“孝”的关系进行了全新且极有价值的阐发,并逐渐形成了仁孝思想的基本格局。
一、仁孝相辅相成
在孔孟思想中,仁与孝关系密切。孔子《论语·学而》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将孝视作为学的开端,主张由切己平常的孝悌出发,在日用常行中渐次入仁。在孔子看来,仁是最高的德性,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但如何成就并通达仁境则是工夫论与方法论范畴的问题。孔子提出从简便直截的孝悌入手,在具体的孝悌实践中渐次上达仁境。如《论语·雍也》云:“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构成了孔子工夫论的基本进路与仁孝观的基本内容。孟子则进一步将孝悌视为仁的基础与发端。如《孟子·尽心上》:“亲亲,仁也”,直接视爱亲为仁;《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侍奉自己的亲人就是仁的实质内容。由此可见,孔孟思想中仁孝相辅相成:孝为仁的实质与求仁的基本方法,而成就并通达仁境则成为孝的最终目标。
近溪思想归宗孔孟,故对仁孝关系的论述呈现出对孔孟仁孝观的认可与趋同,体现了对孔孟思想的回溯,强调仁孝的一体性。例如,近溪在论及仁孝关系时曾明确表示两者并无分别:
孔子云:“仁者,人也。”盖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从父母一体而分,亦纯是一团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而后能践形。践形即目明耳听,手恭足重,色温口止,便生机不拂,充长条畅。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即孝无不全矣。[1]430
在此,近溪指出仁孝无差别的关键在于“仁者,人也”,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仁者,人也”,“仁而人”。“仁”乃“天地生生之大德”,化生万物,构成人的存有论依据,人因禀受“仁”而成“人”。其二,“仁者,人也”,“人而仁”。“为仁由己,即人而仁矣”[1]27,仁德必须通过人来彰显,并最终落实到“为仁由己”的个人实践上,即“目明耳听,手恭足重,色温口止”等日常行为活动。因此,近溪言“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与仁是一而二、二而一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孝经·圣治》:“人之行莫大于孝。”孝为百行之先与为人之本,故“人既成,则孝无不全矣”。就此而言,仁与孝亦相辅相成:一方面,孝悌是从人的内在仁性生发出来的自然德性,通过孝悌这一具体行为提供不竭的动力。生生之仁构成了孝的形上依据;另一方面,仁德之彰显必落实到人身上,具体而言即要落实到人对孝悌的道德践履中,并通过推扩与感通而日渐臻于仁境。因此,“孝以成仁,亦以仁成”[1]969,仁孝“亦无分别”。明显地,近溪将“仁与人”以及“人与孝”一体而观,且指出3者相互依存。由此,人成为仁与孝的中间媒介并将两者紧密关联。对此,他还有更具体的论述:
以其所以为子者为人,是谓事天如事亲,而可以言仁矣;以其所以为人者为子,是谓事亲如事天,而可以言孝矣。此孔子之教也,孟子以一言尽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人而曰“大”,则与天地合德,不亦仁乎?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亦孝乎?赤子之心不失,即可以为大人,是孝固所以成其仁也。惟至于大人,然后能不失赤子之心,是仁又所以成其孝也。然则仁与孝而已矣,必兼举而言之,其义始备。[1]986
近溪认为,以侍奉父母的方式侍奉上天为仁,以侍奉上天的方式侍奉父母为孝。虽然仁与孝的侧重点不同,但两者在践行上实无差别。如此,近溪将孝提升到与仁同等的高度。此外,近溪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将仁孝两者统筹起来。“大人”与天地同德,故可称仁;赤子之心乃孩提先天具备的爱亲敬长之心,可称孝。保持“赤子之心”必可上达天道成为“大人”,而成为“大人”必定不失“赤子之心”。所以,“仁人”与“孝子”必然也互相成就且不可分别,“必兼而举之”。
二、孝弟为仁之实
近溪强调“仁”“人”以及“孝”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双向贯通,是要说明孔子的仁学是形上与形下双向贯通的一体之学,且主张回归孔门宗旨亦是要回归孔门彻上彻下的一体圆通之仁学。近溪看来,“仁者,人也”,孔子的“仁学”亦是“人学”,但宋明儒者却舍本逐末,轻孝悌而慕仁义,偏重于超越层面之“仁”义(仁学)而忽略了实践层面之“人”义(人学),致使所作学问脱离实际,日益玄虚。事实上,近溪回归孔孟宗旨是为纠正宋明理学之弊病,其倡导仁孝并举亦是为强调“人”的实践义,贯通形上之仁理与形下之实践,进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仁学”。
近溪以孔子仁学思想为范本,并将《大学》一书视为孔子对求仁之学的集中概括。“其心将以仁其身者,仁万世入人之身,而恐无凭据,故既竭心思而继以先王之道,于是取夫六经之中,至善之旨,集为《大学》一章,以为修、齐、治、平规矩,所谓格也。”[1]216他指出,孔子忧心世人执着于玄虚的仁体,茫然不知如何求仁,而六经所记古圣先贤之道为到达万物同体的仁者境界提供了重要借鉴,故孔子竭力探寻并写就《大学》一章,通过“修齐治平”的规矩集中归纳了六经中成圣之道与求仁路径。近溪曾言,《大学》被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一句道尽[1]216,该书所阐明的成圣规矩不过是赤子天生具有的“孝悌慈”的不断实践而已。因此,“修齐治平”的成圣路径无非是“孝悌慈”的具体实践。近溪对朱子和阳明学说表达了不满:“其旨趣,自孟子以后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见得当求诸六经,而未专以孝、弟、慈为本,明有阳明先生见得当求诸良心,亦未先以古圣贤为法。”[1]5他认为宋代大儒朱熹虽重视古圣经典,主张求天理与仁道于六经,却没有以孝悌慈为学问之本;明代大儒王阳明虽明白成仁需内求良心,却未能效法“古圣贤”之道。事实上,近溪对两者的批评是一致的,认为他们都忽略了对《大学》中“孝悌慈”具体实践方法的把握,致使学说思想日益背离孔门宗旨,难成万物一体的仁境。近溪此番批评旨在通过提揭孔孟仁孝一体之学,高扬孝悌慈,为求仁与致良知提供简易直截的实践路径,从而纠正宋明理学执持本体与忽略工夫之偏。对此,他补充道:
盖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义。殊不知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也。今看人从母胎中来,百无一有,止晓得爱个母亲;过几时,止晓得爱个哥子。圣贤即此个事亲的心,叫他做仁,即此个名而已。三代以后,名盛实衰,学者往往知慕仁义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1]135
近溪以“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一句总结仁孝关系:仁义只是个虚名和抽象概念,而孝悌才是其实义与具体方法。这显然是从名实关系角度论述仁孝两者的关系。他批评后世学者只追求仁义之虚名而不重视孝悌之实义,殊不知实现仁义的根本方法在于孝悌慈。近溪再三指出孝悌是构成仁义的实际内涵与成就仁境的根源,主张以“孝悌”来落实“仁义”。因此,孝悌是近溪求仁的根本方法和工夫路径。
“孝弟为仁之本”是孔子探讨仁孝关系的基本命题,历来学者对此句的解释不一。汉儒大都认为孝悌是天生自然无伪的情感,是仁的根本,也是实现仁的根源和基础。程颐则反对汉儒之说,“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之是仁之本则不可”[2]。他认为,仁是人内在固有的善性,而孝悌无论意为爱亲之情还是孝悌之行,都属外在的“已发”而不属内在仁性的范围内,仅是“仁性发而为用”的具体表现。但孝悌作为人降生后仁最初的发用,是实践仁最切近且最直接的方式,以此作为求仁的发端,则能悟得仁道。但孝悌的实践只是仁的一部分,仅是践履仁道及步入仁境的根本或开端,距离实现“仁”还相差很远。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观点,释“为仁”为“行仁”:“为仁,犹曰行仁……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3]这一诠释构成了宋儒及阳明对仁孝关系论述的基本看法。基于阐扬“仁虚孝实”的基本主张,近溪力主汉儒之说,认可“孝弟是仁之本”: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犹根也,树必根于地,而人必根于亲也。根离于地,树则仆矣,心违乎亲,人其能有成也耶?故顺父母、和兄弟,一家翕然,即气至滋息,根之入地也深而树之蕃茂也,将不可御矣。然则厚其亲者,实所以厚其身也夫![1]333
与程朱从体用角度论述“孝弟为仁之本”不同,近溪强调孝悌为“仁之本”,即孝悌是仁的“本根”。孝悌不仅是践行仁义的开端,更是成就仁境的根源。近溪以树木与地面及人与其亲的关系作比仁孝的关系:树必根于地而人必根于亲,树木离于地则死而人违其亲则难成。以此推知,孝悌为仁之根本,离于孝则仁不存。概言之,孝悌构成了仁的根本,达成仁必有待于对孝悌的落实、扩充与发展。此外,近溪将“仁”与“人”相互贯通,高扬“人”的实践义,由“孝弟为仁之本”得出“孝弟为人之本”的结论:
“古本仁作人最是,即如人言,树必有三大根始茂,本根也,夫人亦然,亦有三大根,一父母,一兄弟,一妻子。树之根,伐其一不荣,伐其二将槁,伐其三立枯矣,人胡不以树为鉴哉?”[1]379
很明显,近溪将孝悌慈作为人的学问之基与立身之本。由此,孝悌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孝悌慈而天下归仁
近溪力主“仁虚孝实”之说,高扬孝悌慈,确有将孝悌慈视为形上本体的倾向,但他还是多从形而下的实践层面论述孝悌是行仁的发端和根本。《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意思是施行孝悌本身不是目的,应在此基础上超越家庭伦理之爱,博爱大众,追求万物一体之“仁”。近溪亦秉持孔子这一思想取向:孝悌慈为求仁本始,应在施行孝悌慈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爱的对象,直至达到万物一体之仁境。超越本体的“仁”虽是抽象概念,但构成了行孝之最高理想和终极目的。这体现了近溪诠释仁孝关系既入世又超越的辩证思路,即在不离于又超越日用伦常的情况下实现追求超越仁体的目标。
关于追求超越之仁的具体路径,近溪言:“仁既是人,便从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说:‘仁者人也。’下即继以‘亲亲为大’,谓之‘为大’,盖云亲其亲,不独亲其亲,直至天下国家,亲亲长长幼幼,而齐、治、均、平也。此则所谓人上求仁,又所谓中心安仁,尽天下而为一人者也。”[1]186近溪常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一句阐述孔门求仁之方,此句亦是近溪求仁路径的集中表达。“仁者人也”意味着要通过人的实践去求仁。“亲亲为大”具体包含两种含义:首先,可将“大”释为“重要”与“切近”,“亲亲为大”意为求仁必须落实在爱亲敬长的日用伦常之中。其次,近溪在此主要将它释为“扩充”之意。所谓“亲亲”不仅停留在孝道的范畴,更意味着将“亲亲”由家庭伦理扩充到社会伦理。“亲亲”即“孝”,是“仁”的原点,“亲亲为大”意味着要以“孝悌慈”贯穿行仁之始终,推扩至天下国家,直至达到“中心安仁,尽天下而为一人者”的至仁境界。此“仁”才是真正的“仁”,是“大人之学”与“大学之道”的目标,亦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
近溪反复强调“孝悌慈”彻始彻终、一以贯之且通贯天下。“孝悌慈”不仅是天生自然的明德,更是一种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的普遍伦理。“孝以成仁”,与之相关,“万物一体之仁”的目标便也不仅是一种人与万物相感通的精神境界,更同时具有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指向和意涵,体现出近溪对“尽天下而为一人”的大同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前者主要是从孝亲敬长之心出发,以道德情感的角度论证万物一体的普遍意义,而后者主要是从孝悌之行的践行与推扩角度论述万物同体,主张立足于道德主体和家庭人伦,由近及远并推己及人,然后视人如己、待疏若亲与一体同善,实现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超越孝悌和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大同理想是近溪仁孝思想的最终旨趣,这从近溪以孝悌慈诠释“为政以德”便可看出:
若泛然只讲个“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则恐于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从之,亦皆漫言而无当矣。若论“以德为政”,却又有个机括,俗语云:“物常聚于所好。”又曰:“民心至神而不可欺。”今只为民上者,实见得此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缘、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报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万物万民万世之命。[1]152
就儒家传统而言,在道德和政治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线,将政治问题视作道德领域问题的延伸,将外王视作内圣的推延和结果,是关于道德和政治关系的基本看法。如《论语·为政》中的“孝慈则忠”,就将事父的“孝”推至事君的“忠”。《大学》则把孝悌慈扩展至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孝悌慈是事君、敬长以及治民的手段。近溪继承了儒家这一传统,进一步将“孝悌慈”道德情感具化为家庭关系内部和社会政治领域的一般行为法则。他指出,“为政以德”的“德”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孝悌慈。孝悌慈不仅是一种人人具备的天生自然的道德意识,还是人们道德实践的切近处,更是道德行动的重要准则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在治理天下的政治实践中,必须以“孝悌慈”为本,将其视为事君敬长与仁民爱物的手段,进而治化天下。“亲亲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于为人之人,则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长,近可以仁民,远可以爱物,齐治均平之道,沛然四达于天下国家,而无疆无尽矣。”[1]180在为政过程中,将孝悌慈沿着由己及人、由下向上以及由家至国的道德实践进路不断推扩,则举国上下莫不大兴孝悌而无生悖乱,便能“可以救活万物万民万世之命”,构建一个能够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社会。如此,“尽孝”和“治国”相统一,更深层次地实现也超越了孝道,实现了“天下归仁”与构建大同社会的理想。“吾辈今日之讲明良知,求亲亲长长而达之天下,却因何来?正是了结孔子公案。”[1]434在近溪看来,将孝悌慈这一切实的道德实践极致推开以实现孔子“天下归仁”的理想,最终构建一个天下之人皆一体而相亲的理想社会。很显然,“作为宇宙与人心的存在模式的‘万物一体’如何化为‘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社会模式,才是近溪‘求仁’宗旨的最终归趣”[4]。
总之,近溪的仁孝观是其在继承孔孟仁孝观的基础上反思宋明理学之弊并寻求救弊方法的产物。他秉承孔孟仁孝并举的思维方式,对仁孝观进行了独特的阐发,进而构建了一个彻上彻下、既入世又超越的一体圆通之仁学。但出于纠正宋儒专注仁体与轻视工夫之偏,其诠释重点不可避免地落在“孝”的一方,使孝悌慈成为其学问的主要内容。近溪晚年更是将“孝悌慈”视为天底下“三件大道理”与古先帝王“三件大学术”,进一步将孝悌慈推广到社会与政治领域,体现了晚明儒学思想世俗伦理化的趋向,是对阳明心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