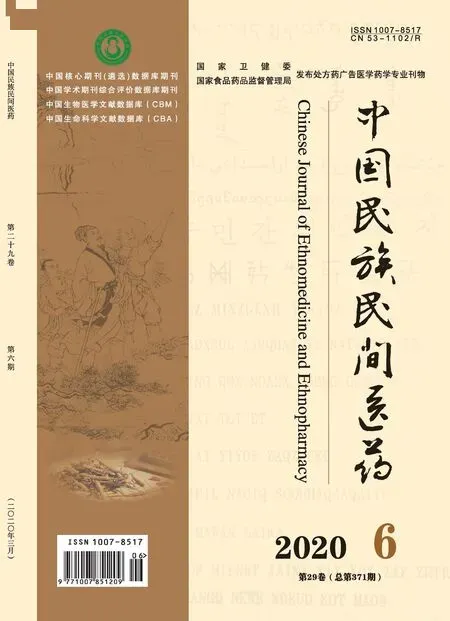李应存教授运用敦煌泻肝补脾汤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验案举隅
2020-01-13李应存
马 楠 李应存,2▲
1.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2.敦煌医学与转化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
敦煌学是当今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医学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医理、诊法、本草、医方、针灸等方面,其中医方类著作记载处方共计1240余首,这些医方治疗疾病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内、外、妇、儿、耳、鼻、喉、眼、口腔、皮肤等各科疾病[1]。李应存教授是我国著名敦煌医学专家,敦煌医派代表人物之一,长期致力于敦煌医学文献的发掘、整理以及临床应用的研究,尤为擅长运用敦煌古医方治疗常见疾病及疑难杂病。
胆汁反流性胃炎是消化系统临床常见病,随着近年幽门螺杆菌感染与慢性胃炎、溃疡病及胃癌等疾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2]。胆汁反流性胃炎的主要部位在胃窦部,因胆汁反流性胃炎引起的胃黏膜损伤主要是由反流胆汁中所含胆盐、非结合毒性胆汁酸等成分造成,故又称为胆汁性损伤[3]。目前,西医临床多以抑酸、中和胆酸以及促进胃肠动力等药物为主,短期疗效尚可,但病情极易反复。近年来中医药在该病的治疗方面展示出其独特优势,中医药可有效地改善胆汁反流性胃炎的临床症状,抑制胆汁反流[4]。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如胃脘疼痛、上腹胀满、烧心、反酸、呕吐等症状,在祖国医学中,可归属于“胃痛”“痞满”“嘈杂”“泛酸”等范畴。其发病多由素体脾弱、忧思恼怒、外邪客胃、饮食不节等病因诱发,李应存教授临床观察发现,该病病机多属肝脾不和,胆热上扰,治疗当泻肝实脾,调畅气机。
1 泻肝补脾汤
敦煌泻肝补脾汤来自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卷藏于敦煌藏经洞,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的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5]。该卷内容较为完整,突出五行格局,经纬五脏用药,并以脏腑学说为基础论述疾病的治疗与方法,别具特色。书共载医方50首,其主治及配伍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且非常具有临床意义。敦煌泻肝补脾汤源自于大泻肝汤与大补脾汤,李应存教授常以泻肝实脾为法,将两方相合治疗证属肝脾不和的消化系统疾病,故合称泻肝补脾汤。
该卷展示了辨治五脏病证的经方,其中大泻肝汤原方述:“大泻肝汤。治头痛,目赤,多恚怒,胁下支满而痛,痛连少腹迫急无奈方。枳实(熬)、芍药、甘草(炙)各三两,黄芩、大黄、生姜切,各一两。右(上)六味,以水五升,煮二升,温分再服[1]。”枳实破气散积,化痰除痞;白芍养血柔肝养血,敛阴止痛;生姜温胃降逆、调中止呕;黄芩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大黄泻热毒、行积滞;甘草补脾益气、调和诸药。方中枳实合芍药,调畅气机,肝郁得疏,肝阳得平,破气而不伤阴;芍药合甘草,酸甘化阴,缓急而能止痛;黄芩、大黄苦寒,泄肝胆胃肠郁热。
大补脾汤是为治疗脾气虚弱、胃阴不足、饮食不化所设。原方书载如下 :“大补脾汤。治脾气大疲,饮食不化,呕吐下利,其人枯瘦如柴,立不可动转,口中苦干渴,汗出,气急,脉微而时结者方。人参、甘草炙,各三两,干姜三两,白术、麦门冬、五味子、旋覆花一方作牡丹皮,当从。各一两。右七位,以水一升,煮取四升,温分四服,日三,夜一服[1]。”方中人参补五脏,疗虚损,润肺宁心,与甘草、白术合用,共奏大补脾气、健脾祛湿之功,治疗脾虚不能食者;麦门冬、五味子益气养阴敛汗,与人参、白术同用之效于《本草经解》有述:“(人参)治气脱中寒,同白术、麦冬、五味[6]”;旋覆花升而能降,顺应胃之以降为顺的生理特性,起降逆止呕之功,并可拨气机升降枢纽。干姜善于温散中焦寒邪,与白术相伍以燥湿散寒,鼓动脾胃阳气以助运化。甘草补脾益气,调和诸药,张仲景《五脏论》(敦煌遗书·法藏编号P.2115)谓“甘草有安和之性,故受国老之名”[1]。
2 临床运用心得
李应存教授临床常以敦煌大泻肝汤、大补脾汤治疗各种消化系统疾病,如慢性胆囊炎、急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等,皆获显著疗效[7-9]。李应存教授认为临床常见的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以肝脾不和,胆热上扰为多见,该病病位在胃,与肝、胆、脾密切相关,土虚木乘则脾胃升降失司,且脾胃气机调畅有赖于肝胆之疏泄功能,若肝失疏泄,则脾胃气机失常,久之肝气犯胃,《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有言“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反呕,呕酸善饥[10]”。此病乃肝脾不和且气机逆乱,故可见肝胆失疏泄,脾胃失和降,胆不随胃降而致胆汁不得循常道逆流于胃,灼伤胃络。李教授以泻肝实脾为法运用敦煌古医方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补虚泻实、复其气机枢转则病可见愈。若肝热犯胃、耗伤胃阴,则去干姜,重用麦冬或加石斛、北沙参以养胃阴;肝郁不疏,气机阻滞,则加郁金、香附以疏肝解郁;若肝胆湿热、中阻不运,则加黄芩、栀子以清热燥湿;若发病较久、久病入络,则加三棱、莪术活血消瘀;胃痛甚者,重用白芍并用延胡索柔肝止痛;恶心呕吐者,重用旋复花合用代赭石条畅中焦升降之气;烧心、反酸甚者,加煅瓦楞子、海螵蛸制酸止痛;纳食不运者,加木香、炒鸡内金行气开胃消痞。
3 验案举隅
患者肖某,女,52岁,兰州市西固人,2019年3月14日来诊。主述:胃胀、反酸烧心半年余。半年前于某院检查,胃镜示:胃黏膜充血、水肿明显,可见大量含胆汁的反流液;B超示:胆囊壁稍毛糙;14C呼吸试验提示幽门螺杆菌(Hp)阴性,曾服用奥美拉唑、熊去氧胆酸利胆、多潘立酮等药物效果不佳。于2019年3月17日前来我院就诊,刻下症见:患者面黄、消瘦,半年来体重减轻10余斤,自述胃脘胀满不舒、反酸烧心,食辛辣刺激或生气后加重,并伴有胁、背部胀痛,恶心欲呕,口中干苦,嗳气频,口臭,心急易怒,纳呆不运,眠浅易醒,大便溏,舌淡苔黄腻,舌体胖大且有齿痕,舌下静脉迂曲,脉弦数,左寸关弦甚,右关弱。西医诊断:胆汁反流性胃炎。中医诊断:痞满,辨证为肝脾不和,胆热上扰。治则:泻肝实脾,调畅气机。方予敦煌泻肝补脾汤加减,处方:酒大黄6 g,黄芩15 g,枳实12 g,白芍15 g,党参12 g,白术15 g,干姜6 g,麦冬9 g,五味子6 g,旋复花15 g(包煎),厚朴15 g,炒鸡内金15 g,茯神30 g,莪术15 g,海螵蛸15 g,煅瓦楞子30 g(先煎),木香15 g(后下),炙甘草6 g。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2次服,取药5剂。嘱其饮食清淡,调畅情志,劳逸结合。
二诊(2019年3月22日):脘胀、反酸烧心减轻,精神较前转佳,余诸症皆有所缓解。刻下仍胁、背胀,恶心,口干苦,嗳气,口臭,心急,纳谷转馨,睡眠好转,大便稀溏,日行两次,舌淡苔黄略腻,舌体胖大伴有齿痕,舌下静脉迂曲,脉弦,右关弱。效不更方,在前方基础改旋复花为20 g、木香20 g加强调平降胃气,调畅气机,助阳健脾;加干姜至10 g,加煨肉豆蔻15 g以增温脾燥湿之功;减酒大黄至3 g,白芍至12 g,麦冬6 g,以降润肠通便之弊。用法同上续服5剂。
三诊(2019年3月27日):脘胀、反酸烧心明显缓解,胁痛、背胀、恶心、口苦、口臭止,刻下口稍干、偶嗳气,情绪较前平静缓和,面色较前红润,纳食增加,寐安,大便日一行,较前成型,舌淡苔黄,舌体略胖,齿痕渐消,舌下静脉迂曲减轻,脉弦,右关较前应指有力。守方加党参至15 g,白术至20 g以健脾益气,减黄芩至12 g,去煅瓦楞子以缓碍胃之弊。以此方续服15剂,用法同前。
笔者于2019年9月18日电话回访,患者自述状况良好,药后症状渐消止,未见明显胃胀、反酸烧心等症,食欲佳,气色明显好转,半年来体重增加8斤。嘱其保持心情舒畅,饮食有节,忌饮酒,少食辛辣油腻之品。
按:本例患者胃镜检查胃中含有大量胆汁的反流液,B超显示胆囊壁毛糙,结合其脘胀、反酸烧心等症状,西医诊断为胆汁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诊断为痞满,李应存教授辨其内因主要为肝脾不和,胆热上扰。患者烧心、胁痛、口干苦、心烦易怒,脉弦左关甚皆提示肝胆火旺、胆热移胃、热扰心神;又因肝主一身之疏泻,肝胆气机不畅则影响脾胃之升降,因而脾清阳不升、胃浊阴不降,升降失调,痞结中焦,故患者出现胃脘胀满不舒、背胀的症状,并伴有反酸、恶心欲呕、嗳气频等胃气上逆之症,《症因脉治》中云:“呕吐酸水之因,恼怒忧郁伤肝胆之气,木能生火,乘胃克脾,则饮食不能消化,停积于胃,遂成酸水浸淫之患矣[11]”;《灵枢·本输》篇曰:“木邪横侵,土被其贼,脾不升而不磨,胃不降而不纳[12]”,内经用五行生克阐述了肝木乘土之理,故脾土受乘则胃不能纳,脾不可运,故患者纳呆运迟;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虚弱,又受肝木所制,其受纳、运化失常则可见面黄、消瘦、右关弱,失眠亦是“胃不和则卧不安”所致;土虚不制水则见便溏、舌体胖大且有齿痕。李教授谨守病机,以法活用古方,选用敦煌泻肝补脾汤并灵活化裁,李教授善用酒大黄,酒制泻下力缓,引药上行,径走肝经,合黄芩以清泻肝火、折火热之势,《本草易读》有言“(大黄)得酒良,黄芩为使,无所畏[13]”;大黄酒制善行,合枳实以梳理肝气、调畅一身气机;白芍苦酸微寒,入肝脾血分,《本草从新》曰:“酸敛肝,肝以敛为泻,以散为补[14]”,白芍不仅可酸敛柔肝,亦可安脾胃,善于土中泻木,如《本草备药》述“胁者,肝胆二经往来之道,其火上冲,则胃脘痛,横行则两胁痛,白芍能理中泻肝[15]”,用以酒大黄、黄芩、枳实、白芍从气分到血分共奏泻肝、疏肝、平肝、柔肝之功,肝胆火降则脾胃气机升降得畅,胆汁可循常道而行。仲景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16],故以党参合白术、干姜、甘草补脾建中除湿邪,调和中焦以拨上下之枢;旋复花升而能降,《本经逢源》言其可“开结下气,祛痞坚,开胃气,止呕逆,除噫气[17]”,胃以降为顺,以通为补,故其可顺应胃的生理特性,乃条畅脾胃升降气机之良药,与干姜、黄芩相伍以起辛开苦降,又合枳实、厚朴、木香、炒鸡内金以行气通腹消痞满;胃喜润恶燥,故加少量麦冬养胃阴,且防干姜、旋复花、厚朴、木香燥胃阴,麦冬亦有消心腹气结、补中之用,陶弘景云:“主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18]”;五味子五味俱备,酸咸为多,故可酸泻肝气而咸滋肾水,又可助脾胃辛开苦降,甘以安中,孙思邈云其可“益五脏之元气”[19];患者失眠乃“胃不和则卧不安”所致,故除以上舒肝和胃之药,再佐以茯神安魂养心;患者舌下静脉迂曲,《本草备要》言莪术可“消瘀通经,开胃化食”[20],故加之以化瘀通络,兼可消食助运,乃活血化瘀药中的胃病专药;海螵蛸、煅瓦楞子可制酸止痛,乃李教授治疗反酸、烧心专用药对。
此病虚实夹杂,李教授泻肝实脾法前期以泻为主,患者二诊肝胆火降,气机始运,症状皆有所减轻,但大便稀溏,日两次,故治疗中期重再在调气机,减凉润之药,加补脾胃之虚,拨动脾胃气机运转之枢纽;患者三诊症状大减,热除气降,脾气渐复,气机得运,故治疗后期以补虚为重,减苦寒、去碍胃之药,使脾胃气机运转得复,病自可康。
4 小结
胆汁反流性胃炎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其发病率逐渐攀升,较难以根治,且极易反复发作。李应存教授认为该病临床以肝脾不和,胆热上扰,木胜乘土为多见,泻肝实脾法为其治疗核心,故以法立方选用敦煌泻肝补脾汤,并根据该病的发病、进展规律及特点,设立“泻实-调气-补虚”三个治疗阶段,临床获得确切疗效,望可为同道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