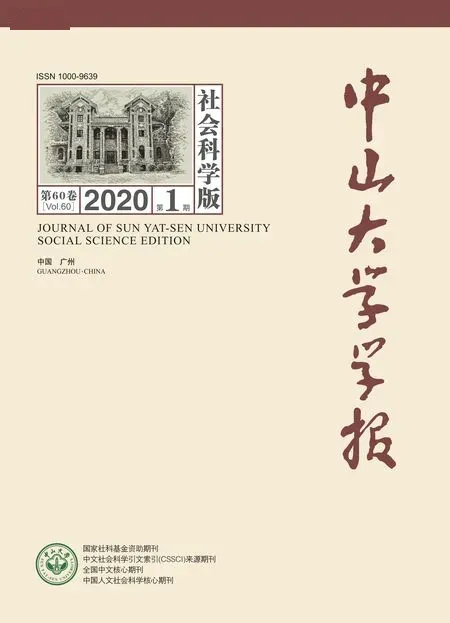“纯化”与“泛化”:以胡著哲学史为考察中心*
2020-01-11陈仁仁
陈 仁 仁
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问题其实从这门学科的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只要研究或写作中国哲学史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只不过不一定明确意识到。从已有文献看,学界真正把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来作为一种方法加以讨论,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在这场讨论中,著名哲学史家萧萐父对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作了比较精当的界定和分析,并主张“或纯化”“或泛化”“两端互补”。这一观点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写作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是开山式的人物,我们可以从“纯化”与“泛化”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和评价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点与价值,并揭示“纯化”与“泛化”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意义。
一、萧萐父关于哲学史研究的“纯化”与“泛化”的主张及其方法论意义
萧先生如此论述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问题,他说:“鉴于哲学史研究曾羼入许多非哲学的思想资料,往往与一般思想史、学说史浑杂难分,我曾强调应当净化哲学概念,理清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把一些伦理、道德、宗教、政法等等非哲学思想资料筛选出去,使哲学史纯化为哲学认识史,以便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但进一步考虑到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哲学,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文化,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而这些年我又强调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1)萧萐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6期,第3页。
从这段论述可知,萧先生所谓“纯化”就是净化哲学概念,理清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把非哲学思想资料筛选出去,从而把哲学史与一般思想史、学说史区分开来。所谓“使哲学史纯化为哲学认识史”,就是说“哲学认识史”才是纯粹的“哲学史”。这里的“哲学认识史”是指“哲学的”认识史,就是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历史。那么“哲学史的研究”就是要研究和认识这种“认识世界”的“哲学的方式”以及这种认识方式的历史变迁,从而“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我们不能把萧先生所谓“哲学认识史”仅仅狭隘地理解为哲学中的认识论和认识方法及其发展史,尽管“哲学认识史”包括这一方面的内容。
所谓哲学史研究的“泛化”,萧先生是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角度论述的。文化是哲学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灵魂,这就意味着文化比哲学的范围更广泛。这同时也是上文所谓哲学史之“纯化”的前提性观念。哲学史的“纯化”是在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除了要剔除伦理道德学术思想史、宗教学术思想史、政治法律学术思想史以及科学学术思想史等方面的学术思想材料,当然更要剔除伦理道德史、宗教史、政治法律史以及科学史等方面的材料,但是所有被剔除的材料,其实共同构成了“哲学史”发展的土壤。了解哲学史发展的土壤,其实就是了解其生长的基础,从而也是了解哲学本身。同时,哲学与文化又都因为与“人”有着最根本的关系,即“哲学”作为“人学”,“文化”作为“人化”,而有共同的根基。萧先生说,“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这就意味着,哲学与文化的共同基础是“人”,这个共同基础的核心内容是“人的价值理想”。文化的各个具体部门和方向,比如伦理、道德、审美、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是真善美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创造活动,而作为文化之灵魂的哲学,则是从总体上对真善美的创造活动的统一实现,也就是说哲学是从总体上影响和推动文化的力量。于是,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和了解,就可以通过对文化史的研究和了解来实现。所以,哲学史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也即“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者“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这就是哲学史研究的“泛化”。
萧先生关于哲学史研究的“纯化”与“泛化”的主张,不只是一个技术意义上的方法,更是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属于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方法论意味着其适用范围可以突破其所论述的对象而达到很广。适用范围越广,其内涵越深,其方法论意义越大。萧先生在阐述这一方法论时,其具体对象可能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的表述是“哲学史研究”,这意味着,“纯化”与“泛化”的方法也适用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其实,所有的研究,若要做得深入而丰满,这一方法都是适用的,只不过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因对象特点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和某些具体的要求。我们这里只是试图谈谈此一方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运用。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个案,然后兼谈此一方法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之成立与发展的意义。我想这也足够表示“纯化”与“泛化”的方法论意义了。
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从“纯化”到“泛化”
1919年2月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8年9月撰成寄出)(以下简称《大纲》),两个月内再版,三年内再版七次,可谓风行一时,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性著作。梁启超赞道:“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2)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0—51页。。蔡元培称赞此书“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3)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页。。冯友兰称此书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3—205页。。当时就有人说这是“一部万人赞赏的‘大著作’”(5)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序言》,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1年,第1页。。直到李泽厚先生依然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Paradigm)的变革。”(6)李泽厚:《胡适 陈独秀 鲁迅》,《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93页。胡适对自己这部书也是相当自信。他在1927年的一封信中说:“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7)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胡适文存三集》卷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118页。在胡适之前,北大已先后有陈黼宸、陈汉章和马叙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谢无量早在1916年就已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而且还有日本汉学家的《中国哲学史》译入中国,但是胡适就是有这种自信,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对象、范围、方法等有比较明确的意识和自觉。这种意识和自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纯化”与“泛化”的过程。
我们知道,胡适的《大纲》是以他的《先秦名学史》为蓝本丰富扩充而来。《先秦名学史》是1915年9月到1917年4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跟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念博士时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英文原题为“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自己译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六册说明”。。1922年,胡适的博士论文英文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出版,他用的英文书名是: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自注中文书名是:先秦名学史。可见,他是把古代的“名学”当作“逻辑学方法”,把“逻辑学方法”当作“哲学方法”的。他说:“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9)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逻辑与哲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6页。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三点认识:一是胡适对哲学史的研究是从哲学方法开始的,二是胡适认为哲学方法的发展决定了哲学的发展,三是胡适认为哲学方法就是逻辑学方法。后来,胡适在《大纲》的《导言》中对哲学的门类进行区分,第二类即是“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他在这句话后面括注“名学及知识论”(1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他对哲学分出的六类内容中,没有方法论。由此可见,在胡适看来,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是同一的,认识论与逻辑学是同一的,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即名学。这实际上就是胡适试图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一番“纯化”而作出的一种尝试。
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纯化”,可以从“哲学”与“哲学史”两个方面来理解。胡适在“哲学”方面的“纯化”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对“哲学”下一个定义作出限定,二是对哲学研究的问题对象和范围作出限定并分类。胡适在《大纲》的《导言》中对哲学下的定义是:“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后来(1923年)他觉得“根本”二字意义欠明确,所以就改了一下哲学的定义:“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11)胡适:《哲学与人生》,《胡适演讲集》卷3,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第281页。这种对哲学的界定,从“解决人生问题”到“寻找人生意义”,似乎越来越契合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的哲学研究从人生哲学开始,而归于人生四境界说,正是中国哲学这一精神的体现。所以,对中国哲学史做“纯化”的工作,也并不像有的学者说的完全就是“西方化”或者“西方味”的哲学。胡适“纯化”哲学的第二个努力是对哲学研究的问题对象和范围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六类:一是“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是“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是“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四是“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五是“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是“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在研究和写作《大纲》之时,胡适对哲学的定义还处在“解决人生问题”阶段,所以他对六类哲学问题和门类中最重“名学及知识论”这一项。因为他认定“每一部哲学史的最主要部分”就是“逻辑方法的发展”(12)胡适:《先秦名学史·前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5页。。于是,整本书的论述他都以名学为主要线索,各家各派都讲到名学。他说:“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伊文子有《刑名》之论:这都是各家的‘名学’。”(13)②④⑤⑥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44,21—22,16,20,21页。这就是打破了学派意义上的“名学”,使之泛化为中国哲学史一条主要发展线索。这是通过对名学的“泛化”实现“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的“纯化”。对“哲学”的“纯化”也是为了便于“哲学史”的纯化。
若单从“哲学史”的视角来看胡适所做的“纯化”的工作,可以从“审定史料”和“形成系统”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两点是胡适极为重视的。他在《大纲》的《导言》里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来谈“史料”问题。一共讨论了“哲学史料是什么”“史料的审定”“审定史料之法”“整理史料之法”四个问题,从理论到方法相当完备。为了“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在“史料”问题上胡适谈了四个操作性很强的步骤:“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②这其实就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蔡元培称赞胡适的《大纲》有一个“特长”就是“扼要的手段”“从老子、孔子讲起”,并且感叹“这是何等手段”(14)⑦ 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3,3页。。这事为什么那么不容易?据冯友兰回忆陈黼宸讲诸子哲学,一学期才讲到周公;据顾颉刚回忆陈汉章讲中国哲学史,一年才讲到洪范。此前讲中国哲学史的老先生们都是从远古传说阶段讲起,以表明中国哲学史的源远流长,而胡适一上手就从老子讲起,前面的全部不讲,这是需要胆量和魄力的,这给学生们也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胡适敢于这样做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老子之前的史料不够。他怀疑《尚书》的史料价值,只承认“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④。他讲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从《诗经》找材料的。很多后世的文献虽然讲到更古的情形,但大多是神话或传说,是当不得史料来用的,所以需要判别和审定。经过判别和审定的史料,然后才有整理的价值。而整理史料的方法,约有三端:一是校勘,二是训诂,三是贯通。校勘是整理本子,经过校勘的本子是研究最基础的材料。训诂是释义,是“字义上的整理”,是为了懂得书的真意义。而“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⑤。这就是要从对史料的整理而形成系统的研究了。这是胡适最用心之处。他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⑥这也是蔡元培在《大纲·序》中指出的胡著一大“特长”,即“系统的研究”⑦。梁启超也称赞:“胡先生专从时代的蜕变,理会出学术的系统,这是本书中一种大特色。”(15)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2页。从作为哲学史料的一部书的内容系统,到哲学家思想的系统,到一个学派的系统,最后到学派与学派之间的系统,都在胡适《大纲》的讲求之列。无论是“审定史料”还是“形成系统”,无非是要剔除掉一些不能作为史料运用的不必要的材料,剔除掉一些不能贯通的头绪,因而可以说这都是对于“哲学史”的“纯化”。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从“纯化”开始的,这不只是说他写作《大纲》时先对“哲学”和“哲学史”作了一番界定和“纯化”,而且从他的为学历程来看,也是从“纯化”开始的,有一个从“纯化”到“泛化”的过程。这一泛化的过程并不是说胡适增加了论述的对象,扩大了论述的范围,比如相对于《先秦名学史》,《大纲》增加了论老子、孔门弟子和杨朱专章,加重了论述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各个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古代哲学的终结等这些外在方面的分量,而是说扩大了哲学内部以及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史方面的论说。扩大了哲学内部的论说,是指由《先秦名学史》中的只谈名学、逻辑史,扩大到了兼谈宇宙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等。这些扩大的内容并非每一方面都会在某一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那里谈到,是根据哲学家思想的实际情况来谈的。而且不只是简单地增加一些内容,还论述了这些哲学内部方面之间尤其是与哲学方法这一主线之间的关系。比如,他论及老子,以老子为名实之争这个问题的最初提出者,老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是“无名”,基于这种方法,所以他的天道观是天道无知、无意志,道即是无,无即是道;他的政治哲学是无为主义;他的人生哲学是无知无欲和不争主义。于是老子的哲学各个方面成为一个系统。对于其他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论述亦是同一体例,以哲学方法为核心,泛化到哲学其他方面的内容并构成系统。
而所谓“扩大了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史方面的论说”,是指扩大了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叙述,并且明确地揭示哲学家的思想是如何从这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衍生出来的。比如他论及孔子说:“要懂得孔子的学说,必须先懂得孔子的时代,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情形既是如此‘无道’,自然总有许多‘有心人’对于这种时势生出种种的反动。”(16)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56,57页。也就是说针对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形,形成不同的思想主张和派别:一是极端的破坏派,比如老子、邓析;二是极端的厌世派,比如那些隐士;三是积极的救世派。孔子就属于第三种。“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地奔走,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懂得这一层,方才可懂得孔子的学说。”②所以,孔子的思想就是要认识到这种“无道”的情况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这样的,然后想办法“变”无道为有道。所以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因为《易经》是从讲“变”的学问开始的。虽然以《易传》为材料讲孔子的根本思想根据不足(17)自从北宋欧阳修质疑孔子作《易传》,后世一般都不以《易》讲孔子思想,而胡适却以《易》讲孔子思想,也未对文献作考察和说明。在这一问题上,胡适似乎并未认真贯彻他在《导言》里讲的“审定史料”的要求和方法。,但是胡适确实立足于社会文化史谈出了孔子哲学的条理来。这就是上文谈到的萧萐父在论及“哲学史研究”的“泛化”时讲的“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
实际上,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泛化”并没有停留于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而且还泛化到了一般思想史和学说史。完成《大纲》之后,胡适相继完成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18)参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六册说明”。。不过很遗憾的是,他把哲学史与思想史完全割裂开来,他不愿意用“哲学史”之名。这不是胡适偶然为之,而是经过了比较深入的思考的自觉意识。胡适的学问有一个从文学到哲学再到史学的过程。在研究和写作“中国哲学史”期间,有人对胡适从文学领域转向中国哲学史,从提倡革命,扫除旧思想,为新文学开路,忽然停住转向故纸堆去编哲学史,感到不理解,认为他是丢开了更重要的工作,而去做不那么重要的事。正是在这种对他的文学和哲学研究的比较和对于转向的质疑声中,胡适表达了自己对于治中国哲学史在现代中国乃“开山”的自信(19)参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之《附录一:西莹跋语》,《胡适文存》三集卷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第118—121页。。这是1927的事。可是到了1930年代,胡适居然提出要取消哲学系,宣扬哲学的破产(20)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1页。。任继愈先生于1934—1938年就读于北大哲学系,晚年他也有回忆:“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21)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早在1929年胡适在上海大同中学演讲《哲学的将来》中,他就提出了“哲学的根本取消”,说“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证实方法”。“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若不如此,但他们不是将来的思想家,只是过去的玄学鬼。”(22)胡适:《胡适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8页。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角度,来提倡科学而否定哲学,实际上在1920年代初的科玄之争中,从胡适对丁文江科学派的支持就已经有了先兆。除了出于对哲学与科学性质的看法,胡适还认识到自己才性之所在,不适合做哲学研究。他讨厌哲学的玄思,喜欢做具体的考证。这是与他早年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脉相承的。他对自己这一偏好的认定也有外部的机缘。1926年8月傅斯年曾经写信给胡适,说他写的《哲学史大纲》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倒是小说史考证,才是第一流的著作。然后也谈到中国人没有“哲学”,只有“方术”,用“哲学”讲中国的思想是错的。他说陈寅恪也是这个看法,不能用伦理学、本体论、知识论去讲中国的东西。凡用这些去讲,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有增减(23)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第43—52页。。由于这种种内外的因素,胡适慢慢转到纯粹的史学研究和具体考证,并且宣称自己是思想史家,不是哲学史家了(24)胡适著,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页。。近年,王汎森对胡适的这一转变的历程有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考(25)王汎森:《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5—13页。。
胡适从哲学史向思想史转变,并且否定哲学和哲学史,是很遗憾的事。假如他能够继续研究哲学史,一定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做出更重大的贡献。实际上,这也是由于他没有认识到哲学史研究中“纯化”与“泛化”的关系造成的。他一心想对中国哲学史作“纯化”的研究,但回头又发现这不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本没有这个系统,只是思想。实际上,不加增减地复述中国哲学史既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如果完全做成西方哲学式的概念范畴推演,也不是中国哲学史。所以,从思想史的意义上泛化哲学史的研究对于表现中国哲学史本有的特点也是有必要的。也就是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以及这门学科,它一定是“纯化”与“泛化”相交融的,不能否定任何一方。胡适做“中国思想史”,其实已经在做“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泛化”工作,只是他没有认识到这一工作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及这门学科的意义,他只是简单否定了这一工作具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性质。他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也没有多大影响,可能与他不再注重哲学、理论,是相关的。他后来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
三、“纯化”与“泛化”及其交融: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成立与发展的前提
可以说,“纯化”与“泛化”及其交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能够成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不对中国哲学史做“纯化”的工作,中国哲学史学科不能成立。不对中国哲学史做“泛化”的工作,很难说这样的中国哲学史是充分体现了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哲学史。不使“纯化”与“泛化”相交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就很难走向深入,很难走得长远,很难推动中国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一学科,也就没有相应的哲学这一学科所要求的对象和范围。所以,我们要成立一门新的学科,就得按这门学科的基本要求来做,否则就不叫“中国哲学史”。这一点蔡元培、胡适和冯友兰等等都是有自觉意识的。冯友兰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2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选出而叙述之”,实际上就是做“纯化”的工作,不做这项工作,这个学科就不能成立。
关于“纯化”工作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原因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受‘等级的阶级’关系的制约,基本上没有从包罗万象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分化出来,和宗教神学、伦理政治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够清楚明朗……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带来难以‘解脱’的‘苦恼’和‘麻烦’。”(27)周继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第67—68页。实际上,中国哲学史研究需要“纯化”的原因并不在社会形态的决定,而在我们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本身成立和发展的需要。西方的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同样经历了“纯化”的过程,从“爱智慧”到“形而上学”再到“本体论”。西方哲学这一过程,都是在封建社会期间完成的。所以说,中国哲学没有分化出来,原因不在于社会形态的束缚和制约,而是与古代中国思想本身文史哲不分家、逻辑性的体系不明显等特点相关。这些特点是有利有弊的。进入现代,分科而治,各作“纯化”,实有利于我们理清本土思想的内容和线索,对以往的思想达到某种程度的自觉。中国确实没有西方哲学那样形式上的系统,但是确实有西方哲学那样的实质性的哲学问题。确如冯友兰先生19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之《绪论》中谈到的:“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2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0页。张岱年以为此说乃“不刊之至论”(29)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自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8页。。因而,把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梳理出来,正是使我国本有的思想在现代走向某种程度的自觉,是对中国本有思想的发展,而不是割断或扭曲。1923年,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说:“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30)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3页。。这个截然的断定当然也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必要成立“中国哲学史”这样一门学科。
要从中国古代庞杂的思想材料中梳理和“纯化”出中国哲学史来,非用现代西方的学术方法不可,否则难以理出一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系统来。西方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源头之一。胡适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他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31)⑦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6,3页。所谓“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是说我们的思想材料经过了清人的考据和整理,而变得可读,可作为史料来运用。所谓“西洋的新旧学说”,旧学说指历史以来的哲学这门学科及其思想内容,新学说则当时西方新的学术方法,尤其是历史学的方法和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即使是“实用主义”,其实胡适用的也是其方法,而非具体的哲学主张。金岳霖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撰写的《审查报告二》中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3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437页。以至于胡适注重对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思想之“效果”评判,在金岳霖看来也是哲学的“成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胡适是把实用主义当方法来运用的。他当时称实用主义为实验主义,他说:“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33)胡适:《胡适文存》卷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212—213页。蔡元培在给胡适《大纲》的序中称赞的“证明的方法”即是实验主义的“实验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即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态度”。胡适所强调的进化论,其实也不过是“历史的态度”中“历史进步”这一个维度而已。而关于思想“效果”的评判,也与实用主义“真理”的主观性这一主张是有距离的。他说:“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⑦可见,胡适所谓“效果”恰恰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态度,是要把某一学说思想的历史影响揭示出来,而不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任意批评古人,或者美其名曰“价值重估”。可见,运用现代西方的学术方法来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料,梳理和纯化出一部中国哲学史来,是形成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必由之路。
以“纯化”的方法建构起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这门学科所呈现出的系统毕竟也是建构出来的,是无法一眼就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思想材料中看出来的。难免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让人觉得这样一种哲学史失掉了中国古代思想本有的特点。胡适由“哲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也有见于此。实际上,哲学史是可以泛化到思想史、文化史上来获得理解的。牟宗三对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曾有过如此论述:“文化之范围太大,可以从各角度,各方面来看,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哲学可以做庞大的文化这一综和体的中心领导观念。”(34)②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1页。这就是把哲学当作文化的核心,当作文化各部门综合体的核心的推动力量。“故欲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开始时可以散开地由各方面来看,从各方面向内凑,如从文学、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凑到核心,还是个哲学问题,这一种讲法可以说是归纳的讲法。哲学地言之,也可说是一种现象学的讲法,即由文化各方面做现象学之分析与描述。”②牟先生是从了解“文化”的角度谈到这一讲法,即由文化各方面往处于核心处的哲学凑,这意味着不了解到哲学这个核心,就不能真正了解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反过来,从了解“哲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不从哲学往文化的各方面去理解,不了解哲学对它们的影响,那么就不能真正理解哲学。如果应用到对于哲学史的了解上,从文化史来理解哲学史,其实正是萧萐父所谓的哲学史研究的“泛化”。
萧萐父进一步指出:“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或由博返约,或由约趋博,或纯化,或泛化,或微观,或宏观,或纵向,或横向,都可以‘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而只有经过这样的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中的反覆加深,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思路、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35)萧萐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6期,第3页。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哲学史的写作是多元的,通过多元的书写,或纯化、或泛化、或微观、或宏观、或纵向、或横向,种种写法都可以,如此才会尽可能丰富地表达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多的内涵,尽可能呈现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本有的特点。这样一来,无论是以西方哲学为蓝本,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两个对子为指导,无论是纯形上学、概念范畴史,还是注重哲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相互关系,这些哲学史或思想史都代表了当代中国人在某一时期对古人思想的理解,只要用的是古人的思想材料,方法是客观的历史的分析,那么它就是“中国的”,不会是“西方的”,都有其价值,不应一概否定。二是在同一部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中,“纯化”与“泛化”不应该是割裂开来相对立的,它们应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此写作出来的中国哲学史才会是有深度的,考虑周全的,才会真正具有典范的意义。不是说某部哲学史只是“纯化”,某部哲学史只是“泛化”。没有“泛化”的“纯化”是空洞的,没有“纯化”的“泛化”是浅薄的。未来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运用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的方法,使两者交融,如此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