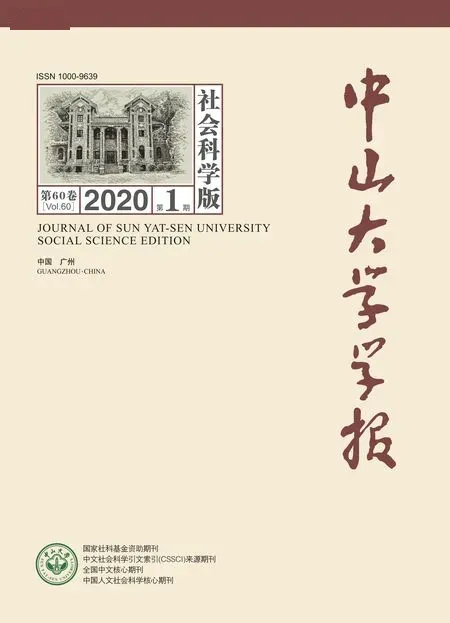清代农作物交流与四川山地民族交融*
2020-02-19秦和平
秦 和 平
问题的提出
清代前期,番薯(甘薯、红苕)、玉米与土豆(马铃薯)三种外来作物相继传入四川民族地区(1)卢勋、李根蟠认为:“我国的玉米可能是从缅甸传进的,我国最早种玉米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这在玉米的别称中也反映出来……西南地区的小苞谷是当地原生植物,西南高原也是玉蜀黍原产地之一。”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51—52页。。这些作物适应了当地的土质、气候及水源等,产量较高,优势明显,省力且方便,加工食用较便利;再因地方官员的鼓励或引种,各地普遍种植,“黑谷垂垂白未包,神仙谷子满山坳。高坡洋芋低坡薯,如此荒年莫浪抛”(2)谭文锴:《竹枝词》,丘良任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五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575页。,成为民众的主要粮食。番薯、玉米或土豆的高产提升了种植业收益,农业地位上升,逐步替代采集兼狩猎的传统经济而成为主要经济业态。然因番薯等作物富含淀粉,保质期短,为消化及利用,促成酿酒等行业兴起,加工及再加工,延长了作物的产业链。种植番薯等作物,食物增多,加快人口增长,有限耕地难以承载,不断溢出“移民”,移动带来交往,交往则促进交融。
番薯、玉米及土豆引种四川民族地区
(一)川东南民族地区
四川东南部(今重庆东南部)是土家、苗及汉族共居的多民族杂居区,番薯、玉米及土豆从毗邻的湖南及湖北传入。
康雍年间,番薯、玉米及土豆传入了湘西、鄂西,因产量高,适应面广,果实、茎及叶片可充分利用,人畜皆食,种收方便,受到汉、土家及苗等各族民众的欢迎,影响到川东南地区。乾隆三十五年(1770),福建闽侯翁若梅担任黔江知县,时值地方灾荒,颗粒无收,民众乏食,嗷嗷待哺。翁若梅采取开仓赈灾、捐赀购粮等方式展开救济,于是黔江“嗷嗷之众,渐次安集”。为避免缺粮困民,实现长治久安,需要种植高产作物,增加食粮。翁知县环顾周边地区已引种番薯,“即以蜀中论,子不见西南诸壤翠叶紫茎累累而秋实者,非薯乎?不择地而生,不择时而生,故曰救荒第一要义也。宜于天下独不宜于黔乎,待命于天,不早为之备,非智也”。考虑原生地引种的优势,翁若梅从福建带来番薯种藤,以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为范本,亲自传授种植、加工及储藏方法,要求地方士绅带头引导民众种植,“自南徂西,施于巴蜀,我树其苗,黔阳之曲”(3)张九章等:《黔江县志》卷3“食货志”,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第26页B。。因地方官引种及示范,番薯在黔江广泛种植,成为当地的大宗作物,还传至毗邻的秀山、酉阳、石柱及彭水等地,“薯本菜类,而贫民以代谷食,山原遍种之,土亦最宜”(4)⑩ 王寿松、李稽勋等:《秀山县志》卷12“货殖志”,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第1页B,1页B。。
“黍名玉蜀满山岗,实好实坚美稻粱。割尽黄云看陇上,秋风送入酒泉香。”(5)张梓监纂,张光杰纂修:《咸丰县志》卷18“艺文志”,同治四年(1865)刻本。引自郭松义、邓自燊编:《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清史资料》第7辑,第147页。乾隆前期,玉米也从湘西、鄂西传入酉阳等地,“包谷则普种,然不可久藏,故无以为积贮计”(6)邵陆修等:《酉阳州志》卷1,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第19页B。,因产量高而受到各族民众的欢迎,引进种植。“玉蜀黍,俗呼包谷,深山广产,贫民以代米麦”(7)《补辑石柱厅志》卷9“物产志”,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第2页A。,逐步替代荞麦、高粱而成为民众的主食,“山地最多者包谷,以其根大易长,人食有余,即可酿酒饲豚,岁计收成分数”(8)王槐龄纂修:《补辑石柱厅志》卷6“风俗”,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第3页B。注,补辑厅志者特别声称:“此《旧志·物产》语也。”(旧志指乾隆四十年(1775)王萦绪纂修的《石柱厅志》)藉此记载,得知玉米至少在乾隆中叶前传入渝东南山区。。《土家竹枝词》有道:“木叉架屋竹编墙,累石涂泥作火床。出臼新炊包谷熟,全家齐坐火池旁。”(9)郑虎文:《土家竹枝词》,王利器、王慎之等编:《历代竹枝词》第2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2页。诗注:“家中累石如北地之坑然,名曰‘火床’。火床之正中为火池,以供炊爨,不食米麦,以露粟为粮,俗名‘包谷’。”诗句形象描述土家农民围坐火塘啃食玉米,其乐融融!道出了玉米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
接着,土豆也随移民流动而传入川东南地区。不同于番薯及玉米的生长机理,土豆结实地下,喜阳而耐寒,往往种植高山区,“洋芋,相传种出西洋,宜高寒之地,邑(彭水)山箐不生诸谷者,多莳以充食”(10)庄定域修,支承祜等纂:《彭水县志》卷3“风俗”,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67页A。。因种植土豆的缘故,带动了川东南高山区的开垦。
番薯、玉米及土豆虽系外来作物,因产量高、用途广而受到各族民众的欢迎,变“洋”为“土”,成为当地的基本农作物。因生长机理的缘故,番薯、玉米及土豆各有适宜生长结实的“优势”区域:番薯适宜种植丘陵及低山区,玉米适宜中山区,土豆适宜高山区。种植区域的差别,使这三种作物呈现垂直分布、遍地种植的格局,拓展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民食稻米而外,包谷为大宗,兼以酿酒,贫富利赖山野,居民多种番薯、洋芋,或掘厥粉以备食用之不足。”(11)张九章等:《黔江县志》卷5“风俗志”,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第46页B。“薯本菜类,而贫民以代谷食,山原遍种之,土亦最宜。”⑩困扰各族民众的粮食短缺得到缓解:“洋芋,蔓生叶,稍类蓝,山后广植,冬种夏初掘食,芋大如胡桃,皮薄而多面质,能疗饥山民,用济半岁之粮。”(12)杨应玑、谭永泰、刘春之编:(光绪)《石柱厅乡土志》“格致”第12节“洋芋”,第28页B(姚乐野、王晓波主编:《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可是,番薯、玉米或土豆的粒大量高,成熟期集中,若不及时处置,形成“剩余”,将腐烂变质,如何有效地消化它们呢?
(二)凉山彝族地区
彝族聚居川西南地区,当地年均气温较低,雨旱季分明,俗称凉山,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因之称为凉山彝族。凉山以黄茅埂山脉为界线,黄茅埂以东称小凉山,以西称大凉山。除个别杂居区外,凉山彝族基本上不种植番薯。
1.玉米传入及扩展
玉米传入彝区在乾隆前期,从东、北及西三个方向并进(13)玉米传入我国的路径,云南是重要的通道,明隆庆《云南通志》、嘉靖《大理府志》等志书均有记载。凉山彝区毗连云南,玉米从云南传入亦有可能,因无清初的相关资料证明,不便论证。,经杂居区而传入腹地,遍及彝地:(1)东边,以乾隆十九年(1754)《屏山县志》记载玉米为最早(14)刑科提本反映,乾隆十九年农民李盛占受曾仲常雇用,来屏山“做短工,帮种包谷,讲定每月三钱银子,没有写立文约”。《刑科提本·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引自郭松义等编:《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清史资料》第7辑,第72页。,知县张曾敏吟诗称赞:“山中绝少水田耕,那识嘉禾有玉秔。终岁饔飧炊握粟,同为粒食太平氓。”(15)张曾敏:《马湖竹枝词》,《四川竹枝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1页。诗注:“‘握粟’,山中谓包谷。”说明玉米在当地已广泛种植,成为民众的主食。屏山系小凉山地区,是汉彝族杂居区,玉米已广泛种植,意味着引入大凉山腹地只是时间问题。(2)西边,乾隆四年(1739)《雅州府志》记载荥经已种植玉米。荥经毗邻汉源,汉源也是汉彝杂居区,接壤大凉山区,传播甚方便。(3)南边,乾隆末年《会理州志》物产篇记载“御麦,俗名包谷”(16)曾濬哲修,严尔譓纂:《会理州志》卷2“物产”,乾隆乙卯年(1795)刻本,第50页A。另,(嘉庆)《宁远府志》(佚名,1960年油印本)“物产志”记载有“玉麦”,说明玉米已在包括会理州在内的宁远府范围广泛种植。。三部志书均反映乾隆初年玉米已在彝汉杂居区广泛种植。

大凉山与小凉山间隔黄毛埂,玉米的“翻越”只是时间的早晚。关于大凉山区何时种植玉米,彝民有这样的传说:
金阳县有个黑彝家支阿大家的人,看见汉人种的包谷,他就去偷。但他不懂得包谷哪部分可吃,他就偷来一些包谷穗穗。煮来煮去不能吃,就说这是不能吃的东西。后来,有一次他看见汉人在摘包谷,才知道是谷包包,于是又去偷来一些包谷包包。在剥包谷外壳时,他说这个东西穿那么多层衣服,这一定是皇帝女儿吃的,所以后人都称包谷为“皇帝女儿饭”。这个人的后裔,至今已传至第十二代。(19)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1963年,第54页。
这段传说反映玉米是从彝汉杂居区引入彝区腹地(大凉山)的,该传说搜集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斯时阿大家已传了十二代人。我们暂以每代人间隔20年,十二代人约240年,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上溯200余年,是18世纪初。据此,我们保守推论至少在18世纪中叶,即乾隆中叶,玉米已传入大凉山区。
当玉米传入后,彝民积极种植,魏源说:“四川野夷在万山之中,越巂、峨边、马边、雷波四厅,汉地环之,惟西南隅雷波、建昌之间,可通云南,东南自雷波西北出越巂,袤长约千三百余里,广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四面皆峻岭老林,绝无门户,必翻大山然后入,一入其中,即多旷衍,产青稞、包谷、油麦、苦荍、萝卜、红稻,以多畜马、牛、羊为富。”(20)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下册)卷11“武事余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3页。注,魏源说这些资料是叙州(宜宾)知府谢兴尧讲述的。道光年间谢兴尧曾带清兵进入凉山彝区腹地。道出玉米在大凉山彝区的种植情况。
因玉米从多地引入,致使彝区玉米存在多个品种,包括“白玉麦(本名玉蜀黍,一名包谷,又名木禾)、黄玉麦、红玉麦、花玉麦、九子玉麦”(21)马忠良修,马湘等纂,孙锵等续修:《越巂厅全志》卷3之二“物产”,光绪丙午(1906)刻本,第1页B。。多品种意味选择的余地大,适应不同环境,能满足生活在不同区域彝民的种食需要。稍后,伴随凉山彝民的持续西迁,玉米也向西传播,遍种西昌以西及云南宁蒗小凉山区。
2.土豆传入及扩张
清代中叶,土豆也传入凉山彝区,但传入路径相反,从云南传入(22)土豆从云南方向传入是凉山彝民的共识,传入的品种不止一种。关于这问题,参见《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相关部分(第54页)。经会理北向传播进入凉山。西昌民间传说:
洋芋即马铃薯,居民以其来自西洋,故呼洋芋。传入宁属之年代,约为清代中叶,由法天主教司铎自滇省携入之。又有谓行经西藏而传入者。清末,有英人基督教牧师,初由昆明来会理设教会,即购运十数马匹驼洋芋而入,及抵会理,乃知会理每百斤价值仅昆明价值之半,足见宁属洋芋之多且廉也。(23)⑤ 李明良:《四川宁属农牧调查报告》,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第21,22页。
检索地方志书,同治《会理州志》记载“洋芋”,志书撰修者还注明:“或作羊芋,烧、煮皆可食,又可为粉。《本草》所谓土芋,一名土卵者,未知是否此物。”其中“烧、煮皆可食,又可为粉”,反映加工及食用土豆多种多样,说明种植较久,群众掌握习性,多样方法能变换口味,拉近食品“亲切感”,避免单一食用法产生的“烦恼”。土豆有耐旱喜阳、抗寒避噬等特点,适宜高海拔区种植。“盖高山气寒,豌豆生长不多,而洋芋特宜生长,宁属夷民无一日不以洋芋为食品,即汉人之种植者,亦占四分之三,盖以稻田缺水,即不栽秧,包谷缺雨,收量必微,惟洋芋一项,即久晴不雨,亦可有收”⑤。查《会理州志》镌刻于同治九年(1870),但搜集资料及编纂应早于该时段,我们认为最晚在同治初年,即19世纪中叶土豆已传入会理彝区。
不久,土豆经会理向北向西推进,传至气温较低的高山彝地。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记载彝区土豆产量高,有“剩余”售卖。“黑彝一种,生于冷山寒谷之中,居于深箐峻岭之上,性情顽野,好食生物,身穿褐布,背披长毡。男则编竹篾以赴市,女则卖洋芋以营生。其强健者以抢劫为生,以偷盗为乐,婚配皆通媒妁,以牛羊为聘,死则火化,置之深山,不许人知”(24)叶如桐、秦定基修,刘必苏等纂:(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卷7“土司志”,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第36页A。另,乾隆三十年(1765)刊刻《永北府志》卷10“物产”记载“芋(紫、白二种)”。不知这里的紫色芋是否是彝民种植的紫(皮)洋芋?如果是的话,土豆(洋芋)传入凉山的时间则会提前。。永北直隶厅(今宁蒗、华坪)与四川盐源一江之隔,当地彝民从盐源迁入而繁衍,因他们来源凉山,其居住地俗称“(小)凉山区”,亲戚往来,相互走动,从四川彝区引种土豆也就顺理成章。
彝区北部雅州(安)府宝兴县,种植土豆时间要更早些。19世纪初(嘉庆年间),天主教传教士引进了土豆,种植穆坪等地(25)1869年3月1日法籍神父戴维在日记中记录:“穆坪的学院建于五六十年前,当时中国对西方宗教迫害甚烈,传教士不得不向蛮族领袖寻求庇护……不久,基督徒和其他汉人就跟着传教士前来,并得到当地管辖者的许可,在此耕作,遵守特殊的条件和缴纳税捐,渐渐山谷就转变为汉人风貌,引进汉人的农耕法。传教士又从欧洲输入马铃薯和包心菜,这两种作物直到今天,仍是山区居民的主食。” (孙前:《大熊猫文化笔记》,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年,第103—104页)从1869年前推五六十年系19世纪初,即嘉庆中叶,穆坪修道院建立于此时,法籍传教士引种土豆也大致在此时期。。汉源、石棉等彝地在清代隶属雅州府,出于对高产食物的追求,彝民引种也很正常,因而我们不会排除土豆从宝兴、汉源等地引入彝区,时间可能不晚于会理的同治年间。光绪年间,雷波、越西等地志书均记载土豆,说明19世纪末土豆传遍大小凉山。
在彝区,土豆适宜种植在海拔2 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山多田少,宜种苞谷,其最高者则宜阳(洋)芋、荍麦”(26)秦云龙修,万科进纂:《雷波厅志》卷32“风俗志”,光绪十九年(1893),第1页B。。彝民还采用羊粪积温保育的种植法,延长了土豆生育期,保障并提高产量。此后,土豆、玉米成为彝民的主食,燕麦等传统作物被迫“让位”,仅作补充食材而已。
(三)川西藏族地区
藏族聚居川西高原,内分甘孜及阿坝两个地区。乾隆年间,玉米随移民带入,在甘孜藏区打箭炉(今康定)等地种植(27)乾隆六十年(1795),打箭炉(今康定)已有贩卖包谷(玉米)的记载,见《刑科提本·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引自郭松义等编:《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清史资料》第7辑,第76页。。嘉庆年间,玉米在阿坝藏区绥靖(今金川)等地种植,“玉蜀黍一名玉高粱,一名戎菽,一名御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出西番,旧名番麦,《农政全书》又作玉米”(28)李涵元修,潘时彤纂:《绥靖屯志》卷4,道光五年(1825)抄本,第6页B。。这段记载说明玉米来源境外,经内地传入藏区。接着,玉米从打箭炉、绥靖等地向西扩张,传入川西藏区腹地,种植河谷农耕区(29)川西藏区海拔虽高,因系横断山脉,金沙江、雅砻江及大渡河等因山形而南北流向,夏季印度洋暖湿气流能到达这些江河的河谷地带,“故其气温,与内地相差无几,凡属农地,皆在此部”。反之,东西方向的河谷则寒冷些。任乃强:《西康图经》,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18页。。(光绪)《定瞻厅志略》与(光绪)《炉霍屯纪略》均记载了玉米,说明玉米于18世纪中后期传入,19世纪后期已在川西藏区广泛种植。
玉米根系发达却扎土浅,“拉”不紧土层,致使表土松散,而藏区山高坡陡,夏季雨量大,冲刷强,曾有官员担心种植玉米会加剧水土流失,造成危害,下令禁种。不过,后任官员转变了态度,鼓励种植,以获得更多粮食,供养更多人口。如瞻对(今新龙)等地,“惟田谷之青稞,则夷民恃以为命,作糌粑度日者也。小麦,亦兼食者也。豌豆、蚕豆半作食用,半喂养畜牲者也。菜子则打油,以供官用者也。包谷亦出,然前禁不准种者也。菜蔬则羊芋、菜菔、圆根。圆根,用处最多,人畜皆食,种者甚多。葱、蒜苗、白菜、莲花白,则汉民种而食者也”(30)张继:《定瞻厅志略》“物产篇”,光绪抄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第12页。等等,道出玉米等作物的种植状况。
与玉米比较,土豆的引种稍晚些,(光绪)《定瞻厅志略》及《炉霍屯纪略》也有记载,称“羊芋”,列入物产类,说明19世纪末两地广泛种植。《巴塘盐井乡土志》(今西藏芒康县盐井乡)关于土豆记载更清晰:“西岸,则黄豆、包谷近亦兼种,而出产无多。近年察其土宜,惟羊芋、麻子、菜子三种,业经试验成熟,不劳粪壅又省人工。羊芋,则觉陇、列丁遍山皆可种植。此物如遇荒歉,大可救饥。麻子、菜子,则尤为关外所乏,如能推广栽种,则麻布、麻索、清油均可就地成业。”(31)段鹏瑞:《盐井乡土志》“树艺”,宣统抄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9年油印,第9页。土豆(羊芋)为何在高海拔藏区遍山栽种呢?原因是土豆茎块长在地下,根系深扎土壤,基本不松动表土,造成水土流失,且藏区日照长,昼夜温差大,产量高,除受到民众欢迎外,地方官员也引进推广。清末德格同普(今属西藏江达)知事创办农业试验场,引进新作物,采取新技术,“教民播种”,鉴于土豆“耐寒,宜于高原沙地,三月下种,七月成熟,不惧风霜”,优势明显,从内地引入种苗,试验选择,用高产实效而向民间推广(32)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88页。。
玉米、土豆增大种植业收益,增添了民众的食物,在传统的酥油茶与糌粑外,有了“饼”状食物,为移民留驻藏区提供食物,促进流动,带来了族际交往。
番薯、玉米及土豆对四川山地民族的作用及影响
农作物之微,非小微也!番薯、玉米等外来作物引入四川各民族地区,优势明显,致使原有作物构成、种植方式、劳力使用或饮食习惯等发生改变,民众因种植番薯、玉米或土豆而“蒙福”,效率明显,还产生系列“连锁反应”。
(一)对土家、苗等族的作用及影响
1.发展加工业及副业
种植番薯、玉米及土豆,优势明显,产量提高,食粮增长,人口发展,催生食品加工业,发展了桐油、桑蚕等副业。
历史上,当地土司控制土家、苗等民众,以“峒”为单元,封闭统治,“峒”土为份地,计口授地,属民领份地,听从调遣,劳役伺候,“更喜不闻征税吏,薄田微雨即年丰”(33)顾彩撰,高润身等注释:《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1页。。雍正年间,清政府改土归流,废土司设衙门,施以直接统治;取缔封锁,开放山区,移民涌入,族群交往,番薯、玉米及土豆因移民携带或官府引种而传播。当地土家、苗等民众迅速接受,广泛种植,替代荞麦、燕麦及高粱,成为基本作物。食物的相对丰裕,带来人口增长。而持续增加的人口,不断超过耕地的承载量,地满人溢,除少数人外迁他乡,辗转垦殖,成为“新移民”,更多人则转向经济林木、副业或运输业等,从事经营,“近年,山地有种膏、桐、漆、枲者,获利稍厚”(34)庄定域修,文承祜等纂:《彭水县志》卷3“风俗·民俗”,光绪元年(1875)刻本,第63页B。,新产业转移劳力,增加入民收入。
玉米、番薯与土豆均富含淀粉、糖等成分,若不及时处置,易吸湿而霉变或发芽,如玉米,“其性逾岁必生虫,民食有余,即不酿酒喂猪,亦不可久贮”(35)吉钟颖等:(道光)《鹤峰州志》卷6“风俗志”,道光二年(1822)刻本。引自郭松义等编:《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清史资料》第7辑,第143页。。番薯虽用地窖储藏,保质期仅半年。土豆多摊在房内敞放,一两月因吸湿而发芽。短促“保质期”促使人们考虑如何尽快加工,转化为其他产品,转移以至增加价值,便催生酿酒、腌制等行业兴起,就地加工延长了作物“产品链”,传递以至增加价值。
种植玉米、番薯或土豆缓解了当地粮食匮乏,影响所至,有些人不再种粮而因地制宜,转向种桑养蚕或种桐榨油等林木或药材,新辟了收入,更推动桐、茶、油或药材等副业的发展,桐油、茶油、黄连及猪鬃等因地理适宜、量多质高而成为主产品。市场交换进一步改变旧有封闭状况,以封锁为标志的土司统治的终结成为时间问题,即便清政府不废除,土司统治也难以持久!辗转收购、长短运输农副产品,活跃了山区经济,带动交换,消化了富余劳动力;互通有无,川东南山区与湘、鄂、贵等地商品交换频繁,构建了交融共生关系。
2.促进交往,人口增加,“新”行业消化“富余者”
番薯、玉米及土豆等由移民或官员引进,当移民定居后,会与土家、苗及汉等“土著”交往交流,如秀山“设县以后,吴闽秦楚之民悦其风土,咸来受廛,未能合族比居,故颇杂五方之俗。其土著大姓,杨氏、田氏、吴氏、彭氏、白氏,或千家或数百家,亦皆错互散处,至其通族共事,相互亲睦,乃雍然有古风”(36)王寿松、李稽勋等:《秀山县志》卷7“礼志”,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第10页A。。移民与土著彼此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改进种植方式,提高技艺,改变“农不知粪,圃亦不知粪,故园蔬瘦小,蔬不肯嫩采,果不待熟鬻”的旧俗(37)王槐龄等:《补辑石柱厅志》卷6“风俗”,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第3页B。,施肥剪枝,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交往促进融合,致使川东南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如秀山县,乾隆九年(1744)统计1 570丁,“丁”既指成年男人,也指承“粮”的家庭单位(户),也是1 570户。按五口之家计,全县不到万人。同治年间,秀山已有41 824户、28.4万余人(38)王寿松、李稽勋等:《秀山县志》卷5“赋税志”,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第2B—3B。,百余年间人口增长20余倍。人多消耗多,过大消费容易造成贫困,“数十年来,滋生日蕃,流寓亦日集,而民贫愈甚”(39)王槐龄等:《补辑石柱厅志》卷2“田赋”,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第3页B。。摆脱贫困就要加大开发领域,压力迫使部分人种植经济作物或发展加工业,外销交换,藉市场交换增加价值;并为加工企业或商铺提供原料,服务加工或贩运业,转换价值,实现增值,转移劳力,消化“富余”者。
(二)对凉山彝族的作用及影响
1.加快“家支”分蘖,“打冤家”等推动人口移动
引入土豆及玉米后,彝民利用乡土知识调适了种植方式,发挥出作物的“优势”,尤其是土豆,块茎大,产量高,亩产数千斤。高收益提升了农业地位,种植业替代采集兼畜牧混杂经济而成为彝地的主要经济类型。
当种植业成为经济主业后,土质、水源及气温等成为影响作物丰歉的重要因素,收成改变了彝民的认知:从轻视土地到重视土地,过去“夷不能酿而性耽于酒,汉人作奸者,因以酒诱之。始则以酒易其粮食,而昂其酒价;粮食既尽,则赊与之,而笔之于簿。夷人不识汉字,又值醉后,一任汉人之登记也。久则多而不能偿,乃令夷人以地相准,仍浼汉人书券。山多未开垦者,夷人亦不甚惜,往往以数石酒作银数十两,而数十里山冈尽入卖契之中,夷人亦绝无后言”。丰产的玉米及土豆体现了耕地的价值,彝民重视了土地,“嗣后,夷人渐知自爱其土,亦不肯受汉人欺弄”(40)刘文蔚:《雷波琐记》,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16页AB。,“用酒换地”行为再不会发生。
玉米及土豆虽易种耐瘠、产量高,但非“懒”庄稼,种植、经营及收获也需要劳力。栽种越多,需要劳力也越多,对劳力的需求改变了彝民的生育观念,鼓励多生多育,重视男性。生育意愿变为社会舆论,推动人口持续增长。如凉山广泛传颂罗洪阿昧娶亲而得“福报”的故事,讲述了罗洪阿昧妻子木阿姐出嫁途中,因掩护野雉脱险得到“福报”。她嫁到罗洪家后生育了九个儿子,后代众多,家族强盛,扩张各地。编撰者搜集该传说时感叹:“倮夷中未闻有称道其祖宗某人功德或古代某人英雄者,余尝问以孟获其人,皆不知之,可见口传之故事无多,至仁爱道德,更不重视矣。独木阿姐释雉一事,诸夷以其不忍伤害一命之微,竟得子孙繁盛之报,至今艳称之,引为光荣历史。”(41)郑少成等修,杨肇基等纂:《西昌县志》卷12“夷族志”,1942年铅印本,第21页B。透过现象看实质,该传说反映彝民对后代,尤其是男性后代的重视,折射种植业对彝民生育观念的影响。
人口快速增长壮大了“家”(家族),分蘖频繁,“支”持续涌现。地域因人口增加而“拥挤”,躁动不安,人们因琐事纠纷而滋生矛盾,纠集家支成员展开械斗(“打冤家”)。与彝民迅速增长几乎同步的现象是,“打冤家”增多,规模扩大。胜者占地拓展,败者远走他乡,寻找新的栖居地。从清代中叶起,凉山彝区出现持续的迁移潮,“人住东方,往西方走”,大量彝民越过安宁河,进入九龙、泸定、盐源、木里及云南宁蒗、永胜、中甸及兰坪。
2.新作物带来新移民,改变清政府彝区政策
其实,番薯、玉米等作物也传入四川内地,时间更早些(42)四川内地,雍正初已有种植番薯的记载,乾隆初有种植玉米记载。,增产效果或许更明显,亦导致人口增长。有限耕地难以容纳,一些人被迫外移,寻找栖身处。“穷走夷方急走厂”,他们便向凉山彝区迁移。如会理等地,“嘉庆初年,黔省洊饥,蜀疆多寇,民情浮动,喜于迁移,男携女负,十百为群,不数年,新户增至八九千家矣。饥饱相形,勤惰互见,或以梯山以作田,或滨河而谋产,垦地焚林,其利十倍。莳烟种蔗,其利百倍,居民日以困,流民日以饶。昔日之膏腴,而今为沙砾矣;昔日之刍牧,至今而为禁地矣。于是,木穷于山,鱼穷于水,五金穷于八厂,百货穷于四门,不待鼓击旗开,有识者已隐忧之”(43)邓仁垣等修,吴钟崙等纂:《会理州志》卷7“边防”,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第19页B。。盐源“今则安集滋生,不巡而力,不召而来,汉民较番多逾十倍矣……昔患民少,今患民多。每岁中,自秦、楚、吴、黔及川东、川北来者以千计;自凉山迁入者,倮夷以百计”(44)辜培源等修,曹永贤等纂:《盐源县志》卷3“食货”,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第1页AB。。嘉庆十六年(1811)总督常明饬令宁远府知府查勘彝地汉疆的界址,清理移民,“凡汉种夷地,无论佃当顶买,俱令呈验纸约、木刻,划清界址,载入册内,并散给门牌,编联填写。俾得互相稽核,一载有条。始得夷界、户口、地土遍查清楚。根据禀报,一律完竣,统计招有汉佃之土司土目五十四处,夷地内共有汉民八万七千六百八十九户,男女四十二万五千三百四十七丁口”(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四川常明奏折”。关于当时宁远府各县及各土司土目辖地清查移民的大致人数,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常明疏略”。。此次清理的42万余人绝非小数目!反映内地移民进入彝地的严重程度。
移民来到彝区,也需要耕地生产食物,求生存得发展。因垦殖或租佃土地等,少数移民不免会与彝民产生矛盾,当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便演成对抗,酿成武力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从嘉庆年间起,凉山彝区持续发生彝汉民众冲突的重要原因。为消除彝汉民众因争地而冲突,避免接触成为清政府的政策选项。四川总督常明便要求地方官员划分汉彝疆界,禁止移民进入彝地开垦或租佃;限制彝民外出,也不准招佃移民,用隔绝避免族际冲突,隔离便成为清政府管控凉山彝区的主要措施,直至清末。
其实,因土地争夺或租佃矛盾等导致彝汉民众冲突是少数。多数时候,彝汉族民众友好交往,互通有无,形成亲密关系。“彝人离不开盐巴,汉人离不开皮货”,彝地牲畜、皮革、玉米及药材等外销汉区,内地烟、盐、针线及布匹丝绸等运入彝地,甚至粮食也被彝民购买,“千袋万袋,不如上山羊皮口袋”。彝民接受、掌握并传播内地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及修筑塘堰手艺,提高了种植技术;彝民让其子寄拜毗邻汉民,“倮夷称仇人为冤家,称交好之汉区团绅为亲家,则有打亲家之俗。打亲家者,黑夷具礼物,以其子拜寄团绅为义子,谓之干儿子,呼团绅为干保爷,团绅须优予奖给,于是谊若姻亲,常出入其家”(46)郑少成修,杨肇基等纂:《西昌县志》卷12,1942年铅印本,第17页A。,结成“干亲家”关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彼此照应。
(三)对川西藏区的作用及影响
玉米、土豆增加了藏区,主要是河谷沟坝及交通沿线的作物品种,“较昔年物土大变,地献其灵矣”(47)刘廷恕:《打箭炉厅志》卷上“物产”,光绪稿本,甘孜州文化馆,1979年油印,第33页。。种植业发展促进土地垦殖。如炉霍虾拉沱,“光绪二十七八间,有法国牧师田养莜于此设立教堂,招夫开垦,得良田四千余亩,教种大豆、花生、玉蜀、马铃薯等,产量甚丰。由于人烟辐凑,成为本县之重镇”(48)刘赞廷:《炉霍县图志》,民国稿本,民族文化宫,1962年油印,第19页。。玉米及土豆增加了粮材,满足了民众的口腹需要,也促进人口增长。清代后期川西藏区人口呈现快速增长,究其原因,固然与更多的移民迁入、交流、融合有关(见下论述),也与粮食增加密切相联。民以食为天,食物决定着人口的数量及质量。
玉米或土豆呈粒状或块状,炙火烤熟便可食用,打破了藏地传统的糌粑、酥油茶食物限制,解决了移民留驻的食物“困境”,扩大了内地与藏区的交往。任乃强认为:清初百年(顺康雍三朝)进入甘孜藏区的内地民人约3 000人,年均30余人;清中叶百廿年(乾嘉道咸四朝)有1.6万人,年均120余人;清后期五十年(同光宣三朝)达2.1万人,年均420人,呈现持续倍增的现象(49)任乃强:《居留西康之汉人》,《西康图经》,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28页。。为什么清末甘孜藏区移民会出现倍增的现象?(1)内地人口急剧增多,人地矛盾尖锐,驱赶失地者来藏区垦荒谋生,求得发展。(2)藏区种植玉米和土豆后,移民熟悉其习性,生产及加工便捷,食用无障碍,可解决口腹需要,能在藏地立足。当移民扎根谋生,形成较大的群体。据统计,清末甘孜藏区“客籍”已有五六千户,人口两三万,占总人口的8%以上;阿坝藏区的“客籍”情况也类似。持续而来的内地民人与藏民交融结合,人口因之快速增长。
农作物交流与族群交融
18世纪以来,番薯、玉米及土豆等外来作物传入中国西南地区,部分山地民族发生持续的人口外迁。除彝族外,还有傈僳、拉祜、苗(花苗)、瑶、哈尼等民众也分别向西南方向不断移动,并进入缅甸、傣国及老挝。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注意到中国西南族群持续迁徙的现象,分析山地各类作物的种植状况、劳动力使用及贮藏特点等(50)② [美]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6章表3“作物的逃避特征”,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247—250,1—2页。,探讨谷地与山地、种植水稻或玉米等影响族群规模、地位及财富等差异的关系。但他却将这些山地族群的持续迁移视作逃避国家(统治者)的管理,如称“最好把这些山地居民看作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在过去2 000多年中,他们成功逃避了谷地国家项目的压迫——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役和战争”或躲避谷地族群的挤压而迁移,他还想像“纳比亚”(Zomia)这个区域成为这些族群迁徙的“乐土”②。
的确,数百年来中国西南部分族群在移动,尤其进入18世纪后,迁徙规模扩大,流动加快,形成了所谓移民潮。然而,我们认为他们的持续移动并非为躲避“国家项目的奴役”而采取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事实上,这些族群均有自己的土司土目、头领或山官等“管理者”,“国家”只能假手于他们而实施统治,间接控制,俗称“羁縻”,底层民众与“国家”不发生联系,谈不上直接受奴役、征赋税。至于斯科特声称他们受谷地族群压迫而迁徙的说法也与事实不副。多年来,部分谷地族群也同山地族群一样地迁徙,迁移地或停留点的环境还可能更恶劣,前引清中叶迁至凉山彝区的40余万人就是典型事例。我们认为,西南部分族群持续迁徙的重要原因,是原生活区人口多,密度大,因“拥挤”而发生“排斥”,推赶部分人被迫外迁,寻找新的栖身处。当种植番薯、玉米及土豆后,新增的粮食加快了人口增速,致使群体的迁移更频繁,毕竟寻找“乐土”过“幸福生活”是人类追求的共性。再者,迁移并非某族群的行动而是多族群的“共同前进”,迁移带来接触:接触交往、交融共生或矛盾冲突。本文通过四川各民族地区引进及种植番薯等外来作物后产生的影响已作了分析。我们还想阐释的是,同为引种了外来作物,加快了人口增长,因环境不同,习俗有异,后果也不尽相同,消除“富余者”方式也有异。所谓迁居“纳比亚”说法是不全面的,必须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川东南民族地区因种植番薯等外来作物后新增人口被新行业“消化”而少有移民。如前所述,番薯等作物的保质期短,为能及时“消化”,当地或建酿酒等作坊,加工番薯等作物,实现物品转化,延长产业链;或转作饲料,畜养牲畜家禽,变成肉类或蛋类,再藉加工业或副业的生产、贩运或交换来消化“富余”。那些“溢出”土地的劳力或作坊或商铺或贩运,从事生产、加工及经营,完成番薯等的形态转化,转移并增加了物品的价值。加工、运输及商贩等业吸纳并消化“富余”劳力,流动在行业间进行,减少甚至避免了对外迁徙。就是说,新作物催生新行业,以新行业来消化“富余”者,毋需迁徙“纳比亚”。
凉山彝区种植玉米及土豆后增长的部分人口则以迁徙解决。玉米及土豆增多了彝民口粮,“自从有了紫洋芋,农民很少饿肚肠”,增长了人口。玉米及土豆的“高产”体现土地的价值,反映了种植业的“可靠”性。农耕经济逐步成为彝区的经济主业,劳动力受作物种收影响形成不平衡,闲“松”忙“紧”,对劳力的季节性需求,个别人以捆绑或买卖人口解决,更增多彝区人口,加剧“拥挤”。“拥挤”发生“摩擦”,“打冤家”(械斗)使得“胜者”扩大了地盘,消除“拥挤”。“败者”则往迁安宁河流域以西地区。“现在(50年代初)四川西昌地区约有二十万彝族、云南丽江专区约有七万彝族就是由凉山迁来的。据调查,他们迁到新住地的年代大都在十代以内,以五六代为多,也有一两代的。他们由凉山迁出的原因,是为了打冤家以及反动政府的围剿”(51)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63页。。彝民的持续西迁,固然与“打冤家”或“反动”政府围剿有关,但更在于人口“拥挤”产生的“摩擦”,当地缺乏加工或副业等“消化”方式,“富余”者只得外迁。或许这是斯科特说的寻找“纳比亚”,但并非“逃避统治的自由”行动。
玉米及土豆传入藏区,便利了移民迁徙,促进了族群交融。“粮食宜兼种也……内地之民渐次出关,宜兼种苞谷、黄豆、高粱、小米各项为汉人习惯之食”(52)金飞辑:《清末西康垦务档案抬残》,《边政》第9期。。种植玉米、土豆伴随来的是新食法——“块状”食品加酸菜汤,降低了粉状糌粑加酥油茶的饮食“阻碍”。地广人稀、食物可寻影响并吸引民人迁徙,有粮食就能留驻人!清代,进入藏区的内地移民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他们留驻后,多与当地妇女结婚,组成藏汉合璧家庭,繁衍后代(旧称“扯格娃”,今称“团结族”)(53)任乃强:《扯格娃》,《西康图经》,第421页。。藏汉民众交融,带来了藏区人口的发展。
于是,我们认为番薯、玉米及土豆三种外来作物传入四川民族地区后,改变了经济类型,加快了人口增长,导致了群体迁徙,然而这些迁徙并非“逃避统治的自由”,而是族际交往交融的互动带来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