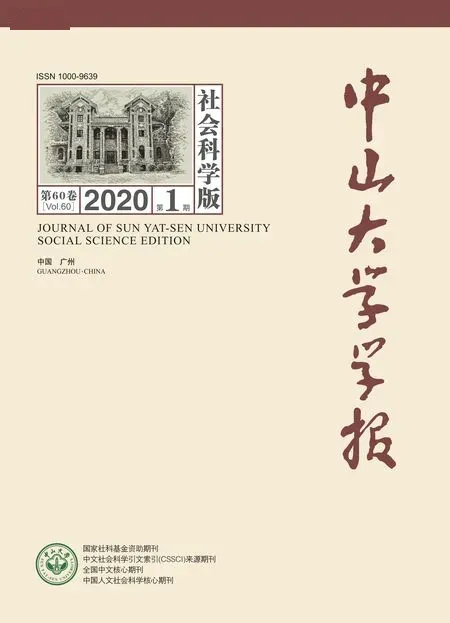明散曲历史观的新旧格局及其曲学思想根源*
2020-01-11马昕
马 昕
自班固开辟以诗咏史的先河,咏史(1)咏史常与怀古相伴,但学界向来认为二者判然有别:咏史多出于书斋写作,怀古则需要面对古迹现场。但这一判断并不严谨,实际上有大量咏史作品也会登临遗迹,只是不在诗中表露而已。咏史与怀古的界限在唐代之后渐趋模糊,本文所涉时段已不需要对此进行严格区分。关于咏史与怀古两种题材的融合问题,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辨析。遂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咏史诗的创作,自六朝至于晚唐,体制渐称完备,风格亦趋多元。而到宋代,词作为新兴的诗歌文体,随着其文人化进程的展开,也逐渐形成自己的咏史创作传统,王安石、苏轼、李纲、贺铸、辛弃疾等人皆有此类名作传世,可为表率。金元时期则出现了散曲这一新鲜的抒情诗歌体裁,在散曲创作的版图中,历史题材的地位异常凸显。咏史散曲亦随之成为举足轻重的创作类型,引起学者的重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咏史)散曲作品内容厚实,感情浓烈,寓意深刻,比起大量描写男女风情、纵酒归隐的散曲作品来,它严肃、尖锐,更具政治色彩和时代气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散曲思想内容的深度和高度。”(2)陈昌怡:《简论咏史怀古题材的元散曲》,《江西教育学院学刊》1985年第1期。而这种所谓的“深度和高度”,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悲剧意识,甚至可以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元代散曲家在写作咏史散曲时,相当普遍地认为:历史上的人与事皆如过眼云烟,最终都要化作尘土,既然如此,倒不如不关心成败,不计较兴亡,甚至不在乎是非。学者将这种现象的成因归结为“对命运表现了无可奈何的畏惧,而没有激起自身的力量感和尊严感”(3)万晴川:《元人咏史散曲中的悲剧意识》,《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1期。,而这又与元代汉族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有关。
即便到元亡以后,政治环境和文人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代表散曲创作“本色”的这种悲观消极情绪仍然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咏史题材来讲,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所形成的阴郁悲慨、故作放达的语言艺术风貌也一直充当着较为主流的风格形态,并且形成了独立发展的创作习套与文学传统。它更多地受制于文体规范,而不是时代环境。但是,明散曲并非铁板一块,其中的历史观念出现了一些可贵的新变。明代曲家在旧有的写作套路之外,创出一系列全新的写法,既呼应了明散曲的整体发展特点,也为我们了解明人的历史观念打开一扇门户。过去,学者们对元散曲历史观的问题关注得稍多一些,而对明散曲中的历史书写,尚未见到有分量的成果,本文即就此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明散曲历史观的突破与新变
(一)笑看功名谈成败
元代咏史散曲中的消极史观,首先表现为对功名事业的淡漠和对英雄人物的讥讽。元代曲家虽然受制于社会政治的大环境而难以在仕途中获得一骋抱负的机会,但他们反而收起卑怯的面孔,转而以倔强执拗的姿态面对“功名”二字。这甚至影响到那些本来可以入仕的曲家,使这种弃绝功名的态度成为元散曲的一种超越阶层与民族差异的普遍化的基调。因此,身居官场高位的张养浩会说“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4)④ 张养浩著,王佩增笺:《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笺》,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27,123页。,贵族世家出身的贯云石则表达了“识破幻泡身,绝却功名念”(5)杨朝英选,隋树森校订:《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2,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7页。的想法。但是,明代曲家常借助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事迹,来表达对功名事业的赞颂与渴慕。例如薛论道有[朝天子]《屈伸》四首(6)⑦ 薛论道著,赵玮、张强校注:《〈林石逸兴〉校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3—75,299—301页。,第一首提及渭水台前垂钓的齐太公和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二首提及苏秦身佩六国相印,第三首提及司马相如成都题桥和齐太公非熊入梦,第四首提及韩信封侯拜将、诛灭项王。这些都是历史上的成功人物,而每首都以“声名”二字作结,诸如“满乾坤声名荡”“满乾坤声名震”等,足见作者对功名事业的渴慕。
在元代,咏史散曲的基调是嘲讽英雄人物,认为他们对功名的追求,最终都难以抵抗死亡,无论生前多么威严显赫,死后都要化为黄土。所以,张养浩在[山坡羊]《骊山怀古》中说:“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④但他们忘记了,追求功名的快乐实在于不懈追求的过程,而不在于寻求永恒的胜利成果。以化为黄土的终极结局来解释人物成败,实是一种套路化的做法。明人散曲多能跳出这一习套,以刚健笔法描述英雄壮举。这尤其体现在一些笔法细腻的套曲当中。例如位列“国朝一十六人”的明初曲家王子一,有套曲《十面埋伏》(7)张禄:《词林摘艳》卷3,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第336—346页。,叙述了汉初三杰各自的英雄谋略。《词林摘艳》也收录一首无名氏所作套曲,也写十面埋伏,对包括项羽在内的楚汉英雄作了更加细致的刻画。曲中不仅写到韩信“九里山施展六韬书,大会垓亲摆布”,张良“高阜处悲歌声能散楚”以及各路诸侯、诸般人马的阵前英姿;更为可贵的是,作品还写到项羽虽已穷途末路,却仍然是一副“雄纠纠将军催着战驹”(8)张禄:《词林摘艳》卷4,第529页。的凛然英姿。对失败英雄的同情,淡化了对成败结果的态度。虽然所有人的结果都是化为黄土,但更重要的是英雄人物的性情与作为以及他们为追求事业成功而英勇奋斗过的身影。
不过,单纯叙述古人的壮举,终归是隔了一层,关键还是要将这种对英雄的赞颂与仰慕化作自身奋进的动力。薛论道[朝元歌]《待时》四首,都讲英雄待时而动的道理。其二提及商山四皓和齐太公,说“风云际时志自酬”,“各自有各人时候”⑦。既然“各自有各人时候”,那么对于写作散曲的文人来讲,恰恰也是如此。且看李应策的[朱履曲]《席间晤刘大府马总戎和此刘系谪官》,这首曲是为一位贬谪官员所作,其中引述汲黯、班超等人贬谪、外迁的经历以及最终功成名就的结局,就是为了鼓励这位贬谪中的友人,“到而今赫赫声华许并追”(9)李应策:《苏愚山洞续集》卷8,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44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205页。。古代英雄的事例成为明人自我勉励与相互劝慰的资源,相比元代曲家千人同声的悲观腔调,其精神面貌的变化是巨大的。
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要想在功名事业上有所作为,往往要寄托于才学与谋略。他们摆脱战场杀伐与政坛斗争这一传统的“立功”范畴,而将文学名世、“立言”不朽也视作一种足可追求的功名。例如康海[落梅风]《有感》云:“张良智,范蠡谋,都不如贾生词赋。响当当美传千万古,有奸谀怎生厮妒?”(10)康海撰,周永瑞点校:《沜东乐府》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页。贾谊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完全不足以和张良、范蠡相提并论;但其文章流传后世,足可压过张、范,因此康海认为,这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理想。
可以说,从元散曲对功名的冷漠态度,到明代曲家对功名事业的赞颂、渴慕以及对功名范围的拓展,都体现了明代散曲作家希望有用于世的强烈诉求。而这种诉求又与他们所欣逢的时代密不可分。
(二)欣逢盛世论兴亡
元代咏史散曲的悲观情绪,在个人层面表现为对成与败的漠视,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对兴与亡的麻木。元代曲家普遍认为,历史上一切繁华盛世皆如过眼云烟,最终都会走向衰落与消亡。这也许是基于他们眼前凄惨的现实景况,繁华不属于他们那个时代,而他们在现实中能够见到的,多是兼并战争后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但明人却往往能以相当充沛的自信来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一反元曲习套,将混乱失序留给历史,而将繁华鼎盛留给当今。虽然明代的政治环境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算不上昌明,但明代曲家却总能怀抱着颂圣美时的心态,来衡量历史与现实孰优孰劣。
其中一些作者很明显受到台阁文学风气的影响,借助咏史散曲装点太平。例如殷士儋(1522—1581),山东济南人,曾在嘉靖时期担任过翰林院检讨,又在隆庆年间担任礼部尚书,隆庆三年(1569),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入阁担任辅臣,后因受高拱排挤,于隆庆五年(1571)请辞归里。他有一首套曲《咏怀古迹》,写家乡济南的名胜古迹,应是归里后所作。该曲在历数济南著名景点后,开始怀想严光、张翰的归隐之乐,似乎仍陷入不问兴亡、只知享乐的遁世趣味中。但所幸,接下来便突生转折,发出惊叹:“呀!喜遭逢累朝累朝全盛,托赖着一人一人有庆,四海无虞罢战争。偃武销兵,重译来庭,万国咸宁,祥瑞休祯。尽如今讴歌登览乐余生,这受用皆天幸。”套曲尾声则将其感念皇恩、感恩盛世的意思和盘托出:“感皇恩覆庇深,抚微躯频内省。捐糜何以报朝廷,一点丹心常耿耿。但祝愿当今明圣,万年天保贺升平。”(11)殷士儋:《明农轩乐府》,刘祯、程鲁洁编:《郑振铎藏珍本戏曲文献丛刊》第5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46页。在济南这样一个历史遗迹众多的古城,作者看到的并不是断壁残垣,而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认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济南历史上最美好的时期。
说起盛世,在明代之前的历史上,早已出现过众多伟大的时代与贤明的君主。明人称颂盛世时,常与那些贤君盛世作比较,每每认为当今尤胜往古。例如《词林摘艳》等散曲集都收录了一首无名氏的套曲,题为《武功》。这位曲家认为明朝“过舜尧”,“迈禹汤”,“量宽如文景”,“豁达似高光”,“道仿三王”,“智压在孙吴上”(12)张禄:《词林摘艳》卷10,第1254—1255页。,几乎将所有伟大的时代碾压一过。这首作品虽然有阿谀之嫌,却也代表了明散曲独特的历史观念。
将这种圣朝自信发挥到极致的,是对金陵这座都城的意义开掘。金陵,既是六朝的都城,又是明初的都城。六朝在此建都,国运都不久长,居于繁华之都,竟守偏安之局;朱元璋却能借助钟山王气一扫寰宇,享国长久。在元代咏史散曲中,六朝与金陵,每每成为曲家表达繁华消逝之叹的载体;但在明代咏史散曲中,金陵却成为一座光荣的都城。且看景时珍的套曲《登高有感金陵景》,在历数金陵繁华市貌之后,便切入历史比较的环节:“想齐梁晋宋陈,有朱李石刘郭,不多时天数轮着。”“争如我大明朝,迈唐尧,一班儿宰辅匡扶,尽都是武略文韬。演武的胜孙杨卫霍,修文的赛伊尹皋陶。”(13)佚名撰,任讷、卢前校订:《北曲拾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b—2a页。同一座金陵城,却有彼时之衰与今时之盛的差别。
金陵的光荣,不仅在于它开启了伟大的明朝,还关涉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华夷之辨,而这也正是元明咏史散曲在兴亡问题上表现出种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六朝长期遭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伐;而同样定都于金陵的朱元璋,却能一举推翻元廷,结束长达百年的异族统治。这一区别,使明散曲中的“金陵怀古”主题增添了一抹浓重的政治色彩。例如梁辰鱼的套曲《拟金陵怀古》,其小序明确指出,“卑古崇今”是该曲的创作宗旨。因此,吴与越之兴亡更替,长安、洛阳、邺城之相继凋零,都与当今圣朝之繁华形成鲜明对比;而金陵古都终于在数千年后等来“东南天子”朱元璋,使其重获新生。序文末云:“因拟怀古之作,陋尔偏安;实寓尊王之词,欣兹一统。”(14)⑦ 梁辰鱼著,吴书荫编集校点:《梁辰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5,365页。所谓“尊王”,暗寓“攘夷”之义,认为明朝的一统在历代王朝序列中具有尤其不凡的意义。施绍莘也有套曲题作《金陵怀古》,在叙说六朝更替之后,感叹道:“叹前朝,真儿戏,到如今,英雄泪。还笑几许么(幺)么,要窥神器。谁知天命有攸归,和阳一旅,日月重辉。笑谈间万里,扫腥膻羯胡北去,雪尽中原耻。替古今争气。钟山呵护,别开天地。”(15)施绍莘撰,来云点校:《秋水庵花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6页。“腥膻”“羯胡”“中原耻”这样的字眼,无不关涉民族问题。
而“咏三分”这种咏史主题,本来与华夷问题无关,因为魏蜀吴三方力量皆非蛮夷入主。但明人仍会在三国故事中强行渗入华夷之辨。例如丘汝成套曲《咏三分》,从楚汉之争说起,继而讲到三国鼎立,重点称颂诸葛孔明,却专门谈到他平定南蛮的功绩,说这是“心存汉室,恢复华夷”(16)张禄:《词林摘艳》卷4,第553页。。这样写,就历史评论本身来看,不免有些轻重失当;但对于彰显明人意识形态来讲,却恰好切中了关键。
(三)明辨忠奸讲是非
元代咏史散曲的消极与虚无还体现在对政治伦理的漠视,由于元朝统治者长期轻视儒学建设,官僚系统普遍缺乏政治信仰,而散曲又先天是一种并不严肃的讽刺文学体裁,因此容易在谈论历史人物的时候,嘲讽忠义之士,泯灭是非界限,以遁世归隐的生活方式回避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坚守。因此关汉卿在[乔牌儿]中说“且休题,谁是非”(17)吴国钦校注:《关汉卿全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623页。,王仲元[江儿水]《叹世》也说“谁待理他闲是非,紧把红尘避”(18)无名氏选辑,隋树森校订:《类聚名贤乐府群玉》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但是到明代,儒家信仰迅速重建,忠义观念深入人心,气节之士层出不穷。即便在散曲文学中,忠义观念都深深植入曲家的精神世界。加之,明人在历史面前表现出突出的自信心态,因此往往当仁不让,敢与奸邪划清界限。即便曲家自身命运坎坷,饱受冤屈,却仍然坚毅沉着,大节不亏,在政治伦理问题上尺寸不让。
例如王九思本为忠节之士,却因与刘瑾为陕西同乡,被名列瑾党,遭到贬官,次年又被勒令致仕,当时年仅45岁。此后他家居四十载,政治抱负化作东流。其命运之坎坷,足可引人唏嘘。然而这并未使他对儒家忠义观念产生怀疑,反而坚定地说“平生自信修仁道,谁敢与吾敌”。他虽然也看到了“盗跖颜回命不齐”的荒诞史事,却依旧主张“春秋世教赖扶持”,俨然一派纯儒气象。观察他的咏史散曲,要注意两个特别重要的主题。首先是他对隐士的态度。王九思本人的归隐,并非贪图安逸享乐的生活,实是出于被迫,貌似身在田园,实则心在魏阙。因此,王九思赞赏鲁仲连“蹈海耻扶秦”,正是因其鄙视秦国背弃礼义,即所谓“文休丧,德要存,君能倡义我何云”。其次是他对屈原的态度。屈原遭谗蒙冤的经历与王九思多有相合之处,因此王九思对屈原每多同情。在写到屈原时,他说:“每思奸恶心如辨,题品忠良味自甘。”(19)李开先撰,王九思次韵:《南曲次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第31a页。这份傲然与固执,尤能感动人心。
而谈到屈原,使我们想到元散曲中大量出现的“嘲笑屈原”现象。明人不仅不嘲笑屈原,反而正面称颂其忠义。例如梁辰鱼的套曲《过湘江吊屈大夫》⑦,专门“为吊孤忠魄”而作,曲中对屈原只有同情,没有嘲讽。另有收录于《雍熙乐府》的无名氏作品[朝天子]《述古人》其七,也称赞屈原为“忠正”之“大贤”(20)郭勋辑:《雍熙乐府》卷18,《四部丛刊续编》,第10a—10b页。。又比如明末人龙膺(1560—1622),湖南常德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他在万历十七年(1589)始任国子博士,后因屡次直言上书,不容于朝廷,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南归常德,迁延至次年才前往杭州出任盐官。在即将启程去往杭州时,龙膺与友人罗廪以散曲唱和,作[黄莺儿]《南归》二十首,其七云:“是三闾近邻。是长沙后身。谁怜折槛披忠悃。”龙氏以屈原自比,显然谈不上嘲笑,主要还是同病相怜。其九又云“连横合纵,鼓舌尽仪秦”(21)龙膺:《龙膺集》卷14,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56—660页。,批评了屈原的对手张仪以及与张仪一样靠着摇唇鼓舌捞取功名利禄的苏秦。将龙膺对屈原和张仪、苏秦的评论相较,其是非标准便显而易见了。
对政治伦理和是非观念的认真探讨,是明代咏史散曲一个明显的特点,也使得这类作品的境界陡然提升。施绍莘套曲《金陵怀古》小序云:“盖怆兴废于前人,总成陈迹;而辨是非于后死,差有古心。”“辨是非”,正是作者对自己提出的严肃要求。曲文中提到了靖难之役:“竟谁知北平兵至,破金川天心暗移。腐儒当国等儿嬉,纷更是非,不合时宜。周官制,成何济,成王已挂袈裟去。孤臣泪孤臣泪滔滔江水,年年化,年年化,杜鹃啼。”施绍莘将建文帝比作成王,将靖难之役比于管蔡之乱,实已表达其基本立场。对于这样语涉政治禁忌的作品,时人评语中征引了王世贞对《拜月亭记》的批评意见:“无词家大学问,一短也。既无风情,又无裨风教,二短也。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三短也。”评点者认为《金陵怀古》全无这些弊病,尤其是能够“裨风教”、讲是非。施绍莘《花影集》还收录了胡献征(字存人)的评语:“此关系大文字,非目空四海,胸藏万古,岂能雄浑如此。”(22)施绍莘撰,来云点校:《秋水庵花影集》,第34—36页。在明代,词学尚且陷入吟风弄月的花草习气中不能自拔,人们却对散曲抱有如此期待,不得不令我们惊讶。这大概正是咏史这一题材元素在起作用。元代曲家对历史的看法过于消极悲观,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不尊重,因为他们并未真正地将历史看作可资借鉴当今的思想资源;而明人竟认为席间消遣之用的散曲作品,一旦涉及历史题材,便具备以古鉴今的力量,这一尊体思路,与明人对现实社会超强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密不可分。
明散曲历史观的这些突破与新变,可以说是对元散曲的一种提升。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为散曲艺术在价值观上的干瘪实现了一次救赎;在文学艺术层面,又为散曲艺术争取到一条重要的尊体途径。但事实上,在明代咏史散曲中,以上这几种崭新的创作方法与元散曲中旧有的写作习套其实是长期并存的,甚至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与创作风格也都是大量兼容的。虽然新的写法已经出现,但旧的习套仍在延续。这一新旧杂陈的现象又表现出复杂性与不平衡性,即其在明代文学的各个历史阶段里,在散曲作家的不同阵营中,都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存在形态。对此,我们还需要深入到明散曲发展史的时空维度中,作更细致的研究。
二、明散曲历史观的新旧格局
要对明散曲历史观的新旧格局加以描述,首先要在时间维度上为明散曲历史观念的演变历程进行基本的分期,其次还要注意到南北曲家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些许差异。在正德之前的明代前期,散曲创作长期处于衰微的状态,涉及历史题材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难以形成一种格局和态势。明散曲的历史写作主要出现在正德、嘉靖时期和万历至崇祯时期,下面分别论述。
(一)正德、嘉靖时期
正德、嘉靖时期是明散曲的第一次创作高峰,以陈铎、杨慎、金銮、夏旸等人为代表的南派曲家,和以康海、王九思等人为首的北派曲家,先后扬声于曲坛。
南派曲家在历史观念与写作模式上几乎全盘继承元散曲,都表现为消极悲观的气质,未见到有明显的新变迹象。例如陈铎在[朝天子]《归隐》二首中说“石崇富易消,范丹贫到老,那一个长安乐”,“韩元帅将坛,严子陵钓滩,那搭儿无灾患”(23)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梨云寄傲》,《续修四库全书》第17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表达归隐远害的避世思想。杨慎在[折桂令]《华清宫》中以“云雨无踪,台殿成空;一片青山,万树青松”(24)② 杨慎著,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8,236页。作结,在套曲《吴宫吊古》中以“越王得计吞吴地,归去层台高起,只今亦是鹧鸪啼处”②为尾声,都沿袭了元代咏史散曲中将歌舞繁华的短暂易逝与自然山水的永恒长存作对比的惯有写法。
北派曲家的情况则稍微复杂一些。
首先,李开先、韩邦奇、常伦、张炼、冯惟敏等多数的北派曲家基本沿袭了元散曲的旧有模式。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李开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傍妆台]百首,其二十一、二十四、三十三、三十五、四十、四十一、四十九、六十四、六十八、七十二、九十三、九十九、一百(25)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52—1465页。都涉及历史内容,并且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成败、兴亡与是非问题的含混态度。尤其是其二十四中对屈原的嘲笑口吻,真与元散曲的思想状态毫无二致。韩邦奇也是一副悲观论调。他的[折桂令]《金陵》在历数六朝繁华后,却说这些“都做了一场话柄,还落不得半个虚名”。[满庭芳]《洛阳怀古》讲述完东都往事,便说“今和古成长梦,只丢下些虚名虚姓,模糊在断碑中”。[水仙子]《同州道中怀古》也说“长春宫麋鹿游,把豪华都做了一望荒丘”(26)韩邦奇:《苑洛集》卷12,《续修四库全书》第1269册,第546—547页。。显然,他善于描写繁华败落之景,认为一切豪华盛景终将化为泡影。常伦少有任侠之气,曲中含有盛唐气象,但他被谗弃官后,却转入玩世闲隐一途。他的咏史散曲也多表达归隐志趣与全身远害之思,例如[雁儿落带清江引]其一:“石崇富结雠,韩信功催寿。荣华有是非,年命无先后。五柳庄儿常自守。”(27)常伦:《写情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68页。以上诸家所呈现的这类论调,其实也是正德、嘉靖时期北派曲家的主调,与南派曲家并无明显差别。可见在此阶段,新观念与新写法仍未占据曲坛主流。
其次,康海、王九思二人的一部分作品仍然继承元散曲旧有模式,却在另一部分作品中表达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展现出全新的气象,从整体上呈现出新旧杂陈的格局。一方面,康、王二人都因刘瑾伏诛而遭受牵连,壮年即被迫辞官,隐居田园数十年,绝无再入仕途的希望。这样的挫折经历使二人能够与元代曲家达成共鸣,在散曲中表达一些心灰意懒的悲观言论。例如康海有[清江引]六首,都以“懒”字作结,写的也是古代隐士的事迹,“醉卧东山归去懒”“梦觉南柯心更懒”“百尺竿头心力懒”“起草明光魂梦懒”(28)⑦ 康海撰,周永瑞点校:《沜东乐府》卷1,第27—28,23页。等语,更将这种“懒意”表达得绵长动人。王九思则较多地表达全身远害的思想。例如其[山坡羊]《阅世》其一批评“淮阴侯见识错”,称赞“子房公智量高”。韩信与张良的愚智对比,正是元散曲中屡屡出现的“桥段”。另一方面,康、王二人的性格中又含有骨鲠刚强之气,在长期的归隐生活中能够寻求到积极正面的精神支撑。例如康海[落梅风]《有感》其一写“草离离遍遮秦汉宫,利和名算来何用”,还是一副消极论调;其二却说,“张良智,范蠡谋,都不如贾生词赋。响当当美传千万古,有奸谀怎生厮妒”⑦,将功名事业转入立言不朽的范畴,这对于立功不遂的康海来说,不啻为一剂解药。王九思则对忠义大节尤其看重,他在[清江引]《再次前韵咏古》十首中侧重于隐士的节烈而非淡泊,在[傍妆台]百首中也提出“春秋世教赖扶持”,“每思奸恶心如辨,题品忠良味自甘”,明辨政治是非成为其历史观念中的重要成分。
(二)万历至崇祯时期
万历至崇祯时期是明散曲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以梁辰鱼为首的南派曲家逐渐占据曲坛主流的位置,而李应策、薛论道等北派曲家也有非常丰富且重要的作品传世。在此阶段,无论南派还是北派,都以表达积极进取的历史观念为主。
首先,在南派曲家中,只有吴国宾、高濂、周履靖等人的个别作品表露出消极史观。例如吴国宾[黄莺儿]其五(29)吴廷翰著,容肇祖点校:《吴廷翰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9页。抒发了对功名事业的鄙夷,高濂套曲《警悟》(30)胡文焕编:《群音类选》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9—2362页。表达了繁华尽逝、成败皆空的思想,周履靖套曲《山林慨古》也说自己只愿“每日间徜徉云水,笑傲渔矶”(31)周履靖:《闲云逸调》,民国间刻本。。而梁辰鱼、施绍莘、陈所闻这几位重要曲家都集中地表达了积极进取的历史观。正如上文所论,梁辰鱼在咏史散曲中基于华夷之辨的观念,而抒发对明朝的赞美之情,认为今胜于昔;并且对屈原的忠义品质表达敬佩,对其不幸遭遇给予同情。施绍莘则在套曲《金陵怀古》中提出“辨是非于后死”的宗旨,称颂朱元璋驱除鞑虏之功勋,并抨击朱棣靖难之无耻。此外,陈所闻咏史散曲的主题仍然是称颂忠义之士。例如其[驻马听]《拜岳墓》中称赞岳飞“独秉精忠”,并向秦桧发出诘问:“试问奸雄,流芳遗臭孰轻孰重。”他在[驻马听]《吴山拜伍相庙》中评论伍子胥时,也将议论重点由对其蒙冤含恨的同情转移到对其“一寸丹衷”(32)陈所闻辑:《新镌古今大雅南宫词纪》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741册,第780页。的称赞上来。陈所闻另有一首[懒画眉]《吊方正学祠》,说方孝孺“死甘十族古今难,正气犹生白日寒”(33)陈所闻辑:《新镌古今大雅南宫词纪》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741册,第795页。。总之,这三位南派曲家的历史观念都偏于积极正面,尤其关注忠义是非的问题。
其次,北派有两位杰出的曲家,即李应策和薛论道,此二人的历史观与康海、王九思一样,都表现出新旧并存的态势。
李应策是以新为主,以旧为辅。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几首外,还有一首[水仙子]《因辽事感怀》。该曲由寇准签订澶渊之盟,联想到尉迟恭和班超的千古功业,抒发对“英雄济国难”(34)⑦⑧⑨ 李应策:《苏愚山洞续集》卷22,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44册,第557,562—563,573,568页。这一人生理想的向往。[混江龙]《闲咏》二首则提到了“傅岩千古济川才,班超万里封侯相”,借以抒发“想拨燕然山顶石,请转高华屿底洋”⑦的立功志向。在渴慕功名事业之余,李应策还对政治是非表达明确立场,例如[清江引]《阅史感宋诛檀道济而伤之》中批评檀道济“把万里长城误”,并顺便提到“还有个秦桧把高宗误”⑧。而那种明哲保身、全身远害的论调则仅见于[桂枝香]《感时事作》⑨这样的个别作品中。
薛论道则是新旧史观各占一半。在功名成败的问题上,他经常劝人少涉名利。[水仙子]《成败》四首列举了项羽、苏秦、范增、韩信、萧何、范雎、李斯、晁错等历史人物,说他们“到头来谁是豪杰”(35)薛论道著,赵玮、张强校注:《〈林石逸兴〉校注》,第134,161,92,244—245,179页。。其[黄莺儿]《怀古》其二更直接说出“多成多败,都是梦一场”。但是,薛论道又在另一些作品中表达对功名事业的渴慕与赞赏。上文所引的《屈伸》四首且不论,再看其[朝天子]《志学》其一中说:“凿壁引光,萤火练囊,一个个都为相。”对匡衡和孙康勤学苦读而得以身列朝班的经历不乏艳羡之情。[桂枝香]《时不遇》四首虽然讲的是怀才不遇的愤恨,但毕竟其前提首先是胸怀立功之志。正如曲中所言,即便“壮志三尺短”,却仍然“一心万里长”;即便“自恨轻投笔”,也是因为“无能答圣朝”,如果有时与能,自然还是要一展平生抱负的。而与“时不遇”主题相对而言的便是“待时”,上文所引[朝元歌]《待时》四首中,就列举了韩信、朱买臣、姜太公、管仲等人作例子。他们都起于草莽寒素,却因为得到机遇而能一飞冲天。薛论道的消极史观主要集中在个人成败的问题上,而对于忠义大节,他的立场却非常坚定,并无新旧并存的余地。例如他在[黄莺儿]《吊韩信》中批评韩信“但持忠,一心无二,焉到未央宫”,背后正是忠君思想。
从时间维度来看,明散曲越发展到后面,积极进取的历史观就越占据上风。在正德、嘉靖时期,只有康海、王九思比较多地以这种历史观结撰成篇;到万历至崇祯时期,就演变成南北派曲家共同的趋势,而元散曲的旧有写作模式则成为边缘。从空间维度来看,北方曲家的历史观较为刚健,南方曲家的历史观则稍显保守,后者对新史观的接受也相对较晚。出现这一时空格局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单看作品,恐怕难以得知,还需要深入到明代曲家的曲学思想中来观察。
三 新旧格局背后的曲学思想根源
散曲作家在其作品中表露出何种历史观,并不能用曲家本人的性格或经历来解释。并不能说性格豪迈者或功名顺遂者,其历史观一定是进取的;反之亦然。例如史观较为保守的韩邦奇,却以创作边塞题材著称,实具北派豪放本色。而梁辰鱼和施绍莘都长期困于科场,不免心灰意冷,甚至沉迷于书写艳情,但他们的几首咏史套曲却都严辨华夷,标榜忠义。
而且,也不能从南曲、北曲的体制因素来为明散曲的史观差异现象求得解释。持积极史观的康海、王九思和持消极史观的李开先、常伦、杨慎,都是南北曲兼作。例如,王九思既用[北双调·清江引]来赞颂隐士节烈,也用[南仙吕·傍妆台]来奖掖鲁仲连的忠义心肠。韩邦奇在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厌弃时,也是南北曲兼有。
最后,我们将目光锁定在曲学思想上,尤其是曲学与诗学思想的关联处。笔者发现,持有积极史观的曲家,往往更认同诗、曲同源,并且更倾向于将散曲进行诗化改造,从而使其偏离金元以来的“本色”特征。而诗学对散曲的改造,之所以能酝酿出历史观念的变化,则与明代中晚期的文学复古运动息息相关。那些与复古派关系密切或在思想上认同复古主张的文人,例如康海、王九思和梁辰鱼,他们在散曲中也就更容易抒发积极进取的观念。而那些与复古派有所疏离的文人,例如杨慎和李开先,或受吴中文学风气的影响,或受唐顺之诗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在散曲中就容易放浪于形骸之外,形成较为消极悲观的历史观念。我们仍然按照第二节所划分的两个阶段来分别论述。
(一)正德、嘉靖时期
在康海的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诗、曲同源问题。关于散曲的起源,明代诸多论家中,以徐渭和王世贞的影响为最大。徐渭《南词叙录》(36)徐渭著,李复波、熊澄宇注释:《南词叙录注释》,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关于《南词叙录》的作者是否为徐渭,骆玉明、董如龙曾撰文《〈南词叙录〉非徐渭作》(《复旦学报》1987年第6期)予以否定,但徐朔方就此撰写《〈南词叙录〉的作者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戏曲研究》编辑部编:《戏曲研究》第28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49—254页)予以反驳。双方意见各有优劣,学界迄今仍多用旧说,本文亦从之。和王世贞《新刻增补艺苑卮言》(37)王世贞:《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695册,第537页。都认为散曲起源于金元时期,因胡乐不协于南词,故而发展出北曲,这大概代表了明人的普遍认识。康海的看法则提出于徐、王之前,他在《沜东乐府序》(1513)中说:“古曲与诗同,自乐府作,诗与曲始岐而二矣,其实诗之变也,宋元以来,益变益异,遂有南词北曲之分。然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38)任中敏编著,曹明升点校:《散曲丛刊》中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08页。可见康海将散曲源头追溯至《诗经》与汉乐府,比金元时期要久远得多,这不仅具有明显的复古色彩,而且将散曲直接与《诗经》、汉乐府所代表的“言志”传统联系起来。正德十四年(1519),康海在为王九思《碧山乐府》所作序中又说:“诗人之词以比兴是优,故西方美人,托诵显王;江蓠薜芷,喻言君子。读其曲,想其意,比之声,和之谱,可以逆知其所怀矣。”(39)康海:《碧山乐府序》,王九思:《碧山乐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5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481页。这里所谓的“词”实指散曲,而所谓“诗人之词”,则是诗人所作之曲,是诗化了的曲,因此也具有言志写怀之意,在其中寄托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就是非常正常的事了。曲学理论的这一突破,正是康海散曲在历史观上实现新变,进而脱离元曲“本色”的理论前提。
如果说康海将散曲言志的理论依据诉诸《诗经》《楚辞》、汉乐府,那么王九思则将其诉诸李杜之诗,这更切近于前七子诗宗盛唐的主张。王九思《碧山续稿序》(1533)云:“风情逸调,虽大雅君子有所不取,然谪仙、少陵之诗亦往往有艳曲焉。或兴激而语谑,或托之以寄意,大抵顺乎情性而已,敢窃附于二子以逭予罪。”因李杜诗中皆有艳曲,因此散曲也可稍免留连风月之讥。更重要的是,李杜之艳曲,其意旨亦不在于艳冶,而是因事感兴,托风月以寄意。这样一来,散曲便具有了返于正道的可能性。王九思在明嘉靖间刻本《碧山新稿》卷首自序(1541)中还说散曲“语虽未工,情则反诸正矣”,便是借散曲之体,寓积极进取之价值观。
与康、王相反,杨慎将曲与词混融为一,推动了散曲的俗化进程。杨慎的诗学思想就以浅俗为追求,他评判杜诗“意求工而语反拙”,而应该“愈俗愈工,意愈浅愈深”(40)杨慎著,王大淳笺证:《丹铅总录笺证》下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18页。。将康、王与杨慎的曲学理论所呈现出的雅俗分途,与他们在散曲中传达的人生观与历史观,实现了某种对应的关系。正是这种俗化的倾向,使杨慎的散曲继承并发扬了元散曲的旧有写作模式,呈现出一种悲观消极的思想色调。学界在评价杨慎散曲时,经常将其悲观色彩归因于杨慎被贬南疆数十载的悲剧命运,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康、王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的散曲在气质上存在的差异,不应只以知人论世之法来解释,还应归结到雅化与俗化这一曲学思想差异上来。
同样以浅俗为散曲本色的,还有李开先。他曾将自己所作的市井俗曲辑成《市井艳词》一书,这本身就是一种崇俗去雅的行为。他还在《市井艳词序》(41)③④ 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上册,第565—566,596—597,567—569页。中称散曲“直出肺肝,不加雕刻”,“其情尤足感人”,“真诗只在民间”,因此典乐者“放之不可,不亟以雅易淫”。他又在《西野〈春游词〉序》③中谓,诗与曲“意同而体异”,前者宜含蓄,后者须通俗,若以作诗之法约束散曲,则“乖矣”。而散曲的本色特征应以金、元为标准,符合这一标准,便是“词人之词”;若掺以诗法,则是“文人之词”。二者相比,他倾向于前者。李开先能有这种尚俗的曲学思想,根源恐怕还在诗学。他在《市井艳词又序》④中指出,初学作曲者往往追求“文”,但登堂入室者则转而追求“俗”,这与学诗的过程相似。因为初学作诗者容易追求“古”,也就是复古模拟;而深造其境者则开始追求“淡”,这种“淡”的境界又恰恰指向了唐顺之“率意信口,不调不格”(42)唐顺之著,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的诗学思想。可见,李开先从作诗之法联想到作曲之法,是受唐顺之诗学的启发,同时也是对前七子复古诗学的反动。如上所论,李开先以金、元为散曲的本色标准,将“诗以言志”的追求排除在散曲创作规范之外,那么他在自己的曲作当中完全沿袭金元散曲的消极史观,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二)万历至崇祯时期
正德、嘉靖时期,明朝政局开始趋于暗弱,但统治秩序依旧得以维持,国家尚处于总体安定的局面中。因此,文人在散曲中植入进取史观时,主要发自纯粹的理论探讨,尚显优游不迫。而到万历至崇祯时期,政治更趋腐败混乱,内忧外患层出不穷。面对这样艰困而荒诞的时局,曲家亦不能完全抽身世外。这一时期的散曲,在历史观方面展现出更加积极的面貌,将忠义思想融入其中,在文学精神的层面上完成了较为彻底的雅化。梁辰鱼、施绍莘等南派曲家和薛论道、李应策等北派曲家皆以刚健之气撰作咏史散曲,但他们通向这一终点的路径各不相同。
梁辰鱼在嘉靖后期走上曲坛,虽然他的散曲以写情赠妓之作著称,但这只是其散曲成就的一个侧面。在艳情的对立面,是他以沉雄阔大的胸怀书写历史,阐发兴亡之论。事实上,他本人年轻时就已“精心在经史”,“欲究治乱旨”(43)⑦ 梁辰鱼著,吴书荫编集校点:《梁辰鱼集》,第101,371页。;而其著名的传奇作品《浣纱记》也借吴越兴亡故事来警戒明朝统治者正确应对国家忧患。上文就已提到,梁辰鱼在套曲《拟金陵怀古》小序中寄托了“尊王攘夷”之意。他在另一首套曲《拟出塞》的小序中也一再强调“天限华夷,人分蕃汉”⑦之意,借昭君出塞的旧题,影射嘉靖后期的两重外患:一是蒙古俺答汗发动的“庚戌之变”;二是对江南沿海地区的倭寇问题。尤其是后者给身处江南的梁辰鱼带来了更加直接的冲击。梁辰鱼将民族情绪融入其历史观念当中,形成积极进取的政治见解,与元散曲那种不问是非、不讲忠义的写法完全不同。所以,单看其艳情之作,会觉得梁辰鱼与元曲的差别仅在于更加雅致的文辞;但若看其咏史之作,就会发现他为明散曲灌注了何等鲜活的生命力。
与梁辰鱼相比,薛论道实打实地有过边塞军旅经历。他年少时因亲没家贫而放弃举业,转读兵书,自负智囊。当神堂峪有警,他献策于制府,却敌十万众。守大水峪,亦料敌如神,歼敌无算。薛论道从军三十年,一生直面北方边患,维护国家安定的责任感尤其强烈。武人的刚直之性,辅以文人的忠义之气,使他的散曲迥异于一般的文人创作。他在《林石逸兴自序》(1588)中认为自己的散曲作品“或忠于君,或孝于亲,或忧勤于礼法之中,或放浪于形骸之外,皆可以上鸣国家治平之盛,而亦可以发林壑游览之情”(44)薛论道著,赵玮、张强校注:《〈林石逸兴〉校注》,第408页。。薛论道将自己的散曲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忧勤于礼法之中”的作品,是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刚健之曲、武人之曲;二是“放浪于形骸之外”的作品,是文人逸士之曲、怀才不遇之曲。前者的创作根源是他“竟堕武流”,屡建惊人之功;而后者的根源则是他“自分樗散”,未获腾达之途。如果只有后者,便与寻常曲家无异;幸亏有前者,才使薛论道成为明代散曲史上的一朵奇葩,在散曲艺术殿堂中深深烙下了“忠义”二字。
说到忠义,在明末最追求忠义气节的,首推东林党人。而北派曲家李应策恰是东林党重要人物,具有颇为强项的性格。其散曲最突出的特点是援引时事,近于“诗史”。他在曲中写到东北战事、万历三大征,也写到内阁之腐败无能、阉党之肆无忌惮。叶晔指出:“元散曲以来的‘避世—玩世’主题,以及清丽雅正的文学风格,在李应策笔下,变成忧国忧民、充满政治责任感的士大夫精神。散曲成了李应策政治抱负的代言书,发挥了与传统诗歌相同的道德功用,‘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同样在散曲这一俗文学样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45)叶晔:《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将这种时事风格转入咏史题材,就化为其刚健进取的历史观。他的散曲《因辽事感怀》,看似书写宋辽之事,实则此辽正是彼辽,借用澶渊之盟暗指东北战事。他在《阅史感宋诛檀道济而伤之》二首中抨击檀道济和秦桧的误国误民,实则影射阉党横行、奸佞当道的政治现实。由历史牵连出时事,这种写作手法使李应策的咏史散曲具有更加明显的现实观照,是那种单纯的论古之作所不能比的。
通过上文对散曲作家曲学思想的梳理,我们也为本文所描绘的明散曲的时空格局做出了解释。首先,从空间维度来看,北方曲家康海、王九思受复古文学思想影响甚大,他们将散曲艺术溯源至《诗经》、汉乐府或李白、杜甫,用以突出其类同于诗的言志功能,从而完成去俗向雅的散曲改良;而杨慎与吴中文学传统关系密切,李开先则深受唐顺之诗学的影响,都与北方复古文学相对立,因此他们主张平淡通俗的散曲风格,主张崇俗去雅,维护元曲本色。正德、嘉靖时期散曲中所呈现的史观差异,表面上呈现出北方曲家积极者多,南方曲家消极者多的态势,实则主要是由散曲作家与复古文学思想的关系来决定的。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积极史观在正德以后的散曲中越来越取得优势,到明末更是充分融入了儒家忠义思想。其思想根源从单纯的理论探讨层面,延伸到了社会政治的现实层面。在这背后,仍然难以完全摆脱散曲在雅与俗之间的徘徊与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