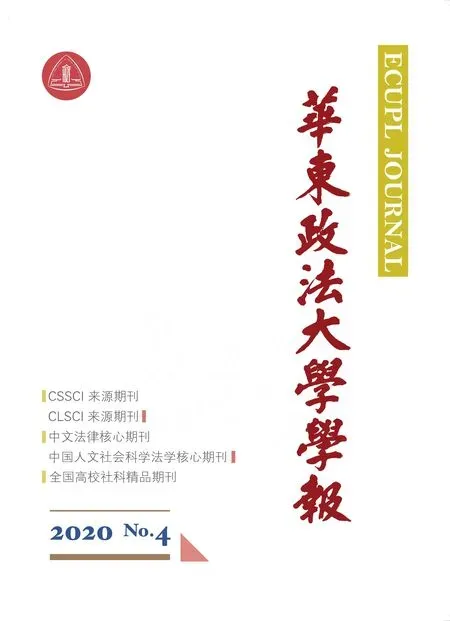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的论证进路及其批判
2020-01-11王艳慧
王艳慧
一、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的论证进路
明斯基认为,人工智能是一门令机器做那些需要由人类用智慧做的事情的科学。〔1〕See J. Copel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Wiley-Blackwell, 1993, p.1.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说:“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2〕[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王太庆校,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52 页。两者虽然论证方向相反,但论证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试图得出人和人工智能无差别的结论。正是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与人类的相似性,导致中外学界对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的呼声极为强烈。笔者综观各种倡导性观点,大体可以归结为两种论证进路:一种是基于人工智能创作作品著作权归属、合约履行、侵权责任等现实问题的解决,认为需要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笔者称之为功能主义进路;另一种是认为除自然人之外,法人团体、其他组织、动物等实体逐渐被纳入民事主体之列,民事主体范围有扩张的趋势,人工智能当然也可以获得民事主体地位,因果关系的建立依靠的是类比思维方法,笔者称之为价值主义进路。以下分别述之。
(一)功能主义进路
功能主义进路立足于社会关系变动的现实,认为人工智能引起的权属争议、法律行为后果、损害赔偿等责任承担问题只有通过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才能获得圆满解决。
有学者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和人工智能的“近人性”,意味着其将具有甚至已经开始具有一种颇具特色的能力,即“脱离人类控制而独立行动”,而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有能力独立影响他人的权利义务,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此种相对应的义务或权利归诸他人在一般情况下难言合理,也不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理,而只能归于人工智能。这意味着要认可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进行,它们撰写的稿件会变得有所不同,风格也大相径庭,这种独创性来自人工智能系统物质载体的自主学习,而不是来自其设计者、训练者或所有者,将其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是一个可行的方法。〔3〕参见李俊丰、姚志伟:《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一种法哲学思考》,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第84、85 页。有学者认为,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解决涉及人工智能产物的权利归属纠纷和人工智能侵权纠纷,需要从人类权利优先的立场出发,运用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赋予人工智能独立的法律人格。〔4〕参见杨清望、张磊:《论人工智能的拟制法律人格》,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第91 页。有学者认为,因为有人工智能这一特殊实体的存在,其产出物所有权、智力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和侵权损害的责任承担打破了现有的法律体系,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主体资格,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才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5〕参见贺栩溪:《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研究》,载《电子政务》2019 年第2 期,第103 页。还有学者认为,智能机器人的著作权归属、数据权利确认、侵权责任认定等争议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认定智能机器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应以“理性”作为智能机器人享有民事权利的根本依据,可以把智能机器人划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机器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机器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机器人,据此确定智能机器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范围。〔6〕参见叶明、朱静洁:《理性本位视野下智能机器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认定》,载《河北法学》2019 年第6 期,第10 页。
(二)价值主义进路
价值主义进路立足于民事主体范围不断扩张的趋势,认为自近代以来以自由意志为内核的自然人民事主体的伦理性逐渐松动,人作为唯一主体的正当性已经不复存在,法人团体和动物逐渐被纳入民事主体之内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当然应该像法人和动物一样被赋予民事主体地位。
有学者认为“实力界定权利”,权利主体的范围并非固定不变,权利主体的外延不再限缩于生物意义上的人,物种差异也不再是获得权利主体地位的障碍。比如历史上奴隶、妇女和黑人争取权利的抗争运动,动物和法人权利主体地位的获得也是其重要性程度不断提升的结果。〔7〕参见张玉洁:《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权利及其风险规制》,载《东方法学》2017 年第6 期。有学者认为,法律主体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其意涵范畴在不同人类文明阶段有所差异,生命体如人类、动物,无生命体如建筑、船舶、法人,在法律主体制度史上皆存在,确立“电子人”具有主体制度空间。〔8〕参见郭少飞:《电子人法律主体论》,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3 期,第42 页。有学者认为,从人工智能的特性分析,其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智慧工具属性,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的独特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法律人格。但这种法律人格同自然人或现有的拟制法人并不完全相同,应当确立人工智能的有限法律人格。〔9〕参见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载《东方法学》2017 年第5 期,第50 页。有学者认为,伦理性并不是民事主体的必然要求,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历史演变阐释了民事主体只是社会需要的法律形式,以法律工具主义为中心的权利与义务应是认定民事主体的法律标准,赋予智能机器人有限人格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需求,因而,其提出了人工智能“工具性人格”的概念。〔10〕参见许中缘:《论智能机器人的工具性人格》,载《法学评论》2018 年第5 期,第153 页。还有学者认为,处理人工智能主体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法律不应介入人工智能的技术黑洞,在人工智能具备智能(自主)时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在不具备智能时将其视为权利客体,特殊情况下将其“拟制”为民事主体。〔11〕参见陈吉栋:《论机器人的法律人格——基于法释义学的讨论》,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 期,第85 页。戴维斯教授认为,人工智能与法人类似,既然法人可以拥有法律人格,人工智能也应当拥有法律人格。艾博特教授也认为,赋予非人类作者/发明人法律人格,将为人类利用动物和人工智能之创造能力提供新的激励手段。〔12〕参见[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王太庆校,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12 页。
二、对功能主义进路的批判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衔接取决于法源与方法论之间的分工,裁判的过程就是从法源到个案正义的推进,法官在个案中不得拒绝裁判及法律解释、漏洞填补、法律续造等法律方法的运用,使得法源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特征。在民法方法论指导下成熟起来的法教义学,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抽象条文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发挥了找法、补法、统法和正法的功能。〔13〕参见汪洋:《私法多元法源的观念、历史与中国实践——民法总则第10 条的理论构造及司法适用》,载《中外法学》2018 年第1 期,第128 页。面对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首要选择是通过现行民法规范辅之以民法方法论予以应对。现有的民法规范以自然人为当然主体,法人团体次之,在不考虑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只能是作为客体存在的“物”。
其一,人工智能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个争议:一是人工智能作品是否构成“作品”,也就是是否具备独创性特征;二是如果构成“作品”的话,著作权归属于谁。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一般是基于算法、规则、数据等前置性安排,似乎不具有独创性,但最新的人工智能已经从模拟求解的符号主义模式发展到“仿生学”的人工神经网络的联结主义模式,具备深度学习的能力,它所生成的内容就连编程人员也难以预料,因此是具备独创性的,这种“作品”符合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要求。关于著作权归属问题,我国《著作权法》第二节规定了原创作品、翻译作品、汇编作品、合作作品、职务作品、委托作品等不同类型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都是发生在主体的“人”之间的著作权关系,既然人工智能作品也是作品,似乎《著作权法》对之无法进行调整。但笔者以为,以生成作品为使用价值的人工智能与其他消费品无异,都旨在实现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的使用目的,其生成作品恰恰是为了实现消费目的。此时可以把“作品”视为人工智能的孳息,将作品著作权归属于所有权人。〔14〕参见[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王太庆校,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71 页。
其二,人工智能合约的履行问题。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相对性,我国新出台的《民法典》 第464条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第50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些规定所体现的核心精神就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具有订立与不订立合同的自由,具有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对合同条款具有一般理性人的认知能力,能够预见订立合同、履行合同、违约所应当承受的法律后果,所以合同只能发生在具有意志能力的当事人之间。人工智能虽然具备一定的类似于人的认知能力,但却不具备意志能力,对自己的行为没有道德判断能力。它的行动是有理由的,但这一理由并不是人类对其进行道德肯定或道德否定的理由;而真正的道德理由既是行动者行动的理由,也是其他人对该行动者的行动进行回应的理由。〔15〕参见刘振宇:《人工智能权利话语批判》,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 年第8 期,第35 页。因此,人工智能的行为与人类行动之间不具有社会性关联,当然排除于合同适格当事人之外。对于智能合约,这个术语至少可以追溯到1995 年,是由多产的跨领域法律学者尼克·萨博(Nick Szabo)提出来的。他给出的定义如下:“一个智能合约是一套以数字形式定义的承诺(promises),包括合约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16〕参见MBAlib 智库·百科“智能合约”条,来源:https://wiki.mbalib.com/wiki/%E6%99%BA%E8%83%BD%E5%90%88%E 7%BA%A6,2019 年12 月29 日访问。智能合约的核心特征是减少协议执行过程中的人工干预,通过自动执行减少现实生活中违约行为的发生概率。而事实上,合同目的的实现就在于合同的履行,全部合同法的主旨也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智能合约的这一机制恰恰是保障合同履行的手段。合同目的不是智能平台的目的,而是使用智能平台的人的目的。因此,人工智能没有自己独立的意思表示,它只是按照既定的程序自动执行合同主体的意志。如果是因为程序设计或开发导致的条件触发问题,承担不利后果的合同当事人只能向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开发者等进行追偿,此种情形适用《产品责任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即可实现。
其三,人工智能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人工智能致害的责任承担问题是倡导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学者所提出的重要理由,他们认为,只要人工智能拥有主体地位就可以自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且不说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拥有和支配责任财产的现实可能性,即便从规范技术上创造条件,最后也只能回归到雇主责任或者法定代理的老路,而且还会与雇主责任和法定代理的原有规范意旨产生新的冲突。笔者以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人造物”,其诞生必然体现设计者、开发者的主观目的。弗朗西斯(Frances)等人曾提出过5 条将机器责任后果与设计者、适用者相关联的规则:〔17〕See Grodzinsky, F. S., et al.,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Computing Artifacts: the Rules and Issues of Trust” 42(2), ACM SIGCAS Computers and Society, 15(2012);转引自吴习彧:《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6 期,第64 页。规则一,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开发者或者组织者,应该对该产品以及该产品带来的可预见性效果负有道德义务,这种道德性义务与其他设计者、开发者、组织者或者有意识地将该产品投入社会系统使用的人员一同共享。规则二:上述共享性义务并非是零和博弈。个人的义务并不因为有更多的人加入设计、开发、组织或者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群体中而缩减。相反,个人应当对人工智能产品的行为及投入使用后的影响负责,这种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指他能够合理预见到的。规则三:特定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人(明知状态下的使用)应当对其使用行为承担道德性义务。规则四: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者、开发者、组织者或者使用者的义务范围限于他们对社会系统中的人工智能产品的合理认知。规则五: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者、开发者、组织者、 促进者以及评估人员不应对使用者就人工智能产品本身,或者其可预见性的作用,或者其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进行明示或暗示性的欺骗。这5 条道德规则既构成人工智能相关行为者行动的道德理由,也是司法裁判中说理论证的实质理由。因此,人工智能致害的责任应由其背后的设计者、开发者、组织者、使用者等“人”的主体来承担,具体情形根据《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法》相关的归责原则和追偿规范予以救济。另外,发展风险是产品责任中的免责事由,人工智能生产者要通过购买保险、履行跟踪观察义务等方式满足免责条件。〔18〕参见杨立新:《人工类人格: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兼论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载《求是学刊》2018 年第4 期,第95 页。同时,还可以借助保险、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提供更多的责任承担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功能主义进路的以上三点现实理由都可以被现有规范予以涵摄,没有必要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但法学方法论的适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法律规范的僵硬和体系封闭的不足。
三、对价值主义进路的批判
价值主义进路的核心思想是伴随着法人团体、其他组织、动物等被纳入民事主体之列,民事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自然人不再是唯一的主体,人工智能也当然可以成为民事主体。其中蕴含了三个不同层面的含义:(1)形式上的:民事主体范围扩张;(2)方法上的:类比式思维,其中又包含两个分支,人工智能与法人相似、人工智能与动物相似;(3)实质上的或结论上的:人的主体性被消解。笔者采取的论证思路是:第一步,回溯民事主体的思想史渊源,澄清民事主体地位的价值内涵,借以回应含义(3);第二步,分别讨论法人团体的民事主体价值和动物的民事主体价值,说明它们与自然人民事主体的关联,以及与人工智能在价值上的本质区别,进而回应含义(2)和(1)。
(一)民事主体的思想史渊源
实在法上民事主体地位的制度设计伴随着思想史上人的主体性的确立,经历了客观法向主体法、义务法向权利法的转变过程。人从探求外在世界的终极本原转而关注人自身,是人为自己立法时代的产物,具有深刻的伦理内涵。
1. 主客体二元观念的诞生:客观法转向主体法
在人类的童年,人类并没有与其他存在(生物性存在,甚至是非生物性存在)相区分,因为这时人类尚缺乏发现、甄别自身与他物区别的能力,进而人类在这种物我一体的状态下,适用着统一的自然法。〔19〕参见江山:《人际同构的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5 页。这个自然法是判别在人与神、与自然、与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一切问题上是非好坏的绝对标准。施特劳斯将其称为自然正确或自然正义。〔20〕参见徐航:《自然法的存在与虚无——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法概念考辨》,载《学习论坛》2017 年第11 期,第72 页。“自然”既是实体存在物,同时也是实体存在物之所以为实体存在物的原因。而“自然”是被古希腊哲学家们本着“凡事皆有因”的逻辑发现的。〔21〕See Grodzinsky, F. S., et al.,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Computing Artifacts: the Rules and Issues of Trust” 42(2) ACM SIGCAS Computers and Society 15(2012). 转引自吴习彧:《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6 期,第73 页。在这种自然正义观下,人与物无分主客体,一切统摄于自然的必然性之下,遵循自然的生活就是良善的生活。基督教神学将世界的最高主宰由自然换成了上帝,人与自然区分的观念逐渐显现。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借用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因”和“第一不动的原动者”的概念,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论证,充塞于自然的“逻各斯”就令人信服地变成了人格化的上帝。〔22〕参见柯岚:《托马斯·阿奎那与古典自然法的巅峰》,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 年第2 期,第45 页。自然法不再来源于自然,而是来源于体现上帝之理性的永恒法,是作为理性造物的人对永恒法的分有,其本质上是人所专有的自然理性。“人被认为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即是上帝的从属,又是它的合作者。”〔23〕[意]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 年版,第44 页。人作为上帝特殊的受造物就与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及至近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终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解构和贬降了自然,人通过理性发现了一套不同于上帝启示真理的自然真理。以至于培根认为“自然和人的王国中,人就是上帝”。〔24〕江山:《人际同构的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15 页。至此,人相对于自然获得了完全的主宰能力,自然变成了人认识、支配和改造的对象,而人则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笛卡尔明确提出了“人—物”主客二分的结构,人类历史真正进入了属人的时代,奠定人为自然立法、为自己立法的根基,客观法完成向主体法的转变。
2. 自然权利观念与民事法律人格:义务法转向权利法
民事主体地位的获得通过实在法上赋予民事法律人格来实现。而民事法律人格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从古罗马法上基于身份的差等人格到近代自然法典上普遍的平等人格,伴随着客观法向主体法转向的历史进程,并通过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观念得到完整的展现。〔25〕参见李拥军:《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民事主体制度与理念的历史变迁——对法律“人”的一种解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 年第2 期,第45-51 页。及至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既以神学的上帝打压和贬低自然,又以复兴古代思想为名借助自然驱逐上帝。格劳秀斯率先把自然法的特征归属于人的范畴,否定自然法是整个宇宙的法则并贯穿于万物之中,认为人性是自然法的基础,法的来源和存在依据是人类对有序生活的内在追求。〔26〕参见任宇宁、李永军:《神启、理性到实证:西方自然法哲学的革命性转向》,载《新疆社会科学》2015 年第5 期,第11 页。而霍布斯则从认识论上颠覆了传统自然法的价值基础,他把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解构人类社会,找到了个体“人”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再根据“人”重新组合建立政治社会,这种“分析—综合”的机械论自然哲学彻底否定了传统道德哲学一切关于人的“至善”的目的论前提。〔27〕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朱敏章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版,第81-160 页;吴增定:《人是不是自然世界的例外?——从斯宾诺莎对霍布斯自然权利学说的批判说起》,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3 期,第6 页。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的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的是一系列的权利。〔28〕参见江山:《人际同构的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 页。从霍布斯开始,包括洛克、卢梭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家提出了自然状态的假说,探讨人在自然状态下依据自然法所享有的天赋权利,人不仅是独立、自由、平等的,还能够基于本性通过缔结社会契约建立政治国家。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努力使人第一次不依赖于外在的自然或神意而创建自己的共同体,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使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体现。在自然权利观念的影响下,1796 年《普鲁士普通邦法》、1804 年《法国民法典》、1811 年《奥地利民法典》等一批自然法典诞生。《法国民法典》第8 条明确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确认和维护了人的平等人格和尊严,这部法典也成为人类法制史上弘扬自然法理念的光辉典范。〔29〕参见马俊驹:《从身份人格到伦理人格——论个人法律人格基础的历史演变》,载《湖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6 期,第47 页;孙聪聪:《人格作为法律主体的伦理与技术——基于历史进路的考察》,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第82 页。至此,基于人的自然权利,民事主体资格被赋予所有的自然人,在法律上人人平等,人类进入权利法时代。
3. 自由意志与实在法的权利能力:自然人转向伦理人
近世以来,受德国民法传统影响的国家都在实在法中以权利能力为确立民事主体资格的标志。权利能力这一概念是蒂堡在《潘得克吞法的体系》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权利能力的取得条件并不包括身份因素,而是基于对人的生理属性进行伦理判断而取得的。〔30〕Anton Friedrich Justus Thibaut, System des Pandekten-Rechts, Bd. I, 2. Aufl., Johann Michael Mauke, Jena, 1805, S.156-159.转引自杨代雄:《主体意义上的人格与客体意义上的人格——人格的双重内涵及我国民法典的保护模式选择》,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 年第4 期,第56 页。伦理人的发现是由康德哲学完成的。在康德的理论中,将伦理学和物理学等量齐观,认为两者都是以普遍必然规律为对象的科学,一种规律是万物循以产生的自然规律,一种是人类的意志,在自然的影响下给自己规定的规律,是自由规律、道德规律。〔31〕参见[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 页。自由规律不是从经验中来,它纯粹是自我对自我的立法,因此即是绝对命令也是绝对自由。康德认为:“道德原则并不是公设,而是理性据以间接规定意志的规律。意志受到这样规定,就成为纯粹的意志,正因为如此,就要求有这些必要的条件,使它的规范得到遵守。”意志自由的根据在于“必须预先认定人是可以不受感性世界摆布的,能够按照超验世界的规律,即自由的规律来规定自己的意志”。〔32〕赵俊劳:《自然人人格的伦理解读——兼论德国民法典人文主义的价值起点》,载《河北法学》2009 年第5 期,第34 页。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意志自由并非将自己限定于主观领域,当意志自由按照普遍的正义法则将自身扩张到外物上,就形成了私法上的权利。由此可见,意志自由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条件,也是主观权利的价值源泉和逻辑起点。〔33〕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54、55 页。既然每个人先天就具有意志自由的本质属性,当然也能够成为私法上的权利主体,这是先验原理的必然逻辑结果。所以,萨维尼说:“法律关系的本质被确定为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34〕[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I 法律渊源·制定法解释·法律关系》,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年版,第335 页。“所有的法律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存在,即存在于每个人内在的自由意志当中。人格或者法律主体最原始的概念必须和人的概念相一致……权利能力和个人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35〕Siehe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m Roemischem Recht, Bd. 2. Berlin bei Deil und Comp.1840, s. 3、236.普赫塔在《现代罗马法讲义》中指出,人格(persnlichkeit) 是使人(mensch) 成为权利主体的属性,是一种可能性或法律力量,即权利能力。〔36〕Georg Friedrich Puchta, Vorlesungen über das heutige rmische Recht, Bd. I, 4. Aufl., Bernhard Tauchniss, Leipzig, 1854, S. 56.转引自杨代雄:《主体意义上的人格与客体意义上的人格——人格的双重内涵及我国民法典的保护模式选择》,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 年第4 期,第56 页。《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说明书认为,不论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个体性及其意志,承认其权利能力是理性和伦理的一个戒律。〔37〕参见[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58 页。权利能力概念承载着现代民法维护人的伦理价值和个体尊严的使命。所以拉伦茨说:“《德国民法典》认为每一个人都生而为人,对这一基本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全部后果,我们只有从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出发才能理解。”〔38〕[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45 页。人不再把目光聚焦于世界本源的探求,人首先是人,而不是因为法律的确认而使其成为人。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全面考察完成了哲学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也实现了自然人向伦理人的理解转向。
(二)法人与动物民事主体地位的价值
法人作为组织体逐步取得了与自然人同样的民事主体地位,部分国家的实在法还对动物的民事法律地位做出了特殊规定。但细致考察相应的规定及其价值可以发现,它们都未能撼动民事主体的伦理根基,二者更与人工智能具有本质区别。
1. 法人民事主体地位的价值及与人工智能的区别
团体作为人格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比如自治城邦、市镇、乡村,还有帝国后期的行省、僧侣会、私人志愿团体等,这些往往类似于现代公法意义上的法人。〔39〕参见[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51-53 页。到11 世纪时各种宗教团体占主导地位,还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伊斯兰穆达拉巴的康曼达。〔40〕参见[美]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第429、430 页。穆达拉巴,是伊斯兰合伙的一种形式,一方只负责投资,另一方负责管理投资,这两种角色银行均可承担。参见[加拿大]帕特里克·格伦:《世界法律传统》,李立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10 页。但第一个使用“法人”术语的学者是德国法学家胡果,有关法人性质的讨论开始于深受康德影响的萨维尼提出的拟制说。“法律人格是在每个个人的意义上被表达的。法人,是我们对照个人而进行的技术上扩充得到的纯粹拟制主体。”〔41〕Siehe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m Roemischem Recht, Bd. 2. Berlin bei Deil und Comp.1840, s.236.这种学说否认法人的伦理属性,法人的主体地位仅仅是一种法律的技术设计。与之相对的是贝塞勒和基尔克所倡导的实在说(又称团体本位说),这种学说认为法人作为团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意志的伦理实体,甚至是高于个人的生命单元。〔42〕参见吴宗谋:《再访法人论争——一个概念的考掘》,“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第64、65 页。转引自漠耘:《主体哲学的私法展开:权利能力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216 页。还有一种学说是由法国学者米休和撒莱等人提倡的组织体说,认为法人是作为一个组织体而实存,这个团体能拥有自己的意思,是依整体程序讨论的结果。〔43〕参见漠耘:《主体哲学的私法展开:权利能力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227 页。在《德国民法典》通过以后,人们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接受了这一制度事实。有学者认为,法人制度的出现纯粹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法律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与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44〕参见尹田:《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 年第1 期,第123 页。这种工具化思维很容易合理化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的类比要求。因此亟须澄清的是,法人团体是否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无论是萨维尼的拟制说,还是基尔克的团体本位说,都必须承认法人团体能够形成自己的意志,这种团体意志能够行使权利、承担义务达到与自然人主体同样的效果,这正是组织体说的基本主张。也就是说,法人的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仍然由组成法人的自然人来完成,是自然人依照程序进行的一种集体契约,这种契约独立于组成法人的自然人,但最终仍可以追溯到自然人,所谓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原理正是从此而来。法人主体相对于自然人主体而言,仅仅是形式上的差异,在行动能力上没有本质区别,法人制度的创立没有根本改变民事主体地位的伦理根基。人工智能作为人造物与法人这种自然人组织体存在本质区别,它没有自己的意志能力,无法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所以两者的类比无法成立。
2. 动物民事主体地位的价值及与人工智能的区别
20 世纪中叶以来,风险社会来临,环境损害日益严重,很多物种面临灭绝的危机,人们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探讨如何保护环境、资源、动物等自然事物,一些环境法学者和民法学者提出了动物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的问题,认为基于自然法而提出的天赋人权并非人类所独有,动物也应该享有自由、平等、身体完整等基本权利。还有一些学者从动物与人的生物学联系,动物的社会性、文化性、道德性诸方面论证“动物应为法律上之主体”。〔45〕参见高利红:《动物应为法律上之主体》,载吴汉东主编:《私法研究》(第4 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 页。有鉴于此,《德国基本法》在2002 年进行了修改,以建立保护动物的国家责任,不过是在该法第二章(“联邦和州”)而非第一章(“基本权利”)。〔46〕参见[加拿大]帕特里克·格伦:《世界法律传统》,李立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8 页注154。《德国民法典》将总则编第二章标题“物”改为“物和动物”,第90a 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受特别法律的保护。以不另有规定为限,关于物的规定必须准用于动物。”〔47〕《德国民法典》(第4 版),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30、31 页。《瑞士民法典》也紧随其后,在新增的第641a 条中规定“动物非物”,但物法对它们仍然适用证明所有权、买卖等规定。〔48〕参见[加拿大]帕特里克·格伦:《世界法律传统》,李立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8 页注154。这使得动物的法律地位变得极为模糊,动物非物,也不是人。纵观世界各国,采取这种做法的国家寥寥无几。动物不能成为民事主体的根本障碍就在于动物尽管和自然人一样具有生物属性,有的动物还有群居的社会性特征,但动物没有意志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无法形成对法律的规范性认知。这里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有关动物的所有讨论都是人在讨论,动物是无法参与其中的。当然与动物相比,人工智能不仅没有生物属性,也无法形成对法律的规范性认知。而且就价值取向而言,对动物的保护是出于对人类工具理性的反思,尤其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破坏性效应的反思。人工智能是人类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需要反思的事情,与保护动物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两者根本无法类比。
从以上对民事主体地位的思想史溯源可以发现,建基在伦理人观念基础上的民事主体制度是现代民法制度的根基,是客观法向主体法、义务法向权利法、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的成果,是人类逐渐祛魅走向文明的重大成就,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制度坚守。法人制度的创设并没有动摇这一制度的根基,动物也无法现实性地承受民事主体地位的资格,人工智能与法人和动物在性质上都存在本质差异,与后两者不具有可类比性。由此,诉诸类比方法的价值主义进路也无法成立。
四、结论:捍卫主体法的保守主义态度
无论人类社会多么不情愿,数字时代真的来了。〔49〕参见王勇:《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主体理论构造——以智能机器人为切入点》,载《理论导刊》2018 年第2 期,第63 页。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说机器人伦理问题、人机关系伦理问题、人文精神危机、数字鸿沟、贫富分化、产生“无用阶级”、侵犯隐私、金融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监管困难等。〔50〕参见马长山:《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及其法律规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6 期,第47-54 页。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是否应当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问题。目前,倡导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的学者大体遵循基于社会现实的功能主义进路,和基于类比法人、动物民事主体地位的价值主义进路展开论证,笔者从现有民法制度的规范功能和回溯民事主体确立的思想史渊源角度予以批判。现行民法规范辅之以民法方法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法教义学,产生民法法源的开放性效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概念主义的形式缺陷和体系封闭的弊端,能够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予以回应,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著作权归属、智能合约、智能侵害责任等都能被现行法规范所涵摄,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通过对民事主体确立的思想史考察可以发现,自然人民事主体地位的确立伴随着世界观上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与独立、自由、平等等天赋的自然权利观念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最终康德意志自由的先验哲学划定了人与外物的本质区别,为实定法上的权利能力制度提供了伦理基础。伦理人的意义在于不需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而是人自身的意志能力即可确定人之为人,这种意志能力具有规范性认知,对“应当”具有辨别和选择的能力。对于人的发现关涉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演进历程,其间经过了客观法向主体法、义务法向权利法、本体论向认识论的重大转向,是人本主义的实践,是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确立过程。因此,民事主体制度的设计不是单纯的立法技术的使用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伦理内涵。一旦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意味着两种智能主体的并存,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建立的法律关系大厦将面临倾覆的危险,主体法时代的法律框架将可能坍塌,人的历史将被改写。自从1869 年杰芳斯在改进布尔逻辑代数的基础上创制第一架逻辑计算机,对人类思维进行机械化加工的进程就开始了,但逻辑终究是有界限的,它只是对人类思维进行定量研究,是一般思维的单纯形式的科学,抽调了一切内容。〔51〕参见马玉珂主编:《西方逻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322、386 页。人工智能依赖于思维的机械化,是模仿人的认知,是理性的思辨运用,与意志支配行动的实践理性不同,实践理性依据道德律令以实现“善的意志”为最高目的。寄望于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是对理性不同运用方式的混淆。〔52〕参见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62 页。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工具性思维渗透进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科技对伦理的僭越,已经造成了人的生命的无“意义”感。〔53〕参见[芬兰]冯·赖特:《知识之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1-88 页。诚如著名科学家霍金所言:人工智能的真正风险不是它的恶意,而是它的能力。人工智能的成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隆重的事件,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结。〔54〕参见赵万一:《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辨析——兼谈对机器人进行法律规制的基本要求》,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 期,第161 页。人的历史是社会活动的历史,人通过生产实践来确证自身,但人也就此可能被自己实践活动的产品所奴役。在没有神的世界,人类需要自我救赎。面对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人应当坚持保守主义态度,这对于法哲学的重大意义在于:从人类独有的理性出发,推导出人在与外部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作为主体的自由属性,并将其设定为法权体系展开的逻辑条件和终极目标。〔55〕参见陈璞:《论网络法权构建中的主体性原则》,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3 期,第74 页;陈景辉:《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1 期;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载《比较法研究》2018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