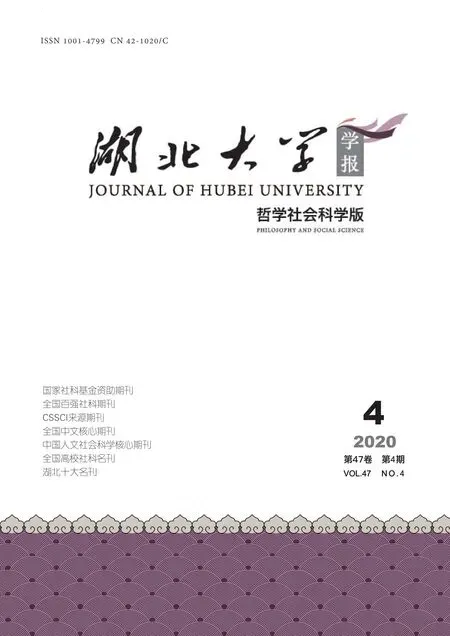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原则及其困境
2020-01-11陆鹏杰
龚 群, 陆鹏杰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爱或仁爱是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中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价值概念。在中国儒家伦理观念中,仁爱处于首要地位,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西方思想史上强调爱的伦理主要是基督教,基督教提倡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因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种平等的爱,一般又称之为博爱。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与儒家的仁爱,这两者是有所不同的。儒家仁爱观念强调“仁者爱人”,但是以孝悌为本,所注重的是亲亲疏疏,即亲者则亲,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则疏远些,爱是有差等的。基督教强调一视同仁的博爱,不过,这种博爱观念的背景则是对上帝的信仰。除了基于血缘家族背景和宗教背景的仁爱观或博爱观外,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仁爱观?或者说,从其他进路是否还可以提出一种仁爱观?本文主要讨论一种从功利主义进路而来的仁爱观,即斯马特(J.J.C.Smart)的普遍仁爱观。基于血缘或基于宗教信仰的仁爱观都有它们的不足,斯马特基于功利主义的仁爱观是否是一种更可取的仁爱观?或者说它是否会有其本身不可克服的困境?
一、“普遍仁爱”:功利主义最高道德原则的转换
近现代以来,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是一种重要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它的最高原则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最大多数”这一概念所指是相对于一定范围的人口而言。在最大范围意义上,就是全人类范围的最大多数;在一定国家范围内,就是这一国家人口的最大多数。因此,“最大多数”的说法并非是将全体人类纳入到考虑的范围内,而是选取其中的最大多数。“最大多数”这一量词也可以在可比较的意义上使用,是在不同选项所涉及的人口意义上的最大多数。这两种意义上所说的“最大多数”在数学意义上到底是多大的量呢?如就前者而言,是85%、90%,还是95%?没有一个功利主义的经典作家告诉过我们。就后者而言,即在A、B、C等不同政策选项所涉及的人口意义上,取其可能惠及的最大多数;这一种“最大多数”仅仅是可比较意义上的,换言之,如果A选项比B选项所惠及的人口多1%,而比C选项少1.5%,那么,选择C选项就是正确的。功利主义这一原则中还有一个重要概念——“最大幸福”。“最大幸福”这一概念也可在总量意义上和可比较意义上使用。在总量意义上,即是指一定幸福指数在人口总量上所达到的最大化,这里可以说是人口基数越大,那么,幸福总量越大;在可比较意义上,则是就一定可比人口或确定性人口来说,幸福指数相对于以往历史时期所达到的最大化。就前者而言,即使平均每人的幸福指数不变,但在人口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最大化的幸福总量必定增长;就后者而言,即使人口基数不变,但平均每人的幸福指数不断增长,从而达到幸福的最大化总量。还有第三种情况,即在不同选项中那个“最大”量上使用。假设有A、B、C多个选项,如果实行其中某个选项,就能够带来可比较的较小、较大或最大幸福,那么,就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而言,选取那个能够在可比较的幸福量上的最大幸福才是在道德上能够得到赞同的选择。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其“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首先是在行动决策意义上使用,如果我们的行动决策选择了那个能够带来最大幸福的行动方案,那么这就是正确的选择。当我们在行动前面临可比较选项时,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进行行动决策选择,换言之,就是把“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看成是一个指导我们行动决策的原则。同时,“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又是一个行动评价原则,这是因为,在行动或执行政策决定之后,我们可以依据这一原则来对我们的行动或行为进行评价。假设在三种方案中,我们选择了其中并不能够带来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方案,在可比较意义上,我们的行动或执行政策的后果,对于大多数人就没有产生最大幸福,那么,这样的行动或政策后果就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或者说,我们就失去了为这样的行动或政策进行辩护的强有力的理由。在功利主义看来,这样的行动就不是正当的行动。不过,功利主义作为一种行动(行为)评价理论有它的不足,因为决策本身是与动机相关的,但后果才是功利主义进行评价的依据,并且是唯一的依据。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动机就一定能够导致想往中的理想后果吗?当然,囿于本文主题,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
在规范伦理学理论中,功利主义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相较其他理论而言,体现了伦理学对道德善的追求的理想境界。自古希腊以来,伦理学就被认为是对善或幸福追求进行探讨的学问,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所设的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幸福,伊壁鸠鲁的伦理学就被人们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然而在思想史上,虽然不同的思想流派都认肯这样一种追求,但是却极少将其量化。“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中的两个“最大”,从普遍意义上看,体现了功利主义对人类大多数的一种仁爱情怀。换言之,功利主义意识到,历史上伦理学家们都指出人类行动是趋于善的,但是并非所有行动或行动方案都可以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一种最大的善。可是,边沁等人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是否就是对于人类这一追求的完美表述呢?对于边沁等人提出的这样一个原则,人们仍然认为它在道德上不够高尚,这是因为“最大多数”这个概念,就意味着把相对一少部分人从道德关怀中排除出去了。无论我们怎么说这个“最大多数”(如不管是90%,还是95%、96%)是多大的最大多数,总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没有进入到功利主义的道德关怀之中。当我们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时,是否可以牺牲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的幸福?或以他们的幸福为代价来换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功利主义的这个原则来看,并非不可以。相当多的伦理学家都对功利主义的这个最高原则提出了批评。如麦金太尔就十分形象地批评说:“如果在一个十二人组成的社会中,其中十个人是虐待狂,他们将从拷打其余两人中得到最大乐趣,那么,遵从功利原则的命令,这两个人就应当受拷打么?”(1)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10页。显然这是很荒谬的。功利主义的这一最高原则似乎在这样的批评面前得不到辩护。
当代功利主义的一个最大改进,就是对“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最高原则的改进。当代重要的行动功利主义者斯马特所做的努力就是通过后果概念将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改进为一种后果论的普遍仁爱原则。斯马特在《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Utilitarianism,ForandAgainst)一书中,对行动功利主义(act utilitarianism)的界定是:“大致地说,行动功利主义是这样的观点:一个行动(an action)的对与错唯一地依据它的后果的总体的好与坏,即该行动对全人类的存在者(或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的福利(welfare)产生的效果(effect)。”(2)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4.换言之,就行动功利主义的标准而言,一个行动的好与坏,不在于对行动者本身而言的好与坏,而是从全人类的存在者或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的视域来看,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后果。这里我们看到,斯马特放弃了边沁功利主义最高原则中的关键性概念——“最大多数”,他用“全人类的存在者”这一概念取代了它。斯马特说:“为了确立一种规范的伦理学系统,必须诉诸某种终极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他与他的对话者共同持有的。他诉诸普遍仁爱(generalized benevolence),也就是追求幸福的意向,总而言之,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对全人类或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而言的好的后果。”(3)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p.7.这一说法较之前面更进了一步,即好的后果是对于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而言,在前面的表达是在括号中提及,而这里明确把“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放在与“全人类”并列的地位。但是,什么样的动物可以称之为有知觉的存在者?他并没有进一步讨论。斯马特敏锐地把他的后果之好命名为“普遍仁爱”的原则。什么是“爱”或“仁爱”呢?爱或仁爱在于对被爱对象的呵护、关照,更是对其幸福意向的尊重、保护或促成,换言之,当我们爱某一个人,应当是希望和促成他/她的幸福。“benevolence”一般译为“仁慈”、“慈善”,即对他人有着实质性好的行动或事情,这种实质性的“好”在某种意义上都与人们的幸福感相关。因此,无论是儒家之仁爱还是基督教的博爱,都可以归之为我们的行动是为了被爱对象的幸福。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伦理学没有不认为追求幸福是所有人类存在者的普遍意向,幸福是所有人所欲求的目标。而当我们自己的行动后果是以对所有人类存在者或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而言的好后果时,这也就是“普遍仁爱”的意志倾向,即“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对全人类或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而言的好的后果”。与儒家的“仁者爱人”要求以及基督教的“对邻人的爱”要求相比,“普遍仁爱”无疑是一个更高的普遍爱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儒家仁爱观的不足,即如果不是具有像宋代张载那样的境界,我们难以把我们的爱扩展到超出我们的亲朋关系之外,更难说“民胞物与”了。这一普遍仁爱观,对于基督教的博爱来说,应当说在爱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其优点是不需要有宗教信仰的前提,而只是从道德上提出了一个理想目标。
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是他的行动功利主义理论体系中所设置的最高道德原则和目标。这一原则不仅是一个对行动的总体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对我们作为道德行动者的任何具有道德意义或可能产生道德后果的行动的要求。功利主义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功利主义关注的基点是人们的行动,或每一个可能产生道德意义的行动。对于斯马特的那个一般性的命题——“一个行动(an action)的对与错唯一地依据它的后果的总体的好与坏,即该行动对全人类的存在者(或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的福利(welfare)产生的效果(effect)”(4)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p.4.,我们要注意到,斯马特所说的“一个行动”,实际上应理解为“我们的所有行动,或每一个行动”,即是将我们所发生的所有行动都包括在内,因而是一个在他看来对所有人类的所有行动的评价衡量标准。自边沁以来,功利主义就声称它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是对所有人的行动有效的道德标准,就此而论,斯马特的功利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没有区别的。
不过,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后果论与边沁的后果论是不同的。边沁的功利主义也强调对一个行动的好与坏的评价,要看一个行动的后果,但是,边沁的行动后果是从行动者本身的视域来看的,并且边沁的后果论是一种快乐主义的后果论,即边沁强调从行动者自身出发,强调一个行动为行动者带来或产生的快乐的量是否多于痛苦,如果是,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行动,如果不是,则是一个不值得肯定的行动。斯马特则把边沁的行动者相关(agent-relative)的后果论改造成了行动者无关或行动者中立(agent-neutral)的后果论,尤其是把行动者的视域从行动者本身无限拉开,以全人类存在者甚至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视域来看待一个行动后果的好与坏。换言之,任何一个行动者在从事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时,都自觉地把自身考虑拉开,而将自己的行动与全人类存在者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因而并不是边沁意义上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从自我快乐意义上的简单相加(5)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在边沁那里,社会幸福也就是个人幸福的简单相加,因而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也就是每个人的幸福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从普遍超越意义上的全人类存在者的福祉成为了功利主义思考的重心。因此,这不仅是一种新的后果论,同时也是一种不同于边沁的道德最高原则,即后果论的普遍仁爱原则。这种后果论从行动者中立角度关切幸福,是将所有人或所有存在者的幸福作为目的来追求。因而,这样的原则,明显地可以规避麦金太尔式的攻击。这是因为,即使我是一个虐待狂,也不应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斯马特把行动的评价从行动者那里移开,将所有存在者的幸福作为自己行动好坏的标准。
斯马特后果论的普遍仁爱原则,是从一种理性超越的层面,而不是从人们的经验层面来提出的。边沁提出的快乐主义的后果论,是可感知、可亲身体验的后果论。斯马特要求我们将自己的视域转换为所有他者的视域来审视自己的行动,这是一种理性要求,而不是感性直观的体验。他与边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边沁强调我们的行动给我们自己所带来的快乐和痛苦,强调快乐与痛苦的量比;斯马特则要求我们超越自己,以理性来预测或把握行动后果。那么,“快乐”与“痛苦”这样感性体验的概念还有意义吗?我们注意到,斯马特的后果概念不再是快乐与痛苦的量,而是行动所产生的对于所有他者而言的好的事态(the stat of affair)。前述已指出,这样一种视域又可以说是一种行动者中立的视域,所谓行动者中立,即不从行动者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而有所好恶,而是不偏不倚(impart),对所有他者的利益都一视同仁地关心或爱护。同时,功利主义还有另一个基本要求,即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决策理论,当我们面对可选行动方案时,那能够实现最大化好的方案是功利主义所赞许或肯定的方案。儒家差等之爱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决策论,而是一种仁者怎样施爱的方法论,即爱从哪里下手的问题。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原则则是功利主义的后果论的具体化,即后果的好与坏要以是否符合这样一种普遍仁爱的原则来衡量。儒家的仁爱强调施从亲施,即爱从最好下手的地方开始,在儒家看来无疑能得到直接的好的后果,但很难说能得到从普遍意义上看的最大化好的后果。在斯马特看来,则只要是能够最大化这样一个可普遍化目标的行动,就是可以得到其行动功利主义辩护的行动。换言之,儒家的仁爱也并非不注重后果,但它所注重的是行动的直接后果,即对自己的亲人的关爱或呵护,而对于这一行动之后还是否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那些不是自己的亲朋,甚至是陌生人,则语焉不详;但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追求,不仅是要求将自己的行动目标与自己本身拉开距离,而且是要求从普遍意义上能够最大可能地做到和做好。然而,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能够成立或得到辩护?
二、“普遍仁爱”的困境
斯马特对边沁的功利原则进行转换,提出了迄今为止功利主义最为崇高或高尚的伦理原则。然而,这样一种崇高的普遍仁爱的功利后果论一提出,就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即人们何以能够做到?德性伦理学家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就对斯马特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他们两人观点相对的两篇文章就同时收在《功利主义:赞成或反对》这本书之中。威廉斯的批判是以案例法进行的。他举了两个案例:
案例1:乔治是一位刚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青年人,他已经有了家室和孩子。现在毕业了,急于需要有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但现在的就业行情使得他所学的专业很难找到工作。他的妻子在家照料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成了问题,因此妻子不得不外出工作。一位老化学家知道了乔治的困难处境,很同情他,主动建议他来自己的实验室工作,并且答应给他一份较高的报酬。不过,老化学家告诉他,这个化学实验室的工作是研究制造生化武器。乔治很想要工作,但他有很强的人道主义情怀,不愿意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制造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因而他想拒绝老化学家提供的就业机会。然而老化学家对他说,如果他不来工作,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做这份工作,而且另外来的人会比他更热心做这项研究。实际上,老化学家自己也并不热心进行这样的研究,因而对于那个更热衷于这份工作的人并不感兴趣,他更愿意让乔治来做这份工作。乔治的妻子也有这个意向。现在乔治非常为难,他很爱他的妻子,对妻子的意见一般很尊重。但是,他内心确实很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那么,乔治是否应当接受这份工作?(6)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pp.97-98.
案例2:植物学家吉姆在南美考察植物,他来到一个小镇的中心广场。广场靠墙处站着一排被捆绑着的20个印第安人,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看押着他们。这些军人中,负责的是一位上尉军官。吉姆和这位上尉早就认识,但他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相遇。上尉今天准备处决这些印第安人,不过,他对吉姆说,为了表示对来自国外到访者的友好,如果吉姆亲手处决一个印第安人,他就把其他19个人都放了。如果吉姆不接受这一要求,全部印第安人都将被处死。但吉姆从来没有杀过人。那么,吉姆应当如何抉择?(7)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p.98.
从斯马特的行动者中立的后果最大化好的要求来看,在第一个案例中,乔治应当接受研究制造生化武器的工作。这个“应当”是从这个可能行动的后果来看,不仅对他的家庭、他的妻子来说是增加了幸福感,同时对老化学家来说,用乔治比用他人更让他心情好。并且,后果主义会认为,即使乔治不做,也有其他人会做,甚至会更热心做这份工作;而如果乔治接受了这份工作,则相比其他人做这份工作而言,还增加他的家庭的幸福以及老化学家的快乐。因此,依据斯马特的后果主义最大化好的普遍仁爱标准来看,乔治应当接受这份工作,即由于乔治接受这项工作,增多了这个世界的更多幸福或快乐。然而,乔治从情感上不能接受这份工作,这与他的人道主义情怀有根本冲突。因此,如果按照行动者中立的观点,从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好的标准要求来看,牺牲乔治的人道主义情感才是正确的选择。就第二个案例来看,让吉姆亲手杀人,这对于一个考察植物的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事。他所受的道德教育从来就把无辜杀人看成是一种道德的恶。然而,同样地,如果从行动者中立立场,即不从吉姆自己的情感感受而从后果主义的最大化好的标准要求来看,则应当赞许这样一种行动。威廉斯说:“以一种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感情,它们就像是与我们的道德自我毫不相干,也就是说,因此失去了行动者的道德身份(同一性)的感觉,以一种近乎直白的说法(in the most literal way),失去了完整性(integrity)。并且就此而论,功利主义将一个人的道德情感与他自己相异化……更基本地看,这也是与他自己的行动相异化。”(8)J.J.C.Smart,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p.104.“完整性”在这里是在人格意义上讲的。在威廉斯看来,人的道德情感、情操以及信念,都是人格或道德人格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遵从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的要求,从行动者中立的立场看,乔治和吉姆都应把自己的情感和操守看得一钱不值,这也就必然破坏人格的完整性,导致对自我人格的异化。
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是功利主义诞生以来的最高道德要求,它超越了边沁所提出的最高道德原则,然而,十分吊诡的是,如此崇高的道德要求却会导致人的道德人格完整性的丧失,导致人的情感与行动的异化。不仅如此,后来人们的批评还指出,这种从全人类的存在者出发的普遍仁爱要求,还会导致对个人生活计划的侵犯,即导致对个人生活整体的完整性的破坏。假设行动者A现在已经是一个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原则的信奉者,他觉得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体现这个原则,并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今天刚领了工资,在计划了一个月的基本生活开支后,还会有一些富余。他决定以普遍仁爱原则来指导自己使用这些资金。他以往有每月去餐厅改善一下生活的习惯。如果他还像以往一样,他的功利主义信念就会告诉他,这样的选择不是正确的选择,而正确的选择是把他用以改善生活吃大餐的钱捐赠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将会把他这些钱用以救济那些非常需要资金的病人或穷人。可当他的朋友邀请他一起去餐厅,他还是抵挡不住美餐的诱惑。马尔甘(Tim Mulgan)也设计了一个“阿夫鲁特”案例:阿夫鲁特(Affluent)是发达国家的一个富裕公民,她是一个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原则的信奉者,已经多次给了慈善机构有意义的捐赠。她现在正坐在她的书桌前,桌上放着支票本。在她面前有两本小宣传册,一本是介绍有声誉的援助机构,另一本是关于当地剧院公司的。阿夫鲁特现有的钱,或者够捐赠给慈善机构,或者够买一张戏票,但不能两者都做。因为她喜欢戏剧,买了票,虽然她知道,如果她把钱捐赠给慈善机构,将产生更好的效果(9)Tim Mulgan,The Demands of Consequent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如果从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原则,即全人类存在者的福祉来看,行动者A和阿夫鲁特的选择是不正确的。首先,从他们的信念上看,最终他们没有做到,因而表明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信念;其次,从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原则来评价,很明显,他们没有满足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好的要求。也就是说,不仅是因为信念不诚必须谴责行动者A和阿夫鲁特的行动,而且因为他们的行动没有满足普遍仁爱的后果最大化好的要求。那么,怎样做才是符合后果主义的这一要求的呢?
斯旺顿(Christine Swanton)设计了这样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现在是个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后果主义的信奉者,已经把他的普遍仁爱原则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我一直喜欢看电影。有一部《世上最快的印第安摩托》的电影,我一直想看,但却没有机会看。有一天,我生活的小镇电影院正好要放这部电影。当我拿出钱来准备去买票时,斯马特的最高道德原则在我头脑中出现了。因此,我痛下决心把钱捐赠给了慈善机构。第二天,我的朋友见到我,绘声绘色地向我描绘了这部电影,又勾起了我想看的欲望。但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原则还是占了上风。我有一辆老沃克斯豪车,有点不好使,我想修理它。但是,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原则提醒我,修理沃克斯豪车需要一笔钱,这些钱如果捐赠给慈善机构,将产生更大更好的后果。因此,想修理我的汽车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于是我把这部我喜爱的车卖了,并把卖车的钱捐赠给了慈善机构。我还有整理自己门前花园的爱好,但我现在发现,保持花园、整理花园需要一笔钱,如果把这笔钱捐赠给慈善机构,将帮助更多急需钱的病人或穷人,于是我在门前花园改种了一点菜。但我看到还有穷人在路边卖菜,这使我意识到,把钱用来买他的菜更是帮助了他。于是我放弃了种菜。慢慢地,我变得越来越可怜(10)Christine Swanton,“The Problem of Moral Demandingness”,in Timothy Chappell,ed.,New Philosophical Essays,London:Macmillan Inc,2009,p.111.。
这里的主人公由于信奉了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后果主义,因而自己想看的电影无法看了,自己喜爱的车无法拥有了,甚至自己的园艺爱好也觉得不对了,因为如果不是考虑自己的资产、钱财怎样更好地为自己所用,而是为了解救他人苦难或痛苦,那么,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放弃。换言之,如果我是一个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后果最大化道德原则的信奉者,那么,我的整个原有的人生计划都将改变。例如我爱好哲学,但如果将我的爱好与其他人的生活更需要我去服务相比,从全人类存在者的福祉来看,为他人服务将能更直接增多其更大效益。那么,从斯马特的观点来看,放弃我的哲学爱好,去做慈善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人们批评普遍仁爱的后果主义道德要求是一种严苛性要求,遵循其要求,就必然导致个人生活计划异化,从而破坏正常人生活的完整性。
现在要问,个人道德人格的完整性不重要吗?个人生活规划的完整性不重要吗?普遍仁爱的理想道德要求不是崇高的道德要求吗?为什么如此崇高的道德要求会造成对个人道德生活以及整个生活的异化?我们发现,任何一个人的常识道德(the morality of common sense)都不会认为,个人道德人格的完整性不重要,个人生活规划的完整性不重要。因此,这表明,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是与人们的常识道德或日常道德(the ordinary morality)的道德要求相冲突的。一种很崇高的道德要求,但如果付之实践,将使得人们的生活完全变得无从着落。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道德观点来看,这几乎是不可思议。当代哲学家卡根(Shelly Kagan)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人们的常识道德与斯马特从全人类存在者的视域出发的普遍仁爱的道德是冲突的。站在常识道德的立场上,人们将强烈地抵制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最大化好的道德要求,因为斯马特对人们行动的要求是一种很极端的要求。卡根说:“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激进的要求。它要求我们的行动不是关注我们自己进一步的计划和利益,或者那些我们自己所赞成的个人的东西,而是要考虑所有他者的利益,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总体的善。它要求我问,如果所有事情都考虑,我如何能够作出我的最大的贡献,虽然这将施加值得考虑的重负在我身上,并且它禁止我做任何比这贡献更少的事。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的大多数行动是不道德的,因为我几乎都没有最佳地使用我的时间和资源。如果我对我自己是诚实的,我承认,我持续地没有做到我所能做到的那样好。”(11)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换言之,假如我们完全信奉这样一种普遍仁爱的道德观念,那么,我们所有从自我利益需要考虑的事情都是不好的,都应受到道德的谴责。
三、“普遍仁爱”与日常道德
斯马特的问题就在于普遍仁爱的后果最大化好的道德要求与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存在深刻的冲突。日常道德作为经验世界的生活道德,恰恰并不要求我们将所有的生活规划都从这样一种需要理性把握的超越自我的立场来考虑。在日常道德的意义上,行动者的道德人格(包括情感、尊严等心理因素)和生活规划的完整性是优先考虑的。日常道德并不以某种崇高的道德或产生更大善的要求来剥夺人的情感或破坏人的生活规划的完整性。个人人生规划的完整性是人们好生活谋划的基本论题,是个人存在的精神见证,同时个人的道德人格(包括道德情感、心理)是每个人的道德同一性的基础。所谓道德同一性,指的是我们的道德精神生活以及我们的道德行动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所保持的一贯性,从而人们能够依据我们在以前或当下的行动预示我们未来可能有的行动或行动方式。人的道德行动之所以能够保持同一性,就在于道德人格的相对稳定性,或者说,道德同一性就其内在性而言,在于道德人格的同一性。而当我们的道德人格由于遵循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而导致人格异化或人格分裂,那就意味着人格同一性的丧失。日常道德认为,损害个人的人格完整性或人生规划的完整性都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是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那里展开的。卡根认为,至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接受斯马特那样对人们行动严苛性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我们认为日常道德的判断不会有问题。所有道德生活世界中的行动者,都不可能离开自己的情感、利益和由于自己的情感、利益所给出的道德视域。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则要求信奉者完全摆脱普通大众自我的生活世界,摆脱自我利益立场,抹杀自我的道德情感或将自我的道德情感服从抽象超越的普遍的最大化好的要求,然而确实是只有极少数人,如像特雷莎(Blessed Teresa)那样完全放弃自我而牺牲自己的人,能够做到。把这样一种在所有人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道德,看成是一种普遍性要求,不仅是一种超越的理想主义,而且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道德极端主义。
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与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的对立,在于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以及提出了一种超脱于生活的道德理想。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生活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规划以及基于生活规划的日常生活。将行动者的道德立场与自我的道德情感、自我的生活规划等拉开距离,站在一种全人类所有存在者的立场上来看待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问题是,我们普通人能够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吗?那么,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与人们在日常道德生活中以行动者相关的道德要求的对立,是否意味着他的道德要求必然失败?换言之,普遍仁爱何以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前提下做到如斯马特所要求的?
日常道德的正确性在于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思考的边界,保护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存或使每个人自己生活得好是每个人类存在者的首要责任。卡根说:“就日常道德的这个观点而言,允许我有利于我的利益,即使是我这样做而不能导致总体的最好后果。既然给了行动者选择履行行动的权利,并且这些行动从一种中立性的视域看,并不是最优的,我就将这种允许称之为行动者中心选择(agent-centered options)。”(12)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p.3.卡根指出,日常道德认可了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利益选择范围,当人们的目光仅仅关注这些利益范围之内的事,并由此而决定其行动,日常道德并不持反对意见,或者说,日常道德是赞许的。那么,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是否与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完全冲突呢?冲突无疑存在,但是否可以解决?我们认为,解决这两者冲突的前提在于:首先,承认行动者中心选择的合法性;其次,在行动者相关的前提下,给予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一定的道德空间。换言之,把这两者看成是完全不相容的,可能也不符合人的道德心理。
实际上,每个人类行动者并非完全是行动者相关的行动者,也并非完全是行动者中立的行动者。换言之,这两者并非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对立的。与斯马特对普遍仁爱的最大化好的追求相反,经济学上的经济人的概念则认为,人唯一追求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所有人都是自利经济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讨论经济学的经济人的概念时,面对的就是这种最大化自我利益的自利经济人假设,他认为,即使是在逐利的市场条件下,人也不可能是唯一地追逐自我利益。阿玛蒂亚·森说:“在伦理考虑中的人的概念,有一种实质性的不可减少的‘二元性’。我们把人看作为一个行动者,承认和尊重他有着形成目的、承诺、价值等的能力;同时我们也依据好生活(wellbeing)来看待一个人。”(13)Amartya Sen,On Ethics and Economics,Cambridege:Basil Blackwell,1987,p.41.阿玛蒂亚·森认为,像苏格拉底的“我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伦理学问题,都对经济学有着极重要的意义。现实中的人既是一个追求自我利益的、有理性的人,同时也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的,有一定价值承诺、社会责任和义务观念的人。在他看来,人的自利动机服务于个人的好生活方面;但是,人作为一个行动者,同时具有形成价值、义务和超出个人好生活的社会目标的能力。因此,服务于自我的善观念和服务于他人、社会的善观念这两者的动机与目的都是我们的人性结构所决定的。一味地认为只有超越自我利益的普遍仁爱才是道德正确,与一味地认为我们只能最大化自我利益的经济人假设都不符合我们的人性本性。面对这个问题,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人性“二元性”结构很值得我们重视。
日常道德并没有要求我们去做那些我们认为牺牲太大而必须去做的事,“如它不能要求我把我的自由时间贡献给为了政治压迫而去战斗,不能要求我放弃我的奢侈生活而去支持癌症研究”(14)Shelly Kagan,The Limits of Morality,p.4.。换言之,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充分肯定每个人对自我好生活或幸福的理解,给予了人们的自我计划充分的肯定和相当的自由空间。以自己的合法收入或合法经济来源来经营自我生活、发展自我,这并不违反日常道德,虽然这样做并不能带来最大化好的后果。尽管如果捐赠我的资金去援助非洲穷困地区或支持癌症研究,更有利于人类幸福,但是,日常道德同样认为,个人把资金花在自己的生活上也是无可厚非的。日常道德对于我们对自己好生活的规划持肯定态度,同时,对每个人在维持自己的体面生活之外而对社会或全人类他者所负的义务并不持反对态度。如像孟子所赞许的:某人路过一个村庄,见一个孺子在井边玩耍,有掉进井里去的危险而出手相救。这就像我们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孩掉进并不深的池塘,下去救人只是会弄湿我们的衣服一样。这样对他人施以援手的行动并不是牺牲我们的道德重要性的行动,日常道德无疑持赞许的态度。所谓“道德重要性的行动”,是指如果为了救人可能我们不得不流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行动,这是具有道德重要性意义的牺牲;而如果救人仅仅是下浅池塘会弄湿我们的衣服,就是没有牺牲掉道德重要性的善举。不过,如果需要冒生命危险去救某一个或多个陌生人,日常道德可以赞许我们这样做,但并不要求我们这样做(斯马特的后果最大化好的行动标准则要求我们这样做)。还有,如果我在享受了我所向往的电影之后,还有更多富余钱财,我把这些钱财捐赠给慈善机构以救济正在挨饿的穷困人,日常道德并不反对。在人类的灾难面前,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同情那些处于苦难中的人,在不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前提下的捐赠行动,与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并不冲突,而且是高尚的。但是,如果在我们为自己的好生活所规划的每一个行动前,都要将这样的行动与可能最大化好的行动选择相比较,从而放弃自我的人生规划,这样的行动日常道德并不赞许。换言之,日常道德对于从行动者中立立场来看待的后果最大化或普遍仁爱的道德行动,承认行动者相关的限制(agent-relative limited)(15)日常道德承认行动者中心的合理性,但结合人性的另一面,即人也可以在承认行动者中心的前提下,超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有着超越于自己利益的道德要求,因而必然承认行动者相关的限制,也就是行动者中心并非是无限的,而是应当有边界的。这也承认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有其合理性,但同样有适用范围。,承认对于可普遍化仁爱的最大好的行动应当确立日常道德的边界。如果不超出这样的边界范围,那么,日常道德与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最大化好的要求是一致的。
总之,斯马特所提出的从全人类存在者的角度来衡量我们每一个行动后果的好坏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无视了人性内在的自我利益与人格完整性的要求,与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存在着深刻冲突,因而不可能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真正指南,从而在实践中必然失败。但是,如果承认日常道德的限度,即承认在一定限制内的行动虽然不能产生最大化好的后果,仍然是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同时承认我们在可能的情境条件下,还有更多为了他人或社会创造更多的善或较大可能的好,那么,日常道德同样也是赞许的。当然,我们也并非一定要站在日常道德的立场上看待我们有可能最大化好的行动。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最大化好的行动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向人们展示了更高尚的道德行动方向。因此,在我们能够追求自我好生活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实现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我们完全不应否定这样的行动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不过,如果遵循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最大化好的道德要求,如对威廉斯所说的乔治、吉姆而言,必然导致对他们的道德人格的异化或扭曲,那么,这样的要求则是不可取的。维护道德人格的完整性如同维护人生规划的完整性一样,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从总体上看,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与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具有相容性的一面,但在特定场合或特定情形下,两者的冲突仍然有可能发生,而在发生冲突的情形下,捍卫我们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规划的完整性,就显得无比重要。
附注: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