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院派”跨出一步
2020-01-11黄天骥
黄天骥
我1952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可以说,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人。
198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一届的成员有钱鍾书、王力、王季思等先生,共二十多位著名学者。第二届是二十一名成员,召集人是朱德熙教授,成员有王达津、霍松林等老一辈学者。其中,有四位中年人,即章培恒、叶子铭、裘锡圭先生和我。到现在,除裘先生和我以外,诸位均归道山,而我也成为耄耋一翁了。
我毕业留校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科研工作。我给自己定下学习的目标是:“戏曲为主,兼学别样。”
按此目标,我把许多时间放在戏曲文献整理和对中国戏曲史方面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便参加由王季思教授主编的《全元戏曲》一书的工作。在2011年,国家重点攻坚项目《全明戏曲》,则由我和黄仕忠教授担任主编。该书计约有5000万字之多,还需要到全世界各地图书馆访书,任务艰巨繁琐。
我负责全部明代戏曲的点校最后审阅工作,这工作比《全元戏曲》更难。因为明代的杂剧和传奇与元杂剧的情况完会不同,它在一出戏中,曲牌可以南北互用,即在一曲戏中,有时用南曲,有时用北曲。更麻烦的是,有时在一首曲中,会把不同的曲牌,凑集在一起,这曲牌用几句,那曲牌又用几句,组成一首新的曲子。这一来,留存下来的曲谱等工具书,无法查阅,只能凭文意断句,这很容易出现错误。加上版本中出现大量生造的俚语俗字,处理时十分麻烦。有时,为了一首曲子的断句,竟需花费几个小时,左右思量,才敢确定,弄得头昏脑胀,真不足为外人道。幸而,我们的团队多年辛勤工作,《全明戏曲》2018年已由管辖部门验收“结项”,评审专家评为“优秀”。其中“全明杂剧”部份,亦计约有600万字,将由中华书局先行出版。
此外,我把“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和在其他刊物发表过的戏曲研究论文,收集为《冷暖室论曲》一书,201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我的《西厢记创作论》和《牡丹亭创作论》等著作也连续出版。我还出版过《元明清散曲精选》《元曲三百首》等十一二种普及性读物。2008年,我和康保成教授主编并出版了《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
为了结合教学需要,我还出版过计各有50万字的《周易辨原》《诗词创作发凡》,以及《纳兰性德和他的词》《黄天骥诗词曲十讲》等论著。同时参与由袁行霈教授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作为“宋元卷”的分卷主编。
201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把我的论著结集出版为《黄天骥文集》,共十五卷、近500万字。在这里,靦颜列举,只在于说明,我自知确实属于“学院派”的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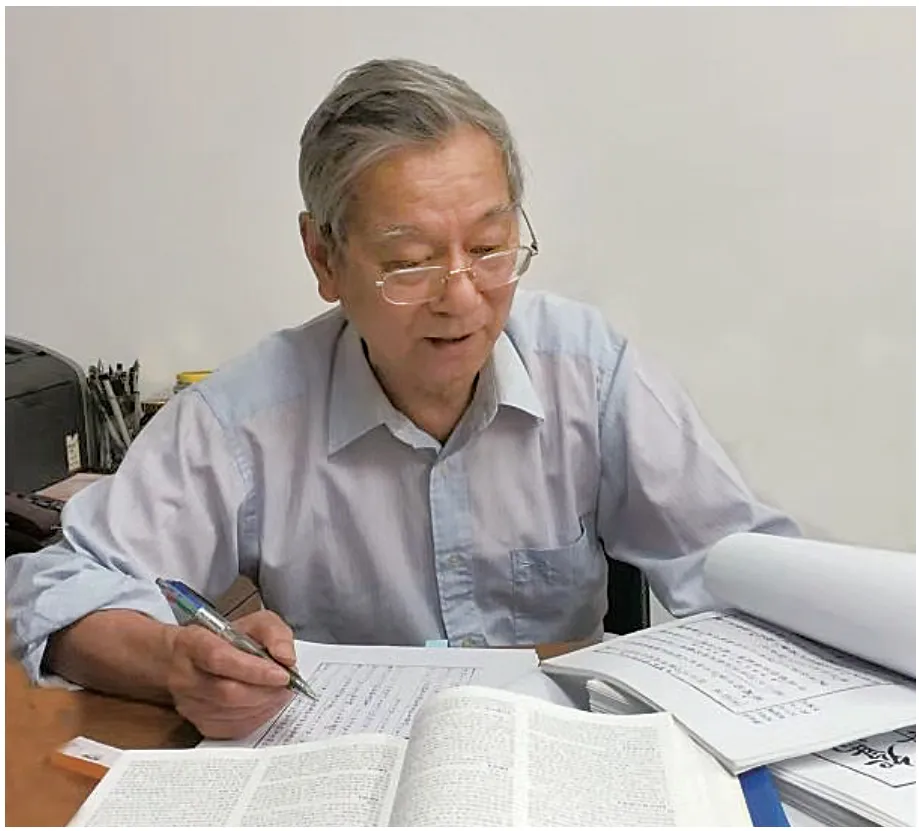
“学院派”并没有什么不好。学习研究古代文学,整理古代文献,继承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本来就是我们在学院里的教师应有责任之义。但我又觉得,如果运用我们的知识和现实需要直接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变化,让广大群众能够接受和理解,不是可以进一步“古为今用”,更能“接地气”了么?话虽如此,但一直想不到如何解决,只在心㡳里暗自打鼓。
我是1996年初被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聘为文史馆员的。加入省文史馆后,我常得到省文史馆领导的支持和督促,如把我的著作《方圆集》列入馆员文集的第一种,这既是对我的鞭策,也使我增加了学习和工作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接触到来自社会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在广东省文史馆,有不少馆员是著名的诗书画家,有些馆员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只念过私塾,没有什么学历学籍。但不能不承认,好多老一辈馆员,在诗词书画文史以及地方掌故等方面,基础深厚,成就斐然。像李曲斋先生,是清末探花李文田之孙,他没有上过大学,广州解放后在街道工作。但大家公认,他的诗书画成就极高。书法家陈景舒先生,曾当过陶瓷学徒,在餐馆当过小工,但隶书极佳,有“隶书王”之誉。他们有学识,有曲折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和市井百姓有密切的联系,和我们终日只在书房里用功的“学院派”,思路和经历大不一样。我和他们接触,常感到眼界一新,知道天外有天,彼此各有所长。对于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和整理的“学院派”学者,倒应该更多学习他们之所长,更多像他们那样眼光瞧下,多想想怎样从市民大众的需要出发,把深奥化为浅近,把枯燥化为有趣,以便更适应现实社会和人民大众的需要。
记得在1996年,广东省委组织《新三字经》的编写,作为少年的普及读物。我奉命担任副主编和主笔。该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颇受群众的欢迎,发行达5000万册,并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有一天,偶然遇见李曲斋先生,他对我说:“这小书,写得不错呀!适合青少年需要。你可以再搞下去!”我笑了,说:“这是省委领导的主意。我总不能架床叠屋,再写一本《新千字文》吧!”李先生却正色地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从《新三字经》中看到,您能吸取前人诗赋的写法,有古文写作的基础。现在,正提倡建设旅游文化事业,如果在景点中,有新撰的对联、碑文,不是会增加它的文化涵量吗?”我恍然大悟。的确,从服务现实需要出发,作为文史馆员,不光可以在书房里整理古籍,划划写写,还可以用一己之长,直接为社会、为百姓服务。
说来凑巧,过了几天,零丁洋畔的珠海市桂山岛,筹建文天祥广场,周围选取并镌刻文天祥多首诗篇,作为诗碑,约请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书写。而广场中心,则需要以一篇序文,统一说明兴建广场的宗旨和缘起。该岛主管者是中山大学校友,便邀我作序。我想起曲斋先生的嘱咐,遂欣然命笔。《序》不长,姑录如下:
珠海市桂山镇文天祥广场序
零丁洋上,碧浪连空,白鸥掠波,锦鳞潜泳。我桂山镇雄立海中,老树依岩,银滩卷雪,迎旭日之光华,揽天风之浩荡。近年经济发展,帆樯如织,而岛上民众,胸襟似海。每于花朝月夕,极目微茫,俯仰今古。乃忆八百年前,南宋丞相文公天祥,抗元兵于粤赣,陷魑魅之牢笼,系孤胆于烟波,集天地之正气。船过零丁,慷慨吟哦,痛感山河破碎,空负头颅,身世飘摇,竟同萍絮。既悟人生之悠悠,谁无一死;誓取丹心之耿耿,留照汗青。诗成掷笔,血泪交迸,惊风雨而泣鬼神,撼心魂而垂千古。斯人一去,海宇留芳,伫听涛声,啸歌如在。我镇世代得接忠风,百姓倍怀英烈。望洋兴感,意气干云。遂填海湾新地,辟建文天祥广场,更镌诗碑卅二,播扬文天祥佳句。旁开馆厦,广陈史迹,岩矗雕像,遥瞰天南。冀中外游侣,访胜寻幽,受文化之熏陶,承爱国之传统。尝闻风和日丽,波底尚掀乱流,安定岂可忘忧,开放常思忠悃。今日苍苍岭树,如见旌旗,猎猎长风,犹闻警铎,去者已矣,来者可追。共期群策群力,振兴中华,俾我列祖列宗,扬眉吐气。是为序。
写成后,我请几位老先生审阅,都还认可。这块碑文,便树立在“文天祥广场”中心,我也曾经看到有好些游客围观。想不到,曾被认为是“选派余孽桐城谬种”的文言文,若处理得当,在学习诗词文史的基础上加以变化,也可以为现实服务。后来,我也应省市一些单位之邀,写了不少碑文,加上发表过的诗词,合编成《冷暖室别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书中有20多篇碑文,与中山大学校友捐建的大楼有关,在写作上虽然良莠不齐,也特别受到中大学子和校友的欢迎。
我以学习过的诗词歌赋为基础,用文言的文体,写出一些能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文字,作为文史学者,这是一种尝试。但始终觉得,这只能给稍有文学水平的小众服务,也只能算是在象牙塔里走出了半步。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遇见广东人民出版社原社长、著名作家岑桑先生。那时,他正在主编《岭南文库》。他一见到我,便说:“我知道您对明清文史有兴趣,对岭南文化有体会,而《岭南文库》中必须有研究屈大均的论著,这工作就交给您了。”长者命,我应不敢辞。但是,当时我正忙于《全明戏曲》的工作,卷帙浩繁,我终日在故纸堆中校点,弄得头昏脑胀,实在为难得很。但也只好抽些时间,首先捡出屈大屈的《广东新语》,略作准备。
又真凑巧,《广州日报》副总编、校友黄卓坚来探访我。她知道我是广州西关人,便问我,近西关荔枝湾的改造工作,很受欢迎,我是否愿意去参观一下?当时,我也想在百忙中散散心,她便开车陪我前往游览。饭后,她说:“黄老师,能否为我报写一篇短文,谈谈广州和岭南的生活和文化?”
粤谚云:“鸡臂打人牙较软”(意思用鸡腿塞进人的牙关,吃了只好服软)。她陪我参观了大半天,只请写篇短文,我岂能不答应?那时刚好快到元宵节,便写了一篇广州人怎样过元宵的短文。过了两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文章反响很好,再写一篇吧!交稿时间不限。”我一想,也不难,过了两周,又写了一篇有关解放前广州儿歌的短文给她。谁知道,这文章发表后,她又来电话:“黄老师,不得了啊!许多读者来信来电,要求您继续写下去。您务必每一周发一篇有关岭南文化的短文给我!”这就让我犯难了。当时,我正在忙于《全明戏曲》的工作,哪有工夫顾及其他,当时便拒绝了。但经不起她一磨再磨;再者,天天对着线装书和工具书,翻来捡去,实在也累得发慌。如果写些记叙略带抒情性的短文,换换脑筋,也未尝不好。同时,刚刚读过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觉得他不也是在百忙中,随手把所见所闻纪录成书的吗?几经踌躇,便答允了。
从此,每到周六晚上,我在散步后便躲进办公室,写了文章,即从电脑发给责编。这一来,等到每周的周三,便有一篇有关岭南风物文化的短文在《广州日报》上发表。编辑部还把我的连载文章搞成《生猛广州·淡定广州》的专栏。在每期文章的下面,选登几条读者的看法,作为“互动”。这样一来,我这专栏更引发读者的兴趣。当时,《广州日报》每天销售一百多万份,读者极多,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我的“专栏”很受欢迎。在校园里碰到一些同事,或到市场里遇见混熟的卖鱼人,常会问我:“黄教授,下一期写什么?” 有一回,我的妹妹要买蜂蜜,店主人正在看周三出版的《广州日报》,闲聊几句,店主指着我在当天登载的专栏问她:“看过这专栏吗?好好睇(看)的呀!”妹妹说:“这是我哥写的。”店主一听,颇为高兴,竟对她另眼相看,给予蜜糖原价九折优待。
看来,我在屈大均《广东新语》的启发下,通俗地把文史知识以随笔的方式传播,也能服务于大众,受到欢迎。这专栏连载近一年半,约80篇。花城出版社于2014年即把拙文结集出版,计有25万字,就取名为《岭南新语》,把我的专栏文章类似《广东新语》的做法,分为“岁时”“城垣”“食俗”“粤韵”“市声”等项。出版后,广州市教育局把它列为中小学生阅读教材,让青少年了解和热爱乡土文化。 2017年,该书获得广东省的通俗读物一等奖。这书的出版,连同我在2012年出版的《岭南感旧》,实际上是我对岭南文化作了比较全面的思考和研究。
习近平同志说:“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这些年,我把在学院里获得的文史知识灵活运用,或写碑文,或写随笔性文章,从家国情怀出发,希望能留住乡愁。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从“学院派”直接跨向社会的一步,初步找到了自己作为“学院派”文史工作者如何更“接地气”的途径。
这里所说的小故事,都是在我参加省文史馆馆员工作后,偶然碰上机会发生的,但也确与我长期思考在象牙之塔从事文史整理研究的工作者,找寻如何进一步“古为今用”,如何为人民大众发挥所长克服所短的想法有关。如今,我虽进入耄耋之年,幸尚顽健,希望能贾其余勇,为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多做一点工作,为文化自信事业多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