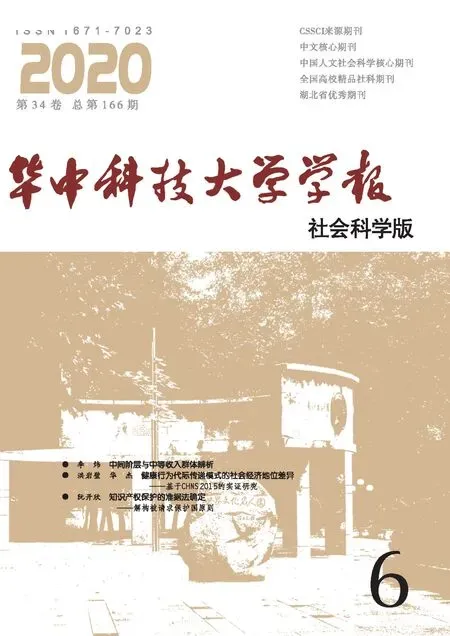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确定
——解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
2020-01-10阮开欣
□ 阮开欣
引 言
在国际私法领域,被请求保护地法(lex loci protectionis)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已经得到各国普遍认可。知识产权保护事项涵盖权利内容与侵权责任,权利内容包括权利的成立、生效、维持、排他范围、限制和有效期等,侵权责任包括归责原则、禁令救济和损害赔偿等。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规范,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在立法中不同程度地明确了被请求保护国原则。201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法律适用法》)第48条和第50条分别对知识产权的内容和侵权责任规定“被请求保护地法律”为准据法。2007年《欧共体关于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864/2007号条例》(简称《罗马二号条例》)第8条第1款规定,基于侵犯知识产权而产生的非合同之债所适用的法律应当是被请求保护国法。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第110条第1款规定,知识产权由被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的法律支配(1)又如,2004年《比利时国际私法典》第93条规定,知识产权适用被请求保护国的法律。2005年《乌克兰国际私法》第37条规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的法律关系,适用该权利需要保护的国家法律。1999年《澳门民法典》第47条规定,著作权、相关权利及工业产权,均受提出保护要求地法规范。1999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编第1120条规定,知识产权适用保护该权利的请求被提起地国的法律。2001《立陶宛国际私法》第1.53条规定,知识产权及其保护,适用据以申请保护该权利的国家的法律。参见齐湘泉.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被请求保护地法”有多个其他称谓,如“权利要求地法”“权利主张地法”(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在2000年拟定的《国际私法示范法》第95条采取该措辞)和“权利来源国法”(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10条(3)款(a)项采用该措辞,英文原文为“state under the law of which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rose”)。对于注册性知识产权(需履行法定注册程序的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和注册商标权),“被请求保护地法”同义于“权利授予地法”,也称为“注册地法”“登记地法”或“申请地法”。有的法律文本根据注册性和非注册性知识产权进行区分,分别对其准据法规定“注册地法”和“被请求保护地法”(2)例如,1967年《法国民法典》第2305条:工业产权由注册国登记地法规定。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20条:对发明者或其利益继承人的保护,适用专利证书发出国或专利申请地法。商标权的法律冲突可以采用专利权法律冲突的原则,也就是依商标注册证发出国或商标申请地国法。;而有的法律文本则不进行区分,统一作出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规定。这两种做法(区分式和非区分式)实质上是一致的。例如,美国法学会的《知识产权: 调整跨境诉讼中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原则》(简称《ALI原则》)采取区分式(3)《ALI原则》第301(1)条规定,知识产权的成立、有效性、存续期间、性质、侵害及其救济所适用的法律:(a)对于注册性权利而言,系各个注册国的法律;(b)对于其他知识产权而言,系各个被请求保护国法。,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原则》(简称《CLIP原则》)采取非区分式(4)《CLIP原则》第3:102条规定,知识产权的成立、有效性、注册、权利范围与存续期间,以及有关其权利之所有其他事项,应适用的法律系被请求保护国法。。
虽然被请求保护国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保护在形式上似乎不存在争议,但如何在实质上理解“被请求保护地法”并未达成共识,该冲突规范容易被司法机关错误地予以适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请求保护地法”往往被误解为“法院地法”,我国法院容易基于该错误理解而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鲜有审理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被请求保护地与法院地高度重合,适用作为法院地法的中国法不存在结果上的差异。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对外民商事交往不断扩大,“侵外”管辖具有现实需要而将在我国逐渐发展[1]。在审理侵犯外国知识产权案件时仍直接以中国法作为准据法,不符合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适用,有悖于应基本坚守的知识产权地域性。目前,我国理论界基本意识到“被请求保护地法”并非“法院地法”,但“被请求保护地法”的实质连结点没有在理论上被充分论证并予以明确,以至于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正确的适用,因而实质上仍陷于适用“法院地法”的困境。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源自现行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但公约所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是否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规范一直没有定论。鉴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内涵和外延长期缺乏清晰深入的阐释,本文旨在梳理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源流与形成,厘清现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关系,进而阐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作为冲突规范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从实然意义和应然意义上解释如何确定该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准据法,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源流与形成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保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确定。著作权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肇始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1款(国民待遇原则)和第2款(自动保护与保护独立性),该冲突规范的措辞源于第2款:“保护的程度以及为保护作者权利而向其提供的补救方法完全由被要求给以保护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对于著作权以外的知识产权,这两项基本原则也奠定于相应的国际公约,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其暗含了专利、商标、企业名称、地理标志等工业产权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
在知识产权制度产生初期,各国知识产权法基本上只保护本国知识产品,而外国知识产品不享受内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以著作权为例,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只保护美国国民或居民的作品,1831年版权法修正案还明确规定“法律不禁止印刷、出版、进口或销售美国国民或居民以外的任何人撰写、创作或制作的书籍、图表、戏剧、乐曲、雕刻、照片”(5)Copyright Act of February 3, 1831; 4 Stat. L., p. 436.。美国最高法院在1834年判决的“惠顿诉彼得案”(6)Wheaton v. Peters, 33 U.S. 591 (1834).从司法层面明确了外国作品不受美国版权法保护。又如,英国法院分别在1828年的“德郎爵诉肖案”(7)Delondre v. Shaw (1828) 2 Sim 237.和1831年的“盖查得诉莫里案”(8)Guichard v. Mori (1831) 2 Coopers 216.中明确外国作品不受英国版权法保护[2]。在工业产权方面,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曾要求外国人在本国具有居所(主要营业场所)的情况下才享有申请专利和商标的权利[3]。奥匈帝国1858年商标法只允许本国的工商业机构申请商标(9)Austria-Hungary,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Marks and Other Denotations, 7 December 1858, art 9 (1872 Reports, p 3).。德国1874年商标法规定其商标注册只向存在商业登记的公司予以开放(10)Germany,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Marks of 30 November 1874, art 1 (1879 Reports I, p 50).。
在只保护本国知识产品的情况下,一国的知识产权可能被本国赋予广泛的积极域外效力(11)关于“积极域外效力”的定义和阐释,参见阮开欣. 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域外效力[J].河北法学, 2018(3):85.,笔者将其称为“来源国原则下的域外效力”,即在域外使用本国知识产品的行为理论上受到本国(知识产品来源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制,一国不会限制本国知识产权排他性的空间效力。鉴于内国规范管辖权的扩张无需外国的认可而独立存在,来源国原则下知识产权的积极空间效力没有地域上的边界,而该约束力至少可由知识产品来源国的司法机构或执法机构予以认可和实施。美国最高法院在1940年判决的“谢尔顿诉米高梅公司案”(12)Sheldon v. Metro-Goldwyn Pictures Corporation, 309 U.S. 390 (1940).则是来源国原则下域外效力的一个例证。在该案中,米高梅公司制作的电影剽窃了美国作者谢尔顿创作的剧本,该侵权电影在多国上映,实际上该行为侵犯了原告作品在多国的著作权。而美国法院对于这一系列的版权侵权行为单纯适用美国法律,并根据侵权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收益判予原告损害赔偿。
在各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完全缺乏合作互助的历史环境下,来源国原则下域外效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其至少在规范层面为知识产品创造者在域外提供了“理想”的实体权利,防止知识产品只在一国具有法律保护效力而导致权利人对域外侵权行为完全“束手无策”。至少在侵权人居所地或其财产所在地在本国的情况下,对于在外国使用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利益损害,权利人仍可能利用本国的执法资源得到救济。但是,由于来源国原则下域外效力难以被来源国以外的国家所认可,盗用知识产品的行为仍容易在来源国以外肆意泛滥,跨国贸易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滋生条件。只要侵权人及其财产处于来源国以外,那么权利人就难以在法律程序上得到实际的救济,此时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由此可见,来源国原则难以契合国际发展的趋势。
国际经济发展的需求推动国际合作的形成,一些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开始出现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关系。来源于一国的知识产品基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在其他国家受到保护。这就意味着,在本国使用他国知识产品的行为会受到本国(保护国)法律的规制。不过,在少数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关系的历史初期,知识产权的国民待遇原则并未广泛确立。当时主要共存三种情形: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来源国原则以及两者的兼并适用(笔者称为“取低原则”)。在著作权领域,历史初期的最主要情形是,对于外国作品的法律保护采取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和来源国原则的兼并适用,该“取低原则”是指选取本国(保护国)的著作权保护与来源国的著作权保护之间较低的保护。例如,法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在1880年达成的协议中明确,作者在保护国提出的权利不能超过作者所属国所享有的权利[4] 57。通常情况下,知识产权条约要求一国对于另一国知识产品的保护采取对等的互惠待遇,缔约国之间应采取相同的保护原则,即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来源国原则或“取低原则”中的一种原则。但当时也存在个别的著作权协议采取国家之间非对等的做法,如A国对B国作品采取被请求保护国原则,而B国对A国作品采取来源国原则。譬如,根据比利时与西班牙在1880年订立的协定,比利时作者在西班牙享有的著作权依据比利时的法律(来源国原则),而西班牙作者则可以依据比利时的法律在比利时享有著作权(被请求保护国原则)[4] 58。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较强的公共政策属性,一国的知识产权法在另一国具有广泛的域外效力,这会对另一国的公共政策产生威胁。因此,一国知识产权法原则上应当只适用于在本国使用知识产品的行为,不能被用于规制在外国的使用行为,而在外国使用知识产品的行为只能留给外国知识产权法予以规制,不考虑知识产品的来源国。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决定了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来源国原则难以成为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主要原则。自从《伯尔尼公约》与《巴黎公约》分别于1886年和1883年获得通过,被请求保护国原则逐渐成为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主流原则,早期所存在的混乱状态逐渐消除。一百多年以来,《伯尔尼公约》与《巴黎公约》的缔约国数量不断增长,其地域范围已经覆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也一直被新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所传承。
有观点认为,现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与知识产权准据法的确定完全无关,一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采取任何准据法确定规则,不受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约束。该观点是不成立的。一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采取知识产品来源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显然会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保护原则。根据来源国原则,在外国保护程度低于内国保护程度的情况下,外国人难以享受到不低于内国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确立国民待遇原则的同时,还明确了知识产权的独立保护原则,这意味着知识产品在一国的权利保护独立于其他国家的保护,尤其是独立于知识产品的来源国。实质上,独立保护原则正是对来源国原则的否定与排斥。当然,一国有权在符合国际条约的情况下自行允许他国知识产权法在本国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来源国知识产权法在本国的效力。现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保护原则的例外,来源国原则在特定情况下存在一定的适用空间。《伯尔尼公约》第7条8款规定的“保护期比较规则”,允许成员国对于外国作品的保护期适用作品来源国的著作权法,保护国著作权保护期长于来源国著作权保护期的情况豁免于国民待遇原则。“保护期比较规则”沿袭“取低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著作权领域的来源国原则。
另外,在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缔结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统一实体规范的提议,其具有法律统一性和可预期性的优势,但这种解决法律冲突的终极做法会对国家立法权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知识产权与一国的公共政策具有较密切的联系。显然,在各国知识产权法迥异的情况下,建立统一实体法来直接调整各国知识产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短期内难以获得各国的认可。在《伯尔尼公约》谈判之初,德国代表团曾极力主张著作权的统一实体规范,但遭到法国、瑞典和瑞士代表团的反对。瑞士政府指出,尽管对作者权利的保护采取统一实体法原则值得期待,但考虑现行各国法律和公约的差异,恐怕这会长期推迟本公约项目的促成[5]。由于统一实体规范的方案难以通过,各国最终达成妥协,即在《伯尔尼公约》中引入国民待遇原则,并配以最低保护标准以防止一国采取过低的保护[6]。
二、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实然与应然
(一)现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并未直接规定冲突规范
虽然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来源于国民待遇原则和独立保护原则,但现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并非冲突规范的直接规定,一个典型的冲突规范(除单边冲突规范外)必然存在指引确定准据法的连结点,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并不存在指引知识产权保护准据法的明确连结点。根据知识产权的独立保护原则,一个知识产品可以在各国具有平行独立的权利。一国独立权利的效力范围完全依据该权利所在国的法律规定,外国人可以依据国民待遇原则享有保护国法律规定的权利。但是,对于行为人基于何种连结因素受到该权利的制约,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并未予以明确规定。
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作为知识产权侵权冲突规范的表述则是,知识产权侵权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该冲突规范的表述在字面上没有显示确定的连结点。显然,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连结点并不简单地是权利人或当事人的“请求保护地”,知识产权侵权的准据法不可能仅是一方当事人请求选择的知识产权实体法。例如,A国国民甲(居所在A国)在B国使用了A国居民乙的知识产品(甲侵犯了乙在B国的知识产权),但乙在A国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该知识产品在A国的权利(主张A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可见,请求保护A国知识产权并主张A国法律的适用不一定能被A国法院接受,A国并不一定是知识产权侵权法律适用的连结点所在地。
实际上,被请求保护地的知识产权法能否适用于涉案行为取决于保护国对于本国知识产权空间效力的态度。涉案行为部分或完全发生于外国的情况下,内国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积极域外效力加以规制由内国自主决定,而内国可能进一步规定内国知识产权法对于涉外侵权行为的适用规则(本文简称“二次”规则)。当发生于外国的行为符合内国“二次”规则所规定的连结点时,在外国使用知识产品的行为受到内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制。例如,我国曾经出现过基于属人原则的“二次”规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04年发文规定,权利人和侵权人均为我国国民的情况下,在外国实施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适用我国著作权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13)《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京高法发〔2004〕49号,2004年2月18日发布。。根据该规则,我国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基于属人原则的积极域外效力。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国民情况下在外国发生的著作侵权行为,我国法院适用中国著作权法作为准据法并不违反《伯尔尼公约》。可以看出,一国采取“二次”规则并不违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要求,而是符合现行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
申言之,现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下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笔者称为“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并非完全的冲突规范,知识产权保护准据法的连结点还有待保护国“二次”规则加以明确。在前述例子中,如果A国法律规定A国知识产权具有某种积极域外效力(假设“二次”规则:A国国民在外国使用A国国民的知识产品,适用A国知识产权法),以至于甲的行为落入了A国知识产权法的空间效力范围,那么根据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A国知识产权法可以作为准据法来判断甲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承担侵权责任。
不可否认,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准据法指引的作用,它至少确定了知识产权法对于纯粹保护国域内侵权行为的适用,原则上不考虑权利主体或侵权主体的属人因素。但是,对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需要“二次”规则的介入,而“二次”规则的介入可能导致多国知识产权法对于同一使用知识产品的行为予以重叠适用的结果,知识产品在某一地域的利益受到多国法律的支配。在前述例子中,基于A国的“二次”规则,甲在B国使用知识产品的行为受到A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制,侵犯了乙在A国的知识产权,但其行为同时受到B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制,也侵犯了乙在B国的知识产权。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重叠适用是对行为违法性的评判,即只要涉案行为违反任一国的知识产权准据法,那么行为人则因其侵权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
从“被请求保护国”的文义来看,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与一般冲突规范的区别不仅在于“二次”规则的介入,还在于其存在“请求前提”,即知识产权准据法的适用需要以权利人的选择主张为必要前提。根据“请求前提”规则,法院不能主动适用当事人未主张的知识产权准据法。例如,乙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认定甲侵犯了乙在A国的知识产权,主张A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但被诉侵权行为并不落入A国知识产权法的空间效力范围,而只能属于B国知识产权法的空间效力范围(B国是仅有的被请求保护地),那么法院既不能适用A国知识产权法,也不能适用B国知识产权法,只有在乙提出B国知识产权保护请求的情况下,法院才能适用真正地被请求保护地法律(B国知识产权法)。虽然“二次”规则的介入可能导致多国知识产权法的重叠适用,但根据“请求前提”规则,只有当权利人在一个诉讼中同时主张多国的被请求保护地法,涉案行为同时落入多国知识产权法的空间效力范围,法院才可能在一个案件中对同一知识产品的使用行为重叠适用多国知识产权法。“请求前提”规则表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不同于重叠性冲突规范,后者具有多个明确的连结点且必须同时适用多个连结点所指向的准据法。
“请求前提”规则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其有利于诉讼中明确涉案知识产权的地域属性,保障知识产权人在诉讼中的意思自治,即有权自主选择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其主张的权利。例如,侵权人侵犯了同一知识产品在A国和B国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权分别在A国法院和B国法院对于A国和B国的知识产权提起侵权诉讼。这样一来,对于A国市场的利益侵害,权利人可以单独在A国法院获得损害赔偿,而对于B国市场的利益侵害,权利人可以再向B国法院请求损害赔偿。如果法院没有在判决中明确其所审理知识产权的“国籍”,那么涉案知识产权的地域属性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法院审理的权利与当事人主张的权利不相符,以至于法院作出的判决具有不当的既判力。比如,权利人在A国法院主张A国知识产权,而A国法院审理了A国和B国的知识产权并作出判决,权利人再向B法院提起诉讼,B国法院可以基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而拒绝管辖。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一国法院只适用了一国知识产权法而认定一国法院只审理了一国知识产权。在一个诉讼中,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事实并非必然与准据法的选择有关联,比如,法院可能以外国法无法查明为由而适用本国法。可见法院最终确定的准据法不一定是涉案连结点所指向的准据法。
(二)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行为主义”
对于“二次”规则,目前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采取“行为主义”,即一旦使用知识产品的部分行为或关联行为(包括预备、引诱、帮助侵权的行为)处于一国之中,那么整个使用知识产品的行为都受到该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制。“行为主义”是对知识产权积极域外效力的过分扩张,使得一国法院可能对于任何在地域上与本国有一定关联的跨境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例如,甲在A国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主要零部件后出口至B国,乙进行组装后销售给B国的用户,根据“行为主义”,A国法院可以将A国知识产权法适用于该跨境侵权行为。在各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规范缺乏正确认知和充分共识的现状下,“行为主义”是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下最常见的“二次”规则。在知识产权中的特定领域,某种程度的“行为主义”既有部分法域的立法予以规定,也有部分法域通过司法实践加以确认。
许多国家对于知识产品载体的制造权、销售权等专有权利(包括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与专利产品的生产权、销售权、许诺销售权)采取“行为主义”,即认定本国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侵害只考虑本国域内是否实施了专有权利所控制的特定行为,不考虑知识产品载体是否在域内产生效果(是否出口至域外的市场)。根据“行为主义”,即使知识产品载体不会被国内的公众所接触,而是全部出口至国外,仅仅在国内实施了生产制造或其他特定行为就足以使行为者承担侵犯本国知识产权的责任。例如,德国最高法院于2004年判决的“CD出口案”(14)Urteil des 2. Strafsenats vom 3.3.2004 - 2 StR 109/03.中,在德国生产的涉案光盘全部出口至保加利亚,涉案生产行为被认定为侵犯德国著作权。又如,德国最高法院于2003年判决的“光学设备耦合器案”(15)Urteil des X. Zivilsenats vom 16.9.2003 - X ZR 179/02.中,被告仅仅在国内实施了产品的广告宣传,而涉案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均发生于域外,法院依据德国专利法认定域内的许诺销售行为构成专利侵权。
除了知识产品在实体产品领域的传播,“行为主义”在通信传播领域的应用也较为常见。欧洲曾对于通过卫星向公众传播的行为采取“发出规则”(emission theory),即通过卫星向公众广播节目只受到卫星信号发出地的著作权法规制,而不用考虑卫星信号接收地的著作权法。1993年通过的《欧共体卫星广播与有线转播著作权与邻接权指令》第1条(2)款(b)项将“通过卫星向公众传播”限定在“仅发生于承载节目的信号传入到通向卫星的不间断通信链所在地”(16)Council Directive 93/83/EEC of 27 September 1993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tain Rules Concerning Copyright and Rights Related to Copyright Applicable to Satellite Broadcasting and Cable Retransmission 1993 O.J. (L 248), at art.1(2)(b).。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在1998年判决的“洛杉矶新闻社诉路透社案”(17)L.A. News Serv. v. Reuters Television Int’l, Ltd. 149 F.3d 987 (9th Cir.1998).中,路透社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合营企业维视新闻社(Visnews)复制了原告享有版权的视频,并通过卫星信号将该视频播送至欧洲和非洲的用户,该行为被认定为违反美国版权法。与之类似,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于2000年判决的“国家橄榄球联盟诉黄金时间24合资企业案”(18)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v. PrimeTime 24 Joint Venture, 211 F.3d 10 (2d Cir. 2000).中,涉案行为是将承载节目的卫星信号从美国传送至加拿大的用户,其也被认定为侵犯美国版权。
基于美国对本国利益的过分追求及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势立场,“行为主义”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现行美国成文法在专利权方面规定了不以域内被控产品全部落入权利要求范围为前提的“行为主义”。美国1984年专利法第271条(f)款规定:(1)行为人未经授权在美国供应专利发明的所有或实质性部分的部件(这些部件并未组装),以主动引诱这些部件在美国以外被组装(若该组装行为发生于美国,其构成专利侵权),应当承担专利侵权责任;(2)行为人未经授权在美国供应专门用于该发明的部件(并非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主要产品),知晓这些未组装的部件会在美国以外被组装,应当承担专利侵权责任(19)35 U.S.C. § 271(f).。美国司法实践也多次对该域外专利侵权规定的适用进一步加以明确与解释。美国最高法院在2007年判决的“微软公司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案”(20)Microsoft Corp. v. AT&T Corp., 550 U.S. 437 (2007).中指出,第271条(f)款中的“部件”必须是物理存在的有形物,不包括无形的软件(微软公司向境外生产商发送Windows软件的行为不符合该域外专利侵权规定)。美国最高法院在2017年判决的“生命技术公司诉普洛麦格公司案”(21)Life Technologies Corp. v. Promega Corp., 137 S.Ct. 734 (2017).中得出,第271条(f)款(1)项中的“实质性部分”是数量上的衡量,仅仅是多部件发明中的一个部件不属于“实质性部分”的部件(涉案产品是具有五个部件的基因检测工具包,域内供应其中一个部件的行为不符合该域外专利侵权规定)。
商标法和版权法方面,“行为主义”在美国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美国商标法中“行为主义”的起源性判例则是美国最高法院于1952年判决的“斯蒂尔诉宝路华手表公司案”(22)Steele v. Bulova Watch Co., 344 U.S. 280 (1952).,美国人斯蒂尔在墨西哥组装从美国购买的手表部件,把宝路华标识印刻于手表上后在墨西哥进行销售,法院对此适用美国商标法予以规制。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判例则是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在2016年判决的“商人乔食品店诉哈雷特案”(23)Trader Joe’s Co. v. Hallatt, 835 F.3d 960 (9th Cir. 2016).,加拿大人哈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州购买商人乔食品店的商品后运送至加拿大,其在加拿大开办了一家模仿商人乔的店铺以销售从美国进口的商人乔商品,法院认定该行为侵犯了商人乔食品店在美国的商标权。美国版权法领域也不乏认可“行为主义”的判例,除了前述两个卫星信号相关的判例外,一个标志性判例则是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1988年判决的“更新艺术公司诉莫迪恩出版公司案”(24)Update Art Inc. v. Modiin Publishing Ltd., 843 F. 2d 67 (2d Cir. 1988).。该案中,莫迪恩出版公司及其在纽约的子公司将原告享有版权的艺术图案放入其在以色列发行的报纸中。美国法院认定该域外侵权行为受美国版权法的规制,并根据美国版权法支持在以色列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
需要注意的是,侵权事项包括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域外侵权行为受到本国法的规制意味着域外产生的损害赔偿也可以根据本国法予以认定,本国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有权获得域外产生的损害赔偿。美国最高法院在2018年判决的“西部盖克公司诉ION公司案”(25)WesternGeco LLC v. ION Geophysical Corp., 138 S.Ct. 2129 (2018).中认为,权利人对于第271条(f)款规定的侵权行为在域外所产生的损失可以依据美国专利法获得赔偿。在该案中,原告西部盖克公司拥有一项海底测量系统的美国专利,该系统采用横向导引技术获得更高质量的测量数据,作为原告的竞争者,被告ION公司未经许可生产、销售落入原告专利权范围的测量系统,其在美国只生产竞争产品的部件,而后将部件运送至美国境外进行组装并销售。美国法院最终认定,西部盖克公司有权根据美国专利法获赔竞争产品在美国境外导致的所失利润。
(三)应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效果主义”
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实施地并不一定是效果产生地。如果甲在A国生产侵权产品的零件后出口至B国并进行组装和销售给B国消费者,那么A国仅是侵权行为地,而B国是效果产生地。与“行为主义”不同,“效果主义”是指涉外行为(知识产权侵权)应当受到效果产生地法律的规制,特别是涉案行为完全发生于效果产生地之外的情形。“效果主义”并不以侵权效果的实际产生为前提,仅仅要求侵权效果产生的实质可能性。无论是否存在“行为主义”,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适用采取“效果主义”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效果主义”下的知识产权积极域外效力属于法律空间效力的合理延伸。虽然原则上国家规范管辖权应限制于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但是“效果主义”下的积极域外效力属于规范管辖权空间效力外溢的正当例外情形。即便是属地性较强的公法,“效果主义”也同样适用,如一国刑法可以适用于效果发生于内国而在外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6条3款就对此予以规定。美国《涉外关系法律重述》第2版和第3版均明确“效果主义”下的域外效力属于规范管辖权的自身范畴(26)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 402(1)(c)(1987); Restatement (Second)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 18 (1965).。美国法中存在一个重要的法律解释原则——无域外效力推定原则(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ity):除非立法者有明确表示,推定成文法仅具有域内效力。而“效果主义”本质上使法律适用豁免于无域外效力推定原则,美国法院在许多法律领域的判例中认可“效果主义”下的域外效力,并排除无域外效力推定原则的适用[7]。
缺乏“效果主义”会导致行为人通过在域外实施侵权来规避本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制,以至于本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缺陷[8]。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在2018年判决的“斯潘斯基公司诉波兰电视广播公司案”(27)Spanski Enterprises, Inc. v. Telewizja Polska, S.A., 883 F.3d 904 (D.C. Cir. 2018).就是一个典型的判例。被告波兰电视广播公司在2009年将其频道波罗尼亚TVP在美洲的传播权(包括通过网络的传播权利)独占许可给了原告斯潘斯基公司,被告在其经营的网站上提供其电视节目的点播服务,但为了保护原告在美洲的独占许可权,被告采取了地域屏蔽技术(geoblocking),防止处于美洲的用户在其网站上接触到涉案频道。然而,原告的律师在2011年发现涉案频道中的特定内容(51集电视节目)没有被适当地予以地域屏蔽,美洲的用户可以在被告的网站上进行点播观看。该案争议的焦点则是被告在美国境外实施的行为是否侵犯了美国版权,对此美国法院给予了肯定的答案并依据美国版权法中法定赔偿规则判予306万美元(每集6万)损害赔偿。美国版权局作为法庭之友对该案提供的意见被法院采纳,其指出了否定基于“效果主义”的域外效力会导致简单规避版权的两个具体后果:(1)使用美国境外的服务器可以让大规模的盗版犯罪行为免除侵犯美国版权的刑事责任;(2)圣地亚哥和埃尔帕索(靠近墨西哥的两座美国城市)的电视台可以将广播天线移至蒂华纳和华雷斯(靠近美国的两座墨西哥城市)以免除其获得美国版权许可的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狭义“行为主义”(“行为”的实施地仅指效果产生地以外的行为所在地,本文对此简称为“狭义行为地”)不能用于规避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效果主义”。跨境使用知识产品的行为符合狭义行为地的法律并不意味其豁免于效果产生地法律的适用,至少,效果产生地法院管辖跨境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仍然适用本国法律,不会考虑狭义行为地的法律。美国最高法院于1890年判决的“伯施诉格拉夫案”(28)Boesch v. Graff, 133 U.S. 697 (1890).中,被控侵权的产品是被告在德国合法购买并进口至美国的灯炉,该产品落入美国专利权的范围且未获得美国专利权人的授权,因此法院认定其侵犯美国专利权。虽然涉案产品在来源地系合法产品,但其在市场所在地属于侵权产品,行为实施地(德国)专利法的允许并不能排除效果产生地(美国)专利法对于跨境行为的适用。
由此可见,目前国际上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法律适用的主要现实状态是“效果主义”与狭义“行为主义”的共存(广义“行为主义”):跨境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既受到效果产生地知识产权法的支配,也受到狭义行为地知识产权法的规制,只要涉案行为不符合任一准据法,权利人可以依据该准据法获得救济。例如,卫星广播领域的“鲍格胥规则”(Bogsch theory)(29)该规则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Arpad Bogsch)提出。受到广泛认可,即广播版权内容需要同时符合信号发出地和信号接收地的版权法[9] 66。根据广义“行为主义”,如果跨境行为同时违反了狭义行为地和效果产生地的法律,仅仅损害了一个法域的利益,权利人却可能会得到双重侵权赔偿。德国最高法院于2002年判决的“费尔斯伯格发送器案”(30)Urteil des I. Zivilsenats vom 7.11.2002 - I ZR 175/00.中,涉案广播信号的主要接收地是法国,只有法国公众可以接收该信号以收听法国拉加代尔广播公司的法语节目,而信号的发出地包括德国萨尔州的费尔斯伯格(与法国接壤),德国与法国的集体管理组织均向拉加代尔广播公司收取了版税。欧盟法院意识到“鲍格胥规则”所产生的双重收费问题,其在2005年判决的“费尔斯伯格发送器案”(31)ECJ Case C-192/04 Lagardère v. SPRE [2005] ECR I-7199.中指出,收取版税应当考虑广播的各种因素,特别是实际和潜在的观众、广播节目的语言。这实质上意味着欧盟法院在广播节目的版税问题上采纳了“效果主义”,该案中德国的版税基本上应该予以免除[9] 94。
广义“行为主义”下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冲突规范,其难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胜任冲突规范的本质职能。冲突规范的任务在于协调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即在多个法域的法律可能竞相适用于某民事关系时,指定适用哪一个法域的法律作为准据法,从而解决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冲突问题[10]。而“行为主义”下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并没有协调法律适用的竞合关系,其均认可狭义行为地法和效果产生地两种法律对于跨境行为的适用,知识产品在狭义行为地法和效果产生地法之间的利益没有得到合理分配,效果产生地国关于知识产品的规范管辖权会受到行为实施地法律的不当干预。随着各国经济相互关联程度不断提高,跨境使用知识产品情形日益频繁,“行为主义”严重阻碍知识产品的跨境传播和利用。假设跨境使用知识产品行为根据效果产生地的法律属于合法行为,而适用狭义行为地知识产权法的情况下则属于侵权行为,那么“行为主义”下狭义行为地法会不合理地干涉知识产品在效果产生地的利益。美国最高法院戈萨奇大法官在“西部盖克公司诉ION公司案”的反对判决意见中指出,多数判决意见实质上赋予专利权人通过美国专利控制外国市场的权利,这让美国专利法在外国市场起到很奇怪的作用,因为管辖专利发明在外国的生产、使用和销售的法律应该仅仅是外国法律,而非美国法律。
理想的冲突规范意味着该准据法选取规则在各国都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以至于各国采纳相同的冲突规范后不同国家的法院审理同一民事法律关系时会选择相同的准据法,进而作出相同的判决,以保障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在各国和谐统一。而“行为主义”下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与冲突规范的本质目标相背离,甚至可能恶化法律冲突而有悖于国际私法的发展。第一,由于狭义行为地法律不当干涉了效果产生地的市场,效果产生地的法院显然应拒绝狭义行为地法律对于跨境侵权行为的适用,其至少能以公共秩序保留为依据而仅仅适用效果产生地的知识产权法。可见,“行为主义”下,狭义行为地法院和效果产生地法院在审理同一跨境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时会分别适用其本国法律(法院地法),从而可能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第二,一国采取或扩张“行为主义”可能会引起“行为主义”在他国的恶性循环。戈萨奇大法官在其反对判决意见中表达担忧:允许美国专利权人利用美国法院来扩张其在外国市场的控制,可能招致其他国家利用自己的专利法和法院来对我们的经济施加控制。假设美国芯片制造商在国外研发新芯片时侵犯了外国专利,但其仅在美国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和销售,外国法院可能认定美国公司对此承担侵犯外国专利权的责任。第三,由于“行为主义”属于规范管辖权的不当扩张,一国法院基于“行为主义”作出的知识产权侵权判决难以在另一国家得到承认与执行,特别是涉案侵权行为的效果产生地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ALI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具有“效果主义”的属性,其在第301条的官方评论指出:“被请求保护国”的表述与市场导向方法(market-oriented approach)契合。《ALI原则》关于不正当竞争的准据法规定也对此予以印证。不正当竞争法可被用于保护没有权利法定化的知识产品利益(如商业秘密),其冲突规范在措辞上不适合采取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但其对于知识产品权益保护的准据法规则与传统知识产权的准据法规则在实质上应是一致的。《ALI原则》第301(2)条规定:“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导致的非合同之债所适用的准据法,系直接和实质性的损害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各个国家之法律,不考虑实施引发损害的行为所在的国家”,可见,该规定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适用采取“效果主义”,并排除“行为主义”。
为了使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真正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规范,有必要对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予以修正,即消除“行为主义”而仅仅采取“效果主义”作为“二次”规则。在应然意义下,效果产生地是知识产权侵权冲突规范的真正连结点。只有在各国均采取“效果主义”的情况下,知识产品在各国的利益才能得到合理分配,其在一国的利益仅受到一国知识产权法的支配,一国的知识产权法不会干扰另一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从而促进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礼让。法院适用“效果主义”下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才可以有效地解决跨境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维系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和谐统一。因此,“效果主义”符合应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法院在审理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应当考虑效果产生地的法律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 。
(四)反致规则应内化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存在例外情形,即本国知识产品与外国知识产品在本国享受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差异,对于本国知识产品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而对于外国知识产品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或国际条约。该内外差异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本国知识产品的保护程度低于外国知识产品的保护程度(本文简称“内低外”)与本国知识产品的保护程度高于外国知识产品的保护程度(本文简称“内高外”)。一方面,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完全允许“内低外”,对本国知识产品采取“内低外”的保护属于一国的自治范畴,一国甚至有权对本国知识产品规定低于公约最低标准的保护。只要外国知识产品的保护未低于公约最低标准,“内低外”所形成的超国民待遇不受国际公约的约束。例如,美国的作品登记要求使版权的权利成立方面存在“内低外”,美国作品的权利人需依据美国版权法进行作品登记才能在美国提起侵权诉讼,而外国(非美国)作品可以适用《伯尔尼公约》的自动保护原则和最低保护标准,无需以作品登记作为在美国提起侵权诉讼的要件。另一方面,“内高外”本质上与国民待遇原则相违背,其只能存在于国际公约对于国民待遇原则作出例外规定的情形,如 “保护期比较规则”(《伯尔尼公约》第7条8款)、“实用艺术品的互惠原则” (《伯尔尼公约》第2条7款)、“追续权的互惠原则”(《伯尔尼公约》第14条之三)等。
可见,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简单地适用被请求保护地的知识产权实体法会与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制度产生矛盾。“内低外”或“内高外”的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个国家,各国立法不同程度地采纳了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保留事项,同时不少国家的立法也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而直接适用被请求保护地的知识产权实体法会导致国民待遇例外制度落空。以我国为例,《著作权法》第2条、《商标法》第17条和《专利法》第18条规定了外国人根据其所属国与我国共同签订的协议或共同参加的条约在我国享受保护,同时《法律适用法》第48条和第50条明确了知识产权内容和侵权责任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因此,为了使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和国民待遇例外的两方面规定和谐共融,有必要将反致规则内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
申言之,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适用被请求保护国的法律,应当包括该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适用法,即国民待遇例外机制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确定规则。将反致规则内化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法律解释可以有效地化解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与国民待遇例外之间的适用矛盾,为知识产权国民待遇例外制度的运行扫清理论障碍。特别是在管辖法院的国家并非涉案知识产权的被请求保护国的情况下,反致规则内化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尤其重要,因为非保护国的管辖法院容易忽视被请求保护国存在知识产权的国民待遇例外机制。例如,假设A国版权保护期是作者终生加七十年,B国版权保护期是作者终生加五十年,A国采取“保护期比较规则”,其作为版权保护期事项上某种程度的准据法确定规则,B国作品在A国的版权保护期应依据B国版权法(作者终生加五十年)。在涉及B国作品在A国版权的侵权案件中,A国属于被请求保护国,C国法院管辖该案并适用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时应考虑A国采取“保护期比较规则”。基于反致规则的存在,A国关于保护期的这项准据法确定规则指向B国版权法。据此,内含反致规则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保障了法院在保护期问题上适用B国版权法,而对于版权保护的其他事项仍适用A国版权法。
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本身就意味着,一国对于本国知识产权事项的法律规范享有最终决定权,其完全可以通过冲突规范将知识产品的规范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让渡给其他国家,即对于本国知识产权事项适用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实体法。在现行制度下,内含反致规则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不仅应当适用于知识产权保护事项,也应当适用于知识产权归属事项[11]。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与归属事项的冲突规范,不会由于反致规则的引入而产生法律适用的体系紊乱,反致规则统一作用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归属事项,对于其中的不同事项均适用同一国家的知识产权实体法。虽然我国《法律适用法》第9条对反致制度予以排除,但内含反致规则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专门针对知识产权的内容和侵权责任,第48条和第50条作为特殊规定可以优先第9条一般规定以适用于知识产权事项。
三、被请求保护国原则适用之完善
(一)司法实践之完善
自《法律适用法》生效以来,我国法院逐渐在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对于准据法确定引用第48条或第50条规定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但是,由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在理论上长期并未被予以充分阐释,法院在判决书中的援引只是流于形式,实质上沦落为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知识产权法),以至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立法规定丧失其应有的意义,几乎形同虚设。因此,在理论上厘清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内涵可以为涉外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的准据法确定提供指引,从而使《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在实践中发挥冲突规范的真正功能。
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和整理大量判决书后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律适用法》中被请求保护国原则规定的援引和适用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简单引用模式”,即在判决书中援引《法律适用法》第48条或第50条的规定后直接得出中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其欠缺司法三段论中的小前提,不存在任何关于连结点的分析或解释(32)例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243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民终23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三终字第87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500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知终字第106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民终字第23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民终797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124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琼民三终字第80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终268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云高民三终字第116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冀民终483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303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终609号;(本文对于同一地区法院采取相同或类似方式的案件只列举一个判决书案号,不再列举同一地区的其他案件。)。与其实质类似的做法是,在法条引用后仅仅指出涉案知识产权的被请求保护地为中国,再得出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的结论,这仍然没有透露法院如何选取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连结点(33)例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初764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416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知终字第389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1341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43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桂民终358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终字第00249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终585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琼民终825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603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终505号。。“简单引用模式”在我国最为常见,几乎各地区法院均采取过该做法,其缺乏完整的涵摄过程,致使判决书不符合应有的论证规范。第二种方式是“法院地模式”,即在法条援引之后指出提起侵权诉讼或救济的法院所在地为中国,进而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34)例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73民终23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74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民终137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终字第373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津高民三终字第16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民终812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三终字第247号。。实践中“法院地模式”略少于“简单引用模式”,目前仍被我国许多法院所采用。该做法错误地将被请求保护地等同于法院地,显然不符合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第三种方式是“侵权行为地模式”,即法条援引之后指出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于中国境内,故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35)例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73民终35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民终247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22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1107号。。我国只有少数法院曾采用“侵权行为地模式”,其符合“行为主义”下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但与应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存在一定的偏差。
此外,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适用还普遍存在两点缺陷:其一,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内容和侵权责任两种事项,而大多数判决书只引用了《法律适用法》第50条(侵权责任)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规定,以此代替涉案知识产权所有事项的准据法适用,笔者仅发现个别判决书中同时引用第48条和第50条并提到知识产权的内容和侵权责任两种事项(36)例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初字第1279号。;其二,被请求保护国原则需要“请求前提”,大多数判决书在适用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时并不强调权利人所主张涉案知识产权的“国籍”,只有少数案件的判决书中加入了“请求前提”(37)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13990号。。
从应然的角度说,法院在审理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首先需要让权利人明确其请求保护的知识产品的权利所属地,其次考虑涉案事实的效果产生地与权利人主张的权利所属地是否吻合,在两者一致的情况下再考虑效果产生地的法律是否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待遇例外制度。如果权利人所主张的权利所属地并非涉诉行为的效果产生地,那么涉诉行为没有落入权利人所主张权利的地域范围,也就是说,权利人对于涉嫌侵犯B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主张A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此法院可以直接裁定驳回权利人提起的侵权诉讼。如果权利人所主张的权利所属地是涉诉行为的效果产生地,且效果产生地的知识产权法关于涉诉问题不存在国民待遇例外机制,那么权利人主张的效果产生地知识产权法则是涉案知识产权的被请求保护地法。以涉外贴牌加工纠纷为例,OEM企业在国内实施贴牌行为后将产品出口至国外,商标权人在国内法院提起侵权诉讼,需要向法院明确其主张哪个国家的商标权,并对商标权的有效性和权属予以初步证明。法院需要判断涉案贴牌产品流入市场的国家(效果产生地)是否为权利人主张的商标权所属国,并在排除相关国民待遇例外机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认定相关进口国的商标法是涉案商标权侵权的准据法。当然,如果贴牌产品可能返销至本国市场,那么本国商标法也可能成为商标权保护的准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判决的“本田株式会社诉恒胜公司案”(38)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38号。中考虑涉案产品可能回流至国内市场而导致我国相关公众关于产品来源的混淆,适用我国商标法并认定OEM企业侵犯商标权。从这点来看,该判决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效果主义”,仍然符合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应然规范。
(二)条约谈判之应对
厘清被请求保护国原则有利于本国应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条约谈判,防止他国知识产权法效力不当扩张而损害本国利益。“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及其同等概念逐渐出现于一些国际条约(如《罗马二号条例》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文本之中,但条约文本及其缔约谈判过程中缺乏对这一概念内涵的明确界定,以至于条约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准据法确定存在模糊性,这可能导致一个缔约国基于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接受另一缔约国“行为主义”所产生的域外效力。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主持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以下简称“判决公约”)在起草讨论过程中曾纳入知识产权条款,2017年2月发布的草案还包含了知识产权侵权的准据法审查条款,即间接地要求判决来源国法院对于知识产权侵权适用“权利所属国法”(英文原文为“law governing that right”,其等同于“被请求保护国法”)。根据判决公约草案中准据法审查的规定,如果原判决法院没有对于知识产权侵权适用被请求保护国法,那么被申请法院无需基于公约义务承认与执行知识产权侵权判决[12]。易言之,如果在一个缔约国的原判决法院选择了符合判决公约要求的被请求保护国法,同时该判决也满足判决公约中的其他条件,那么在另一缔约国的被申请法院有义务予以承认与执行。
在“被请求保护国法”缺乏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采取实然意义的理解自然符合国际条约的规定。根据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原则,一国完全可以对于本国知识产权法的域外适用自行设定“二次”规则,致使本国知识产权法控制知识产品在外国的利益。该情况下所建立的国际条约会促使一国基于条约义务被动地认可另一国的“二次”规则,使得一国关于知识产品的规范管辖权现实地受到另一国知识产权法的侵蚀。以判决公约草案为例,假设A国采取“行为主义”以至于在B国使用知识产品的行为(涉案行为与A国存在一定的关联,如涉案产品是在A国进行加工而出口至B国)落入A国知识产权法的规制范围,A国法院管辖该案件并适用A国知识产权法的情况下作出侵权判决(本文将这类案件的判决简称为“行为主义”判决)。鉴于A国法律属于实然意义的被请求保护国法,在“行为主义”判决符合判决公约其他要求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向B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行为主义”判决,致使在B国使用知识产品的行为现实地受到A国知识产权法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行为主义”判决的被申请人往往是判决被申请国的国民或居民,而非判决来源国的国民或居民。一国“行为主义”的存在及其在他国得到实现不仅是对他国规范管辖权的威胁,更是对他国利益的现实侵害。我国一旦接受国际条约中的这类规定,本国利益会直接受到其他国家“行为主义”所带来的损害。我国较多情况下是“行为主义”判决被申请人的所属国。例如,美国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在2012年判决的“阿尔法轮胎公司诉山东玲珑轮胎公司案”(39)Tire Eng’g & Distrib., LLC v. Shandong Linglong Rubber Co., 682 F.3d 292 (4th Cir. 2012).属于“行为主义”判决妨碍我国规范管辖权的典型案例。该案中,原告阿尔法公司是一家生产矿用轮胎的美国公司,位于阿联酋的被告阿尔多波维公司(Al Dobowi)通过原告雇员获得了原告享有版权的轮胎设计图,并与位于中国的被告山东玲珑公司合作生产销售与原告设计相仿的轮胎。阿尔法公司遂向弗吉尼亚东部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其中最主要的指控则是版权侵权。地区法院指示陪审团采取“根源行为规则”(predicate-act doctrine):如果版权侵权的来源行为发生于本国,那么在外国发生的侵权行为也受到本国法律的规制,版权人对于侵权人在外国使用作品所产生的损害也可以依据本国法获得赔偿。陪审团基于“根源行为规则”支持包括美国以外的法域范围销售侵权轮胎所产生的损害赔偿,从而给出了高达两千六百万美元的赔偿额,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均对此予以维持。可见,承认与执行外国“行为主义”判决将现实地侵害本国利益。
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在于对“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加以限制解释,即在相关国际条约文本中对“被请求保护国法”或同等概念加入“效果主义”的限定。该限制解释的做法可以避免本国基于条约义务而认可外国“行为主义”下的知识产权域外效力。例如,在判决公约草案的准据法审查条款中,明确“权利所属国”仅限于使用知识产品的效果产生地,那么一国法院所作出的“行为主义”判决则不能基于公约在另一国得到承认与执行,因为其并未适用“效果主义”下的“权利所属国法”,无法通过准据法审查条款的“审查”。判决公约最终排除知识产权的主要原因无非在于各国担心他国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扩张致使本国利益损失,特别是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而言,他国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扩张会严重架空本国知识产权法,故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应更加谨慎缔结相关国际条约。在国际条约中加入“效果主义”的限制解释能够解决这种忧虑,防止国家利益问题对于条约缔结的影响,从而促进相关国际私法条约的达成,有助于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