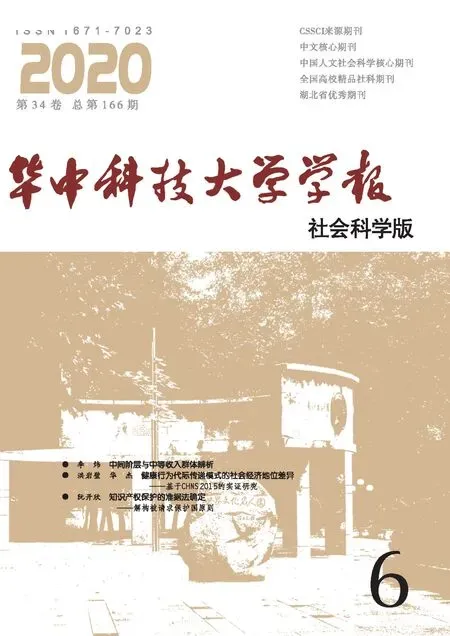城中村拆迁还建居民收入变化与住房租赁生存依赖
——以武汉市为例
2021-01-04蔡银莺殷宇超段鑫宇
□ 蔡银莺,殷宇超,段鑫宇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低效用地再开发成为城市存量建设用地内涵挖潜的主要途径;加之城中村在环境、治安等方面的问题突出[1] [2] [3],城中村拆迁改造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4]。城中村的土地产权及社会保障等较为特殊,改造涉及原住居民、开发商、地方政府等多方主体的利益[5],直接关系社会的稳定,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现有研究关注城中村改造的起源[6]、利益博弈[7][8]、改造路径与模式[9][10][11]等,拟破解城中村改造带来的增值收益分配不协调的问题;或从城中村拆迁改造居民的生活状况变化[12]、改造后农民的悖论心理[13]、居民归属感[14]以及生计资本流动[15]等微观层面,关注城中村改造对原住居民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外,学者还从“转制”后村集体股份公司的管理和村民出路[16]、塑造克服贫困条件的反贫困改造方法[17],以及实现城中村存续的“自我原位”改造[9]等提出建议,以应对改造对还建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带来的限制性。然而,已有研究鲜有定量分析城中村拆迁还建前后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化,尤其缺乏较为准确地揭示改造补偿后还建家庭的住房租赁收入状况及其生存依赖程度。
住房是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住房出租或出售是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手段[18]。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城市住房供需矛盾突出。已有研究证明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租赁在一定程度上为低收入外来务工人口解决了居住问题[19],同时也为部分因文化水平低和生存技能限制而在城市就业市场缺乏竞争力的城中村原住民带去了稳定的收入[20]。城中村拆迁改造作为一种强大的外生作用力,将原本农村集体福利产权住房直接转化为城市社区住房,增加了住房资产在交易市场与正式租赁市场的准入机会,相比原本被限制交易、无市场价值的农村住房,还建后住房的财产功能得到增强。以往关于城中村改造的研究极少从拆迁还建前后住房财产带来变化的角度去思考,且研究主要集中在位于繁华市区、发展较为成熟的典型城中村[7][9][16],对于拆迁前位于城市边缘、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城中村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此外,由于城中村拆迁改造一直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缺少公开、透明的数据资料,以往涉及改造补偿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相应的量化研究。本文在武汉市鲤鱼洲家园、十里玫瑰等典型城中村改造安置社区开展实地调研,分析城中村改造还建居民的收入变化与住房租赁收入依赖度,拟揭示城中村拆迁改造作用下还建居民收入的流动性特征,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更新涉及的社会治理及还建居民后续生计能力提升等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参考。
二、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域概况
城中村本是位于城市边缘的农村,后因城市发展需要、征用农民土地进行城建而保留下来的农村居民点。城中村的形成游离于城市规划体系之外,不完全的城市化过程造成城中村土地权属和使用混乱、居住环境恶劣、基础设施缺乏和社会治安差等系列问题[21]。武汉城中村作为“问题村”一直备受政府关注[22],数量最多时高达160个。2004年9月,武汉市正式启动“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工作,综合改造范围包括江岸、江汉、汉阳、武昌、洪山等主城区,涉及总人口35.66万人,房屋面积4000万m2,土地总面积21381.82万m2,相当于全市规划中2020年建成区面积的1/4(1)参见《中共武汉市委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武发[2004]13号),2004 年9月10日。。为提高改造质量,武汉市还出台《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暨“三旧”(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市人民政府关于妥善解决全市“城中村”改造还建房项目规划建设手续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等相关文件。截至2015年末,武汉市已经全面完成98个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工作,形成了一定的改造模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具有典型性。其中,武汉市城中村拆迁还建存在以按住房初始建筑面积等量补偿和按家庭人口人均100 m2(独生子女按人均200 m2)补偿两种模式,在文中分别简称为模式一和模式二。
课题组2016-2017年在洪山区光谷青年城和华中农业大学西苑社区进行城中村拆迁改造的预调查。在此基础上,2019年7-9月重点选取武汉市汉阳区十里玫瑰、十里锦绣、铁桥新家园、龙阳雅苑、龙阳御园、世纪龙城、鲤鱼洲家园、鲤跃龙门等八个城中村拆迁安置社区开展深入调研,详细了解拆迁改造对居民家庭收入状况的影响。此次调研的安置社区与被拆迁的村庄处在相同区域,避免居住社区区位差异所造成的影响。且这些小区所在位置均在二环线之外,拆迁前位于城市建成区边缘,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外来人口与住房租赁现象很少,属于典型的成长型城中村[23]。在住房补偿模式方面,前六个小区按原住房面积等量补偿,鲤鱼洲家园和鲤跃龙门则按人均100 m2(独生子女200 m2)补偿,代表了武汉市城中村改造的基本补偿类型,具有典型性。这些安置小区涉及的城中村拆迁启动时间基本集中在2012年左右,还建时间在2016年,采用现房安置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具体补偿时,居民家庭可根据自身情况在应补范围内选择还建住房面积,少量未补足或超出部分面积折算成货币进行补偿或向拆迁方购买。此外,拆迁补偿主要以住房补偿为主,货币补偿主要用于支付被拆迁居民在还建前的临时安置费用,除此之外的货币补偿总体较少,且补偿所得住房多未取得房产证,住房出售现象极少,因此还建前后住房财产性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住房租赁性收入上。
(二)数据来源
考虑还建家庭数据分布的均匀性,每个小区按5%~10%的比例抽取样本,共随机抽样425户还建居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剔除关键信息缺失的无效问卷,回收411份有效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家庭人口构成、社会经济特征、拆迁前后住房资产变化以及拆迁补偿等基本信息。在所有样本中,拆迁前后家庭人口数量发生变化的比例仅为6.8%,且拆迁前后家庭劳动力构成基本不变,因此可不考虑拆迁后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9,满足α>0.7的标准,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值为0.000,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良好的结构效度。受访者中57.9%为家庭户主,男性占56.3%,平均年龄57.6岁,平均受教育年限7.7年。
三、城中村拆迁还建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及住房租赁状况
(一)城中村拆迁还建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及变化
受访安置社区所在的城中村拆迁改造主要发生在2012年,本文的调研时间为2019年。为避免收入受时间及物价上涨等影响,以武汉市城镇常住家庭人均收入为参照,将受访家庭在城中村改造前后的收入转化为与同期武汉市城镇居民具有可比性的收入并分组。依据《武汉统计年鉴2012》和《武汉统计年鉴2019》中城镇常住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收入分组标准,将城中村拆迁前后居民家庭按收入划分为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5个等级,具体见表1。按上述标准,调查的217户家庭在拆迁前属于武汉市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收入户,比例高达52.8%;高收入家庭有36户,仅占8.8%。拆迁还建后,低收入户家庭明显减少,仅占9.2%,中等偏下收入户占28.3%,中等收入及以上的家庭比例由拆迁前的47.2%提高到62.5%。总体来看,城中村拆迁改造前受访居民家庭收入与武汉市城镇居民收入相比,绝大多数处于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水平,而还建后绝大多数家庭处在中等及以上收入水平。

表1 城中村拆迁还建前后受访居民家庭收入分布状况
从表2可见,拆迁还建后原高收入户的年收入达到258788元,较拆迁前增加50247元,增长幅度为24.1%;原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收入户的年收入在还建后分别增加了42362元和37910元,增长幅度分别达到62.6%和40.3%,高于武汉市同期同等水平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4.8%和34.3%)。从还建居民家庭的收入结构来看,拆迁还建后住房租赁性收入的增长最为明显。还建后居民家庭户均年收入从122942元增长到166265元,其中住房租赁性收入增加18949元,占到家庭收入增量的43.7%。低收入家庭年均住房租赁性收入增加19330元,高收入家庭年均增加24812元,分别占家庭收入增量的45.6%和49.3%。将居民家庭拆迁前后的各项收入变化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拆迁还建后受访居民的家庭各项收入及总收入水平均有明显的提高。

表2 城中村拆迁前后居民家庭的收入结构及其变化 单位:元
综上所述,住房租赁性收入的增加是城中村改造后还建居民家庭收入改善的重要原因。此外,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可知,拆迁前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年限带来的工资、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上调,其他收入则更多地和居民家庭自身情况有关,说明拆迁改造带来的收入变化主要体现在住房租赁性收入上。因此,本文将进一步从住房租赁收入的取得上进行分析。
(二)城中村拆迁还建居民家庭住房租赁收入及依赖状况
还建居民家庭的房屋出租收入及其在家庭收入所占份额反映了还建居民家庭对住房租赁性收入的依赖程度,其中,城中村拆迁还建补偿模式直接决定居民家庭的住房面积和住房套数,进而影响住房租赁性收入及家庭收入。
1.还建后居民家庭房屋出租的户数明显增加,租赁收入依赖性增强

图1 拆迁前后居民家庭住房租赁性收入依赖状况
由图1可知拆迁还建前城中村居民家庭有住房租赁的比例极低,411户受访样本仅有59户将房屋出租,占比为14.4%。拆迁还建后,受访家庭有住房出租的比例显著增加,达到46.96%。其中,按原面积等量补偿(模式一)和按家庭人口补偿(模式二)两类还建模式的调查样本,拆迁前有住房出租的比例分别为17.2%和10.4%,拆迁后有住房出租的家庭比例分别为34.9%和63.6%,房屋出租的比例增幅明显。此外,还建后居民家庭对于住房租赁性收入的依赖度也明显提高,拆迁前住房租金收入占家庭收入10%以上的仅有33户,仅占样本的8%;拆迁还建后该比例增加至38.93%,有160户家庭的住房租金占到家庭年收入的10%以上。这充分说明城中村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家庭的收入结构及生计来源,住房租金收入成为还建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构成,尤其按家庭人口还建的模式二与按原住房面积还建的模式一相比,拆迁后住房租赁户数和收入均显著增多。
上述住房租赁性收入依赖度的显著差异源于住房租赁需求和住房状况的变化。一方面,受访居民原来所在的城中村尚处于发展初期,外来人口和租户并不多,村内多为本村居民,没有产生明显的租户需求现象,住房租赁情况尚不普遍;拆迁改造后,原有城中村转变为城市居住社区,之前“环境脏,秩序乱,设施差”标签已经逐渐褪去[10],加上城市化使得附近商圈得到发展,还建小区中外来人口增加,租户需求明显,且环境条件的改善也将带来租金价格的普遍上涨,从而提高了家庭住房租赁收入。另一方面,拆迁前居民家庭拥有的农村集体福利产权住房基本上只有一宅,受住房结构的限制,可用于出租的住房面积较少,拆迁前仅有的租赁现象多出现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这与此类家庭普遍拥有更大的住房面积有直接的关系(表3)。还建后,获取住房补偿的居民家庭持有的住房套数普遍较多,除自住以外有富余的住房能用于出租,且住房结构变化(套数增加)导致空间独立性更强,相较拆迁前独栋的住房形式更容易出租。由此可见,城中村拆迁改造后居住社区化及住房套数增加是导致居民家庭住房租赁性收入变化的根本原因。
2.补偿模式导致还建居民住房租赁收入存在差异,按人口补偿的获益度大
对比两种还建模式,还建居民住房租赁收入获取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按人均100 m2还建标准进行住房补偿的居民家庭获取住房租赁性收入的情况更加普遍。从表3可知,城中村拆迁改造前,按原农村住房面积等量补偿的模式一,因还建居民家庭原有住房面积主要集中在300 m2左右,拆迁方出于成本的考虑,按照原面积等量补偿(若按人口进行补偿平均每户将比现在多补78 m2)。而按人均100 m2还建的模式二,居民家庭原有住房面积普遍较大,平均面积超过600 m2,若按照面积等量补偿(平均每户将比现在多补150 m2),成本较大,因此采取每人100 m2,独生子女每人200 m2的方式进行补偿。根据补偿结果可以看出,按照面积等量补偿的家庭前后住房面积的差异不大,拆迁后住房套数位于2.5~4.4套之间,出租套数为0.4~1.4套。按照人均100 m2进行补偿的家庭,还建后的住房面积相比拆迁前明显减小,通常还建居民家庭人口基本在3人及以上,且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多代同堂的现象,因此获得的住房面积补偿依旧要高于按原面积等量进行补偿的家庭,其还建后平均住房面积高达411~526 m2,户均持有4.1~5.2套住房,用于出租的住房则达到1.2~2.3套。因此,该模式下居民家庭平均住房租赁性收入也更高,达到每年每户39891~61484元。
3.住房租赁对于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存在生计依赖与财产红利效用分化

表4 拆迁还建家庭住房租赁及收入贡献度比较
由表4可知,拆迁还建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其房屋出租的比例及收入相对越低,但房租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贡献率却相对越高,存在住房租赁生计依赖现象。调查的78户低收入家庭中有25户将还建房屋出租,占样本的32%;户均年房屋租金收入在34984元,占家庭收入的27.6%,成为家庭生计的重要来源。相反,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将拆迁还建房出租的比例越高,户均房租收入也明显高于低收入家庭,但租金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仅占15%,租金仅作为家庭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构成。研究表明,收入水平越高的还建户更有条件将还建房屋出租,以增加家庭收入来源。房屋出租收入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是家庭生计的重要来源,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财产红利的重要表现。拆迁改造后住房租赁收入的效用不同,则会进一步扩大还建家庭的收入分化。

表5 城中村拆迁还建前后还建居民家庭收入分布变化 单位:%
(三)城中村拆迁还建前后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
收入流动性是指不同时期居民收入所处社会位序的动态变化,能够反映家庭经济水平高低的转变[24][25]。为分析城中村拆迁还建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状况,笔者首先将两种拆迁模式下受访居民家庭收入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城中村拆迁改造前,按原农村住房等量还建补偿的居民家庭收入状况相对较好,主要处于中等偏下、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占71.8%;城中村拆迁还建后低收入户的比例由18.5%减少到10.9%,而中等偏下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分别增加了9.3%和4.3%,且还建后这两类家庭的比例达到60.6%。相较而言,按人均100m2的补偿标准进行还建的模式二,受访居民家庭拆迁前的收入水平总体较差,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收入户的比例高达67.7%;拆迁还建后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整体明显提升,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收入户的比例分别下降30.7%和8.1%,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的比例分别由拆迁前的12.1%和12.7%提升到了32.9%和31.8%。总体来看,按模式二还建的家庭收入水平变动更大,一方面与拆迁前这些家庭的收入水平整体较低、提升空间大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还建后该模式下居民家庭进行房屋出租的比例和获得的住房租赁性收入更高有关。从还建后收入的分布来看,参照武汉市家庭收入水平标准,两种模式下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均呈现出“两端少,中间多”的情况,一方面拆迁还建后低收入户的比重均明显降低,另一方面高收入户的比重依旧很小,居民家庭逐渐向武汉市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集中。

表6 拆迁前后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转换结果 单位:%
从表6可以看出,拆迁还建前后各类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但整体上仍有一定比例的家庭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且产生收入流动的家庭多以上下变动一个等级为主,尤其是拆迁还建前后居民家庭很少发生收入较低和较高水平之间的跨越式流动,这表明收入水平具有“局部流动,整体固化”的特点。其中,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收入户的流动主要以水平的提升为主,两种模式下的比例达到55.3%~89.2%,而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主要以水平的维持和小幅度升降为主,比例达到69.4%~90.9%,相比之下按照人均100 m2进行住房补偿(模式二)的家庭收入流动情况更好。为了进一步探究住房租赁性收入的取得对于还建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将居民家庭分为有住房租赁收入和无住房租赁收入两类,并对其进行分析。由表7可知,还建后拥有住房租赁性收入的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情况明显更好,证明租赁收入的取得会对还建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变化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而还建后也有一小部分没有将住房进行租赁家庭,其收入水平也有所提升,这主要是由于拆迁带来的其他补偿及家庭自身的原因改善了收入情况,但这些因素的作用有限。

表7 拆迁还建后不同租赁状况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结果 单位:%
整体来看,拆迁还建后住房租赁性收入的取得令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尤其对于拆迁前水平较低的家庭。尽管如此,低收入户及中等偏下收入户在拆迁还建后想要成为中等收入以上的概率较小;而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虽然房屋租赁情况也会对其收入流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维持在原有水平的家庭比例仍超过3成,剩下的大部分家庭也仅下滑一个等级,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收入水平下降。
四、城中村拆迁还建居民家庭收入变化与流动性存在的问题
城中村拆迁改造后住房租赁性收入增加直接影响还建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增强家庭的消费能力。从拆迁前后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流动状况来看,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固化特点。拆迁前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在改造后经济状况整体有所改善,但拆迁后仍集中在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还建居民家庭收入的提升除拆迁还建带来的住房租赁性收入增长之外,由自生能力决定的工资性收入等未得到根本的改善,收入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城中村拆迁改造虽然使得原住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产生向上的流动,但由于居民家庭人力资本等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其自生能力提升仍存在局限。
(一)职业及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存量不优影响家庭收入及自生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表8 拆迁还建前后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家庭职业、受教育水平变化状况 单位:%
已有研究证明,家庭成员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存量及其结构是影响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26][27]。为进一步探究导致还建居民家庭收入分化的内在原因,本文进一步对还建居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存量状况进行统计,具体见表8。结果发现,拆迁改造前后,除从事农林牧渔行业的人员比例明显减少外,整体上居民家庭成员从事的职业及受教育水平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这说明拆迁改造带来的收入增长在短时间内难以从根本上缩小家庭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的差距。不同还建模式下,各类家庭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分布情况大致相同,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家庭成员的职业集中在产业服务人员、零星散工人员和企业公司人员,且部分家庭中无业人员的比例较高,而高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家庭成员的职业则集中于党政事业单位人员、企业公司人员,表现出明显的职业差异,这与相关研究结论相一致[28]。此外,各收入水平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小学及初中,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并有不少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达到大专及以上。由此可见,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在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上存在差异,且不同还建模式下居民家庭的情况相似,表明该特征分布具有一般性。从这些特征出发,结合调研获取的家庭收入特征并对其进行分析,拆迁前收入水平较低和水平较高的家庭在职业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导致职业回报的差距显著,且拆迁改造难以改变这个状况。因此,拆迁带来的租赁性收入增加虽然能够影响收入水平的流动性,但受限于家庭成员职业技能等人力资本存量不优的限制,很难导致较低收入家庭向较高收入家庭的跨越。
(二)缺乏长期理财规划普遍影响城中村还建居民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
从不同家庭样本所体现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特征出发,结合调研获取的家庭收入、支出等方面的情况,笔者分别对其进行分析,发现还建居民家庭普遍缺乏长期理财规划,尤其是拆迁前收入水平较低、还建后获得住房补偿较好的家庭。这类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职业构成中零星散工和无业人员的比例较高,收入不稳定。调研发现,虽然依靠拆迁还建住房财产而获得的住房租赁性收入较高,但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导致自律性较差,这类家庭在获得突然降临的财富时往往产生优先满足物质需求的心理;同时,职业的不稳定性导致日常闲暇时间较多,容易受到周围相同群体的影响而产生盲目的跟风行为,从而出现品牌消费、娱乐性消费等非刚性需求支出显著增加的现象;更有少部分人员由于自身盲目性而染上赌博等恶习,沉迷于短期金钱消费带来的满足感而缺乏长远的理财规划,未能将拆迁补偿收入或财富用于自身职业技能提升或拓展其他生计来源。因此,拆迁补偿及租赁收入仅能带来短期的物质满足,还建居民家庭的自致性因素使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收入结构中存在的缺陷。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择武汉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中具有典型性的鲤鱼洲家园、十里玫瑰等八个还建小区为调研区域,实地调查、获取城中村改造前后居民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还建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及其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拆迁还建后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整体得到改善,家庭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比例减小,住房租赁性收入比重增加。其中,住房租赁性收入占家庭收入增量的43.7%,成为拆迁还建家庭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城中村拆迁还建后因居住社区化及住房套数增加,带来住房租赁供给条件明显改善,加上外来人口增长而形成的租户需求现象,住房租赁性收入成为还建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其中,按人均100 m2获得住房补偿的家庭出租房屋较为普遍,比例达到63.6%,所获得的住房租赁性收入也较高,每户每年达到39891~61484元。拆迁还建所增加的住房租赁收入对于低收入家庭的生计功效明显,占到家庭收入的27.6%。
住房租赁收入增长直接促使还建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得以增强,家庭的收入位序得以提升,但基本呈现“局部流动,整体固化”的特征,以较原有的收入水平提升一个收入层级为主,未出现明显的“暴富”现象。整体而言,城中村居民家庭收入由拆迁前“底端大,顶尖小”的低中收入为主的结构形态,转变为拆迁后“两端少,中间多”的正态分布态势。以武汉市同期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为基准,拆迁前52.8%的受访家庭处于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水平,拆迁还建后62.5%的居民家庭处在中等及以上收入水平,低收入户的比重明显降低。从拆迁还建补偿模式来看,按照人均100 m2获得住房补偿的家庭收入流动状况较好,还建后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提升较快。但受还建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不优等自致性因素的限制,要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水平仍存在关键性障碍。存在低收入家庭成员职业不稳定、受教育程度低、工资性收入偏低等结构性缺陷,以及还建家庭普遍缺乏长期的理财规划和合理的消费习惯等问题,这会抑制家庭未来发展能力的提升,从而无法将拆迁还建产生的收入改善及财富积累优势有效转化为家庭的发展动力。
(二)政策建议
第一,城中村拆迁还建要特别重视收入水平不高家庭的生计能力建设,在补偿过程中可以将政策适当地向这类家庭(尤其是低保家庭、主要劳动力伤残家庭等)倾斜,如设立该类家庭的专项补贴、为这些家庭优先提供还建小区内的相关工作机会(如门卫、园艺、保洁岗位等),避免其对住房租赁性收入产生过高的依赖。
第二,拆迁补偿要推动构建多元化的补偿机制,同时要重视多数还建居民文化素质不高、专业技能缺乏等现状,为他们组织就业技能培训,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有条件的还建小区还可以建立专门的服务中心,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对补偿后获得住房财产性收入较高的家庭进行投资理财知识的推广和创业信息的普及,帮助其拓展生计来源,增强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建立健康、可持续的家庭发展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