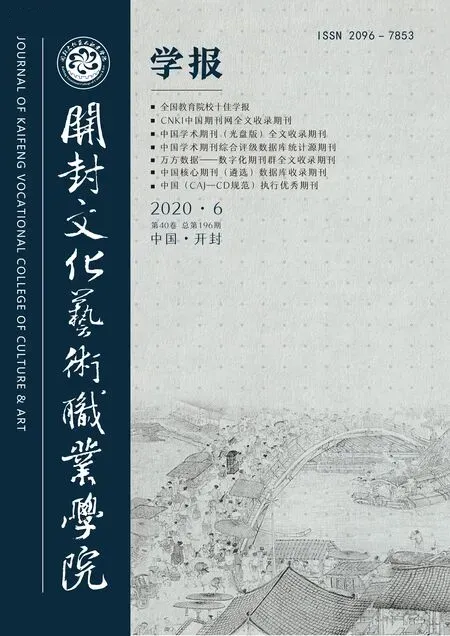白先勇的离散书写研究
——以《谪仙记》为例
2020-01-10沈燕
沈 燕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南通 226000)
英语中的Diaspora(离散)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动词speiro(意为“播种”)和介词dia(意为“遍及”)。离散最初指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被迫放逐迁移的经验;后来,该词指涉16世纪奴隶交易中非洲黑奴被迫迁移的经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人口的流动也随之加剧,学界对离散的理论建构随之出现在众多领域,如种族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等,离散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离散一词中的“被迫性”逐渐被淡化,无论是犹太民族的离散,还是西非黑人的迁徙,皆非源于自愿,都带有强烈的被迫性。离散文学则是伴随着离散现象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以特定的文学形式去表现个人或群体的离散现象,关注离散群体从原居住地离开后的心理变化,同时关注离散者在异质文化中面临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问题。
白先勇,作为中国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正是离散者真实的生活写照。白先勇祖籍桂林会仙镇山尾村,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上海和南京,后来于1948年迁居香港,1952年移居台湾,1963年母亲病逝后他赴美留学。童年时期的战争与疾病、少年时期的政治环境变迁及青年时期经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构成白先勇的成长背景。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入文学创作中,塑造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离散人物,如吴汉魂、李彤、玫宝、黄凤仪……他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了离散群体内心的焦灼和痛苦,以及他们离散生活的艰难。小说集《纽约客》是他离散书写最好的呈现,作为《纽约客》开篇之作的《谪仙记》,无疑是白先勇离散书写的代表作品,本文拟以此篇为例,探讨白先勇的离散书写。
一、空间的离散引发浓郁乡愁
《谪仙记》讲述了出生于国民党高官家庭的大小姐李彤和她在上海贵族中学中西女中的三个同学黄慧芬、张嘉行和雷芷苓出国留学,后李彤因父母意外去世,家道中落,逐渐放逐自我、最终香消玉殒的故事。
出国前,李彤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上海虹桥路的豪华别墅里过着被他人艳羡的贵族生活,“她们在上海开舞会,总爱到李彤家虹桥路那幢别墅去。一来那幢德国式的别墅宽大堂皇,花园里两个大理石的喷水泉,在露天里跳舞,泉水映着灯光,景致十分华丽”[1]1。出国后,她依然光彩照人,“李彤一到威士礼,连那些美国的富家女都让她压倒了”[1]3,“在威士礼的风头算是出足了”[1]2,“来约她出游的男孩子,难以数计”[1]3。在她身上,离散的被迫性被淡化了,从她们急于出国的言行中,读者感受不到被迫离散的味道。但是,“一九四六年她们一同出国的那天,不约而同地都穿上了一袭红旗袍,四个人站在一块儿,宛如一片红霞,把上海的龙华机场都照亮了”[1]2,4人不约的行为恰恰是内心对空间离散不舍的外在表现。此外,从她们4人在美国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也隐约能感受到空间的离散在这4人内心引发的浓郁乡愁。
随着空间的转移,故乡从近在眼前变成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思念,它承载了过去多少年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但随着空间的离散,这些都逐渐变成遥不可及的回忆。在《谪仙记》中,原来的一封封家书寄托着李彤对故乡的怀念,但在父母遭遇意外双双身亡之后,李彤丧失了可以寄托相思之情的载体,她彻底“实现”了空间的离散。而李彤的朋友们为了消解离散引发的浓郁乡愁选择抱团取暖,只要有假日就聚在一起。空间的离散在聚会中被她们主观地淡忘,因为她们相信,只要聚在一起,就可以屏蔽周围汹涌而来的文化冲击。
二、身份认同危机背后的悲哀
之前有很多研究者认为,离散经验的产生势必伴随着“去国”这一行为,因为离散在早期专指犹太民族的被迫离散,这种离散经验的产生是和被迫性分不开的。但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离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离散经验已经和被迫离开逐渐脱节,纵使离散者有跨国行为,但在形体、文化、心理等方面,若没有出现认同困境,可能也未必能称之为离散行为。王赓武先生根据自己对散居海外的华人的研究,提出了散居者中存在着的5种身份:“旅居者的心理,同化者,调节者,有民族自豪感者,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者。”在白先勇的《谪仙记》中,李彤和她的朋友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身份认同危机之于李彤在刚离家时并没有彻底显现,她带着固有的贵族身份离家,机场送别时“李彤的母亲搂着李彤哭得十分伤心,连她父亲也在揩眼睛,可是李彤戴着一副很俏皮的吊梢太阳镜,咧着嘴一径笑嘻嘻的”[1]2。而且“李彤说她们是‘四强’——二次大战后中美英俄同被列为‘四强’。李彤自称是中国”[1]2。显然,她是带着浓郁的民族自豪感离开的,这种主动的离散行为并没有在她身上引发任何身份认同危机。
李彤的离散经验更多地始于父母的骤然亡故,在跨国行为发生之后,她依然过着和国内一般的贵族生活,并在和好友的交谈中多次提及她是“中国”,这是一种身份认同感的外化呈现。父母的意外亡故不仅让她感受到彻骨的悲痛,更让她彻底失去精神家园,她一下子从贵族的高台上跌落,身份认同危机伴随而生。小说中,她逐渐表现出和身边人的格格不入,对生活的放纵,喝酒要喝烈性的曼哈顿,在舞池跳激烈狂乱的恰恰舞,身边经常更换不同的男伴,在赌马中一意孤行地选择冷门马匹等,这所有行为都是她身份认同危机的外化呈现。学者霍尔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离散身份是通过转变和差异的方式来保持自我不断更新的状态。离散者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建立过程因时间、地点、事件、个人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这在李彤身上有很好的表现。白先勇将笔触聚焦在李彤父母失事前后的变化上,为我们刻画出一个性格迥异的李彤,可以说,李彤离散经验的建立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从有民族自豪感者到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者的过程,是伴随着她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而被逐渐巩固的。
与李彤不同的是,她的3个同伴始终生活在身份认同的夹缝中。从表面上看她们都属于主动离散群体,因为家世优越而出国留学,过着他人眼中光鲜亮丽的生活,但这其中也不可避免有被迫离散的可能,如从众心理下的被迫离散等。一方面,如何回应居住地强烈的文化冲击,对她们来说是个艰难的问题。她们内心深处无法割舍对故乡的思念,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等让她们深切留恋,并且在自身的文化体系遭受异质文化威胁时,身份认同的困境让她们倍感苦闷。例如,小说中的慧芬坚持要在纽约举行婚礼,“她说她的老朋友都在纽约做事,只有住在纽约才不觉得居住在外国”[1]4,在布法罗住了6年后执意要回到纽约,“她说她宁愿回纽约失眠去……沉闷无聊的生活对我们也是非常不健康的”[1]16。显然,群居生活能让离散群体在异质文化中获得身心的安全感,可以暂时消解跨国环境下身份认同的苦闷。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场景——牌局。例如,黄慧芬和陈寅的婚礼上,李彤对陈寅说:“幸亏你会打牌,要不然我们便不准黄慧芬嫁给你了,我们当初约好,不会打牌的男士,我们的会员是不许嫁的。”[1]5-6还有他们在纽约的周末生活中这样描写:“他们都爱打牌,大家见面,不是麻将便是扑克。两对恋人的恋爱时间,倒有泰半是在牌桌上消磨过去的。”[1]11牌局在作品中具有隐喻作用,这些离散群体借助牌局寻求安全感,寄托对过去的回忆,消解内心的苦闷。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固有身份遭受异质文化冲击的问题,在这种文化冲突中必须重构自己的身份,小说恰恰很好地展现了这群人的离散生活状态。虽然内心坚守着精神家园,但面临生存困境,她们也会不由自主地从异质文化中寻求安全感,如养成喝咖啡的习惯,日常对话中也常夹杂英语等。可见,她们应该介于同化者和调节者的夹缝之中,她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如何以牺牲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为代价而迅速地融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和文化并与之相认同”[2]。在身份重构过程中,她们迫切需要寻求到一种让自己感到满意而舒服的身份归属,以削弱处于夹缝中的心理压力。
三、离散书写背后折射出的边缘人困境
白先勇谈及自己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创立《现代文学》的时代背景时曾说:“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事实上我们父兄辈在大陆建立的那个旧世界早已瓦解崩溃了,我们跟那个早已消失、只存在于记忆与传说中的旧世界已经无法认同。我们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荫下得以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得挣脱父兄扣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套旧世界带过来的价值观以求人格与思想的独立。”[3]103这段话可以说是白先勇的心声,他自身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但台湾社会族群构成的复杂性又让他无法真正融入台湾本土文化之中,去美国留学也许是无奈的逃离,身上浸润着中西文化的因子,却无从归依,于是,他用自己的笔写出了如他一样的“边缘人”的痛苦。他在散文《蓦然回首》中说:“像许多留学生,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和信仰都得重新估计。”[4]316显然,白先勇本人是经历过这种文化和身份认同困境的,何去何从,他有着最真实的体验,他创作的离散群体,也就显得异常真实。不难发现,白先勇在《纽约客》中塑造的人物大多集中在美国的大都市如纽约、芝加哥等,这些繁华的城市是离散人群的聚集地,同样也就成了离散焦虑最集中呈现的地方[5]。
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离散群体面临的必然问题,同样,这也是一个动态过程。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呈现出节节败退的趋势,很多主动或被迫离散的群体开始发现本土文化的缺陷,甚至对本土文化丧失信心。但是,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又让他们不自觉地去维护悠悠大国源远流长、丰厚润泽的文化传统,边缘人的心理一旦出现,便催生了很多离散书写。白先勇在《谪仙记》中为我们刻画了两类不同的离散人物,不管是处于文化夹缝中的痛苦焦灼的黄慧芬等人,还是放弃坚守、自我毁灭的李彤,都折射出“边缘人”的离散生存困境。在得知李彤自杀之后,张嘉行脱口而出:“李彤就是不该去欧洲!中国人也去学那些美国人,一个人到欧洲乱跑一顿……她就该留在纽约,至少有我们这几个人和她混,打打牌闹闹,她便没工夫去死了。”[1]22一席话道出心中所想,离散群体在面临居住地强势文化的冲击后依旧想回归母体文化来寻求心灵寄托,她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是对抗到底还是妥协自保,这是多数离散群体生存现状的集中呈现。
小说中黄慧芬和陈寅在回家途中的一段描写很好地展现了她们内心的焦灼,“可是她坐在我身旁的那一刻,我却感到有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从她哭泣声里,一阵阵向我侵袭过来……顷刻间,我感到我非常能够体会慧芬那股深沉而空洞的悲哀,我觉得慧芬那份悲哀是无法用话语慰藉的,这一刻她需要的是孤独与尊重”[1]25-26。纵使慧芬无法理解李彤放纵自我的行为,但从内心深处却对李彤的死亡怀着深切的同情。李彤的悲剧何尝不是她们这个离散群体的悲剧呢?面临强势文化的进攻,她们进无可进、退无可守,无论是黄慧芬等人个体上对原文化的坚守,还是李彤对强势文化的无奈妥协,被同化似乎是无法逃避的必然结局,这种悲哀才是最深沉而空洞的。
结语
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文化差异性逐渐削弱,文化的包容性逐渐显现,这表现在不同文化上,其开始呈现出的融合与借鉴的趋势,而并非如传统意义所言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制和消解。白先勇以李彤等人的故事作为载体,去表现离散群体在面临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危机时的悲怆,从而引发世人对离散现象的关注,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