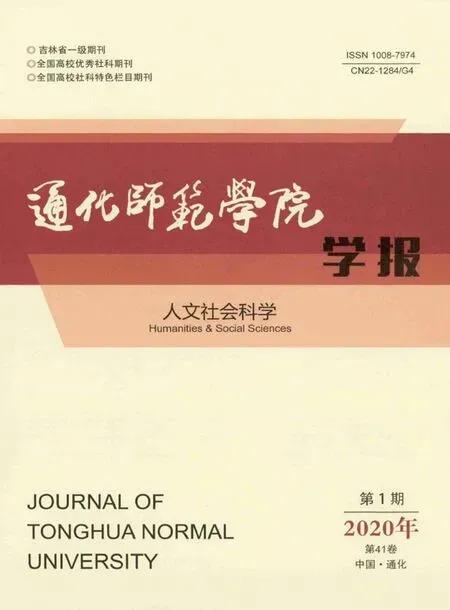时间词“刚才”的形成与发展
2020-01-09李惠超
李惠超
“刚才”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常用时间词之一。“刚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刚过去不久的时间”,《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指出,“刚才”是时间名词,表示“说话前不久”[1]。例如①本文语料来自北京大学语言研究所CCL语料库。:
(1)他说,今天上午拉奥总理与李鹏总理举行了会谈,刚才又会见了江泽民主席,双方谈得很好,说明访问进行得很顺利,而且富有成果。(人民日报1993年九月)
(2)就在刚才冠军争夺战终场哨响之前,中国女篮还面对着巨大的威胁。(人民日报1993年七月)
(3)陆小凤道:“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一瞬之间,往往就会发生很多变化。”(古龙《陆小凤传奇》)
语言学界对时间词“刚”和“刚才”,以及“刚”的叠加式“刚刚”的意义和用法等方面进行过很多讨论。邢福义指出,不应将“刚刚”仅仅视为时间副词,而应将“刚刚”分为“刚刚1”和“刚刚2”,其中“刚刚1”同时间副词“刚”,而“刚刚2”则同时间名词“刚才”[2]73-74。冯成林从辨析“刚刚”和“刚才”的词性入手,提出了划分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的4 条标准[3]。周小兵则讨论了当“刚”和“刚才”做状语时,动词后跟的表时间词的差别,指出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时段标志[4]。
然而以上文章更多着眼于“刚才”与“刚”“刚刚”之间在语义和用法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且更多地局限在共时层面上的比较分析,鲜有系统地研究“刚才”一词的历时演变的论述。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从历时的角度研究“刚才”的语义及功能演变,就很难从根本上准确地掌握其共时层面的意义及用法。在此我们拟探究时间词“刚才”的形成过程及其生成机制。
一、“刚”和“才”的语法化
我们认为,时间词“刚才”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先由排列上相邻的两个单音节近义时间副词“刚”“才”固化为一个双音节时间副词,进而再由时间副词发展为时间名词。
要了解“刚才”如何而来,就不能忽视作为其构词语素的“刚”和“才”的发展和演变。通过研究副词“刚”和“才”的语法化历程,才能知晓时间词“刚才”从何而来,进而阐明这一演变过程的内在机理。由于“刚”和“才”远早于“刚才”一词产生,且“刚”和“才”在古代汉语中也是常用词,产生了丰富的义项和繁多的用法,限于篇幅,我们主要分析“刚”和“才”语法化的演变历程
(一)“刚”的语法化历程
1.先秦至唐末的发展
《说文解字》对“刚”的释义是:“强断也。从刀冈声。”按段玉裁注:“强断也。强者,弓有力也。有力而断之也。周书所谓刚克。引伸凡有力曰刚。”可见“刚”的本义为形容词,我们记作“刚1”。“刚1”既可以指物质的坚硬,也可以泛指事物的某类特性或人的品性,此时的“刚”依其语境,语义有所差异,如:
(4)采薇采薇,薇亦刚止。(《诗经·采薇》“刚”表“硬”义,指植物长大时的样子。)
(5)金,坚刚之物。(《周易》王弼注“刚”表“坚硬”之义)
(6)刚而塞,将而义。(《尚书·皋陶谟》。“刚”表“刚强”之义)
(7)旅力方刚,经营四方。(《诗经·小雅·北山》。“刚”表“强盛”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形容词“刚”本身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褒义或者中性词,但当形容个人品性时,在语境的制约下,有时也会有“固执,不变通”的隐含义。如:
(8)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蜀书六》)
(9)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三国志·魏书十》)
到了唐代,基于“刚1”衍生出了方式副词“刚”的用法,即由“性格(品性)刚直,固执”向“行为(手段)强硬”的转化,我们记作“刚2”。如:
(10)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全唐诗卷七八三·悼妓诗》)
(11)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蔻花。(唐·冯衮《戏酒妓》)
例(10)的“刚留得”、(11)的“刚牵引”可理解为“强留得”“强牵引”,副词“刚”表示“(行为)强硬”之义。
在“刚2”所处的语境中,即在“S+刚2+V+O”句中,施事者S 强硬地(“刚2”)实施了动作V 以达成某种目的,由一般的生活经验可知,这一动作V 造成的结果一般是受事者O 所不希望接受的——因为如果这一结果是O所希望见到的,则S 往往不需要使用强硬的方式即可实行动作V。由此可以推知,在“S+刚2+V+O”这一结构里,蕴含着反意愿实现(对于受事者的)的语义成分,而这也是之后“刚2”向“刚3”转化的重要原因[5]。
由于“S+刚2+V+O”这一结构里,蕴含着“反意愿实现”的语义成分,因此从受事者的角度看,基于转喻机制的作用,人们在心理层面上将这一结构的标志词“刚2”与“不愿发生的事态”联系到一起,进而使“刚2”衍生出表转折的“偏偏、却”之义,我们将它记作“刚3”。自唐代开始,就有:
(12)刚有下水船,白日留不得。(唐·孟郊《留弟郅不得送之江南》)
(13)溪云洞鸟本吾侪,刚为浮名事事乖。(唐·皮日休《醉中偶作呈鲁望》)
(14)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唐·卢肇《竞渡诗》)
由上述用例可知,自隋唐开始,方式副词“刚2”开始逐渐向限定副词“刚3”转化。
2.宋元之后的发展
宋元之际是近代汉语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副词“刚”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刚”的含义和用法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早在唐代,“刚3”就有如下用例:
(15)可怜夭艳正当时,刚被狂风一夜吹。(唐·白居易《惜花》)
此处的“刚”当然可以理解为“刚3”,即表示“偏偏、却”之义,但将其理解为表示行动或情况发生不久的表时间的副词义同样也说得通。而到了唐末以及宋代,有了更加明确的用例:
(16)刚有峨嵋念,秋来锡欲飞。(唐·齐己的《思游峨嵋寄林下诸友》)
(17)刚被时流借拳势,不知身自是泥人。(唐·蒋贻恭《咏金刚》)
(18)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宋·苏轼《花影》)
(19)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南宋·《五灯会元》)
其中例(18)(19)的“刚”语义指向非常明确,表示前后句之间的动作或状态间隔时间短暂。因此,至迟到北宋中期,“刚”表示行动或情况发生不久的时间副词的用法已经产生,我们记作“刚4”。“刚3”到“刚4”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语用环境造成的,语境吸收(аbsоrрtiоn оf соntеxt)是促进其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
ВYВEE,PERKINS & PАGLIUСА[6]和TRАUGOTT &TROUSDАLE[7]的语法化理论认为,语义可以随词汇项或构式语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即词汇项或构式能够将语境意义吸收。我们称之为语境吸收(аbsоrрtiоn оf соntеxt)[8]。如张谊生曾指出,“敢”原来只有“敢于、胆敢”的意思,后来由于“敢”经常用在反诘句中,“敢”就有了“岂敢”的含义,成为评注性副词[9]。
当一个句子中出现两个前后承接或者有逻辑关联的事态,而其中一个是“刚3+V”这种结构时,由于表“偏偏、却”的关联副词“刚3”指向说话者“不愿发生的事态”,那么从说话者的角度看,由于说话者需要表达对“刚3+V”情况出现的不满或不希望其发生的感情,因此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事态很可能是与其相对立或者冲突的,整个句子往往具有转折的意味。由于“刚”经常性地出现在转折的语境下,在语境吸收的作用下,产生了表示“事态转折”的隐含义。此时的“刚”的意义不仅仅是“不愿发生”,而更多的向“未期望发生”或“没料到”转化。如:
(20)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唐·王智兴《徐州使院赋》)
结合语境,此例中的“刚”依然表示“刚3”的“偏偏、却”之义,但其中没有“不愿发生”的隐含义,而只是表示“(事情)出人意料”的转折义。
在人们的认知里,表示转折的两个动作或事态往往间隔的时间较短。一方面,作为说话者如果要表示某一个事态的转折,其选择的上一个比照的事态在时间上往往相隔较近,而不会回溯很远,这样既方便听话者更好理解,也更符合正常人的思维;另一方面,当两个动作时间间隔时间较短时,人们也往往会将其与事态的转折联系起来。比如英语的whilе 是从“同时”的意思演变为让步转折的意思,是一个主观化的过程。演变是由如下的语用推理引起的:whilе 连接А 和В两个动作,表示在发生В 的同时发生А。由于说话人还主观上对А 和В 的同时发生感到意外(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概率不高),因而产生出转折的意思[10]。这可以说明,在人们的认知心理上,“时间间隔短”与“事态的转折”存在关联。
综上所述,在语境吸收的作用下,刚3在唐末开始逐渐产生了表示行动或情况发生不久的时间副词义“刚4”,且“刚4”一般出现在两个分句中的前一句。不过在宋代,时间副词“刚4”出现的频率仍然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关联副词“刚3”的用法依然存在而没有被其他词取代,因而“刚”一词多义容易混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与“刚4”同义的时间副词“才”出现得更早(下文会有讨论),使用也更广泛。如在《全宋词》中,“刚”总共出现过125 次,去除其中表名词和形容词的部分,仅有寥寥几例可以被看作时间副词“刚4”。而在《全宋词》中,“才”出现共1022次,其中大约600例左右都可看作时间副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时间副词“刚4”。整个宋代文献中,“刚”表时间副词的可信用例也十分稀少。因此,我们认为,在宋元之际时间副词“刚4”虽然已经出现,但并不常用,原因可能是由于同时间副词“才”用法、意义接近,因其出现时间较晚而较少地被使用。
到了元代之后,由于副词“刚”产生诸多其他衍生义(如表限定副词义“仅仅”,在此不多赘述),其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增多,时间副词“才”的使用频率逐渐减少,“刚4”这一用法开始变得更为常见,如:
(21)那人家。我才刚去要籴米。他不肯粜与我。他们做下现成的饭。教我们吃了。(元·《老乞大新释》)
(22)不看时万事全休,这一看,好似霸王初入垓心内,张飞刚到灞陵桥。(《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
同时,“刚4”也产生了新的变体——重叠形式的“刚刚”如:
(23)刚刚腾胧睡去,忽听得床前脚步响,抬头起看,只见一个人揭开帐子,飓的钻上床来。(《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
有时还在“刚刚”后面加助词“的”,如:
(24)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元《西厢记杂剧》)
因此,至元末明初,时间副词“刚4”的用法又被重新激活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元以前“刚”作时间副词的用法主要基于“刚3”(偏偏、却)的用法衍生而来,“刚3”在语境吸收的作用下产生了时间副词“刚4”的用法,但由于同副词“才”用法、意义接近而不常用。到了元代,由于转喻机制的作用,“刚”的时间副词用法又被重新激活了,且产生了新的变体。
(二)“才”的语法化历程
相比较“刚”而言,时间副词“才”的语法化过程相对简单。按《说文》:“才,草木之初也。”“才”的本义是“草木之初也”,引伸为“凡始之称”,因而含有“开始,起点”这一义素。在人们的认识中,表示“初始”“起始”的事物往往容易同“数量少”或“数量小”联系起来。因此,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先秦以及秦汉时期,表示动作的量小或者动作涉及的事物量小的限定副词“才”已经出现,我们记作“才1”如:
(25)秦始皇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攻之,宗庙灭绝矣。(《汉书·贾山传》)
(26)今虏使到才数日,而王广礼教则废;如略善收吾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后汉书·班超传》)
随着“才1”使用频率的增加,其语义也逐渐泛化,开始从“动作、数量少”开始向“(间隔)时间少”转移。在唐宋时期,“才”作时间副词的用例逐渐增多,我们记作“才2”:
(27)子细思量争不怕,才生便有死相随。(《敦煌变文集》卷七)
(28)今夕未竟明夕催,秋风才往春风回。(唐·白居易《短歌行》)
(29)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宋·杨万里《池上》)
元明之际,由于近义时间副词“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趋势,时间副词“才2”的使用频率逐渐减少,但至今依然存在。如:
(30)小二道:“我的鸡才在笼里,不是你偷了是谁?”(明·《水浒传》第七十七回)
(31)“怎么才来就要走呢?”(现代·于晴《红苹果之恋》)
综上所述,限定副词“才1”由“才”的基本义引申而来,之后由于语义泛化“才1”逐渐向时间副词“才2”转化。“才2”至迟到唐末已经出现,表示“两个动作距离时间短”,在元明之际逐渐被副词“刚”取代,但这种用法至今仍然存在。
二、“刚才”的产生和发展
(一)“刚才”的词汇化
“刚”和“才”至迟到元末明初,都可做时间副词,且作为时间副词意思相近,都表示“两个动作距离时间短”或“动作在不久前发生”,可用的场合也相似,因而在明代开始常作为同义副词连用,强调“时间短”的语义,如:
(32)且说崔禹正行之间,忽见火起,急催兵前进。刚才转过山来,忽山谷中鼓声大震,左边关兴,右边张苞,两路夹攻。(《三国演义》第八十二回)
(33)刚才把辛环压住了,闻太师勒转墨麒麟,举鞭照顶门上打来。(《封神演义》第四十一回)
在(32)(33)两例中,“刚才”看似位于主语位置,和现代汉语“刚才”一词相近,但实际上此处的“刚才”=“刚”+“才”,意义上仍然是两个同义副词的连用,在句中充当状语,仍可视为副词。结合上下文语境可知,(32)实际上是省略了主语“崔禹”,而(33)的主语是“闻太师”。 将(32)(33)两例中的“刚才”替换成“刚”或“才”,句子的基本意义以及结构都不变。以上2 例的“刚才”表示“行动或情况发生不久”,其意义等于“刚”或“才”,但由于同义连用,其表示“时间短”的程度有所加强。
时间副词“刚”和“才”组合而成的“刚才”原本应为副词。但由于副词“刚才”原本就是两个近义副词叠加形成,因而从意义和用法上而言,从“‘刚’+‘才’”到时间副词“刚才”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如以上的(32)(33)2 例,此时将“刚才”理解为一个词或是两个副词“刚”和“才”的连用,都说得通。“刚+才”的连用通常出现在句首,且往往出现在有一前一后两个动作的句子里,具体表示两个动作之间的间隔时间短。
明代中期“刚+才”开始逐渐凝固为一个词,如:
(34)八戒道:“哥,你往那里去来?刚才一个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赶了去也。”(明·《西游记》第二十一回)
(35)刚才不是揭盖头,他自家笑,还认不出来。(明·《金瓶梅》第四十回)
(36)我刚才分明梦见六姐向我诉告衷肠,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着武松,是好伤感人也!(明·《金瓶梅》第八十八回)
(37)事体总在刚才所言了,更无别说。(明·《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而我们由上文可知,“刚+才”的同义连用表示时间短的程度加强,但34-37例中,虽然勉强都可以用“刚”将“刚才”替换,但除37 外,其他几例用“才”替换“刚才”非常勉强。更重要的是,例37中还出现了“在+刚才”这样的名词特有的搭配。可见此时再将上例中的“刚才”理解为两个词的连用已经不妥。再如:
(38)玉楼道:“刚才短了一句话,不该教他拿俺每的,他五娘没皮袄,只取姐姐的来罢。”(明·《金瓶梅》第七十四回)
此时结合语境,且从语义和逻辑上来说,如果认为“刚才”还是副词连用,那么从语义上看此处“刚+才”连用以进一步强调“短了一句话”这一动作发生不久,但这并没有实际的语用意义,只用一个副词“刚”和“才”已经足够了。这里的“刚才”最合理的理解应为表示某个过去的时刻。
但以上(34)-(38)5 例,除(37)以外,并不能有足够的证据清晰地判定句中“刚才”属于名词或是副词。因此,我们认为,此时“刚才”已经成词,但还处于副词和名词的过渡阶段。
明代中期出版的《三国演义》以及《水浒全传》中,“刚才”分别只出现了2 例和1 例,但在同时期稍微刊行的《西游记》以及《金瓶梅词话》中,“刚才”分别出现了16 例和63 例,而到了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缘传》“刚才”一词则出现了多达186 次。考虑到《三国演义》以及《水浒全传》虽然出版时间在明中叶,但作者罗贯中、施耐庵应为元末明初人,我们可以认为,至迟到明代中期,随着“刚”和“才”连用次数的频繁,“刚才”逐渐凝固为一个可以单独运用的词。
同义连用也是“刚才”的词汇化重要动因。王力先生认为:“汉语大部分的双音词都是经过同义词临时组合的阶段的。这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是两个同义词的并列,还没有凝结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单词。”[11]而这些“临时的组合”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时间的推移等因素逐渐成为一个新词。
(二)“刚才”的逆语法化
到了清代,时间词“刚才”的用法已经基本与现代汉语“刚才”无异,如:
(39)正说着,只见狄希陈坐完了帐,出来陪他舅子。那宾相吃完酒饭未去,仍把刚才那些话又对了狄希陈辨白。(清·《醒世姻缘传》第四十四回)
(40)老婆子见是探春,连忙陪着笑脸儿说道:“刚才是我的外孙女儿,看见我来了他就跟了来。我怕他闹,所以才吆喝他回去,那里敢在这里骂人呢。”(清·《红楼梦》第八十四回)
(41)稚燕看着,方晓得凤孙的继母病故,一封报丧的电报。到此地位,也没得说了,把刚才的一团怒火霎时消灭,倒只好敷衍了几句安慰的套话,问他几时动身。(清·《孽海花》第二十三回)
我们知道时间名词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定语,而时间副词不能。在以上的例证中,出现了如(39)“介词+刚才”的结构,也出现了如(41)里的“刚才”+结构助词“的”,以及(40)里的“刚才”+“是”这样的搭配。这足以说明,此时的“刚才”已经具备了充当主语和定语的名词性功能。由此,我们可以说,至迟到清代中期,时间名词“刚才”已经形成,且语义和用法基本完善。“刚才”这种从虚词(时间副词)向实词(时间名词)的转化,在汉语史中并不多见,我们将其称之为逆语法化(dеgrаmmаtiсаlizаtiоn)的一种[12]。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基于转喻机制的作用。
副词“刚才”的本义是指“行动或情况发生不久”,我们由上文可知,“刚才”最早出现在处于有前后两个动作的语境时,在这一语境下“刚才”仅仅只表示“(某一动作)发生不久”,更准确地说是“两者间隔时间短”,或“前一个动作在后一个动作发生前不久发生”,如上述的例(33)中的“刚才”按语境而言,仅指“压住”和“举鞭……打来”这两个动作的间隔时间短。其时间参照点是后一个动作发生时,与说话者当前所处的时间点无关。
但是言语交际具有实时性,说话者显然更愿意提及正在发生的或不久前的事实,而不是过去很久的事实。因此虽然副词“刚才”的时间参照点只与后一个动作相关,但实际上言语交际里提及的后一个动作发生的时间点,经常与说话者的时间点非常接近,甚至有时就是在“说话时”同步发生的。因此,随着对“刚才”使用频率的增加,人们在脑海中开始将“后一个动作发生时”这一时间参照点与“说话时(现在)”逐渐混同,随之而来的就是“刚才”的意义逐渐从“后一个动作发生前不久”向“距现在不久”转移。如:
(42)我刚才分明梦见六姐向我诉告衷肠,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着武松,是好伤感人也!
此时“刚才”已不仅仅出现在有前后两个动作的句子里,其词义不再是“(某一动作)发生不久”,而是表示“距现在不久”之义。这一语义的变化对“刚才”的逆语法化非常重要。原本副词“刚才”的本义“动作发生不久”或“两者相隔时间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对应的时间范围也很模糊;而“(动作)距现在不久”则是一个更加确定的时间范围。因此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刚才”所指向的动作发生的时刻也更加容易确定。因此当人们看到“刚才”时,可以直接由动作联想到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人们将“刚才”和过去某个相对确定的时间段相联系起来,开始直接用“刚才”表示原先其指向的动作发生的时间段,其意义从“(动作)距现在不久”向“过去某一段时间”转移,进而完成了从时间副词到时间名词的转化。
综上所述,至明代中期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刚才”由时间副词发展为时间名词。至清代中期“刚才”的意义以及用法基本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