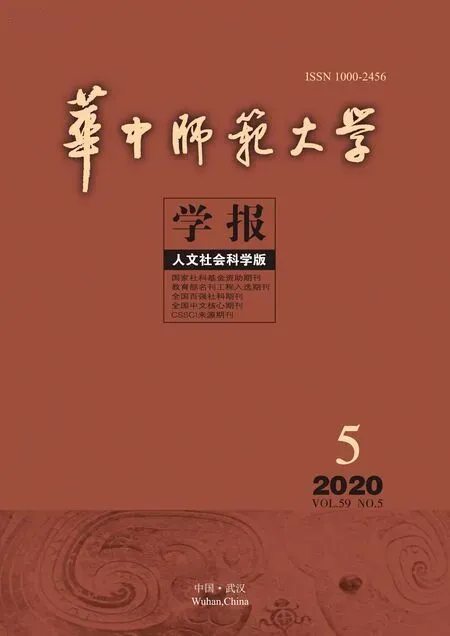梅花象喻与南宋审美文化
2020-01-09刘培
刘 培
(山东大学 文史哲编辑部, 山东 济南 250100)
“审美文化”一词最早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席勒在其《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的,这个概念在当时被赋予了审美陶冶、审美修养、审美培养等含义。国内学术界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叶朗,出现在他主编的1988年出版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中。在该书中,叶朗这样界定这个概念,他说,“所谓审美文化,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①,叶朗的界定其实是对席勒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他指出审美文化是由人类审美活动所生成的,包括三个部分:“各种艺术作品,具有审美属性的其他人工产品”,“审美活动的观念体系,也就是一个社会的审美意识,包括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价值标准等”,以及人的审美行为方式②。中华文化的象喻系统中,许多象喻的生成与当时的审美活动密切相关,“审美文化”这个概念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象喻生成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和有意义的启迪。本文将从审美文化的视野考察梅花象喻的生成,以期加深对这一中华文化象征符号的认识。
在中华文化象喻系统中,花卉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梅花从宋初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南宋以来,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方触目所见的梅花遂成为人们寄托审美情感的最重要花卉。尤其是南宋中后期至元初,梅花象喻被不断塑造,逐渐成为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象征。四库馆臣说:“《离骚》遍撷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意,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江湖诗人,无论爱梅与否,无不借梅以自重。凡别号及斋馆之名,多带‘梅’字,以求附于雅人。”③其实,这只道出了崇尚梅花的表象,当时梅花象喻已经充分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不可缺少的审美元素。《梅花喜神谱》是南宋后期成书的一部题诗梅花画谱,其编者的这段话颇可注意:“余于花放之时,满肝清霜,满肩寒月,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茆屋边,嗅蘂吹英,挼香嚼粉,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其态度冷冷然,清奇俊古,红尘事无一点相著,何异孤竹二子、商山四皓、竹溪六逸、饮中八仙、洛阳九老、瀛洲十八学士,放浪形骸之外,如不食烟火食人,可与《桃花赋》、《牡丹赋》所述形似,天壤不侔。……虽然,岂无同心君子于梅未花时闲一披阅,则孤山横斜,扬州寂寞,可彷佛于胸襟,庶无一日不见梅花,亦终身不忘梅花之意。”④牡丹、桃花等只能述其形似,作者认为它们本身没有值得表述的精神韵味可言;而梅花富于韵致,能传人之精神与境界,故而时人爱梅如狂,目见鼻观之不足,写其神于翰墨,以便随时披览。在当时,梅花不仅关联着日常生活,而且还勾连起古之仁人志士,联系着传统,寄托着社会人格理想和审美期望。
梅花形象能够融入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当时审美文化对其受容程度增大密切相关。笔者将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尝试讨论梅花象喻被塑造的过程,以期揭示梅花象喻被塑造成华夏文化象征的前提条件。
一、梅花审美的丰富性与南宋文人生活
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改窜前人而点铁成金,其他如“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湖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等,将梅之花、香、枝、影等纳入鉴赏范围,开拓了梅花审美的新境,引起宋代文人,尤其是南宋文人的广泛注意,林逋因此成为咏梅文化的重要代表。咏梅文化的高潮出现在南宋时期,文化中心的南移是其基础,这种南方习见的树种之所以能在艺术天地超越众卉而独占鳌头,除了其花、香、枝、影具有审美价值外,应当还有更为深层的因素,因为具备这种审美价值的植物不仅仅只有梅花,为什么梅花会独冠群芳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⑤,平常的风物,有了梅花的点染,就变成了风景。梅花的树形姿态多端,株高适中,适合构景,这是它进入人们生活审美视野并引起歌咏的重要原因。梅花横斜多变的花枝和无叶衬托而淡雅素净的花朵,置于山石、水体、乡野、街市、茅舍、园林等各种背景下,均能呈现出意韵深远的画面。也就是说,它极具构图禀赋和画面感,平淡的风物,点缀以梅便境界全出。这一点,从咏梅文学多通过各种各样的背景来展示便可得到证明。辞赋长于铺排,展示梅花这一特点相当充分。比如李纲的《梅花赋》写道:“若夫含芳雪径,擢秀烟村,亚竹篱而绚彩,映柴扉而断魂。暗香浮动,虽远犹闻,正如梅仙,隐居吴门。丰肌莹白,娇额涂黄。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飘香。娇困无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临镜严妆。吸风饮露,绰约婵娟。肌肤冰雪,秀色可怜。姑射神人,御气登仙。绛襦素裳,步摇之冠。璀璨的皪,光彩晔然。瑶台玉姬,谪堕人间。半开半合,非默非言。温伯雪子,目击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东郭顺子,正容物悟。”⑥雪径烟村、竹篱柴扉,这种种惯常的景象因梅的点染而顿生韵味,构成一幅幅素雅的画卷。在景象各异的背景烘托下,梅花更显得姿态绰约,引人入胜,赋中把梅花比作梅仙(汉之梅福)、梅妃、姑射神人、瑶台玉姬、温伯雪子⑦、东郭顺子⑧,由人间高人、美女进而为仙女、神女和得道的高人。这些比拟,刻画出梅花拔出俗态而刚柔相济、富于动感美感的姿态以及花型花色的明媚动人、赏心悦目。梅花姿态多变,如美女之临妆、静立、缓步、巧笑,如仙女之御气登仙、严妆下凡,如高人之目击道存、正容物悟。李纲的这段由实而虚、由姿态到神韵的描绘充分展示了梅花在各种不同背景下变化多端而富于层次的美感,揭示出梅花审美的丰富性,这也是它在构景方面的优势所在。
张嵲的《梅花赋》在展示梅花构景的丰富性方面也颇有特色:“若乃远壑冰消,疏林雪后,沙村迥而日晚,石涧浅而寒溜。临山径之欹危,出茅檐之左右。或芬敷而盛发,或伶俜而欲瘦。或含葩而未吐,或喷蘂而竞秀。其高者如举,其低者如坠。其疏者如刻,其密者如缀。其素者如愁,其绛者如醉。倾日而照者如笑,迎风而靡者如愧。睹节物之芳华,乱乡愁于晚岁。怀故园之春色,惟兹花之颇类。”⑨赋中写到梅花生长的荒寒环境,林间、溪旁、丘壑、山径、沙村、茅店,梅枝或虬曲苍劲或横斜舒展,花朵或喷蕊绽放或含苞待放,与周遭环境构成一幅幅美妙的画卷。文中的如举如坠是写花朵在枝头的形态,如刻如缀是写疏密不同的花朵附着于枝柯的姿态;如愁如醉是写花色或浅或深,韵致各异;如笑如愧是写梅花在日光与和风中的种种情态。荒村夜店这等荒寒景象,有了梅花的点缀而生机盎然。它勾连起沙村茅檐,勾连起游子对家乡的种种记忆,因此,赋以“怀故园之春色,惟兹花之颇类”点睛,梅花在乡愁记忆中的意义得以彰显。
“梦回春草池塘外,诗在梅花烟雨间”⑩,梅花的绽放如同谢灵运诗中所表现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那样,让人眼前一亮,心胸顿时开朗。它是南国早春最先盛开的花朵,二十四番花信风之首,它是冬日出现的第一道亮色,给生活在漫长阴冷中的人们带来惊喜,使萧瑟阴郁的景物顿时焕发出生机,周遭的景物也因之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刘辰翁在《梅轩记》中说:“吾尝谓梅者使其生于暄淑之景,而立乎桃李之蹊,虽翛然欲以其洁独,而争妍者有其色,好懿者无其人焉。是其独也时也,好之者亦时也,若二三月之间,则莫之好矣。”指出梅花引起人们的热爱与其早发特征密切关联。释仲皎《梅花赋》多角度描绘早春之梅:“翳彼梅萼,参乎雪花。香度风而旖旎,影临水以欹斜。莹若裁冰,带玉溪之潇洒;清如熏麝,辟仙苑之光华。且夫晴云乍敛于东郊,丽日才升于南囿,酥萼失艳,铅葩独秀。含宿雾以凄迷,洗晨霜而孤瘦。冻开蜡蒂,自宜清峭之天;吹破檀心,谁怯黄昏之候。莫不山屏冉冉,水镜盈盈,蓓蕾似连璧,枝柯在交琼。嗟额上之半装未了,何眉间之一剪先横。竹叶杯中,野店谩资于幽咏;梨花梦里,晓云难驻于高情。”这段文字如拉伸自如的镜头,摄取梅花远近不同的景致。首先是特写,摹写梅花初发,如雪花般轻盈,梅香随风飘动,似乎具有韵律;接着是中景和远景,描绘早梅临水弄影、隐于寒雾,以及丽日下、山水间的旖旎情态;然后转入近景,刻画在山屏水镜的背景下梅花的蓓蕾和仍积有残雪的枝柯;最后点出人的赏梅咏梅,这种种的景致因人的介入而具有了意义。王铚的《梅花赋》则写道:“方隆冬之届候,属祁寒之鼎至。瞻远岫兮无色,盼丛条兮失翠。彼美仙姿,夐存幽致。春风万里,报南国之佳人;香艳一枝,富东君之妙意。观夫离类绝俗,含新吐奇。”在景色惨淡的氛围中,梅花的出现传达着春的讯息,预示着蛰伏的生机蠢蠢欲动,骀荡的春风即将来临。“离类绝俗”是指梅花早春第一枝,异于众卉;花色淡雅,拔出流俗,故而“含新吐奇”。苏籀的《戏作梅花赋》描绘梅花乃报春使者曰:“百卉僵冻几摧兮,妙切瑳而雕刻。揠宇宙之英淑兮,嗾林薄之萧瑟。高柯乔干,丛蘖槎枿兮,偃亚竦蟠而奇崛。”在百卉僵冻的时节,梅花的出现一扫林间萧瑟之气,其或挺立或虬曲的躯干,极具拗劲之张力,似乎昭示着生命活力的跃动。赋中的“嗾”,尽显梅花绽放而抑郁顿消的欣喜感,一字传神。
梅花与文人生活紧密结合,为人们全方位体会它的美提供了契机。梅花的早发特点和构图禀赋,加之易栽培,适应性强,使它在南国众卉中独冠群芳,这为它加深与文人的联系、深入文学与文化之中奠定了基础。梅花是南方山野间遍生的树种,由于气候的原因,北方罕有生长。成书于北宋时期的《本草图经》说:“梅实生汉川山谷,今襄汉川蜀江湖淮岭皆有之。”《岭南异物志》有“南方梅繁如北杏”之说。邹浩《梅花记》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岭南多梅,土人薪视之,非极好事,不知赏玩。余之寓昭平也,所居王氏阁后半山间,一株围数尺,高数丈,广荫四十步。余杜门不出,不见它殖何如,问之土人,咸谓少与此比。然此株正在王氏舍东,穿其下作路,附其身作篱,丛篁榛棘,又争长其左右,余久为之动心。顾王氏拘阴阳吉凶之说,不敢改作。顷遇花时,但徘徊路侧,徙倚篱边,与之交乐乎天而已。欲延一客,饮一杯,竟无班草处。一日坐阁上,闻山间破竹声,策杖往观焉,则王氏方且遵路增篱,以趋岁月之利。欣然曰:‘时哉,时哉!’谕使辟路而回之,彻篱而远之,视丛篁榛棘而芟夷之。环数百步,规以为圃。”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梅花在岭南极为常见,且岭南多生长花树,故而它不为人们所重,以柴薪视之。由江南到岭南的邹浩处心积虑延以入圃,则反映了士人爱梅艺梅之习。
艺梅渐盛于隋唐,南宋和元代进入兴盛时期。南渡以来,世风渐趋奢靡,达官富贾竞相辟建园墅,齐民百姓也多喜以花草树木装点茅檐。近宅旁多植卉木以构景,远居处则求野趣之天成。南宋园林艺术因之逐渐远离了追求平远、壮美、雄浑的境界,日益转向诗化、画化、精致化,显现出巧趣柔美、清雅俊逸、精深幽邃、幻化多致的写意特征,移步构景上佳的梅花自然成为重要的景观树种。正如范成大指出的:“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在当时,像范成大、辛弃疾、张镃这样的官员多踞湖山野田营造亦农渔亦园林的大型庄园以颐养天年。仅饶州(今上饶)一带就有杨万里的诚斋、韩元吉的南涧、洪适的盘州、洪迈的野处、向子湮的清江芗林、任诏的盘林。这些庄园中,少不了广植梅花。如辛弃疾在饶州的带湖、瓢泉庄园就种植不少梅树,这从他的咏梅词创作可以看出来。张镃则于“淳熙岁乙巳,予得曹氏荒圃于南湖之滨,有古梅数十,散漫弗治,爰辍地十亩,移种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别圃江梅合三百余本,筑堂数间以临之。又挟以两室,东植千叶缃梅,西植红梅,各一二十章。前为轩楹,如堂之数。花时居宿其中,环洁辉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复开涧环绕,小舟往来。”范成大既在他的石湖庄园艺梅百本,又购园地遍植梅花:“余于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数百本,比年又于舍南买王氏僦舍七十楹,尽折除之,治为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吴下栽梅特甚,其品不一,今始尽得之,随所得为之谱,以遗好事者。”这些具有一定文化品位和感召力的官宦的艺梅赏梅咏梅好尚具有引领风气的效应,而且与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文人学士形成创作上的互动,这对推动梅花意象向社会文化的渗透,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对于一般读书人而言,在自己的园地庭院宅旁窗下植梅已成常态。有于田宅植梅者,如幸元龙的小园:“渠流泓泚,梅竹潇爽,觞咏其间,自娱自足,不与流俗伍,其渊明之风乎”;杨简的湖边蜗居:“虽朔飙之戒寒,烂丹丘于四山,而压冰之梅独出其奇,吐孤芳而盘旋。玄冥又从而佐之,翦玉镂瑶,雨花其间。有家如此,亦可谓奇矣”;有于庭院植梅者,如吴儆之小庵:“庵之西有梅,旧为灌木所蔽,枝干拳曲,苔莓附之,与会稽之古梅无异。盖梅之隐者,老而甚癯,山泽之儒也”;常棠之小园:“于是锄莠削芜,艺梅畚竹,重楹列牖,盖瓦级砖丹如也”;俞德邻:“居室之西有隙地,衡从数十武,老梅穉竹,攒立丛倚,间移花卉杂焉。趣虽未就,暇之日杖屦或可往来也”;黄大舆:“予抱疾山阳,三径扫迹,所居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逾,略已粲然。于是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以为斋居之玩”。为官者也喜在自己的官衙居处植梅,如张栻:“植梅竹于前,而其后为方沼,向之茀不治者一旦为靓深夷衍之居,于以问民事,接宾客,奉燕处,无不宜者。”李石:“方冬春交,雪霰风雨之会,屋之东隅无他草木,唯梅竹二物,如相视而嘻,而相语以悲者。方念所以流转弃摈以即死,得为此惠者,乃天也。”薛季宣:“武昌尉寺旧无憩息之地,退食之次,燕伸无所。番阳王彦材作尉此邑,始即其堂之中庑,少加葺垩,辟其夹砌,树梅焉,命之曰‘梅轩’,以便安其退省。”刘学箕:“屋宇靓深,梅竹茂密。前通州治之东厅,接以过廊”。一些地方也因植梅而为人们注意,如当涂的尼山,卢钺写道:“尼山在城东五六里,前未之闻。山不在高,有景则名。其麓古梅数十株,乃他山之所无,亦江南之所罕有。询之野老,证之梅经,后望封植,几百余年,苏干鳞皴,蟉枝翔翥奇壮,益横发捷出。如列仙之臞,盘礴玉峰,云裳月佩,飘飘乎欲凌天风而高举;如茹芝之老,龎眉皓鬓,衣冠甚伟,傲睨汉聘,方嵬岸而容与。含章之阁,白玉之堂,扬之月观,杭之孤山,未必若是美且都也。然斯梅专美一丘,不求人知。”
处在触目而见梅的环境中,人们对赏梅情有独钟,感受深刻,赏梅成了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梅花姿态的画面感所焕发的多层次的美感容易引发欣赏者情绪、精神的移入,引起心理共鸣,融情入景,进而形成能够体现人的文化积淀、情趣、人格修养的情境,启发人们兴发感动的生命活力。梅花超强的构景禀赋和多层次的美感,使它容易进入欣赏者的情境之中,唤起欣赏者的知识和情感积淀,激发生命活力,使人的心理期待、人生愿景、人格理想、审美情境等通过梅和它营造的画卷得到彰显和抒发。因此,人们对梅花的歌咏能够充分调动起内心丰富的情感体验,一往而有深情。比如李石在《梅坞记》中写道:“屋檐之南有老梅,株如柱轴,一根别为三四股,可荫十许步,环以数小竹外,悉芟去之。仍辟屋一角,作一窗,以即其荫。每每风日开阖,煜然之光,蓛然之声,往来几砚书帙间,与静境相接,如行村坞,因以坞名之。又植穉柏二百周墙之阴,与梅为佳伴。他日凌冬霜雪爱玩之树,是又其拙之拙者也。”幽窗静几,梅花弄影,读书燕居生活因梅的介入而充满情趣。文天祥在《萧氏梅亭记》中写道:“于其读书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作亭于屋之西偏,周之一径,被径一梅亭,后有廊,有诗画壁间。前方池,广五尺,饲鱼而观之。邻墙古树,蔽亏映带。清风徐来,明月时至。”月印疏影,风送暗香,孤寂的读书生活有梅为伴而妙趣横生。
学界对宋人的赏梅活动研究颇多,本文不再赘言,笔者想指出的是,宋人赏梅重视沟通物我、超越自我,这是一个观我观物的过程,审美主客体交流交融的过程,心灵舒展、活力释放的过程。研究者多以“比德”来概括南宋的咏梅文化,这是将其简单化了。而且,他们对梅的情感往往由观赏而爱恋、仰慕,进而企望与梅合一,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境界上的超越,这并非单单是对某种德行的比附。唐庚的《惜梅赋》写自己与梅花境遇相似,因而惺惺相惜,赋曰:“县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于何时。荫一亩其疏疏,香数里其披披。侵小雪而更繁,得胧月而益奇。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溷其幽姿。前胥史之纷拏,后囚系之嘤咿。虽物性之自适,揆人意而非宜。既不得荐嘉实于商鼎,效微劳于魏师。又不得托孤根于竹间,遂野性于水涯。怅驿使之未逢,惊羌笛之频吹。恐飘〇之易及,虽清绝而安施。客犹以为妨贤也,而讽予以伐之。嗟夫!吾闻幽兰之美瑞,乃以当户而见夷。兹昔人之所短,顾仁者之所不为。吾宁迂数步之行,而假以一席之地,对寒艳而把酒,嗅清香而赋诗可也。”己与梅皆混迹于胥史之地,梅不能展其幽姿馨香,己不能伸其济世怀抱,俗人不解梅韵,荒远难遇知音。对寒艳而把酒,嗅清香而赋诗,既是赏梅,也是悯己。梅与我,俨然是出离俗世的知音。这种引梅为知己的手法在咏梅文学中极为常见,可见宋人的审美境界和精神境界与梅格是相连相通的。
林敏功的《梅花赋》将观梅描绘为怀远、相见、仰慕的恋慕过程。赋曰:“对重云之惨惨,曾北风之萧萧,闵草木之殄瘁,惊梅花之缀条。忆昨载酒寻芳,狂魂暗消。眺瞻乎重冈远岫,宴乐乎风晨雪朝。江回岛树,竹抱溪桥。寒英粲然,宛其见招。可援可攀,可游可处。忽兮薄怒,不可晤语。左揖袂兮素娥,右拍肩兮青女。香浮浮兮实来,意默默兮暗与。实来兮可期,默默兮增思。当时坐上曾赋诗,庾郎敏捷何郎迟。不唯春恨陇头见,曾使新妆梦后宜。乐莫乐于相遇,悲莫悲于将去。恨羌笛之送愁,怨回风之撼树。昔行乐兮可追,今行乐兮非故。感颜色之屡荣,迫岁华之又莫。岁莫如何,伤情实多。挈之以永怀之佩,申之以无斁之歌。有美人兮在空谷,澹幽茸兮耿幽独。思公子之同归,回契阔兮騑服。”愁云惨淡,北风萧瑟,应是寒梅绽放之时,然而载酒寻芳,狂魂暗消,落寞之情反衬出睹梅而“惊”的欣喜。江回岛树、竹抱溪桥的画面因梅而顿生春色,绽放的寒英仿佛在召唤自己,然而“忽兮薄怒,不可晤语”,其不可亵玩的刚贞品格令人由爱而敬。梅花像人们意念中的神女,美丽而神圣,那浮动的香气仿若与人沟通心灵,暗自相期。乐莫乐于相遇,悲莫悲于将去,当众卉盛开之时,梅花将翩然而去,留下绵绵不绝的思念。这篇赋以美女赋、神女赋的爱而不遇的套路来描写梅花,将与之相遇的经历描绘为一段带有缺憾的美丽的情感经历,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杨万里的《梅花赋》也是这样的套路,但他选取一个梅花绽放的小景以寄意,赋曰:“爰策枯藤,爰蹑破屐,登万花川谷之顶,飘然若绝弱水而诣蓬莱,适群仙,拉月姊,约玉妃,燕酣乎中天之台。杨子揖姊与妃而指群仙以问焉……歌罢,因忽不见。旦而视之,乃吾新植之小梅,逢雪月而夜开。”月夜赏梅,天地澄澈,亦真亦幻,梅花摇曳的姿态被描绘为仙女的歌舞,墙角小梅绽放被描绘为仙女下凡。又如谢逸的《雪后折梅赋》描写雪夜折梅,赋曰:“耿夜阑之青灯,沉万籁于岑寂。忽竹林之风声,颤檐端而索索。徐披衣而启户,飞雪花之如席。眺溪上之寒梅,亘千林于一色。恐青女之下临,唁玉妃之堕谪。竞孤峭以相高,两含情而脉脉。乃策壶公之杖,乃蹑阮生之屐。度横彴以跰跹,排寒威而辟易。绕琪树之玲珑,攀琼柯之的皪,摇疏影之横斜,漾清溪之寒碧。披绪风而香冷,引轻素而烟羃。忘冻手之欲龟,携纤枝而入室。映几研之璀璨,藉海岱之玉石。寓逸想而自成,若愤余之幽僻。觉毛发之森疏,迷今夕之何夕。因燎薪而拥炉,泣铜瓶之唧唧。起取酒而自温,倾小槽之珠滴。昔花月之成妖,幻武公而夺魄。余少贱而多难,岂曰耳目之敢役?往就醉而曲肱,吼怒雷于鼻息。晓援毫以陈辞,纪作梦之戏剧。”由风声飞雪引出寒梅,由“两含情而脉脉”引出折梅以寄意,由携梅入室转入对梅酌酒,因梅畅叙,怀梅入梦。整个折梅过程环环相扣,对梅的仰慕之情愈转愈深。咏物文学喜以神女、仙女、美女来比况花卉,南宋咏梅文学在运用这种手法时多将梅花描绘得高雅绝俗,爱恋倾慕之情融汇其中,足见它在人们审美世界中的地位。
梅花是南方随处可见的树种,也是触目而见的风景,与人们的生活、审美文化等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建立起深入而广泛的联系,人们对它给予的关注和倾注的情感是其他卉木所无法比拟的。梅花象喻浓厚的域性特色,加上主流文化对它不断充实与丰富,使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成为代表南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甚至是南方政权所代表的华夏文化正脉的符号。因此,元代那些执着于华夏文化纯洁性与正统性的人们,往往借重咏梅来表达亡国之思和对华夏文化的执念。
二、梅格塑造与南宋社会审美理想
梅花象喻与南方、华夏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华夏文化的象征符号,除了地域性特征外,还离不开社会审美理想对它的充实、改造。审美理想是人们对于美的最高要求和愿望,是在审美感受基础上形成的对美的一种完善形态的忆憬和向往,它指向未来、指向人的生活远景的创造性想象。南宋社会的审美理想,偏向于闲适自然、旖旎多姿而又抱道自守、格调高雅的美感。人们对梅花审美的体认与塑造,正是遵循着这样的审美理想。
陆游有咏梅诗句曰:“一春花信二十四,纵有此香无此格。”整个春天,报信之花二十四,然即便花香可与梅香比肩,但却无梅之“格”。可见,它异于众卉最为突出的是其有“格”,梅格的具体含义,从陆游诗中看,是指这句诗前面表述的内容:“素娥窃药不奔月,化作江梅寄幽绝。天工丹粉不敢施,雪洗风吹见真色。出篱藏坞香细细,临水隔烟情脉脉。”梅具有谪仙人的美质,清高而娉婷婀娜,皎洁而旖旎多姿。此句的下文“放翁年来百事惰,唯见梅花愁欲破。金壶列置春满屋,宝髻斜簪光照坐。百榼淋漓玉斝飞,万人辟易银鞍过。不惟豪横压清臞,聊为诗人洗寒饿。”写梅花对作者精神世界的感染力,这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可见,梅格是指梅的美学风范,是社会审美理想对其塑造的结果。关于梅花的美学风范,人们讨论较多的是皮日休对宋广平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的一段议论。梳理这些讨论,我们或可窥见梅格的具体内涵以及社会审美理想等因素对梅格生成所起的作用。
皮日休的那段议论出现在他的《桃花赋》序言中,他说:“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节,刚态毅状。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文中说宋璟《梅花赋》“清便富艳”,当是指行文流畅、辞藻华美、用典繁缛,属于文章审美范畴,关乎作者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审美诉求。“富艳”这一词组最早出现在范宁的《春秋谷梁传注疏序》,他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所谓“艳”,当指使用富有色彩感的文词,使意象丰富、鲜明;“富”即文词盛多、雕琢、繁饰之意。文中的“贞姿劲节,刚态毅状”“铁肠与石心”是指为政态度,政治操守。皮日休将不是一个意义层面的审美与政治态度两个范畴等量齐观,显然是不恰当的。严正的政治家难道就不应该欣赏、创作“清便富艳”的、具有徐庾体风格的文章吗!文中提到的“徐庾体”其概念内涵有一定争议,但总的来说,是指南朝庾肩吾、庾信父子和徐摛、徐陵父子引导的绮艳文风,既包括诗赋这样的有韵之文,也包括无韵之“笔”。皮日休这里用到这个概念,是指宋璟《梅花赋》的绮艳风格,而非“宫体诗”的那种轻浮格调。这段议论引起了苏轼的注意,他在《牡丹记叙》中说:“然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今以余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又岂足信哉!”指出托名宋璟的《梅花赋》著作权有问题。但是苏轼与皮日休所见很难说就是同一个文本,他的议论并没有涉及“铁心石肠”与徐庾体的关涉问题。晁补之对此则有较为通达的看法,他说:“而余亦尝论广平严毅,所谓没向千载,凛凛犹有生气者。至于人之所同为,不害其异,而鹿门子庸何怪乎?张良、崔浩,皆昔之所谓豪杰。良宜魁梧奇伟,而貌状乃如妇人女子;浩若不胜衣者,而胸中所怀,踰于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识君子之大体也!……以广平之铁心石肠,而当其平居,自喜不废,为清便艳发之语;则如敬之之疏通知方,虽平居富为清便艳发之语,至于临事感愤,余知其亦不害为铁心石肠也。”认为人的器识与审美心境、审美理想是有区别的,其观点相当深刻。
南宋以来,人们对宋璟《梅花赋》的议论并没有像晁补之那样通达而圆融,更多的意见是在“文如其人”的前提下试图使“铁心石肠”与“清便富艳”取得一致。李纲在《梅花赋》序中说:“皮日休称宋广平之为人,疑其铁心石肠,及观所著《梅花赋》,清腴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广平之赋,今阙不传。予谓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其标格清高,殆非余花所及。辞语形容,尤难为工。因极思以为之赋,补广平之阙云。”他认为梅花“标格清高”,与宋广平的“铁心石肠”具有一致性,铁心石肠是作赋者的性格特征,也是梅花的美感特征,二者具有一致性,因而能够产生共鸣。他指出宋广平赋已经不传,因极思以为之赋,补广平之阙,亦即以“清腴富艳”之笔调摹写梅花。李纲所说的“标格”,是指风范,风度,梅花具有“清高”的风范仪态,故而可与人的“铁心石肠”相匹配。梅花独拔百卉,非特仅仅是早发,更在于其“标格清高”。梅之“标格”与“梅格”语义相同。“梅格”一词最早出自苏轼诗中。他在《红梅三首》其一中写道:“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认为即使是和桃杏花色相似的红梅花,因其具有“梅格”而高出“绿叶与青枝”的桃杏花,诗老(石延年)将其以桃杏花一般等闲视之,有焚琴煮鹤之嫌。石延年的《红梅诗》有“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之句,表现初见红梅的诧异之情,应该说这句诗很有表现力,但苏轼认为拿梅花和桃杏相提并论是唐突了梅花,因为梅花标格清高,常花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据载苏轼曾说:“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疎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写物之功乃指传神写照,表现物象之精神格调,对于梅花而言乃是应该写其梅格,因此讥诮石延年诗是“陋语”、“村学中体”。陆游在《芳华楼赏梅》诗中提到的梅花之“格”,是继承苏轼的说法,而更进一步指出“格”,即审美风范,是它异于众卉最突出之处。李纲以标格清高标举之,也与苏轼的看法一脉相承。他创作的《梅花赋》将梅花比作神女、仙女、美女,比作脱去尘俗的美男,以华艳繁缛的辞藻和变化多端的表现手法全方位描绘梅花之构景和婀娜多姿的仪态,远绍南朝徐庾体之神韵。不过,他是以一种景仰的、心向往之的情绪来运思行文的,处处在彰显它不同凡俗的美韵和仪态。可见,他所理解的梅格乃是清高与“清便富艳”的统一,亦即“铁心石肠”之刚与旖旎多姿之柔的统一。在赋中,李纲写道:“惟标格之独高,故众美之咸具。下视群芳,不足比数。桃李逊嫮,梨杏推妍。玫瑰包羞,芍药厚颜。相彼百花,孰敢争先?莺语方蛰,蜂蝶未喧。独步早春,自全其天。至于功用已周,敛华就质,落英飘〇,结成青实。钟曲直之真味,得东方之正色。傅说资之以和羹,曹公望之以止渴。用其材可以为栋梁,采为药可以蠲烦热:又非众果之所能仿佛也。”这是在铺排梅花的姿态和构景之后的结穴之笔,指出梅花标格独高,众美咸具,它的美超越众卉之上,而调鼎和羹之功、栋梁之才、蠲烦热之效,又非众果之所能仿佛之。梅的功用如同人的政治才干,可比拟“铁心石肠”的济世襟怀的崇高美,其旖旎多姿的韵致具有阴柔的特点,刚柔相济是梅格的重要内涵。
李纲对梅格的理解具有代表性,人们在强调其凌寒独放、可堪大用的品格时更不会忽略它的姿态美,或者说,它理想的美学风范是刚正不阿与旖旎多姿兼具的风骨之美。王铚说:“皮石休曰:宋广平铁心石肠乃作梅赋,有徐庾风格。予谓梅花高绝,非广平一等人物不足以赋咏。”认为宋广平之人格与梅格是相通的。葛立方说:“近见叶少蕴效楚人《橘颂》体作《梅颂》一篇,以谓梅于穷冬严凝之中,犯霜雪而不慑,毅然与松柏并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铁肠石心,安能穷其至?此意甚佳。审尔,则惟铁肠石心人可以赋梅花,与日休之言异矣。”认为梅格清高,与松柏并配,非桃李所可比肩,唯有宋广平那样的铁肠石心方可写梅花之韵,传梅花之神。姜特立在《跋陈宰梅花赋》中也说:“夫梅花者,根回造化,气欲冰霜。禀天地之劲质,压红紫而孤芳。方之于人,伯夷首阳之下,屈子湘水之傍,斯为称矣。自说者谓宋广平铁石心肠,乃为梅花作赋。呜呼梅乎!其将置汝于桃李之间乎?余谓唯铁心石肠,乃能赋梅花。今靖侯不比之佳人女子,乃取类于奇男伟士,可谓知梅花者矣。”促成梅花描写由美女向贞士形象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乃是人们对梅格认识的日益深入。姜特立认为“铁心石肠,乃能赋梅花”,反映出“铁心石肠”之刚与旖旎多姿之柔已经完全融通于梅格中,亦即“禀天地之劲质,压红紫而孤芳”。周紫芝在《双梅阁记》中对梅格刚柔相济之美诠释得更为具体生动,他说:“草木之妖丽变怪所以娱人之耳目者,必其颜色芬芳之美。而梅之为物则以闲淡自得之姿,凌厉绝人之韵,婆娑于幽岩断壑之间,信开落于风雨,而不计人之观否,此其德有似于高人逸士隐处山谷而不求知于人者。方春阳之用事,虽凡草恶木猥陋下质,皆伐丽以争妍,务能而献笑,而梅独当隆冬冱寒风饕雪虐之后,发于枯林,秀于槁枝,挺然于岁寒之松让畔而争席,此其操有似于高人逸士,身在岩穴而名满天下者。余之论梅有得于此,而无所发其狂言。……以赋和靖之诗而草广平之赋,然后知余言之非夸也。”他认为宋广平的《梅花赋》应是像林逋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梅之姿态韵味,方能传神写照,而梅之美乃在于“闲淡自得之姿,凌厉绝人之韵,婆娑于幽岩断壑之间”,是高洁与美丽有机的统一。
南宋人对梅格的体认主要表现为对“铁心石肠”与“清便富艳”的统一,刚与柔形成的张力为梅花审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内涵。楼钥在《跋陈昌年梅花赋》中说:“皮日休赋桃花,欲状其夭冶,专取古之美女以为况。此赋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胜高人以极其变。梅固非桃可比,体物之工,亦又过之。”他认为陈昌年的《梅花赋》体物之工超过“状其夭冶”的皮日休的《桃花赋》,且“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胜高人以极其变”,这说明陈赋在追摹徐庾体风格方面甚至超过了皮日休的《桃花赋》,虽然都是在描写花卉,梅毕竟不是桃花,因其标格甚高,华艳的描绘应能对梅格传神写照,因而文章情感应崇雅端正。张镃在《梅品序》中说:“梅花为天下神奇,……但花艳并秀,非天时清美不宜。又标韵孤特,若三闾大夫、首阳二子,宁槁山泽,终不肯俯首屏气,受世俗湔拂。间有身亲貌悦,而此心落落,不相领会,甚至于污亵附近、略不自揆者。”文中提到的“标韵”即标格、梅格。梅花之有标韵,如人中之屈原、伯夷、叔齐具有不受世俗浸染的品格。梅花精神气质的高洁出众和“花艳并秀”形成了刚柔相济的风度仪态。
梅格的刚柔相济还体现在梅的枝柯形态上,范成大在《梅谱后序》说:“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其新接稺木,一岁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酴醾蔷薇辈者,吴下谓之气条,此直宜取实知利,无所谓韵与格矣。”梅花异于众卉在于“韵”和“格”:格,指品格;韵,是指富于美感的情趣、仪态。“韵”“格”其实就是标格,或者梅格。范成大理解的梅格是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所表现出的瘦劲虬曲的力度美和横斜逸出的飘逸美,亦具有刚柔兼济的特点。而新生的枝条与常木无异,无韵、格可言。他有《古梅》诗曰:“孤标元不斗芳菲,雨瘦风皴老更奇。压倒嫩条千万蕊,只消疏影两三枝。”梅的美不仅在于花朵之美以及不与众卉争春的特征,更在于其老劲之美,因而嫩条与繁花不及疏影与老枝。因为虬枝疏花方显刚柔兼济的韵致。梅格刚柔相济的美也体现在枝柯与花朵的呼应上。何梦桂在《邵梅间诗序》说:“天地冰霜,万木冻折,而冰姿铁骨,玉蕊琼英,傲然独出于万物之表。故于是时,上下尘世无一物得与梅齿。其清彻寒绝雅宜在梅间者,惟雪与月。”“冰姿铁骨”与“玉蕊琼英”形成一种呼应关系,体现着梅的清雅高洁,只有雪与月能与之配合,构成标格清高的画卷。陈著的《梅窗记》则较为全面阐述了梅格的各个层面:“梅于植物,癯而益劲,枯而益奇,故其色淡中自韵,如古君子。其香夐绝,不染富贵脂泽气;其实酸,不投甘,昔人至以和羹方大用。非杜少陵莫敢索笑,非林和靖不能以诗写。而世之人不识梅、不见梅者,类拾人余唾,借以自表揭,辱梅矣。”“凡物之香者或无色,色者或无实,三美具,又劲且奇,有岁寒操,非梅而何?……雪霜之玉以妍之兮,而将茹其芳而清之胚。雨露之膏以成之兮,而将落其华而质之培。媚柔秾郁彼纷纷兮,此寂寞矫自享于山之颠、水之隈。而将冠方山、佩飞霞与周旋兮,苟初心之不践有如梅。”梅花具有癯而益劲、枯而益奇的枝干,色淡而自成美韵的花朵,绝远悠长的馨香,酸而不俗的果实,无尘杂之气而合于大用,凡此种种,构成了梅花的飘逸美、“劲且奇”的刚硬美、清高闲雅与济于世用的华实相生之美的“三美具”特征。而以此格调,与霜雪雨露相沆瀣,与山颠水隈相映衬,不与众媚柔秾郁争春色而自成高雅绝俗之美境。
梅格的刚柔相济之美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南宋人对此的体认与塑造反映出当时的审美理想具有兼容贞刚操守与旖旎情思的倾向,这与时代风气密不可分。南宋以来文学发展逐渐脱离追求理趣的哲理性超越之路数,走向直接表达人生感受和审美理想,走向以平常之心感受生活,体认生活,表现生活。过去那种横亘在文人心里的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索和彻悟的冲动在现实的苦难中消磨殆尽。他们处庙堂则慷慨激昂,高论煌煌;居江海则啸风吟月,随运乘化,魏阙之思相对淡薄。可以说,较之北宋,南宋文人的心态更具世俗化和生活化。因此,其审美好尚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往的追求妙解天人、澄怀观物转向追求旖旎婉转、摇曳多姿,由浑朴大方转向细美婉约。他们所崇尚的美逐渐向低回柔婉、旖旎多姿的阴柔美靠近,欣赏更贴近生活的、能为更多的人所接纳的清倩灵动的美。同时,北宋后期兴起的理学在南宋以来滋生旺长,标举道德人生、强调士人节操的“崇正”的文艺思潮也在塑造时代审美风尚方面起着作用,尤其是理学对耕读传家生活观念的改造与标举,使得乡居生活具有了在修身齐家中进行治国平天下大业的含义。可以说,南宋的审美理想就是在世俗化和道德化两种美学取向的矛盾冲突中发展的。标格清高而内心光风霁月、鸢飞鱼跃,成为人们较为普遍的人格追求。梅花美学风范的塑造,正体现了时代审美理想的特征。
三、梅花象喻与审美境界
洪咨夔在一部书稿的跋文中曾提到“其赋梅,有‘天不能寒独有梅,一涉春风不足奇’之句。读之至此,怅然久之,曰:其有分寒饿也耶?余于此有会,其亦有分寒饿也耶?”梅花凌寒独放,处寒饿而卓然而立,体现着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南宋人在梅花象喻的塑造中,相当重视对道德情怀的开掘,在早发报春的形象外,梅花形象还融入了凌寒冒雪的内容,彰显着君子人格和道德境界。
美是道德的象征,中国传统审美高度重视美和善的统一。审美境界不可以抽离道德因素,道德境界也包含着审美因素,审美因素缺失,道德境界将不够完善,不够理想。缺少道德修养的主体是难以形成和呈现审美境界的。艺术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呈现着一种人格美育精神。梅格的塑造,同样立足于道德境界,融汇着人格美育精神;而且这种塑造只有进入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的层面,审美价值才能得到彰显和提升。当然,梅花象喻的审美构建必须遵循“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原则,道德因素不应作为概念,而应当作为一种直观融化于审美境界中;反之,梅花书写就会变成道德的图解和演绎,美感会大为削弱,甚至失去审美意义。
在宋人的梅花书写中,人格追求和道德境界在南宋中后期越来越突出,这与理学对人生观念的渗透密切相关。成就君子事业是传统文化当中人格修养的主要目标,在儒家看来,君子的重要标志是德行,道德修养一直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学更是将品德修养作为贯彻天理与人性的核心内容,把一切人事物理都建立在德性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行为都用德性来规范,来评价。因此,养成道德就成了理学塑造人格的核心内容。
梅花的特征与人们的审美境界契合处甚多,审美之“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它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这是它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人们对梅格的体认与塑造,在道德情怀与旖旎情思之刚与柔的两极展开,体现着他们的人格追求和审美境界。如王铚的《梅花赋》写道:“韵胜群卉,花称早梅。禀天质之至美,凌岁寒而独开。标致甚高,敛孤芳而独吐;阳和未动,挽春色以先回。原夫尤物之生,英姿特异。方隆冬之届候,属祁寒之鼎至。瞻远岫兮无色,盼丛条兮失翠。彼美仙姿,夐存幽致。春风万里,报南国之佳人;香艳一枝,富东君之妙意。观夫离类绝俗,含新吐奇。妙有江山之兴,萧然风露之姿。气韵雅甚,精神远而。”赋作开宗立意,对梅花充满膜拜之情,指出隆冬时节,万物萧瑟,梅于此时,含新吐奇,气韵雅甚,生气远出,传达着春天的信息,展示着造物主的伟力。因而,梅花标格清高,离类绝俗。赋作铺排其旖旎多姿的美感曰:“其时掩苒半开,娉婷一笑。绚红日以朝映,耿青灯之夜照。何郎秀句不足以咏其妍,徐熙淡墨不足以传其妙。城隅璀璨,遥瞻妍女之殊;月下横斜,乍织鲛人之缭。至若霜岛寒霁,江村晚晴,竹外烟袅,松间雪清。恼远客以魂断,悦幽人之眼明。”梅花在清风中含笑半开,如袅娜娉婷的少女,或在春回大地的辉光里,或在幽窗青灯的氤氲里,尽展其风姿、韵致之美,难以传之笔端,在城隅、月下、江村、竹外、松间,梅花处处,风光处处,远客见之思乡,幽人见之一扫愁绪。赋作反映了作者对这种妩媚婀娜之美心向往之,一往深情,同时又突出其坚持操守的刚硬美的一面:“譬夫豪杰之士,岂流俗所能移;节义之夫,虽阨穷而愈厉。时当摇落之候,气极严凝之际。兹梅也,排风月而迥出,傲霜雪而独丽。色靡竞于阳春,志可期于晚岁。”处阨穷而愈厉、傲霜雪而独丽,这不正是人们所景仰的那种“铁心石肠”吗!王铚有诗咏梅花曰:“急晷驰轮岁将歇,我更荒村转冰辙。凝岩万物冻无姿,水墨陂塘葭苇折。是谁向背此间来,破蕚梅花伴幽绝。遥山谁恨天作愁,澹尽眉峰半明灭。清香自满不因风,玉色素高非斗雪。竹篱凝睇一凄凉,沙水澄鲜两明洁。天仙谪自广寒宫,定与桂娥新作别。尚怜孀独各相望,多情与照黄昏月。从来耐冷月中人,一任北风吹石裂。漫劳粉镜学妆迟,欲写冰肤画工拙。千古无人识岁寒,独有广平心似铁。我因花意拂埃尘,尚恐人传向城阙。诗成火暖夜堂深,地炉细与山僧说。”此诗运思与结构与这篇赋基本相同。诗作在荒寒之景的背景上描写梅花,写梅香、梅影,由月下梅姿展开想象,将梅比作月宫的谪仙人。诗作从凌寒、美丽两个角度来凸显其自洽自适的道德情怀,与其赋作运思相同。幸元龙的《梅花赋》则把梅花描绘为天上的花之神:“瑶台三十有六宫,宫之西北有玉宸焉。玉宸之西有虚白之室,银河环绕,玉绳隐映。庭有水晶,奇花万株。花之神曰雪骨真人,冰绪缟衣丰腴清艳,炫耀心目。”这是将之提升到花神的地位,以突出其标格之高。然后多角度描绘它旖旎动人的美:“微风乍生,婉笑娇舞。踏红绿之茵,立青褐之竿。精采动荡,月姊羞缩。妬逐坠天,流行草木。英灵发挥,钟为腊花,风韵高洁,自成一家。淡月黄昏,的皪疏雅,轻烟浮霁,孤绝潇洒。标格并姑射之皎洁,峻态度罗浮之艳野。”作者描写梅的美韵,始终将其与神仙、仙境联系在一起,以呼应开篇“花之神”的定位,彰显其美丽而不同凡俗的高贵品质。赋作还以一幅幅画面感极强的文字来表现梅花的内涵:“青女飞霜,滕六镂霙,万林惆悴,寒梢独春,夷之清也。倒影孤崖,浮香幽涧,璚骨卧雪,粉面临风,惠之和也。红绽雨肥,乌绞烟蹙,味调金鼎,功剂上堂,尹之任也。”梅之清、和、任就是美丽而不俗,贞刚而济世。
对梅花审美境界的体认是在乡居生活的背景下展开的,因而也深深打上了乡居的烙印。由于读书人群的扩大,南宋文人群体构成发生了变化,在野文人增多,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导力量。他们的生活情趣自然会影响到社会审美好尚,影响到梅格的塑造。由于文人的主体生活于乡间,追求野逸之趣便成了生活风尚的主流。那些生活于城市的文人,也在诗文中憧憬乡居的闲逸,心系农桑之事,那些建筑在城市的园林馆墅,也表现着乡野情调,园田韵致。整个南宋时期的文学书写,田园生活情韵乃是一重要关目。梅花作为南方习见之物,与广大乡居文人的精神世界联系密切,为“贫贱者”所青睐,而与富贵生活颇为疏离。刘学箕就说:“梅贵清瘦,不贵敷腴。雪后园林,水边篱落,似全其真。若处之名园上苑,对之急管繁弦,是四皓之去商山,夷齐之入瑶室矣。”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何澹的《绕花台赋》是少见的描写“名园上苑”之梅的作品,赋曰:“陟彼春台兮,意百卉而回环,乃独取于南枝兮,岂孤洁而难攀。秉太皡之权舆,赋姑射之容颜,视桃李兮牛走,与松筠兮臭兰。泄天机于庾岭,寄驿信于长安,逮香魂之告谢,收鼎味之余酸。盖有始有卒,非若他品异类,徒一时之美观。山泽有癯,帢巾氅衣,恶尘俗之入眼,喜冷淡而生姿。命曰清友,以遨以嬉。共寄情于巵酒,敌照座之十眉。岁晏寒凝,木落草衰,云四垂而一色,瑞六出以交飞。”赋作描写名苑中梅之早发和凌寒的节操,具有富贵不能淫的含义,而点出赏梅者山泽之癯的身份,则仍是在强调梅花与贫贱者精神相通。宋人赏梅重花不重实,就在于梅实与和羹之用关联,暗示着为宦的“富贵”生活,正如欧阳守道所说,(梅花)“亭亭霜雪中,矫矫冰玉姿,高人贞士之所赏爱以此。自古有和羹语,世间佞舌例借此作梅好事。梅可敬顾和羹也哉?开此口者汲汲富贵人也。梅有知,当不肯与闻。”
田园生活虽然被冠以“隐居”之名,但是没有被赋予太深的与“志深轩冕”相对立的意义,而是以常态化生活的面貌进入到文学书写中。刘辰翁在《蹊隐堂记》中指出,隐居不应是刻意为之的行为,他发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义,认为隐居不必是孤山之梅与小山之桂,也不必是竹林之密密与兰畹之幽幽,它应该是一种常态化的生活:“若古有道之士,种花食菜,实未离乎人间,而亦不可荣以禄,殆真隐矣,桃李何负于隐哉!方时艳阳,华如桃李,能不顾省?而穷山枯槁者睨而远焉,彼诚有乐乎彼,而名之所归,政复不能不累乎彼也。人之情性,隐者讵相远哉!……今夫静对轩窗,行唫花下,生意自然,一举目而足,不待游嬉远想,而光阴华悴,感发无穷,则学之所得或在是矣。园林如此,他时子孙仕宦,倦而思归,乃与松菊留情,居然无异,则亦兹花之为助也,何伤于出,而何憾于隐?”在这里,仕与隐的对立被打破了,过去那种离群索居、批判“大伪斯兴”的意义被解构了,它只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生活状态。同时,田园生活的美,联系着人们对太平之世的想象图景,它不仅是悠然而乐的,而且也具有常态生活中的种种况味,融汇着坚守人格操守的种种内涵。也就是说,布衣的生活,要有旖旎的情怀和高旷的胸襟,才有品味,有格调。这种生活情调,正如廖行之在《题舅氏耕隐图》诗中所说:“诗书事业可公卿,垂上青冥却反耕。舍己芸人吾弗尔,种田得饱我何营。一犁春雨宁论力,万里秋云会享成。堂上更书无逸语,也知稼穑重金籯。”躬耕稼穑之所以高于追求功名富贵的劳碌人生,就在于它的闲适自然而内心充实。南宋人理解的乡居生活,具有闲雅自适、自洽圆满、刚贞自守、内心充实的韵味,他们为梅花所赋予的清高而旖旎的含蕴也是这种生活美的映射。耕读传家生活是当时读书人较为普遍的生活状态,他们把生命之根本深扎于土地之上。传统意义的隐居守志,已经不是一种与仕宦和富贵对立的生活信念,而是真实的生活方式,隐居书写中对大道既隐的批判意义因之大为削弱,代之以躬耕励志和对乡居生活情趣的真切体认。乡野园田和茅檐静斋中触目所见的梅花,成为人们寄托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人们对梅格的塑造,也是对乡居中的自我同一性的坚守与塑造。那一幅幅充满乡情野趣的梅花图卷,何尝不是人们在表现自我、塑造自我!
乡居野处,与梅为伴,生命因梅而倍感充实,生活因梅而充满意趣。周紫芝在《双梅阁记》中写与主人徜徉圃中,为阁命名,文曰:“与之徜徉圃间,得双梅对植草间,适得其中,若有为之者。仆笑曰:此造物所以为君之名其阁也。今当培其根而封植之,毋使榛菅之梗其根而蝼蚁之宅其腹也,毋使牧人之践以牛羊而园夫之寻其斧柯也,则此两玉人者当复为君粲然一笑,而姑射之山殆为君圃中物矣。向吾所谓隐处山谷而不求知于人,与夫身在岩谷而名满天下者,昔也闻其风而悦之,今则为之周旋于旦暮之间矣,岂不快哉!它日倚虚檐之旷快,俯木末而高眺,雪霁月出,撷孤芳而荐酒,览清芬而危坐,则君之有得于梅者当自知之。”生活于乡野之间,梅之清高秀雅启迪人之胸襟清旷,人之隐居求志亦在彰显梅之格高调逸,人与梅互相映发,互为风景。许棐《梅屋记》写道:“小庄在秦溪极北,屋庳地狭,水南别筑数椽,为读书所。四檐植梅,因扁‘梅屋’。丁亥震凌,屋仆梅压,移扁故庐。客顾扁而问曰:‘昔吟逋爱梅,未尝一日去梅。尔爱梅,无梅屋,扁梅屋,犹饥人画饼,奚益?请去扁。’予曰:‘向也以梅为梅,今也以心为梅,扁何问焉?扁可以理观,不可以物视。片木,二字而已;理观,四壁天地,万卷春风。庾岭香,孤山玉,岂襟袖外物哉!龂龂以争其无,喋喋以衒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请别具只眼。’”由目中有梅到心中有梅,是人的精神境界与梅花之美的融汇过程,也是一个梅格提升人格的过程,居处虽然屋庳地狭,但是有梅为邻,因而德不孤。李石的《红梅阁赋》生动地描绘了乡居生活与梅为邻的境界:“(梅花)含太素以独秀,破小萼之微丹。友松与篁,真伯仲间。咄严霜其何畏,似古人之岁寒。夜色希微,檐月沉浮。揽衣起步,谁与献酬。耿耿清质,忍令暗投。影横陈以向夕,香彻晓而不收。……美哉,天赞我也,其何不承。有琴我援,有酒我酌。我亦有身,曷云不乐。蹈大方于无闷,味至理于淳朴。望三山之匪遥,欲翔风之寥阔。”静处茅檐,朔风动地,人与小屋,如天地间一虚舟,挺立于风中的梅花正在凌寒绽放,与松树幽篁,凌寒傲霜,同为道友,构成一幅彰显生命活力的图景。月光给这幅图画笼上一层梦幻的色调,这幅图画的剪影映上白屋纸窗。对此美景,援琴酌酒,凌然有高世之志。这其实是极普通的乡居图景,然而有梅为邻,顿时趣味盎然。
当时的人们往往借梅花来抒发乡居心境和审美境界。张侃在《借轩赋》中写道:“入则绳枢,出则扶藜。竹有晚节,梅有清姿。水能容量,山能呈仪。自得膜外之乐,不染世间之丝。”穷居陋巷,有竹梅为伴,山光水色,触目所见,皆成风景,梅花将人带入精神自足的美境。林学蒙的《梅花赋》表现了以梅为友的乡居生活:“余之为人也,山林习惯,世味心灰。即蜗居之东偏,种半亩之疏梅,相与盘桓,日不知几回。岁寒亲友,问心开怀。时夜将半,疏影横斜,牵牛饮河,忽相顾而兴悲,念岁月之几何。”人的生命感受已经与梅融为一体,故而因梅而兴叹,托梅以寄意。梅花成了他们感受人生、启迪情思的重要媒介,抒发人生感受的重要载体。王迈在《盘隐记》中写道:“水如镜,石如玉,花卉异品,呈巧献状,怪松如蟠虬,修竹如琅玕。酴醾堆架,芙蓉出水,深红浅白如妃嫱之妆。绕砌芳兰万本,异香袭人,如佳子弟。雪天梅花盛开,清标雅韵,又如群仙绰约,联缟裳而朝蕊宫也。”生活于乡间,四时卉木应接不暇,四时风景纷至沓来,而梅花的点染,又使乡居恍若处身仙境,让人获得精神的愉悦与人格上的升华。姚勉在《月崖前集序》中写乡居夜读,以梅为伴的悠然之境、陶然之情:“余性好山水,城郭不能有之,乃迭石作假山,下凿小池,横木为桥,环山为墙,外植梅竹,清事略具。既望,夜漏下三皷,月已高,窗纸昼明。予方拥衾危坐,霜风微起,竹的淅有声,栖禽竞飞其间。亟披衣出檐玩明月,倚栏良久,步立桥上。天高月小,寒影在地,水澈浄如镜,鱼畏寒不复出,独梅影在水间。仰视梅已三两有花,清思逼人,无与领此者。忽记友人潘清可日尝以集寄予,未暇读,亟取读之,真若嚼冰咽雪,不知孰为山水,孰为梅竹,孰为霜月,且孰为诗也。”月明之夜,梅影映窗,暗香浮动。或于窗下读书,听风动竹声,或于小园徘徊,观寒梅着花。若于此时有清雅之文章为伴,则人与梅与文,互相感发,呈现陶然于天地间的美境。人们敏锐地感觉到,乡居野处,因梅花的介入而焕发出盎然情趣;耕读度日,因梅格的映照而意味充盈。生活因为有了梅花,才成为风景。
在乡居生活中,梅花体现着人们的审美境界,是人们寄托性理,表现人生感悟、生命感受的知音。包恢在《远斋记》就说:“斋外梅竹相与照映,盖致远心地洒然,而境地之胜亦如之。况深于琴,精于诗,鼓于斯,赋于斯,则山鸣泉响,梅动竹应,若皆知音者。”梅已经由风景的一部分变而为生命的一部分,梅动竹应,人心随之起舞,若知音之相感,精魂之相通。何梦桂在《邵梅间诗序》写道:“清溪有诗人,癯然一髯翁,江空岁暮,顾影无俦,独于梅花树下,抱膝浪吟,酾酒酹花,若将与雪月分席者,因自号曰梅间。夫风尘涴人,满目皆是,踉空足音,跫然以喜。梅虽无言,余必知无拒子也。”梅虽无言,道尽诗人心中之郁垒。黄大舆说自己辑《梅苑》的目的是为了寄托乡居生活的感受:“若夫呈妍月夕,夺霜雪之鲜,吐嗅风晨,聚椒兰之酷,情涯殆绝,鉴赏斯在,莫不抽毫遣滞,劈彩舒聚,召楚云以兴歌,命燕玉以按节。然则妆台之篇、宾筵之章,可得而述焉。”徜徉在月下雪中的梅树下,沉浸在暗香的氤氲中,兴发感动,情不能已,抽毫遣滞,劈彩舒聚,以写眼前之景,抒心中之情,或者录前人咏梅之作,以导泄己之感触。
梅花象喻在孤静、幽雅、清冷的审美情境中融入了“清”、“贞”等的精神内涵,具有融通贞刚拗劲与旖旎多姿的特点,梅花审美之境界的探索,兼具君子风范和平民化品格,为穷居野处者引为寄托。梅花素淡、冷峻、清冽、幽妙,梅枝疏淡、清瘦、虬曲、老健,梅影横斜、交疏、飘逸、幽峭,以之点染图画,境界顿出,形成清雅逸致、娴静淡雅、清疏遒劲的风神意趣。这与人们对自足自洽而清倩灵动的美的追求深相契合,集中体现了人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受,并进而成为“南方”生活样态和生活情趣的象征符号,成为士人普遍追求的人生境界,成为士人君子襟怀与人格美的写照。
综上所述,梅花能够成为一种意义承载丰富的花卉,与它自身的形态特征密切相关,这为它进入审美生活的各个层面提供了可能。南宋时期,士绅阶层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承载者,梅花象喻,表现着他们的审美理想、人格诉求与人格境界。士绅阶层本身,有着浓厚的“在野”的特点,这一阶层的审美理想和道德理想有着广泛的基础,具有“大众”的特征。因之,以士绅为主体塑造的梅花象喻不同于那种贵族气息浓郁的牡丹象喻,而更具平民色彩,更具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品质。
随着宋元以来对梅花的不断塑造,梅花逐渐深入到华夏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华夏的象征。中华文明与其他具有生命力的文明一样,趋向于在更高层次上认识人、认识人的价值,趋向于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与解放。随着文明的进步与文化交流融合的加深,梅花之美一定会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知。如今,任何中国人,不论在国内、在国外,都以爱梅为荣。梅花蕴藏着中国人的特性本质,散发着中国人的道统,凝聚着人类的人性文化,相信梅花在以后的岁月里,依然会承担起凝聚民族人心、维护民族统一、增强民族自信的伟大使命。
注释
①②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第259页。
③《四库全书总目·〈梅花字字香〉提要》,见永瑢等著:《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38页。
④宋伯仁:《梅花喜神谱序》,见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第34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3-44页。本文中《全宋文》皆来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⑤杜耒:《寒夜》,见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637页。
⑦《庄子·田子方》曰:“子路曰:‘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郭庆藩集释,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708页。)
⑧皇甫谧《高士传》云:“东郭顺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则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择何足以称之。”(皇甫谧撰:《高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
⑨张嵲:《梅花赋》,见《全宋文》186册,第286页。
⑩杨公远:《次程斗山韵》,见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7册,第42063-420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