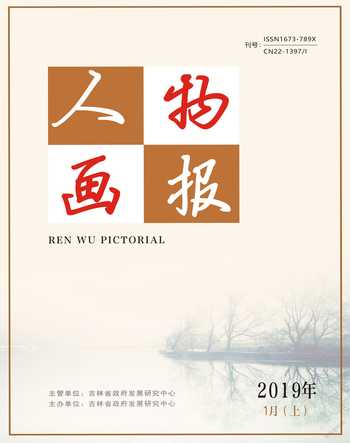博物馆参与式展览的观众体验研究
2020-01-07张冰
摘 要:博物馆作为一个公众社会组织,其许多活动都必须在观众参与体验下进行,可以感受到在展览和活动的设计过程中,观众自身的参与和表达成为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从观众体验角度切入,分析博物馆参与体验角度的转变,以探究博物馆的展览设计与观众体验之间的主动与被动关系,提高观众参与热情,发挥博物馆公共教育功能,以思考博物馆体验更多的可能性。
关键词:展览设计;公众参与;娱乐化
一、博物馆展览发展中的观众参与度变化
目前博物馆参观方式来看,各个博物馆比较常见的是“一对多”传统静态参观形式。展览参观观众的年龄层比较集中,大部分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专业人员和院校学生,普通民众人数比例相对较小,这种现象在二三线城市尤为明显。随着技术的发展,互动类型的展览应运而生。就现场情况来看,展览的观众群变得相对宽了一些,展览现场不仅有家庭群体,同时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以及年轻学者。
21世纪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剧院等文化机构不再是以往庄重肃穆的神殿,博物馆从单一同构型的“大众”转变成“社区”的公共大众平台,博物馆会更注重观众互动体验的多元化。
近年来我们见证了博物馆为了吸引观众,越来越多的使用可以互动的展览项目。互动类型展览的盛行标志着展览体验由审美转向体验,由静观转向互动,对于这一展览趋势,博物馆学家彼得·冯·门施曾说:第三次博物馆革命发生在2000年,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虽然我们还没对它正式命名,但其关键词就是“参与”[1]。参与式展览围绕主题运用各种多媒体技术手段设计情境,借助游戏、情景模拟的手段,鼓励观众动手动脑参与展览,将观众从被动的观看过程转变成一个欣赏、发现与思考的双向传播体验学习过程。在参观的过程中加入触觉的有形参与,这让观众体验互动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表达和传输,同时聚焦于身体交互、以及创造力的设计互动,并在实践中具体化为行动。
二、博物馆展览设计中观众体验的主动与被动
博物馆作为教育学习的第二课堂,具有自由选择的、非正式情境的双重教育特质,如何满足观众的需求,如何把这种博物馆教育特质发挥到最大?博物馆展览设计如何满足观众学习、探求实践、欣赏的需求,是博物馆设计目前最关心的话题。本章节分析的是在展览设计上如何调动观众参与主动性,以期达到博物馆参与体验的最佳效果。
(一)观众被动观看
传统展览形式围绕展品内容的进行静态展示,展览设计类似于学校课程理念,以流线式方式展开。观众的参观方式也是跟随讲解员解说被动的参与。但是就现场情况来看,参观者并不一定规矩的按照策展人设计的路线解读展品,这种行为被特芮南称为“主动的闲散”和“文化逛街”。传统的展览的观看时间和学习效果取决于观众本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同时也取决于观众自我学习的兴趣。观众在展览扮演被动接受者的角色,观众与展品之间的互动存在于观众自主选择,也就是说观众与博物馆的关系是分离的。
近年兴起的沉浸式展览打破传统展览平面、沉静的体验感,将新媒体技术应用到展览当中,强烈的声光电的视觉冲击,观众会产生时间和空间上的游离感,产生强烈的视觉效应。例如2019年7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灵的畅想—梵高艺术沉浸式体验”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展览,现场将梵高的艺术作品投影到墙壁上循环播放,同时与画作一起播放的还有或悠扬或悲戚的音乐,大面积的动态画面调动多感官沉浸式体验感和观众参与积极性。沉浸式展览表面看来是由大众传媒带来的图像动态化、流动性,实质上观众被刻意的视觉技术控制,并且在图像刺激的重压之下容易产生逃避图像的冲动。观看者被观看对象控制,图像通过对观看者欲望的捕捉控制了主体,使其在不知不觉间服从了图像所传达的意志,在我看来,沉浸式展览的观众参与度仍然有待考究。
上述二种情况,传统流线式展览以及沉浸式展览的展览方式其实质都是被动的,背后缺失社会脉络和环境脉络的考量[2],缺乏个人、社会、环境的综合考虑。单向的展览设计致使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几乎为零,观众实际参与度不高。
(二)展览设计的观众主动参与
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核心问题是如何做到更具開放性和参与精神。美国博物馆协会在1992年的《卓越与平等》报告中就指出:博物馆是观众与观众、观众与实物进行交流的场所,并通过相互影响来增进体验[3]。
1、物与人:参与地点的重新审视
博物馆参与式体验设计的优势在于采用多种手段调动观众的积极性,建立信息双向流通渠道,当传播者将展示信息公开后,观众可以对展示信息做出反应,并在现场将信息反馈给原传播者,这样就有了双向互动特性的信息传播方式,缩短了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观众拥有了“现场表达”的权利。
在肯塔基的国家童子军博物馆其中一个影院,观众可以扮演侦探的角色寻找一名失踪儿童,剧情将依照观众的选择来发展,大家投票的结果就是下面将要播放的内容。童子军博物馆这种播放影片的设计模式,故事情节由观众意愿推动,充分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以这样一个方式观众真正参与到展品的展示和传播当中来,取代了仅仅是专家才有阐释博物馆作品的特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博物馆民主化的体现。观众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发现展览与知识之间的关联,在博物馆交互中创造新的内容。博物馆与观众这种传统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越来越模糊,观众体验从我变成了“我们”。博物馆体验从单向的、被动的体验转向多元的、双向的参与式体验。
2、人与人:观众与观众之间的社交双向传播
博物馆为观众提供了创作、分享并于他人交流的场所[4],互动体验不仅存在观众与展品的互动,也存在于观众与观众之间的社交[5],而参与式展览就为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实用性的空间[6]。
雷安德罗·埃利希在中央美术学院重新制作并呈现的“太虚之境”是一个典型的参与式展览。展览利用装置、现成品、雕塑、视频,甚至音乐等媒介和视听觉形式,成功制造了众多挑战我们感知惯性的文化景观。“太虚之境”《游泳池》作品是一个悬浮在空中的装置,仿佛人在另一个时空里漫游,如果没有其他观众的参与,岸上的观众无法完整的感受水池底下的波动。可以说,参与式展览实现了由我到我们的社交式体验,观众变成是展览的创作者、传播者、消费者。
“太虚之境”的另一个作品《建筑》也把观众的参与度充分调动起来。其灵感来自于唐人街的经典招牌和防火外墙,通过唐人街反射国人的生活,采用镜子为投射载体,反射出一个立体的中国城镜像。在活动体验过程中,观众在地面的门窗之间坐躺等活动动作,镜子会反射出来,这时观众自己的身体又和图像之间形成新的关系。观众在参与过程中,不仅能够看到自己,也与其他参观者共同组场景,当参与人数不断增多时,才能体现展览的最佳效果。此时地面上的砖砖瓦瓦已经不重要了,是观众自己的创造给他们带来愉悦感,也是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带来的社交体验,因而艺术家的设计就成了观众进行创造的平台,为观众自己的表达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太虚之境”打破传统展览观众被动旁观者的状态,观众成为展览的参与者、贡献者。展品不是放在橱窗中的圣物,观众可以触摸展品,也可以进行互动,观众变成展览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参与式展览促使观众与展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博物馆与观众的关系认为:博物馆是传播者,观众是接受者;参与式展览观众的关系认为:观众是生产者和创造者。传统博物馆的观看方式依赖文本的阐释,这使得阐释本身受展览内容的限制。而参与式展览为观众提供多维度的感知,而非单纯阅读,互动体验作为博物馆观看的补充。可以说参与式展览为观众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以及客观解释的机会。
三、参与式展览中艺术体验与娱乐化的考量
娱乐功能是博物馆既定存在的功能,娱乐化与艺术体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学自博物馆》中,作者约翰·赫·福克和林恩·迪·戴尔金就提到,没有明显证据表明观众去博物馆的目的是要么学习、要么娱乐;几乎毫无例外的是,观众都是兼顾学习和娱乐的。去博物馆的个体是寻求一种学习导向的娱乐体验[7]。博物馆参与式体验的愿景是不仅能让观众仅获得体验与快乐,更重要的是让观众在娱乐中获得深层次的思考和感悟,并在这种愉悦中加深这种体验,激发进一步的学习。
参与式展览借助游戏、情景模拟的手段,在公共领域展开的一种叙事性体验,大大提高了展览的参与性、趣味性,寓教于乐,达到交流和操作的作用。在这里需要反思的是:参与式展览的娱乐方式是否恰当,或者说过度的娱乐化是否造成展览的孤立和知识的获取困难。参与体验怎样能避免过分娱乐而不丢失博物馆本质特征,又能达到与其他游乐场等娱乐场截然不同的要求,尽力做到在娱乐中学习,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这个问题是博物馆人员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未来博物馆发展的趋势,是博物馆人一直追求的目标。另外,博物馆也应该扩大观众的参与空间范畴,不仅局限于参观过程,在参观前展览设计和参观后展览效能评量中也加入观众参与,共同营造公众满意的博物馆。
参考文献:
[1](美)妮娜·西蒙.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G].喻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
[2]福尔克和戴尔金在《博物馆体验》中提出“互动体验模式”,认为博物馆体验是个人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3]美国博物馆协会主编.博物馆教育与学习[G].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4.
[4](美)妮娜·西蒙.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G].喻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4.
[5]葛伯恩(NelsonGraburn)認为人们期待博物馆要充满三个重叠的经验之需求其中之一就是社交(一种社会经验的分享).
[6]70年代,地理学家SheldonAnnis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观众反应的三个共存的层次之一就是:实用性的空间(社交互动的场域).
[7]常丹婧.“博物馆娱乐”的特性及误区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博物馆》2019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
张冰(1996.1.14)女,汉族,山东省,单位:山东艺术学院,学位:硕士,职位:学生,研究方向:美术教育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