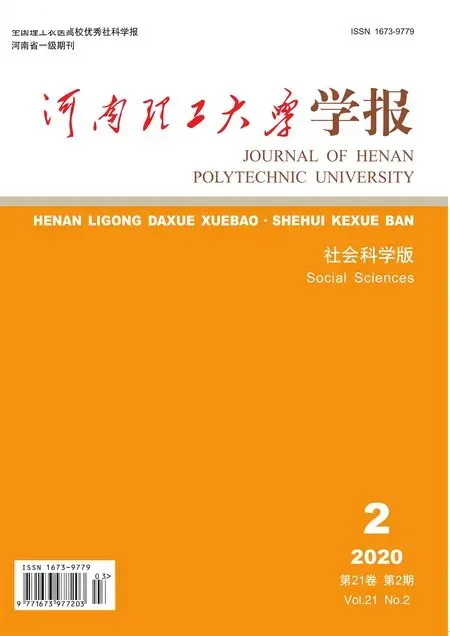唐代进士科“试读”考论
2020-01-07彭健
彭 健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自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问世以来,众多学者仿其写作格局,撰写类似选题,逐渐掀起“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浪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唐代“科举与文学”作为“制度与文学”范畴下的一部分,尽管前人对之论述颇为详备,但囿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尚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和空间。如对《通典》所载之“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1]354之“试读”试项,历来争议不断。清人徐松,今人傅璇琮、陈飞、徐晓峰等学者已对其作出见解。审视以上学者之研究思路,皆以唐代科举文献为主体,忽略了事物的出现必然有一个漫长的酝酿、发展过程,唐代科举制度亦是对前代人才选拔制度继承和发展之结果。因此,本文力图立足于相关唐代科举文献,将唐代科举考试制度放入人才选拔制度的历史长河中,尽可能地结合古人治经读史之方法,对贞观八年进士“试读”试项作出解读,以进一步探究唐代科举与文学。
一、有关进士“试读”试项的讨论
从现存可见的文献资料来看,有关唐初科举考试的记载不多,这便给此一阶段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载:“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2]1因此,一般将武德四年(621)视作唐代科举考试的开始。但据考证得出,武德四年(621)四月朝廷虽颁布诏令举行科举考试,但仅举行了“士族所趣向”的明经科考试,而“武德五年 (622)当是唐代科举考试进士试的较早时间。”[3]唐初明经、进士二科皆试策,明经试墨策;进士试时务策。太宗贞观八年(634),即是举行科举进士试的第十二年,朝廷于“止试策”之基本考试制度之上诏令进士加试“试读”经史一部,相关文献记载如下:《通典》卷十五载“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1]354;同书卷十七作“大唐贞观八年三月,诏进士读一部经史”[1]402;《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作“贞观八年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 ”[4]1379;《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九《贡举部》亦云:“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5]7388由此不难发现,上述所列之文献资料皆指向贞观八年(634)诏加进士“试读”经史这一事实。然而,文献对于“试读”之方式,及第之标准只字未提,这便给后世之学者带来理解上的困惑。那么,贞观八年(634)诏令进士加试之“试读”试项到底是如何试制呢?清人徐松认为:“进士初惟试时务策五道,至是加读经史,仍试以策,非帖经也。”[6]17徐松认为此年加试之“试读”经史仍以“策”的考察方式进行,更非帖经。其推测大概是根据文献所载唐初明经、进士二科“止试策”,且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廷颁布《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规定:“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7]344-355确有进士试史策之例。而帖经试项则是永隆二年(681)科举考试改革以后施行的考试项目,故试帖可能性不大。且此阶段除却“试读”经史这一诏令,别无任何有关“试读”的记载,亦无其他形式的考试办法,故猜测“试读”经史仍以“策”的形式进行。傅璇琮亦从其说,认为“贞观八年(634)所谓‘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只因为原来所考的策文是时务策,现在再加上从经书和史书各一部中出题目,考问经史大义,这仍是试策”[8]165-166。陈飞认为:“徐松这个断语是不正确的 , 他或许未能理会杜氏所言 “加试” 既有转折之意, 则加试后就不应仍 ‘止试策’”[9]36-45。陈先生反对“试读”经史为试“策”经史之说,认为“试读”经史“应该是一个试项”,“‘试读经史’很可能是‘帖读’,属试帖之一种,而不应属于试策”[10]122。类似于明法、明算科目中“帖读”或“读帖”试项,“其考试方式是在指定的文章中空出若干帖(一般为三字一帖),令考生在考试时连同上下文一并“读”出来,而不是像通常帖经那样用笔“写”出来,前者可谓‘口试帖经’,后者则为‘笔试帖经’”[10]122。徐晓峰一反陈飞“试读”经史为“帖读”或“读帖”经史之说,认为此年的“‘试读’或等同于‘习读’,如果再考虑到经史的试法,那么试策的可能性是最大的”[11]16-18同时认为“贞观八年进士科‘试读’经史的意义或许可如是表述:‘借鉴明经科加试经策、继承传统试制的同时,又创立了进士科试史策的新试制。’”[11]16-18徐先生仍从徐松、傅璇琮之论,认同“试读”经史即是“试策”经史。对于以上诸家推论,笔者于《唐初试策变迁略考》一文中也曾有过质疑:其一,“若是进士加试经史策,何不直接诏加进士‘试策’经史一部,何以要诏令曰‘试读’,实行的却又是‘试策’经史”[3]?其二,陈飞先生以为“‘试读经史’即是‘读帖’或‘口试帖经’,乃依据明法、明算科目中‘帖读’试项来推测,实为不妥”[3]。笔者依据《唐六典·尚书吏部》所载弘文、崇文两馆之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训练以及学业考试中确有试“读”经史项目,“弘、崇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亦不拘常例(原注: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者,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其试时务策者,须识文体,不失问目意,试五得三。皆兼帖《孝经》《论语》共十条。)”[12]45-46故推测认为“贞观八年(634)进士试读经史一部乃考考生的诵读能力,而非‘试策’或‘帖读’。”[3]
笔者之所以不惮其烦地梳理诸家对贞观八年(634)进士“试读”经史的推论,不仅仅是阐明并重申笔者之推论,认为此年之“试读”经史确是一个考试项目,“试读”经史既非进士试“策”,亦非“帖读”或“读帖”,而是考察举子对经史的诵读能力以及熟悉程度。除此之外,尚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上述之讨论皆局限于唐代科举制度而探讨考试项目,忽略了唐代科举考试制度与唐前的人才选拔制度之渊源关系。因此,在考述唐代考试制度时应遵循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将视角深入到唐前的人才选拔制度中,从渊源上考察“试读” 试项。 其二,既然是“试读”经史,那么唐及唐前之治经读史之方法或许不应当被忽略,可作为解读唐初进士“试读”经史之参考。其三,正如上文陈飞先生所说,“试读”经史可能是“帖读”或“读帖”经史,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就需要以唐代考试制度为基础,对“试读”与“帖读”两种考试项目作比较,以揭示“试读”考试“读”的本质。
二、“试读”渊源考论
在解读进士“试读”试项之前,须摆脱今日读书观念之禁锢,回到古人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生活中去。之所以如此强调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盖因古人著述,多不加标点。学子拜读大作,首先须得断句分章,其次方可诵读文章。相较今日之学子来说,其诵读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笔者以为,大唐贞观八年(634)之进士“试读”经史试项的设置,目的是为了考查进士举子以“离经”断句为基础的诵读能力。“离经”断句长期以来被视作治经读史的入门技能,其后逐渐被引入到人才选拔制度中,历经变化最终形成唐代进士科“试读”考试项目。故笔者拟追溯以“离经”断句为基础的诵读之源流,并梳理诵读逐渐被引入人才选拔试项之过程,以揭示“试读”既非“试策”,也非“帖读”,而是作为独立考试项目之合理性。
(一)“试读”与句读关系考
古人读经,首重“离经”断句,也被称为句读。西汉戴圣《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3]957-960由此可知,习经欲达“知类通达”之大成境界,须得至少九年孜孜不倦地学习,而其初始阶段,即一年所考之“离经辨志”。那么,何为“离经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乡也。”[13]959孔颖达疏:“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辨志,谓辨其志意趣乡,习学何经矣。”[14]1053郑孔二人将“离经”解释为断章绝句,类似于今天的分章断句;而“辨志”,则是“离经”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即对圣贤志向的体察。郑孔等人将“离经”视为研习儒家经典的入门技能,是有深层原因的。古人所习之经书典籍与今日所见之书籍大有不同,现今所见的书籍,多经后人整理点校,编辑而成,而古人所作文章,一般是没有标点的。这便给古人阅读带来极大的困难,故古人读书多跟随名家大儒学习,其最基础最首要的便是“离经”断句。因此,“离经”断句也就是句读成为古人诵读古籍、辨伪存疑、义理阐发等治学的基础,故古人多重视对“离经”断句的培养。如高诱《淮南子注》载其从小就师从卢植,学习句读,“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15]5。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篇记载了大儒马融从班昭学习《汉书》句读之始末,“大儒马融从受《汉书》句读”[16]493。韩愈《师说》亦云:“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17]42-43一方面强调授其句读并不是作者心目中真正的传道解惑;另一方面也重视句读的学习,认为句读是解惑之基础,“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又如宋代朱熹,吕祖谦所撰《近思录》载明道先生行状云:“诸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18]27亦将句读视为孩童初读书时的重要学习内容,不仅学校注重培养,明道先生还亲自指导儿童句读。不仅如此,宋代科举考试便曾有考试句读之例,如秘书郎何澹言:“有司出题,强裂句读,专务断章,破碎经文。宜令革去旧习,使士子明纲领而识体要,考注疏而辨异同。”[19]3636再如明代黄佐《泰泉乡礼》卷三《乡校》载:“平旦施早学之教,诵书,正句读……以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然后治经。句读少差,必一一正之。”[20]616-617吕坤《呻吟语摘》卷一《礼集·谈道》:“艰深幽僻,吊诡探奇,不自句读不能通其文,通则无分毫会心之理趣;不考音韵不能识其字,识则皆常行日用之形声,是谓鬼言。”[21]44《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时,案《礼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注曰:‘离经,断句绝也。’则句读为讲经之先务。”[22]162皆强调“离经”断句作为基础技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自先秦至明清,句读不仅被视为古书学习以及初学者教育的第一要务,同时也是学子考核的重要内容。
这就不得不跟贞观八年(634),诏令进士加试“试读”经史一部产生联系。正如上文所述,唐及唐前的书籍是没有标点的,学子在阅读之前必须先研习“离经”断句,训练句读能力。故此年之加试“试读”经史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考察考生的句读能力。特别是贞观八年(634)正处于唐代科举考试的初创期,考试方式多参照前代而设,故“其初止试策”,明经试墨策,其考试范围主要是以儒家经典及注疏为主,出题方式以“录经文及注意为问”[12]45,要求“其答者须辨明义理,然后为通”[12]45。明经考生出于及第的目的,自然会熟读儒家经典文本以及注疏。而进士科只试时务策,考察的是考生应对时政事务的对策,不需要试策经史,故进士举的考生不会像明经举子一样去研读儒家经典,也不需要或者说没有能力像明经试的举子一样去研习儒家经典。换句话说,进士举子对儒家经典书籍以及史学文本尚处于初学阶段,根据传统的习经惯例,初级阶段重视的是学生“离经”断句的能力。故此年之“试读”经史绝不可能是难度较高的“试策”经史,若是进士“试读”经史以更难的考试方式进行,其考试方式必被清楚明了地诏令出来,如“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至二年正月十四日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4]1373。天后虽上奏文武百官习读老子《道德经》,但却以“试策”的方式进行考核,故注明“所司临时策试”,“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同时,“试读”经史亦不可能是“帖读”经史,至于原因,此处暂且不表,下文将详细论述。但从治经读史之传统来看,贞观八年(634)进士加试“试读”经史,很可能是以“离经”断句为基础的诵读。
(二)“试读”与人才选拔的关系考
除却上文所述“句读”与“试读”之关系外,也应当重视唐代科举制度与前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关系,从源流上追述并考察唐代“试读”考试制度。据王定保《唐摭言·试杂文》云:“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 所试皆答策而已。”[2]6王定保注意到唐代科举制度与汉代人才选拔制度的渊源关系。然而,汉代以察举制为主要代表的人才选拔制度亦得益于先秦的各种人才考察制度。因此,追溯人才选拔制度之源流及背景,或可从中攫取微弱信息,以助于解读贞观八年,进士“试读”经史试项。
“试读”的萌芽状态,或可追溯到有记载的先秦诵诗活动。先秦时期,便曾有瞽蒙诵读诗文以补察时政、规劝君王之举。《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23]852-853工者,瞽蒙也。瞽蒙者,“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24]1864等之乐官。郑玄注此条时曾引杜子春语云:“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故《国语》曰:“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24]1865班固《汉书·贾谊传》也曾记载:“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25]2249由此可见,此时诵读诗文已成为下取民意,上谏天子的重要方式。但尚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一时期之诵读可能更重视节奏以及音乐伴奏,瞽蒙等作为乐官,必将采集或编撰之诗文配以乐曲,以达到诵读之最佳效果。二是诵读主要是以脱离简牍等载体的方式进行,其诵“读”的意义较弱,实际上更倾向于背诵。总的来说,此一阶段之诵读更倾向于配乐之下的节奏把控和背诵,其相对于本文论述之“试读”经史来说,“读”的意义较弱。同时,诵诗还具有帮助处理时政事务之功用,故孔夫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6]152可见诵诗已成为先秦民众生活的重要部分,故当时之学子教育皆重视对诵读的培养,如《礼记·内则》言幼年即学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13]440言及学子十三岁时便学乐诵诗。荀子亦认为“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16]89。认为学子学习应始于诵经而终于习礼,皆强调诵读之重要性。因此便有“迁生龙门……年十岁则诵古文”[27]383。尽管这一教学方式曾遭受后人质疑:“夫古者教学,自数与方名,诵诗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问人之资近与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谓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岂古今人有异教与?”[16]153但诵读作为一种重要的培养方式,于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兴,诵读便成为重要的选拔方式之一,如《汉书·艺文志》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25]1721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文字》亦载:“古者,十年入小学,学书计,十七能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28]6所谓讽书,“犹今言背诵默写也”[29]93。可见诵书是当时的考核办法之一,能诵书九千字者,即可为吏。不难发现,汉代之讽书考核方式,是对先秦诵诗诵文活动的继承和发展。不同的是,先秦时期诵读之主持者由乐官出身的瞽蒙等担任,诵读时可能需要伴以乐曲,而汉时则由太史全权考核,无需音乐相佐,其形式更趋向于背诵。又《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周防,字伟公,汝南汝阳人也……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30]2559-2560周防因能诵读经史,遂拜为守丞。毫无疑问,诵读已成为人才选拔的诸多方式之一。然而,随着政权不断地更迭,人才选拔制度虽也经历察举制至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的演变,但其考核方式却具有内在的渊源性以及关联性,诵读之考试办法也日益新变。据《隋书·经籍一》载:“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31]933尽管今之所见文献记载较少,无从知晓“试读”的通过标准以及具体实施办法,但从“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一句来看,晋时之国学考核亦秉承前代诵读诗文的传统,虽命名为“试读”,实乃诵读考核之延续,与前代之诵诗读文一脉相承。“试读”作为考试项目名称正式登入考试舞台,并为后世特别是唐代科举考试所蹈袭,遂有大唐“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1]354。值得注意的是,贞观八年(634)进士所课之“试读”试项略有区别于传统的诵读方式,此处之“试读”更倾向于参照书本诵读,“读”的意义得到充分显现。毫无疑问,大唐贞观八年(634)进士“试读”经史一部乃是对传统诵读诗文的继承和发展,“试读”演变为独立的考试项目具有历史传承性,故徐松、傅璇琮等学者将其视为“试策”经史,实有待商榷。
除却贞观八年(634)进士加试“试读”经史一部以外,其后的唐代科举考试中也不乏“试读”经史之例。如上文所引之《唐六典·尚书吏部》载:“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者,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12]45-46强调弘、崇两馆之学生对《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史书须“读文精熟”,且达到“言音典正”之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关系极为密切,科举考试所考的内容,即是官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换言之,弘、崇两馆所试之“读文精熟,言音典正”,即是科举考试“试读”史籍之要求。又《旧唐书·归崇敬传》载,建中元年(780),国子司业归崇敬于科举考试改革奏文中云:“《论语》《孝经》各问十得八,兼读所问文注义疏,必令通熟者为一通。”[32]4018-4019仍“试读”《论语》《孝经》所问文注,且须达到“通熟者为一通”之及第标准。再如《唐会要》载,长庆二年(822)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敕旨:‘宜依,仍付所司。’”[4]1398殷侑的奏文充分肯定了史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的地位,并奏请国子监生徒习读,从奏文内容来看,殷侑的奏文是对前文所述弘、崇两馆生徒读史课史之延续和发展,不同的是学习对象乃国子监生徒。奏文中虽未说明考核方法,但可推测其考核方式仍类似于弘、崇两馆之“读文精熟,言音典正”以及试策的考核办法。由此可知,“试读”仍是学习经史及考核经史的重要办法之一。
总之,贞观八年(634)进士加试“试读”经史,其渊源可追述到先秦之诵诗读文活动,其后“诵读”成为研习各种经史典籍的重要方法,并逐渐被引入到人才考核和人才选拔制度中,成为唐代科举考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贞观八年进士“试读”经史,并非“试策”经史,亦非“帖读”或“读帖”经史。
三、进士“试读”非“帖读”
笔者以为,欲较为深入了解贞观八年(634)诏加进士“试读”经史试项,必对陈飞先生所认为之“试读”即是“帖读”或“读帖”之论进行解读。陈先生有如此论断,乃根据明法、明算科目中“帖读”或“读帖”试项推论得出,“其考试方式是在指定的文章中空出若干贴(一般为三字一贴),令考生在考试时连同上下文一并“读”出来,而不是像通常帖经那样用笔“写”出来,前者可谓‘口试帖经’,后者则为‘笔试帖经’”[9]122。这里有必要对“帖经”作简要了解,据《通典》载:“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1]256简言之,“帖经即是将经书左右两边遮住,只开中间一行,再用纸遮盖三字,考生根据前后经文补充句子,将所缺的三个字写出来即可。一般每条帖三字”[33]。可以见出,正如陈先生所言,“帖读”与“帖经”之区别主要是以笔试答帖或口试读帖。然而,陈先生所依据之明法科与明算科是如何试制呢?据《新唐书·选举志》载:“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 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34]1161又“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辑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辑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34]1161。根据“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帖读十得九”条,可知明法、明算科目确试以“帖读”。那么,明算、明法科目“帖读”始于何时?其“帖读”与“帖经”有着怎样的关系?检阅现今可见的文献资料,发现与明经、进士、俊士等列为常科的明法、明算科目试制记载较少,但仍可从永隆二年(681)朝廷颁布的《条流明经进士诏》诏令中窥斑见豹。诏令规定:“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乃严加捉搦,必材艺灼然。合生高第者,并即依令。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常式。”[7]549诏令言及明法、明算试制“亦量准此例”,却未言明准明经例还是准进士例。但从其后明法、明算的“帖读”试项来看,明法、明算的考试方法正是参照了明经科而设,这也说明了“帖读”试项是“量准”明经“帖经”试项的产物。而明经“帖经”亦是此年颁布诏令以后方付诸于考试中,此前明经科“止试策”,即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墨策,并无试贴之先例。若遵照陈飞先生之言,进士“试读”经史即“帖读”经史发生于贞观八年(634),其试贴之时间提前了整整47年。但进士“帖经”亦是参照明施行,这里可参照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廷颁布的《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诏云:“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7]344-355这是进士试贴之最早诏令,而诏令中进士帖小经亦是发生于永隆二年(681)至开元二十五年(737)之间。因此,断无明经考试尚无“帖经”试项而进士诏令加试“试读”经史却试以“帖读”。进一步推之,若仔细解读“帖读”,“帖读”包括了两种考试方式,一是诵读;二是“帖经”。那么,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贞观八年(634)进士“试读”经史一部,永隆二年(681)之后明经试以“帖经”,而明法、明算等科目参照二科取士制度,试以“帖读”。因此,以明法、明算科目“帖读”来推测贞观八年(634)进士“试读”经史乃“帖读”经史,实有欠妥当。
除此之外,尚有几点可佐证贞观八年(634)“试读”经史并非“帖读”经史。其一是研习经典并非易事,考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相关经史知识。正如《唐六典》云:“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12]45唐代纳入科举考试范围之儒家经典包括正经九部,《孝经》《论语》兼经两部,共计十一部经典。此外,尚有《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经典。如此多的经史典籍想要熟读精深,就算是对以经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明经举子来说也大为不易。韩愈《送牛堪序》便言及明经诵经之艰难:“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17]246更别说以试时务策为主体的进士举子,于加试性考试中试以难度更高的“帖读”,将所缺之文字读出来,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作为加试性的经史试项,自然不会以太过困难的测试方式进行,进而影响和偏离进士试“止试策”的正常考核目的,从而影响进士试的人才选拔。故此年是不大可能或者说没有必要“帖读”经史的,相反,较为容易的以“离经”断句为基础的诵读恰是督促和考察考生阅读经史的最佳方式。
其外,唐代对举子习经尚有年限规定,《新唐书·选举志》云:“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34]1161这里不妨如此假设,举子同时研习以上经典,最快也需一至三年;若是逐一研习,则需要将近十五年,这尚未包含研习史籍之年岁。对于进士科来说,贞观八年(634)以前“止试策”,并未涉足专门性的经史考试。那么,朝廷欲实行新的考试内容,必然有过渡或者准备的时间。然而贞观八年(634)之进士试经史实行得较为突然,并未有相应的准备时间。故其考试办法不可能一开始就试难度稍高的口试性“帖经”和试策,而是会选择考察较为基础的以“离经”断句为本的诵读能力。实际上,贞观八年(634)加试“试读”经史一部可看作是为永隆二年(681)以后进士帖经以及进士试“史策”作准备,贞观八年(634)进士象征性地诵读经史,不仅是为了给予进士改革试经史提供准备条件,同时也让进士举的考生有充足的时间去研习经史,以确保人才选拔的有效进行。
其二是进士以“帖经”为大厄。正如前文所述,“帖经”作为考试项目,其难度较高,对于进士试的举子来说,尤为艰难。“帖经”作为进士科考试项目被规定下来,乃见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廷颁布的《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诏令规定,“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7]344-355为过,尽管其及第标准远远低于明经举子“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之通过标准,但仍造成“进士以帖经为大厄”之囧境,其后不得不以诗“赎帖”,以弥补“帖经”之黜落。正如《唐语林》所载:“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声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35]714。其实未到天宝初年已有以诗“赎帖”之例,如《太平广记》载:“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36]1029崔曙者,《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五记为“开元二十六年进士”[37]3602,换言之,“帖经”作为进士试的必试科目之伊始,便允许以诗“赎帖”。由此可见,“帖经”对于文士出身的举子来说极为困难,自贞观八年(634)加试“试读”经史一部,至开元二十五年(737)诏令进士帖经,其间经历了百余年的习经和试经准备,尚出现进士举子以“帖经”为大厄,最终不得不以诗“赎帖”之现象,更何况贞观八年(634)进士初试经史,断不可能是“帖读”或“读帖”,亦即是陈飞先生所认为的“口试帖经”。
四、结 语
总之,自武德四年(621)举行科举考试以来,科举考试制度便在不断的探索和调整之中。唐代科举制度虽然有了契合时代的新变,但其本身仍有蹈袭前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元素,科举制度的健全,考试项目的设置亦未能脱离前代人才选拔制度以及读书治学习惯的影响。尽管先秦时期并未形成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但其学习经史典籍重“离经”断句及诵读的入门方法为后世继承,历经唐宋,延续至明清。不仅如此,以“离经”断句为基础的诵读自汉逐渐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考核内容,并于晋时演变为“试读”。唐袭旧制,在经史的垂鉴教化作用的驱使下,于大唐贞观八年(634)诏令进士加试“试读”经史一部,鉴于进士初试经史的特殊性,其考试方法“试读”遵循了前人以“离经”断句和诵读为基础培养能力的治经读史之方法。“试读”即是诵读,既非试以经史策,亦非“帖读”或“读帖”。“试读”试项的设置,不仅是督促进士举子诵读经史之加试性考试项目,同时也可视作是为永隆二年以后(681)的科举考试改革,尤其是进士试帖及试“史策”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