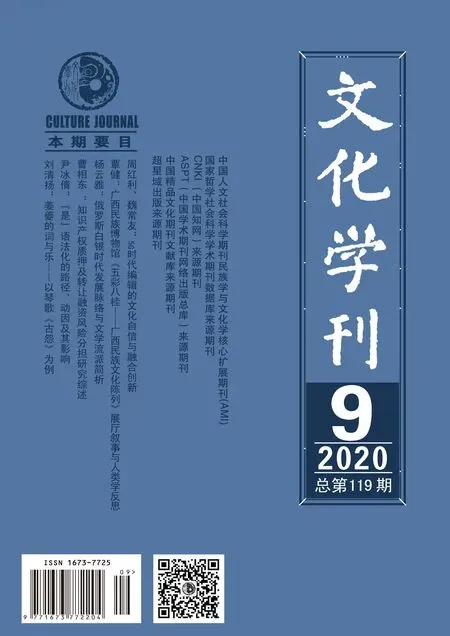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文心雕龙·辨骚》“博徒”一词褒贬新议
2020-01-01黄傲鑫
黄傲鑫
一、20世纪以来的三种声音
刘勰《文心雕龙》的《辨骚》篇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其中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辨骚》篇的归属问题,究竟属于“文之枢纽”之总论,还是属于文体论;第二,刘勰对《楚辞》的评价的标准问题,是否具有“崇经抑骚”的思想倾向;第三,篇中具体关键词的训诂是否精当,主要是关于“《雅》《颂》之博徒”一句中“博徒”一词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通过厘清前人对此发表的众多意见,笔者认为以上看似三个问题,其实彼此不能脱开关联,归根结底是为了讨论刘勰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态度问题。进一步来说,关于“博徒”一词的释义确乎是这三个问题的关键,因为对“博徒”一词的解释不仅是解开另外两个相对宏观问题的基础,也对还原《辨骚篇》的本旨以及刘勰的楚辞观都有重要意义。
叶汝骏先生在2016年1月发表了《20世纪以来〈文心雕龙·辨骚〉研究综述》一文,对整个20世纪以来关于“博徒”一词的争论作了回顾,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对学界所持不同观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清黄叔琳在《文心雕龙辑注》中引《信陵君传》“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1]为注,意在说明“博徒”一词的出处,并未注明何意,考《史记·魏公子列传》,亦未见有对该词的训释。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进一步将其解释为“人之贱者”[2],这种带有贬义色彩的解释多为后人所承袭,如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训为“赌徒,微贱者”[3];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释为“低贱之人”;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释为“贱人”,引申为“下品”。这些基本上是赞同“博徒”为贬义的,也是一直以来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观点。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此产生疑问,认为“博徒”一词当为褒义,如韩湖初认为应释为“博通雅颂之士”,并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博通之徒”。易健贤考释“博徒”为“广而博之者”和“广闻博识者”。李金坤认为“博徒”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意为“博雅通达之传人”。党圣元、罗剑波等学者也基本持褒义的观点。
也有学者通过对这种主褒义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作了新的探讨,主要有李定广、伏俊琏、卢盛江、李飞等,均认为“博徒”虽然是以雅颂为标尺对楚辞的贬低,但贬低的程度是很轻微的。至杨德春《〈文心雕龙·辨骚〉“博徒”正诂》则认为“博徒”一词介于褒贬之间,属于中性词。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基本上厘清了关于“博徒”一词争论发生的历程,如果进一步研究,不难发现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主张褒义的学者们对“博徒”一词做出的解释并没有文献支撑,而是把“博徒”一词看成“博”与“徒”两个单音节词的组合,这一点是否合理则需要进行追问和商榷。
第二,反对褒义的学者基本上仍然利用了最初的材料和方法进行论证,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李定广在其论文中阐明了新的理由,即“博徒”一词在古籍中皆用作贬词而无用作褒词者,且“博徒”在《知音》篇与《辨骚》篇中皆为贬义。遗憾的是,这并没有成为贬义色彩的力证,而是越来越成为“中性词”说的基础,于是“博徒”一词是中性词的说法便带有了折中色彩。
事实上,李定广先生的思路是可取的,只是并没有把文献坐实,也需要相应的佐证才能成立,这也给了我们新的启发。
二、缺乏文献支撑的“褒义说”
对于一个词的解释,尤其是古代文献中的词语,不仅需要上下文的疏通,也需要相应文献的支撑。也就是说,如果假设“博徒”可以被解释成为“博雅通达之士”,那么能否在古籍中找到相应的案例,古人有没有这种用法。如果忽视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对“博徒”一词作更多的复合文本的解释,并不单单是“博雅通达之士”这一种理解了。很显然,李定广先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发现古籍中并没有把“博徒”训为褒义的这种用法。其实这样说也不客观,因为我们发现在乔琳所作的《巴州化成县新移文宣王庙颂序》中确实存在“博徒”用作褒义的例子:
故夫子之前,未曾生夫子;夫子之後,不复有夫子。宇宙古今,倬惟一人。谓天能生,曷不能数生也?故曰非天生耳。河图凤鸟言其德,梁木泰山言其用。谦以况物,物由我成。且孔圣之道,恢张而天下理,杀而天下乱,观其可以卜理乱也。领徒三千,博徒三万,桓文不足侔其众。[4]
这篇序文是为了记载当时巴州夏旱,身为化成县令的卢沔在孔庙祈雨灵应,因此出具家财重新修庙的事情。这段引文表达了对孔子的赞颂,其中“领徒三千,博徒三万”一句虽少见于群经,但是作为对孔子弟子的统称,应该是言其门生弟子广众。所谓“领徒”,《唐律》载:“诸领徒应役而不役,及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役者,过三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5]此处的“领徒”是指“带领囚徒之人”,显然不是乔文中“领徒”的意思。其实,“领徒”乃是佛家的词汇,佛家有“领徒投佛”[6]的典故,这里的“领徒”是带领徒弟的意思,因此与“博徒”并不构成关联。那么乔文中出现的“博徒”则应泛指众多门徒的意思。这样一来,“博徒”则似乎可以有一个中性词的解释,即“众多徒弟”的意思。至于能否用来解释《辨骚》篇中的“博徒”,则需要追踪一下这则文献的出现时间和场域。
《巴州化成县新移文宣王庙颂序》的作者乔琳恐并不为人所熟知,我们也只能跟据《新唐书》和《旧唐书》对此人作一些粗略的了解:
乔琳,太原人。少孤贫志学,以文词称。天宝初,举进士,补成武尉,累授兴平尉。……入为大理少卿、国子祭酒。出为怀州刺史。琳素与张涉友善,上在春宫,涉尝为侍读。[7]
乔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学,擢进士第。性诞荡无礼检。郭子仪表为朔方府掌书记。与联舍毕曜相掉讦,贬巴州司户参军。……琳年高且聩,每进封失次,所言不厌帝旨,在位阅八旬,以工部尚书罢。帝由是亦疏涉。[8]
《新唐书》和《旧唐书》都对乔琳有过记载,考其生平,乔琳于天宝初擢进士,天宝三载(744)甲申五月改年为载,天宝初当在天宝元年五月至天宝二年五月之间,即公元742至743年,考玄宗朝科举,在天宝二年曾有贡举重试之例,乔琳当在此科中进士第。《旧唐书》载:“及官军收京师,当处极刑,时琳已七十余……”及官军收京师则在757年左右,此时乔琳已七十余岁,可知乔琳写作《巴州化成县新移文宣五庙颂》一文也该在此之前。刘勰写成《文心雕龙》当在齐末梁初,即公元502年左右。两相对比,乔文晚出生至少两百年。虽然后出的文献也可能说明之前的语言习惯,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其他更早的例子,所以就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博徒”一词虽然有不是贬义的用法,但是这仅有的一例却不能被用来解释《辨骚》篇中的“博徒”。只有彻底排除了这个例子,才能说古籍中并没有把“博徒”训为“通达博雅之士”或者其他褒义色彩意义的用法。
三、是“贬义”而非“贬抑”
通过文献中对“博徒”用法进行分析,我们虽然知道“博徒”一词不能解释为“博雅通达之士”,但是“博徒”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要确定其解释的合理性,而是要尽可能确立这一解释的唯一性。也就是说,对于“博徒”一词,我们需要证明能且只能有这种解释。
首先,《文心雕龙》是用典范的骈文写成的,如果按照赞同“褒义说”的学者们所言,“博”应是取“博通”“博达”“博雅”“博衍”“渊博”之义,“徒”即“徒弟”“学徒”“弟子”“传人”之义,进而将“博徒”连释,即为“博雅通达之传人”。很显然是将“博徒”作为两个单音节词的复合形式,而且是形容词加宾语结构,即“博”字是修饰“徒”字的,那么根据骈文对仗的技法,下文中“英杰”一词也该是这种结构。
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9]
时孝武自揽威权,……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10]
宗诚少处乡隅,学疏才拙,加以境遇窘穷,不能应科举。游四方,是以于天下英杰。[11]
不难发现,对于“英杰”这个词的使用是很稳定的,即是“英雄豪杰”的简化,在古汉语中还有“英豪”“英才”“俊杰”“豪杰”等,这些均不构成内部的定中关系,而且也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词语使用,而不是拆分成为两个单音节词的复合形式。所以,《辨骚》篇中“雅颂之博徒,辞赋之英杰”一句也该是遵循这一语法结构。既然“英杰”不构成定中结构,那么把“博徒”解释成定中结构的“博雅通达之士”也就没有道理了。
其次,通过现有的材料或者语料来看“博徒”一词在刘勰之前,刘勰同时,乃至刘勰之后都能有什么解释。詹锳《义证》加引《史记·袁盎列传》“吾闻剧孟博徒”为注,并附《集解》“博荡之徒,或曰博戏之徒”,此处贬义色彩明矣。又恐这两例距离南朝齐梁相隔甚远,语用有失真之处,便又引《知音》篇“彼实博徒,轻言负诮”一句为例,并解释范文澜先生的注说:“意为《楚辞》比《诗经》差一点”[12]。以此看来,训“博徒”为低贱之人当是确论,为了使“博徒”一词在古汉语中的解释链更加完整,笔者给出齐梁以后至明清的用法:
司马当时,开阁雄都。枥上驵骏,腰间辘轳。交结豪贵,亦交博徒。[13]
长安二年,鸾台侍郎韦安石,尝于内殿赐宴。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博于上前,言辞犯礼。……陆元方退而告人曰:“向见韦公叱博徒,吾等为之寒心,此真宰相。”[14]
交游的人,总是些剑客、博徒、杀人不偿命的无赖子弟。……就有那一班儿意气相投的人,成群聚党,如兄若弟往来。[15]
通过列举的材料,大致可以看到“博徒”一词其实都是贬义的,实指那些浪荡子弟,打架斗殴之徒,这也说明乔琳《巴州化成县新移文宣王庙颂序》中“博徒”的用法并没有后世文献的支撑。我们甚至可以看出来“博徒”不论我们如何去解释“博”,归结到“徒”字都是与“礼”相违背的一类人。刘勰在《辨骚》篇中之所以说是“《雅》《颂》之博徒”,就是基于《离骚》并不是完全符合经典,而“徒”字则能准确而不失生动地把这层意思传达出来。
最后,“博徒”作为贬义词也能在文本中获得合理的解释。刘勰说《楚辞》“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这是从文体、风格等方面同经书进行比较,就文风而言,虽然《楚辞》继承了《诗经》的优良传统,但是夹杂了战国纵横捭阖之文风,不及春秋三代《雅》《颂》之典丽。事实上,刘勰自己也曾感受到这种一切都根据经书来进行创作的难处,他在《序志篇》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镬。”古代经书的语言词汇很难符合当前的语用需要,因此刘勰也只评论《离骚》内容是否与经书符合,并未强行要求语言风格也靠近经书。面对这种创新,刘勰认为《离骚》能“取熔经意,自铸伟辞”乃是对经书的一大蜕变,并对这种创新感到惊喜,虽然“博徒”一词带有贬义色彩,但刘勰对《离骚》却并不贬抑,反而称赞其“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至此,刘勰对《楚辞》《离骚》的态度也就变得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