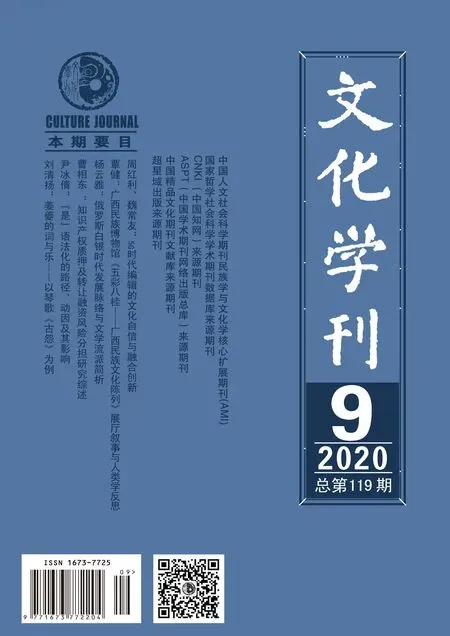月是故乡明:评何昭明散文集《青松岭》中的故乡情怀
2020-01-01胡家琼
陈 群 胡家琼
关于故乡,作家马卫民这样解读,“家乡是刻在骨子里的一个称呼,是溶入血脉中的一种牵念,小时候经历的一些事就像一瓶窖藏的老酒,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绵长厚重而韵味悠久”[1]。在何昭明看来,故乡是祖父辛劳的背影,是祖母诱人的饭香,是年少时光里的悲欢离合。《青松岭》这本集子包罗万象,有少年时光的求学生涯,中年岁月里的三线建设,古稀之年的回忆故乡,在丰富的内容中,最为让读者感动的是作者悬车之年的思乡情怀。
一、感恩祖父母,常思故乡情
常言道,离家三十里,即是外乡人。但著名乡土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血缘和地缘是人类永恒的牵挂,根植于心,经久不变。“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可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2]因此,无论后来我们身居何方,故乡记忆将永不可遗忘。特别是对于从小饱受分离之苦的作者来说,故乡意义更加深远。父亲早逝、母亲远嫁,从小由祖父母养育,年幼便离开故乡到他乡,故乡成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创作《青松岭》时,作者虽已离乡近六十载,但古稀之年的他老当益壮,不坠家乡情怀,用数年时间完成创作。这份赤子情怀,一览无遗。他怀着感恩之心从事创作,终其一生,特别是祖父母的音容笑貌时刻铭记于心。祖母做的“牛角糯米糍粑”,清香浓郁;二刀肉烟熏火腿,沁人肺腑;豆豉辣椒小豆酸汤,清香可口,过年才能享受的香喷喷的新米饭,令作者感觉温暖而惬意。“已满头银发的祖母,对着用小碟子装菜油、用‘灯草’做灯芯的昏黄灯光,一边给我们补衣服,一边在屋里等我们。夜深时,祖母就在后檐沟的门边,隔着桃树石榴树,亲昵地呼唤我和妹妹的乳名……”年迈的祖父终年辛劳,双手因常年握锄头磨出了老茧,双脚到了冬天都是裂口,却从不在家人面前诉说。日子虽苦,但有祖父母的日子总是香甜。记忆中,每到年下杀猪,慈爱的祖父总是会把平时不舍得吃的腊肉给他们解馋。
儿时的我们,最盼杀“年猪”。
年猪一杀,祖父就在堂屋的神龛前,搭个高高的木架子,把祖母用盐、花椒粉之类腌好的猪肉放上去,在下面烧起“圪蔸火”,一边“秋”腊肉,一边打草鞋,一边给烤火取暖凑热闹的我们“摆龙门阵”……
经过七八天的烟熏细火烤,那些“秋”着的腊肉,也不知不觉开始滴油了。祖父见哪块又瘦又黑里透红,就用刀割下来,在柴火上烤熟了给我们吃……祖父慈爱地笑着,看我们“馋猫”似地歪着头吃”烤腊肉”的神情,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浮现……
在文中,作者几次提到祖父虽是一介农夫,却及有远见,为了使他完成学业不辞艰辛。“祖父为了完成我们学业,先是让年仅五岁的我在‘祠堂族学’与幺叔伴读;继是停止幺叔学业,将我又牵又背又骑马地送出求学,来到才成家不久的幺姑家附近的‘苗寨私塾’启蒙;再是送到在山城工作即将成家的二叔处继续;后又将我接回故乡,在乡中心小学走读高小。真是耗尽心血,含辛茹苦,栉风沐雨,历尽艰辛。”而祖父到了弥留之际,他在听到了祖母对他承诺无论日子再艰难都要把孙儿拉扯大的承诺之后才合拢双目。
有惦记才有牵挂,有牵挂才有行动,对故乡的感恩化成了真切的行动。所以当有能力回报家乡之时,作者何昭明对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自己绵薄之力改善当地落后的教育条件和出行问题。作者的家乡在深山之中,为了解决出行难的问题,他几经踌躇,思虑再三,痛下决心,恳请当地农办原主任向有关部门如实反映情况,并一次次亲临现场踏勘路线走向。经过上级部门的关心和众乡亲的支持,终于使乡村公路通车。从此,深山险隘变通途,十余村寨受惠。为了改善教育环境,修建小学,他一次次自费陪同我国香港地区的徐先生搞调研,写报告,送材料,选校址,商设计,参奠基,贺竣工。彼时的交通,没有高速公路,并不像如今便捷,每次来回都要辗转一天,疲惫不堪,但何先生从未言说辛劳。当各级领导、父老乡亲、学校师生赞美他,褒奖他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尽心尽力牵线搭桥,要将他的名字刻于石碑时,他却大有“愧感交加”“心余力拙”之感。这都充分体现了其一心为家乡、不图半点虚名的儒家风范。
二、绵绵细语皆见故乡风情
故乡记忆是重获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重要桥梁,寻根溯源是对父辈的另一种祭奠。在作者的记忆中,故乡虽然落后,但文化深厚,结构稳定,这许是何氏人才辈出、淳朴民风得以传承的原因所在。费孝通先生认为:“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3]在《青松岭》中,作者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详细记录何氏家族的历史,及以“重教兴学,耕读为本”的族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何氏历朝历代都有显官。何氏名人,从列国时期、西汉魏晋、隋唐五代,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让何氏后人引以为荣和自豪,并激励后人不断奋进。作者赞美何氏无论在晚清年间,为“训子侄诸孙辈”,成立私塾学馆,还是在民国时期,饥荒状况之下都要兴学。作者还抒写何氏家风的优良,父辈虽没有丰功伟绩,却有远见抱负。作者深情回忆,自己虽不是“祠堂族学”的在编学生,仅仅是来去自由跟读上大课,印象并不深刻,然而,当时上学的那狭窄小路,寒冬的“村夜玹音”,学校周围的“松林野趣”,星期天的“深山晨牧”,学伟堂叔的“板壁练字”都铭刻在记忆的岩壁上,历久弥新。
回忆故乡,作者绵绵之情溢于言表。在作者的记忆中,何氏寨子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四周青山环绕,满目碧翠,是风水宝地。据说寨子位于龙头之上,龙嘴伸进寨前的“麻塘”里吸水。寨子总是和大自然和谐共存,连那些羊肠小道都是大自然给家乡最好的礼物。小山背后岩半腰的那个“龙潭”常年清澈见底,龙潭里流出的清泉终年不断。肥沃的山间缓坡上,种着油菜、胡豆、豌豆之类。每到春天,一块块金黄的菜花点缀在紫色的胡豆花中间,竟相散发出阵阵清香。
在作者自豪不已不能忘怀的记忆中,还有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却依然心怀善意的人们。“清晨,迎着爽爽微风,和幺叔站在齐腰深、油绿绿、叶片又宽又长又点头哈腰的‘土烟’地里。别说数次亲手给烟们除草、打杈、用油枯施肥的幺叔,就连我自己,也有一种来自丹田油然升起的喜悦感、成就感和自豪感。”幺叔的善良不仅对人,还有物。“幺叔家喂的那头比水牛还高大还壮实屁股又滚圆的大黄牛,每天早上,富有爱心的幺叔都要牵它去吃‘带露水’的嫩草。同时,还要割一背箩‘茅针草’‘熟地草’‘马耳朵草’等品种多样的鲜草背回家去喂它。那些不背包或背包小的苞谷杆,趁着又嫩又甜,幺叔就毫不留情地砍来给它‘享受’。”后来,进入困难年代,艰难的日子也未曾让幺叔幺婶打牛的“主意”,有人再三劝说幺叔:“喂牛的那一大铁锅菜稀饭‘重得很’,干脆把它卖掉算了。厚道的幺叔总是笑笑,说它‘乖’,十来年‘哈欠都不打一个’‘是天赐的缘份’,不肯卖……”
三、心怀悲悯,情系民众
出生农村使作者对于困难有了切身体验,这是一种天生的零距离。故乡是他的起点,是他永生难忘之地。他竭尽全力关爱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并通过作品抒写苦难,表达悲悯。在《青松岭》中,他怀着普世之爱,揣着沉重之心,关爱着他的乡亲父老。
孩提时的苦难似乎还在昨天,每天早出晚归,要走十来里山路才到学校。下午放学,早上吃的酸汤包谷饭已所剩无几,肚皮老是咕噜咕噜“直造反”,饿得脚耙手软。生活的苦难使得自然界的一切果实都寻来充饥,“牛角猛”“红刺猛”“糖郎”“鸡屎猛”等,都被一路走一路摘来充饥。没过多久,“大食堂”就散伙了,甑无颗粒的人家开始吃往年喂猪的糠壳。继以猪草充饥,手脚浮肿,饿殍路旁。板壁练字还历历在目,少年老成的学伟堂叔从田地里抠出来的白浆泥,搓成条状晒干当粉笔。五十年后,重回故里,在清明族会上,学伟堂叔声言他“家庭拖累”“力不从心”“耕饲繁重”,诚辞族长。作者欲请学伟堂叔教自己山歌孝歌,全盘写出,可惜去回匆促,未能谋面,唯留遗憾。再有机会问及时,据说他从小“身子单薄”,不堪农事重负,年及“花甲”便病逝故里。寿木安葬,皆是族人筹办。光阴似箭,白云苍狗,作者顿感物是人非,不能自己,阵阵悲酸,涌上心头,黯然而泪下。
看着处于困苦境地的家乡父老,作者以同情的姿态,冷静的思考,用实际行动关爱和帮助亲人。让作者欣慰的是,近几年,在国家惠民政策的支持下,家乡人民终于摆脱苦难,走上了幸福之路,苦难之后是阳光,悲悯之中见希望。
四、结语
在《青松岭》中,作者饱含赤子之情,对家乡尽情书写。这其中,看似平实叙事,实则情深意切。对于故乡,作者的心境是复杂的,有失落,有激动,如同马卫民先生在《我的村庄我的家》里描述的感受一致。“回顾这些年,从青春年少的轻狂到老有所悟的沉稳,那些曾经澎湃的情感渐渐归于寂静,从容不迫地走回灵魂的故乡,时常感悟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开始寻找那些即将消失的往事和渐渐远去的村庄,轻轻地打开那些尘封于记忆深处的内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4]对于家乡,他们都心怀感恩,希望以作品回馈桑梓,以深情告慰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