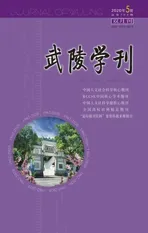论道德恐惧的三重维度
2020-01-01陈晓曦
陈晓曦
(滁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关于道德的各种话题,历史上从未像今天一样广受人们的热议。社会各界都空前地关注道德状况,讨论道德现象,提出新概念,如道德悖论(钱广荣)、道德冷漠(高兆明)、道德恐惧(周维功)等。尤其是近几年来,周维功先生连续发文就道德恐惧概念进行界定和讨论:2014年在《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恐惧——一种道德冷漠的心理基础》、2015年在《江淮论坛》第5期发表《“道德恐惧”辨》以及在《宿州学院学报》第7期发表《论“道德恐惧”的成因及克服的途径》,2017年与周宁合著在《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道德恐惧”再探析》、同年与周宁合著在《江淮论坛》第4期发表《道德自由何以可能》等。尽管最后一篇文章的篇名没有直接使用道德恐惧这一概念,但是文章还是在讨论人如何克服道德恐惧与实现道德自由的问题。受周维功先生启发,笔者尝试从三个角度对道德恐惧的概念进行阐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作为生存论之伦理情绪的道德恐惧
任何一个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体验、存有观念和宗教性的经验与体验的精神结构,比如崇高、神秘、神圣、敬畏等。天地万有、创世神话等重大事件相对于个体而言,其体量、伟力、恒久意义都是绝对的、超越的。西方哲学史告诉我们,虔敬是沟通神人、联系永恒与有限的不二途径,有神人合一的狂喜或迷狂。柏拉图的对话篇《斐德罗篇》就罗列了四种不同的迷狂[1]。同样,东方民族也有类似的内在体验,对超绝之物的威严感到震撼,对自己有限的、身体性的存在感受到不完美甚至是罪责意识,无限与有限似乎存在着根本无法消弭的鸿沟,因而产生了畏惧感。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崇高、神秘、神圣与敬畏被集中指向天,中国先民对天的敬畏与恐惧就变成了对天所代表的精神之真正守护。《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17在《论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先贤的这种生存伦理情绪的恐惧体验,当然它属于道德恐惧,而在文化中又集中体现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天命意识。这种天命意识散见于《论语》各篇多处。虽然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但是孔子对天命的敬重,居仁由义的使命感,人生匆匆、有限而任重道远的责任情怀是浓郁的:“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2]172朱熹对“三畏”的解释是:“畏者,严惮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2]172在朱熹那里,面对天赋之理(命令),人人都有“不能己”而戒谨恐惧;在类比的意义上,大人与圣人言同于天赋之理(命令),同样存在“不得不”畏的忌惮。
对伦理情绪的道德恐惧,有两种解释是需要加以辨析的,因为它们或显得隔靴搔痒,或显得外在而肤浅。其一,把这种恐惧感归结为先民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认识能力的低下。不过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民族在社会发展较低水平的时候都有这种作为伦理情绪的恐惧感,相反只有文化自觉到一定程度的民族才有这样的高级情绪。其二,把这种类似于宗教性的体验,即作为生存论意义的伦理情绪之道德恐惧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需要,似乎这样才使人心安。其实,心理学治疗手段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完全可以有另外的可替代的途径来消解或缓解某种心里紧张。所以我们说恐惧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根基性的,而不是心理学或现象界上的。
一方面是如处深渊一般的生存情绪,另一方面是孔子通过仁以为己任来充实经验性生命,力图让自己心安、不惧、无忧。这两方面非但不冲突,反倒是统一的。因为修己安人、下学上达是在充实经验世界的自我,思慕巍巍荡荡先贤境界,建立的是死而后已、求仁得仁的道德人格;而如承大祭、战战兢兢,面对于穆不已的绝对天命存在,经验世界的个体总会倍感欠缺。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于人之存在维度上的恐惧与普通情感上的恐惧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说不出前者恐惧的精确对象是什么,所以孔子经常对不及时行仁义、知错不改感到忧虑,面对不舍昼夜的河水也会引发他天命道德式的感喟。而后者则不然,比如,普通人对疾病、灾祸的恐惧,有着明确的恐惧对象。所以一旦对象不存在了、消除了,恐惧的情感就会随之消失。医生如果误诊,认为一个人患上了绝症,那么患者可能陷入极度惊惧之中;随着医生澄清事实,说是一场误诊,那么该病患会立即感到释然,先前的惊惧一扫而空,只是虚惊一场。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猛兽等的恐惧则更加不同了。但是,一种伦理性的情绪则不然。儒家说的敬畏、不安之类的恐惧,绝非针对某个存在者,更像是针对自身,即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欠缺、罪过与不洁。从价值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生存情绪一方面是无法排遣的、挥之不去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本身是好的。换句话说,人之为人的意义就是从这里体现的。这种深深的不安和基于完美与欠缺的对比,特别是在道德完善性上的对比,牢牢嵌在人的内心,构成了人不断反省的动力源与根本依据。
道德恐惧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办事小心谨慎,犹如林黛玉进贾府般“不肯多行一步路,不肯多说一句话,生怕被人耻笑了去”。林黛玉的恐惧表现的是一种陌生感、对自己身世的顾影自怜,因而也就完全不同于原始儒家的天命感意义上的恐惧。因此,这里丝毫不存在“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情感,只有生怕自己做得不好而无法被那个共同体接纳的顾虑。对治林黛玉恐惧的情绪,也不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立己达人之路,而是现实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当然也包括如愿以偿地走进她理想的婚姻生活。
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道德恐惧与宗教情绪是非常接近的,有时候我们很难将其加以区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思想实质上也包括了宗教性体验。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中国儒家或儒学之外没有再成立什么儒教,因为超越性的诉求已经溶解在儒学之中了。一言以蔽之,“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的作用”[3]。究其原因,在于儒家独特的“以天论德”的思想传统。如果我们不从儒学语境来理解道德恐惧,而是从西方宗教体验来看就更加明显了。著名学者吴学国指出:“人由于反省到他对超越者的背离,而感到应受惩罚。人们感到,惩罚作为对自然存在的污染之否定,其实是使灵魂重新净化的涅槃之火,因而对于他的精神存在而言,它非但不是一种损失,反倒是获得拯救的阶梯。所以求道者不会以某种狡计逃避惩罚,而只能充满恐惧地等待审判的来临。”[4]对此阐释得更加生动的是西蒙娜·薇依的精神自传,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她与神的精神相遇以及此世分离的深刻体验,比如,她感受到了自己从基督体内诞生,“基督教是奴隶们的宗教......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5]。所以,无论从宗教、非典型性宗教还是纯粹的生存论意义上的伦理性情绪方面看,他们都有共通的道德恐惧。
不过周维功先生在文章中也特地把这种道德恐惧排除在外,他说:“本文定义的‘道德恐惧’既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恐惧,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敬畏,既不是泛指人对‘道德’的恐惧,也不是指由‘道德’所引发的人的恐惧。”[6]显然这是他为自己的立论确定了一个空间与范围,这并无不可,毋宁说还使其后面的论证更为集中了。但是,道德恐惧本身确实也包括伦理性情绪,所以我们将其列为道德恐惧的第一个维度。下面将从德性论维度继续展开分析。
二、作为德性论之道德勇气缺乏意义的道德恐惧
如果说恐惧(fear)的对立面是勇敢(courage),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思想就是我们讨论道德恐惧的最好资源了。亚氏认为,道德德性既非天生,也非简单地由老师传授;它们通过实践而获得,通过废弃而丧失。道德德性既非一种能力(如智力或记忆),也非一种激情(如一阵愤怒或怜悯)。只拥有能力或激情,还看不出人品格的好坏,也不知该得到赞扬还是责备。好人之为好人是因其灵魂的持久状态,“它们是中庸和品质”[7]1114。道德德性是人选择得好又做得好的性格状态。选择得好是指选择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做得好包括在各种具体的行为中避免过度和不足。就勇敢的反面——恐惧而言,其具体的对象乃是“不同形式的恶”,包括坏名声、贫困、疾病、孤独、死亡等。这里,亚氏表达了“当恐则恐、当惧则惧”的思想,无所畏惧并不能成就所有的德性,相反,对一些坏的事物感到恐惧反倒是正确的、高尚的,不感到恐惧才是卑贱的。从希腊城邦政治的实际出发,亚氏对于勇敢德性的界定在士兵这一类人群上着墨较多,其目的显然是培养城邦护卫者的勇气。这样我们把勇敢的德性与勇敢的品质归结为:“在面临巨大危险时一方面虚妄的信心、另一方面过度的惧怕之间的中庸;勇敢的人之所以选择面对和承受这种惊怕,是因为这样选择的承受是高贵的,相反则是卑贱的。”[7]1116由此可知,怯懦就是恐惧过度,以不当的方式,畏惧不该畏惧的对象。虽然勇敢意味着无所畏惧,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无所畏惧就是勇敢、有所畏惧就是怯懦,因为有所畏、有所怕、有所惧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把世间一切感受还原到苦乐上,勇敢者显然就是承受痛苦者,进一步说,勇敢也意味着对快乐做出一种节制。反过来看,恐惧的人显然就是无法承受痛苦的人,恐惧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对手头的或眼前的快乐无法割舍。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论述的勇敢及其相关的恐惧、害怕、怯懦主要针对城邦,尤其是卫士的品德,那么《论语》中论及的勇敢则是君子的品德。孔子多次谈论过勇敢之德性,典型的就是“知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而关于忧惧的讨论,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回答司马牛问君子一章中。孔子的回答是“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在现实世界,从一个自然人到君子的修身过程,有许多德性需要培养,比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终极意义上如何克服恐惧,孔子的方案是仁勇并用,似乎并不是单一地用勇气来对治怯懦。不但如此,勇敢的美德在孔子那里还作了一种“内转”的处理,表示对勇敢进行一定程度的节制,这也是孔子与亚氏的鲜明不同。比如,孔子一直就对子路的勇表示出一种警惕。子路问君子是否崇尚勇敢,孔子的回答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季氏》)
道德的理性不仅要在外部行动上建立权威约束,更要在个体内部确立“就有道而正焉”的自反意识。所谓见贤思齐、观过知仁、过则勿惮改就是这个意思。整部《论语》都反映了孔子对改过的重视,以圣贤、君子为准绳的对照反思,力图在自身之内形成对率性冲动纠正的习惯,无疑就是勇敢的内转,如:“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孔子对不能和无力改过表现出无比的痛心疾首。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子罕》)孔子如此强调改过,以至于在他看来,过错本身似乎不是过错,惟有不改过才是真正的过错,所谓“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当然换一个说法,这种改过思想确实也是一种勇气,它可以克服内在的自大和冥顽,因而迁善和改过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在孔子看来,品格上的道德恐惧,既属于勇气不足,也属于仁心不畅,而且后者似乎还要更多一点。也就是说,矫治道德恐惧除了培养勇敢的意志品质,更在于涵养仁德,让仁心充盈起来。不但如此,还因为好勇容易造成偏差,所以在孔子看来,勇敢首先不是指士兵在沙场上的一往无前,而是君子勇于内省、勇于改过。有鉴于此,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中的勇敢受到了梁启超的置疑。梁启超对泰西、日本人常言的“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倍感愤怒,于是写下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8]。当然有学者将此认定为“中国古代文明早熟的特点”[9],笔者以为是有待商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释导读本)译者邓安庆先生在该书的“勇敢”注释部分就写道:如儒学中为什么是“仁义礼智信”,而民间儒家伦理却说“百善孝为先”?勇敢在我们的伦理传统中为什么不是一种重要的德行?勇敢的德性力量与尼采推崇的“强力意志”的力量是什么关系呢[7]119?这个问题是需要整个学术界,乃至整个民族通过思考与行动才能回答的。
实际上,周维功先生小心翼翼界定的道德恐惧概念,即“道德主体因基于各种可能的压力、风险或威胁,尤其担心自身或者家人遭受重大伤害,胆小怯懦,失去道德勇气和道义良知,逃避、放弃本应承担的道德责任”[10],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些对“可能的压力、风险、危险或威胁的特殊恐惧”,说到底还是应该通过勇敢来克服。哪有勇敢不伴随压力,不承担危险、危险或威胁呢?当然,结合今天中国的实际,就是说,一个“好人”应该有“善报”,即舆论环境和社会制度应当为见义勇为者提供良好的保障。这一点归根到底是人的德福一致的诉求。对周维功先生的道德恐惧概念最准确的理解应该在第三个维度上,即作为德福关系失调意义上的道德恐惧。
三、作为德福观意义的道德恐惧
德福的关系问题,就是德福一致的理论可能性、实践形态与路径问题,也即哲学中的“圆善论”“至善论”问题,涉及哲学对人命运的终极关怀与伦理学的最高实践原则。中国德福思想之芽蘖初见于《尚书·洪范》中的“五福”(寿、富、康宁、行好德、考终命终)、“六极”(凶短折、极、忧、贫、恶、弱),并直接发轫于《易传·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的观念。德福关系在政治治理(以德配天)、社会秩序(天鉴在下,礼别尊卑)、个体成人之道(天人同有)的不同层面构成一套人感天应学说系统,在观念、信仰与实践领域发挥着重大指引、调整与规范作用。可以说以“天应”为中间保证力量,连接德行与福报,构成中国德福一致思想的根本特征[11]。
德福思想在西方也是自古有之,且事关宏旨。作为伦理学问题肇始于柏拉图,康德通过道德神学“公设”(灵魂不朽、来世、上帝存在)给予了理论回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正义和快乐的关系首次呈现了德福命题,其基本立场是:正义的人,才是灵魂平静、生活快乐的人;当然正义的人自始至终都依赖于城邦制度设计的正义。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在欧洲分别展开为情感主义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以改造旧制度、创建新制度为宗旨的法国启蒙运动和智性思辨的德国启蒙运动等多种面相。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诞生的功利主义思想直接就把道德界定为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德福一致的关系一目了然。弗朗西斯·哈奇森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那种行为就是最好的行为,以同样的方式引起苦难的行为就是最坏的行为。”[12]总之,尽管儒家有“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学术思想资源,甚至有数千年的“公私之辨”“义利之辨”的传统,但是好人有好报的观念依然是最强劲最朴素的道德心理。同样,西方的道德神学路径虽然把道德性的回报与结果安放在了来世,但普通人内心也一样存在德福一致的强烈要求。黑格尔指出:“个人意志的规定通过国家达到了客观定在,而且通过国家初次达到它的真理和现实化,国家是达到特殊目的和福利的唯一条件。”[13]简而言之,好公民在国家生活中应该有家园之感,他的道德行为应当得到承认,而不是承担个人的风险,哪怕是偶然的风险;反之,国家应该为公民的德性生活提供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一旦国家提供的制度保障缺位或不畅,其直接后果就是德福一致断裂,人与人的信任断裂。因为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在主导层面上指望“天”作为担保力量,继续设想天罚天佑来担保道德评判了,尽管在个体层面个人依然还可以在内心保持这种道德信念。周维功先生认为,学界讨论的道德冷漠现状,实际上有些“冤枉”,因为他们有着道德感情(如愿意去扶摔倒的老人),也有健全的道德认知(帮助弱小是美德),但是他们担心“碰瓷”、事后反被“讹诈”,而且最主要的是,诉诸法律后还有可能得不到一个公正的裁判。这一串推理,反过来在心理造成恐惧,因此才表现为“放弃道德责任,知善不行、见义不为”,进而“采取某种视而不见、见而不为、回避躲让乃至逃离的态度,从而便可表现出来具有鲜明特点的道德心理怯懦和道德实践不作为”[14]。如前所述,如果从德福一致与正义的实现和保障机制角度说,周先生所说的道德恐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所以,周先生就此思考的解决之道——激发人的正能量,重建社会信任——也当属正道。
不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很多,但可能会引起负面效果的毕竟是少数,做好事“被碰瓷”多属于助人这一德目,除此之外的善行义举依然数不胜数。我们不能因为社会在“热议”什么,就过于关注这个热点。做道德的人,完善自我人格,坚持办事公道、服务社会、加强自律,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媒体出于自身的种种考虑,会把一些个别情况变成话题,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基于德福一致想象受阻而致的道德冷漠,其实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绝大部分的道德冷漠还是属于对自我的要求不高以及道德软弱。比如,不说谎,恪守学术道德,奉公守法,孝敬父母,宽宏大量,保护环境,体谅他人等等,并不需要担心什么不良后果,也基本上不存在事后“被反咬一口”的情况。
余 论
在2017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周维功先生继续完善其提出的道德恐惧概念,为其增添了新的立论空间。他认为,在技术社会里,一个行为是不是道德还要经受专业视角的考量。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突飞进程,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在高风险社会境遇中,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命运。种种不确定性导致责任漂流性、道德模糊性,导致主体处于纷繁芜杂、进退失据、无所适从的道德境地,进而质疑自我的价值判断、道德责任与道德能力、道德行为选择和担负后果,这就衍生出了“道德情境不确定性”①。2011年的国家卫生部颁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就旨在提醒救助者采取适宜救助措施,切忌鲁莽行动、好心做错事。可见,救助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导致“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现象产生的一大因素[15]。的确,面对一个行乞者,他究竟是不是真乞丐,我们没法确定;而且现代社会的“相关规定”也经常与实际情境相冲突。比如,地铁里的广播一遍遍说“严禁地铁内乞讨、卖艺”,所以即使面对一个真实的乞丐,我们也会犹豫:大家都不相信他。我如果施舍了,从某种意义说是害了他,因为他本可以早些离开从而多讨要一些。另外,面对跌倒的老人,也出现了技术壁垒的“分情况讨论”,谁又能确保自己既做得善又做得对呢?所以,从技术社会的道德情境的复杂性来说,道德恐惧是非常有道理的。当然,这种带有盘算和权衡性质的心理过程,究竟有多少属于“恐惧”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构成“恐惧”,这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述。
无论如何,道德恐惧的内涵也无法单单通过德福关系失调或现代复杂社会来穷尽。宗教性、类宗教性的生存论意义上的伦理情绪之恐惧,依然是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并构成当代人可诉诸内心的最高价值源泉。而基于道德勇气缺乏的道德恐惧,实际上占据大多数时空。作为勇气,远远不止见义勇为这一种,它甚至关乎人类的启蒙与解放。康德在1784年9月30日发表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如果这种受监护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则它就是咎由自取。因此,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16]这里,勇于思考,勇于运用理智,完全超出了塑造公民道德品质的畛域,走向了为行动的主观意愿立法。由于这种立法是理性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因而是道德的自律。这种自律的自由,即通过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作为纯粹理性中不可认识的本体理念之意志自由,就通过理性批判而以“理性事实”确立下来,成为伦理形上学进一步推论的基础。这样,以正义的政治共同体为基础的自由伦理秩序就可望将人类带入真正的永久和平。安妮·阿林森在《恐惧,勇敢与基督教》一文中写道:“犹如斯多亚哲学提出的那样,勇敢乃是一种原生性德性(primitive virtue)。如果火是普罗米修斯给予人类最早的礼物,那么,勇敢就是让人们用火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人类的进步端赖于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去完成新的事务、思考新的想法,克服新的危险。”[16]就其本质而言,道德乃是自身善念(无论是原生的还是获得的)的冲出,整个身心受其调动,从而把生命连同生命的价值推向高处。总之,综合地把握道德恐惧概念,有助于澄清与化解相关误读与误解,有助于新时代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注 释:
①参见周维功在安徽省哲学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的思考与探索”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是《道德情境不确定性促生道德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