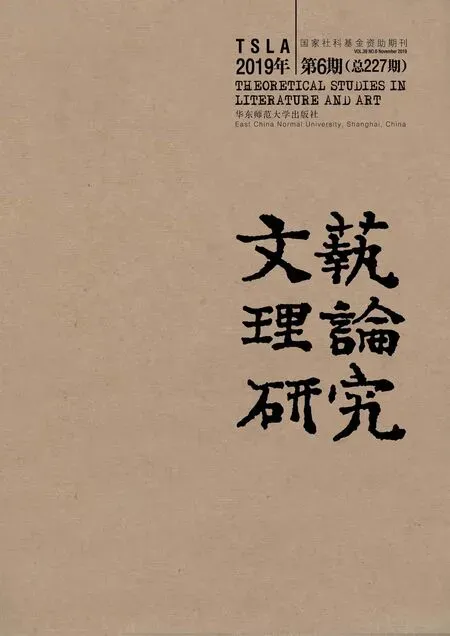艺术正义的类型与亚类型
2020-01-01王云
王 云
人类社会只要存在一天,便会有善行和恶行。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善行和恶行也即正义行为和不正义行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阿得曼托斯之口说,“正义是至善之一,是世上最好的东西之一”(郭斌和等译56),“[……]正义确是最善”(54)。正义是最大的善,那么其他的善呢,譬如善待动物?你可以说这是善行,但却很难说这是正义行为,因为它并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152)政治学上的善也即发生于人群之间的善,因而基本上可等同于正义。正义之所以仅仅是发生于人群之间的善,乃因为正义与人的权利尤其基本权利有着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正义这一范畴的内核就是人的权利。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强调:“任何情况,只要存在着权利问题,便属于正义的问题。”(62—63)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说:“权利还被用在纯伦理意义上来指什么是正义的。”(54)由此可见,发生于人群之间的善行和恶行既分别是正义行为和不正义行为,也分别是维护人的正当权利之行为和侵犯人的正当权利之行为。
故事性(演故事和说故事)艺术只要呈现社会生活的图景,就不免要描述发生于人群之间的善恶行为及其冲突。在历时两千多年的世界艺术史上,数不胜数的戏剧、小说和电影等以(比较)正确的道德态度和立场描述了发生于人群之间的善恶行为和善恶冲突,显见艺术正义(艺术世界中的正义)是故事性艺术的永恒主题。依此推理,艺术正义应该是故事性艺术研究中的永恒话题,艺术正义学说也应该成为相当成熟的理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时下研究艺术正义的著述几乎都出自“法律与文学”的学者而非文学或其他艺术的学者之手,“法律与文学”是法学的跨学科分支,他们研究艺术正义的旨归在法律而非艺术。由于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对艺术正义的类型结构、生成原因、社会效应以及研究艺术正义的方法论等缺乏深入的探究,因而对艺术正义的认知始终模糊不清,最终导致了艺术正义学说始终处在半生不熟的状态之中。本文试图破解艺术正义的类型结构问题,以期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推动艺术正义研究的进展。
一、完全艺术正义与不完全艺术正义
故事性艺术的创造者只要以正确的道德态度和立场描述发生于人群之间的善行和(或)恶行,尤其是善恶行为之冲突,我们都可以认为其作品彰显了艺术正义。艺术正义这一概念的内涵是,在以正确的道德态度和立场描述善恶行为及其冲突的过程中,故事性艺术所彰显出来的主张合理分配权利和维护正当权利的观念。看多了这类作品,敏感的受众或许会发现,它们所彰显的艺术正义似乎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笔者姑且将这两种类型分别命名为“完全艺术正义”和“不完全艺术正义”。完全艺术正义和不完全艺术正义的异同在于,它们皆有分配性正义这一要素,但前者同时又有补偿性正义这一要素,而后者却付之阙如。由此可知,它们是两个相对的却又是内涵大小不一的概念。
简言之,分配性正义是合理分配权利的原则。有些权利是基本权利,譬如生命权和财产权等,这些是在人群中平均分配的也即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有些权利是非基本权利,譬如残障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有获得社会的特殊关照或保护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因人群而异,并非每个人都能享有。法律等强制性规范如果体现了合理分配权利的原则,那便是严格意义或广泛意义上的“善法”。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都会依照善法行事,但也必有极少数成员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违背“善法”,从而损害他人(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这就需要补偿性正义予以救济。
补偿性正义从分配性正义中衍生而来,如果说分配性正义是合理分配权利的原则,那么补偿性正义便是维护正当权利的原则。“善法”既体现前一种原则,也体现后一种原则。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说:“[……]矫正的公正也就是得与失之间的适度。”(138)他所谓的“矫正的公正”也即后世学者所谓的“补偿性正义”。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史纲》指出,亚里士多德将“正义”拆分为两类:“分配性的正义”和“补偿性的正义”(60)。作为严格意义上“善法”的法律主要通过矫正正当权利被侵犯而导致的恶果来维护正当权利,而作为广泛意义上“善法”的法令和规章同时通过矫正正当权利被侵犯而导致的恶果和弥补因维护他人正当权利而导致的损失来维护正当权利。分配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是笔者区分完全艺术正义和不完全艺术正义的重要哲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依据。
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好莱坞电影往往以分配性正义观念即正确的道德态度和立场来描述人的善恶行为及其冲突,也即在呈现与善恶行为及其冲突相关之情节的过程中“褒善贬恶”,然后,它们又往往以补偿性正义观念来建构“赏善罚恶”的情节,此类情节大多出现于结局处。譬如元代关汉卿杂剧《鲁斋郎》。鲁斋郎是一个“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恶霸,自称“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关汉卿,“包待制”369、358)。他的一大罪恶行径是“强夺人家妻女”。在该剧第一至第三折中,作者详尽地描述了鲁斋郎任意霸占银匠李四的妻子张氏和六案都孔目张珪的妻子李氏,从而导致李张两家妻离子散的过程。通过呈现如是情节以及“全失了人伦天地心,倚仗着恶党凶徒势”等大量曲词和说白,作者不仅抨击了鲁斋郎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权贵,而且还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以元朝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阶层。如果说前三折是批判元代权贵侵犯他人生命权、财产权、人身安全权和自由权的罪恶行径,揭露元代社会之大夜弥天,那么第四折则通过惩罚鲁斋郎而警戒了元代为非作歹的权贵们。在这一折中,包拯“用心”“设智”骗过了皇帝的眼睛,将“苦害生民”“恶极罪大”的鲁斋郎送上了断头台(358—82)。
绝大多数与善恶行为及其冲突有涉的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好莱坞电影皆有“褒善贬恶”和“赏善罚恶”这两层内容,就彰显完全艺术正义而言,它们是最为典型的艺术族群。也由此可知,作为形而上之道的完全艺术正义是由作为形而下之器的“褒善贬恶”和“赏善罚恶”彰显出来的。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某一类情节的“赏善罚恶”是笔者对以下三种情节的省称:施恶者有恶报,行善者有善报,无辜者无恶报。当人们非常顺口地说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已基本上忽视了这第三种情节。所谓无辜者无恶报,也即在不同程度上矫正无妄之恶报,这可是不少彰显完全艺术正义之作品的主要情节,譬如清代蒲松龄之《胭脂》(收录于《聊斋志异》)。
在这一短篇小说中,山东东昌府秀才鄂秋隼无意间卷入一桩杀人案,被指控图奸杀人。严刑拷打之下,他“不堪痛楚,以是诬服”。这桩由县令审定的冤案后为济南知府吴南岱所推翻,但吴同时错认书生宿介为凶手,故屈打宿介以成招,第二个冤案最终为山东学使施愚山所推翻。鄂秋隼无辜,自然不该受恶报,宿介无大恶,自然不该受大恶报,这便是矫正无妄之恶报。尽管这篇小说不乏施恶者有恶报,但其情节之重心无疑是无辜者无恶报。不过,矫正无妄之恶报并不意味着可以补偿所有的损失。宿介有小恶,受皮肉之苦似在情理之中;而鄂秋隼无纤芥之恶,受皮肉之苦则完全是无妄之灾,错误已经铸就,如此损失完全无法补偿。窦娥的冤案最终也被平反,这同样是矫正无妄之恶报,可她丢了性命,这样的损失又该如何补偿?
在这三种情节中,施恶者有恶报出现的频度最高,行善者有善报出现的频度最低,介乎其间的是无辜者无恶报。何以如此?这与完全艺术正义的生成原因密切相关。当社会正义某种程度上的匮乏无法(完全)满足人们客观意义上的安全需要,因而也无法(完全)满足人们主观意义上的安全需要(安全感需要)时,人们就不得不直接从完全艺术正义甚至宗教正义中满足自己主观意义上的安全需要,即获得虚幻的安全感。在马斯洛看来,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虚拟补偿,因为安全感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是致病的,“所以他就被驱使去弥补这一致病的匮乏”(197)。在现实生活中,最容易破坏人们安全感的是有人施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其次是有人无辜却遭受丧失生命和自由之灾祸。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对社会正义匮乏之补偿的完全艺术正义必然会把重点置于施恶者有恶报和无辜者无恶报之上。惟其如此,才能在较大程度上给人以安全感。当然,行善有善报同样也很重要,它可以给行善的人尤其是以善抗击恶的人以道德安慰,从而鼓舞他们间接或直接地阻遏恶的力量。但比之于前二者,它毕竟是次要的。
大异其趣的是,20世纪之前的西方戏剧和小说、清末以来的中国戏剧和小说也往往以分配性正义观念即正确的道德态度和立场来描述人的善恶行为及其冲突,但大多仅有“褒善贬恶”的情节,而缺乏以补偿性正义观念建构起来的“赏善罚恶”情节。就彰显不完全艺术正义而言,它们(尤其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最为典型的艺术族群。试以美国H.B.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年)为例阐述之。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最善良的奴隶是汤姆叔叔,最能善待奴隶的奴隶主是奥古斯丁·圣·克莱尔,最能善待奴隶的奴隶主家属是“几乎像个天使”的伊娃(伊万杰琳·圣·克莱尔),然而结果呢?他们无一有善终。除了在两个混血女奴的捉弄下邪恶凶残的奴隶主西蒙·雷格里无节制地酗酒以至精神失常外,其他同样邪恶凶残的奴隶主、奴隶主帮凶、奴隶贩子和逃奴猎手却无一遭受恶报。但是,这部长篇小说却无情地揭露了美国蓄奴制骇人听闻的真相,深刻地批判了其令人发指的罪恶。当得知奴隶主亚瑟·谢尔比为化解自己庄园的财务风险而将汤姆叔叔和小哈利卖给了黑奴贩子丹·黑利时,谢尔比夫人当着她丈夫的面说:“这是上帝对奴隶制的诅咒!——奴隶制是最恶毒最该诅咒的东西——对主人是诅咒,对奴隶也是诅咒”(斯陀夫人35)。当雷格里准备将汤姆叔叔折磨至死时,作者感慨道:“血腥残暴的景象使人心惊胆战。有人敢做的事别人却不敢听。和我们同为人、同为基督徒的人们所受的痛苦,即使在密室中也无法说出来,因为它会折磨人的灵魂呀!然而,啊,我的祖国!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法律的庇护之下做出来的呀!啊!基督!你的教会几乎是沉默地看着这一切的呀!”(426)这部小说以其对蓄奴制的血泪控诉震撼了美国社会,也震撼了全世界,它是小说版的《解放黑奴宣言》。
1903年是中国小说史的重要年份,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和金天翮《孽海花》的部分章回均于该年刊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这四部长篇视作“谴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并在概述嘉庆以来中国时局的基础上对此类小说做出了总体性评价:“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至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291)。
严格地说,彰显不完全艺术正义的中国小说就是从这四大谴责小说起步的。不过,此时的中国小说依然处在从传统至现代的转型过程之中,尽管吴沃尧创作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但他也创作了《果报》《德清冤妇案》和《厉鬼吞人案》等不少彰显完全艺术正义的笔记小说。即使在这些基本面为彰显不完全艺术正义的谴责小说中,偶尔也会出现彰显完全艺术正义的情节,如在《老残游记》续集第八回中,老残在地狱中目睹施恶者遭受酷刑。在中国小说史上,描述地狱酷刑的作品所在多有,如南朝齐王琰《赵泰》、明瞿佑《令狐生冥梦录》、明李昌祺《何思明游酆都录》、明冯梦龙《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和清蒲松龄《续黄粱》等。时至20世纪初,刘鹗居然还在描述这种超自然恶报情节,这实在是传统小说界的惯性使然。
当社会正义某种程度上的匮乏无法(完全)满足人们主客观意义上的安全需要时,有些艺术家力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褒善贬恶”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并进而鼓动他们改造社会,从而促成社会正义(在更大程度上)的实现。如同《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四大谴责小说,绝大多数彰显不完全艺术正义的作品都把“贬恶”放在比“褒善”重要得多的地位,易言之,在这类作品中,揭露和批判恶行要远多于彰明和褒扬善行。之所以如此,乃因为恶行蔓延必使人间变成万劫不复的地狱,比之于善行无法发扬光大,它更是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社会正义的障碍。鲁迅《〈自选集〉自序》说:“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468)鲁迅所设想的不完全艺术正义对于社会产生的正面效应曾经并将继续为艺术实践活动所证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Stowe,H.B.”条指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刊载和出版“在启发民众的反奴隶制情绪方面起过重大作用,被列为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之一”(239)。同样促进了社会正义之实现的是美国社会主义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The
Jungle
,1906年)和韩国电影《熔炉》(首映于2011年9月22日),前者促使美国国会于1906年6月30日通过《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后者促使韩国国会于2011年10月底通过《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在艺术正义问题上,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好莱坞电影与20世纪以前的西方戏剧和小说、清末以来的中国戏剧和小说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前者偏重完全艺术正义,而后者则偏重不完全艺术正义。当然,倾向性并不意味着绝对性。宋南戏《张协状元》、清吴敬梓《儒林外史》、获奥斯卡五个奖项的好莱坞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年)等皆彰显了不完全艺术正义,但这类作品总体上比例很小。莎士比亚《麦克白》、英国哥尔德斯密斯长篇小说《威克菲尔德牧师传》(1764年)、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以及18、19世纪的大多数欧洲情节剧(melodrama)等皆彰显了完全艺术正义,但这类作品总体上比例也不大。在不少人心目中,20世纪之前彰显完全艺术正义的西方作品比例很小,这恐怕是一种错觉。由于西方艺术理论的精英主义传统,那些作品在戏剧史和小说史的书写中大多被遮蔽,众多的情节剧就是著例。
二、完全艺术正义与“诗的正义”
完全艺术正义也即西方人所谓的“诗的正义”。1678年,英国批评家托马斯·莱默推出其《上一个时代的悲剧》(The
Tragedies
of
the
Last
Age
Consider
’d
)。该专著说:“在历史上不难发现,正义者和非正义者往往遭遇相同的结局,美德被遏制,而邪恶却登上了王位;他们(指西方古代的作者)认为,这些过去确实存在的事实是不完美和不恰当的,以至于很难阐明他们本想阐明的普遍而永恒的真理。在历史上还不难发现,这种不公正的赏罚分配确实令最具智慧的人困惑,令无神论者诋毁神圣的天意,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如果一个诗人想要寓教于乐,就必须使正义完全得到伸张。”(Zimansky22)这里的“正义”(justice)也即该专著所说的,相对于“历史正义”(historical justice)的“诗的正义”(poetical justice,为后世学者修正为poetic justice)(27)。结合该专著的其他论述,显见上引这段话阐明了以下三个重要观点,并隐性地涉及了支撑这些观点的论据:第一,现实世界中未必都是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甚至相反的情况亦时常出现,但这不能成为在戏剧作品中呈现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甚至善有恶报、恶有善报之情节的理由。“诗人应该是一个哲学家而非史料编纂者”(Zimansky62);“诗是想象力的孩子”,“想象力之于诗,如同信仰之于宗教”,想象力是“翱翔于理性之上”的(20)。因此,即使世上“很多事情天然地令人不快”,但诗人在“妥善模仿”时,依然可以虚构出“令人畅快的事情”(23)。
第二,为了寓教于乐,一个戏剧诗人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中公正地分配赏罚,也即给善行以善报,给恶行以恶报。“戏剧通常被称为美德的学校”,它就是“为传授道德观”而设的(Zimansky17)。当“历史[……]既不适合教导人,也不容易愉悦人”时,诗人“就不能依赖历史,把它作为(创作的)样本,而应该对历史去粗取精,使之升华,从而创作出更具哲学意味、比历史更准确的作品”(23)。莱默的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完全艺术正义而非整体意义上的艺术正义才能培育人们的道德感——是西方艺术理论史上几乎所有的完全艺术正义论者的共同偏见。
第三,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不仅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而且也是基督教上帝的神圣旨意。诗人应该描述这样的情节,因为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是“神祇的代言人”(Zimansky19—20),今天的诗人也应该成为基督教上帝的代言人。“如果(诗人所虚构的)人世生活几乎不合全能的上帝之意愿,(也就是说)上帝神圣的意图可能未被(诗人)领会,那么,他们(仅此而言)将永远不会被原谅,也肯定不会被理解。”(22—23)约140年后,叔本华将“诗的正义”说贬为“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或者基本上是犹太人的”学说,并非没有来由(333)。
英语国家的文学或美学辞典皆有poetic justice这一条目,其中权威者如J.A.Cuddon等的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Chris Baldick的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M.H.Abrams的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它们如是界定“诗的正义”:它“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好人受到应有的奖赏”(Cuddon681)。“作为一种道德安慰,(它)分别将幸福和不幸的命运赋予善良和邪恶的人物。”(Baldick261)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安排:[……]让各种人物分别获得与其善行或恶行相称的尘世间的奖赏或惩罚”(Abrams230)。美国当代学者琼C.格雷斯曾经指出:“诗的正义并非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原则而是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隐含的信条。”(Grace43)诚哉斯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诗人们和说故事的人在关于人的重大问题上说法有错误。他们说,许多不正义的人快乐,正义的人痛苦;还说,做不正义的事有利可图,只要不被发现;正义对别人有利对自己有害。这些话我们应该禁止他们讲,应该命令他们去歌唱去述说与此相反的话,[……]我们一定要先找出正义是什么,正义在本质上对正义的持有者有什么好处[……]。弄清楚这个以后,我们才能在关于人的说法上取得一致意见,即,哪些故事内容应该讲。”(张竹明译85)柏拉图的意思是说,艺术作品就应该以褒善贬恶和赏善罚恶这双重情节来彰显完全艺术正义。
柏拉图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倡导完全艺术正义?他的思路如下所述:人大多趋利避害,如果艺术作品一味地表现“许多不正义的人快乐,正义的人痛苦”,一味地宣扬“做不正义的事有利可图,只要不被发现;正义对别人有利对自己有害”,那么,还有多少人愿意做好人,还有多少人不会做坏人?用《理想国》中阿得曼托斯的话来说,那便是“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选择正义,而舍弃极端的不正义呢”(郭斌和等译54)。这与冯梦龙的思路可谓异曲同工。《人兽关叙》曰:“德而无报,谁相劝于树德?怨而无报,谁相惩于造怨?”(40—41)此语意即,若行善而无善报,有多少人还会劝告他人多行善;若施恶而无恶报,有多少人还会警戒他人勿施恶。如果略作推理,我们应该可以说:若行善而无善报,有多少人还会常行善;若施恶而无恶报,有多少人还会不施恶。由此可知,完全艺术正义并非——如五四以来的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只有负面社会效应而无正面社会效应。要之,尽管诗的正义这一概念为莱默所创立,但这种思想的首创权无疑属于柏拉图。
第一个挑战柏拉图完全艺术正义思想的是亚里士多德。无论中西,彰显完全艺术正义的主要是“罚恶”而非“赏善”的情节,但《诗学》首先从“能引起哀怜和恐惧”这一“悲剧摹仿的特征”出发否定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由福落到祸”的情节(朱光潜84—85);其次从观众审美趣味的角度贬损赏善罚恶情节:“例如《奥得赛》就用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双重情节。由于观众的弱点,这种结构才被人看成是最好的;诗人要迎合观众,也就这样写。但是这样产生的快感却不是悲剧的快感。这种结构较宜于用在喜剧里”(85)。问题的关键在于,亚氏不仅认为悲剧不应有赏善罚恶情节,而且还认定在戏剧诗、史诗、抒情诗中,戏剧诗尤其悲剧诗是等次最高的诗之体裁(《诗学》13、107)。受其悲剧观和诗的等次说的双重影响,后世的西方批评家大多贬斥赏善罚恶情节,而在戏剧和小说创作中避免这类情节竟成为后世西方艺术家的集体无意识。
诗的正义说问世之后,在赏善罚恶情节和诗的正义问题上形成两大阵营:赞同的有约翰·丹尼斯、萨缪尔·约翰逊、理查德·莫尔顿等;反对的有高乃依、约瑟夫·艾迪森、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也许我们可以分别将他们称为艺术正义问题上的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艾布拉姆斯曾不无感慨地说:“自莱默生活的年代直至今日,对莱默一味兜售的诗的正义观念,重要的批评家或文学作者要末不接受;要末有高度保留地接受。”(Abrams230)这无异于说后一阵营远比前一阵营强大(前一阵营不仅人数少,而且其中也仅有丹尼斯和约翰逊是重量级批评家)。后一阵营的强大还表现在——仿佛是亚氏挑战柏拉图的重演——他们往往主动出击,批判前一阵营的诗的正义观念。
他们批判诗的正义的思想武器不外乎以下四种:模仿说内含的艺术真实观、与艺术真实观密切相关的认识功能说、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悲剧观、黑格尔的“永恒正义”说。进入20世纪后,这些同样是王国维、胡适、鲁迅和朱光潜等批判完全艺术正义的思想武器。浏览一下叔本华抨击约翰逊的一段话,也许能让我们对这些批判的武器有一点感性认识:“要求所谓诗的正义,这是来自对于悲剧本质的全盘误解,事实上,是对于世界本身性质的误解。撒缪尔·约翰生博士对莎士比亚某些剧本的批评,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样的见解,暴露了这种见解的肤浅,因为他十分天真地哀叹这些剧本完全忽视了诗的正义。[……]只有那种肤浅的、乐天派的、清教徒理性主义的观点,或者基本上是犹太人的人生观,才会要求诗的正义,并在满足这一要求上找寻自我安慰。”(叔本华332—33)
最早引入诗的正义这一术语的中国学者当属王国维。受叔本华和黑格尔之影响,他在《红楼梦评论》(1904年)中说:“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此足以知其非诗歌的正义,而既有世界人生以上,无非永远的正义之所统辖也。故曰《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11)然而,使用此术语最多者当为朱光潜。他的《悲剧心理学》(1933年,张隆溪译)、《文艺心理学》(1936年)和《西方美学史》(1963年)等主要著述中多有“诗的公道”的踪影。鉴于王国维和朱光潜在文学和美学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一般来说,被他们使用过的西方文学或美学术语也为从事文学或美学研究的学者所熟知,但“诗的正义”似乎是一个例外。盖原因有二:其一,尽管英语国家的文学或美学辞典几乎都专辟poetic justice这一条目,但没有一部中国相关辞典有“诗的正义”的条目。这一现象折射出五四以来我们对完全艺术正义的偏见。其二,poetic justice曾被汉语学者译为或转译为“诗的正义”“诗歌的正义”“诗的公正”“诗的公道”“诗的报应”“诗意的公道”“诗歌国的正义”“诗学正义”“诗性正义”“文学正义”和“文艺中的正义”等。这形形色色的译词不易让人以为它们同出一源,不易让人以为它们指称的是同一种艺术现象。
无论中西,时下使用诗的正义这一术语的多为“法律与文学”的学者而非文学或其他艺术的学者,不过他们往往误用这一术语,这其中甚至包括大有名声的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她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把poetic justice作为大而统之的“艺术正义”而非“完全艺术正义”来使用,显见她并不知道此术语的确切所指。其实,这也是中国“法律与文学”学者经常进入的误区,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对此做出误判:“让我们先来看看努斯鲍姆提出的诗性正义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就学术渊源来说,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继承了休谟和亚当·斯密曾经提出的旁观者的正义”(《诗性正义》15)。“诗性正义”是努斯鲍姆“提出”的吗?如前所述,莱默的专著出版于1678年,而休谟和亚当·斯密则分别生于1711和1723年,“诗性正义”何以能够“继承”他们的“旁观者的正义”?
三、经验性与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
完全艺术正义又可细分为两种类型:“经验性完全艺术正义”和“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它们是完全艺术正义的类型,自然也就是艺术正义的亚类型。“超验的”(transcendental)有两种主要释义,一是宗教上的“超自然的”(supernatural),另一是哲学上的“先验的”(a priori),笔者在宗教意义上使用“超验的”一词。
如果说经验性完全艺术正义是由自然的力量(主要是人的力量)主导的褒善贬恶并进而赏善罚恶的情节彰显的完全艺术正义,那么,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是由超自然的力量(主要是鬼神的力量)主导的褒善贬恶并进而赏善罚恶的情节彰显的完全艺术正义,是借助宗教正义(并非莱布尼茨《神义论》所谓的“神义”)而实现的完全艺术正义。前者是再现型的完全艺术正义,是符合客观世界形式,遵循客观世界逻辑的完全艺术正义;后者是表现型的完全艺术正义,是疏离客观世界形式,违背客观世界逻辑的完全艺术正义。如前所引,艾布拉姆斯将“诗的正义”界定为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分别获得与其善行或恶行相称的尘世间的(earthly)奖赏或惩罚”(Abrams230)。earthly一词表明,他无意间忽视了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的存在。
一般来说,经验性完全艺术正义远多于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不过,彰显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的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数量巨大,如唐传奇《霍小玉传》《谢小娥传》和元杂剧《窦娥冤》《盆儿鬼》等。关汉卿《窦娥冤》中有一段情节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便是窦娥的“三桩儿誓愿”。窦娥在临刑前说,“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在此后的剧情发展中,这三桩誓愿竟然一一应验。如果说楚州三年亢旱(楚州地处淮南,却“三年不雨”)在现实生活中还略有可能性的话,那么,六月雪(阴历六月即“三伏天”,却“下三尺瑞雪”)几乎没有可能性,血溅白练(血溅旗杆上的白练,却无一点“滴在地下”)完全没有可能性(197—202、206—207)。这不能不说是神祇显示的奇迹。如果说“神迹”仅仅表明神祇对这一冤案的态度,从而预示着伸张正义的极大可能性,那么,窦娥遇难三年后发生的“冤魂诉冤”则使伸张正义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在中国戏曲和小说中,“冤魂诉冤”这一情节模式大约有三种子模式,即托梦诉冤、遗鬼迹诉冤和当面诉冤。当窦娥之父窦天章以“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身份到楚州“审囚刷卷”(复审刑案)时,窦娥竟然把这三种诉冤方式全用上了:她先是“托一梦”与其父亲,并在梦中做哭诉状;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其父不打算细看,因而已“压在文卷底下”的关于“窦娥药死公公”(其父并不知她已改名为“窦娥”)的案卷“翻在面上”;最终向其父当面诉说了她蒙冤遭难的全部经过。经窦天章认真复查,案情终于水落石出,张驴儿和赛卢医等均受到程度不等的严厉惩罚(202—11)。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荷马《奥德赛》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等以一些超自然的赏善罚恶情节彰显了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自中世纪始直至20世纪之前,此类作品在西方数量奇少。不过,同时作为文学文本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似乎代为发挥了它们的功用。但丁由《地狱》《炼狱》《天国》三部曲连缀而成的《神曲》是这一时期彰显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的、空前绝后的经典之作。
在《神曲》中,但丁在维吉尔或贝雅特丽齐的引导下先后游历了地狱、炼狱和天国,亲眼目睹或亲耳听闻了施恶者或违背基督教教义者之亡魂于地狱遭受苦刑、有七宗罪的基督徒之亡魂于炼狱经受磨练从而消除罪孽并获得新生、行善者或为基督教事业做出贡献者之亡魂于天国享受幸福生活的情景。《神曲》的思想资源是基督教的教义,它的善恶观和正义观均来自后者,这是它的复杂之处。哈罗德·伯尔曼说:“在即便是最富神秘色彩的宗教里面,也存在并且必定存在着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关切。任何一种宗教都具有并且必定具有法律的要素——确切地说有两种法律要素:一种与共同信仰某一特定宗教之群体的社会活动有关,另一种则关系到宗教群体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更大群体的社会活动。”(70)这番话若换成佛教的说法,那便是“一切世间法,即是出世间法”(《大方广佛》637)。从《神曲》“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关切”或“世间法”的因素来看,它在西方艺术史上仍不失为彰显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的最重要的作品。
20世纪40年代以降,好莱坞产出了大量彰显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的电影,它们主要是由《蝙蝠侠》和《超人》为其开端的大多数超级英雄电影(有些仅彰显了经验性完全艺术正义)。这是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堪与希腊和罗马多神教相媲美的西方造神运动。
如同彰显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彰显此类正义的西方史诗(《神曲》也不例外)和电影同样把重心放在“罚恶”而非“赏善”上,不同的是,中国的艺术作品同时以冤魂报冤、冤魂诉冤、冤魂司神职、神罚、神启、神迹这六种超自然恶报情节模式来彰显此类正义,而西方的艺术作品基本上只用神罚这一种情节模式。如是差异折射的是西方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中国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差异。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分别简要地描述了这两类宗教的不同特征:“有自己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它自成一种社会制度,有其基本的观念和结构。”“其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35)正因为分散性宗教的开放性特点,因而它吸纳世俗因素和制度性宗教因素的冲动和能力非常强大。
公元313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此后,基督教逐渐取代罗马多神教而成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方宗教。如果说基督教是典型的制度性宗教,那么此前的希腊多神教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罗马多神教也即非典型的制度性宗教。不管西方哪一种制度性宗教,它们基本上只有神罚这一种超自然恶报情节模式。使徒保罗说:“朋友们!不要为自己复仇,宁可让上帝的忿怒替你伸冤,因为圣经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定报应。’”(321)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文本最多也只会呈现由神罚和神迹组合而成的情节,如在《出埃及记》第14章中,耶和华以一阵强烈的东风吹开海水,把红海某处的海底变成了干地。当摩西领着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后,耶和华又使海水合拢,淹没了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宗教文本如此,深受其影响的西方艺术文本自然也会把神罚作为唯一的超自然恶报情节模式,今天的超级英雄电影依然承袭了这一情节模式,只不过以超级英雄这样的类神祇取代了宙斯和耶和华这样的神祇而已。
尽管中国有着佛教、道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三种制度性宗教,但在小说和戏曲创作逐渐繁荣的唐、宋、元、明、清,真正主宰了中国民间社会,也深刻影响了艺术创作的却是熔佛教、道教、宗法性传统宗教之因素甚至儒家的伦理观和民间的迷信于一炉的民间信仰这一分散性宗教。金耀基等指出:“佛教、道教作为制度性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为分散性的民间信仰提供了精神资源,更使得宗教的民间形态完全可以将上层意识形态的控制放在一边,以其分散而又灵活的方式展现宗教在中国社会不竭的生命力。”(杨庆堃12)为民间信仰提供精神资源的远不止释道两家。元代孔文卿杂剧《东窗事犯》写岳飞等被害和秦桧在阴间遭报应事。该剧既有地藏王化身为呆行者叶守一,在灵隐寺斥责秦桧陷害岳飞之罪恶行径的情节,又有岳飞等冤魂“奉天佛牒、玉帝敕”和“东岳圣帝”之命向宋高宗托梦,诉说自己为秦桧所害之冤情的情节。多种宗教之神祇在同一部戏曲和小说中精诚合作,这实在是中国古代故事性艺术的常态,由此可见民间信仰对这类艺术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西方的制度性宗教为了突出神祇在伸张正义中的作用而将其确定为唯一的罚恶主体,那么中国的分散性宗教则会“动员”三种力量一起罚恶。这三种力量分别是冤魂、神祇和以包公为代表的、既能聆听冤魂的申诉,又能接受神祇启示甚至直接领受神祇旨意的清官。有必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以及胡适和梁漱溟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汉族是一个没有宗教感的民族(杨庆堃2—4)。但为何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中的超自然恶报情节的比重和模式远大于或远多于西方同时期的小说和戏剧?如果不建构起分散性宗教这一视角,我们恐怕很难解释这一现象。
不过,在西方的艺术作品中偶尔也能看到非神罚类的超自然恶报情节。1990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人鬼情未了》(Ghost
)曾获第6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它描述了年轻银行职员萨姆·惠特与女友莫利·约翰逊情深意笃。萨姆的同事卡尔·布鲁纳为扫除窃取银行巨款的障碍,雇杀手害死萨姆。成了鬼魂的萨姆心有不甘,于是,他通过一个通灵者,让莫利知晓了自己的冤情。莫利去警察局报案,以求将卡尔绳之以法。警察们哪敢相信如此“荒唐”的案情。万般无奈之下,萨姆只得向纽约地铁中一个法术高明的老鬼学习,久而久之,遂修炼得一身人间行走的好本领。最终他既保护了莫利,保住了巨款,又使卡尔及其所雇的杀手遭受了恶报。如同萨姆的鬼魂,出品于2000年的好莱坞电影《危机四伏》(What
Lies
Beneath
)中的麦迪逊的鬼魂也是先试图通过中间人向公权力申诉,遭阻之后才动用了“私刑”,换言之,先试图“冤魂诉冤”,遭阻之后才“冤魂报冤”。这两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近三十年来西方艺术家在创作彰显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的作品时汲取世界其他地区宗教资源的努力。四、经验性与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
如同完全艺术正义,不完全艺术正义也可细分为两种类型:“经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和“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当然它们也是艺术正义的亚类型。如果说经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是一般意义上的、由人的力量主导的褒善贬恶情节彰显的不完全艺术正义,那么,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是特殊意义上的、由鬼神等超自然力量主导的褒善贬恶情节彰显的不完全艺术正义,是借助宗教正义而呈现的不完全艺术正义。前者是再现型的、与客观世界的形式和逻辑相符的不完全艺术正义;后者是表现型的、与客观世界的形式和逻辑相悖的不完全艺术正义。如同经验性完全艺术正义,经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也极为常见,故无须以例释义;至于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就未必为人们熟知了,试引几例以详之。
清毛祥麟《墨馀录》中有《席某返魂》:江苏吴县“席某”与同乡“某”在淮北合作经商十余年,因经营有方,故所获甚丰。两人交情深厚,席某之女已与某之次子订婚。没料想席某突然在客栈暴病而亡。某不仅为他料理后事,扶送其棺柩归故里,而且还将详细记载历年经营所得的账本及钱财交还席家。某因此博得诚实无欺的好名声。一日,席某之魂附在其女儿身上,语其妻曰:“某昧良以伪册示汝,匿银若干,汝固不知也。”“我归已久,欲与汝一言,而无可凭者,因恨某以人死无据,欺汝孤寡,必欲与之理论,故假女体,亦不得已也。”随后他便给某写了一封信函,邀其前来席家核算账目。某得此有着席某字迹的信函,惊恐万分,但无奈之下只能赴席家。席某之“女”神态严肃地对某说:“余与君情同胶漆,我死,意必以孤寡累君,何骨肉未寒,而情同陌路耶?”接着,便按账目逐一指出,应该给多少,而实际少给多少。核对完毕,“女”问某何以昧良侵吞?某羞愧至极,无言以对。“女”最后说:“我念旧好,不诉冥曹,亦不以为怨。倘此后再有私心,我能祸君,无贻后悔,今已证明,请君自便。”(毛祥麟310—11)显然,《席某返魂》仅有超验性“贬恶”情节而无超验性“罚恶”情节,它彰显的无疑是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
如果说《席某返魂》中对某之恶行的谴责来自鬼魂,那么,清代辜澧《王老虎传》(收录于清王葆心辑《虞初支志》)中对王老虎之恶行的谴责则来自神祇。江西资溪“有王姓者,以盘剥起家,人号为王老虎。年六十,蓄二艾妾,无子,日敲木鱼诵《三王经》自忏悔。一日,邻居素号活无常,经其门,闻木鱼声,笑曰:‘死期将至,诵经何益!’无常言祸福多奇验,王闻之色变,遂问故。告曰:‘尔生平得分外财三千,犯冥谴,某日当死。’王不觉汗下,私念:果死,妾终为人有,资虽多,亦无所用。即刻日嫁二妾,还借者券,免其偿。制衣衾棺椁皆具。”一日,在与朋友话别后的归家途中,见一妇人投河,王大呼曰:“有能救者,赏金若干。”救起后,问其何故轻生。原来某盐商贪恋此妇美色,故设一圈套:借钱给其丈夫,且从不要求他偿还,等到积年利重,无法偿还时,该盐商便要求以其妻抵偿。王携银子登该盐商门,盐商居然不受。“王怒,以头触石,血淋漓不止,骂曰:‘某借若金,偿如券足已,而必以人偿,是媒祸也。我三日当死,死若家,等死耳(同样是死)。’即拔利刀将自戕。商惧,纳金出券固谢。”时至应该离世的那一天,王“沐浴更衣,具酒食宴戚友。既罢,端坐厅事。日既暮,挑灯达旦,卒无他异。始疑无常赚(诳骗)我,召之来,将让(责备)之。无常蹩而前,怨曰:‘尔旬日闲散金三千,已抵悖入罪,又救人一命,全人夫妇,且增寿一纪,有一子矣。冥官以予多言泄事,予重杖,创犹未愈。’裸而示之,信。王自后力行善事,得娶妾,果得一子,年七十乃死。”(辜澧511—12)
这两篇笔记小说中的某和王老虎皆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但最终也都主动或被动地赎回了自己的罪孽甚至自发地行善积德,否则,他们都将遭受超自然恶报,因而这两篇小说更像是彰显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之小说的“未完成版”。其实,这正是它们的样本意义之所在,因为绝大多数此类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中的犯罪孽者头上都悬着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明代还真有一篇彰显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的文言小说,经过改编却成了彰显完全艺术正义的戏曲和白话小说。
明代邵景詹《觅灯因话》中有《桂迁梦想录》:施济两次救少时同学桂迁及全家于危难之际,桂家因此避免了妻离子散和流落街头的厄运。但桂家在施济提供给其居住的施家祖传地产上掘得大量白银,却昧心侵吞。更可恨的是,当施济去世后施家家道中落时,桂家不仅赖帐不还,而且还以种种言行侮慢施济妻儿,从而导致施妻郁抑而亡。几年后,桂迁遭受同乡刘生诈骗,且损失五千多两银子。就在桂迁拟刺杀刘生的前夜,忽得一噩梦:其妻、二子和小女“皆成犬形”。经此一梦,桂迁幡然悔悟,且尽力采取补救措施,后桂家果然未得恶报。时至晚明,李玉和冯梦龙分别将此小说改编成传奇《人兽关》和话本小说《桂员外途穷忏悔》(《警世通言》)。《桂迁梦想录》与这两部作品最大的差异是,前者噩梦未成真,后二者噩梦皆成真。这一案例表明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与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其实仅相距一步之遥。
并非所有彰显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的作品都是彰显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的作品之“未完成版”。明代周朝俊传奇《红梅记》有两条故事线,其中之一描述了“李慧娘”的故事,这一故事改编自明瞿佑《剪灯新话·绿衣人传》中“绿衣人”和贾似道另一姬妾之故事,而孟超1961首演于北京的昆剧《李慧娘》则改编自《红梅记》中李慧娘的故事。这两次改编使关于李慧娘的叙事越来越趋向于彰显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
“绿衣人”和贾似道的另一姬妾无辜被害后并未以鬼魂之身当面指责过贾似道,但《红梅记》中的李慧娘无辜被害后却这样做了。当年李慧娘被害的起因是,随贾似道游西湖时,见站在断桥上的裴舜卿一表人才,便情不自禁地叹曰:“呀,美哉一少年也!”(周朝俊4)故在第17出《鬼辩》中李慧娘鬼魂对贾似道说:“说的来教人痛杀。則他(指她自己)在断魂桥盼上个人清雅,少年郎瞥見了冷嗟呀。並不曾背地里通些情話,也下曾背人儿眼角眉梢去挑弄他。却怎生半声納采,一剑儿分花(指她自己被贾似道一剑斩杀)?”(83)如果说这还仅仅是“薄责”,那么,《李慧娘》中李慧娘鬼魂对贾似道说的那简直就是“痛斥”了:“你当相爷的,惯把冤狱安排下”(48),“你凭钻营,卖国害民,吃尽宰官粮”(49),“俺笑那君王无知昏庸,认你做好平章。你却向元兵称臣投降,任意诛杀,苦害善良,死后的李慧娘,全不怕你这贼丞相”(50)。说起《红梅记》的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还有一个情节也值得一提,即第24出描写大势至菩萨化身为一个疯癫的和尚,对贾似道说:“似道,非道,你荒淫残暴。”(124)
根据史实,《红梅记》第26出也叙述了贾似道在被押解至贬所的途中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一事,因此,这是一个经验性完全艺术正义与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相结合的戏曲。相形之下,《李慧娘》却是经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与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相结合的戏曲。在这出戏的第一至第五场中,裴舜卿等众多剧中人物以及还未沦为鬼魂的李慧娘对贾似道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无疑彰显了经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
无论是经验性完全艺术正义还是经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它们都是纯粹的,不掺杂超验因素的。相反,无论是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还是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它们大多不纯粹,大多掺杂着经验因素,因为描述社会生活的图景毕竟是艺术作品的基本取向。在《窦娥冤》第三折中,窦娥唱道:“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198)表面上是埋怨天地,实质是控诉黑暗的社会现实。我们应该记得,此时的窦娥还活在人间。
超验性完全艺术正义和超验性不完全艺术正义的生成有着诸多原因,然其中最大的原因无疑是力图赋予艺术正义以神圣性,从而彰显其“天道”的意味。伯尔曼《法律与宗教》说:“正义是神圣的,否则就不是正义的。神圣是正义的,否则就不是神圣的。”(105)“在最高层面,正义与神圣同为一物,否则,不仅所有的人,而且整个宇宙,乃至上帝本身都要罹患永久性的精神分裂症。”(126)这里的“神圣”绝非衍生意义上的而是实际意义上的神圣,因为伯尔曼明确地说过,“这种神圣性就是法律的宗教向度。”(141)尽管伯尔曼讨论的是法律正义,但将这番话用来阐明超验性艺术正义的生成原因之一并无任何不妥。
结 语
在通向艺术正义之腹地的道路上,横亘着四大路障:艺术正义的类型结构、生成原因、社会效应以及研究艺术正义的方法论,而其中位居首列的无疑是类型结构,因为不同类型甚至不同亚类型的艺术正义有着不同的生成原因、不同的正面或负面社会效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的是不完全艺术正义同样有着负面社会效应),用以研究它们的方法论也有不小的差异。研究任何一个略有复杂性的理论问题,我们需要的往往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谱系而非一个科学的概念,无奈西方批评家只奉献了诗的正义这一个概念(是否科学尚可再论),这也就是艺术正义的研究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根本原因。为讨论这一话题,本文陈述了不少中西艺术现象和艺术思想,不论你对此是否熟悉,若没有科学概念以及由此建构的理论框架,我们如何清晰地、富有逻辑性地来言说它们?无命名即不存在,任何艺术现象和艺术思想若不被科学概念和理论框架锚定,它们在人们的意识中实质上都是不存在的。由上述三点可知,破解艺术正义的类型结构问题是深入研究艺术正义的基础性或前提性工作,反过来说,无法破解这一问题,也就意味着无法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处。在试图破解这一问题的同时,本文也略微涉及了与此有着密切关联的不同艺术正义之生成原因、社会效应以及研究艺术正义的方法论。囿于篇幅,笔者无法对它们展开深入的探讨,而只能付诸另文。
注释[Notes]
① 关于国际学界在艺术正义研究方面的现状,可参阅H.Kabashima,et al.eds.The
Idea
of
Justice
in
Literature
(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GmbH,part of Springer Nature,2018)。这本论文集共收录了14篇论文,它们的作者分别是中国台湾、西班牙、德国、智利、葡萄牙、捷克、日本、巴西、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国家或地区“法律与文学”的学者,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② 该专著全名为The
Tragedies
of
the
Last
Age
Consider
’d
and
Examin
’d
by
the
Practice
of
the
Ancients
,and
by
the
Common
Sense
of
All
Ages
,in
a
Letter
to
Fleetwood
Shepheard
,Esq
。③ “永远的正义”即黑格尔《美学》所谓的“永恒正义”。
④ 参见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参见题名中有“诗性正义”的“法律与文学”的著作和论文,恕不一一列举。
⑥ 在但丁的文学想象中,第二至第九层地狱中的亡魂均遭受了程度不等的惩罚,不过其中有些生前并非施恶者,而仅仅是贪食者、创立、传播和信仰基督教所谓的异端邪说者、自杀者、倾家荡产者、渎神者、男同性恋者等。
⑦ 有些亡魂生前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行善者,他们只是虔诚的教士、修女、神父、圣徒、教会领袖、神学家、经院哲学家甚至在历史上毁誉参半的国家领袖。
⑧ 明代安遇时所编的《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中还真出现了包公灵魂直达天门,上奏玉帝的情节。明代《轮回醒世》中的《天曹两遣官》云:天曹知晓人世间的钟鸣远和吴小三“恶已盈贯”后,遂“批与陆巡按施行”和“批与熊知县施行”。清代袁枚《子不语》中的《阎王升殿先吞铁丸》云:刑部郎中闵玉苍“每夜署理阴间阎王之职”。他们竟然都可以同时在两种政法体制中做官。
⑨ 《人兽关》:桂迁之妻与一子投胎为犬;《桂员外途穷忏悔》:桂迁之妻与二子投胎为犬。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brams,M.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1999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iao Shenbai.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3.]——:《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 - -.Poetics
.Trans.Luo Niansheng.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62.]——:《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 - -.Politics
.Trans.Wu Shoupeng.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65.]《大方广佛华严经》,佛驮跋陀罗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Avatamsaka
Sutra
.Trans.Buddhabhadra.Taisho
Shinshu
Daizokyo
.Vol.9.Taipei:Shin Wen Feng Publishing House,1983.]Baldick,Chris.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Berman,Harold J.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Trans.Liang Zhiping.Beiji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3.]Cuddon,John Anthony,et al.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London:Penguin,1999.《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6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冯梦龙:“人兽关叙”,《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明代编第三集,俞为民、孙蓉蓉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
[Feng,Menglong.“Preface to Samsara between Human and Beast.”Compilation
of
Xiqu
Criticism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The
Ming
Dynasty
.Vol.3.Eds.Yu Weimin and Sun Rongrong.Hefei: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2009.]Grace,Joan C.Tragic
Theory
in
the
Critical
Works
of
Thomas
Rymer
,John
Dennis
,and
John
Dryden
.Cranbury: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75.关汉卿:“窦娥冤”,《全元戏曲》,第1卷,王季思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81—211。
[Guan,Hanqing.“The Grievance of Dou E.”The
Complete
Xiqu
Works
of
the
Yuan
Dynasty
.Vol.1.Ed.Wang Jisi.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9.181—211.]——:“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全元戏曲》,第1卷。王季思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358—82。
[- - -.“Lu Zhailang.”The
Complete
Xiqu
Works
of
the
Yuan
Dynasty
.Vol.1.Ed.Wang Jisi.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9.358-82.]辜澧:“王老虎传”,《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劝惩卷,陆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Gu,Li.“A Biography of Tiger Wang.”A
Categorized
Edition
of
Literary
Sketch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Persuasion
and
Warning
.Ed.Lu Lin.Hefei: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199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Xun.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9.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5.]——:“《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68—70。
[- - -.“Preface toA
Personal
Anthology
of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4.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5.468-70.]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Maslow,Abraham H.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3rd
Edition
).Trans.Xu Jinsheng,et al.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7.]毛祥麟:“席某返魂”,《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劝惩卷,陆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310—11。
[Mao,Xianglin.“Xi and His Partner.”A
Categorized
Edition
of
Literary
Sketch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Persuasion
and
Warning
.Ed.Lu Lin.Hefei: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1994.310-11.]孟超:《李慧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Meng,Chao.Li
Huiniang
.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62.]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Mill,John Stuart.Utilitarianism
.Trans.Xu Dajia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4.]玛莎·努斯鲍姆:“走向诗性正义”(代译序),《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0。
[Nussbaum,Martha C..:“Towards Poetic Justice (Preface to Translation).”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Trans.Ding Xiaodong.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0.1-20.]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Plato.The
Republic
.Trans.Guo Binhe,et al.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86.]——:《理想国》,张竹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
[- - -.The
Republic
.Trans.Zhang Zhuming.Nanjing:Yilin Press,2009.]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Pound,Roscoe.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
.Trans.Shen Zongling.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0.]亚瑟·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蒋孔阳译,《西方文论选》下卷,伍蠡甫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31—36。
[Schopenhauer,Arthur.“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Trans.Jiang Kongyang.Selected
Reading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Vol.2.Ed.Wu Lifu.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9.331-36.]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史纲》,熊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Sidgwick,Henry.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
.Trans.Xiong Min.Nanjing: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斯陀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王家湘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Stowe,Harriet Beecher.Uncle
Tom
’s
Cabin
.Trans.Wang Jiaxiang.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8.]《新约全书》,《圣经》(现代中文译本)。香港:联合圣经公会,1979。
[The
New
Testament
.The
Holy
Bible
(Today
’s
Chinese
Version
).Hong Kong:United Bible Society,1979.]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集》,第1册。周锡山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Wang,Guowei.“Commentary onThe
Story
of
the
Stone
.”Selected
Works
of
Wang
Guowei
.Vol.1.Ed.Zhou Xishan.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8.]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Yang,C.K.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Trans.Fan Lizhu,et al.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7.]周朝俊:《红梅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Zhou,Chaojun.The
Bower
of
Red
Plum
.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Zhu,Guangqian.A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Vol.1.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79.]Zimansky,Curt A.,ed.The
Critical
Works
of
Thomas
Rymer
.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