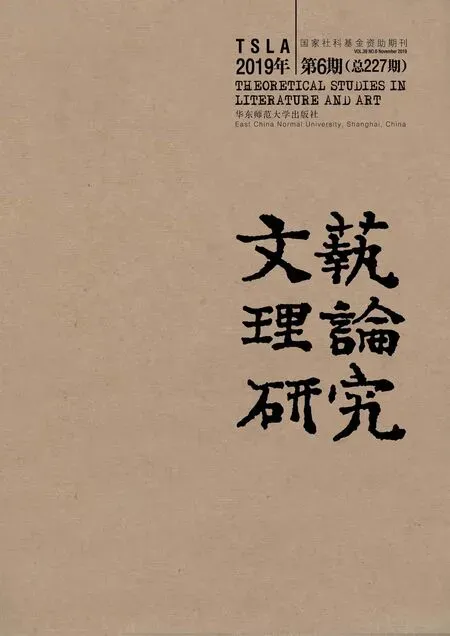论初盛唐诗人对言志缘情说的传述与发展
2020-01-01刘青海
刘青海
对诗歌本质的理论表述,在唐以前主要有言志和缘情两种观点。唐人对言志说和缘情说都有沿承,并且有所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两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与唐诗本身的发展形成较为明显的呼应关系。事实上,言志、缘情等诗歌本体论构成了唐代诗学最基本的理论,对唐诗创作有深刻的影响。对此问题,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的讨论。本文从回顾言志缘情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出发,以初盛唐诗文中对言志、缘情说的表述为研究对象,联系初盛唐诗歌的创作实践,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回应,并以此就正于学界方家。
一
有关诗言志的问题,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阐述。众所周知,“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孙星衍70),朱自清《诗言志辨》称其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194)。先秦时期,“诗言志”的诗学观念相当普遍,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杨伯峻1135)之说,《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王先谦133)。提法类似。已有学者对先秦时期“诗言志”说的发展历史作过这样的概括,“先为春秋行人赋诗所遵引,成为赋诗的原则,后来又经先秦诸子从各自的立场加以阐述,其在先秦时代又有着很广阔的绵延,可以说是先秦时代唯一的诗歌定义,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钱志熙6)。“诗言志”的具体内涵,在先秦时代也是有发展的,概括地说,就是其“志”的内涵有一个从表现群体意志向表现个体意志的演变过程。周代是政教国家建立的时代,存在乐教和诗教制度,“诗言志”是早期诗教体系的核心,因而“志”包含较多的政治与伦理内涵,具有群体之志的性质,对此学界已有论述。战国中期以后,王纲解体,乐教沦丧,“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宋玉《九辩》),诗歌逐渐转向表现因“失职”而“不平”的个人之志,“志”也用来泛指人的思想、意愿、情感。
汉代以来,《诗大序》又进一步发展了从《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以来情、志相结合的思想,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它一方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二者同时受到“礼义”的约束和规范(《毛诗正义》271),在情、志二者的关系上,更重视志(张少康 刘三富22)。汉代诗赋分流,赋体如体国经野的京邑赋之类,主要表现群体之志即国家意志;刘歆《遂初赋》、崔篆《慰志赋》、冯衍《显志赋》、曹植《愍志赋》等一系列“求志道志(诗以道志)之作”(饶宗颐),主要表现个人之志。后起的文人五言诗则以表现个人之志为主。汉末乐府如曹操《秋胡行》《步出夏门行》,皆以“歌以言志”卒章,可见“言志”本体观在汉魏之际仍很普遍。从汉魏诗歌如仲长统《见志诗》,曹植、何晏《言志诗》可见,其对“志”的理解是很自由的,既指向体现群体原则的政治与伦理内涵,也有对个体的思想情感和意愿的表达,二者往往并不截然分开,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汉末王纲解体,儒家礼教废弛,个人情感的表现不再受到压抑,在诗赋中的表现也相应增加。而随着表现内容的拓展,诗歌的风格和技巧也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诗史从此迈入文人诗的时代。陆机敏锐地注意到此,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张少康71)的重要观点,使诗歌艺术中的“情”从狭隘的伦理领域进入到广阔的审美领域,情感作为独立本体的地位得到确立,不再从属于伦理。此后,沈约《七贤论》强调“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严可均3117),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在宗经的前提下提出“情者文之经”“此立文之本源也”(詹锳1157),都承认“情”是诗歌独立的本体。与此相应,六朝文学创作也转向对“情”的积极表现,新出的缘情说一度成为诗歌本体论的主流观点,其影响直至初唐诗坛。
“缘情”说盛行的同时,六朝时对诗歌言志的表述也并未中断。如西晋潘岳《悼亡诗》“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王增文287),陆云《赠汲郡太守诗八章》“虽无赠之,歌以言志”(逯钦立701),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南山其五》“诗以言志,先民是经”(722),东晋桓伟《兰亭诗》“数子各言志,曾生发清唱”(910),北魏高允《答宗钦诗》“诗以言志,志以表丹”(2203)等等。再如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嵇中散康言志》;庾信《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十首》;梁武帝萧衍曾“命沈约言志赋诗”(姚思廉480);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谓“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严可均3011),《与刘孝仪令悼刘遵》“酒阑耳热,言志赋诗”(2999);甚至陈后主《上巳宴丽晖殿各赋一字十韵诗》也有“言志递为乐,置觞方荐寿”(逯钦立2515)的表述。可见即使在向来被认为是以缘情绮靡为主的齐梁陈时代,尚存赋诗言志的传统,至少“诗言志”说的理论尚在传承。当然,这其中有些属于一种习惯性的表达,有时诗人则直接以“言志”来指代作诗这件事。至于创作实践上,像左思《咏史》、陶潜《饮酒》、鲍照《行路难》、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等名作,也是以善于言志而著称的。
总的来说,先秦言志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本体论,与儒家诗教有内在的紧密联系;而缘情说的产生是以汉末儒家礼教废弛为前提的,多抒写与政教人伦无关的情感与生活,在艺术技巧上更加重视声律、对仗等技巧的锤炼。
二
唐初一般作者对诗歌本体的认识,仍在不自觉地延续着六朝的缘情说,而且主要是沿承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基本观点。
目前所见唐人最早有关本体论的表述,见于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释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启》“莫不诗极缘情,而赋穷体物”(董诰4177)。其称举诗赋,全用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之说,这也代表了唐初文人对诗歌本体论的一般理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或稍后,李百药《赞道赋》以“异洞箫之娱侍,抒飞盖之缘情”(633)论诗赋,与法琳“诗极缘情,而赋穷体物”相似,仅措辞略有变化。其后《北史·文苑传序》云:“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李延寿2778),则直接以“缘情”为诗歌的代称。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令狐德棻《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君碑铭》赞誉于志宁“缘情极绮靡之能,体物穷浏亮之趣”(董诰611)。又上官仪《为李秘书上祖集表》称美高宗“垂衣视典,探群玉之幽赜;虚己缘情,动兼金之歌咏”(697)。二人对本体的表述与上官体的“浮艳”风格一致,在高宗朝宫廷诗风中具有代表性。
初唐诗坛对缘情说的传述,基本上是简单地沿袭六朝缘情绮靡之说。但也有一些诗人在传述时,将缘情与艺术构思、表达等更具体的创作问题联系起来。如乾封二年或稍后,于敬之《桐柏真人茅山华阳观王先生碑铭》将“警思缘情”与“抽毫写虑”并提(834)。所谓“警思”,即警策之思,在艺术上有求深求新的倾向。又石山辉《金赋》云:“无体物之奇策,失缘情之妙旨”(4415),崔融《报三原李少府书》云:“缘情体物,诚所不工;雕朽砺铅,有时牵拙”(979)。“奇策”和“警思”,意思相类,正是“牵拙”“不工”的反面。上述三例,在表述“缘情”的同时兼重诗歌的艺术技巧,这也符合缘情说重视技巧的特点。
唐初诗人在本体论上,主要是沿承陆机缘情说,在艺术上追求新警奇妙。但也有一些诗人在传述缘情说时,开始将其与教化、风化之旨结合。这是值得注意的理论发展的新现象。如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许敬宗《为司徒赵国公谢皇太子寄诗笺》云:“窃惟化成天下,资系象以导洪源;体物缘情,自风骚而绵列代。”“化成天下”典出《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正义》37)。此一理论在南北朝后期至初唐,一直作为人们认识文学功能的主要理论出现。许《笺》将“化成天下”与“体物缘情”并举,虽仍沿用陆机缘情说,但以诗赋为人文的代表,又兼顾诗歌的伦理之用。这当然和答谢的对象是皇太子有关系,也体现出贞观君臣渴望开创盛世的一种努力。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武三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云:“至若缘情体物,属事比辞,取之以义方,先之以风化。清词海富,缛藻云繁。凡所著述,皆成典训”(董诰1069)。将“缘情”之作与“义方”“风化”相联系,视同经典,也与前述法琳、李百药全袭缘情说有所不同。从传统的逻辑来说,教化之类的说法主要是与言志说相结合的。但这时候的诗人却将缘情说与教化之旨相结合。这反映出唐初诗人对诗歌本体的体认,是以缘情为主流的。并且,上官仪以“缘情”称美高宗,武三思又以缘情说赞美武则天之母杨氏,足见无论高宗还是武后都缺少对言志说的表述,其本体论总体上以传述缘情说为主,也与此有关。
上述诸例,许敬宗、李百药、令狐德棻、崔融等人,都是唐初著名的文学家,且涉及赋、启、书、碑铭、笺、表等公私文体。写作的性质,则既有上书朝廷或皇太子的表笺,也有性质为“大手笔”的碑铭,还有友朋之间的书札。论诗的对象,既有帝王、太子及其戚属、重臣,也包括诗人自己。由此可见,当时朝堂之上主流的诗学观念,仍旧是沿袭六朝旧轨,以缘情说为主的,这也符合唐初诗风的普遍倾向。
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言志说作为一种儒家正统的诗论,即使在齐梁陈时代也仍然有所传述。再者,和缘情说相比,言志说的“志”有较多的政治伦理内容,与儒家教化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故历代君王,无论其自身好尚如何,其对本体论的表述,常常以言志为尚,甚至在创作上有所体现。这方面唐太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太宗“本好轻艳之文”(谢无量53),其诗多浮艳之作。以致“宫体之势,初唐以太宗好尚,一时甚盛”(钱仲联19)。但太宗是有为之主,私下里“戏作艳诗”是一回事,遇到君臣唱和的场合,则不宜提倡体制非雅、于教化无益的“艳诗”,而是标举“言志”。如其《帝京篇十首》序云:“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吴云3)又其《登三台言志》《秋暮言志》,也是“诗言志”论的成功展示,虽仍不免于梁陈宫体形似写物的积习,但像《登三台言志》之“扇天裁户旧,砌地剪基新。引月擎宵桂,飘云逼曙鳞”(36),还是努力追求一种气象和新意的。相比之下,许敬宗奉和之作,《奉和秋暮言志应制》套语可厌,《奉和圣制登三台言志应制》属于中规中矩的切题之作。
但太宗赋诗言志的举动,并没有改变贞观诗坛上弥漫的梁陈宫体绮艳之风。当时人对于诗歌本体的表述,也并未因此一归于“言志”。毕竟对于一个成熟的诗人来说,有关诗歌本体论的表述往往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并且与其创作相一致的。相反,除上引太宗和许敬宗的唱和之作外,其余诸人对本体的表述基本都是传述缘情说的。故太宗虽有赋诗言志之举,对于当时诗风也未见有更大的影响。当然,贞观末年许敬宗、武周时武三思等人表述“缘情”的同时,兼有“化成天下”“义方”“风化”等政教内容,后来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复古诗学(包括言志说在内)之所以能够很快地产生影响,缘情说内在的求变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三
高宗、武后时期,在朝之士有关诗歌本体的表述基本上是传述缘情说的,已见前述。几乎与此同时,王勃、骆宾王、陈子昂等年轻的诗人进入长安,在仕途上急于求进,并且在诗文中积极表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热情。他们对诗歌本体的表述,既有言志,也有缘情,比此前所述法琳、上官仪、崔融等人只传述缘情说要复杂得多。要之,他们标举言志说,但并不简单地反对缘情说。他们对“志”的标举中,也包含了“情”的因素。
初唐诗人中,较早明确标举言志说的诗人是骆宾王。骆宾王在本体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由六朝缘情说溯流而上,标举更为古老的言志说:
《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并序》:夫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陈熙晋16)《答员半千书》:张评事至,辱惠书及诗。[……]盍言尔志
,岂若是乎?(279—81)《晦日楚国寺宴序》:诗言志
也,可不云乎?(320)《初夏邪岭送益府窦参军宴诗序》:诗言志
也,可不云乎?(322)从上述引文可见,骆宾王言志说的主要理论来源有二:其一是《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其二是《论语》记载孔子谓其弟子云:“盍各言尔志?”(朱熹82)“亦各言其志也”(131)。上述“诗言志”论的前提是言为心声,《周易》所谓君子“修辞立其诚”(《周易正义》15)。这里的“志”,显然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联系,其主要的内涵,无外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同时与“情”相通,不仅有离别之情,更多感伤身世之意。故骆宾王言志说的“志”,其内涵是很丰富的。
从对诗史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骆宾王对于诗歌本体论从“言志”到“缘情”的发展有着明确的认识,体现出在本体论上的自觉。其《和学士〈闺情诗〉启》云:
窃惟诗之兴作,肇基遂古。唐歌虞咏,始载典谟;商颂周雅,方陈金石。其后言志缘情,二京斯盛
;含毫沥思,魏晋弥繁。[……]河朔词人,王、刘为称首。洛阳才子,潘、左为先觉。若乃子建之牢笼群彦,士衡之籍甚当时,并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爰逮江左,讴谣不辍。非有神骨仙材,专事玄风道意。颜、谢特挺,戕罚典丽。自兹以降,声律稍精。其间沿改,莫能正本。[……]宏兹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际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国,厚此人伦。(陈熙晋221)他用“言志”和“缘情”两种理论来论诗,并且认为以言志和缘情为本体,是两汉确立的一个传统。这一论述是符合诗史的实际的。因为缘情说之提出虽在晋代,但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概括,是建立在对汉魏晋以来诗赋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的。骆宾王此论,实际上是肯定了缘情说和言志说在诗歌和诗学发展史上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当然,他批评齐梁诗“莫能正本”“淫哇”非雅;又赞美学士之诗能“宏兹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际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国,厚此人伦”,则其所谓雅正,仍归于《诗》的伦理教化之用。另外,骆宾王对晋宋诗歌的态度也很值得注意。不同于陈子昂《〈修竹篇〉序》用“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徐鹏16)将晋宋诗一笔抹倒,骆宾王对晋宋诗歌是多有肯定的,故云“潘、左为先觉”“士衡之籍甚当时”“颜谢特挺,戕罚典丽”等等。当然他对晋宋诗歌也有批评,但主要针对玄言诗,所谓“非有神骨仙才,专事玄风道骨”。今天看来,骆宾王的评价更符合晋宋诗歌创作的实际。这种评价的合理性,和他所持的诗歌本体论也是分不开的。
骆宾王既然将“言志”和“缘情”并举,故其诗论,每云“申情”“抒情”“寓情”:
《饯李八骑曹序》:虽相思有赠,终结想于华滋;而素赏无暌,盍申情于丽藻
。(324)《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诗人五际,比兴存乎国风
。故体物成章,必寓情于小雅
;登高能赋,岂图容于大夫。(3)《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得风字》:虽漆园筌蹄,已忘言于道术;而陟阳风雨,尚抒情于咏歌
。(69)《在狱咏蝉并序》:庶情沿物应
,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158)骆宾王也肯定“缘情”,但其所谓“情”,往往以比兴出之,寄托着诗人的志向和身世,实际上和“志”是相通的。这方面其咏物诗尤其具有代表性。他说“情沿物应”,是强调咏物诗的创作,要处理好“情”和“物”的关系:“物”是写作的对象,而“情”才是诗歌表现的主体。作为对象的“物”,必须贯彻主体之“情”,其应如响;而对“情”的表达,又不能脱离“物”的本身,虚空乱道。以其代表作《在狱咏蝉》为例,句句写物,也句句写诗人沉冤不白之情、高洁不群之志,可以说完美地诠释了“情沿物应”的诗学内涵;艺术上突破了齐梁形似写物、缺少个性的弊病,以善于托物寓兴见长,能够取物之神,物我之间,浑融无际。《在狱咏蝉》诗中所表现的,既有属于“六情”之一的“哀”,也有与传统儒家伦理相关联的“志”。这种托物写志的方式,也是汉魏诗人常用的。由此可见,骆宾王的诗歌本体论,在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体现出“情志一也”(《春秋左传》406)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骆宾王在本体论表述上具有突出的新意,不仅表现在情志结合、言志缘情并重,而且还与六朝初唐单调地传述“缘情”之说不同,他采用了抒情、申情、寓情等多种表现方式,反映出诗人对诗歌情感本质更丰富、更活泼的体认,与初盛唐之际唐诗在抒情艺术上的发展是相应的。
王勃的诗歌本体论,也兼举“言志”和“缘情”。但于二者颇有轩轾,这点与骆宾王不同。其总章年间(公元668年—669年)所作《平台秘略论》论《艺文》云:
论曰:《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
。是故思王抗言辞颂,耻为君子;武皇裁勑篇章,仅称往事,不其然乎?至若身处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诗以见志
,文宣王有焉。(蒋清翊302—303)显然,王勃在诗歌本体论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一方面鄙薄“缘情”之诗、“体物”之赋为“雕虫小技”,非“大者远者”,不值得君子“役心劳神”;另一方面肯定文宣王萧子良“身处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的“见志”之诗。王勃言志说的另一特色,在于其所谓“雅志”“幽怀”,偏于以“山川”“烟霞”之知己自居的个人志趣:
《游山庙序》:盖诗以言志
,不以韵数裁焉。(208)《别卢主簿序》:盍陈雅志
,各叙幽怀
,人赋一言,同疏四韵云尔。(262)《仲氏宅宴序》:盍各赋诗,放怀叙志
,俾山川获申于知己,烟霞受制于吾徒也。(202)《秋日宴季处士宅序》:人赋一言,各申其志
,使夫千载之下,四海之中,后之视今,知我咏怀抱
于兹日。(192)此种“雅志”“幽怀”,先秦两汉诗歌中罕有表现,却是晋宋以来山水田园诗歌的表现主体。王勃在理论上加以肯定,并将其纳入传统言志说,相对于先秦两汉与儒家伦理相联系的言志说来说,其实是一种开拓。与此相联系,王勃“见志”论包括圣人之志与君子之志两个不同的层面。其《上吏部裴侍郎启》云: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
。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然窃不自揆,尝著文章,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谨录古君臣赞十篇并序,虽不足尘高识之门,亦可以见小人之志
也。(129—33)《周易·系辞传》云:“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周易正义》81)开物成务,使天下人各得其志,此圣人之志,近于前述“化成天下”;著述立言,见志后学,此君子之志。王勃自己的诗歌创作,显然是以表现君子之志自期的,末句“小人之志”,乃是一种谦辞。与王勃诗歌在由初唐沿承齐梁陈隋到盛唐提倡汉魏风骨这一发展中位置相应,我们看到王勃在唐代诗歌思想的发展史上,也处于同样的位置。
在将“雅志”“幽怀”纳入传统言志说的同时,王勃对缘情说也有所汲取:
《夏日宴宋五官宅观画障序》:惊鸿擅美,丹青贵近质之奇;吐凤标华,宫徵得缘情
之趣。(195)《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一时仙驭,方深摈俗之怀;五际飞文,时动缘情
之作。(199)《为人与蜀城父老第二书》:感序缘情
,登高寄赏。(186)将“摈俗之怀”与“缘情之作”对举,则其所缘之情,也是与个人之志相关的。尤其是他将“感序缘情”与“登高寄赏”相对,则其所缘之“情”,与其所见之“志”一样,都指向登山临水的雅志、幽情。可见在王勃的表述和实际创作中,“志”和“情”的内涵虽有不同,在指向个人怀抱这一点上却是相通的。
唐初文学承梁陈之旧,诗歌中不尚言志咏怀,而多缘情体物之作。和唐初文臣相比,骆宾王、王勃虽不废缘情说,但他们大量地标举“言志”“见志”,其理论主张对当代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其中包含的倡导之意是明显的。骆宾王和王勃在创作上志尚风云,词多江海,诗歌风格也和前述以宫廷诗人为主的唐初诗人不一样,以雄奇阔大为主。在诗歌本体论上,骆举“言志”,多标“比兴”“寓托”,王标“见志”,崇尚“雅志”“幽怀”:二人于传统言志说都有个人化的发展,言志、缘情二者具有某种交融之势。同时,“志”的内涵的扩大,是唐人对言志说在实践上的一种发展。
四
陈子昂(公元661年—702年)以继圣自任,相比骆、王二人,其诗歌本体论的“言志”立场更为彻底:
《金门饯东平序》:请各陈志
,以序离襟。(徐鹏178)《薛大夫山亭宴序》:诗言志
也,可得闻乎?(180)《饯陈少府从军序》:盍各言志
,以叙离歌。(182)《晦日宴高氏林亭并序》:盍各言志
,以记芳游。(276)这里的志,“就是离别之情”(乔惟德46),或者是包括离情在内的个人怀抱。其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实为诗人咏怀之作,也就是以诗言志。陈子昂倡言复古,“主张诗要有兴寄,实际上是要求恢复诗歌的言志传统。[……]从陈子昂的整个创作实践看,兴寄应该包括诗人从现实中感发的多方面的思想感情,诸如对时政的批评,对世事的感慨,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个人功业的追求等等”(霍松林485)。言志与兴寄,构成陈子昂复古诗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属于诗歌本体论,后者属于艺术表现论,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偏废。虽然其《〈修竹篇〉序》中论述复古理论时,提倡的主要是“风骨”“兴寄”,未提及“言志”。但他在其他论诗场合大量地标举“言志”,已经说明“言志”在其复古诗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陈子昂乃至此前四杰、庾信在以诗言志时,大量地引入咏怀,也是一个需要专门论述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陈子昂对“言志”的表述,多在别序或宴集序中出现。送别、宴集往往参加人数众多,是传播诗论的一个重要渠道,也说明他对言志说是有意提倡的。以《晦日宴高氏林亭》诗为例,当时参加宴集并赋诗者多达二十一人(计有功86),规模很大。其中《全唐诗》尚存其诗者,有王勔、崔知玄、韩仲宣、周彦昭、周彦晖、高球、高瑾、高绍、高峤、弓嗣初、王茂时、徐皓、长孙正隐、郎余令、陈嘉言、刘友贤、周思钧、陈子昂、解琬等19人,其中不少与陈子昂过从甚密,有的也有对言志的表述。以另一次宴集中孙慎行序为例:

根据题下小字,知诗序作者为孙慎行,料想当日亦参加宴集并作诗,可惜诗已失传。序末言“度志陈诗”,在诗歌本体论方面也是属于言志论的。参与这次宴集的崔知玄、韩仲宣、高球、高瑾、席元明、陈子昂、孙慎行等七人,其中有五位也参加了《晦日宴高氏林亭》的唱和活动,可见诸人来往密切,故在诗歌本体论方面也颇多同气。而此次宴集,不仅诗序标明“度志陈诗”,而且所作皆为四言,称得上是一次复古的诗学实践。这也表明言志确实是复古诗学的重要内容。从现存文献来看,陈子昂对风骨、兴寄的提倡及有关言志的表述都不算很多,但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李阳冰《草堂集序》引卢藏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王琦1445)此后的盛唐诗风,基本上是朝着陈子昂构想的声律、兴象、风骨兼备的道路向前发展的。陈子昂诗论在当代的传播和影响,现有的研究多从李、杜和韩愈等人的接受及其《感遇》组诗的艺术典范性等方面来把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子昂以言志说为重要内容的复古诗学在当代诗人群中的传播和影响,宴集唱和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式。这一点在现有研究中似乎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以往对陈子昂复古诗学的重视,主要集中于《〈修竹篇〉序》中的表述,尚未注意到更为广泛的他对言志说的提倡影响。对此点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掌握其复古理论及其在当时的提倡。
五
子昂之后,以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的盛唐诗人在诗歌本体论方面,相对初唐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对本体的表述有多歧和统一的不同。初唐诗歌和诗学在对齐梁的沿承中又孕育着变化,故其对本体的表述也呈现出多歧的样态:大体而言,太宗和高宗朝的诗坛,其对本体的表述是以缘情为主的;而后起的中下层文人如骆宾王、王勃、陈子昂,其对本体的表述往往言志、缘情兼叙,甚至同一诗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本体的表述也不完全一样,这一脉络直透盛唐。与之相对,盛唐诗人对本体的表述基本上是以言志为主的。对“缘情”的表述,可举者仅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楼颖《〈国秀集〉序》引述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以为“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傅璇琮等264),与其偏于绮丽婉约、讲究色彩和声韵之美的选诗标准相一致。二是对本体的表述所依存的文体不同。初唐对本体的表述主要存于别序、诗序、集序等序体文。盛唐序文鲜有对言志的表述,除玄宗诗序及《国秀集序》外,笔者仅见陶翰《送王大拔萃不第归睢阳序》“诗而咏言,将以述志”(董诰1495)一例。与此相对的,盛唐诗人往往是直接以诗言志。故本节对盛唐言志论的探讨,主要是围绕言志诗来展开的,尤其是那些在诗题中明确标明“言志”的作品。
盛唐较早的“言志”诗,为中宗朝宰相崔湜罢相外放途中所作《景龙二年。余自门下平章事削阶授江州员外司马。寻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阳途中言志》(彭定求661)。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五月,崔湜以在吏部铨选中贪贿,选人失当,为御史弹劾下狱,免死外放。诗言“毫发顾无累,冰壶邈自持。天道何期平,幽冤终见明”,则诗题所谓“言志”,实为陈情表白之意,主题和前举骆宾王《在狱咏蝉》相近。
睿宗朝比较有代表性的赋诗言志活动,是韦嗣立与诸人的唱和。太极元年(公元712年),韦嗣立作《偶游龙门北溪。忽怀骊山别业。因以言志。示弟淑。奉呈诸大僚》诗,抒其幽隐之志。“还悟北辕失,方求南涧田”(986),言己欲从初心,隐居山野。张说、崔日知、魏奉古、崔泰之奉和之作,如魏奉古《奉酬韦祭酒偶游龙门北溪忽怀骊山别业因以言志示弟淑奉呈诸大僚之作》“迹是东山恋,心惟北阙悬”(989)、张说《奉酬韦祭酒嗣立偶游龙门北溪忽怀骊山别业呈诸留守之作》“野失巢由性,朝非元凯才”(969),亦皆关涉出处之道,正呼应题中“言志”之意。可见诸人唱和,正是一次以诗言志的实践。又崔日知《冬日述怀奉呈韦祭酒张左丞兰台名贤》,韦嗣立、张说、崔泰之皆有和作。张说《和冬日述怀诗序》云:“崔光禄述志论文,首贻雅唱,诸公嘉德序事,咸有报章。”亦以“述志”论诸人之诗。可见在当时,赋诗言志的观念是很普遍的。以诗言志的观念和实践,当然也并不限于诗题中标明“言志”“言怀”“述志”的诗作。韦嗣立、张说皆位登宰辅,又喜唱和,上述对“言志”本体的传述与诗歌唱和的实践,无疑对当时的诗坛风气有相当的影响。
玄宗朝无论朝野,以诗言志的唱和都很普遍。朝堂之上,开元年间玄宗曾有两次重要的赋诗言志之举。其一为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秋,玄宗作《早登太行山中言志》(38),苏颋、张九龄、张说、苗晋卿、张嘉贞等人奉和。玄宗之作,章构和写景都和太宗《秋暮言志》颇多相似之处,应是有意规仿太宗昔日赋诗言志之举。与太宗诗中表现出的求贤若渴、励精图治相比,玄宗“凉德惭先哲,徽猷慕昔皇”的表述乍读似嫌虚泛,当与“野老茅为屋,樵人薜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数句合读,方能体味出其中隐含的志得意满之情。故臣下和作,如苏颋《奉和圣制登太行山中言志应制》“愿以封书奏,回銮禅肃然”(908)、张九龄《奉和圣制早登太行山率尔言志》“之罘称万岁,今此复同声”(596)等,皆作颂声。其二为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玄宗作《惟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张说、张九龄奉和。玄宗之志,即“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诗以“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30)二句写之。张说《奉和圣制温泉言志应制》“始知尧舜德,心与万人同”(945)直言其志,张九龄《奉和圣制温泉歌》“渐渍神汤无疾苦,薰歌一曲感人深”(578)兼论及其“感人”的艺术效果。此外,玄宗诗序中也常有“言志”的表述:
《〈春中兴庆宫酺宴〉序》:诗以言志
,思吟湛露之篇
;乐以忘忧,惭运临汾之笔。《〈平胡〉序》:爰作是诗,聊以言志
。《〈游兴庆宫作〉序》:诗以言志,歌以永言
,情发于衷,率题此什。《〈鹡鸰颂〉序》:申友于之志,咏常棣之诗
。(37—41)上述四首,也都有臣子属和。虽未在题目中标明,但序中“言志”之意,则无论玄宗原唱还是臣下和作,都有明确的表现。如《春中兴庆宫酺宴》唱和,玄宗原唱“曲终酣兴晚,须有醉归人”,张说《奉和圣制春中兴庆宫酺宴应制》“镐京陪乐饮,柏殿奉文飞”(966),皆体现《诗·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之旨(《毛诗正义》421)。又《平胡》唱和,玄宗原唱“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臣下唱和,如崔漼《奉和御制平胡》颂“直将威禁暴,非用武为雄”“干戈还载戢,文德在唐风”(彭定求1114),韩休《奉和御制平胡》赞“叨荣逢偃羽,率舞咏时文”(1133),皆呼应此旨。又《游兴庆宫作》唱和,玄宗原唱“所希覃率土,孝弟一同规”,张说《奉和圣制暇日与兄弟同游兴庆宫作应制》酬以“永言形友爱,万国共周旋”(967),也是如此。
显然,太宗、玄宗朝以诗言志的君臣唱和活动,带有很明显的政治教化色彩,所言之志,兼有个人之志与圣人之志两类,属于文教的重要活动。不仅玄宗本人以君臣唱和为六义教化的内容,如其《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云:“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股肱良足咏,风华可还淳”(28)。张说《赴集贤院学士赐宴应制得辉字》,也将此种宴饮唱和誉为“欲知朝野庆,文教日光辉”(965)。前引当时大臣属和之作,也多有“文德”之颂。对于不能参与唱和活动的朝廷官员来说,君臣唱和中以诗言志的实践,其中共同的政治理念的表达,又会成为他们揣摩和模仿的对象,由此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和观念产生复杂的影响。
盛唐诗学以复古诗学为主体,故言志也是盛唐基本的诗歌思想。这一时期的复古诗论,以风骨为核心的概念之一。相对于初唐诗坛,盛唐宫廷唱和活动相对减少,有关“言志”的理论表述也相应减少,诗歌日益成为诗人的一种个体抒写。但从根本来讲,在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中,言志理论更加深化了,艺术表现也更为丰富。以李杜为例,他们对历史上丰富的言志传统有深入汲取,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李白集中言志之作甚多,有四首诗题即标明言志。其中《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甫吟》”(王琦1065),抒写志士不得时用的苦闷,是典型的言志之作:其余诸作,如《宣城长史弟昭赠余琴溪中双舞鹤,诗以见志》“何当驾此物,与尔腾寥廓”(1042),表达置身霄汉的青云之志;《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将欲继风雅,岂徒清心魂”(1041),抒写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志趣;《春日醉起言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1074)则是诗人浮生若梦当及时行乐的人生观的流露。当然,李白《梁甫吟》《行路难》等也是言志之作,艺术上更加酣畅淋漓。
李杜诗歌善于用托寓和比兴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志趣。李白常以“抟摇直上九万里”(王琦512)的大鹏自况,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仇兆鳌1438),多托喻于凤凰。二人集中咏物诸作,皆可见志。其余赠答、行役、咏怀诗中,也多言志之作。托寓和比兴本就是传统以诗言志的方法,咏物诗中常用,李杜对传统的一大发展,在于其诗歌普遍具有言志的特点:赠答如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王琦910),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仇兆鳌74);行役如李白《郢门秋怀》“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王琦1017),杜甫《北征》“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仇兆鳌395);咏怀如李白《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王琦1113),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仇兆鳌264)等等。言志和怨刺一样,都是儒家诗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唐代复古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杜是盛唐怨刺诗学的代表人物,又都在以诗言志方面对传统有较大的发展。其诗歌创作中言志与怨刺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宜另撰专文加以探讨。
总之,对诗歌本质的理论表述,在唐以前主要有言志和缘情两种观点。唐人对言志说和缘情说都有传承和发展,并且在不同时期,其具体表现也不同:一、唐初诗坛承陈、隋之旧,故太宗朝无论理论和创作,普遍以传述缘情说为主。虽然太宗本人曾多次赋诗言志并令臣下属和,但这主要出于政教目的,未能改变当时朝野诗歌普遍的缘情特征。二、高宗、武后时期,在朝之士仍以传述缘情说为主,而骆宾王、王勃等年轻诗人则兼叙缘情与言志说,且有提倡言志之意,这和他们在仕途上锐意进取并在诗歌中加以积极地表现是分不开的。陈子昂更是以复古为旗帜,标举言志,并且通过宴集唱和来加以传播,造成影响。三、盛唐的诗歌本体论以言志说为主,每每形之于诗,朝野皆然。玄宗君臣的言志唱和活动兼有诗教的目的。李杜诗篇,各种题材都普遍带有以诗言志的特点,艺术表现也更加多样。不过,初盛唐诗人对言志缘情说的传述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尤其是盛唐言志说的发展,在诗歌创作艺术方面上有丰富的表现。本文所作的,还只是一个初步勾勒。
注释[Notes]
① 毕万忱:“言志缘情说漫议”,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编委会辑,《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丛刊(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6页)指出“先秦至六朝,关于诗歌言志抒情的理论已经形成一条鲜明的路线”。但有关该路线在初盛唐的发展,则付阙如。
② 王秀臣“‘诗言志’与中国古典诗歌情感论”,《文学评论》2(2014):148,较早指出早期“诗言志”论的群体特性,“志是一种带有道德预设的情感体验[……]因其注重整体社会的人伦特性和普遍价值观念而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
③ 系年据何格恩《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0年)。
④ 详参刘青海“论唐代怨刺诗学的发展历程——以李杜及其接受为中心”,《文艺研究》8(2017):44—5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Chen,Xijin.Annotations
to
Collected Works of Luo Binwang.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5.]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Dong,Gao,et al.eds.The
Complete
Prose
Writings
of
the
Tang
Dynasty
.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5.]杜预注 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Du,Yu,and Kong Yingda,eds.An
Interpretation
of
Zuo
’s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to
th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Ed.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傅璇琮 陈尚君 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Fu,Xuancong,Chen Shangjun,and Xu Jun,eds.Newly
Edited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 Select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14.]霍松林主编:《中国诗论史》。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
[Huo,Songlin,ed.A
History
of
Chinese
Poetic
Theories
.Hefei: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2007.]饶宗颐:“论《文选》赋类区分情志之义答(李)直方”,饶宗颐主编,《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庆祝港大金禧纪念特刊·文心雕龙研究专号》。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第88页。
[Jao,Tsung-i.“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iatingZhi
(Aspiration)andQing
(Emotion)in theFu
Category of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An Answer to Li Zhifang.”Special
Issue
on
the
Study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for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1911-1961
).Ed.Jao Tsung-i.Hong Kong:Dragon Bookstore,1965.88.]计有功辑撰:《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Ji,Yougong,ed.Recorded
Matters
Pertaining
to
Tang
Poetry
.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08.]蒋清翊:《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Jiang,Qingyi.Annotations
to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Bo.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5.]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Li,Yanshou.A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Lu,Qinli,ed.Poetry
from
the
Pre
-Qin
to
Han
,Wei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8.]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Peng,Dingqiu,et al.eds.The
Complete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6.]钱仲联:《梦苕庵专著二种·李贺年谱会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Qian,Zhonglian.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i He.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84.]钱志熙:“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文艺理论研究》5(2017):6—18。
[Qian,Zhixi.“The Evolution of the ‘Poetry as an Expression of Aspirations’ Theory and Its Multi-layered Meaning.”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5(2017):6-18.]乔惟德 尚永亮:《唐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Qiao,Weide,and Shang Yongliang.Poetics
of
the
Tang
Dynasty
.Changsha: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0.]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Qiu,Zhaoao,ed.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Du
Fu
’s
Poems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5.]宋玉:“九辩”,《楚辞集注》,朱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Song,Yu.“Nine Arguments.”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the Songs of Chu.Ed.Zhu Xi.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79.]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Sun,Xingyan.Annotations
to
Present
-and
Ancient
-Character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6.]王弼注 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Wang,Bi,and Kong Yingda,eds.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to
th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
.Ed.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Wang,Qi,ed.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Bai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9.]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Wang,Xianqian.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Xunzi.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王增文:《潘黄门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
[Wang,Zengwen.Annotation
to
Collected Works of Pan Yue.Zhengzhou: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2.]吴云 冀宇编校:《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Wu,Yun,and Ji Yu,eds.Collected
Works
of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Xi’an: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6.]谢无量:《骈文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
[Xie,Wuliang.A
Guide
to
Parallel
Prose
.Shanghai:Zhonghua Book Company,1940.]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Xu,Peng,ed.Collected
Works
of
Chen
Zi
’ang
.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7.]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Yao,Silian.A
History
of
the
Liang
Dynasty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73.]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Yan,Kejun,ed.Collected
Essays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o
the
Period
of
the
Six
Dynasties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Yang,Bojun,ed.Annotations
to
Zuo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5.]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Zhan,Ying.Annotations
to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9.]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Zhang,Shaokang.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Rhymed Prose on Literature.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4.]张少康 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Zhang,Shaokang,and Liu Sanfu.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nd
Criticisms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0.]郑玄笺 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Zheng,Xuan,and Kong Yingda,eds.An
Interpretation
of
Mao
’s
Edi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to
th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
.Ed.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Zhu,Xi.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the Four Book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6.]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Zhu,Ziqing.Zhu
Ziqing
’s
Essays
on
Classical
Literature
.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