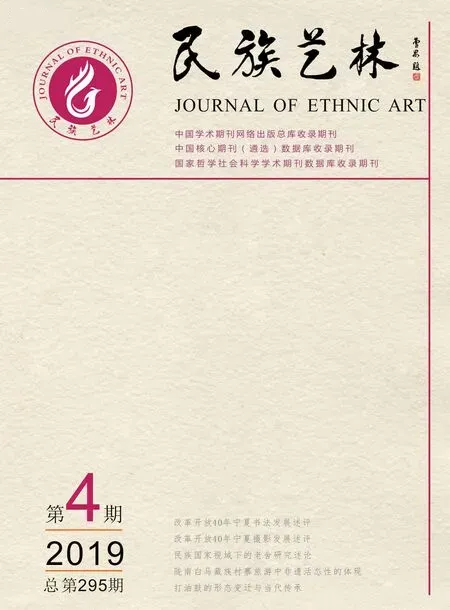论毕赣电影的诗性特质
2019-12-30李婧
李 婧
(山东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近年来,国产电影发展势头迅猛,艺术电影渐渐脱离曲高和寡的困境,发展形势可谓一片大好。新生代导演们在其个人风格基础上,对电影美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毕赣是新生代群体中别具一格的一位,其影作以诗性著称,处女作《路边野餐》荣获多个国内外电影节奖项,也为其打上诗意、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凭借这部影片,毕赣的美学追求和才华受到业界的肯定,第二部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也成为2019年第一部“现象级”艺术电影,在保持毕赣个人一以贯之的风格的基础之上,修补了诸多技术硬伤,甚至有了更进一步的技术革新——长达60分钟的一镜到底,做到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史无前例。与其说毕赣在通过电影记录生活,不如说是在为观众营造充满诗意的梦境。帕索里尼于1965年在《诗电影》中提出“诗电影”的概念,帕索里尼认为电影是一种符号系统,指出这些符号系统来自“一个完整复杂的由具体形象组成的世界”“既包括周围环境中人们的表情动作,也包括回忆和梦境”[1]。海德格尔则认为诗性是对存在的揭示。塔可夫斯基称“诗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一种叙述现实的特殊方式”[2]。毕赣电影中的“诗性”气息已然成为其高度个人化的标志,诗性的叙事、诗意的长镜头以及诗化的意象表达是其影片中的显著特征。
一、诗性的叙事美学
(一)抽象化的叙事时间
毕赣的两部影片《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叙事风格上达到高度一致性: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摒弃了传统的以“因果逻辑”为基础的叙事模式,在一种虚实相间的场域中进行叙事,以此将诗性融入叙事,在叙事完成的同时达到影片的高度诗化。毕赣的处女作《路边野餐》围绕主人公陈升的经历展开,由现实和梦境两部分组成,影片选择12年后陈升出狱作为叙事起点。陈升出狱后在老家凯里的小诊所上班,为寻找侄子卫卫踏上了去镇远的火车,途中经过一个名叫荡麦的小镇,开启了一段亦真亦幻的梦境。影片叙事时间的处理明显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来回切换,现实中不断穿插着回忆。广播里有关“野人”的新闻在影片中不同时间、地点多次出现,使得叙事时间更加抽象化。有关“野人”的新闻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时,是九年前的新闻播报,而第二次出现时变成了一条实时新闻,暗示着叙事时间倒回过去,而当下发生的事情则为陈升的回忆。陈升为了寻找侄子卫卫,乘火车去镇远的途中来到荡麦,在荡麦遇到的骑摩托的青年,青年与卫卫有着一样的习惯爱好,暗示这是长大后的卫卫,又暗示着叙事时间跨越至未来。而陈升与理发店女人——自己的妻子——的相遇,暗示叙事时间又重返过去。这些情节将叙事时间模糊化的同时,造成时间上的错乱感和抽象性。荡麦的叙事时间,既是见到长大后的卫卫的未来,又是见到死去妻子的过去。这一处理方式,使得整个故事像是蒙上了一块毛玻璃,变得亦真亦幻。陈升为理发店女人当街演唱《小茉莉》,实现自己想为妻子唱歌的愿望,而在临别前将《告别》的磁带送予理发店女人这一情节,实际上是当年老医生与情人分别的场景在陈升与理发店女人身上重演,陈升穿的是老医生托其送予老情人的衬衫,磁带也是老医生送给情人的,这两样东西对于老医生来说意味着与旧恋情的告别,而对于陈升既是与陌生的理发店女人的一次新恋情的开始,又是与妻子的一段旧恋情的结束。开始与结束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发生,与开头《金刚经》的内容形成呼应,意味着时间的往复性和永恒性。
《地球最后的夜晚》仍是采用非线性叙事,为观众连接起了一条莫比乌斯带,利用“拓扑变换”象征时间的循环往复和永恒性。故事分为现实与梦境两部分,是由这两部分的无缝衔接搭建起了这条莫比乌斯带,一些在现实时空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友情里的亏欠、亲情里的遗弃、爱情里的求而不得,都不可思议地在梦境中实现一次又一次和解。现实部分的时空不停地在“十二年前”和“十二年后”交替,12年后罗武因父亲过世重新回到凯里,踏上了寻找万绮雯的旅程,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断穿插12年前罗武与万绮雯的情感线,借助钟表、手枪、绿皮书、黑桃A、老鹰、照片、苹果、野柚子、水火等符号及罗武时而乌黑时而灰白的头发作为提示,用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完成了所有线索的铺垫,同时也达成了抽象化的叙事时间的铺设,时间随着叙事的发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而长达一小时的梦境的展现,将时间元素进行了更具“诗化”的处理。12岁的小白猫、出走的母亲以及还是凯珍的万绮雯,几个在罗武不同人生阶段出现的人物同时出现在同一时空中,叙事时间被完全断裂重组。而影片最后在燃烧中暂停的烟花,将时间禁锢在烟花燃烧的一分钟的美好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协助完成整部影片对于时间的诗化处理的同时,将毕赣电影中关于时间永恒的话题延续下去。
(二)虚实结合的叙事空间
无论是《路边野餐》,还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都在影片中完成了自己对于“空间”的重构,正是利用“虚实结合”的叙事空间营造出影片亦真亦幻的朦胧感和浓厚的诗意情怀。
《路边野餐》的叙事空间由凯里、荡麦和镇远三个地理区域构成,其中凯里和镇远是两个真实存在的空间,在影片中也承担着现实部分的叙事任务,这两部分的叙事空间是真实的。而荡麦则是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空间,主人公陈升乘去往镇远的火车半路下车来到了荡麦,在这里他遇到了成年后的卫卫、死去的妻子以及酒鬼等人,这个空间将陈升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起来。在这一部分中叙事的真实性被搁置,更像是人的记忆深处容易被潜藏的一个区域,是一场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梦境之旅。而在处理荡麦和镇远两个空间的叙事线时,毕赣有意将虚实空间的界限模糊化,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整部影片的叙事空间的虚、实结合紧密,影片的诗性得到最大化的流露和呈现。陈升在如梦如幻的荡麦完成了与过往的告别,再次踏上前往镇远寻找卫卫的旅程,而来到镇远的陈升手中的望远镜是荡麦的青年卫卫给的,给花和尚的纽扣则是在荡麦洋洋的裁缝铺里拿的,在镇远的现实叙事中又融进了在荡麦梦境中的物件,将整个故事的叙事时空模糊化、抽象化,叙事空间虚实结合。
二、诗意的长镜头美学
长镜头是毕赣擅长并钟爱的表现手段,无论是在《路边野餐》中,还是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长镜头的使用都在影片中占据了大篇幅。长镜头于当下而言已然不是一种新奇的手段,尤其是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对长镜头的使用可谓比比皆是,然而毕赣对于长镜头的使用却与前者大不相同。毕赣影片中的长镜头不再单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去运用,而是充分融入叙事当中,且对于主题的凸显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路边野餐》中的荡麦之旅、《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漫长的梦境,不难看出毕赣用长镜头展现的是超现实的部分。巴赞提出长镜头理论,意在强调电影的本性是对于客观世界进行复原,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论认为只有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才是名副其实的影片。而在毕赣的影片中,长镜头似乎带有对长镜头理论和物质现实复原论进行重审的意味,毕赣借助影片声明电影是非真实的同时,又欲通过承载记忆的梦境来表现真实,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加强了影片的诗性和哲学意味。
《路边野餐》中陈升半途下车,来到一个名叫荡麦的小镇,开始了一段短暂又漫长的旅程,通过长达42分钟的长镜头展现,加之主观式的视角,制造出诗意和梦幻,用极具风格化的手段承担着继续叙事的任务。影片中的长镜头的使用实际上已经成为叙事文本的一部分,而因技术简陋和拍摄条件所限造成的技术硬伤也使得这部分长镜头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动荡感和粗粝感使得梦境的抽象性和变异得以真实立体地展现,潜藏于其中的情感与诗意,犹如睡梦中所带来的阵阵欣喜。毕赣采用长镜头的方式实现了过去与未来、虚与实之间的无缝衔接,无论从剧情上还是情感上都极富有层次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镜头的单调感和乏味感。这部分长镜头并没有采用一个固定视点来叙事,摒弃了摄影机一味追随主人公的视点,而是随着剧情发展不断发生变化。长镜头始于青年卫卫骑着摩托车载着陈升前往荡麦,镜头本是跟随二人的,二人骑行的速度愈来愈快,眼看就要逃离镜头,镜头忽而拐进一条小胡同走了一条捷径,从小胡同内出来后,骑着摩托的二人恰好迎面而来。镜头不再是全知视角,犹如与一个途径的第三者的偶遇,而小镇里的人不断勾起陈升的回忆,叙事视点也由陈升变为青年卫卫、女孩、镇上等人的视点,将多人物视点的故事从主观、客观视角做了多个解读。而在这段时空不明的长镜头中,陈升看到的青年卫卫,一刻不停歇地在火车上画着时钟,梦想时间能够倒流,留住即将离去的恋人,与现实中童年的卫卫不停在家中的墙上画钟表的情节相呼应,火车行驶带着画在上面的钟表逆时针运转,仿佛在那一刻时间真的倒流了。陈升有关友情、亲情和爱情的往事一并通过这段长镜头得以重现,其中两个重要道具——老医生的衬衫和磁带——的出现,协助陈升以老医生与情人的离别方式完成与前妻的告别,使得这段长镜头中过去与未来、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被打破,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的纽带。《地球最后的夜晚》中以长达一个小时的长镜头展现一段连续的梦境,12年时间里在罗武生命中出现的人和物,在迷宫一样的密闭空间中涌现。加上3D技术效果的运用,最大限度地接近梦境本身,同时使得现实中的无解与矛盾在梦中得以消解。梦本来即为人潜意识中的一种记忆,长镜头将现实与梦境结合,斑驳不清的叙事线以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交织在一起,进行错位、重组,形成了意识与潜意识的循环往复。在梦里,时间和空间扭曲变形,现实和梦境的交织,正是毕赣影片诗意传达的重要方式。在现实中断裂的情节得以完整展现,罗武与自己生命中代表着友情、亲情、爱情的几个重要人物重逢又告别,一次又一次实现与过去的和解。梦中,幼年白猫与被万绮雯打掉的孩子融为一体,通过打乒乓球和球拍上的老鹰符号的映射,罗武终实现了与好友白猫和未出世的孩子的和解;长得跟白猫母亲一模一样的红头发女人,是罗武母亲的映射,罗武借助臆想出来的以爱为名的借口重新正视遗弃,以儿子的身份帮助母亲与男人离开,实现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告别;凯珍则是被卖给左宏元之前的万绮雯,罗武在梦中实现与万绮雯一同飞向太空和一起念咒语使房子旋转,弥补爱而不得的遗憾。现实部分出现的符号在梦境中一一对应,而一切却又像一团解不开的迷雾,想讲爱情,我们却只看到映在水中的月亮;想讲亲情,我们却只看到黑夜中上锁的铁门;想讲友情,我们却只看到一个个腐烂的苹果。毕赣执着于梦境部分使用长镜头拍摄,实则欲将对于物质现实的复原植入梦境,意在深入人物的潜意识,洞察人物内心最真实最直观的部分,告诉观众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全部在梦境中,那才是现实最真实的模样。影片最后,绽放的烟花始终停留在一分钟的永恒中,罗武的所有执念也停留于此。
三、诗化的主题表达
(一)梦与时间
梦与时间是毕赣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随处可见的钟表和时钟及超现实梦境部分,都是将影片主题诗化的重要方式。毕赣的电影中存在明显的佛教思想,相较于后期拍摄的《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其早期拍摄过一部名为《金刚经》的短片中对于佛经的使用更加直接和明显。《路边野餐》中通过呈现三个不同时空,追溯友情、亲情、爱情三种不同情感搭建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开头处引用《金刚金》中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来强调有关时间概念的建构,而这三句话与影片的叙事时空和结构相映照,统领了叙事的发展,为影片奠定了诗意的基调。佛教思想追求心性的淡如水,《金刚金》为佛教经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世间万物皆为虚妄,关键是人内心的转变,而陈升放不下过去的回忆,现实生活中无望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卫卫身上,所以毕赣通过营造一场潮湿又迷幻的梦境,帮助陈升摆脱生活的无常,做到“万物皆空”的境界。而那盘名为《告别》的磁带中也唱道“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也在暗示时间的不可逆和不可调和,梦里贯穿了陈升在不同时空的情感纠葛。在时间的主题框架中,也渗入毕赣对于生命、死亡以及情感等多重维度的思考,毕赣的影片在讲梦与时间,实际上是在讲时间漩涡中的人。在讲述凯里的故事时融入了诗的元素,借助诗句文本与叙事线相辅相成,为观众构建起诗性主题的一部分;而陈升进入荡麦的梦境则是全片诗意最浓厚的段落,将时间拆解重塑,完成了非线性叙事;镇远的段落中,陈升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老医生的情人,被大河挡住了去路,野人也没有现身,火车上画着钟表逆时针回溯驶向时间的另一头。毕赣称“时间就是一只隐形的鸟”,他通过展现一个完整的持续的时空段落,并为之加上诗意色彩,将时间的概念融入影片的主题当中。
《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对于梦的呈现方式与《路边野餐》不同,《路边野餐》是通过将现实空间碎片化,在梦境中进行打乱重组,而《地球最后的夜晚》则是营造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幻觉世界,注重对人物的潜意识的体现,3D画面所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感也使得梦境世界更具立体感。在梦境的塑造上,两部影片对比而言,《路边野餐》是更加接近真实的梦境,除了时空上的跳跃感之外,更为重要的有叙事视点的不断变化,这些都是梦应该有的特征。而《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3D长镜头梦境,并没有跳出主要人物的视点,时空跳跃性也不如前者。《地球最后的夜晚》想要展现的并不是如《路边野餐》一般塑造一场真实又虚幻的梦境,而意在深入挖掘人物的潜意识,而梦的失真恰恰使其成为一面与现实映照的镜子,梦中的一切与现实相呼应,将时间的概念嵌入其中的同时,利用潜意识去完成人物的内心和解。
(二)寻找与和解
《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叙事主线均是由“寻找”母题构成,不管是陈升寻找卫卫,还是罗武寻找万绮雯,两人的“寻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对于过往的追寻,在寻找的过程中前往未知,在永恒的时间里和循环往复的空间里学会放下和与自我和解。
《路边野餐》中的陈升出狱后在凯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他的生活实际上的无望的,侄子卫卫成为其唯一的精神寄托,而镇远之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卫卫,“寻找”的主题贯穿影片。荡麦这个段落中将记忆碎片化打乱重组,形成一种诗意的叙事美学,陈升来到荡麦在紊乱的时空秩序里与过去、未来相遇,在这场梦境中陈升心中的执念被放下,领会到了片头《金刚经》所要传达的禅意。毕赣影片里“寻找”不仅仅停留于此,还是关于身份和文化的认同。《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都选择在毕赣的老家贵州拍摄,在文本叙事的同时也添加了不少当地的民俗文化。《路边野餐》中陈升前往镇远寻找卫卫,受老医生之托帮忙找到其情人林爱人,林爱人是当地有名的音乐大师,陈升前往镇远的途中遇到了一群年轻学徒,他们前往荡麦举行一场流行音乐会。这一行为是与传统的师承关系相悖的,此处流行音乐与苗族传统音乐已然形成了一个对抗,现代与传统相互交织,而自始至终陈升仍旧没有找到林爱人,实则林爱人已经过世,影片最后的出殡正是其葬礼,实则暗含毕赣对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的思考,这里的“寻找”又有了文化寻根的意味。陈升在荡麦穿着老医生的衬衫,为妻子唱精心准备的《小茉莉》,将名为《告别》的磁带赠予妻子,完成了与妻子之间的告别,同时母亲的绣花鞋缓缓沉入水底,也完成了与自己因入狱对家人、朋友的无法偿还的懊悔、愧疚的告别。影片以荡麦之梦为分界线,陈升完成了现实中矛盾的消解,找到了重新构建自我的方式,完成了和解与救赎。
四、结语
《路边野餐》作为毕赣第一部长片,极具个人化风格,用方言将台词和诗句生活化,增强影片诗意的同时稀释了影片文本的晦涩,让凝聚其间的人生观哲学观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地球最后的夜晚》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文本表达上都更为成熟和完整,通过建构莫比乌斯带将时间概念立体化,诗意的呈现更具沉浸感。毕赣的两部影片均洋溢着浓厚的“诗性”的色彩,毕赣深受塔可夫斯基的影响,意将“塔式”美学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使其成为影片驶向诗性的一叶扁舟。这种诗性不仅体现在影像上,也体现在文本表达上,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长镜头美学都与诗意主题达到了很好的呼应。当下电影市场受资本和受众影响,电影的商业化严重,艺术电影仍旧呈现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帕索里尼坚称电影的本质是诗性,而“电影想要取得合法的第七艺术的称号,有必要探讨其与诗的关系,也就是电影中存在的诗意性存在究竟为何物的问题”[3]。在当下“诗性”极度缺乏的电影界,毕赣的出现无疑为艺术电影诗性的试验和探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艺术电影的春天也需要更多的诗性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