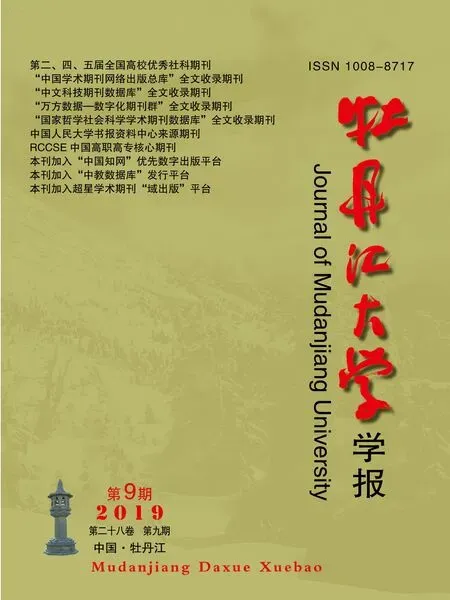《红叶》:印第安文化的堕落
2019-12-27范若孜王书戎
康 杰 范若孜 王书戎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1 引 言
印第安人形象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印第安人的历史、神话和传说是福克纳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之一。福克纳在《红叶》《公正》《求爱》《瞧!》《去吧,摩西》和《修女安魂曲》等几部作品中对印第安人形象着墨甚多,描勒了印第安人对于白人入侵他们的家园所采取的应对态度,白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印第安人的迁移对约克纳帕塔法人的后代所产生的影响,为读者展演了“约克纳帕塔法”王国中印第安人历史的消亡和白人以及黑人历史的开端。
《红叶》是福克纳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一个关于约克纳帕塔法印第安人的故事。其时间背景是19世纪初,一个名叫伊塞提贝哈的印第安酋长死了,依照印第安人的古老宗教习俗,酋长生前的马、猎狗以及贴身黑奴都要为他陪葬。黑奴逃走了,于是印第安人采取了一系列的追捕行动。黑奴最后被印第安人抓住,不得不接受悲惨结局。小说的叙述者在印第安人的视角和贴身黑奴的视角之间来回跳跃转换,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双重视角,使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各自与历史的关系。
2 消极怠惰的印第安人
印第安文化的堕落反映在方方面面,文化的堕落实际上已经摧毁了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怠惰,他们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历史上的他们却是了不起的勇士,因此,可悲的现实在他们身上就显得更加悲惨。叙述者将三篮和路易斯·贝里这两位印第安人描述为:“身材矮胖,有点结实,像城市居民;大腹便便,脑袋硕大,灰褐色宽宽的大脸盘。”[1]518莫克图贝身上所体现的特征,与传统意义上印第安酋长所具有的勇士首领的种种特质有着天壤之别。他身高仅有五英尺多一点,体重却重达二百五十磅。印第安人放弃了以打猎为生的生活方式,开始在种植园里定居下来。惰性主宰着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身体状况可以看出他们缺乏活动。印第安人的穿着看起来不伦不类,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传统服饰和从白人商人那里购买的衣服与饰品混搭在一起。追捕贴身黑奴的两个印第安人穿着衬衫,戴着草帽,一只胳膊下夹着卷得整整齐齐的裤子,这是福克纳笔下的印第安人所共有的一个习惯。莫克图贝的服饰包括一件双排扣长礼服、一条衬裤和伊塞提贝哈从巴黎带回来的一双红跟拖鞋。在莫克图贝的所有穿戴物品中,最能象征印第安人堕落的物品就是这双红跟拖鞋,它们意味着印第安人有意识地割裂了自身与土地的联系。
莫克图贝继承了由他的祖父杜姆拼凑起来的汽船屋作为他的住所。小说中的河流象征着印第安人的古老原则:强壮威武和富有活力,当印第安人抛弃这些原则时,他们宛如离开水面的汽船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慢慢地变得支离破碎。当三篮和路易斯·贝里请莫克图贝带领他们追捕贴身黑奴时,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位新酋长与这座旧汽船屋之间的相似之处。莫克图贝肥硕无比,一动不动地坐在木条椅上。他身穿一件绒面呢上衣、一条衬裤和一双红跟拖鞋,这双拖鞋因年代久远已经开裂,同时又被他那双肥脚撑得变了形。汽船本应在河流中劈波斩浪,但它却被固定在砖墙上,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废旧物品、生锈器具、镀金床和斗鸡的粪便,船上的木质结构已经腐朽,床上的镀金也已剥落,百叶窗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莫克图贝就像这艘汽船一样,本应充满活力,英勇无敌,但却因自己的毫无节制和停滞不动,连同整个部落的印第安人,都变得身体超重、迟钝怠惰和愚昧落后。
小说的第二部分描述的印第安人的简史表明,印第安文化的堕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杜姆获取权力的详细过程清楚地表明,他篡夺酋长的头衔是他的部落文化随后堕落的主要原因。在成为头人之后,他为部落获得了更多的黑奴,这也加速了印第安文化的堕落。到他死的时候,对于印第安人而言,照顾黑奴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一次讨论该如何对待黑人的会议上,部落的长老们决定从事蓄奴和贩卖奴隶的生意。正如罗伯特·芬克所言,“这种毫无目的地追求物质财富的荒谬做法已经到了极端不合逻辑的程度。”[2]从贩卖黑奴的生意中所获得的资金成为印第安人加速自身文化堕落的另一诱因。伊塞提贝哈用贩卖黑奴赚来的钱出国旅行,国外文明的种种诱惑导致了他进一步的堕落。印第安人越是模仿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就越远离自己与荒野的原始关系。为了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表象,他们诉诸于对荣耀和礼仪的盲目忠诚。但是,缺少了荒野对生命的滋养,印第安人的荣耀和礼仪已经成为空无一物的躯壳。
3 充满生命活力的黑人
与印第安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贴身黑奴与其他黑人的身上却体现出无限生命活力。贴身黑奴身手敏捷,反应机敏,而且具有长距离奔跑的能力,身体状况极佳。如若不是身中蛇毒,印第安人可能要花费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抓到他。当他看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会立即采取行动,以此来不断增强自己忍耐的意志力,有一次他竟然吃了一只活老鼠来充饥。当他被蛇咬伤之后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之际,他才彻底明白自己对生存的渴望是如此地强烈,为了防止蛇毒扩散,他竟砍掉了受伤的胳膊。贴身黑奴在逃跑时“只穿着一条印第安人从白人那里买来的粗布裤子,腰间的皮带上挂着一个护身符”。[1]534逃离种植园之后不久,他脱下裤子,在身上涂上一层泥,以防蚊子的叮咬。他用泥巴而不用从白人那里买来的衣服保护自己,这一行为颇具象征意味,因为泥巴这一天然的保护层暗示了他与大地的紧密联系。他的护身符包括两件物品,一件是半幅伊塞提贝哈从巴黎带回来的珍珠母眼镜,象征着他与伊塞提贝哈的终身契约;另一件是一个水腹蛇的头骨,象征着他与蛇的图腾关系,他对它们怀有崇敬之情,因为他曾经吃过一条蛇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或许他在非洲的童年时期就学会了以这种方式来尊重动物的生命,但是在美国,他的印第安主人的做法肯定也强化了他的黑人导师在这方面对他的言传身教,因为非洲和美国的原始民族都以图腾关系来表达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当水腹蛇咬伤他之后,他对它说道:“哦,祖先,”[1]538这也表明水腹蛇即是他的图腾。蛇是生殖力、运动力和生命力的传统象征,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贴身黑奴身上所具有的相似特征。他们最相似的特征在于他们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一个是身体上的亲近,一个是精神上的亲近。
位于汽船屋中央的小屋是黑人的主要聚集地,他们在屋里存放着举行非洲宗教仪式所需的祭祀物品,每当月亮盈亏到某种形状时,他们就汇聚在这里开始祭祀仪式,在夜幕降临后将仪式转移到存放仪式鼓的小溪尽头,鼓是黑人来到美国之前的非洲生活的最珍贵的象征。他们在荒野中比在种植园中更有家的感觉,他们拒绝割舍与森林的原始神圣关系,因为森林是他们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传统来源。汽船屋象征一种毫无意义的礼仪,对于印第安人而言,实质上意味着他们自身文化的结束。对于黑人来说,在中央小屋举行的仪式只是他们在荒野中无拘无束地庆祝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各种活动的开始。
4 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对比
福克纳通过光明与黑暗、有声与无声、运动与静止的反差来表明黑人的生命活力与印第安人的怠惰散漫之间的鲜明对比。在追捕过程中,光明与黑暗的传统象征意义在贴身黑奴身上发生了反转。黑暗通常与恶魔、邪恶、罪恶、毁灭、无知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但是小说中的黑暗却为贴身黑奴的逃跑提供了掩护。他总是在太阳下山后开始逃跑,白天的时候他就躲藏起来,因为他害怕光明,此时的光明对他而言意味着暴露、俘获和死亡。通常情况下,印第安人似乎只有在白天的光照下才感到舒适自在。当他们在黄昏后接近沼泽中的贴身黑奴时,他们变得害怕起来,决定等到第二天早上再抓他。当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时,贴身黑奴不再对白昼有任何的恐惧。黎明时分,印第安人回到沼泽,发现黑奴仰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用自己的本族语唱着一首歌。面对死亡,他颂扬着阳光给予生命的力量。
有声的和无声的形象意义也发生了转变。当三篮和路易斯·贝里讨论黑人的无礼和野蛮本性时,坐在他们面前的黑人在中央小屋里默不作声,从而间接地帮助了逃跑的贴身奴仆。他们的沉默不语表达了他们作为一个族群的团结一致、他们对同族兄弟的忠诚以及他们对印第安礼仪的蔑视。对贴身黑奴而言,声音代表着被抓和被杀后他将失去的那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荒野的联系。当他静静地躺在谷仓里等待主人死去时,他听到了三种声音:小溪尽头黑人们的仪式鼓的咚咚声,“老鼠沿着温暖的、老朽的、斧砍的方椽爬过时爪子发出的窸窣声”[1]533以及伊塞提贝哈的猎狗的嚎叫声。鼓声让他想起部落的庆祝仪式;窸窣声让他记起曾经吃过老鼠来维持生命;猎犬的声音让他回忆起和伊塞提贝哈一起打猎的情景。
福克纳采用运动意象来展示贴身黑奴的生命活力。叙述者反复提到贴身黑奴的奔跑,这是他的生命活力和忍耐意志力的最重要的标志。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能见证生命的运动。被印第安人抓获之后,贴身黑奴仍然尽其所能地紧紧抓住生命的律动不放手。他努力地吃东西,不停地咀嚼,但食物从嘴里滑落,流到下巴、脖子和胸口上。尽管恐惧妨碍着他去做这些基本的生命运动,但是他的强烈的忍耐意志力强迫自己的身体去模仿吃喝的动作。福克纳采用静止的意象来描绘印第安人的消极被动和堕落腐化。印第安人喜欢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行动,很少在意时间的流逝。黑奴每次看到追赶他的印第安人时,他们总是一边磨磨蹭蹭地走路,一边不停地抱怨追捕的工作。当印第安人把贴身黑奴围困在沼泽地里时,他们并不急于抓他,“我们会给他时间……明天不过是今天的另一种叫法而已。”[1]540第二天早上,他们一动不动地蹲着,直到黑奴对着太阳唱完歌。时间不会打扰印第安人,因为部落的仪式已经预先注定了黑奴的命运,这也是印第安人堕落到如此地步的原因。“故事由始至终体现了福克纳对仪式行为的高度重视:他对黑人抱以同情,同时感到印第安人为了生存也需要继续他们的仪式,尽管奴隶制度已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旧的风俗。”[3]空洞仪式的停滞不前已经使印第安人的个体人格失去了活力,他们已经无法适应部落中发生的变化。福克纳曾说,“红叶指的是印第安人。它是曾经窒息、压抑和摧残过黑人的自然的蜕膜脱落,没有人能够阻挡它。”[4]
5 结语
通过印第安人形象与黑人形象的对比,福克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印第安文化无可挽回的堕落。他们的文化如朽木死灰一般,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他们自己的世界(没有白人和黑人),另一个是与白人和黑人共存的世界——他们试图同时生活在这两个世界里。从《红叶》中我们可以看出,印第安人采用了许多白人定居者的方式,尤其是奴隶制。效仿白人的奴隶制是印第安文化堕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印第安人将这些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均归咎于白人,而非他们自己。《红叶》所体现的讽刺意味在于:印第安人为了维护部落荣耀而采取的行动戏剧性地表明,作为一个部落,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这种荣耀。通过《红叶》中所塑造的印第安人形象,福克纳表明,印第安文化的堕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白人的侵略性与印第安人的被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