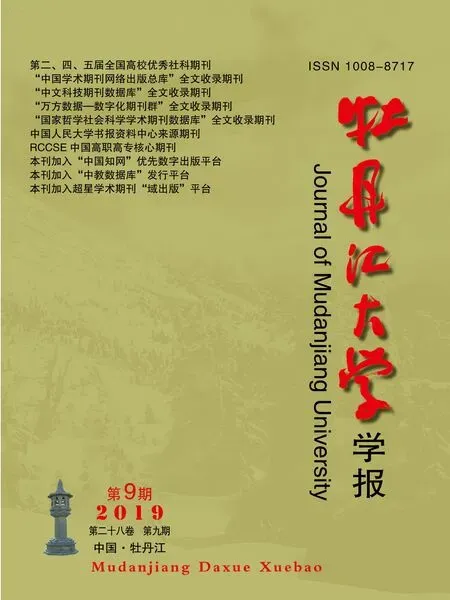论王允之
——琅琊王氏家族危机中的支柱
2019-12-27黄伟
黄 伟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琅琊王氏家族作为中古时期的第一等士族,前后延续700年之久,实所罕见。《梁书》卷三三《王筠传》中记载沈约评骘王氏家族之语:“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1]487此语,足见琅琊王氏家族其时之兴盛。东晋一朝,琅琊王氏家族势力更是在王敦、王导的运作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学术界的前贤时彦对王氏家族及其主要成员的研究已经创获颇丰,①但由于王氏家族英杰辈出,王敦、王导等人又光芒太甚,王允之少有不虞之誉。目前学术界专门研究王允之的文章并不多见,笔者不揣鄙陋,略陈愚见,试论述王允之在琅琊王氏家族危机中所起的支撑作用,希冀可以重新认识其时王氏家族所面临的危机、世家大族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东晋初期看似平静政局下的潜流所在。
一、醉酒污面堪成大器
王允之,字深猷,王舒之子,王敦、王导是他的从伯。其时王氏子弟依借家族之势,平流进取即可位居公卿,故并不热衷富贵险中求的军功之途。到了王允之这一代军事人才严重匮乏,王允之是当时家族中为数不多拥有军事能力的人,作为王氏家族后辈中的佼佼者,王允之也因此被王氏家族的顶梁柱王敦和王导分外看重。据《晋书》卷七十六《王允之传》记载:“总角,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入则共寝。”[2]2001王敦认为王氏家族他作为家族接班人来培养的意思,可见王敦对王允之器重之深。此外,王导对王允之,也同样分外重视,王允之的父亲王舒去世后,晋廷封王允之为义兴太守,而王允之却以守孝为名拒之,子侄中唯有王允之最为像他,所以时时让他跟随左右,出则同车,睡则同寝,王敦从家族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其目的肯定是想通过言传身教,让王允之有所增益,王敦无子,大有将不上任。而当时庾亮以帝舅之尊而权遇非凡,使得王氏家族的主心骨王导寝食难安。为家族大局计,王导给王允之写信道:“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2]2002言辞恳切中透露期望之深,将家族重任压在王允之的肩上,希望他能担起家族责任,缓解家族危机。王敦、王导作为琅琊王氏家族的掌舵人,他们同时对王允之另眼相看足以说明王允之其时在王氏家族内部的重要地位。
王允之的本传中有一段记载,似乎很少被人所关注,但我们从中探赜索隐,亦可推测出他在其家族中的重要地位。记载说:“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2]2001
其一,王敦起兵谋逆本应是机密之事,有倾家覆族之险,哪怕至亲骨肉也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可在商量如此大事之前还让王允之陪其一起饮酒,可知王敦没有刻意回避王允之。其后密谋允之既能悉闻其言,表明王敦与钱凤与他同处一屋,并没有另寻他处进行商讨。虽说允之已醉,可王敦并非那种处事轻浮,粗枝大叶之人。据《晋书》卷九八《王敦传》记载:“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2]2553王恺请的客人必定都是当时的权贵,皆是见过世面的云端之人,王恺敺杀女伎使在座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相比之下王敦却依旧神色自若,可见王敦遇事何其的沉着淡定。又本传记载:“敦眉目疏朗,性简脱,有鉴裁。”[2]2566上述史料表明王敦为人十分镇定有度,鉴裁有决,因此不可能会犯商量密谋起兵之大事还让不相干人在场的低级错误。唯一的解释就是王导对允之异常的信任,这份信任恐怕不仅仅是源自王允之是他的侄子,毕竟王敦不只有允之这一个侄子,为何不拉其他子侄一起饮酒,更多的应该是他对王允之的看重。
其二,之后王允之回到建康将事情告知其父王舒,王舒立即和王导一起将此事上奏给晋明帝。②这背后隐藏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掘隐索微,加以分析。王导、王舒都是王氏家族的翘楚也是久浸政治官场之人,不可能仅凭王允之一面之词就草率地俱启明帝,何况王敦还和他们血脉相连,并非外人,按理说谋逆是灭族之罪,势必会牵连自身,他们更应该替其遮掩才对。可历史往往就是这般令人出其不意、吊诡难猜,他们偏偏真的相信了允之的话选择如实上奏明帝,而非隐瞒不报,两个如此聪慧之人为何会有如此不智的举动,此举不得不让人深思。笔者推测,这极有可能是王氏家族几位主要成员为家族大计考虑,联手给晋明帝演的一出戏罢了,王允之恰好也参与了演出,而且充当的角色还是一条贯穿的主线。理由有二,首先是王敦刚刚密谋起兵,王允之就要离开回京定省,这个时机是不是选的有点蹊跷。若毫不知情也就算了,可他当时虽说醉酒但毕竟在场,之前王敦也已有怀疑并且照视,此举定会再次勾起王敦的怀疑,前文已说王敦是鉴裁有决之人,能识人断物,王敦最明智的决定肯定是寻个合适的理由加以阻止,这样可保万无一失,可王敦偏偏答应了!所有的巧合结合在一起,恐怕就不仅仅是巧合,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预谋。其次要知道王敦两次起兵性质不同,如果说第一次起兵是被动的话,第二次起兵就是主动了,且带有暗移晋鼎之心。但起兵之事毕竟有倾家覆族之险,谁也不能预料其结果,所以必须有一个万全之策,于是就有了这出戏。若王敦得胜,他们本就是家族兄弟且事先暗通款曲,王敦自然不会为难他们。若他日王敦兵败,王导、王舒则属于大义灭亲,有首告之功,事后晋明帝不便责难。即使王敦一支失势,他们依旧可保王氏家族门庭不坠,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确实如此,王敦死后王氏家族依然屹立于江左。
“魏晋所杀,子皆仕宦”③[3]2048的政治现象看似矛盾,其背后所隐藏的却是政治平衡的揭橥。王氏家族虽受王敦之乱的影响,却未因此退出政治舞台,可知此次事件对王氏家族的走向至关重要,在如此大事中出现王允之的身影,表明王氏家族的长辈对王允之的看重,足见王允之在王氏家族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二、建武军功崭露头角
王敦和王导阅人无数,他们同时对王允之的另眼相看说明王允之必有过人之处,而王允之后来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他们失望,尤其是在军事上的成就。
据王允之本传载:“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请曰:‘臣子尚少,不乐早官。’帝许随舒之会稽。”[2]2002在王敦之乱平定后,晋帝就想要让王允之出仕,但其父王舒没有同意,理由是允之年级尚小,不愿意他过早做官。细加揣度,这个理由不免有些牵强。其一,在当时门阀政治格局下,士族子弟进入仕途本就轻而易举,门阀世家为家族大计,安排族中子弟早早进入仕途之例并不鲜见。其二,魏晋南北朝之时,男女大概在十三到十七岁就已婚配,其时早婚现象至为普遍。④王允之死于咸康八年(342),年四十,王敦之乱平定是太宁二年(324),此时王允之已经22岁,结婚少则五年,多则九年,已算大龄青年了,何来年纪尚小之说。笔者推测应是王敦之乱初平,政权的钟摆虽已回到原位,但钟声的余响却让晋明帝难以释怀,晋明帝对王氏家族已经心有芥蒂,很难再像以前那般信任有加。虽说王舒父子有功,但毕竟与王敦血脉相连,同属一族,虽此时温和以待,许以官禄,难保不会秋后算账。此时让王允之出仕时间点过于敏感和尴尬,王舒实难安心,还是将其置于身旁比较稳妥。其后王舒让王允之随他一同前去会稽足可表明王舒的心思。
王允之的军事能力真正得以展现是参加平定苏峻之乱,也正是凭借平乱之功开始担任军职,为王氏家族在军事上增添了一份保障。据《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载:“及苏峻反,允之讨贼有功,封番禺县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将军、钱唐令,领司盐都尉。”[2]2002这则史料只讲述了王允之讨贼有功以及平乱后的封赏,并未指出王允之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的具体功劳。但我们结合其他一些史料还是可以还原其大概功勋的。兹引史料如次:
《晋书》卷七六《王舒传》:既而(韩)晃等南走,允之追蹑于长塘湖,复大破之。[2]2001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扬烈将军王允之与吴兴诸军击(张)健,大破之,获男女万余口。[2]2631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峻遣将韩晃、张健等袭姑孰,进逼慈湖,杀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将军司马流。[2]2629
《晋书》卷七《成帝纪》:甲午,苏逸以万余人自延陵湖将入吴兴。乙未,将军王允之及逸战于溧阳,获之。[2]174
按,第一则和第二则史料中知王允之击败了韩晃和张健两人,这两个人可不是什么虾兵蟹卒,无名之辈。由第三则史料知他们皆为苏峻的部将,且苏峻派遣他们两袭击姑孰如此重要之地,两人还率军击杀了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将军司马流,可见两人应是苏峻的心腹大将并且是其主力所在。而王允之竟大破韩晃、张健这两支主力,战果颇丰,这不仅削弱了苏峻的军事实力,也肯定打乱了苏峻原定的计划,无疑加速了苏峻失败的进程,王允之的功劳必然不小。如果说击败韩晃、张健功劳不小,那击败苏逸就应是功勋卓著了。第四则史料中所载的苏逸是苏峻的弟弟,且苏峻死后就是苏逸接替其位的,⑤足见苏逸在叛军当中地位的重要性,王允之能够击败苏逸,这份军功的分量不言而喻,记载中说他平乱后封侯拜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庾氏家族势力的日益凌压和族中子弟严重缺乏军事人才双重困境下,王允之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最欣慰的恐怕要数王导了,这无疑让王导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一个家族的兴盛不衰绝不仅仅单靠一代人就能完成,只有不断注入新的力量才能保证这个家族的活力,王氏家族必须在原有的军事基础上注入像王允之这样新的家族血液,方能与庾氏家族相颉颃。
三、出镇之际缓解危机
东晋初期,王氏家族在江左维持家族不坠策略是军政齐握、里外相合,王导坐镇中枢,王敦领军外镇,他们俩好似一双翅膀共同支撑着王氏家族的发展,使得王氏家族顺风顺水,宗族子弟遍布朝野,其势力当时在江左没有任何家族可以与之比肩。而王敦叛乱的失败打破了王氏家族原定的格局,没有了王敦在上游的强藩威震,下游的王导开始变得步履维艰,一只翅膀很难保持家族势力发展的平衡。其时王氏家族的危机的来源除了晋帝的有意疏远外,更多的应该是来自庾氏家族的日渐兴起,王允之的军事实力成为王导缓解家族危机的一个重要依赖。
史载:“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2]1714咸和四年(229)对王氏和庾氏家族来说都不平凡,可以说是两个家族势力此消彼长的一个关键点。庾亮外镇建康上游的芜湖,使王氏家族的势力发展受到极大压制。庾亮出镇芜湖的政治背景是因其引发苏峻之乱,迫于建康的政治压力而为之,并非情愿外镇,而是无奈之举。不过庾亮在芜湖一镇守就是五年之久,直至咸和九年(334)统领江、荆的陶侃去世,庾亮才移镇武昌,镇守时间之长估计连王导都未曾料到,毕竟庾亮当初是被迫外镇,他定以为庾亮待事件平息就会伺机重回建康的。不过庾亮改镇武昌对王导来说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恰好给了王导在建康上游部署军事防御的机会,王导趁机安排王允之出镇芜湖。当然王导并未被这突如其来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对于允之出镇芜湖他没有急于求成,以免激起与庾亮之间的矛盾,而是采取先占于湖再镇芜湖的策略。据《王允之传》记载:“(允之)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将军,镇于湖。”⑥[2]2002咸和末当指咸和九年(334),王允之入镇于湖恰好和庾亮移镇武昌是同一年。但于湖并不是王导的最终目标,充其量只是为下一步安排王允之镇守芜湖而选择的一个跳板,也是对庾亮的一种政治试探。就在王允之顺利屯驻于湖,王导正苦心寻找合适的理由让王允之入镇芜湖时,北方的石虎帮王导解决了这个心病。因为咸康元年(335),石虎兵寇历阳。《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载:“季龙(石虎)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振。”[2]2763石虎此举对王导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王导恐怕连做梦都要笑醒,如此良机王导要是都不去充分利用真的有点对不住石虎了。王导立马上奏晋成帝请求征讨,“夏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2]179此次军事行动的先机拜石虎所赐,后续却由王导筹划,衔接得异常完美,让王导既达到内政目标又缓解了家族危机。就这样,王导借着石虎南下的契机,打着征讨的旗帜,名正言顺让王允之从于湖移镇芜湖,完成了在建康上游军事防御的部署。
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当世人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并非历史,而是复杂多变、利益纠缠的现实政治,他们所做的每一个抉择都来自谨慎细微的考量。[4]171此语用来形容王导异常贴切,王导在缓解家族危机时,每一个决策都会深思熟虑,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谨慎小心。安排王允之镇守芜湖极大地缓解了庾亮在上游施加给王氏家族的压力,也正因王允之屯驻芜湖,建康的王导才仿佛有了屏障,方能得以安心,不会担心庾亮由武昌朝发夕至,王允之在缓解家族危机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四、结论
王允之处于琅琊王氏家族由兴盛转向守成的特殊时期,其时的王氏家族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在家族处于危机的关键时期,王允之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积极配合族中领袖王导,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能力,领军外镇,试图缓解家族危机,如若没有王允之的维持,其时王氏家族所承受的压力怕是更加严峻。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咸康、建元之际是琅琊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关键时刻,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其后王氏家族虽有显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依赖宗族余荫、社会影响,直至晋末,真能影响政局之人绝无一人。[5]122先生的话极度肯定了王允之对王氏家族所做的贡献。历史好似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出来自各个方向的光源,但我们不能只关注那些比较明显的而忽略掉那些不太显眼的光源,只有还原尽可能多的光源,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丰满的历史。同理相揆,我们不能只看到王敦、王导对王氏家族势力发展起到的作用,而对王允之维持家族势力所做的付出视而不见,这不是我们研究历史所应采取的方法。研究王允之在王氏家族处于危机时的所作所为,对我们了解其时王氏家族的处境、世家大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东晋政局相对平静下的潜流所在都有一定的意义。
注释:
①这一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陈寅恪的《论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卜宪群的《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吴鉒鉒的《豪门政治在南方的移植——王导的“愦愦之政”》,《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王汝涛的《魏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研究》,《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王连儒的《东晋中宗、显宗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余晓栋的《王舒与会稽——兼论王敦之乱对琅琊王氏的政治影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等。
②陈启云,罗骧在《社会名望与权力平衡:解读王敦之乱》一文中认为;“王导、王舒之所以会上奏明帝,是因为王氏家族此时已经分为两派,以王敦为首的激进派和以王导为首的温和派,两派的共同之处是都在维护王氏家族的利益,差异则是行事方式不同。”要知道,王导、王舒的首告会大大增加王敦失败的概率,王敦一死,王氏家族整体的军事实力必定会有所削弱,对王氏家族的利益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以王导的智慧不会想不到这一点,那王导此举似乎就没有做到以家族利益为重。
③《太平御览》卷四四五引王隐《晋书》。
④参读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文中指出魏晋之时自上至下普遍存在的早婚现象,并论述其原因与人口、寿命以及家庭宗法观念有关。薛瑞泽在《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认为两晋时期女子婚龄一般为十六岁以下,男子的婚龄一般为十五岁。
⑤据《晋书》卷一百《苏峻传》记载:“峻司马任让等共立峻弟逸为主。”可知苏逸是苏峻的弟弟,且苏峻死后代替了苏峻的位置。
⑥王导选择于湖作为过渡应是于湖与芜湖都属于丹阳郡,相隔甚近。据《晋书》卷十五《地理下》载:
“(丹杨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五万一千五百,建邺、江宁、丹杨、于湖、芜湖、永世、溧阳、江乘、句容、湖熟、秣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