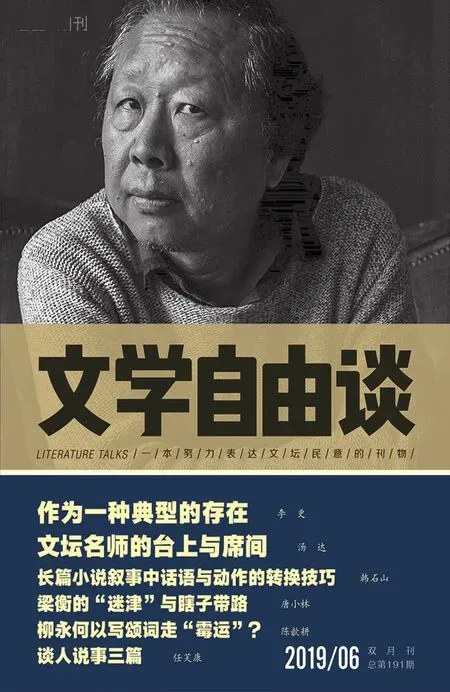欧美文学中的宗教“人设”
2019-12-27刘世芬
□刘世芬
倘若离开宗教谈欧美文学,是否就像人离开了空气?
这种印象,来自欧美名著中那一个个宗教人物。
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呈现给我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形象:阴冷变态的黑衣教士克罗德·弗罗洛和悲悯宽怀的卞福汝主教。同一作家笔下的这两个宗教人物,充满着文学与人性的丰富想象,令人回味无穷。
《巴黎圣母院》中的克罗德·弗罗洛被称为色欲教士。这位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是一个被命运折磨,又可悲又可怜的人物。他由父母做主献身神职,从小过着与众不同的幽居生活。他终日沉溺在书籍和典籍中,十八岁已成为受人尊敬的博学之士。修道院的灭绝人欲,使他的孤独、寂寞无以排遣。随着地位高升,学识增长,他的内心反而更加苦闷。尽管他拼命压抑着内心积郁已久的不安和躁动,命运还是让他遇到了青春洋溢、美丽动人的吉普赛少女爱斯美拉达,他内心的欲望被点燃。克罗德第一次看到爱斯美拉达时,他“那深凹的眼睛里却迸发出非凡的青春火花,炙热的活动,深沉的欲情”。作为教士,竟然爱上一个被世人嘲笑的吉普赛女郎,这简直就是对以前所遵从的神意最大的侮辱。那种无奈和痛苦,真实体现了人性的异化:严厉,苛刻,自私,虚伪,狠毒……这也决定了一开始他对爱斯美拉达的爱的畸形和残缺。这个自命清高、崇尚神学、戴着宗教假面的男人,强抢,跟踪,嫁祸,甚至威胁,用尽了一切可以得到爱斯梅拉达的手段。那狰狞可怕的沉郁面孔,让人不寒而栗。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他渴望得到那个近乎完美的女孩,时而幻想放弃神职的一切,只祈求凡人的男欢女爱。但是,长期以来的宗教教义告诉他:爱情是最可怕的异己力量,是凶神。他害怕自己被凶神附体,可当他发现爱斯美拉达爱着卫兵队长弗比斯时,所有的理性都被摧毁。他歇斯底里地变成杀人犯,最终因为得不到爱斯美拉达的爱,一步步陷入恶魔的泥潭。
克罗德是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也是宗教的刽子手。他身上虽有教士的阴险和虚伪,但也有人性被压抑的悲哀。欧美文学中,不乏这类关于宗教的讽刺与反思。
《悲惨世界》却给人大大意外的“正能量”,这就是卞福汝主教。我所认识的一位神职人员甚至把卞福汝主教崇拜为宗教信仰的“天花板”。
饥寒交迫的冉·阿让从监狱出来,四处碰壁。终于有一个人指给他卞福汝的教堂,那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在这里,他遇到了比太阳还温暖的主教,并听到了这样的话:“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但是要问他是否有痛苦。……您安心待下吧。……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我的兄弟’。”
每一个在暗夜的海上泅渡的人,听到这番话,该是怎样的晕眩战栗!可是雨果多么尊重人性,他没让这个倒霉蛋瞬间被感化为“好人”,他懂得世间还有另一种叫做“惯性”的东西,他让冉·阿让“恩将仇报”——吃了一餐此生从未吃过的好饭,睡了此生从未睡过的好床。当冉·阿让精力恢复,内心思绪万千、凌乱杂沓的时刻,他盯上了马格洛大娘放在桌上的六副银器和大汤勺。尽管他心里反反复复,踌躇不决,最终他还是偷走了那些银器。
早晨醒来,马格洛大娘愤怒地向卞福汝主教报告“失窃”,卞福汝的戏才真正上演。他柔声说:“那些银器难道真是我们的吗?” 伟大的雨果!他把世间惯常的思维扭转了一百八十度,他在用《圣经》思考:世间万物均属上帝。卞福汝主教对马格洛大娘说:“我占用那些银器已经很久了。那是属于穷人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当然是个穷人了。”当三个警察把“窃贼”冉·阿让交到主教面前时,这位主教大人竟当着“小偷”的面,给警察上演了更为神奇的一幕:“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这时,冉·阿让像是个要昏倒的人。他睁圆了眼睛,浑身发抖,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他的面色,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可以表达得出来。主教的仁慈宽厚唤醒了冉·阿让的良知,从而挽救了这个正在滑向罪恶的灵魂。冉·阿让是幸运的,但是主教大人又懂得,爱,绝不是无原则的纵容:“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此前,卞福汝主教一直就是同行眼里的怪物:收留囚犯,把自己宽敞的主教府改成给穷人治疗的医院,将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九十捐给慈善事业,而他自己却生活简朴。与克洛德相反,这“悲惨世界”里惊心动魄的一幕,温暖戳心的一幕,违背常理的一幕,让我们记住了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卞福汝主教。
《悲惨世界》中始终弥漫着一种宗教气息, 雨果宣扬基督教仁慈博爱和宗教感化的巨大力量,简直到了无与伦比的完美地步。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教会对人们精神的奴役, 同时又将宗教视为改造人性与社会的手段,成为一种千灵万验、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这种近乎童话的描写,正是双鱼座雨果天真梦幻的流露,但某些时候却可能成为他的一种局限。到生命的后期,雨果深信“神的存在”,他“至少每隔四小时必定祷告一次”,那是他给自己规定必须要完成的功课。尽管我不太喜欢雨果的絮絮叨叨,但他塑造的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让他永远活下去。
欧美文学脱胎于宗教,极少见某部欧美名著中不涉及宗教。然而,欧美文学浩如烟海,却没见有哪些宗教人物“撞衫”。从人性出发,而不是从“需要”出发,这也是欧美文学中宗教“人设”不曾同质化的原因。
《三个火枪手》具有浓重的宗教背景,全书贯穿着国王路易十三与权倾朝野的黎塞留红衣主教之间的矛盾。这部书的宗教笔墨除放在黎塞留身上外,更大比重是向邪恶女子米拉迪·温特倾斜。米拉迪最初的身份原是修女,她天生丽质,艳若桃李,但又两面三刀,口蜜腹剑,心如蛇蝎。火枪手达达尼昂为其美貌所动,巧构计谋,潜入内室,诱其失身。一次追捕中,四位火枪手终于揭开了米拉迪的老底:由于不甘寂寞,她诱惑了一个小教士与其同居;教士身陷囹圄,她也被刽子手——小教士的胞兄烙下一朵百合花。百合花在基督教中别具意义,即,上帝赐给亚当的第一个妻子莉莉丝的淫邪、忤逆之意。整个故事背景就在修道院中展开,却又充满谋杀、背叛、堕落……大仲马笔下的人物多为奇葩,这部作品更充满了对宗教的嘲讽。
《红与黑》通篇充满了宗教内部的倾轧和争斗。这让我们明白,原来宗教圣地也不是净土,也有阴谋权变,也有奸恶。
于连在到市长家做家庭教师之前,已经跟谢朗神甫学习了三年,但八十多岁的神甫一眼便看出小于连性格深处“郁结着一股热情”,同时看出那不是一个教士“应具备的克制和对尘世利益的完全弃绝”。善良的神甫眼含泪花对弟子说:“您若当了教士,我担心您是否能获救。”于连大为感动,心中不免惭傀;他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爱他,他高兴得哭了。整部书里,从谢朗神甫被“整” 下台,到于连在神学院期间眼睁睁看着各宗教大人物之间的明争暗斗,教士们的“傲慢无理”,神甫之间时常“酸溜溜”,互相打小报告、拆台,等等,几乎天天上演。最为著名的就是神学院的考试,为了扳倒神学院院长彼拉神甫,主考人为于连设计了一个奇怪圈套,尖刻地责备他在“世俗作家身上浪费了时间”,脑子里装了不少“无用的或者罪恶的思想”。这时于连才恍然大悟“中计”,彼拉神甫的职务很快被解除。事实上,彼拉神甫是一个真诚、不搞阴谋、忠于职守的人,最后也难免成为宗教争斗的牺牲品。
最意味深长的,还有《复活》的宗教手法,不但开头和结尾均大段引用三个“福音书”原文,书中的章节段落也无不充满了宗教氛围。其中有对教堂“喜悦、庄严、欢乐和美好的气氛”的描写,对应着玛丝洛娃堕落前的圣洁、美好时段,这时,“一切都很美丽,但最美丽的却是那穿着雪白连衣裙、系着浅蓝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着鲜红蝴蝶结、眼睛闪耀着快乐光芒的卡秋莎”。
但不久,我们又见识了一座“监狱教堂”,“一个富商花了几万卢布重建的,显得色泽鲜艳,金碧辉煌”。而滑稽可笑的是这个监狱教堂的宗教仪式。站满囚犯的教堂里开始还一片肃静,但其中有病犯、妇女、儿童,难免“擤鼻涕声、咳嗽声、婴儿的哭声,偶尔还有铁链的哐啷声”响起。“司祭身穿一件样子古怪而行动不便的锦缎法衣”,“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就哐啷发响”。那些祷词本来就艰涩难懂,“如今既念得快,又唱得快,就越发难懂了”。饥饿的孩子们看见圣餐显得饥不择食。仪式持续了很久,以赞美词开始,以“饶恕我吧”结束。然后又是一套新的赞美词,最后以“哈利路亚”终结。
托翁指出:“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一切,神职长官和俗世长官也都信奉它,而在犯人中间,少数几个人看透了这类玩意儿,心里暗暗好笑,大多数人却笃信,那些包金的圣像、蜡烛、金杯、法衣、十字架、反复叼念的“至亲至爱的耶稣” 和“饶恕吧”等等,都蕴藏着神秘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就可以在今世和来世得到许多满足。
在当时的俄国,贵族家庭大都有私人神甫传教,比如外国人基泽维特就定期在聂赫留朵夫的姨妈家传教。“我们的罪孽这样深重,将要受到的惩罚又这样严厉而且无法逃脱,”他突然容光焕发,声音温柔甜蜜地说,“现在有救了!……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上帝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了他的独生子,他的宝血……”只有聂赫留朵夫感到“十分恶心”,他悄悄站起来,“皱着眉头,忍住羞愧的呻吟,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自己的房间去”。
聂赫留朵夫在营救玛丝洛娃的过程中,接触到向他求救的教民,这就是他四处奔走的教派信徒案。这也是当时沙皇俄国的宗教现实。这一点,在契诃夫的《脖子上的安娜》中也有体现:五十二岁的新郎阿列克谢伊奇与十八岁的安尼娅在教堂举行了婚礼,按风俗还要举行欢乐的婚庆舞会和晚宴,但他取消了这些,而是到二百俄里以外的一个修道院去朝圣。此举为的是让年轻的妻子明白,即使在婚姻问题上,他也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以表现自己对宗教的“忠贞”。
对于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算是比较虔诚的作家。阿辽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代言人,他拥有作者所赋予的一切最美好的品质:诚实、慈爱、善良、宽容、纯真……阿辽沙爱着所有人:人生导师佐西马长老,情绪古怪的丽扎,之前素不相识甚至拿石头砸他的伊柳沙,还爱着蔑视上帝、具有虚无主义倾向的伊万。他是陀氏宗教救世理想的具象化。正是因为有信仰,阿辽沙才能在这残酷的现实世界中,展现着美丽与纯净的东西。陀氏的宗教观念长久以来虽是他作品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但也有对于宗教无上神力的质疑。小农奴被狗咬死的那一段,伊万说:如果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那必定是个邪恶的上帝。他拒绝信奉他。佐西马长老死后的尸臭事件,也否认了宗教中的超自然力量。
赫本主演的电影《修女传》所传达的宗教思想令人迷惑深思。历史上有一个习俗——家中第十个女儿长大后,应被父亲“贡献” 给修道院。赫本饰演的修女嘉比雅就是被父亲送到修道院当护士。她怀着无比纯洁虔诚的信仰,希望父亲以己为荣,然而父亲却说,“不,希望你快乐。”修道院的生活有着严酷的“规矩”,就像一张巨大而严密的网,笼罩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常人看来,不但难以忍受,还相当荒唐。嘉比雅去刚果参加瘟疫救援,眼见长于她的修女被黑人打死。当地习俗是把凶手抓了喂鱼,而天主教的要求是宽恕。她在这里遇到了爱情,在共同的医护事业中,无神论医生福图纳提对她产生了真挚的爱恋,但修女的身份让她止步。直到二战爆发,身为护士的修女们被要求对受伤士兵,无论敌我都要一视同仁。有一个见习修女偷偷为友军帮忙,嘉比雅也参与进去,这是她第一次在行为和心理上与天主教义背道而驰。她一直以来的矛盾、彷徨、撕裂、痛苦,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指向:修女生活并不适合自己!她请求离开修道院。当她换上自己的少女服饰,更加确认,清规戒律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不宜胸怀理想和激情的人。而这,也正是电影《音乐之声》所表达的主旨:修道院长坚决支持玛丽亚脱离修道院,成为上校的妻子。
《包法利夫人》里的爱玛本人就毕业于修道院。检察官委婉地称之为“马车里的沦落”那一段是这样的:车子掉头往回走,既无目标又无方向,只是随意游荡着“经过”一个个教堂。先是驶过圣波尔教堂,随后是圣维维安教堂、圣马克洛教堂、圣尼凯兹教堂……伴随着教堂的一路“堕落”,福楼拜又告诉我们,“在爱玛奔放的热情中,她爱教堂是为了教堂的鲜花,爱音乐是为了浪漫的歌词,爱文学是为了文学热情的刺激,这与宗教信仰格格不入,也使她对修道院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反感”。于是父亲接爱玛离开修道院时,院长发现“她越到后期,越不把修道院放在眼里”。可是当她嫁给古板乏味的包法利医生,过着乡下无趣的生活时,“反倒留恋起修道院来了”。
“为什么这样一位全能至善的上帝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满是痛苦的世界呢?” ——这是毛姆对宗教的直接质疑。他的许多作品的主角干脆就是一个宗教人物,如“卡塔丽娜”、“奥古斯都”、印度圣者马哈希、神学家蒂乐生。他在《面纱》中描写了一座美好仁慈、广施博爱的中国偏远山村梅潭府修道院,却把自己的牧师叔叔说成一点也不可爱的人;早年读过的《荆棘鸟》,作者考琳·麦卡洛硬是从女性视角切入梵蒂冈高层的派别争斗,直接牵涉的就是红衣主教拉尔夫与女主人公麦吉之间的情欲挣扎,那应是我对文学中宗教元素的最早关注。《美国的悲剧》中的克莱德,作为牧师的儿子却要沿街乞讨着传教;《宠物公墓》中的艾丽很少去教堂,但她第一次参加教堂里的葬礼便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沉寂不安……欧美作家们无不依赖着宗教写作,但宗教在他们身上又是如此地矛盾。最为典型的要数格雷厄姆·格林了。格林是个天主教徒,宗教主题是他擅长的创作主题,但是他又强烈反对人们将他描述成天主教作家。
眼下正读着《加缪传》,我也颇为复杂地打量着宗教对于加缪写作的影响,更让我感到,欧美文学中的宗教虽为“底色”,却无固定刻板的“人设”。欧美文学中的这些宗教人物,形形色色,作者对其褒贬不一,写作手法各异。某些时候,宗教在西方差不多就像一种职业,也注定成为作家们思考不休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