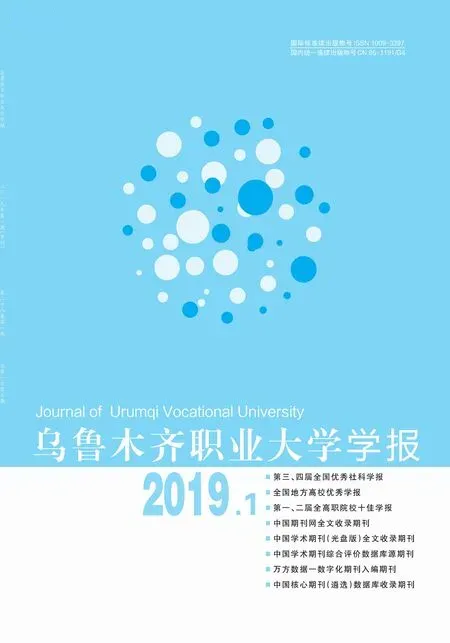情节因果律论证张爱玲小说的核心
——人性
2019-12-27马晓君
马晓君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张爱玲小说自20世纪40年代问世以来一直备受读者欢迎,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张爱玲本人有着独特的艺术思想和写作角度。其作品中独特的譬喻,炫丽丰富的服饰色彩,古朴雕琢的家居刻画都令读者耳目一新。但究其本质,其小说热度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是其情节的特殊性。情节,是小说的精髓。张爱玲的小说情节不落俗套,不为迎合大众口味而虚与委蛇。以时而尖刻犀利、时而优雅哀婉的笔调揭示了一张张露骨的人性图。而其揭示的手段大部分来自于情节。著名学者孙绍振在《文学创作论》一书中用“情节因果律”来探究小说人物的深层情感,用此来论证张爱玲小说的核心——人性也未为不可。
一、情节中的因果性
情节,至少应涉及两种以上相关的感情。故事是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1]情节中的时间关系往往被因果关系所遮蔽,涉及到原因追问的都与情节有关。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就指出:如果一桩桩事情是意外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更能产生这样的(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2]在张爱玲小说《心经》当中,许小寒与许峰仪本是父女关系,故事就按照事件顺序一点点叙述开来,涉及到同学间的玩笑,涉及到家庭的温馨,若一直叙述下去,本是极平凡的一篇小说,但到小寒在为好友绫卿做媒时,意外得知她父亲和好友绫卿一同看电影时,凸显出矛盾。小寒异样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女儿该有的行为,而像一位吃醋了的小女人。再返回看之前的情节,便可发现,作者张爱玲处处都埋有父女畸恋的伏笔。这种意外事件的发生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更易让人产生震惊的效果。这种“意外”直指情节的“突转”,读者的“意外”常常是对“相反方向”的“发现”,亦即对人物心理的新方面的认识。[3]472若小说从相同方向上往下延续,则很难产生对人物心理新方面的认识,从而也达不到令人震惊的效果。小寒对父亲许峰仪已经超越了父女之爱,其畸形的恋情注定不被世俗所容,父亲的移情别恋以及小寒最后想挽回的歇斯底里都是情感的正常表现。但纠其背后的原因,许峰仪的移情别恋无论是偶然的还是故意,亦为不耽误小寒青春年华之举都是人所具有的正常感情和理性。心理学表明:驱使人类行为的所有动机,都源自于欲望。欲望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这种情感的因果性,使小说的结构产生了有机联系,符合形式审美规范的内在统一性。没有原因的结局是不美的,没有结局的原因也是不美的。[3]474由于情感的复杂性,小说中主人公的行为背后可能有多种原因,比如《金锁记》中,曹七巧由温情少女变成心理扭曲的阴狠怪人,不仅由于财欲和情欲的迫使,还在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曹七巧具体的生活环境,情节原因的多元性导致了一个统一的结果,而这结局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其原因也可统一为“人性”二字。
二、情节中因果的不同呈现方式
小说中的情节需要因果的支持,因果靠情节来展现,情节与因果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小说的发展脉络。孙绍振所论述的情节因果律有不同的呈现方式,这些不同的呈现方式即增加了小说的文学性,同时也使小说的情节有效地避免了单一化走向。
(一)情节中情感叠加对小说因果的推动
为了探索人物的情感奥秘,作家不得不把人物推出生活常轨以外,设置一系列的前承条件,使氛围达到饱和度,以期在结尾时产生一种结构质变效果,暴露人物情感深层结构中非常隐秘的奥秘。[3]469在《第一炉香》中,故事的女主角葛薇龙本是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因一个人留在上海读书生活费和学费有困难,又不忍使家人发愁,便求助了与自家早已决裂的住在香港的寡妇姑妈。至此,葛薇龙的生活已经开始走出常态,生计和学业所迫让其寄人篱下,但到此处,小说的氛围还未达到一定的饱和度,人物的深层情感结构还未真正流露出来。葛薇龙还不清楚自己以后将要面临的命运,只是在心里道:“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得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绝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4]13在面对姑妈为她准备的满厨金碧辉煌的衣服时,产生了好奇心,从抱着“看看也好”[4]17的想法到成为姑妈手中招揽青年权贵的棋子,是小说结构上的不断量变。暗恋卢兆麟而不得,见惯了风流场上逢场作戏的把戏,薇龙便想靠嫁人来摆脱自己任人驱使的日子,她选中了乔琪,一个答应给她快乐却给不了她婚姻的人。这让原本想靠嫁人过上流生活的薇龙失望了,面对乔琪的背叛和花心,薇龙彻底对爱情失望了,极度想逃离香港这肮脏的上流社交圈,却在回家的途中经受了风雨而染上风寒,张爱玲在此或暗示过惯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薇龙已成为了温室的花朵,经不住风吹雨打,终究还是要回到温室中去才能继续生活。为了有个依靠,为了继续过上流的生活,薇龙出卖了自己原本纯真的灵魂,与姑妈成为了同类,以色事人,以色赚取钱财。在小说的最后,薇龙回想自己的改变只能无奈地默默流泪。此时,小说结构由量变已经达到了质变,人物情感深层的矛盾显露出来,违背本心地生活与物欲的享受起了冲突,人物的强化情感被推向更深层次的原因——人性,这样,人物的形象就极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张爱玲的很多小说中,情感矛盾的最深层次原因都指向人性,比如《连环套》中为富贵生活攀附权贵的塞姆生太太,《琉璃瓦》中为女儿婚事屡次忧愁的姚先生,以及娶了“白玫瑰”忘记不了“红玫瑰”的佟振宝等。
(二)因果的两极分化
情节中的矛盾造成突转和结果中的意外,引导读者挖掘出小说人物更深层次的情感秘密。有因果反向情节的小说才更加吸引人。要构成情节,必然要有原因和结果在方向上的背离,如果没有因果反向,也就没有情节。[3]476此点在张爱玲小说《色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王佳芝是一名普通大学生,为暗杀汉奸易先生而乔装打扮,隐藏自己身份,却在暗杀过程中,爱上了易先生,从而导致刺杀失败,众人被捕枪毙。在这部小说中,因便是为国刺杀汉奸,果便是为保护汉奸而牺牲了自己。因果反向,尤为鲜明。其中不止一处细节暗示了王佳芝和易先生感情的日渐浓厚,夹杂着怀疑、矛盾和纠结。然而当王佳芝看到易先生花费十一根金条为其买下六克拉的钻戒时,她的心便土崩瓦解了。因为爱情,她放弃了所有的条条框框,这是从小说中可以显而易见一望而知的两极。一旦一个素材乃至一个细节其中包含着原因和结果两极分化的可能时,敏感作家就揪住它不放,把其中的两极挖掘出来,特别是在同一细节同一事件中能检验出不同的结果,追索出不同的原因时,这种题材往往得到作家的钟爱。[3]477《色戒》有显而易见的因果反向,即情节两极分化。此事件中的结果却蕴含着不同的原因,王佳芝对爱情的不顾一切是可以直接观看出来的原因,而易先生的个人性格是隐藏原因。作为汪精卫的特务头目,易先生生性多疑,并且小心谨慎,顾然有对王佳芝的好感但他更在意自己的性命,所以他才会在王佳芝被关进牢狱时不闻不问。不管是易先生的无情还是王佳芝的痴情,都是人性的自然表现。在张爱玲笔下,女性角色大都痴情,从对爱情有所憧憬到对爱情麻木,男性角色大都以玩弄女人感情为主,少有的真情也经不住苦难矛盾的冲击,在人性的抉择中放弃爱情,此种缘由,与作者张爱玲的爱情观有莫大关系。早在其18岁时所作的散文《天才梦》中就有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在张爱玲眼中,人生本是华美的,但总有种种的瑕疵,造成这些瑕疵的原因就是人性中的弱点,像虱子一样令人瘙痒但是摆脱不掉,只能任其发展。故其小说中的因究其本质,便是人性。
(三)实用和理性因果寄托于审美因果
情节在艺术上的深化和原因上的深化是同步的。[3]478作家在叙述情节的时候就是交代原因,在情节发展到高潮时,小说氛围达到饱和,此刻就是探寻深层原因的最好时机。在因果关系中,实用价值因果和科学价值因果都是偏重于理性的,而情感审美的因果与之相反,不以实用性为主而以情感的独特美为高。在理性的压制下,审美情感易表现为潜意识状态。衣食住行等世俗生活是实用价值的主要体现。在张爱玲小说中,这些世俗化的描写比较多,人物的实用功利性更加明显。这点违反审美因果对实用和理性因果的超越。但不可否认的是,若张爱玲小说充斥的全都是实用性因果,则其审美价值会大打折扣,只有审美因果和实用因果统一在一起,其作品才更具有吸引力。在通俗小说《半生缘》当中,一开始审美因果占成分较大,世钧和曼桢的爱情是以纯情开篇的,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面前最终变得面目皆非,其实这里面还蕴含着张爱玲对人性真相的探索。她尖刻地挑剔着人在生存世相后面隐藏着的人性真相,总能够发现种种装饰性表象后面潜藏着的人性— —怯懦,自私,虚伪,冷酷……[5]不难发现,在张爱玲笔下的饮食男女,纵有万般纯情,到最后终会被现实生活逼迫成世俗想要他们成为的样子。在此方面,实用价值超越理性价值,是为其作品的主旨——“人性的刻画”而服务。
三、结 语
张爱玲小说与众不同之处便在于其人物情感层次深厚,且此种情感却非传统小说中一直推崇的审美情感,而是审美情感向实用情感的转化。这与其小说主旨即小说的“因”所揭示的人性有莫大关系。人性的丑陋具有普遍性,易唤起读者情感的共鸣。用女性的笔触刻画人性的丑陋,是张爱玲小说独特的风格,小说中对情节因果律恰到好处地契合更易让读者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