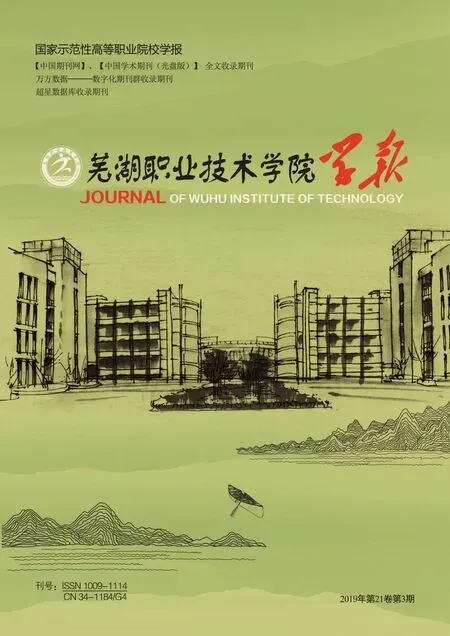个案正义视角下的英国衡平法
2019-12-27陈辰
陈 辰
个案正义视角下的英国衡平法
陈 辰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333)
衡平法是英美法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并非历史的偶然,是个案正义思维同司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宽广的法制背景,是普遍正义思维形式的僵化需要个体正义思维施以补救的必然结果。通过对英国衡平法的产生、发展及具体原则的研究,在个案正义思维下探讨英国衡平法得以纠正法律刚性与不足的法律机制以及衡平法裁量标准的演进,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和认知这一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的发展轨迹与内在价值。
个案正义;普遍正义;普通法;自由裁量;衡平法。
一、引言
司法正义从类别上包括个案正义和普遍正义,前者是指从个别案件具体情形出发,寻求最契合于案情实际的解决途径,通过置身于本案境遇中平衡当事人各方利益,配置各方权利义务,从而取得个案处理最恰如其分的结果;后者则是指对案件处理的选择,不止是从个案中当事人利益权衡出发,而是更多地使个案的处理符合于社会正义标准,以维持社会价值与公共理念的平衡。而中世纪英国衡平法正是以弥补普通法中形式正义取向之不足的面貌出现的,代表“自然正义”的衡平法在运行和演进中始终是以尊重个案正义为价值取向的,因此从分析个案正义的角度入手对于认知和理解英国衡平法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个案正义的抉择
一般而言,作为司法正义的基本取向,个案正义与普遍正义在作用上往往很难划分出明确的界限,普遍正义在多数境遇下都能发挥其典型性作用,使大多数案例中的当事人都能在预知行为结果的模式下实现利益的重新配置,而这种可预知的行为模式是由国家公权力所设定的可遵循的处理方案。而个案正义是以普遍正义为依据的,其适用存在于司法阶段,故在范畴上远低立法层面即已设定的解决情况,审判者在实践中时刻面临着这两种思维选项,如何界定两者关系及如何抉择都关系到司法正义的最终实现。
(一)个案正义的价值内涵
在价值取向上,司法裁量与立法设定都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以实现正义为目标的。司法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具体个案中的正义皆能被妥慎地探索及实践,使得‘个案正义’,得以实现,方为正当。立法公正主要以实现总体公正为目标的,即法的普遍公正。司法审判活动是由无数个案例审判实践架构的,审判者无法设定社会总体的价值目标,因而只能透过个案体现正义的价值[1]。
首先,个案正义是指在案件审判过程中,以遵循法律抽象正义为前提,通过对案件特殊性的分析及案件当事人的特定状况,所作出的最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判决,事实上相当于“利益衡量”或“法益权衡”之要求[2]。该定义由此揭示了个案正义的基本内涵,个案正义只存在于单一的独立个案审理中,而非整个司法审判体系内,这些个案是相对独立且不可重复的。其次个案正义并非与普遍正义完全分离,其实质仍是抽象普遍正义必然的实体化,个案正义以普遍正义为指向,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审判者作出合乎最终目的的价值选择。再次,个案正义的实现是以裁判中当事人利益的最合理分配和效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案正义的取向是在不违背普遍正义的方向的情况下以判决的形式表达对当事人各方最有利的分割方案。因此,普遍正义绝非悬浮于空中的抽象概念,它以不同的程度不断地渗化入它所设定的纠纷模式中,而在此过程中当实际情势的考量比重高于甚至覆盖了制度设计的可靠性时,就需要考量个案正义在裁判中的作用。
(二)个案正义思维的正当性
法之所以能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而法的运行却又不可避免地需要应对一般法规则所无法周延涵盖的个案特殊性,亦即法的安定性与个案正义间的矛盾。传统法学理论立足于法教义学内部的形式化解释和推理,以维护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为价值目标,竭力保持法律适用上的稳定,以规避对设定价值的质疑和对抗。然而这种大前提的预设在遇到小前提相对复杂甚至疑难的情况下就易于产生偏差,使得结论明显背离原有价值设定的本旨,而在审判者发现该偏差后不得不借助引入与法律自身无甚关联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来扶正法的安定性,结果往往使整个推理过程丧失了法律属性,“依法裁量”与“自由裁量”的界限在“超越法律”理念之下愈来愈显模糊[3]。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这一矛盾归结为实在法与正义的矛盾,首先强调了实在法的优先地位,无论其内容合理正义与否,唯有当实在法已成为“非正当法”而致法与正义无法相容时,法律才需要屈服于正义[4]。正如注重甚至拘泥于形式的普通法体系在新情势下的适用将产生偏离价值设定的可能性时,注重个案正义思维的衡平法体系在法与正义的竞合达到一定程度时的出现就具有了必然性。
个案正义作为一种思维,其应用的正当性在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上显现无遗,拉伦茨在讨论个案正义思维的作用时就揭示道:“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对法律进行解释; 如果他发现法律‘有缺漏’,那么还必须予以补充。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也就是他发展法律的过程[5]。”法律天生的拟制性、不确定性、模糊性和不周延性为具体情境下审判者跳脱固有法条窠臼提供了应用途径,他们或选择从立法意志出发将裁量依据寄予原则,或在不同规范发生冲突时作出取舍,这种衡平的个案正义思维某种程度上与“自由裁量”理念相互契合却不等同于“自由裁量”,个案正义的思维在发挥其必要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自在的独立的衡平体系,它的起源以个案正义为主导却又不排除普遍正义思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自有的原则和规则体系。
三、补救正义:衡平法的产生
衡平一词具有以下含义:第一,它的基本含义是公正、公平、公道、正义。第二,指严格遵守法律的一种例外,即在特定情况下,要求机械地遵守某一法律规定反而导致不合理、不公正的结果,因而就必须使用另一种合理、公正的标准[6]。一般的说,法律中往往规定了某些较广泛的原则、有伸缩性的标准或通过法律解释和授予适用法律的人以某种自由裁量权等手段来消除个别法律规定和衡平之间的矛盾。
(一)普通法的不足
征服者威廉的诺曼底征服对于整个英国法产生了决定性作用,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历经亨利一世、亨利二世的司法,逐渐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普通法体系。对普通法来说,最大的困境不是经济发展得有多快,而是自身调节的能力有多弱。
发展到14世纪,普通法自身的缺陷逐渐暴露并开始阻碍其发展,这些缺陷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程序上严重的形式主义使普通法保护范围受到限制也使普通法院审理案件变得迟缓和繁琐。普通法的保护范围是由令状来确定的,没有合乎要求的令状,被害人遭受再大的损害也得不到救济。并且由于普通法体系中保留了日耳曼习惯法重视仪式之法律效力而欠缺对现实情况的考量,导致整个普通法审判效率低下,当事人常会因为某些无关紧要的程序性错误而丧失了寻求救济的资格[7]。其次普通法在经济关系发展的背景下因其陈旧简单的内容而无法适应,尤其是在简单契约、抵押和受益制方面。最后,普通法的救济方式过于单一,审判中无论何种类别的损失当事人仅能以损害赔偿金的形式获得救济,而恢复原状、继续履行等诉求则一概被拒之门外[8],这一制度上的不足极为明显地凸显了缺乏个案正义思维的弊端,也成为衡平法出现的最大原因。
(二)衡平法的兴起
衡平法的兴起有两大背景,即教皇革命与普通法的僵化。1075年格里高利教皇革命引发了教权与王权的对立,罗马教廷希图通过向法律中注入伦理道德来将教皇权威置于国王权威之上,造就了教会法院与世俗法院的分野,是衡平法兴起的历史前提,而普通法的成熟及其弊端的日益显现则是衡平法兴起的法律前提[9]。
如前所述,普通法固守形式主义的特质导致其缺乏对个案的灵活考量,由于普通法的僵化,引起当事人将寻求正义的对象转向国王裁判,从而加剧王权对司法干预,而大法官则代表“国王的良心”依据自己的“良心”来弥补和矫正普通法的缺陷及不公,并对于他认为正义的一方提供救济[10]。在14世纪,当衡平法产生时,作为议会首脑的大法官不必遵循固定和正式的程序来解除案件,而且他们是武断的。随着大法院衡平管辖权的确立,大法院衡平程序逐渐形成于15世纪。一方面借鉴普通法、教会法和罗马法,另一方面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改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到20世纪,法院的衡平诉讼程序已基本定型。大致可分为诉辩程序、中间程序、证据制度、仲裁、听证与判决、审查与上诉等几个阶段,司法法庭是良心法庭。没有机械繁琐的诉讼程序,没有令状制度,没有陪审团。被告将被要求履行所有应根据良心履行的事情。法官可以在没有法律意义的情况下寻求理性和正义的标准。大法官将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融为一体,在根据良心的要求分析具体案件时,没有明确区分法律和事实。他的目的是找出案件的真相并提供相应的救济。在不断博弈和发展的过程中,法官逐渐确立了特殊管辖权。在衡平法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同时,法官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法院体系,即法院。原来的法院没有独立的管辖权,但作为国王的秘书机构存在。从那时起,正是因为法院承担了签发普通法原始令状的责任,它才获得了对某些事项的普通法管辖权。最后,基于法官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对不受普通法保护的案件提供公平救济的实践,法官的法院发展了公平管辖。衡平法管辖权的确立是双重衡平法形成和兴起的根本标志,因为它赋予了特殊的救济程序和司法良知的普通法或法律属性。特别救济程序是一种程序法,或是一种人的成文法、积极法和人民大法。法官的良知是一种实体法,或是一种自然法、应然法和神意法。二者的结合构成了衡平法,也是一种二元衡平法。
四、衡平法中的思维路径
(一)普通法的思维窠臼
庞德认为,以普通法为代表的严格法具有五项重要特征,即形式主义;刚性和不变性;极端的个人主义,即极端强调每一个人都应当照顾自己;拒绝考虑各种情形或各种交易的道德因素权利和义务仅限于具有法律人格的人[11]。严格法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普通法依然包含着正义的价值追求,但却出于法的确定性而缺乏道德观念。
(二)衡平原则与个案正义
衡平法判例思维包含在其丰富而独特的原则之中,这些原则通常以法律谚语的形式出现,在弥补普通法的僵化,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项原则是意图与形式相平衡的原则,其目的是实现实质性的公平正义;第二,鉴于普通法救济的局限性,衡平法不允许无救济的违法行为。法官以“良心”的名义,对违反“正义”和“正义”但不受普通法院保护的纠纷给予公正的司法救助。冀。这一原则为公平正义的整体概念奠定了基础,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当事人权益的司法保护。与普通法在诉讼形式上的僵化和拖延相比,衡平法更注重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是帮助懒惰人行使权利。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或者采取其他救济手段的,法院应当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它不会被接受,因为它是为了保护应有的“公平”和“正义”。
衡平法的诞生带来了大量新的救济方式,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救济权利,产生了新的救济程序,因为衡平法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弥补了衡平法日益僵化的普通法不能为当事人提供完善的司法救济,就其适用范围而言。物权,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用于普通法实体。针对权利保护的不足,制定了用益物权和抵押权规则,针对普通法救济规则的刚性和救济机制的缺陷,解决了普通法无法解决的新的权益纠纷。衡平法救济的确立,从外部对普通法施加了压力,加速了司法救济的自我创新。衡平法的出现打破了普通法在司法救济中的垄断地位,客观上形成了衡平法与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共存与竞争。为了应对衡平法的扩张,僵化的普通法必须进行自我改革,以避免被消灭的命运。
五、从良心到衡平:个案正义的标准演变
英国衡平法的产生并非历史的偶然,也不像某些法学家所说,是“自然正义”通过英王的良心所得到的感知和体现,更不是大法官随心所欲的创造,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宽广的法制背景。
早期衡平法作为一种多元因素共同造成司法模式,被赋予了极为浓厚的神学色彩,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其裁判标准的演变。中世纪的衡平法在处理个别案件中所秉持的“良心”标准,实际上是由良知和心知两部分组成的。良心是对一个特定行为的一个判断行为,该特定行为源自人类对自然法主要原则的先天认知。当个体违背了他们的良心的时候,那么就违反了神法[12]。良心被视为是对个人道德约束,这使良心与个案当事人所追求的公正建立起了联系,但这种着眼于个人境遇的评判标准深受神学乃至客观道德标准的影响,使得法律审判被蒙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判断人们行为是否合乎神意的标准被用来裁量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因此,大法官法院的大法官们扮演着与神甫们非常类似的角色,大法官在法庭上对于良心的探求与神甫在忏悔室中对良心的探求非常相似,他们所关心的同样是被告“精神上的健康”、“灵魂之善”[13]。
有神职人员担任的大法官建立和巩固了大法官法院的衡平裁量权,但随着宗教与世俗权力的日渐分离,客观性的神学标准也逐渐被法官个人的知识水平和个人道德感,个案正义的观念才逐步在审判实践中显现出来,纯粹的宗教理念逐渐转向了更为宽泛的伦理观念。正是基于伦理上的良心,大法官法院始终在个案中关注对穷人的救济,他们在审判过程中并未刻板地遵循条文,而是综合考虑了不同当事人的状况和案件性质。
进入16世纪末叶,良心标准开始走向完全世俗化,并最终转化成了衡平法特有的衡平标准。与良心原则相比,衡平原则更为关注人定法的一般原则与特定情况之间的矛盾,而非关心被告灵魂的救赎,因此,衡平原则对良心原则的取代过程实质上宣告了大法官法院衡平管辖权的世俗化过程。衡平原则在实际操作中,赋予了法官更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更能独立自主地置身于案件事实当中,在一般法律原则与案件事实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拘泥于法律原则,灵活适用程序和诉讼形式,从而保障案件当事人取得最大的利益。
[1]邓江英,潘建明. 创造性思维品质与个案正义的实现[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8):167-168.
[2]范文清. 试论个案正义原则[A]. 城仲模主编. 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C]. 台北:三民书局, 1997:397.
[3]孙海波. 在“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之间——论法教义学视野下的价值判断[J]. 法学论坛, 2014(1):71-73.
[4]韩振文. 法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探究——基于法安定性与个案正义冲突的反思[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4(8):59.
[5][德]卡尔·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上)[M]. 王晓晔,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4).
[6]何勤华,主编. 外国法制史[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50-151.
[7]高桐. 论英国衡平法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J]. 比较法研究, 1987(2):46-52.
[8]高桐. 论英国衡平法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J]. 比较法研究, 1987(2):46-52.
[9][美]哈罗德·白尔曼.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一卷)[M]. 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中文修订版):398-399.
[10]何勤华,主编. 外国法制史[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49-150.
[11][美]罗斯科·庞德. 法理学(第一卷)[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400-402.
[12]耿宁,孙和平. 欧洲哲学中的良心观念[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1997(4):23-29.
[13]冷霞. 英国早期衡平法研究—以大法官法院为中心[D].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2008:265.
British Equity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se Justice
CHEN Chen
Equity la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mon law system. Historically, it is not an accidental product but the combination of thinking on case justice and judicial practice. It has come into being under a profou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a broad legal context, as an inevitable need for individual justice thinking to remedy the rigidity of universal justice thinking.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legal mechanism of correcting legal rigidity and deficiency an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riterion for equitable discretion under the thinking of case justic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specific principles of British Equity law,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the development track and intrinsic values of this unique legal system.
case justice; universal justice; common law; discretion; equity.
DF11
A
1009-1114(2019)03-0019-04
2019-06-10
陈辰(1994—),安徽定远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
文稿责编 孟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