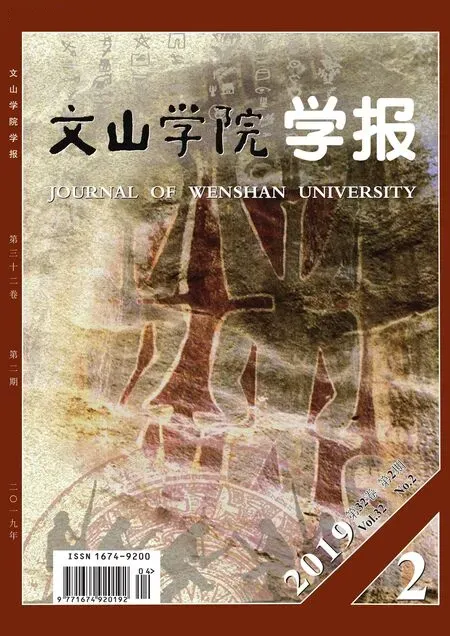杜牧咏史怀古诗对前代作品的超越
2019-12-26杨世全徐旭平
杨世全,徐旭平
(1.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2.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 楚图南文化研究中心,云南 文山 663099)
一、杜牧咏史怀古诗立意对前代作品的超越
杜牧,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晚唐时期著名诗人。杜牧诗作现存500余首,其中咏史怀古诗60余首,在数量上只占其创作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正是为数不多的咏史怀古诗奠定了杜牧“咏史怀古诗圣手”的地位。较之于前代的咏史怀古诗,杜牧这60余首咏史怀古诗在诗歌立意上多有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其写作意识从重道德评价转向重哲理思辨、将历史“已然”化为历史“应然”、放大历史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这些写作的立意角度多为前代作品所较少涉及的,杜牧以敏锐的洞察力抓住它们,并以雄健的笔力赋予其内容因而创作出一篇篇咏史佳作。
(一)由重历史中关键人物的道德评价转向重哲理思辨
在咏史怀古诗的写作中,诗人一般借助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来达到感慨兴衰、寄托哀思或借古讽今等目的,因此其诗作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价,历史中关键人物的生平一般只体现为善或恶、褒扬或者贬低等道德情感色彩,这种较为笼统式的评价往往会忽略了诗作中更具有意味和审美色彩的部分。而杜牧诗歌则将其表现的对象重新放置于历史当中,综合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人物的背景以及社会风气等因素去分析人物,推测人物可能的心理动态和行为。因此杜牧咏史抒怀诗表现出的内容既合情理,又闪烁着独特的思辨色彩,因而更加动人。试对比分析王维和杜牧的同题材作品《息夫人》[1]:
莫以今时宠,难忘旧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王维笔下的息夫人是一个不忘旧爱、不慕荣华富贵的女性形象,虽弱小但忠贞。这些描述既符合史书的记载,也迎合了人们对息夫人形象的期待,仅从立意的角度来看,王维诗作更多的是对历史形象的演绎,其诗作突出表现的是对淫恶者的憎恶和对弱小者的怜悯,仍属道德评价的范畴。而在杜牧诗中,诗人的着力点已不再囿于体现息夫人的忠贞弱小的形象。试看杜牧诗作《题桃花夫人庙》[2]78: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题桃花夫人庙》一诗中前两句虽然也表达了对楚王荒淫的讥讽和对息夫人的怜悯之情,但“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一句将话锋一转,引出另一个与息夫人遭遇相似的女子绿珠作对比,绿珠在面对同样荒淫的赵王时却以死抗争。同样面对权贵,绿珠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当然作者无意去苛责受害者,只是向我们传递出这样一种意味:软弱的受害者固然可悯,但以死抗争者更令人敬佩。这便把全诗的思想境界从传统的道德评价转向了哲理思辨,引发读者对历史人物评价维度的重新思考和认识,使全诗更具思想高度,更值得人们细细思索和品味,从而不落俗套。
杜牧重哲理思辨而轻道德评价的的立意倾向还体现在其他咏史怀古诗中,如面对“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一历史典故,传统的眼光总是从孝顺和英勇无畏等道德色彩出发,突出木兰作为英雄人物光彩照人的一面,很少涉及其他角度的思考。如南北朝民歌《木兰诗》,诗歌的描写从木兰决定替父从军直至木兰衣锦还乡,塑造的都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形象,而木兰作为正常年轻女性应有的情绪则很少提及。而在杜牧诗中,诗人更多是从一个正常女性的角度展开思考。试看《题木兰庙》[2]75:
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
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
诗的首句把木兰征战沙场的英雄形象一笔带过,转而将视角转向木兰作为女性柔弱的一面:在木兰的梦乡中,也应该会有和女伴们对镜梳妆的场景吧。木兰替父从军征战沙场的刚强,以及木兰梦中对镜梳妆的柔弱,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形象的的确确共存于木兰这名年轻女性身上,这组形象的并置并不让人觉得冲突,反而展现出一个真实动人的木兰形象。诗文的最后两句“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既有从传统角度出发的“木兰思乡”的设想,又有具思辨色彩的历史纵向对照,这两种写作意识交相辉映,将杜牧的咏史怀古诗的立意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由历史“已然”走向历史“应然”
在咏史怀古诗的发展历程中,从汉代班固《咏史》开创的“隐括本传,不加藻饰”的咏史模式,发展到左思咏史诗“多摅胸臆”的新型咏史诗,在既定事实的基础上抒发自己的见解和感慨的咏史模式已基本定型,这些诗作呈现的都是已成定局的史实,属于历史“已然”范畴。而在杜牧诗中,历史事实已经不再是表现的重点,仅仅是一个引子,杜牧执历史一端而充分发挥渲染,其呈现出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试看《题乌江亭》[2]91一诗: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乌江亭是西楚霸王项羽败退时自刎之地,本身便具有着悲壮色彩,再加上《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3]更是增添了楚霸王的英雄气节。因此一提及乌江亭,人们无一不为穷途末路的西楚霸王而扼腕叹息。而杜牧在面对这一历史定局时却能发出新论:“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项羽在四面楚歌时拔剑自刎固然体现了可贵的英雄气节,然而江东子弟人才济济,若项羽能忍辱负重卷土重来,历史的走向又将呈现另一番可能。当然,“卷土重来”只能是诗人美好的假设,属于历史的理想状态。但杜牧强调的这种历史“应然”状态,既是历史的合理假设,又强调了兵家须有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而使其诗作不落俗套,令人读来耳目一新。
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和必然往往相伴而行,历史学讲究科学性,记载历史往往重在把握历史的必然因素,呈现出的是历史平稳可知的一面。而历史偶然因其具有的混沌性和不可知性,往往能强化诗作的文学色彩,也因此更为文学家所青睐。杜牧在化历史“已然”为历史“应然”的过程中,历史的偶然性常常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它成为连接诗人主观情感和历史事实的重要存在。如在《赤壁》[2]59一诗中,前两句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当中,而诗的后两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才是全诗最值得重视的地方。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操的史实历来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东风借力”更是被传为佳话,但很少有人设想过排除东风这一偶然因素后历史会是怎样的走向,而《赤壁》后两句诗便大胆假设出这一结局:若没有东风的助力,吴国恐怕连“二乔”也难以保住。“咏史怀古诗既然是以历史为表现对象,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诗人的创作应符合历史真实,但咏史怀古诗毕竟是文学,其本质上仍是个人对历史充满主观情感的想象和解读。”[4]杜牧通过“东风”这一偶然因素的运用,既体现出历史的真实性,也为诗人主观情感和历史的融合提供了契机,从而使诗作符合历史又不落俗套。杜牧诗歌善于选取新颖的立意角度,化历史“已然”为历史“应然”,既使诗歌展现出浓厚的文学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咏史怀古诗的表现范围。
二、杜牧咏史怀古诗在表现手法上对前代作品的超越
在咏史怀古诗的发展历程中,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发展变化较少的部分,鲜有诗人能从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等方面作出创新。而杜牧咏史怀古诗在继承的基础上,从咏史怀古诗的表现手法上作出了突破,这些突破集中表现于逆向思维把握历史、善于构建历史画面、卒章显志以小见大等表现手法上。杜牧对诗歌表现手法的尝试,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咏史怀古诗频于用典、晦涩深奥等弊端,也进一步丰富了咏史怀古诗的表现手法,因此分析杜牧咏史诗的表现手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探究杜牧咏史诗对前代作品的超越之处。
(一)从逆向思维把握历史
咏史怀古诗的写作基于诗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题材的把握,然而写作咏史怀古诗的诗人数目庞大,可供写作的题材又相对有限,一个题材内涵再丰富,书写千遍之后也会流于平庸。而杜牧的咏史诗从逆向思维出发把握历史,跳出儒家正统与千百年来留存下的思想传统,常推翻前人对历史事件的盖棺定论,这使他的咏史诗别具一格,让人眼前一亮。
例如同是面对商山四皓这一历史人物的咏史诗写作,唐代诗人李白的《商山四皓》[5]表现了四老德高望重、辅佐圣明最后功成而隐居山林的历史内容,其诗歌的主体思想是儒家明君贤臣伦理纲常的传统思想。但杜牧却无意因袭前人的创作道路,而是将议论的重点转向商山四皓该不该保太子。[5]试看杜牧咏史怀古诗《题商山四皓庙》[2]81: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诗的前两句概述了吕后强横但太子柔弱这一史实,表明太子无力做出防止吕后专权的事情,而后两句则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议论:如果南军当初不支持周勃诛灭吕氏一族,那么四老当初所谓的安定汉朝保住太子实际上是等于灭了刘氏一族。在儒学仍占主体地位的唐朝晚期,杜牧能一反前人对商山四皓辅佐圣明一事的褒扬,就事论事地提出了合理的质疑,不仅起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具有着深刻的警醒意义。
(二)善于截取历史的深镜头
中国传统艺术自古就有“诗画同源”之说,在诗歌之一文学体裁中,营造出优美动人的艺术画面一直是诗人的追求之一。杜牧也是善于营造诗歌画面的诗人,但不同于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浑融的艺术风格,杜牧咏史怀古诗往往注重截取历史中发人深省、具有哲思的事件,构筑出一幅时空交铸的宏大历史画卷,通过画面本身或末句的一两句议论,达到咏史抒怀或借古讽今的目的。如杜牧诗作《江南春》,这首诗的前两句描绘了一幅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树红花,红旗飘动的春天景色,仿佛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丰富多彩南国大地。诗的后两句诗人的视角转换到南朝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寺庙上,本身就具有深邃色彩的寺庙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更给人一种飘摇迷离的美感。杜牧通过历史镜头的截取,不仅描绘一幅幅绚丽动人的图画,呈现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更表达一缕缕含蓄深蕴的历史情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启迪。
再如杜牧的另一咏史诗《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杜牧写作这首咏史诗的目的是批判和鞭挞玄宗与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但诗作没有选取重大的历史政治场面,反而将表现的重点置于“贵妃嗜荔枝”上,诗的前两句呈现了一幅深远而广阔的骊山图景:树木葱郁,花草繁茂,宫殿和阁楼错落其间,仿佛团团锦绣。在如此美不胜收的骊山景色之下,送荔枝的使者携荔枝绝尘而来,平日里紧紧关闭的宫门也一道道缓缓打开……在这首诗中,诗人以旁观者的身份退居幕后,全诗无一句议论,而讽刺的意味就在一幕幕镜头的转换中传递出来。杜牧善于把握典型的历史事件,并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将其转化为一幅幅历史画面,从而既含蓄又深刻的传达出历史事件的深广寓意,可谓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
(三)少用典故,寓情于景
在咏史怀古诗的写作中,“用典”是最常见的表现手法之一,适当的运用典故往往能收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但是过多的用典往往会使诗歌晦涩难懂,如阮籍的咏史诗。杜牧熟读诗书,熟知历史人物、事件和典故,但在其咏史怀古诗中却很少用典,即使用典也会选取人们所熟悉的典故。如其诗作《登乐游原》[2]59: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此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质朴畅达,平白如话,寥寥数语既勾勒出一幅萧瑟破败的乐游原图,“万古”“长空”浇铸出的广阔时空,都成了承载沧海桑田历史变迁的背景,诗人对历史的慨叹与萧瑟的乐游原图浑然一体。
在杜牧咏史怀古诗中,《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一诗则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佳作。此诗是杜牧游开元寺,登水阁时的所见所闻及触景所发而作的,六朝昔日的繁华已成过往,唯有一片草色连天江水悠悠之景,这一古今联想之间诗人对岁月流逝、世事易变的深沉感慨便倾泻而出。“全诗不用生僻拗口之字,仅仅选取鸟、云、草、楼等常见的诗歌意象,却勾勒出清新淡雅的诗歌画面,传递出深沉的感慨和诗人高雅的情怀。”[7]虽涉及六朝,提到范蠡,却丝毫不影响读者的理解。杜牧在《答庄充书》中曾提及自己的文学主张:“凡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2]195在杜牧看来,一篇好的诗文应先重意,后重气,然后才是文辞章句,杜牧咏史怀古诗中少用典故、寓情于景等特色在诗歌通俗化、意境的营造上作出了探索,较之于前朝用典频频晦涩难懂的咏史怀古诗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
(四)卒章显志,以小见大
北宋苏轼也曾明确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精炼的用语一直为诗歌理论所追求,这一文学主张在杜牧的咏史怀古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杜牧的咏史怀古诗往往能以质朴精炼的语言特色,结合卒章显志、以小见大等表现手法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如杜牧咏史诗作《过华清宫绝句》(其一),此诗的写作意图在于讽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但通诗未发一句议论,而仅仅通过“妃子笑”和“荔枝来”的对比达到讽喻的目的。据《唐国史补》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而荔枝这种鲜果极难保存,在唐代的交通条件下要从涪州运往长安,其耗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而太宗作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博贵妃一笑。杜牧仅仅在诗末轻描淡写的点出“荔枝”,便将太宗的荒唐和对统治者荒淫的批判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可谓章卒而志显,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
在杜牧的咏史怀古诗中,以小见大也是其常用的表现手法,它与杜牧卒章显志的表现手法水乳交融,共同铸就出杜牧诗歌言简义丰的艺术特色。试看其诗作《泊秦淮》[2]46: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杜牧在写作这首诗时唐王朝社会危机四伏,前景可悲之际,带着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杜牧写下了这首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诗作。诗的前两句仅点明了写作的时间和地点,而后两句却从歌女所唱的曲子为切入点,深刻的表现出其锋芒所指:卖唱的歌女不懂什么叫亡国之恨,隔着江水还高唱着《玉树后庭花》。《玉树后庭花》为南朝后主陈叔宝所做之曲,历来被视作亡国之音,诗人表面上似乎是批判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歌女,但事实上商女唱什么曲目完全是由听者的爱好决定的,可见诗人真正批判的对象是那座中的欣赏者——封建贵族、豪绅和官僚。杜牧仅从“商女唱曲”这件小事入手,却表现出辛辣的讽刺,深沉的悲痛,以及无限的感慨,这种以小见大的艺术洞察力和表现力,正是杜牧诗歌艺术表现力炉火纯青的体现。
三、结语
杜牧的咏史怀古诗以强烈思辨的意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探索,拓宽了咏史怀古诗的立意角度及表现手法,在继承前代咏史怀古诗创作基础的同时又做出超越,因而成为晚唐写作咏史怀古诗的集大成者。在咏史怀古诗杜的发展历程中,杜牧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应被低估的。